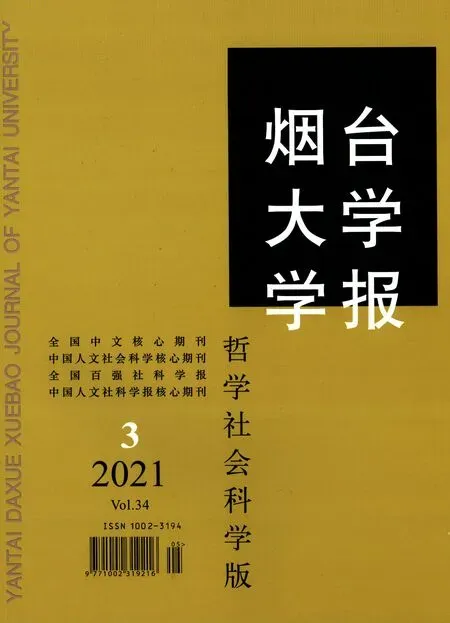中国修辞学的现代转型
——从《文心雕龙》到《修辞学发凡》
丁金国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绝非一日之功骤然出现,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精耕细耘,始成蔚为壮观的语苑辞林。中国修辞学的创立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由零散到系统、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其中《文心雕龙》(刘勰,501-502)和《修辞学发凡》(陈望道,1932)(1)这里标举的《修辞学发凡》是个代表,因为研读可以发现,陈望道先生三部著作《作文法讲义》(1922)、《美学概论》(1921)和《修辞学发凡》(1932)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都与《文心雕龙》有关联,其中尤以《修辞学发凡》总其成,故而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代表。是最为显著的两大高峰,两著虽相距一千四百多年,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其间虽也间出值得投注青眼的伟文华章,然都无法与两书相较,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古有《文心雕龙》,今有《修辞学发凡》”。前者是华夏从无到有语文精粹的积淀,以其体系完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创见颇多为人们所赞许和推崇。沈约赞其“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胡应麟称“议论精凿”(《诗薮·内篇》),章学诚褒为“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后者则是从古到今的转型,刘大白说《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是经过十余年的勤求探讨,几经修改,终成以“语言为本位”,是以古今范例为征引的津梁;张志公认为,在中国的学术史上,《修辞学发凡》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张弓赞其“见解精确,系统清楚”;胡裕树称《修辞学发凡》的最大功绩是建立了我国修辞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我们认为,《文心雕龙》与《修辞学发凡》是学术史上语篇学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两个里程碑式的标石。前者是古典修辞学的巅峰,后者是现代修辞学的范例。二者之间诚然存在着可圈可点的诸多著述,然都难以与之比肩,或偏于一隅,或杂而不精。尤难能可贵的是《修辞学发凡》与《文心雕龙》的嗣承关系,为传承经典、沟通古今树立了典范。
一、《文心雕龙》的性质及作用
(一)《文心雕龙》的性质
作为《文心雕龙》序言性质的《序志》篇,开篇就对书名进行题解:“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2)刘勰撰,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因《文心雕龙》后世版本众多,统一起见,后文引用《文心雕龙》均出自周振甫注释本。“用心”到何种程度,要像雕刻家雕塑艺术品那样专心致志、精雕细刻,既讲究文意,又注重文采。可见《文心雕龙》在于阐明言语活动中对制篇成章的原则、方法及不同言语事件的不同体式。尽管刘勰的“文”指书面文章,但在其全书的论述中,随处都可见口语的踪迹,这一主旨贯穿于全书,充分体现了《文心雕龙》的语言性。
至于《文心雕龙》是部什么性质的书?学界普遍认为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笔者认为它并非是纯然的一部文学批评或美学著作。全书五十篇,有五分之二的篇什是研究言语类型,除《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二十篇外,《辨骚》亦应属语类研究,共二十有一。就其影响而言,屈骚是过渡中的一种新的言语类型,在古代语文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此看来,二十一篇中纯粹“文学”的只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四篇,其余篇目《诸子》《史传》《论说》的非文学性自不待言。其他像有韵文《赞颂》《祝盟》篇和无韵文《诏策》《檄移》篇等,均属应用文。各篇的行文顺序大致是:概念诠释、渊源流变、特征、基本功能、运行语境、代表作及作者等,有的还对风格特征作了阐述。从学术体系上看,与其说是文艺理论或修辞理论,莫不如说是言语活动中的语篇制作理论,是集语篇理论、文艺理论和修辞理论为一体、博大精深的巨著。多学科混杂、相互依存,远不为怪。因为彼时正是人文思潮觉醒的时代,经学与其他学科开始分离,文、史、哲肇始自立门户,然而在“文”里,却是理论、方法、审美形态混杂在一起,正等待着学术体系的裂变。在彼时的学术生态中,出现语篇、美学和修辞等混杂现象实属自然,甚至直至今日,依然如此。如修辞学,离开语篇制作过程的研究,到哪里去找修辞?《修辞学发凡》的“消极、积极”论,足以证明学术生态的实际状况。
在魏晋时期的文库中,《文心雕龙》区别于其他经史子集的显著特点有二:一是“史、论、评”为一体。除有专篇来述史外,每篇都含有述史的过程。理论阐发与述史并行,是《文心雕龙》的一大特征。在述史的同时,融涵着作者对所论对象的评议。《文心雕龙》五十篇点评了百多位作家作品,可谓融史、论、评为一炉的大观。如《辨骚》篇立论伊始,就以史证之、解之,论者的评议间贯其中。《辨骚》篇开端就言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对屈骚的评价是“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称赞屈骚是“惊才风逸,壮彩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全篇都在评论,对屈骚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评述,且对前贤时哲的观点,作了中肯的评点,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屈骚的重要参考。
一是在方法论方面,刘氏首创了“以学带术”的原则。“术”是方法,“学”是理论,以学统术,术中有学,学中有术。如《征圣》篇中谈到制文说语的方法论原则时,提出“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情;明理以立体,隐义以藏用”。四个标准,两两对应,博与简相对,明与隐相应。“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繁简隐显都应视具体环境而为之。《总术》虽篇目为“术”,然其所论则也重在“学”,并非在论述言谈驭文之术,而是在阐释言谈驭文之理。《总术》篇:“赞曰:文场笔端,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体定下来后,即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可见《文心雕龙》并未将学与术严格分开,如果硬要分,只能是“以学带术”。以学带术演化至今日,已成为多个学科的治学之圭臬。鲁迅先生就曾赞过:“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模式。”(3)鲁迅:《〈诗论〉题记》,《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其之所以能成“为世模式”,是因为其“包举洪纤”,具有严整的学术体系。
关于《文心雕龙》的体系,刘勰在《序志》篇里作了概要交代:一,“文之枢纽”;二,“论文叙笔”;三,“剖情析采”;四,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五,“长怀序志”。今人周振甫的归纳是:总论(第1-5)、文体论(第6-25)、创作论(第26-44)、文学史(第45)、作家论(第47)、鉴赏论(第48)、作家品德论(第49)。刘勰对语篇的体类,确实情有独钟,文中曾多次强调“位体”,“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熔裁》篇);“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知音》篇)。“位体”即语篇制作伊始,就应将“体”设置好,也就是“语体为先”。刘勰之所以对“体”如此看重,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体类,刘氏认为均源自经书。作为典谟的经书系圣人所作,圣人依据“道”而垂文。既然“沿圣以垂文”,那么,要明道只能“因文而明道”。著文的宗旨既然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体乎经”就是要按经的体类行文说语,故而《文心雕龙》用五分之二的篇幅来论述各个体类。体类清楚了,就可以依照“六观”,逐次自然有序地构组起一个以宗经明道的语篇论学术体系。由此可见,《文心雕龙》集前贤研究之精华,为汉语语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之所以能成为开山奠基作,就在于它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且既符合彼时的语文事实,又可跨越时空,为华夏一千多年来的语文实践活动服务。《文心雕龙》实际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语篇学论纲”。
(二)《文心雕龙》的奠基作用
所谓“奠基作用”是指某一学说或理论,对某类社会或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具有超时空的解释力和指导功能,为该理论或学说的发展,确立了牢固的基础。“基”者,是一个学科或理论学说赖以生存的根基。根基,是由决定一个学科存亡的决定性要素构成。在通常情况下,决定性要素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对于语篇学来讲,其决定性要素的提取,我们认为,至少应投注如下三个视域:情境、表达者、接受者。从三个视域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社会性、历时性和融通性的特征。社会性不难理解,即从视域所提出的任何要素,都必须覆盖言语社群整体,任何人、任何群体、在任何场合,只要是言语活动,都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接受全民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跨越时空,通行于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故而称之为历时性,泛时功能是语言异质性机制所使然。融通性指语篇内部各语类间各要素的游动性而言,作为根基要素,并非为某体类所专,而是可通行于各语类间。从当代的角度进行检视,《文心雕龙》之所以对汉语语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奠基作用,就在于刘勰所提出的语篇理论,符合汉语言语运用的实际,是历史经验的集萃。不仅可以规约彼时的为文造语, 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代的语篇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烛照导航功能。需要说明的是,鉴于语类间性质的差异,不同的“要素”在量上频次参差,实属自然。现从五十篇中提炼出来的决性要素,用当代语篇学术语表述,即题旨、情境、体类、表达、语脉、声律、接受、风格等八个范畴。
语篇论的八个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分布如下:
1. 题旨 即语篇的主旨、主题、旨意、旨趣、趣旨、目的、动因、内容等。“题旨”一词最早见于冯梦龙《警世通言》,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正式列为语篇的构成范畴,其在《文心雕龙》中多以“情”“思”“志”“意”“道”或“情志”的形式出现。故其发端就亮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的题旨。在刘氏看来,要写好文章,话语清晰,就要学习经文。因为经文都是圣人“本乎道”而作。只有体乎经,才能师乎圣,才能揭示宇宙的本源,以抵制时下的异端邪说和矫揉造作的社会语文形态,故宗经明道就自然而然成为《文心雕龙》的题旨,渗透于每篇之中。
2.情境 这一概念是上世纪中叶由境外移入,在《文心雕龙》中,多以“物”为标识出现。强调人的精神、情志、思维活动,都必须有所依托,“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篇)。《诠赋》篇有“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色》篇中有“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物”者,即神、思、理、意、情、志所依存的物质基础。《文心雕龙》中“物”共出现48次,分布于《原道》《宗经》《物色》《序志》等一十九个篇章中。其中有二十余例的语义阐释一致,均为客观外界的社会或自然景物。正因为有“物”的凭借,才能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故而才有“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与物游”即语篇的题旨情趣与外在客观情境相适应所达到“思理为妙”的境界。
3.体类 “体类”在《文心雕龙》中多以“体”的形式出现。然“体”却代表着三个重要范畴,一是体类、语类、语式或语体;一是语篇的结构类型体裁;一是风格,或语势、气势、风骨等诸多概念。作为语类诠释,战国初的墨翟(前468-前376)就曾言道:“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语类论是《文心雕龙》的毂轴,五十篇中,二十一篇是分门别类谈论各体语类。刘勰在《熔裁》篇里,特别提出制篇三准则:首先“设情以位体”即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体类;其次“酌事以取类”选择切合体类的事例;最后则“撮辞举要”以凸显语篇的要义。《知音》篇再次强调:“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即为题旨置厝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与特定语类相适应。“体”即现代的语体、体裁、文类、体式、文体或体制。全书从语类角度说“体”,粗略计之共有一百四十七处,偶也用“类”附理指事。
4. 表达 《文心雕龙》中没有将表达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进行论述,而是将其放在语类中予以阐释。如在《论说》篇中,对论说的解释是:“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理行于言,叙理成论”。《文心雕龙》虽无现代的“记叙”“说明”“描写”“抒情”之界定,但对这些现代表述,均置于某一体类中予以阐释。如“记叙”的表达集中在《史传》篇,认为“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强调“忌泛论,按实书”。“说明”则分布在《铭箴》《诔碑》《诏策》《章表》《启奏》等应用性语篇中。而“描写”和“抒情”两类,《情采》篇:“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黻黼,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熔裁》篇:“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隐秀》篇:“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另有《议对》篇,实际上是现代的“对话”。(4)丁金国:《论语篇的表达系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结构 “结构”在《文心雕龙》称“语脉”“义脉”,集中论述有《章句》《熔裁》和《附会》诸篇。《章句》篇是从微观入手,依据情理、韵律,逐次铺开,“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以达“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熔裁》篇阐述的是语篇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认为“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附会》篇则着重讲统摄语篇整体的是义脉,“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结果是“统绪失宗,辞味必乱”。语脉即贯穿于语篇始终的流动性语义潜势。语脉这一概念是地道土生,最早由宋范季随提出。范氏认为凡论语著文,都应“从首至尾,语脉连属”。(5)转引自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与语脉相近的概念,有“义脉”(刘勰)、意脉(宋李涂、吴可)、文脉(元杨载)等。与西论比较,语脉与“连贯”最为贴近,它涵括了“衔接”与“连贯”的全部意义。
6.声律 《情采》篇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声文五音,即声律,是“为文之道”之一,是语篇构成的重要成分。《文心雕龙》还设有专篇《声律》,揭示语篇声律的内涵和渊源:“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精神)枢机,吐纳律吕(韵律),唇吻而已。”在刘勰的心目中,将五音提到语篇构成不可或缺的地步,这在学术史上还是首次。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语篇中,缺了声律,则不成其为语篇,唯有声律的升降起伏,才能传递出足够的话语信息,才能“五音比以成韶夏”。
7.风格 尽管刘勰所处的时代,“风格”用来阐释审美形态业已显现,但刘氏并未采用,而代之以“体性”“体貌”“体势”等。作品的体裁规定了作品的结构类型,势不离体,即体成势。《文心雕龙》设有《体性》专篇。“体性”实际上是个复合概念,“体”者,存在于言语社群集体意识中的言语体式;“性”者,指表达者个体在言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由个体性情所决定的语篇风格。故而“体性”涵括了语体和风格,将其仅释为风格之意,显然失之偏颇。“体”最早用以论文说语的是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非一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进而确认“体有万殊”,其原因是客观世界“物无一量”(《文赋》)。可见,这种“体”,不为个体所左右,是一种客观的为言语社群所公认的体裁,即语类。由体裁决定风格的命题,到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将“体”所对应的风格作了系统化整理,单独抽出来创建为汉语风格论体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作了正负相对的处理: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体性”篇中所显现的风格是由个体的才、气、学、习等主观要素所决定的,故另设“定势”篇,专论由体裁、语辞和韵律等客观要素所决定的“体势”。 可见,两篇中的所谓“体”实际上一是存在于言语社群所共识的客观体裁,一是言语个体的性情所凝聚的气势、格调。这种气势格调所凝结的是个体与社群、客观与主观、语体与风格的精髓。
8.接受 语篇接受理论是刘勰首倡,先于德国姚斯(H. R. Jauss,1967)的接受论一千四百余年。(6)理论界誉为“前沿”的接受理论,公认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德国姚斯((H. R. Jauss)所提出。其要点是: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姚斯的接受论发表一年后,1968年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问世,认为文本产生之时就是作者消亡之刻。接受理论被巴特推到极致。刘勰在《知音》篇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身。”并指出妨碍“知音”的障碍:一是世俗陋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二是“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建言接受者应“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接受者应“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倡导“圆照”“博观”“平理若衡,照辞若镜”。刘勰所论切中“接受论”的要害,今天依然放射着理论的光芒。
二、《修辞学发凡》的转型功能
(一)《修辞学发凡》的转型意义
转型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生存环境主动求新求变的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事物的结构、形态以及运行模式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转型的前提条件是操作者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依据客观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一个学科或理论进行整体性重构和调整,创造出新的结构、形态和运转模式,以适应变化了的外界语境。
《修辞学发凡》的重要贡献在于成功完成了中国修辞学的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成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的转型;第二阶段是从仿洋摹外到构组符合汉语实际的实用现代修辞学。第一阶段的转型表征是:(1)语言载体的更迭,由文言、骈体更迭为现代白话。如对“对偶”的解说,《文心雕龙》是“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7)刘勰撰,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第384页。。《修辞学发凡》则为“说话中凡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成双作对排列成功的,都叫着对偶辞”(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见《陈望道文集》(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36页。。(2)“题旨”的更迭是根本性的,由《文心雕龙》的“尊道、崇圣、师经”的话题主旨,转变为以普及言语知识、指导言语社群成员语用实践为宗旨。(3)信息结构类型的置换,由《文心雕龙》的述史、议论、评说为一体的信息结构,置换为解说言语知识和技巧为鹄的。
第二阶段是从仿洋摹外到服务于华夏语文教育和语文实践的汉语修辞学。在《修辞学发凡》前,中国已有不少修辞学著述。依治修辞学史者所论,除复古论者外,余者多为仿洋派,(9)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宗庭虎、袁晖:《汉语修辞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先后有龙伯纯(1905)、王易(1926/1930)、陈介白(1931/1936)等。为核准事实,笔者特请友人协助调阅了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岚力的二书。经披阅发现,龙王陈三氏主要依日人岛村的《新美辞学》(10)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1年。和五十岚力的《新文章学讲话》(11)五十岚力:《新文章讲话》,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9年。为蓝本,予以增改为汉语例句、构式,构组起汉语修辞学。其模仿痕迹十分显著,岛村《新美辞学》前一、二两编的全部,和五十岚力的《新文章学讲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移入,如“消极”“积极”“语采”“想采”“文体论”“语姿”等术语。唐钺与仿日派不同,侧重在从语用心理的“科学”角度,来阐释各辞格的潜能。唐钺的《修辞格》(1923)主要仿英人讷斯菲尔德的《高级英文作文法》。该书白话行文,设格颇多,用例甚勤,重在心理比较,自成一体。在外论迅猛涌入、国人修辞意识觉醒的年代,陈望道先生冷静以对、悉心精研,吸收外论养分,以《文心雕龙》为根基,精心培育出属于华夏的语篇论著:《作文法讲义》(1921)、《美学概论》(1926)和《修辞学发凡》(1932)。尤其是《修辞学发凡》,是熔《作文法讲义》和《美学概论》之精,熔铸出具有转型功能的语篇学著作,故有人称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修辞学发凡》的性质
对《修辞学发凡》的性质,理论上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因为《修辞学发凡》问世时,正是中国修辞学躁动时期,古与今、土与洋、俗与雅、学与术等各种观点交错磨合,所以《修辞学发凡》的出现确有发凡起例态势。《修辞学发凡》将交际活动中最为平常的过程及其结果,定性为“修辞学”自在情理之中。加之此前已有多部“修辞格”的著述问世。实际上仔细翻检《修辞学发凡》不难发现,所谓修辞学研究对象——“修辞现象”,陈望道先生对其解释是: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写说发表的全过程是修辞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所有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既然三阶段是修辞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言语交际,那么“修辞现象”自然就不再神秘莫测,而是伴随人类生命的言语活动。由此看来,《修辞学发凡》的修辞学,称其为言语学、语用学,也未尝不可。用新世纪的眼光来看,应是标准意义上的“语篇学”。说是语篇学的理由有三:其一是研究目标与语篇学一致,都是在探索一切可利用的语言文字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可能性;其二是坚持的标准,都是服务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切性;其三是都在寻找一种对写说行为的理论阐释体系。如果将《作文法讲义》一并思考,其语篇性特征就更加明显。
(三)《修辞学发凡》的体系
《修辞学发凡》的轴心是“两大分野、三种境界”。作为两大分野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反映了言语实践中的客观事实。在言语实践中,所谓消极修辞,实际上是基础语用原则,任何语篇之所以得以产生,都由这个基础原则所使然。所谓积极修辞,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生的,不妨称为“人为藻饰”。可见,所谓消极、积极之分,实际上即通用言语和加工言语的二分。三种境界(记叙、表现、糅合)内蕴的是由五种表达方式所组成的语文体制。在《作文法讲义》中,详尽讲述了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和诱导文。这五种体制是语用者经过无数次的语用实践,抽象出来的俗成构式。之所以能够俗成,是因为其各自内部有着规律性的结构规则。二分野三境界统摄了五个重要的语用原则,即题旨与情境、内容与形式、自然与人为、语体与风格、常式与变式。
“题旨与情境”高频出现在《修辞学发凡》中。作者认为:“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故而是“修辞的第一要义”。在言语活动中,凸显题旨情境是陈望道先生对语言科学的重要贡献。一切言语现象的观察分析,必须结合题旨情境进行,那种脱离特定题旨情境的所谓纯客观的抽象研究,对语言运用无任何意义。
“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虽是常谈之语,然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易事。《修辞学发凡》认为:“内容和形式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所以,离开内容讲形式,或离开形式讲内容,都是片面的。然在实际言语生活中,“形式过重”或“内容过重”是常发生的现象,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分寸,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自然与人为”在《修辞学发凡》中称其为“消极”与“积极”。自然交流是言语实践的常态,它要求内容上“明确、通顺”,形式上“平匀、稳密”,更习见的情况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绝对的消极修辞或绝对的积极修辞,严格讲是不存在的。史上的所谓“美文”,应是积极修辞的典范之作,但其“垫底”的仍是自然态的语言文字。
“语体与风格”,《修辞学发凡》设有专章论述“文体或辞体”。《作文法讲义》从对象或方式上分为五体: 记载、记叙、解释、论辩、诱导;《修辞学发凡》从表现入手,专注于审美形态,分为简约与繁丰、刚健与柔婉、平淡与绚烂、严谨与疏放。《修辞学发凡》将“文体或辞体”置于理论基石的位置,作为审美形态的“体性”(风格)被单独列出予以重点阐发。陈望道先生对语体与风格的思考从未停止,从《作文法讲义》《修辞学发凡》直到其晚年,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认为“讲风格,要从篇章着眼,风格是修辞特点的综合表现”(1964年4月10日),“要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1965年9月20日)。(12)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245-246页。
“常式与变式”,《修辞学发凡》第十篇专论“变化和统一”。“统一”即言语社群所公认的原则与规则,它需要相对的稳定,故而可称为“常式”。又鉴于题旨情境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从而决定了修辞方式的多样性和易变性。陈望道先生特别强调:“每个具体的切实的修辞现象,都是适应具体的题旨和情境的。”因此,言语活动中的各种构式都处在绝对的变化之中,所以说,常式是相对的,变式是绝对的。“从这统一类同的一面着眼,我们便又可以在那变化无定之中,得到一种大体可以分门别类的头绪,这便是语文的体式。”
(四)《修辞学发凡》对《文心雕龙》的整合与提升
治修辞学史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推定《修辞学发凡》是受日人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岚力及西方等修辞学的影响而成书。所谓影响,除“消极”“积极”概念命题袭用外(然亦经过质的改造),辞格和语文体式则是源自《文心雕龙》,就连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岚力的“文体论”,他们自己都承认参研了中国的《诗经》六义——《文心雕龙》(刘勰)——《文则》(宋 陈騤)——《沧浪诗话》(宋 严羽)——《文筌》(元 陈绎曾)——《文体明辨》(明 吴讷)——《读书作文谱》(清 唐彪)文脉。尤其二书的“文体论”,其范畴提取与界定源自《文心雕龙》的痕迹清晰。而《修辞学发凡》并无日著的痕迹,相反从开篇到收结,每篇都有《文心雕龙》的征引。明文标注征引《文心雕龙》隽语十五处,默蕴《文心雕龙》的理论主干则随处可见。陈氏对《文心雕龙》的嗣承关系,昭然耀于字里行间。与其说陈望道先生受日论和西语的影响而著述《修辞学发凡》,不如说是直接嗣承刘勰的语篇学思想。笔者有感于此,故引发出探索二者的渊源关系的欲望。
陈望道先生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整合与提炼,熔铸出《修辞学发凡》体系。这个体系上文已有论述,这里集中就如下四个问题进行讨论:两大分野和三种境界、题旨与情境、辞格、语体与风格。
关于“两大分野、三种境界”,在陈望道的心目中,凡是运用修辞格的语篇都是积极修辞。故五到八篇的三十八个辞格,自然均为积极修辞,余者为理论述说或体类举要,其引例多为二者兼而容之。消极修辞的标准是:“内容方面明确、通顺;形式方面平匀、稳密。”其基本要求是:“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1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见《陈望道文集》(2),第45页。与此相应的,《文心雕龙》有《章句》《练字》《指瑕》《附会》《总术》等篇。
章句篇云:“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分章造句是言语交际的最基本步骤,分章恰当方能使语篇中心突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全篇结构严谨;用词造句准确稳妥,才能达到语义明确。《附会》篇有言,强调“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从而达到语义明确通顺,结构平匀稳密,臻达《总术》篇所望“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练字》篇所云:“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的四点及《指瑕》篇所指曹植、左思、潘岳等用辞失当、比拟不伦等四条,均为消极修辞范围的问题。有鉴于刘氏的审美情趣所致,整个《文心雕龙》,除上述篇章专论基础语用原则外,绝大部分是“积极修辞”。三种境界实际上是由表达方式所熔炼而成的语文体式,《作文法讲义》集中讲述了记载、记叙、解释、论辩、诱导五种。据查,此五类表达方式,言语实践早已有之,理论表述在两汉以降间有零散方式出现,作为整个表达方式整体,最早确乎源自西论,且很快为国人所接受。上世纪初始,率先在语文教育界推广开来,继之有蒋伯潜、蒋祖怡等著录成篇,广为推行。《作文法讲义》收录在册,然到了《修辞学发凡》,陈氏只在“三境界”中概而论之,以“记叙的境界”“表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取代了《作文法讲义》中语文的体制。代而行之是“文体或辞体”,即刘勰的“体性”“体势”“风骨”,也就是当今学界统称的风格。
“题旨与情境”是《修辞学发凡》的基础,整个体系由其支撑。陈望道先生认为“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情境;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然陈氏警告说: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其密合度常处在离异状态,故而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从情感上去感受,从语义前后的联结关系上去推敲。作为《修辞学发凡》智库的《文心雕龙》,《时序》(实际是序言)篇开宗就宣示“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也就是题旨。刘勰有“本道”“师圣”“崇经”的思想,不难理解,是由彼时的社会舆论形态所囿。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将其作为属文论道的宗旨置于篇首,可见他对题旨的重视。“情境”论是二十世纪语言学的重要发现和进展,是外论与本土结合的成就之一。《文心雕龙》是以“物”作为言语活动所依存的自然社会符号展现于世。认为人之所以有神、思、理、念、意、情、志等活动,则完全是“物”所使然。《诠赋》篇有“体物写志”“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物色》篇则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神思》篇“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概括,凝聚了《文心雕龙》情境论的精粹。刘勰的“物”论,体现朴素的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修辞学发凡》认为随情应境是灌输题旨的必须手段。言语活动适应题旨情境,不仅是切实自然的需要,也是修辞的最高标准,故而是要义中的要义。而要做到《修辞学发凡》所要求:一是对题旨和情境的洞达,二是对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如何能洞达和通晓无定准的技巧和方式,全凭语用者日常“体物写志”的观察和“睹物兴情”历练。正如《修辞学发凡》所要求的那样:一要精密观察,二要系统研究。
“辞格”是《修辞学发凡》的重心,全文283页,其中辞格共158页,占55.6%。辞格论不仅所选格类较精,更入胜的是引例切题、生动、有趣,极易引导受者进入辞格的意蕴。《修辞学发凡》所收38个辞格,在《文心雕龙》中,单独立篇有四,散入其他有六。故有人认为,与其说《文心雕龙》是一部美学或文艺学,莫不如说是一部修辞学著作。从修辞角度讨论《文心雕龙》,前修和时贤多有高论,在这里仅掇其要而述之。
夸饰:所谓“夸饰”,即夸张。刘勰认为:“神道(事物的内涵)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言有难尽精微,故要借助于“形器”(物象)来述形而上之道,所以“文辞所被,夸饰恒存”。他坚持夸饰的原则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明实两乖。”
丽辞:“丽辞”专论“对偶”。对偶和声律是汉语特有,而为西语所无。尽管刘勰身处追逐骈偶时代,然其对骈偶却有清醒认识:是本乎“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黄侃曾评曰:“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然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或鉴于对偶之末流,遂谓骈文为下格;或惩于流俗之恣肆,遂谓非骈体不得名文;斯皆拘滞一隅,非闳通之论也。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事类:《事类》专谈“引用”。“事类”之谓“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认为引事引言来强化语义自古已然。引用分明引和暗引,暗引是将所引的言或事融化在语篇里,明引则需“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舍此,则必定“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值得注意的是,“事类”说与当代“互文性”理论的古今时距差,能引出我们多少联想!
比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刘勰的界定较其前深刻得多,不仅指出比与兴都附托于外物,而且指出“‘比’显而‘兴’隐”先显而后隐。二者虽有别,但相互贯通,比附即借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来揭示事理,起兴则是借物寄情。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融合为一,徜徉于汉语言语活动之中。《文心雕龙》中尚有一些“格范畴”未单独列出。如《谐隐》《练字》篇中的谐隐,即析字格;《声律》篇的“吃文”,即“飞白”格;《物色》篇有“摹状”格,《熔裁》篇中的“繁简”,即节略格。《文心雕龙》中还有一些成格的范畴,如“熔裁”“隐秀”,前者近似“炼意”格,后者贴近“含蓄”格。《修辞学发凡》与之对应的是:夸张、譬喻、借代、引用、比拟、宛转、重叠、反复、对偶等格。
《修辞学发凡》立足于东土,广筛精选出三十八个辞格,配之以切题的古今例证,足以帮助初学者参互印证,故刘大白赞其为“初学者之津梁”。
“语体与风格”是陈望道先生给后代留下的重要研究课题,是其精思深虑了几十年未了的心愿。在《修辞学发凡》中,未用“语体和风格”这两个概念,经常是以“语文体式”“体类”“文体”“辞体”而代之。如《修辞学发凡》第十一篇“文体或辞体”篇名的四次改动,从“语文的体类”(1932)、“辞白的体类”(1945)、“语文的体式”(1954)到“文体或辞体”(1959),足以反映出陈望道对此课题的纠结。针对一些偏颇的言论,他曾在1965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在风格学研究上如何不行,连有关风格问题的科学知识都没有,这就值得讨论了。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的研究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一宗宝贵的财富。我国研究风格,包括语文‘体裁’和表现‘体性’,是很早的,现在更是在研究,今后还要继续地深入研究。不过,我们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不一定是人家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要用人家的样子作标准来否定自己,说自己怎么不行?总之,要知道,我们中国是有风格研究的,是有这方面学问的。尊重这种事实,是学术工作中应有的科学态度和爱国主义态度。我们要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15)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第267页。
陈望道先生对体性品类的设置,较之其前后相关著述的显著点是:时代特色鲜明,服务于语文教育的宗旨明确,故而在论述和例释上,都紧扣应用。为达立意宗旨,首先必须解决“意会”“言传”的问题。陈望道先生认为:“凡是可以意会的一定可以言传。研究修辞,就是要缩小和消灭‘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域。”(16)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第245-246页。解决的途径就是:语言化、科学化。语言化就是从现实语篇的特征中,去寻找语言表现;科学化就是从表现体性的物质要素中寻求不同范畴间的差异。为此,陈望道先生在刚柔两极对照映像中建立起陈氏风格论体系,对各范畴确立的标准,则明确予以标注:
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为简约和繁丰;
由气象的刚强和柔和,分为刚健和柔婉;
由于话里词藻的多少,分为平淡和绚丽;
由于检点功夫的多少,分为谨严和疏放。(1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见《陈望道文集》(2),第257页。
两极对立,就语品而言,无优劣可论。所谓“对立”,“只是假定的两个极端或两种倾向”,实际上现实语篇中的风格形态多是位于两极之间广阔的中间带。陈氏在嗣承《文心雕龙》《诗品》之绪,何以从众多的风格范畴中选择此八品来构组《修辞学发凡》的体系?窃以为陈望道先生是经过了认真慎重地甄选,一是与现实社会语文形态相契合,切实反映社会语文形态的状况;一是更利于普罗大众能从物质性的语言中,尤其是极性对照中,学到语文实践的知识和能力。
三、结 语
《文心雕龙》与《修辞学发凡》代表着一个学科发展的两个巅峰,就像海浪一般,在两个巅峰之间,流动着的是连绵不断的潜涌和暗流。二书之间是同一泓系的两个浪涌,其所传递的是不同时空中的同一清流的动态表现。所以,梳理和归纳二者之间的嗣承关系,当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先辈曾告诫我们:“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18)陈光磊:《语文运动的先驱 语文建设的巨匠》,《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当下修辞学发展的势向,已显露出前进乏力的疲惫态,正等待着外来新理论的充电、加油。与其等待外援,为什么不能向祖宗的典藏中汲取营养丰富的乳汁?从梳理《文心雕龙》与《修辞学发凡》的历史源流着手,也许能找到通向柳暗花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