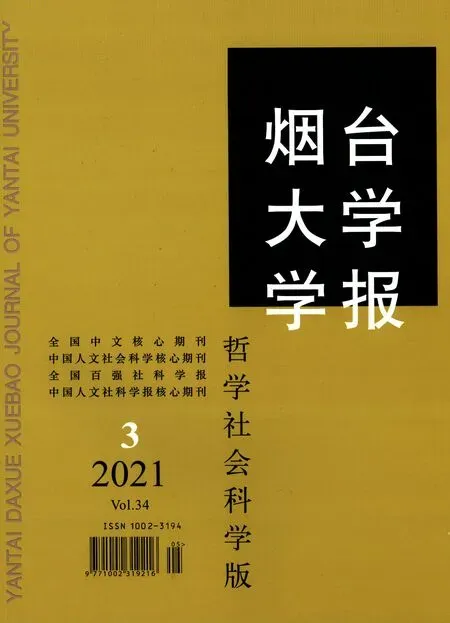姓氏改易、身份变迁与形象塑造
——以党项拓跋氏的内附与自立为例
郝振宇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中国古代社会,姓氏尤其是国姓常常与国家政治相结合,被赋予强烈的社会政治功能。(1)黄修明:《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此亦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夷夏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原王朝可以通过给予内附者赐姓的政治待遇而建立起拟制血缘关系,以此维系中央与边疆关系的稳定。中原王朝对内附者的赐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王朝势强时,赐姓被视作褒奖内附者的政治手段,作用在于“赐姓命氏,因彰德功”;(2)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页上栏。一是王朝势弱时,赐姓成为缓和紧张关系的一种安抚政策,“跋扈之臣与蛮酋贼渠,例皆赐以国姓,谓之固结其心”。(3)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第495页上栏。对接受赐姓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改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发生变化。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氏先后经历李唐赐姓、赵宋赐姓和元昊改姓,无论赐姓或改姓,拓跋氏都能因时顺势地进行身份构建,吸收借鉴中原文化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强化和巩固其地位。目前,学界多从宏观层面关注唐宋王朝的赐姓问题,(4)主要有王凤翔:《唐五代赐姓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张冠凯:《隋唐五代赐姓名史料辑录、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5年;亓艳敏:《唐五代改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闫廷亮:《唐人姓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和田英:《唐代赐姓赐名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赵寅达:《宋代赐姓与赐名现象探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永刚:《宋代西北汉姓蕃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09年;曹听:《宋代西北地区及西夏境内番族汉姓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年;佟少卿:《北宋西北蕃官赐姓赐名现象探究》,《西夏研究》2018年第4期,等等。具体层面上对党项拓跋氏的赐姓与改姓问题还有讨论空间。基于此,本文以党项拓跋氏的姓氏改易为切入点,从长时段来探讨党项拓跋氏姓氏改易背后因时顺势的身份变迁及与之相适应的形象塑造问题,进而明确拓跋氏在民族交融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李唐赐姓:党项拓跋氏的内附与身份转变
唐初,高祖李渊提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边疆民族关系处理策略以期和睦四方、静乱息民。(5)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标点本,第689页。太宗李世民平定东突厥后,“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6)《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册,第1119页。此际,党项羌前后内属者达三十万口,唐朝政府就党项部落集中所处的关内道和陇右道分别设置数量众多的羁縻府州以安置,并拔擢其部酋为都督、刺史,且允许他们世袭。《旧唐书·党项传》载:“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7)《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6册,第5291页。此后,党项诸部开始接受唐朝的封号,成为唐朝西北羁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项拓跋氏亦在太宗时期内附唐朝并首次接受唐朝赐姓,《旧唐书·党项传》:“羌酋拓跋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李靖之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8)《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第16册,第5291页。据此可知,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室通婚且奉吐谷浑为主,有“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的忠君思想。所以,拓跋赤辞在“诸羌归附”唐朝的情况下尚无内属之意,并在李靖攻取吐谷浑时“屡抗官军”。(9)王溥:《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标点本,第1756页。只是后因“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10)《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第16册,第5292页。由此可见,拓跋赤辞内附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此内附行为对保全拓跋氏有积极作用。唐贞观九年(635),太宗派兵征伐吐谷浑,最终吐谷浑主伏允“与千余骑遁于碛中,众稍亡散,能属之者才百余骑,乃自缢而死。国人乃立顺为可汗,称臣内附”。(11)《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第16册,第5298-5299页。在此形势下,若拓跋赤辞与吐谷浑共抗官军而拒不内附,结果就是与宗党离析而被唐军所灭。在拓跋赤辞率众内附后,因拓跋氏在党项八部中“最为强族”,(12)《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第16册,第5290页。太宗区别于其他党项部落对待,“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13)《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第16册,第5292页。以维系人心。
虽然拓跋氏享有赐姓的政治殊荣,但拓跋氏并未以李氏自称。据出土墓志资料,直到唐僖宗李儇再次赐姓之前,拓跋氏一直沿用原姓而未改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拓跋氏第十一代成员。有学者指出,拓跋氏没有改姓是因为没有形成家族命名的传统。(14)杨浣:《五代夏州拓跋部世系与婚姻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短时间内政治感情难以取代族群感情。(1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但是,有唐一代,拓跋氏与唐朝关系十分密切,始终“职贡不绝”。(16)《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第16册,第5292页。据史书记载,贞观以后,“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17)《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第20册,第6215页。《拓跋守寂墓志铭》详细记载了拓跋部因吐蕃侵扰而内徙的情况。唐高宗仪凤年间,“高祖立伽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国家纳其即叙,待以殊荣,却魏绛之协和,美由余之入侍。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圁阴之地,则今静边府”。(18)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1页。拓跋氏自此为部落使,统率十八个党项拓跋氏部落,在拓跋后那时期任静边州都督一职。拓跋守寂之父拓跋思泰在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率众讨袭六胡州叛乱,因功封爵为西平郡公。在唐中后期,党项诸部与唐朝时有摩擦,杜牧在《贺平党项表》中有“今古夷狄处在中土,未有不为乱者”。(19)杜牧:《贺平党项表》,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册,第7772页下栏。但是,拓跋氏与唐朝的关系则相对缓和。唐宣宗李忱在《平党项德音》中有言:“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使抚安,尤见忠顺,一如指挥,便不猖狂,各守生业,自兹必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20)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10页。平夏党项即党项拓跋部,(21)汤开建:《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第考》,《西夏学》第9辑,2014年。此部基本上与唐为善且较为忠顺,以致宣宗有“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的直观感受。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因拓跋思恭平黄巢有功,拓跋氏被再赐国姓。《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了拓跋思恭的事迹:“黄巢入长安,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僖宗贤之,以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次王桥,为巢所败,更与郑畋四节度盟,屯渭桥。……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22)《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第20册,第6218页。僖宗赐姓与太宗赐姓有所不同,这是在唐朝势弱且国势艰危时的笼络举措,即“赐以国姓,谓之固结其心”。(23)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第495页上栏。在赐姓的同时,拓跋思恭已被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一职,成为中央王朝认可的地方藩镇势力。此后,拓跋氏以李氏自称,凭借优越的政治身份和军事力量,在唐末五代各地争雄的混乱局面中乘机发展势力。至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拓跋李氏与中原王朝仍基本维持着臣属关系。之后,拓跋李氏借军事势力和政治威权雄踞西北边隅,基本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成为不容忽视的区域力量,与中原诸王朝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互相往来的关系。(24)史卫民:《党项族拓跋部的迁移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集)》1981年第S1期。
有唐一代,党项拓跋氏由内附者成为地方蕃将,完成了角色的转变,并把握住正确的发展方向,成功跻身强势政治势力成员。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拓跋氏在文化层面也渐次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渐习汉风。这主要体现在拓跋氏上层积极与汉族通婚并学习汉文化,依赖这种共同文化,其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拓跋氏上层逐渐融入汉人群体。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自拓跋氏第六代成员始,男性的姓名中开始出现明确的字辈与排行现象。如第六代拓跋守寂、拓跋守礼、拓跋守义等人,都以“守”字为字辈。第七代拓跋澄澜、拓跋澄泌、拓跋澄岘等人,则以“澄”字为字辈。自第十二代拓跋思恭始,拓跋氏改姓李氏并形成家族命名的传统,字辈与排行更加清晰明确。这种字辈现象,遵循着自汉以来形成的按字辈排列人物世系的基本原则。在汉人社会,字辈是专门用以标志宗族成员辈份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宗族内世系,确保宗支不混淆,昭穆不失序,维护宗族制度。这是中国宗法制社会中人人都必须遵从的一种礼制。(25)欧阳宗书:《字辈——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一种礼制》,《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由此可见,汉文化对拓跋李氏有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文化上的归属意识。这种归属意识对于拓跋氏的长远发展,对于决定文化属性的作用很大。如果说拓跋李氏接受唐朝赐姓主要还是表现为形式上的隶属关系,那么与汉人通婚则促进了文化上的认同与交融。
综上,李唐时期,党项拓跋氏曾两次被赐予国姓,两次赐姓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涵。第一次赐姓是唐太宗对拓跋赤辞率众内附的表彰,拓跋氏身份由吐谷浑的臣属变为唐朝的羁縻都督,拓跋氏与李唐保持着一种相对密切和睦的关系,并在李唐中后期帮助唐政府戡乱平叛。第二次是唐僖宗对拓跋思恭力平黄巢的褒奖,藉由平叛的战功,拓跋氏被再次赐姓,有了定难军节度使的殊荣,成为据有夏绥银宥诸州的地方藩镇力量。后面这次赐姓后,拓跋氏改姓李氏并以李氏自称于世。拓跋氏在跻身唐朝社会上层的同时,又构建起与政治身份相契合的文化身份,并以此调整自身的认同体系。
二、赵宋赐姓:党项拓跋氏的分裂与身份抉择
北宋初,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遣使奉表入贺。建隆三年(962)复遣使贡马,宋太祖“命玉工治带,亲临视之,召其使问彝兴腹围几何,使言彝兴大腰腹,上曰:‘汝帅真福人。’遂遣使以带赐之,彝兴感服。”(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四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1册,第67页。因宋太祖对西北边地采取笼络政策,“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27)《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0册,第10357页。在这种情况下,拓跋李氏则继续与北宋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友好往来的关系,并出兵协助北宋攻取北汉。所以,清人吴广成如此评价双方关系:“李氏自归宋以来,频与汉战,累立大功,其效顺之心可谓诚矣。”(28)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标点本,第35页。
宋太宗时期,拓跋李氏与北宋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新变化。李彝兴之孙李继捧继任定难军节度使一职时没有得到宗族内部的一致支持,以致出现了“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的现象,(2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第56页。而李继捧也没有能力解决宗族内部的权力纷争,所以其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请诏使谕李继捧入觐。与此同时,宋太宗也放弃太祖时许豪酋世袭的羁縻政策,对李继捧的内附给予积极地回应。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来朝,“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太宗随即“遣使诣夏州,护继捧缌麻以上亲赴阙,县次续食”。(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第1册,第520页。李继捧入朝献地之举得到太宗认可,宋廷进一步要求继捧五服之内亲属皆入京师。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愿内徙,“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族帐稍稍归附”。(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太宗雍熙元年九月,第2册,第585-586页。自此,拓跋李氏的势力分裂为两部分,一部以李继捧为首,内附于宋朝;一部以李继迁为首,背宋自立。之后,以李继迁为首的拓跋氏逐渐引领了党项群体的发展走向。
因李继迁不肯降宋,太宗最初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亲书五色金花笺赐继捧国姓,改名保忠,授定难节度使,所管五州钱帛刍粟田园等并赐保忠”。(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辛酉,第2册,第653页。此举意在以李继捧制衡李继迁。在太宗的一系列举措下,淳化二年(991),李继迁“奉表归顺”,北宋“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以国姓,名曰保吉”。(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七月乙亥,第2册,第718页。清人吴广成认为这是“西夏受宋姓之始”。(34)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第55页。北宋赐姓赐名本是“宠以天潢之属”的举动,目的在于“易其倔强之心”。(35)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第55页。从历史发展来看,李继迁对所赐的赵氏身份并未给予积极地回应与认同,而是拿这种政治身份为我所用。他在攻取宋夏沿边的熟仓族时,曾经派人对其进行诱导,其中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表示自己“身已归朝,赐国姓,今后请勿相拒,共禀朝命”。因为熟仓族地处宋夏沿边要道,李继迁“不得熟仓,不能入环庆”,他为达到“入环庆”的军事目的,采取的策略是以赵氏自称,消解熟仓族的戒备以便攻取。李继迁虽接受赵宋赐姓赐名,但其实并没有放弃李氏身份。因为“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李继迁需借用李氏身份以更好地笼络党项豪右,他曾言:“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36)《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40册,第13086页。相比于赵氏身份,“世著恩德”的党项部众对李氏身份认同意识更强,李继迁也要借助李氏身份凝聚党项部众,以图霸业。所以,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李继迁在攻取绥州和银州后,遣使入宋请复宥、夏等州,他直言:“五州故地,先业留遗,拓土展疆,是诚在我。”(37)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第57页。可见,李继迁以李氏自居,致力于恢复“先业留遗”的夏绥银宥等故地。李继迁在与北宋的反复斗争中,借助赵氏身份以交好北宋,坚守李氏身份来团结部众,在双重身份的交替使用中,经过数年奋斗,在取得银夏诸州后建都西平府。因西平府“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的社会风尚,李继迁欲“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38)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七,第85页。在自立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党项因与北宋间连年征战而实力受损,所以,李继迁临死时告诫其子李德明应韬光养晦,与北宋结好,“当倾心归顺朝廷。如一两表未蒙开纳,但连上封章以祈见德”。(39)张方平:《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1476页。李德明遵循其父的政治遗策,“言父有遗命,永无贰心”,(40)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第100页。对北宋实行积极友好的睦邻政策。所以,在李德明称臣于宋的三十年中,“贡献之使,岁时不绝”,而宋仁宗也“以其恭顺,遣使持册封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又加食邑千户”。(41)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第130页。在宋夏关系相对缓和友好的三十年间,西夏的生产获得发展,商业随之活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重大成就。借着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机,李德明励精图治,集中力量实施对河西地区的控制,为西夏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吴广成对李德明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一时期“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使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俸赐既赡,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粟支数年,地拓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42)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第131页。
综上,拓跋李氏自李继捧纳土内附而分为两部,以李继迁为首的一部逐渐继承拓跋李氏在唐末五代积累的政治与军事遗产,并在与北宋对峙的过程中发展成为拓跋李氏的中坚力量。为了维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北宋对“有因归顺,或立战功”的少数民族首领“特赐姓名,以示旌宠”,(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六,哲宗元祐七年八月庚寅,第20册,第11343页。意图通过赐姓赐名以达到笼络少数民族政权和抚慰归顺者的目的。但北宋为笼络李继迁而给予赐姓赐名的政治优待,已不能充分发挥有效的政治功用。因为拓跋李氏自唐末改姓且发展成雄踞西北的地方势力后,更倾向于维系与中原王朝互不侵犯、互相往来的关系。李继迁父子对于赵氏身份并没有积极认同,只是将赵氏身份作为获得发展机遇和获取更多利益的筹码,为西夏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三、元昊改姓:党项拓跋氏的自立与身份重构
李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为定难军节度使。元昊对宋朝始终持排斥态度,他曾“数劝德明勿臣于宋”,即使宋仁宗遣使册封时,亦有“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的愤慨之言。(44)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第131页。对性雄毅且多大略的元昊来说,他始终心怀“英雄之生,当霸王耳”的雄心壮志,废除了其父德明长期实行的从属北宋的政治策略,并积极谋求成为独立的对等国,(45)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开始以强硬的姿态对待北宋。所以,元昊对宋朝赐姓的态度与其祖、父二人截然不同,他甚至认为“李、赵赐姓不足重”而断然“改姓嵬名氏”。(46)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第131页。元昊改姓是拓跋氏身份变革和重新构建的重要一环,标志着元昊与李氏、赵氏身份的割裂。而且,元昊通过改姓以明贵贱,将拓跋群体进一步分化整合,强调自己族属的高贵出身和政治地位,将姓氏区分血缘、社会关系和权利的功能与社会结构的重构进一步整合在一起。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元昊在李继迁和李德明所奠定的基础上称帝建国,嵬名氏升格为帝姓和宗室姓,宋代史籍对西夏宗室有“嵬名族人”(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七,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庚申,第20册,第11146页。和“嵬名亲族”(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九,哲宗元祐七年正月壬子,第20册,第11212页。的指称。然而,元昊称帝建国的行为使宋夏关系迅速恶化,宝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4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仁宗宝元二年六月壬午,第5册,第2913页。但是,北宋的这种惩罚性措施并未对元昊自立的政治诉求和行动产生任何阻碍。因为元昊改姓后,就积极地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原属身份进行革新,对新身份进行系统构建,力图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共同体。他特别将发展民族文化作为在政治上对抗中原的重要手段,即用文化强调政治的独立,用政治实现文化的扩充。(50)朴志焄:《西夏的自国认识及宋朝观——以元昊统治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第15辑,2014年。虽然元昊与北宋政治上交恶,军事上兵戎相见,但在文化上却始终与中原文化难以割舍。因为在唐五代宋初的数百年中,党项群体已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即使元昊试图发展民族文化,但潜意识中这种民族文化还是带有中原文化的深刻烙印。
元昊在建立官制、制定礼乐、议定朝仪和推动文化教育等方面虽突出民族性,实质上借鉴吸收的还是中原文化的内质。官制方面,元昊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礼制方面,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亨等接纳过来,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但元昊更定的礼乐本就原属唐宋,史称:“僖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历五代入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迨德明内附,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51)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第146页。朝仪方面,元昊“久悉中朝典故……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52)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三,第152页。文化教育方面,西夏尚学且尤重儒家经典。元昊创制蕃书以翻译《孝经》《尔雅》,谅祚上表宋朝求取九经,乾顺养贤重学以隆文治,仁孝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遣使请市儒、释诸书”。(53)《金史》卷六〇《交聘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册,第1408页。凡此种种,有力推动了西夏儒学发展与文教兴盛。西夏编纂刊刻的书籍,都带有儒家文化因子。西夏人在借鉴吸收《孝经》及其他儒家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圣立义海》中家庭伦理道德部分的内容。而《圣立义海》更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为主导思想,结合本国风土人情编修的一部百科教科书,供本国学子、庶民学习之用”。(54)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西夏还仿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家苑》一书编成《新集慈孝传》,意图通过中原历史故事为人们树立封建人伦的榜样。西夏编译的《类林》中也以中原汉人事迹宣扬儒家伦理秩序。(55)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金史·西夏传》对西夏尊孔崇儒赞曰:“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56)《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第8册,第2877页。
鉴于元昊在制度设计中内含的诸多中原文化元素,《宋史·夏国传》称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57)《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第40册,第14028页。而宋人富弼更进一步认为:“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中国所有,彼尽知之。”(5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仁宗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6册,第3641页。所以,元昊虽然改姓建国,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建立新体制以突显民族特色,但在无形中却吸收中原文化因子,促进西夏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既不同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也形成了互相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连续统。(59)纳日碧力戈:《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从互联到共有》,《西部蒙古论坛》2019年第1期。
元昊在李继迁和李德明奋斗的基础上谋求独立的政权,不仅反对赵宋王朝给予的赐姓恩荣,更对传承百年的李氏身份进行否定,直接改姓嵬名作为帝姓和宗室姓。因为姓名作为社会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制度意义和情感意义,(60)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元昊通过改姓就是在明确强硬、自立的政治态度。故《宋史·夏国传》有评价曰:“概其(西夏)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61)《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第40册,第14030页。另外,元昊为凸显独立政权的民族性,试图通过创制蕃书、改革服饰、确立官制等系列措施使党项群体可以在心理上自觉认同和主动归属新建立的西夏政权。西夏意欲凸显民族性,但在唐五代宋初数百年的影响下,党项统治群体已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烙印,不能全然抹去,所以西夏始终无法同中原文化彻底割裂,在近两百年的时段内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仍逐渐深化,以致西夏遗民对儒家治国深有认同之意,如高智耀所言:“昔之有天下者,用儒则治,舍儒则乱,则其效也。盖以为儒者以仁义为本,未有仁而遗其亲也,未有义而后其君也。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儒之教也。”(62)《元史》卷一二五《高志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0册,第3072页。
四、结 语
自党项拓跋氏见诸史籍后的六个多世纪里,其姓氏先后经历了拓跋氏、李氏、赵氏、嵬名氏的改易,与姓氏改易相伴随的是拓跋氏的身份变迁与形象塑造。李唐时期,拓跋氏因功被赐姓李氏,由高原河谷地区的游牧者先变为唐朝的内附者,再变为地方藩镇。经唐末五代宋初百余年的经营,拓跋李氏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在军事上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在文化上学习吸收中原文化,逐渐成为一个与中原王朝相类的地方政权。赵宋时期,因李继捧和李继迁的分立而分为两部分,最终由李继迁引领了拓跋李氏的发展走向,在和北宋控制与反控制的反复斗争中,拓跋李氏由地方藩镇渐趋走向自立。元昊则直接放弃李氏和赵氏而改姓嵬名,并把握历史契机,试图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和价值观念等为纽带组成共同体,构建一种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虽然拓跋氏由游牧者的身份逐渐在唐宋更替的时代背景中发展壮大,直至立足西北建立政权。但西夏所据之地原为汉唐旧疆,宋人张方平认为:“盖今羌戎(西夏),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况朔方、灵武、河西五郡,声教所暨,莫非王民。”(63)张方平:《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三,第1475页。王朝统治者亦认为“河西士民素被王化”。(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仁宗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第6册,第3198页。拓跋氏在与唐宋王朝长期的互动交流中不断接受中原汉文化,密切的文化关联使西夏始终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内,这种文化同一性不仅为以后王朝的大统一准备了条件,更有益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因为文化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最深层次的认同。(65)张健:《文化符号、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光明日报》2020年5月8日,第11版。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能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