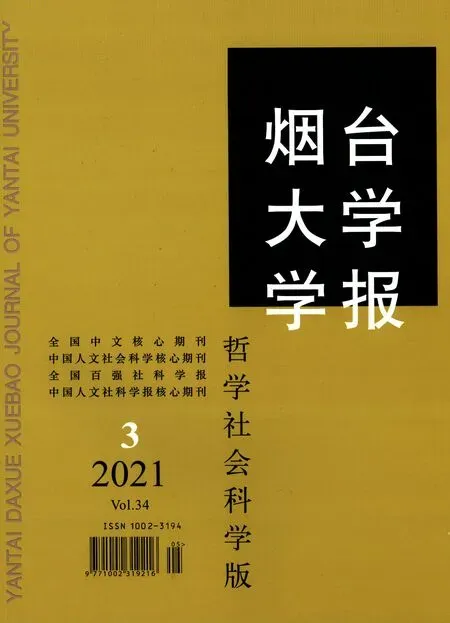杜甫书写与新诗的诗学规范
——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冯跃华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论及中国诗与中国画遵循不同的评价体系,钱锺书曾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过精彩剖析:“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在钱氏看来,“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1)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页。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不仅在古代中国享有崇高地位,“即便在所有道德的与文学的标准都被掷入怀疑和混乱的20世纪中国,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的集团和个人也都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为己所用”。(2)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9页。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臧否,早已逝去的诗人在不同话语中戴上不同的面具,成为“被发明的传统”。而作为“当下”的“现代”,则在“传统的发明”中建构起自身的知识谱系。
具体到胡适而言,作为20世纪中国新诗的奠基性人物,胡适不仅以“尝试”的实验主义精神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其在文学革命初期有关新诗的论述几乎也成为新诗创作与批评的“金科玉律”,影响深广。与此同时,“被发明的传统”作为新诗建构的话语资源,同样被纳入胡适的理论视野之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杜甫得以从“幕后”进入“台前”。有关胡适对杜甫的肆意发挥,学界多有论述,但其中的复杂关联性似乎尚有开拓空间。本文以胡适的杜甫书写与新诗言说为考察中心,试图在二者的复杂关联上有所突破。对白话新诗的提倡如何影响了胡适对杜甫的论述?胡适的杜甫书写在怎样的语境中被纳入白话新诗的历史建构?二者究竟存在怎样难以言说的复杂与困惑?有关胡适的杜甫书写与新诗创作,它们如何在看似“断裂”的历史讲述中相辅相成?又如何在现实的纠缠中相互龃龉?它们如何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中昭示新诗运动初期的历史语境?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白话新诗的起源谈起。
一
关于新诗的起源问题,“横向移植”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梁实秋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到:“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在梁氏看来,与古典诗学的整体性“断裂”构成了白话新诗的必要前提,尽管《尝试集》中的部分新诗不脱中国旧诗的风味,“但是就大体讲来,《尝试集》是表示了一个新的诗歌观念”,“新诗与中国传统的旧诗之不同处,不仅在文字方面,诗的艺术整个的变了”。(3)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见许霆主编:《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经典》,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紧随其后,梁氏提出了早期新诗运动只重“白话”不重“诗”的著名论断,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则是“要明目张胆的模仿外国诗”。(4)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见许霆主编:《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经典》,第213页。
梁实秋虽然尊重胡适早期对新诗运动的贡献,但还是表现了其对早期白话新诗的不满。表面上看,二者的诗学言说构成了有效的交流与对话,但实际上,胡适与梁实秋谈论的诗学问题并不在同一层面上。时过境迁,梁实秋面对的诗学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于胡适在新诗运动初期面临的诗学问题。在梁氏的理论体系中,“白话”作为语言之一种,仅仅是新诗的实体材料,是新诗创作的语言工具。而诗之为诗,则必须遵从诗的艺术与诗的原理。因此,在讨论了“白话”与“诗”的不同侧重之后,梁氏以多数文字讨论了新诗与外国诗的关系,新诗的格律与格调、新诗的音节与重音等有关新诗创作的艺术法则。作为梁实秋与徐志摩的通信文章,发表于1931年《诗刊》创刊号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在对新月派前期的格律实验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对后来者也产生了莫大影响。有关新诗的理论论争,也由工具、载体的外部深入到新诗艺术原理的内部。
但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抛开梁实秋对早期新诗运动的片面理解,胡适早期的诗学言说实际上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开阔的诗学场域。在梁氏的理解中,“白话”与“诗”是不同性质的理论问题,因此,二者可以割裂开来,从而将白话新诗的问题简化为“诗”的问题。但在胡适的新诗架构中,白话新诗作为整体性概念,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当梁实秋轻易地将“白话”问题“悬置”,将白话新诗想当然地视为对外国诗的模仿,梁氏其实已经脱离了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语境。而在胡适这里,新诗固然掺杂了对外国诗的借鉴与模仿,但新诗诞生之初的问题首先不是模仿与否的问题。恰恰相反,早期新诗运动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白话新诗与古典诗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尝试集》中虽有几首译诗,《尝试集》的新诗创作中也能找到外国诗的蛛丝马迹,但在《尝试集》的序言中,胡适对外国诗的言论几乎是一笔带过。在胡适的笔下,有关白话新诗的所思所想,与梁实秋的论述几乎是截然不同,呈现出一副别有意味的面貌。
在《尝试集》自序中,胡适开篇便说道:“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彻。我现在自己做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作诗。”(5)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页。随后的长篇大论,胡适完整回顾了有关白话新诗的动因。与梁实秋不同的是,一方面,胡适承认自己“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6)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第17页。,但另一方面,胡适记忆犹新的依然是同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诗友的唇枪舌战。在激烈的争论中,“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区分与化合问题成为关键分歧所在。梅光迪在指责胡适的通信中指出:“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7)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第19页。在梅光迪等恪守古典诗学规范的诗人看来,“白话诗”之所以不是“诗”,原因不在于“白话诗”对外国诗的借鉴与模仿,其根本原因是“白话诗”并未遵循古典诗学的审美标准与评价体系。因此,胡适提倡的以“白话”为“诗”才遭到梅光迪等人的愤怒指摘,并搬出“诗文两途,古已有之”的古老诗训。
由此可知,梅光迪所谓的“诗之为诗”,与梁实秋所谓的“诗之为诗”截然不同,二者代表了两种互不干扰的诗歌范式。而胡适此时面对的问题,并非梁实秋所谓的“白话诗”是否符合“外国诗”的标准问题,而是“白话诗”如何面对古典诗学评价体系的问题。因此,当梅光迪提出“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之时,胡适自然不能服气:“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8)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第25页。因此,面对梅光迪等诗友的指摘,胡适的反应恰如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描述,一面指出古典诗学资源的缺陷,表达其对古典诗学的不满,一面又要在古典诗学系统内部找到自身的话语资源,以证明自己大有来头:“‘诗之文字’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峨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9)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第20页。
正是在同任叔永、梅光迪等诗友的书信论争中,胡适在对外国诗歌进行借鉴与模仿的同时,逐渐将白话新诗的起源置于“横向移植”与“纵向继承”的双向传统之中。甚至可以说,在胡适的理解中,对“纵向继承”的重视大大超过对“横向移植”的申诉。毕竟,梅光迪等诸多论争者均是以古典诗学的评价标准对白话新诗进行诘难,这就使胡适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精力思考白话新诗与古典诗学资源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赴美留学接触外国诗之前,胡适已经作出两百多首接近白话新诗的“古典白话诗”,这都得益于对白居易、杜甫等古代诗人的阅读与接纳。随着与梅光迪等论争的日趋激烈,胡适对白居易、杜甫等古代诗人的借重也日趋加重。也就是说,不论是还未明确形成“白话新诗”意识之前,亦或是在论争中逐渐形成明晰的“白话新诗”观,与对外国诗的倚重相比,胡适更多依赖于对古代诗歌的真实体验。因此,当胡适日后在《白话文学史》中大谈“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10)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218页。时,抛开结论的对错,这不是对白话文学史简单的凭空架构,而是蕴含着胡适个人的阅读体验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学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杜甫等具有白话倾向的古典诗人得以进入胡适的理论视野,胡适进而将其转化为新诗合法性的古典资源。
二
通过将白话从古代传统中分离出来,在文言与白话的二元结构中,“被发明”的白话在胡适笔下逐步取代了古代文学中以文言为中心的传统。在实际操作中,白话之所以能取代文言成为新的传统,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文指出,面对任叔永、梅光迪等友人的指责,胡适在指出古典诗学固有缺陷的同时,又要在古典诗学内部建构白话新诗的合法性地位。即便胡适为白话文学勾勒出源远流长的历史图景,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白话文学传统的勾勒也仅仅确立了白话新诗的历史合法性而已,白话新诗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优于古代诗歌?白话新诗在哪一层面具备古代诗歌无可比拟的优势?更进一步,白话新诗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在历史的合法性之外建立自身的现实合法性?这才是白话新诗能够取代古代诗的关键所在。
1919年,胡适在为“双十节纪念专号”所写的文章中对白话新诗的历史做了长篇回顾,在这篇著名的《谈新诗》中,胡适明确指出了白话新诗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辩证关系:“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正“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11)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160页。在胡适的宏大构想中,“白话”仅仅是“白话新诗”的第一步,其重心却落在了“形式”与“内容”的连带作用上。这一看法与梁实秋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的表述拉开了差距,二者最终的指涉性更是截然相反。通过对初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反思性批判,梁氏将新诗的发展路径导向了诗歌的艺术本体,是一种“文学本体论”的诗学范式。而在胡适的理解中,之所以会有白话新诗对古典诗歌的取代,其根本原因则是白话新诗的现实指涉性远远超越了古典诗歌的容纳范畴,是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构想。
实际上,早在1916年同梅光迪的论争中,胡适有关白话新诗现实指涉性的理解便表现得明明白白。在梅光迪“诗文两途”的指责之后,胡适便在回信中说到,“今人之诗(“今人之诗”应指当时人创作的古典诗歌——笔者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因此“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12)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0卷,第19页。这段话清晰地表明胡适对白话新诗的构想并非仅仅是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归根结底,语言形式的变异使诗歌具有更强的现实指涉性,同时也更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与接纳。在此论争之后,胡适更是写下一首名为《沁园春·誓诗》的词来明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鉴于漫长的历史岁月,古典诗歌积淀出一套行之有效但又坚若磐石的话语修辞,无论“伤春”“悲秋”,亦或“月圆”“日落”,在胡适看来,这些浓缩了古典审美与古典意识的形式与修辞早已经脱离了彼时的历史语境,而当下诗歌对“伤春”“悲秋”的肆意模仿则是“无病呻吟”的恶习,空洞如无物,同社会现实没有任何的关联。因此,与其选择在古典诗歌的荣耀下“从天而颂”,不如逆天而行,在新时代创造崭新的时代话语“制天而用之”。
表述上的“断裂”彰显出胡适对待古代诗歌的决绝态度。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断裂”的言说却不得不时时向古典诗学资源“借势”,同古代诗歌发生各种或明或暗的关联。正如胡适将古代文学话语划分为文言与白话两个系统,在胡适看来,古典诗歌在内容上同样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其中一派以“伤春”“悲秋”式的“无病呻吟”为主,另一派则“言之有物”,其诗歌创作具备更多的现实指涉性。更重要的是,在胡适的理解中,诗歌是“无病呻吟”亦或“言之有物”,恰恰同语言上的“文言”与“白话”、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构成某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因此,面对以律诗著称的杜甫,胡适的论述简直大逆不道:“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意儿。”(13)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500页。在胡适看来,“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艺儿而已”。(14)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502页。胡适指出,律诗的最大问题在于“杂凑”。由于有格律、押韵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致使律诗“很难没有杂凑的意思与字句”,(15)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502页。这就使律诗往往有一两句是好诗,但整体上较为薄弱。如果从所指层面理解胡适的表述,这也意味着律诗只有少数诗句有表情达意的作用,多数诗句则属“无病呻吟”的范畴。因此,当杜甫打破了律诗的形式桎梏,“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之时,便得到胡适的青睐。
在对杜甫的律诗创作大失所望的同时,胡适又指出“杜甫是唐朝的第一个大诗人”,杜甫之所以伟大,则是因为杜甫的好处“都在那些白话化的诗里,这也是无可疑的”。(16)胡适:《国语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60页。更进一步,之所以“白话化的诗”使得杜甫“伟大”,原因在于“白话”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也不是贵族文学写得出的,故杜甫的诗不能不用白话。”(17)胡适:《国语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60页。在这里,“白话”与“现实”几乎是对等的关系,因为要写出社会的现实与苦痛,所以必须要用白话,反过来说,也只有白话才能写出社会现实的苦与痛。从对“白话”的鼓吹到对“现实”的推重,胡适对新诗的形塑由诗歌的语言层面过渡到诗歌的社会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唐诗的论述堪称慧眼独具,在他看来,所谓“盛唐”,其实应当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人同天宝以后的诗人有着“根本上的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18)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464页。
仔细考察这段字数不多的文字,其中至少涵盖了文学与时代、浪漫与写实、文学的功与用以及文学进化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将“盛唐”诗歌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段,充分显示了胡适敏锐的治学思维。更进一步,胡适的划分并不局限于“盛唐”,这种划分甚至涉及到整个古代诗歌,涉及到古代诗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诗学态度与诗学意识。甚至可以说,从杜甫开始,个人的浪漫感怀抒情开始逐步为沉郁顿挫、忧愤深广的涵盖了更加广阔的现实经验抒写所取代。因此,当胡适发现杜甫不仅在“白话”上为新诗的架构提供了话语资源,其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容纳更是同白话新诗的构想完全契合,由此,“被发明的传统”在不期然间再次融入白话新诗的整体建构之中,成为孵化白话新诗不可缺少的古典资源。当然,不论是“白话化的杜甫”亦或是“现实性的杜甫”,虽然二者代表了“形式”与“内容”的不同维度,但在胡适的理论框架中,二者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相应的是,当杜甫作为古典诗学资源进入白话新诗的历史性建构,也就注定了白话新诗并非简单的“白话革命”,而是一场由“形式”深入“内容”,由“语言”撬动“现实”的整体性的诗界革命。
三
相较于胡适对“白话化的杜甫”与“现实性的杜甫”的提倡,胡适对“打油诗的杜甫”的论述似乎遭到了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原因可能有二:首先,胡适对“打油诗的杜甫”的论述过于乖谬,就其实际接受状况而言,这一观点几乎没有得到后来者认可。其次,相较于对史料与史实的推重,胡适对杜甫“打油诗”的研究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与阐释性,一旦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无法有效转化为白话新诗的古典诗学资源,这一言说便在史实性与功用性的双重层面遭到历史的遗弃。但对研究者而言,这恰恰是问题的开始,作为“打油诗的杜甫”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知识资源?作为“打油诗的杜甫”又为何不被白话新诗所接纳,其被拒绝的原因何在?从拒绝作为“打油诗的杜甫”出发,新诗运动初期的新诗场域存在怎样的规范与禁忌?而作为新诗奠基者的胡适,又如何看待作为“禁忌”的打油诗?所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在对杜甫的现代性阐释中,胡适对打油诗的格外关注似乎不应被忽略。在写于1922年的《国语文学史》中,或许是时间所限,或许是构思不够纯熟,胡适仅用“杜甫很有一点滑稽风味”(19)胡适:《国语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62页。来形容杜甫的打油诗,随后便一笔带过。而到了作于1927年至1928年间的《白话文学史》,对杜甫“打油诗”的论述则上升为核心命题之一。在胡适看来,杜甫创作打油诗同性格相关,而杜甫性格中的滑稽因素则是“遗传”所致,这种性格中的滑稽、诙谐使得杜甫历经劫难仍能坦然面对,因此,杜甫“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20)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470页。更重要的是,打油诗与白话诗具有天然的血脉关联,无论杜甫创制的“新乐府”,亦或杜甫晚年的绝句与小诗,甚至是律诗中叙事意味较强的部分,胡适都将其纳入打油诗的整体框架内来论述。在胡适看来,杜甫创作了大量的打油诗用来遣闷消愁,“他做惯了这类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如《北征》)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21)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493页。初看之下,“嘲戏”与白话诗似乎没有必然关联,但在这里,胡适有关“形式”与“内容”的连带作用再次显现,打油诗之所以通向白话诗,原因在于打油诗中的“嘲戏”溢出了古典诗学范式的边界,在无形中打破了“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制约,逐步成为“白话化的诗”。正因为打油诗同白话诗的密切关联,胡适将杜甫的打油诗上升到整体性的高度,认为“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22)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493页。实际上,胡适对打油诗的论述远远超出了杜甫本身,进而将其视为整个白话诗系统的源头之一。在胡适对“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中,白话诗的来源主要分为民歌、打油诗、歌妓以及宗教与哲理四种,打油诗实际上就是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因为“嘲戏总是脱口而出,最自然,最没有做作的;故嘲戏的诗都是极自然的白话诗”,“虽然这一类的诗往往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然而他们却有训练白话诗的大功用”。(23)胡适:《白话文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第388页。
由此可知,胡适之所以对打油诗另眼相待,原因在于打油诗对训练白话诗的重大功用。与之相应,作为白话新诗最早的“尝试者”,胡适在其创作初期写作了大量的打油诗,这些集“游戏”与“尝试”意味于一身的“打油诗”,可以视为胡适有意于白话新诗的最初起点。因为包含大量打油诗在内,任鸿隽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尝试集》戏称为“一集打油诗百首,‘先生’合受‘榨机’名”。但有意味的是,在最终出版的《尝试集》中,打油诗反而石沉大海,一首未选,似乎胡适在有意抹除《尝试集》与打油诗的血缘关系。一面在《白话文学史》中逐步加强对“打油诗”的侧重,一面却在当下的社会空间中尽力消除打油诗与白话新诗的血缘关系。在相互龃龉、自相矛盾的文学实践中,胡适到底面临怎样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
有关《尝试集》的“自我净化”,姜涛有过详细考察。在姜涛看来,胡适最终将打油诗摈除在《尝试集》之外,似乎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打油诗毕竟属于私人间的游戏之作,“不足以承当赋予‘新诗’之上的现代公共化期待”;其次,“除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外,某种审美上的规约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4)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152页。这一论述可谓精辟,指出了新诗运动初期白话新诗复杂的历史语境。值得补充的是,“审美上的规约”,其具体指向应当是白话新诗对古典诗学资源某种程度的妥协。在两千多年的“期待视野”中,打油诗可以说是作为古典诗学体系的对立面而存在,强大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惯性使白话新诗在新诗运动初期面临举步维艰的历史境遇,其合法性地位一直饱受质疑。因此,胡适在《尝试集》中自觉将打油诗摈除在外,便意味着白话新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完全斩断其与“传统”藕断丝连、若隐若现的关联,或者说,白话新诗最初的“形塑”,是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相互交锋、相互妥协的结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外国诗歌的大规模引进,所谓“诗”的合法性问题,才逐渐由“古代诗歌”的审美标准转换为“外国诗歌”的评价体系,才有了梁实秋“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的言论。
但反过来看,胡适对打油诗的遗弃也很有可能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其“主动”的文学实践。从对“白话”的提倡到对“现实”的看重,直至胡适对打油诗的有意删除,这其中其实包含三个不同的文学维度,也涉及到“白话”的不同功用,其中的逻辑看似简单,实则微妙。在多数研究者看来,胡适新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对“白话”的提倡,从语言层面肯定胡适对“白话新诗”的贡献。但实际上,胡适之所以提倡“白话新诗”,恰恰在于“白话”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从而将“白话新诗”由“语言”层面深入到“现实”层面。但随着“白话新诗”的进一步发展,胡适开始意识到“白话”不仅只有“现实”的单一维度。作为“白话新诗”的首倡者与奠基者,“诗”的文学观念也在时间与实践的双重反思中内化为胡适的思考对象,加之梅光迪、胡先骕等对“白话新诗”的冷嘲热讽,在“现实”的社会功用之外,“诗之为诗”的“诗性”也逐渐成为胡适的关注点。因此,当胡适回头审视曾经的新诗创作,对打油诗的舍弃也是理所当然。而“删”这一主动性的“自我审查”行为,或许也表明胡适不仅是对古典诗学规范的妥协,更是对“新诗”诗学体系的主动建构。“主动”与“被动”相互纠缠,“吸纳”与“舍弃”难以分割,似乎暗示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在新诗运动初期暧昧而复杂的关联。
此外,打油诗与“现代公共化期待”的关系问题似乎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形式”与“内容”的连带性是白话新诗得以建构的前提,随着新诗对古代诗歌“语言”“格律”上的突围,新诗的现实指涉能力远远超越了古代诗歌。但另一方面,“形式”与“内容”的关联既非亦步亦趋又非一一对应,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超前、滞后甚至脱轨,二者的适用范围、现实边界也并非完全等同。因此,打油诗虽然也有“讽喻”的社会功用,但更多的是友人的唱和、自我的调侃以及对无关紧要事物的自得其乐,而这恰恰是胡适极力排斥的诗歌功能,胡适在《尝试集》中对打油诗的排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新体式”与“旧功能”的“交错”不仅意味着新诗运动初期新旧诗歌功能上的相互缠绕,同样也显现出新诗理论构造上的激进与偏差,打油诗的存在便显现出胡适新诗理论架构中较为僵硬、不够灵活的“盲区”。
当然,“盲区”的存在并非胡适的问题,自近代以来,“文学”与“现实”便命定般捆绑在一起,“欲凭文字播风潮”似乎成为文学创作的恒定样态。古代诗歌之所以惨遭淘汰,恰恰因为古代诗歌无法承担此种责任。就打油诗而言,打油诗的书写指向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观照是打油诗充满活力的基本保证,而发展到白话新诗阶段,由于白话新诗必须肩负起“言志”“载道”的重任,对社会现实的倾向性逐渐压倒了打油诗对日常生活的嘲戏与调侃。在白话新诗从“民间”走向“广场”的过程中,打油诗因其特有的民间性不得不被排斥在外。此外,打油诗多是亲朋故友间的自娱自乐以及面对苦难时的自我嘲戏,更多指向个体以及私人空间。而在胡适的设想中,公共性与现实性是白话新诗得以存在的根基。因此,“打油诗”的唱和功能、交际功能、游戏功能、自我调侃等诸多功能便成为白话新诗的排斥目标。在白话新诗从密闭性的私人空间逐渐开放为一个自由交往、讨论现实话题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白话新诗的公共性逐步取缔了打油诗的私人性。起源于打油诗的白话新诗最终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打油诗的诗歌路线,无论是在诗歌的审美能力亦或是诗歌的实际功用方面,二者的分道扬镳也意味着新诗诗学体系的逐步规范。因此,当胡适在《尝试集》中完全抹除了打油诗的存在,实际上也意味着白话新诗对诗学规范的捍卫。随着最后一个暧昧地带的取消,白话新诗的边界逐渐清晰,合法性地位得以确立。
但颇具意味的是,虽然胡适在《尝试集》中取消了打油诗的合法地位,却又在《白话文学史》中对杜甫的打油诗大肆扩写、大加赞扬,相互龃龉的文学现象似乎折射出胡适彼时的蒙昧状态。胡适不得不在语言层面上承认打油诗是白话新诗的根基,但又要在功利层面上否认打油诗的现实合法性。因此,作为“现实话语”的《尝试集》虽然抹除了打油诗的存在,作为“文学史著作”的《白话文学史》依然保留了打油诗的一席之地。当然,《白话文学史》对打油诗的借重有着为白话新诗重述历史的考虑,但似乎也不能忽略胡适的个人趣味,在公共性与现实性之外,胡适选择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打油诗的民间性、个人性留下了可待开发的私人空间,从而避开了“文学”与“现实”最为决绝的对峙,这似乎也意味着胡适在白话新诗上的游移不定。毕竟,对白话新诗的建构并不能以对古代诗歌的完全驱逐为代价!白话新诗也不应当只是在现实与公共的困锁中辗转腾挪,而应当在古今中外的时空中大显身手,在多方吸纳中展示自身的丰富与复杂。历史的发展似乎也预见了胡适的暧昧态度,虽然白话新诗在理论架构上对打油诗予以驱逐,但在新诗的实际发展中,打油诗不仅多次出现在胡适笔下,也受到多数诗人、作家的钟爱。归根结底,古典诗歌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白话新诗也不仅仅是“启蒙”与“革命”,“体式”与“功能”上的新与旧,最终要回归诗人的个体行为。当然,周作人1934年刊登于《人间世》的“五十自寿诗”以及其后诸多“和作”更加说明了打油诗的活力与魅力,而胡适即为当事人之一,这一“历史的倒退”似乎饱含别样的意味。除此之外,由打油诗引发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甚至是革命的反映,在在显示了打油诗在“私人性”之外的“公共性”“现实性”,这恐怕是胡适万万没有想到的。
本文以胡适的杜甫书写与新诗言说为考察中心,从白话、现实与“打油”三个层面考察二者难以厘清、欲说还休的复杂关联。从新诗运动的语言变革起步,胡适在历史重述中将杜甫改写为白话诗人,“白话化的杜甫”反过来又为新诗运动初期的语言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而从“白话化的杜甫”深入到“现实性的杜甫”,白话新诗反思古典诗学的同时,又承继了古典诗学的优良传统,在语言革命之外,白话新诗开始重视自身的现实使命。“白话”与“现实”的相辅相成为白话新诗勾勒出宏大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看似和谐的设想背后,胡适对打油诗的暧昧、游移在在显示了白话新诗的历史局限,新诗运动的现实性与游戏性、白话新诗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甚至是诗歌本体意义上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在社会现实的重压下衍化为结构性分裂,这一切都昭示出新诗运动初期复杂的历史语境。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断裂”来定位自身的白话新诗,最终却是在同“传统”的互文中觉醒为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在“传统”的“滋养”与“桎梏”中建构了新诗运动初期的白话新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胡适的杜甫书写与新诗言说,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在不可思议中成为相互言说的能指与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