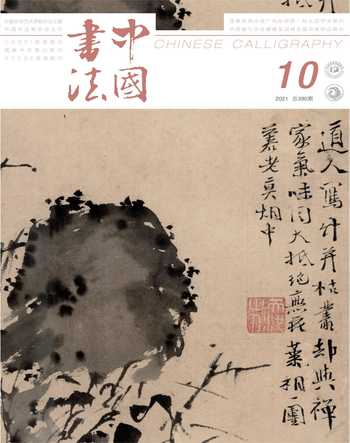魏晋人物品藻与书法品评类型
阴胜国
关键词:人物品藻 书法品评 审美意识 意象式批评
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美学始于魏晋的人物品藻,美学的概念、范畴、词汇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1]与汉代政治性的人伦鉴识不同,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已从实用性转换为艺术性,以超功利的审美眼光审视人的本然质性,重视人物的风仪神理,进而关注个体本身的个性与情感。正是这种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转变,为魏晋六朝的美学与艺术鉴赏批评提供了契机。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物品鉴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自觉和提高,直接而广泛地影响到艺术的欣赏和美学的发展。从思维形式到批评风格,从批评方法到概念术语,魏晋六朝的艺术批评深刻地浸染了人物品藻的痕迹。
『筋』『骨』『肉』的审美内涵
魏晋时期,有关『筋』『骨』『肉』的讨论成为书法理论的重要议题。作为抽象的审美概念,『筋』『骨』『肉』主要是用来说明书法点画线条形态的本质特征。邓以蟄在《书法之欣赏》中说:『骨与筋为笔画成立之根本,无此二者则无所谓笔画,亦无所谓书法也;故称之为笔画之实质,无不宜也。有此实质,然后书法乃可开始。』[2]由是言之,『筋』『骨』实为书法点画线条成立的根本,而『肉』同样如此。然而,『筋』『骨』『肉』概念的提出,与汉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密切相关。汤用彤曾指出:『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3]尽管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由于玄学的化育而重视人物内在的『神明』,但仍未脱离两汉依相术原理论『筋骨』的联系。毋庸置疑,魏晋时期书法理论中提出的『筋』『骨』概念,实际是把原本属于品鉴人物外在可感形体的术语直接移植到书学领域,进而将书法视为与人体结构相类似的审美对象。
从书法理论的演进来看,东汉末期的崔瑗、蔡邕等人多以『象』和『势』作为论书的核心概念,并未明确提出『筋骨』问题。检索现存的书法理论文献,具有审美意义的『筋』『骨』观念的提出,大约在曹魏至西晋间。据张怀瓘《书断》记载,魏末的韦诞在评价东汉杜度的书法时已明确使用『骨』的概念:『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我得伯英(即张芝)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4]南朝王僧虔在《论书》中亦曾转录卫瓘这段评语,但略去『靖得其肉』句。《晋书·卫瓘传》亦载:『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5]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颇为重视书法中的『筋』『骨』『肉』的问题,但对概念的说明尚显模糊。在此基础上,东晋的卫铄则对『筋』『骨』『肉』概念的内涵做出相对具体的论述:『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6]在卫铄看来,所谓『骨』意味着书法线条的刚健有力,『肉』则喻指线条形态的臃肿肥腴;在两者之中,卫铄显然倾向于前者,原因在于『骨』象征着以丰沛旺盛的生命力作底里的雄健刚强的品格。所谓『筋』的内涵与『骨』相似,均系属『力』的美学范畴;但是,『骨』更偏重刚性,而『筋』则偏重韧性,正如刘熙载所指出:『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7]简而言之,『骨』强调刚健之美,『筋』强调弹性之美。『筋』和『骨』虽有不同的品性,但二者相依互成,『骨』的植立离不开『筋』,『筋』的萦旋依附于『骨』。正因如此,卫铄提出了理想的审美标准:『多力丰筋』,即书法线条表现出刚柔相济之美,充溢着内在的生命力量,方能达到理想的『圣』的境界。
东晋至南朝的人物品评由『骨法』而及『神理』,将人的体骨形貌与才性修养、风神韵度结合起来,并以『风骨』概念指称人诚中而形外的精神风貌。与此相联系,东晋以后的书法理论对『骨』的重视要远超『筋』和『肉』,并与『气』『力』结合成『骨势』『骨力』『骨气』等范畴。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评王献之书法时说:『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8]王僧虔在《论书》中谓:『郗超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9]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言:『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10]从这几例评语可见,南朝时期的书论家在保持『骨』的原义基础上,强化审美评价的成分,形成『骨势』『骨力』『骨气』等概念,并且多与『媚趣』『紧媚』等范畴对举。《世说新语·品藻》中记载:『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11]在人物品鉴中,所谓『骨气』主要是指内在气性与外在体骨之间相依互成的精神性品格。与此相似,袁昂评价蔡邕的书法『骨气洞达』,所指称的亦是点画线条所蕴含的既『抱骨』又『含筋』的品格。邓以蛰对此做出详细解释:『以洞达释骨气,中透为洞,则中透者正谓骨也;洞谓骨,则边透为达者谓气可知也。边透似与含忍之力不无关系。何者:骨多之笔,必锋露劲利,正所谓果敢之力之表现也;若边透云者,必为锋当正中而墨浮两边……筋为含忍之力,则边透莫非筋矣。』[12]由是而言,『骨气』所指称的是书法点画线条刚劲雄强、真力弥漫的特征,其生成与作者的郁勃志气和丰沛生命力有密切关系。
人物品藻的价值取向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不仅深刻地塑造着书法『筋』『骨』『肉』范畴,更重要的是人物品评对人物内在本然质性的探讨,直接提示出书法作品的深层意蕴。正始以后,士人群体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学术风气由政治上的清议转为形而上的清谈,人物品鉴遂逐渐转向对人的生命本体的探讨,以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为思想基础,重视玄学所说的『神』或『神明』的表现,提出形存神立、瞻形得神的品评原则。正如徐复观所指出:『当时艺术性的人伦鉴识,是在玄学、实际是在庄学精神启发之下,要由一个人的形以把握到人的神;也即是要由人的第一自然的形相,以发现出人的第二自然的形相,因而成就人的艺术形相之美。而这种艺术形相之美,乃是以庄学的生活情调为其内容的。』[13]作为『第二自然』的『神』,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抽象的生命精神,而是魏晋名士追求的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所外显的玄妙难言的情感表现,也就是由具体的生活细节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情调。从价值取向上看,魏晋人物品鉴对内在风神气韵的重视直接渗透到魏晋六朝的书法品评之中,不仅强调作品表现出来的超越有限形象的精神境界,而且建立起传统书法批评中的『意』『妙』『神采』『气韵』等重要审美范畴。大体而言,魏晋时期的书法审美观念强调『意』的表现,而南朝时期则把对『意』的泛化体认转化为更具概括性和系统性的审美范畴。
随着魏晋时代书体演变的完成,理论家们对于书法的认识和理解已不再局限于文字学范畴与实用价值,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受到普遍关注。曹魏时期,锺繇首先提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主张,强调了书法创作中人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个体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导致书法审美从自然物象的拟喻推演至对主体内在之『意』的抉发。作为精神性审美范畴的『意』,在东晋王羲之的书论中被突出强调:『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14]从这段论述来看,王羲之已经摆脱『观其法象』的取象思维,把主体内在的『意』提到首要位置。『王羲之说法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直接以书法的点画为「意」的表现,并且指出这「意」是「言所不尽」的。以书法的点画为「意」的表现,也就是以书法的点画为个体的内在心灵的表现,而超越了历来的一切形象的比拟形容。』[15]《全晋文》中收录王羲之谈及书法之『意』的文稿,均表达出这种审美内涵。
在继承魏晋理论的基础上,南朝时期的王僧虔、萧衍、袁昂、庾肩吾等人围绕东汉以来的名家及其作品展开全面探讨。他们在品评名家、作品优劣的过程中,把对东晋时期潜在的书法审美观念转化为显性的批评概念和审美范畴。这在王僧虔以『神』为主的批评系统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在王僧虔的品鉴美学体系里,不但有「筋」有「骨」,而且有「形」有「神」,构成了以「神」为主的有机生命系统。它一方面和以往的哲学精神相渗透、融合,还继承了汉、魏、晋的人物品鉴标准;另一方面又和以往的绘画美学相沟通、相联结,发展了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理论,明确地制订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品评标准。』[16]王僧虔在书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书法艺术的『神采』和『形质』的关系做出经典的阐述。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17]所谓『神采』即是书法所表现与『道』相通的情感、精神,所谓『形质』是指作品的笔墨形态。王僧虔在关于『形』『神』的经典表述中,不仅将『神采』置于品评体系的首位,而且主张『神采』与『形质』两者必须兼善,『形质』是寄寓『神采』的形式,『神采』是统摄『形质』的精神。此外,王僧虔在《论书》中大量运用『妙』的范畴表述书法的形质,要求书法体现出笔意之妙。他评价孔琳书法:『但功夫少,自任过,未得尽其妙,当劣于羊欣。』评价锺繇书法:『锺公之书谓之尽妙……铭石书,最妙者也。』评价卫觊书法:『善草书及古文,略尽其妙。』[18]在这些评价中,『妙』被描述为超脱有限形象的非实体性存在,强调书法艺术需从形式法则的物化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人的精神、心灵的自由审美表现。
人物品藻的思维方法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重视人物内在的风韵神理,然而人物内在的精神气韵玄虚而难以捉摸,时人提出『以形求神』『瞻形得神』品评原则,以此解决人物品鉴上的虚无难言。东晋葛洪曾直言:『区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为。』[19]人的精神气质『甚微而玄』,他人对此的识见并不能诉诸理性的分析判断,只有依靠声气相通、心灵相映的直觉体验,借助具体的、直观的形象进行整体品鉴。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指出:『凡题目人者,必亲见其人,挹其风流,听其言论,观其气宇,察其度量,然后为之品题。其言多用比兴之体,以极其形容。』[20]这种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和形象譬喻的传达方式,在南朝时期的书法批评中被广泛运用。
南朝时期,庾肩吾在《书品》中道书法精神内蕴的微妙难名:『敏思藏于胸中,巧态发于毫铦。詹尹端策,故以迷其变化;《英》《韶》倾耳,无以察其音声。殆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是以鹰爪含利,出彼兔毫;龙管润霜,游兹虿尾。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21]尽管书法艺术的无尽神韵难以言宣,但是魏晋六朝的书法批评参照人物品评的方式做出『不可言说的言说』。南朝时期,仿照人物品藻最为相似的是袁昂的《古今书评》和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在这两篇品评文本中,对于古今书家艺术风格的品评几乎全部以自然物象、人格精神的意象来形容比拟。现以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为例,如采用自然景物的意象来比拟:『锺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更多的则采用人格精神的意象来形容:『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22]显然,这种『极其形容』的意象式批评汲取了人物品藻在遣词设喻方面的丰富成果,以自然和人物的具体意象来表达抽象的批评理念,用精炼玄远的语言对作品风格作整体性把握。
从思维特征来看,南朝时期以自然和人物为喻的意象式批评,对书家及作品的认识往往省略分析、推理、论证的过程,直接以精简浓缩的诗化語言做出结论式判断。对于判断的形成机制,张伯伟曾指出:意象批评『是由「目」而「想」,它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批评家从大量具体作品出发,形成了某种抽象的概念,然后再回到作品,用一具体的意象予以说明』。[23]批评家面对具体作品,『睹物象以致思』,即通过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形成与批评对象相类似的意象,进而通过类似感受的描绘来把握形象,体其神韵。意象式批评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直观的特点,在表现形式上则是意象化的概念。正是这种体验性、不确定性,遭到了后世诸如李嗣真、孙过庭、米芾等人的讥讽和指责。孙过庭在《书谱》中曾言:『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24]米芾《海岳名言》开篇便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25]然而,这种意象比况的批评方式却有着『一言常使见全身』的功效,能够以高度凝练而富于形象意味的语言把难以言传的审美感受完整直观地传达出来。『它是批评家对于作品风格的整体把握,是在作品的实际体验中所得到的完整印象,是想象力对于理性的投射。因此,这种用意象的语言所传达的经验就不是理性的分析所可以取代的。』[26]意象式批评的妙处在于,以『勿泥其迹』的感性直观形式,不落言筌地把审美感受深刻地传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