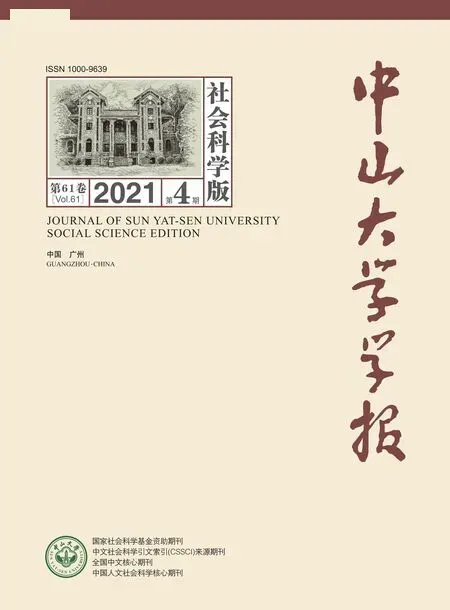摩尼教审判绘画二帧*
[匈牙利]康高宝
在2006年确证大和文华馆所藏之画为摩尼教画像之前,仅有一幅画作与审判有关,即MIK III 4959的背面①Hans-Joachim Klimkeit,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Leiden:Brill,1982,p.37.Gulácsi Zsuzsanna,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Turnhout:Brepols,2001,pp.79-81.在都柏林的会议上吉田豊教授提到另一幅含有审判景象的宇宙图。我曾以The Affili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Judgment Scene in the Cosmology Painting(《宇宙图中审判景象的归属及意义》)为题在奈良的一个会议上讨论两幅画在审判画面上的不同(MIK为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的缩写,该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已并入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但其以MIK标注的藏品编号仍为学术界所沿用)。。该残片出自9至10世纪间的吐鲁番,目前藏于柏林达勒姆区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大和文华馆所藏画作则是出自13到14世纪的浙江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尽管两者存在种种差异,但两幅画作却包含共通的母题:都表现了判官及其身前站立的两个人物②MIK III 4959 缺损,但左侧部分画的是另一景象。古乐慈指出:“平等王左侧第四位人物是另一画面开始的标志,其肩部状态表明他处于另一状态中,即目前画面缺失的那一部分。”参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 of a Chinese Manichaean silk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Yamato Bunkakan,Nara,Japan”(稿本),2009,pp.8-19。,且这两位身不着衣仅用布裹腰。然而这两幅画作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来,因此在判官、其周遭人物及他们之下的人物的刻画上大相径庭,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本文将首先分说这两幅画作,对其中人物提出新解。我将基于宋元绘画传统、摩尼教及佛教文献和表现形式上的内在画像学逻辑展开论述③最后这种方法的准则或仍存在争议,但必须指出的是,先行研究并未清晰地表现出它们充分运用了画像学分析这一手段。。
一、MIK III 4959 V
MIK III 4959 V(图1)表现了三个人物:左侧那位身着红袍,面朝右侧,左手食指竖起,右手持棒。其前站立两名几近赤裸的人物,仅腰间缠以布条,一人脖子上环绕带角动物。两人之间有一对裸露脚掌,其上是一捆绿色谷物。我将集中论述这几处有些古怪的部分,我认为脚掌及这捆谷物提供了一条线索,指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

图1 摩尼教典籍插图(MIK III 4959 V),彩色描金纸本,11×8.2 厘米
该残片由勒柯克公布,但他并未联系到审判。勒柯克对空中的脚掌踌躇难决,作出这样的解说:“肉色脚掌的意义不详。它们或许代表某个人的足迹……这个人的脚步向左而行?”在此勒柯克做了一个阿兹特克象形表意文字的类比(Aztec analogy)①Albert von 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Ergebnisse der Kgl.Preussischen Turfan Expedition.Vol.2.Die Manichäischen Miniaturen,Berlin:D.Reimer,1923,p.61,8b.。克林姆凯特是首位指出该画为审判景象的学者,他指出左侧人物为判官,右侧的两个人物则是被审判者,不过他也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右边的两个人物可能代表的是同一个人。至于他们之间画面表现的内容,他有如下说法:“他们中间有一束绿色植物及两个肉色足印在下面。让人觉得似乎暗示一种两个人物间的因果联系(或许指的是业[karma]?)。”②Klimkeit,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p.37.克林姆凯特认为所看到的其实是第一个人的脚印,实际上指代他的过往行为。这建立了两个人物间的联系,但他的假说却未论及那束植物。
在古乐慈关于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摩尼教绘画的书中,她基本接受了克林姆凯特的主要说法,即该画为审判的画面,但在具体的解释上却不完全认同③Gulácsi,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p.81.关于该残片在原写本中的位置,请见Gulácsi,Mediaeval Man⁃ichaean book art: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and Turkic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from 8th-11th century East Central Asia,Leiden:Brill,2005,pp.163-165。正面文字为赐福功德主的祷词,见Hans-Joachim Klimkeit,Gnosis on the Silk Road,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New York:HarperSanFrancisco,1993,p.275;Gulácsi,Manichaean artin Berlin collec⁃tions,pp.227-228。。在对大和文华馆摩尼教绢画的专门研究中,古乐慈提出了一个新说:“画面背景上可见两个腰间缠布的人物中间有一对脚印和一捆绿色谷物茎秆,很可能表示的是一位已被审判过的人,人已消逝,仅留其足印和他在收获行为(摩尼教选民所禁止的行为)中所犯罪业的象征。”此外,在一个脚注中,古乐慈为这一解释提供了依据:“将这一部分画面视为前景后面的中景乃是因为脚印的位置比两位腰间缠布的人物的脚要高。”④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18,n.46,p.28.日译本《大和文華館蔵マニ教絵画にみられる中央アジア来源の要素について》,《大和文華》119,2009年,第28页及第34页脚注46。古乐慈因此认为两个人物之间有第三个人,即现在看不见的那位,其脚掌象征着他的离开,其罪业在画中用新鲜植物象征,代表收获之罪。
在此我想提供另一种解释,因为我认为画面中的内在逻辑使得后一种解释似是而非。上面古乐慈提到的两位人物,在判官前排成一队,很有可能脖子缠有带角兽首的那位在判官之下,也就是说处在画面的现在时叙述(narrative present)中。而等待审判的第二位,他的顺序应该是在第一位之后,则处于画面的未来时叙述(narrative future)①对此古乐慈的看法是“图上所示后面那个人正等待审判,他正好在画面的右侧边缘上”,见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15;日译本第34页。关于“叙事绘画”这一类型,参见Julia K.Murray,“What is‘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Art Bulletin,Vol.80,No.4,1998,pp.602-615。。因此,介于画作“现在时”和“未来时”中间的,应该不会插入一种过去时的状态,脚掌的位置抬高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脚掌是位于判官左侧的话,那古乐慈的解释就更可信。
我的看法受前一种解释启发而来。克林姆凯特和古乐慈都认同第一位半裸人物的罪业由其脖子上悬挂的带角兽首表示。古乐慈倾向于这代表的是食肉的罪②Gulácsi,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2001,p.81,n.75.,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过我个人认为如画所示,更有可能指代杀害带角动物的罪。这或可由没有任何指向口即“吃”这一行为的事实证实,并且人物的手缚于身后,暗示其罪由双手犯下。同时显然的是双手绑缚并非这些人物的典型姿态,毕竟第二位人物无此特征。相反的是,他双手的活动看起来表明双手并未犯下罪行。因此第一位人物或许双手做出罪业,罪本身可能是斩首、杀害某一种家畜。从逻辑上而言当然也涉及食用杀死动物之肉的罪,只是这在画作中并不明确,或许这不是最恰当的假设,但我从根本上同意古乐慈的观察。如果在第一个情境中所见的缚手及显露出的杀生都有所指示的话,那么同样适用于第二个情境的假设便不那么牵强附会了。
倘若我们猜测在第二位人物之前的“物品”事实上从属于他的话,那么就有如下的解释:他的双脚踩在新鲜的植物之上,因此他的罪可能是破坏明性(the Living Soul),即损毁草木。脚掌指向践踏这样的行为,而植物是象征罪业的对象。这一解释正好也与第二位人物的双手状态吻合,表明他与第一位相反,双手未曾犯下罪行。在此我转引数条摩尼教材料,它们基本都是从忏悔文中来的,其中明确地提及践踏土地或植被是一大罪过:
无上明尊,我等业行不圆,愆咎缠身,所欠甚多。乃因念、语、业中有无羞耻之贪魔阿兹(Āz),仿若以其眼睹之,用其耳听之,用其舌言之,用其手取之,迈其腿行之,于五分法身光中,干湿二地,五类众生,五种草木中招致长久苦痛。③转译自英译本:J.Asmussen,Xustvnft,Kopenhagen:Prostant apud Munksgaard,1965,pp.198-199。另参Xustvnft XV C,Xustvnft III C。
第七种(作者注:伤害干地明性):踩踏于活物之上,即那些踩踏干地的活物。④文书M 12 V 行9—13,参W.Sundermann,“Die vierzehn Wunden der lebendigen Seele”,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2,1985,p.295。
行于道者慎观其步,以免误踏光之十字(Cross of Light),损毁草木。⑤转译自英译本:I.Gardner,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Leiden:Brill,1995,p.208,17-19 ;另参A.Bhlig &H.J.Polotsky,Kephalaia I,Stuttgart:W.Kohlhammer,1940,p.208。
若人于土地上行走,则破坏其地,若活动双手,则坏清净气,清净气者,人类、禽兽、虫鱼、世间万物之明性也。⑥转译自英译本:M.Vermes(trans.)&S.N.C Lieu(comm.),Hegemonius:Acta Archelai,Turnhout:Brepols,2001,p.55。另参C.H.Beeson(ed.),Hegemonius,Leipzig:J.C.Heinrichs,1906,p.17。文书M 801a行577—582的句子理论上适用于此:“若我曾触摸过雪、雨或露水,或曾踩在地球的胞宫上,即某物发芽或生长之地,则造成了伤害(伤害一词的字面义为‘混合’)。”参W.B.Henning,Ein manichäisches Bet-und Beichtbuch,Berlin,1937,S.35,Z.449;Klimkeit,Gnosis on the Silk Road,p.140;另有译文稍异者见J.D.BeDuhn,The Manichaean Body in Disciple and Ritual,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44。上引文书原文为:y wfr'w'r nmb ps'wδ'rm z'y/zβrcy γyy kww/ rwwδ pyrwδ mn/ prywyδ wryδ pryδδ/'skw。I.Gershevitch,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Ox⁃ford:Basil Blackwell,1961,p.128,§864 曾对此句释读提出异议,他在脚注中讨论tγtyy 一词说道:“该句可能是说雪、雨或露水曾进入地球胞宫。”感谢吉田豊教授曾于2009年8月20日京都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他的意见,他认为该句大义为“我曾触摸过雪、雨或露水;它曾进入某物发芽的地球胞宫处,则混合由我而生”。
上引前三条材料都是出自吐鲁番发现的写本,与画作出处相同。因此受审判的两个人物至少是两类造业者:一位双手有罪,杀害动物;另一位以其脚损坏植物。此种情景不像是为了描述特定两个人的审判,更像是一般的说教,这一点可由人物没有特定面部特征看出,以此涵括更多罪的类型,那些对动植物犯下罪业的,以手或以脚犯下的。我们知道,不斩伐草木的禁律是摩尼教选民的基本戒条,奥古斯丁所述可证实:
他们相信听者的明性将返回到选民身上,或许是通过供给选民食物这条捷径,明性得以净化而不会迁居其他肉身。同时他们也相信其他明性将进入牲畜或者植根大地并由此得到滋养的万物之中。因为他们坚信,植物树木均属有情之物,当遭到毁坏时能感受到疼痛,但凡拔除或采摘,都是伤害荼毒。因此,他们认为清理即使是长有荆棘的田地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痴狂地把农业生产这一最无辜清白的营生也看成罪恶多端的杀戮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相信听者的这些罪愆是可以宽恕的,因为听者以这种方式供应食物给选民,意在奉纳给选民的神圣物资在他们的胃中得到净化,供品得到净化,由此奉献它们的听者获得宽宥。这样一来,选民自己并不在田地里劳作,不采摘水果,连一片树叶也不碰,却指望听者带来所有这些为他们所用的物品,一依他们自己愚蠢的思想,终身不劳而活,以他人犯下无数可怕的罪行为生。①《论异端》(De haeresibus)46.12。英译文见I.Gardner&S.N.C.Lieu,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89-190。另参Patrologia Latina(《拉丁教父著作集成》)42:37。
我们可据此猜测画中的人事实上都是选民,这是为什么伤害动植物将带来后果的原因,而从判官举起的双手可知其审判之严厉②参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18;日译本第28 页。Mani's pictures.The didactic images of the Man⁃ichaeans from Sasanian Mesopotamia to Uygur Central Asia and Tang-Ming China,Leiden,Brill,2015,pp.296-297。。毋庸讳言的是,任何对摩尼教图像遗存的解释都很难找到相关文献,特别是针对一件单独的残片,或多或少存在假说性,当我们谈论这一件或下一件画作都是如此,但是多种解释确实存在可能性高低的差异。
二、大和文华馆的三道图
(一)三道图的基本特征
大和文华馆所藏绢画三道图(图2)是在2006 年由吉田豊教授确定为摩尼教的一件绘画③Yoshida,“Discovery of Mani image in Japan”,Manichaean Studies Newsletter 22,2007,pp.21-24.吉田豊:《寧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図」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大和文華》119,2009,第3—15 页。Yoshida,“A newly recognized Manichaean painting:Manichaean Dan from Japan”,In:M.A.Amir-Moezzi,J.-D.Dubois,C.Jullien &F.Jullien(eds.),Pensée grecque et sagesse d’Orient.Hommage à Michel Tardieu,Turnhout:Brepols,2010,pp.694-714。。该画为立式卷轴画,尺寸142×59.2 厘米,约13 至14 世纪作品,是由带明显界线的、高度不一的五个分区组成的。其中三个区域较窄,由上而下分别是:R1、R3 和R5;另两个区域较宽,为R2 和R4。之前的研究已考证,R1、R3 和R5 描绘的分别是天堂景象,人间轮回景象和地狱受苦景象①有关画作描绘的景象,请参: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p.2-3,日译本第17—18 页。吉田豊:《絵画の内容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絵画に表現されたマニ教の教義と教会の歴史》,吉田豊、古川攝一编:《中国江南マニ教絵画研究》,京都:临川书店,2015年,第88—89页。。根据摩尼教教义,这三种去向构成三个可能的重生地②参W.Sundermann,“Manichaean Eschatology”,In:Encyclopaedia Iranica,VIII,1998,569b-575b.吉田豊:《絵画の内容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絵画に表現されたマニ教の教義と教会の歴史》,第90—94页。。尽管这幅画作一般归入六道图③如David Neil Schmid,“Revisioning the Buddhist Cosmos Shifting Paths of Rebirth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Cahiers d'Extrême-Asie 17,2008,pp.293-325。,我仍使用三道图一词,毕竟它只包含三种而非六种重生处④基于从上而下的第二区图像,古乐慈将此画命名为“摩尼救赎说”(Mani's Teachings about Salvation),参Gulácsi,Mani's Pictures,p. 245。。在R2 区,其景象围绕摩尼或说摩尼像,前方有焚香⑤Ebert,“Individualisation of Redemption in a Manichaean Painting from Ningbo”,In:Mani in Dublin,Leiden:Bril,2015,p.157.这一疑似摩尼画像的绘画出自甲府市栖云寺,参见泉武夫:《景教聖像の可能性——栖雲寺蔵傳虚空蔵畫像について》,《国華》1330,2006,第7—17 页及2 图版;Gulácsi,“A Manichaean Portrait of the Buddha Jesus(Yishu Fo Zheng):Identifying a 12th/13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eiun-ji Zen temple,near Kofu,Japan”,亦出自13至14世纪的中国东南地区,就此范围我很难不推想栖云寺虚空藏菩萨像其实描绘的是摩尼,与古乐慈所持意见(上引论文)不同。。R2 区的左侧,分别有一坐着和站立的人物,右侧对称分布两个法师样的人物,如左一坐一立。R4 区两名犯人由怪物喽啰领到坐于书案后的判官面前,有文官在侧,其后还有些许侍从。在梅维恒(V.Mair)的研究之后,古乐慈认为画作近似于日本的“图解”(絵解き)⑥有关“絵解き”,请参I.Kaminishi,Explaining pictures:Buddhist propaganda and Etoki storytelling in Japa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2006。样式,功能为从视觉上说明宗教教义⑦Gulácsi,“A visual sermon on Mani's teaching of salvation:A contextualized reading of a Chinese Manichaean silk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Yamato Bunkakan in Nara,Japan”,《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3,2008 年,第1—16 页。“The Central Asian roots”,p.3.日译本第19页。。

图2 大和文华馆藏三道图,设色绢画挂轴,142×59.2厘米©Yamato Bunkakan,Nara
学者们都认同两次出现在R1 区和R4 区的那位是妲厄那(Dan),是从亡者功德化现出来的神⑧关于此神的考证请见吉田豊:《寧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図」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第6 页;“A newly recog⁃nized Manichaean painting:Manichaean Dan from Japan”,pp.700-701。妲厄那一神,参W.Sundermann,“Die Jungfrau der guten Taten”,In:P.Gignoux(ed.),Recurrent patterns in Iranian religions:From Mazdaism to Sufism,Leuven:Peeters,1992,pp.159-173.C.Reck,“84000 Mdchen in einem manichischen Text aus Zentralasien”,In:P.Kieffer-Pülz &J.-U.Hartmann(eds.),Bauddhavidysudhkara,Swisstal-Olendorf: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1997,pp.543-550.“Die Be⁃schreibung der Daēn in einem soghdischen manichischen Text”,In:Carlo G.Cereti,Mauro Maggi,&Elio Provasi(eds.),Religious themes and texts of pre-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Wiesbaden:Reichert Verlag,2003,pp.323-340。事涉摩尼教、佛教绘画,三道图中的妲厄那人物图像相当复杂,或须另文专门论述。在此我沿用学界的一致看法,即吉田豊的结论,此前亦已为古乐慈和艾有邻接受。。在R1 区的左边部分,可见妲厄那和她的两名随侍正抵达明界,得到三人一组的主人迎接;R1 的右边部分,他们被送离⑨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2;日译本第17页。。送迎二景之间,妲厄那和明界之主端坐大殿之上,建筑上有幡。妲厄那和明界之主三人一组的两次出现都是对称的描绘,不过并非毫无差异⑩值得一提的是,对画的细加核查可知,虽然妲厄那和前来迎接的神确实以同样一种模式出现了三次,但他们的随从在迎和送两种场景中都有所变化:前来迎接的神的两名随从调换了他们袍子上的图案;送离场景中正移交香花宝瓶(常为观音宝物)的那位随从显然与妲厄那到达时带的随侍不是同一人物。另一相近(很可能不是同一个)宝瓶见于R4区其中一名随从之手。,也就是说这两位神共同出现在R1区三次。同时,妲厄那在同一幅画作中的到来(R1、R4)和离去(R1)表明该画通过空间关系来表示活动的时间先后。
这样的一种叙事技巧,借用古希腊、古罗马和希腊化研究的术语来说,可冠以循环式叙事或连续式叙事的标签①F.Wickhoff,Die Wiener Genesis,Vienna:F.Temsky,1895 称之为“连续性类型”,后有Carl Robert 批评并提出有所启发的“纪年法”,然后由K.Weitzmann(Illustrations in Roll and Codex: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Method Of Text Illust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17-36)扩展为“循环法”,并将主人公反复出现在每一个场景中视为主要特征。在A.Snodgrass(Narration and Allusion in Archaic Greek art,London:Leopard’s Head Press,1982)的术语中,包括“单一景”(凝固的瞬间)和“符号型”(多个无同一主人公出现的场景暗示了随机性或时间性)两种描绘类型在内,“循环式”和“连续型”由独立场景中的各自存在或界限上的模糊区分开。从这一点来说,妲厄那在R1 的三次现身可以说是连续性,因为她在R1和R4区的出现反映出一种循环模式。另一方面,三道图中妲厄那仅出现在R1和R4,因此是否适用于普遍的“循环连续性叙述”(即暗示同一主人公的进程)仍存在问题。另需注意的是上引术语虽是用来描述希腊、罗马及希腊化艺术的叙述结构,它们也被艺术史学家用来描述其他东方艺术。如一篇讨论早期佛教叙述模式的名作,即扩展使用“符号型”叙述,并提出一种新的“合并式”叙述,见V.Dehejia,“On the modes of visual narration in early Buddhist art”,The Art Bulletin 122,1990,pp.373-392。。虽然我认为仅这幅画作的叙事技巧就要复杂得多,但这个方面的分析已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外。循环式叙事(cyclic narrative)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主人公数次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以此暗示伴随着主人公活动的时间进程,如日本的“异时同图”(iji dōzu)之说。这样一种古早并广泛运用的技巧,用来表达时段中间或者缺乏任何时间参照的空间坐标中的时间性。就这个因素而言,这幅画并非一个静态世界的描绘,而是叙述一连串的事件。
(二)三道图与十王信仰
正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三道图多个方面基于十王图②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16.日译本第27 页。有关十殿明王像见禿氏祐祥、小川貫弌:《十王生七経讃図巻の構造》,《中央アジア佛教美術西域文化研究》5,1993 年,京都:法藏馆,第255—296 页;宮次男:《十王経絵について》,《実践女子大美学美術史學》5,1990年,第81—118页。《十王経絵拾遺》,《実践女子大美学美術史學》7,1992年,第1—63 页。《十王地獄絵》,《実践女子大美学美術史學》8,1993 年,第5—24 页;海老根聡郎:《金処士筆十王図》,《国華》10,1986年,第20—29页;梶谷亮治:《日本における十王図の成立と展開》,《仏教芸術》97,1974年,第84—95页。《陸信忠筆十王図》,《国華》1020,1979 年,第22—38 页;鷹巣純:《めぐりわたる悪道——長岳寺本六道十王図の図像をめぐって》,《仏教芸術》211,1993年,第39—59页。。一般而言,中国十王图现存有两种类型样式。第一种与《十王经》32 种写本紧密相关③完整经名为《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有时简称为“阎罗王授记经”“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十王经”。多种钞本参见S.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pp. 239—241,包含经变的版本见该书第228—229 页,日本版本情况见第58—61 页。本文延用太史文说法(是书第7页),使用《十王经》一名。,其中有6 种包含出自10 到11 世纪敦煌的插图④Teiser,“Picturing purgatory:Illustrated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In:J.Drège et al.(eds.),Imag⁃es de Dunhuang,Paris,1999,p.177。多数钞本署名“藏川”,此人居成都府大圣慈寺。。另一种十王信仰的重要类型显现于中国的东南地区,尤其是13至14世纪时浙江的宁波地区。在这里,“制作”是一个恰当的说法,因为这类画作曾基于明显的商业目的进行批量制作,其中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是那些带有商业推广性质的题记: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庆元府”一名仅用于1195 年至1276 或1277 年间,所以这些画作一般认为是13 世纪的产物。尽管在陆信忠(约1192—1276)名下有多部画作,这些画作水平却良莠不齐,如雷德侯所说,“它们势必由雇有多名画工的作坊所制作”⑤Lothar Ledderose,“A king of hell”,《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中國繪畫史論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33—42页。。这些画作尤受日本商人青睐,将其中多数带往日本,在所销往之处,触发了此后日本画工对同类主题独特且集中的痴迷①Teiser,“The growth of purgatory”,In:P.B.Ebrey&P.N.Gregory(eds.),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129。日本的地狱概念及十王图,参C.Hirasawa,“The inflatable,collapsible kingdom of retribution:A primer on Japanese hell imagery and imagination”,Monumenta Nipponica 63.1,2008,pp.1-50。。这很有可能也是大和文华馆那幅绢画流往日本的路径,金处士和陆信忠之作得以集中仿制,这些画作今藏于多处:
它们在中国的闻名仰赖于雕版印刷在批量生产中带来新的图像形式。数以百计的画作在这个世纪收入日本、欧洲及美国馆藏。这些画作实则是于12 世纪晚期至13 世纪早期,由宁波的一些作坊与金氏、陆氏家族联合制作的。它们包含十幅卷轴画,每一轴即一个冥王。②Teiser,“The growth of purgatory”,p.129.
即便是匆匆一瞥,也能看出三道图所现图景与宁波画作更契合,而非敦煌类型③在我有关宇宙图中审判画面的前述讲演中,我提出此画面更接近于敦煌类型如P.2870,而非宁波类型。。这一绘画与宁波画像有共通之处,亦可由我们对于摩尼教在浙江、福建的了解佐证,这使得在宁波画作中寻找一种最紧密的画像学类比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十王经的文本也是在分析中必须纳入考虑的,因为它同时包括了敦煌的写经背景和宁波一地的视觉表现形式。还应当提及的是,近年确证的中国东南的摩尼教文献,其中有《冥福请佛文》,包括十王名录,清楚地证实了这些摩尼教徒毫无意外地对这种宗教信仰有所耳闻。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应当指出借用十王信仰并非浙江摩尼教徒的随机选择,而应放置在更广阔的情境中看待。对敦煌样本的调查表明,十王信仰与净土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这对于汉地摩尼教徒的重要性已为人知④有关两者联系的研究综述,请见G.Mikkelsen,“Sukhvat and the Light-world:Pure land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Manichaean eulogy of the Light-world”,In:Jason D.BeDuhn(ed.),New light on Manichaeism,Leiden:Brill,2009,pp.201-212。。无论是文献本身还是题记,都反映了十王信仰的终极目标是避免轮回至三种恶道(畜生、饿鬼、地狱)而重回人道,或更为人期许的,重生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⑤Gulá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p.6-10,日译本第20—23页。。在汉地摩尼教绘画中远非异域之躯的十王信仰,通过清净世界的学说与修行之中介得以最恰当地融合,与诸种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地联结起来。
(三)画像学的进一步考察
作为一种更具体的分析,依据目前已接受的解释,R4 区描绘了妲厄那出现在评判人类功过的景象中,而R1、R3 和R5区刻画的是审判的可能结果。R1 为天堂,R3为人道,R5为地狱;在R4中可见判官坐于案前,在他面前有一幅展开的卷子,正欲在上面写下他面前那位褐色皮肤者的最终判词。在听取了这个人的功过是非后,他左边的那个怪物喽啰将读过的卷轴卷回去,判官看着犯人,或是某个不确定远处,手中的笔举起或将完成判决。这是十王画像中的典型一幕(人甚至能发现同一位置举起的手,如柏林达勒姆区画像),即象征人的命运最终被确定前的那一刻①Ledderose,“A king of hell”,Pl.1.同样的手势也见于宇宙图,见Kósa Gábor,“The iconographical affiliation and the religious message of the Judgment Scene in the Chinese cosmology painting”,张小贵、王媛媛、殷小平主编:《三夷教研究——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77—161页。Kósa Gábor:《中国のマニ教宇宙図に描かれた裁きの場面:図像の起源と宗教的なメッセージ》,《中国江南マニ教絵画研究》,第275—291页。。根据已接受的画像学说法,判官两边的喽啰分别负责读取受审判者的善与恶。宁波所出十王像的审判场景中,着红衣的喽啰陈述的是善,青衣喽啰读的是恶簿②“善童子丹,恶童子绿”,见M.Soymié,“Un recueil d’inscriptions sur peintures:le manuscrit P.3304 verso”.In:Michel Soymié(dir.),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Genève:Droz,1981,pp.171-172。“善簿”“恶簿”,参C.Kwon,The‘Ten Kings'from the Seikadō Library.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9,pp.69-70;Effi⁃cacious underworld:The evolution of Ten Kings Paintings in medieval China and Kore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2019,p.23。中野照男编:《閻魔・十王像》,东京:至文堂,1992,图版3;M.Soymié,“Notes d'iconographie chinoise:les ac⁃olytes de Ti-tsang”,Arts Asiatiques 14,1966,pp.46,74。Fig.1.Wen C.Fong,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38-339.Pl.74c,74e,74f.。这样一种颜色的运用也见于三道图(图2.1),说明它正是源自宁波,本质上分派了同样的角色。

图2.1 大和文华馆藏三道图(局部)判官与红、绿喽啰
与此一致的是两名喽啰的面部特征,它们都呈现兽形怪物样,绿喽啰看起来性情更凶猛恐怖,这也是宁波十王画中青喽啰的常见特征③从这一方面而言,三道图与其他十王像不同,其善簿喽啰无面部特征,见梶谷亮治:《陸信忠筆十王図》,《国華》1020,1979,第23 页图版1;中野照男编:《閻魔・十王像》,第32—33 页图版20,第37 页图版25。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中的一幅画可见两名喽啰,持恶簿的那位表情凶恶,手捧的书卷展开,另一位则表情和缓,书轴卷起,见M.Soymié,“Notes d'iconographie chinoise:les acolytes de Ti-tsang”,p.55,78,Fig.6。波士顿美术馆藏12—13世纪的金处士绘画中的绿袍喽啰,其脸如猿猴或怪物,见Wen,Beyond representation,pp.338-339,Pl.74c,74e,74f。。既然红喽啰手中有两卷善簿,读完并卷到一起,而青喽啰只有一卷,显然在绘画的进行时叙述中,即善恶簿卷起的进程中,这一具体的情况,对褐色皮肤者的结论是功多于过。
卷轴数量的差异并不仅仅通过确切的两轴或一轴这样的描绘来强调,同时也由红喽啰第一卷上面的汉字“壹”来表明④吉田豊:《寧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図」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第9页注释32。Yoshida,“A newly recognized Manichaean painting:Manichaean Dan from Japan”,p.704,n.33.。事实上,卷轴的数量是一种突出重要性的双重强调。相应地,画家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善多于恶的这一事例上,因此褐色皮肤者理论上受较轻判罚。
在褐色皮肤者后面我们看到一位肤色较白的人物,由三名鬼差看管,脖子上戴着枷锁。紧随两名杰出的艺术史学者艾有邻和古乐慈其后,我也同意这个人物是位妇人。此外,我还认同他们的看法,即这位妇人应该是题记中提及的妻子,但不同意他们的假说,说R4的褐色皮肤者是另一位功德主,即丈夫⑤Gulácsi,Mani's Pictures,p.247.;和艾有邻一样⑥Ebert,“Individualisation of redemption in a Manichaean painting from Ningbo”,pp.156,159,158.,我认为丈夫为R2区坐着的那位平信徒。
这位妇人显然将在前一位带走后受审。她的罪要比前面那位重得多,这可由两个彼此独立的方面推断出:其一,皮肤白者由三名携不同武器的侍卫看管,而褐色皮肤者仅有一名不带武器的怪物喽啰看管;其二,她的脖子上有枷锁,而褐色皮肤者身上没有任何限制行动能力的物件。枷锁,借自中古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刑罚⑦律法、刑罚词汇广泛见于该文本,见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p.168。,是十王画中用来说明人有罪时,大量使用的一种符号,如S.3961、P.2003、P.2870和P.4523,以此形成一种明显对照。第二位稍显畏缩的姿态(这类戴枷者的普遍特征)和前面褐色皮肤者的笔挺姿态(尽管明显受他身后喽啰反扣)相对照,进一步显示出上述的差异。总而言之,画像似提示人们关注此人的善簿数,仅有一个鬼差看管,不戴枷锁,笔挺站立,说明这位褐色皮肤者所犯的罪显然比后面的妇人轻。
如若我们将罪的轻重纳入考量的话,那么在R3 即人间这层或甚至是R1 区的天堂遇到褐色皮肤者就是合理的,同时白色皮肤者被带到R5区,于地狱受折磨。这应当是一种意料之内的公正审判的结果,一种司空见惯的惩恶奖善。然而在我看来,通过画像学分析,这幅画作并非只是这样一种老生常谈,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信息。
我们可首先检视画作中肤色的象征性:那些白色皮肤者属于与光明有联系的区域,而褐色皮肤者则归属黑暗些的地区。这样一种浅色和深色的象征用法,更可由与光明教义相联系的所有人物证实。在天堂景象中的摩尼僧、功德主、摩尼像、人间一层的人及判官都是浅色皮肤。那些与黑暗层面有联系的,鬼卒、鬼差和那些在地狱受折磨的人,皮肤颜色不同,或褐或青。在这条基本法则下没有例外。因此,这两类人的肤色就应以象征手法来解释,说明他们的内在性格,而非物理表现,这显然与他们过去的功绩及未来的命运相关。如果肤色是象征性地使用,就不难得出结论,褐色皮肤的人走向他的那类归属,到人人都是褐色皮肤的地狱去,而白皮肤人物最终走到都是白皮肤的人间去。他们分属两种不同地界:作画者使用两种人物的肤色来表明他们在审判后的命运。
这一假说可由其他画像符号证明。更确切地说,是R4 区褐色皮肤人的下方,在R5 区火轮下的左边那个人物。虽然两者不是同一人,但很相近,他们肤色一样,头发稀疏,牙齿的描绘很典型(图2.2)。不管是头发或是牙齿,在画作其他人物里都没有这样的特征。受审者和稍后受折磨者方面的相似性并不仅限于三道图。
因此,R4 和R5 区里两名褐色皮肤者的相似性或暗示一种未来时状态,该名在现在时叙述状态下的受审者将很快被带离,并送往未来时叙述下的火轮受苦。总之,宁波十王画的技巧运用,包括肤色、牙齿刻画和褐色皮肤者的位置都指向一种结论,他未来到地狱的命运在此已有所铺垫。在判官作出不利判决后,鬼卒将褐色皮肤者领到地狱,而白皮肤者则向前走到判官前。既然她属于白的一类,她很可能成为人道轮回中的一类。图中可视的是中国传统的四民范畴:从左往右,依次为商、工、农、士①Yoshida,“A newly recognized Manichaean painting:Manichaean Dan from Japan”,p.698.相近绘画,请见明正统元年(1436年)《新编对相四言》中的插图。。
从中国式的看法来说,这样一种排序的高低等级应该是从左往右排的。因此,画作也许暗示,虽然白色皮肤者身犯多种罪业,轮回人间后她依然可以达到士或上层阶层。重生于贵胄之家在《佛说十王经》中也公然得到强调,尽管其他三种阶层从未提及:
生处登高位,富贵受追长……欲求富乐家长命,书写经文听受持……往生富贵家,善神常守护。①参见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pp.207,208,n.116。
相应地,据此说明,罪业较轻的褐色皮肤者去地狱,但白色肌肤妇人,很可能是题记中的妻子,罪业重得多却能轮回人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逻辑,为什么看起来作恶少的所受判决反而要重得多呢?
对此的解释,我认为画者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白色皮肤妇人有守护和帮助的妲厄那在她上方,而褐色皮肤者却无人保护或帮助。所以审判后的不同命运不是简单地由对象的功罪决定,还由受审时出现的额外助力决定。带着侍从飘扬在白皮肤者之上的妲厄那确实陪同她前往受审,显然将提供帮助,或正看着白皮肤者受囚禁的信仰和善业。正如我们可推断一尊摩尼教神明自然地守护、帮助一名摩尼教信徒那样,很有可能白皮肤者为摩尼教信士,她虽然犯有多种罪业(特别是考虑到可能违反了严格的摩尼教戒律时),但作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听者,在她的最后时刻仍得妲厄那拯救。如若R3显现的确实是白色皮肤者的命运,显然是因为她只是一名听者,毕竟选民能完美地到达明界。汉文摩尼教经《下部赞》中存在希望怜悯并宽恕摩尼教信徒(通常是听者)所犯下的罪的祷词,通常是向固定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神祇祈祷②下部赞行11、28、29、46、54,、64、80、121,148—150,358—359,371、393、404、414和415。。另外,题记清楚表明该画是以一名已婚摩尼教听者的名义供奉的,其名张思义,是“茂头保弟子”,这里的“弟子”很可能指平信徒(听者)。《三道图》中的题记如下:
东郑茂头保弟子张思义
偕郑氏辛娘喜舍
冥王圣[帧]恭入
宝山菜院永充供养祈保
平安愿(王?圣?)□□(安?)日③吉田豊:《絵画の内容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絵画に表現されたマニ教の教義と教会の歴史》,第96—97页。另参吉田豊:《寧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図」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第8 页。Yoshida,“A newly recognized Manichaean painting:Manichaean Dan from Japan”,p.704.《マニの降誕図について》,8a。
众所周知,佛教徒中的“供养”是抄写经文或供奉画像、造像背后的一种基本动机。这种动机在十王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罪者的严厉判罚可由奉纳写经或造像而减轻,通过功德回向来消除或至少减少功德主亲人死后的罪过④A.von Gabain,“Kitigarbha-Kult in Zentralasien,Buchillustrationen aus den Turfan-Funden”,p.49;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pp.202-203,215;“The growth of purgatory”,p.121.“Picturing purgatory”,pp.180-181.。正如回鹘语文献所示,这样一种实践在摩尼教教团中也并非闻所未闻⑤Klimkeit,Gnosis on the Silk Road,pp.374-375.L.V.Clark,“The Manichaean Pothi-book”,I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9,1982,pp.179-180,190-191.Clark 一文的第156—158 及210 页中注释摩尼教梵夹装书籍中的功德回向可由早一些的佛教供养人发愿来解释。。
就此方面,应当注意R2 区的场景看起来更确切的是题记所述的供养画面,一名着褐衣年轻男子将一卷轴画(可能指我们看到的这幅)或一写经呈给摩尼僧,即一名白衣选民。供奉行为应发生于一摩尼教寺院,即题记中的“宝山菜院”,画中央的摩尼像和香炉说明了这一点。尽管R2 左侧人物身份仍需进一步调查,然而总体上看,R2 为供奉场景是比较合理的。选民微张的嘴⑥Ebert,“Individualisation of redemption in a Manichaean painting from Ningbo”,p.158.画作中,嘴微张这一描绘同样见于其他意欲说话的人物,如判官和受审者身边的喽啰。暗示紧随供养行为之后,可能是坐着的选民对供养带来的福报进行训示,因此,古乐慈将此场景定名为“摩尼像旁布道”⑦Gulácsi,“A visual sermon on Mani’s teaching of salvation”,p.4.是可接受的,然而我觉得这一定名却没有表达出这一景象的原始用意。
根据R2四名人物的手印可知,前景是供养行为的发生,其中站立的年轻人手持即将供奉的卷轴,白衣摩尼师双手合十并微微抬起准备接受。后景中坐着的摩尼师在布道。也许是以此次供养的功德为主题,同时坐着的平信徒聆听其训示,并同样双手合十。前景和后景中的活动同时发生,营造出一种供养和接受双边行为的独特平衡。至于R2左侧人物的身份,如果艾有邻所说R4待受审白皮肤者为妇人,那就不能排除坐者是其夫(如题记所述),立者为其子,两者面部特征极为相近。这两位和白皮肤者的紧密关系,还可通过画面中的空间位置证明,他们被分别放置在R2和R4的同一纵轴线上。
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此次供养行为所积的德也许就是妲厄那出现在R4 区助白皮肤妇人(可能是功德主的妻子)一臂之力的根本原因,这些都基于同在画面左侧的那名褐衣年轻人的供奉行为。褐色皮肤者更多的是代表非摩尼教徒,即使罪业不重也要下地狱,因为不受摩尼教万神殿中神明的庇护,必遭永世诅咒。就像《群书类述》(Al-Fihrist)里引用的摩尼原话所说:“人之灵魂分途于三路。其中一条走向天堂花园,那是选民的路。第二条走向世间和恶物,那是守护信仰帮助选民之人(作者注:即听者)的路。第三条走向地下,那是给罪人的路。”①B.Dodge,The Fihrist of al-Nadim,New York:Columbia Press,1970,p.796.此处“罪人”显然指向非选民非听者的那些人,即非摩尼教徒者。古乐慈恰当地描述此场景为妲厄那“介入审判”②Gulcsi,“The Central Asian roots”,p.3.,虽然此次介入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白肤色的摩尼教徒。或许供养人题记题写在慈悲的妲厄那和白皮肤摩尼教信士之间不仅仅是个巧合(图2.3),而是明示供养人像此人一样忏悔曾经犯下的罪业,但仍相信妲厄那的救扶。题记看起来准确地将驾云的慈悲圣众和押解摩尼教徒的那组人连在一起。

图2.3 三道图显示妲厄那救扶信士和题记部分
另一方面,如果以上解释无误的话,这幅画的原型不会是摩尼《图经》(Picture-Book)的一部分,因为此书明确地缺少对听者命运的刻画③《师尊篇章》页234 行25—28,页235 行1—13,页235 行18—21,页236 行1—4,即A.Bhlig &H.J.Polotsky,Kephalaia I,pp.234-236;I.Gardner,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pp.241-242。另参W.Sundermann,“Was therd⁃hang Mani's Picture-book?”,In:A.van Tongerloo&L.Cirillo(eds.),Il manicheismo-nuove prospettive della ricercha.Quin⁃to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 manicheismo,Napoli,2-8 settembre 2001-Atti,Turnhout:Brepols,2005,p.374。。这表明浙江的摩尼教徒,借用同时期十王信仰的宗教图像表现,增补《图经》缺失部分,补充了对于众听者而言(包括此画的供养人)都可理解的信息。
本文所讨论的两个摩尼教审判场景源自不一样的文化背景(9—10世纪的吐鲁番和13—14世纪的浙江),因此应用于图像后大有不同。尽管如此,有意思的是,它们都特写了判官及其前受审的两人,都将重点放在两个受审者的差异上。在我看来,吐鲁番的绘画区分了两类罪行(用手或脚犯下的;对动物或植物犯下的),而更为复杂的三道图对照了非摩尼教徒和摩尼信徒的命运,后者罪孽更重,却因妲厄娜的介入而受更轻的惩罚。此种介入反过来是罪者亲人积德的结果,很可能是因其夫向摩尼教寺院供奉画帧或写经。尽管MIK III 4959 V与大和文华馆三道图描绘的都是审判景象,却不只是着眼于描绘,更多的是劝诫摩尼信徒勿犯诸不善业,激励他们践行更多的可能路径,如供养经像经文,以蠲除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