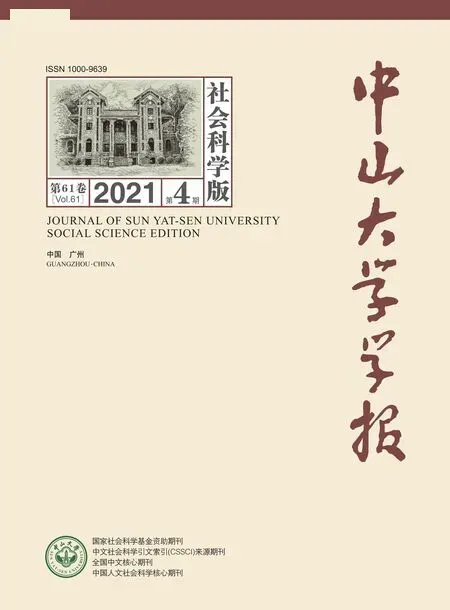风险社会的立法法理学*
——不确定性、社会选择与程序正义
丁建峰
引言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人们需要安全的环境,不亚于需要阳光、空气和水。然而,人类却越来越处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中,雾霾、酸雨、核事故、毒奶粉、传染病、恐怖主义、网络病毒……各种各样的风险无处不在,逼人而来。进入2020 年以来与新冠肺炎有关的种种震动人心乃至催人泪下的事件,都无比清晰地提醒我们,人类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之中。
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①[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22页。。尽管人类的生存一直面临挑战,前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甚至更为艰难而充满危机,但“风险社会”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专属特征。气候、生态、金融、高科技带来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它们与人类活动高度相关,并带来大规模的、长期的、系统的、不可逆的伤害,甚至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②[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22页。然而,“风险社会”作为一个专门描述现代社会的重要理念,也预设了人们对风险有预测、预防和干预的能力。技术水准之提升,社会协调能力之增强,使得今人不同于古人之听天由命或束手无策,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抗御风险。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控风险,特别是在法治的框架下,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准,是当前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由之路。对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实用主义策略不是长远之计,传统的法解释学或法教义学也难能胜任,必须展开深入细致的法理研究。而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理当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论,21 世纪的法学需要从风险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角度,推动理论范式的转换①季卫东:《风险社会与法学范式的转换》,《交大法学》2011年第2卷,第13页。。
尽管对于风险社会的具体法律问题,当代学者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但对于多元的、复杂的风险社会中采取何种方式立法,则鲜有探讨②与风险社会相关的法学论著数量甚多,有代表性的如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何国强:《风险社会治理与侵权法的转型》,《学术研究》2018 年第6 期;张富利:《全球风险社会下人工智能的治理之道——复杂性范式与法律应对》,《学术论坛》2019年第3期。但这些论著大多集中在部门法领域,一般性的法理探讨则较为少见。。本文试图以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对风险社会立法中的法理问题,给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和思路。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千差万别,集结不同个体偏好而成为社会偏好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领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协商民主和程序正义则对形成合理的社会选择结果具有实质意义。本文第一部分辨析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并概述当代风险管理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因应之道。第二部分引入社会选择理论,探讨利益与风险偏好不同的个人,如何形成相对统一的应对风险的法律规则。第三部分探讨社会选择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最后我们对整体理论框架进行总结和展望。
一、不确定性、预防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
要探究风险社会的立法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何谓“风险”。经济学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实为两个不同的概念。1921年,芝加哥学派的先驱弗兰克·奈特首先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不确定性’应当这样被理解: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风险’概念,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恰当地把它们分开。”③Knight,Frank,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The Riverside Press,1921,p.19.按照经济学的标准区分,风险中的随机性是可测量、可计算的,比如掷匀质骰子或扔硬币中的概率。风险中的决策者面临的是数理统计学足以处理的客观概率。而不确定性则指向更难于处理的随机性,它包含着一系列无法预估概率的可能事件,于是,决策者在不确定事件中面临的是主观概率,只能根据非常不充分的信息,对模糊的前景加以预判。故而,“风险”比“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确定程度。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决策者不但无法估算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且连未来究竟可能发生哪些随机事件也缺乏明确的认知。“风险社会”的研究者所论述的“风险”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科学的计算标准在不可预知的风险和灾难面前是失效的,“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的概念已经无法把握这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④[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20页。。由于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科学本身的局限,工业社会的风险评估会变得越来越难。恐怖分子在何时采用何种手段发动袭击?全球变暖的生态影响如何?下一次流行病将在何时出现?甚至,我们无法预期下一次灾难到底是什么,所有一切都是未定之数。风险社会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广泛的、部分可控但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的不确定性⑤由于“风险社会”“风险管理”“风险防控”“风险规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我们在下文会按照语境交替使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两个词,但本文中它们都指代随机事件概率无法预估的高度不确定的情形。。
风险社会立法的最大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要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立法。在风险社会,风险往往是整体的、系统性的,因此,传统的、主要由个体采取的风险防控手段,例如储蓄、购买保险、参加互助组织等方式,都很容易失效。然而既然风险是整体性的,也就意味着对风险的管理控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必须由政府提供或制订法律加以协调。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挑战着规则制定者的能力极限。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可以比喻为赌博,如果输赢的投注不大,那么赌徒只需要最大化预期利益即可;但如果一旦输了会丧身失命,并且输赢的概率不可确知,那么,理性的决策者将不会像一般的赌徒那样冒险,而会尽量地采取谨慎小心的策略。于是,“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就应运而生。
“预防原则”是现代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它的核心内容是:如果人类行为带来了风险,就应当在实际危害发生之前对其加以预防。弱版本的预防原则认为,凡有风险,皆当预防,不能等待科学作出绝对确定的因果证明。强版本的预防原则主张,任何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都应该禁止或严格限制,除非我们能确切证明它们是安全可靠的。很显然,预防原则的强弱程度依系于所要求的证明力度。弱预防原则要求对危害的因果关系证明不需要达到绝对准确,这几乎是一条常识——如果要等到科学百分之百地证明危害发生的机制,必将延误时机,一旦大错铸就,悔之晚矣。弱预防原则历史悠久,现实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体现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新技术规制等诸多领域的法律和国际公约之中①Zander,Joakim,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另外,我国还有学者支持更强的预防原则,参见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相对而言,强预防原则引起的争议较大,其缺陷也较多。首先,强预防原则无视预防成本,必将导致过度预防和过度规制。例如,科学尚不能完全排除使用手机的致癌风险,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禁止人们使用手机②Adam Burgess,Cellular Phones,Public Fears,and a Culture of Preca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其次,风险经常是相互关联的,清除一种风险会带来另外的风险。此时,强预防原则将面临进退两难、无法决策的困境③Goklany 用整本书的篇幅讨论了在DDT 杀虫剂的使用、转基因食品和全球变暖3 个案例中预防措施本身带来的风险,第一章的标题《逃离魔窟,又入狼窝》(Escaping goblins,only to be captured by wolves)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Goklany,Indur M,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 Critical Appraisal,Washington D.C.:Cato Institute,2001。。
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应对风险的另一种基本理论。它的思路是经济学的:既然无法清除所有的风险,那么,就必须进行利益和代价的权衡,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时候,才应当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否则,我们不如承受一定的风险。成本收益分析主张,政府应当努力评估风险的规模,考察风险规制措施带来的各种效应,包括规制措施本身的成本和危害,同时,不断研究那些能达到同样目标但成本较低的替代方案。例如,如果措施A和措施B效果相同而成本不同,那么应该采取成本较低的措施;再如,如果一个预防措施减少了风险C 却带来了更大的替代性风险D,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措施④例如,欧盟曾经立法禁止在儿童玩具中使用聚氯乙烯塑料(PAC),但随之其他材质的塑料玩具涌入市场,儿童的健康反而变得更不安全了。参见B.Duriodé,“plastic panics:european risk regul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BSe”,in J.Morris(ed.),Rethinking Risk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Butterworth-heinemann,2000),pp.142-167。。但成本收益分析也有局限之处,因为在风险防控的决策中,往往涉及多个不同领域价值的权衡取舍与非货币价值的估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没有公认有效的成本—收益估计方法。
大部分合理的风险控制方案都必须在预防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之间,走一条合理的“中间道路”。我们大致可以把风险防控措施从严格到宽松排列出一个顺序:最严格的是强版本的预防原则,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防控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最宽松的是不采取法律上的预防措施,把风险防范交给社会自治。现实中的风险应对抉择,总是落在这两个极端情形之间。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风险防控的理想目标和理想方案可能会大相径庭。比如,欧盟和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规制,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案。欧盟采取的是严格的强制性措施,而美国则侧重自治,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予以规范,其他国家的规制措施也各有不同①孙良国:《法律家长主义视角下转基因技术之规制》,《法学》2015年第9期。。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需要相对统一的风险管理策略时,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风险防控方案之中,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二、风险社会立法中的社会选择问题
社会选择是规范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研究集体决策过程与程序的专门之学。如阿马蒂亚·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说:“如果说有一个可以视为社会选择理论的中心问题的话,那就是:在社会中不同个人所面临的给定偏好、关怀和困境情况下,如何达致恰切的社会总和判断(aggregative judgements)。”②[印度]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译:《理性与自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社会选择是汇集不同的口味、偏好或价值判断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体现了民主立法的要求。以往的社会科学在风险社会的立法和规则制定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其缺陷在于:研究者直接把自己放在立法者的位置上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没有考虑到选择的多元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见和利益高度分化的时代,广泛地吸纳公众参与,通过社会选择过程汇总不同意见,充分保障立法中的程序正义,是建立合理的风险管理法治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专家意见的局限与社会选择的必要性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专家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众则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与技术。同时,普通大众对于小概率事件缺乏确切认知,在风险决策时往往容易犯错。桑斯坦和泰勒等人曾提出“家长主义”的方案,亦即立法机构不能受大众影响,应当直接听取行为科学专家的意见制定默认规则③Sunstein,Cass R,Why Nudge?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在风险社会的立法过程中,专家的意见只是决策的重要依据,社会选择的过程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在此提出若干理由:
第一,专家意见或许是专业的,但不一定是客观的,也未必正确。即以最“科学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例,为了估计相应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必须给各种结果赋予货币价值,比如,森林、新鲜空气、自然环境、动物和人的生命价值。这种赋值必然带有社会文化因素,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④Douglas,Mary and Aaron Wildavsky,Risk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70-73.。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在很多领域,专家的预测能力并不显著优于普通公众。耶鲁大学的泰特洛克(Philip E.Tetlock)比较了专家、业余爱好者和掷飞镖的黑猩猩在国际政治转型、经济增长、核扩散、国家间暴力等问题上的预测,发现专家的预测能力并不比业余爱好者高,而人类的预测能力也只是略微好于黑猩猩⑤[美]菲利普·E·泰特洛克著,季乃礼等译:《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6—60页。。这主要是因为专家在工作时面临的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小世界”,而真实的风险社会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世界”,而其复杂程度与“小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汇集多方面多角度的经验,方能在复杂世界中作出明智的决策。
第二,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公众知情的基础上,公众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很多风险防控的措施,将会对部分公众甚至全体民众的利益造成损害,自上而下强制实施,是难于顺畅通行的。专家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立法机构的成员,有筹划之能,却无问责之实。既然专家无法为自己的方案承担法律责任,也就只能对立法提出建议,而不能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越俎代庖地确定最终方案。而且,所有风险管理的法律必然涉及强制力量的使用,涉及既有权利的重新划定。这就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立法机关的严格审议,否则,法律必然是不正当的,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同。正如哈耶克所评论的:“只有在确使人们遵守大多数人或至少是某个多数所认可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时候,才应当准许实施强制……除非指导强制性权力的原则是多数人所认可的,否则任何强制性权力的实施都是不合法的。”①[奥地利]哈耶克著,邓正来译:《法律、立法与自由》(下册,第二、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273—274页。
第三,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是社会公众而不是专家拥有信息优势。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就在于他对某一领域有专深研究,但立法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专家之专是优势也是劣势,容易局于一隅而作出错误判断。尽管公众很可能在概率方面犯错误,但很多风险防控的规则并不需要估计概率(比如突发事件应急的具体方式)。再者,一些事关风险防控的重要问题,例如法律体系是否存在漏洞、法律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抵牾、法律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实施机制等,不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更为需要的是健全的常识感和勇于“挑错”的责任心。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社会的风险防控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协作,特别是民间组织的运作,而对这一领域,社会公众显然具有更充分的信息。公众固然容易犯错误,但这种错误在立法过程中可以纠正,而数目众多的公众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更容易发现未来法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将会极大地提高立法的质量。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是精英主义者,相信专家胜于普通公众,仍然无法回避社会选择过程——专家本身也经常会出现意见分歧。此时,立法者也必须借助某种机制来汇总专家之间的不同意见。当然,最理想的情形是专家、公众和立法者之间分工协调,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共同设计并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二)单峰偏好与多数同意规则
在风险社会的立法工作中,专家和立法者(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构,或立法机构中的专门委员会)应当有充分的分工协调。专家的任务,在于初步估算各种不同风险防控方案的代价,在技术上确定一条权衡取舍的“可能性边界”。例如,如果要减少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灾难性事件,就必须负担减排、治污带来的成本,同时,还可能带来成本拉动型的物价上升、产出下降和失业问题。最终,我们总会面临一个边界,这是由技术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不可能处处“两全其美”。
如图1 所示,考虑上文所述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可以把“安全”和“产出”视为两个必须关注的维度,图上的曲线代表了一条技术可能性边界。在这条边界上,安全程度的增加必然带来产出的减少,x、y、z三点分别代表“低安全、高产出”“中安全、中产出”“高安全、低产出”的三个风险防控方案,在边界之内的所有点都代表在技术上缺乏效率,故而不应被采纳。必须指出,当可能性边界和不同的可行方案初步确定下来之后,并不存在选择的客观标准。虽然我们可以粗略而模糊地了解客观的技术权衡(例如采取不同的传染病防控策略的代价不同),但仍然无法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这种不同方案的选择是一个“艰难选择”(hard choice):我们无法确定哪个选择具有终极的正确性,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全”和“产出”之间的取舍,实则是“环境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取舍,两个价值维度之间势均力敌,无法兼得,意见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图1 权衡取舍的标准模型
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汇总偏好的方法甚多,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几十种汇总规则,例如博达加权计算法、否决法、锦标赛法、最大最小法、需求显示法、逐次排除最劣者法等等②Gaertner,Wulf,A Primer in Social Choice Theory:Revis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2-119.。这些规则各有优劣,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全体一致同意”(Unanimity rule)和“多数同意”(Majority rule)两种方法。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项提案只有全体参与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取得一致同意,也就意味着全体参与者达成了高度共识。一致同意是非常理想的社会选择结果,它意味着法案是可以自动推行的,不会有任何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投票规则、英美陪审团作出判决遵循的规则,都体现了一致同意的要求。但在一个立法机构实行一致同意,会产生巨大的协调成本,否则法案无法通过。故而,多数同意,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是更为优良的规则。
然而,多数通过的方式可能会遇到困难,如图2(a)所示,如果有甲、乙、丙三个人(或三个群体),其偏好满足甲:x 优于y,y 优于z;乙:y优于z,z 优于x;丙:z 优于x,x 优于y,则多数意见会产生循环,甲和丙认为x 优于y,甲和乙认为y 优于z,乙和丙认为z 优于x,如是,则多数意见会认为x 优于y,y 优于z,z 又优于x。这种循环是不理性的或者缺乏决断力的,它无法在三个方案中得出最终选择。这被称为“孔多塞悖论”或“投票悖论”①本文对孔多塞悖论的描述可参见Sen,Amartya,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n Expanded Edi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3。。

图2 偏好结构与孔多塞悖论
虽然“孔多塞悖论”是社会选择中的一个基本难题,也是对多数同意规则的一个有力反驳,但在单峰偏好之下,这一悖论可以被化解掉。所谓单峰偏好,是指如果把所有的备选项排成一列,则每个人的偏好只能找到一个极大值,在这个峰值所有可能的“侧翼”,偏好逐渐递减而非递增②单峰偏好的数学化表述参见Arrow,Kenneth,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Cambridge,Massachusett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77。。图2(a)中的偏好结构之所以出现了悖论,就是因为丙的偏好有两个峰值x和z,如果丙的偏好变成了图2(b)中所画的那样,就不会出现悖论。此时,甲、乙、丙分别代表“风险偏好”“中庸”和“风险畏惧”。风险偏好的人(甲)能够接受高风险、高产出的方案x,他的合理偏好应该是x 胜于y,y 胜于z;风险畏惧的人(丙)则最喜欢低风险、低产出的方案,其合理偏好应该是z 胜于y,y 胜于x;风险态度中庸的人(乙)则最喜欢中等风险和产出的方案,其合理偏好可以是y 胜于x,x 胜于z。在这样的偏好结构下,孔多塞悖论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如何改变比较的次序,y 都会获胜。在涉及安全与风险的问题上,单峰偏好是相对合理的,因为绝大多数正常人要么敢于冒险,要么小心谨慎,要么偏好中庸,中间状态都不可能是最差选项,这就使得风险社会中的社会选择问题变成了集结多数意见的问题。这对于社会而言是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多数意见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符合我们对立法的一般认识,并且具有很多优良性质:在认识论方面,多数意见集结了尽可能多的信息,更容易达到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如果我们承认“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合理性,那么,多数意见也比较容易满足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要求③Goodin,Robert and Christian List,“A conditional defense of plurality rule:generalizing May's theorem in a restricted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0,issue 4,2006,pp.940-949.。
然而,这里仍然会存在疑点,以上我们仅仅谈论了单维度(单一风险)的单峰偏好问题,而如果将单维度的冲突问题变为多维价值冲突(例如“多、快、好、省”之不可兼得)的情形,那么,则仍然有可能出现多峰偏好和循环多数④Muller,Dennis,Public Choice 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87.。另一个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服从多数意见”仅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但它对偏好的内容是不加判断的。然而在风险情境下,人们恰恰很容易在概率估计、防控措施等方面犯下系统性的错误,不是过度乐观,就是过度小心谨慎,或者囿于一己私利作出短视的决策。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民主立法必须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那么,风险社会下的民主立法则要相当谨慎地避免“多数人的愚蠢”。故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汇集不同意见,还要有效率的汇总信息,以达成正确意见。协商民主和多数规则的结合,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三)社会选择与协商民主
在具有多元价值的风险社会中探讨规则制定问题,面临的不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汇总,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交汇、对话、碰撞乃至交锋。于是,社会选择必然要与“协商民主”①关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有多种译法,例如“慎思民主”“慎议民主”“商谈民主”“审议民主”等。这些翻译方法各有其理据,本文为方便起见,在行文中取学界比较通行的“协商民主”译法。相关联。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对话达成集体决策的方法。在对话过程中,理性而无偏私的参与者提出各种论据,通过说服而不是压制的方式作出决定②Elster,Jon,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7.。协商民主与社会选择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是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发展前沿。传统的社会选择理论认为,人的偏好是先验给定的、不变的,社会选择的任务就是汇集这些给定的偏好,而协商民主则与之相反,认为在公开、理性、包容的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可以改变他们的判断、偏好或观点,不断给出更为明智的判断。“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③[澳大利亚]约翰·S.德雷泽克著,丁开杰等译:《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尽管曾经有一些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和社会选择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但更多的当代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协商民主和社会选择是同一个立法程序的两个部分,社会选择的意见汇总是跟随着协商民主而来的。协商民主相当于一个“助跑”阶段,它有助于形成实质性的、平衡的公众讨论。这意味着在立法过程中所有不同意见、不同视角、不同论据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同时,这些讨论将会实质性地改变参与人的观念和对不同方案的偏好④Fishkin,James,When the People Spea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协商民主具有教育功能,理性对话可以进一步使人们的偏好变得理智而易于达成一致意见。正如扬·埃尔斯特所指出的:“比起单纯的加总或者过滤偏好,政治体系应当着意于通过辩论或对话来改变偏好……加总机制将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因为理性的对话将会带来一致的偏好。”⑤Elster,Jon,"The Market and the Forum",J.Elster and A.Hylland e.d.,Foundations of Social Choice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03-132.通过对话而达成一致,将让社会选择变成极为顺畅之事。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指望对话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许只是一厢情愿。协商和慎思对人们偏好的改变,只能是局部的、渐进的、潜移默化的。针对早期一些研究者的乐观猜测(协商可以达成共识)和另一些评论者的悲观预期(协商不能改变任何意见),李斯特提出了“元共识假说”(Meta-consensus Hypothesis),亦即,要想避免多数同意的悖论,我们并不需要追求绝对的一致意见,只需在“我们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足够了。通过讨论和对话,人们至少可以厘清关键分歧之所在,并且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立场,从而为进一步的汇集多数意见,打下良好的基础⑥List,Christian,"Deliberation and Agreement,"in S.W.Rosenberg 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Can the People Gover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64-81.。例如关于环保的议题,最后总可以归结为“环保—反环保”的冲突,然后,可以从左到右排列出一个谱系,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条线上确定自己的位置,于是,多维度的复杂分歧就变为单维度的峰值选择问题;即使对那些难以解决的多元价值分歧,也可以通过商谈清除极端偏好,达到“准单峰偏好”的状态①准单峰偏好(proximity to single-peakedness)的思想在于,即使我们不能排除多峰偏好,只要多峰偏好在人群中的比例足够小,多数决策仍然是最有效的汇总偏好的方式。参见Niemi,Richard G,“Majority Decision-Making with Partial Unidimensional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9,p.63,pp.488-497。。理性协商不必达成一致意见,却可以使多数决策成为最可行的汇总规则。于是,从协商民主到社会选择,构成了一个民主立法、民主决策的连续过程。
但笔者需要指出,如果把协商民主的价值仅局限于引导出形式意义上的“元共识”,则忽略了协商民主的重要功能——汇集信息和纠正不合理偏好。从根本上说,对话交流之所以有益,在于它能通过信息传递,让人突破狭隘视域的限制。宇宙无穷,规律无尽,人之视野不过如盲人摸象,每个人的认知都只是局部的,贵在自知其所知为局部,则不至于陷入夜郎自大的泥坑。对话协商的本旨,就是建构一个有效的交流机制,让信息自由流动,相互嵌合,集众人之力,共同组合出一幅巨大的镶嵌画,构建起一幅认识世界的完整图像。在对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入全面的基础上,佐之以专家之力,终将构想出更为正确的抵御风险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可以改变那些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偏好,让参与人自身变得更为明智。对话与协商的过程,可以带来更优质的新方案。本文图1描绘的专家给出的“可能性边界”和“可行方案”本身可能只是初步的意见,对话和信息流动可以提出新的应对之策,把可能性边界外推,同时改善若干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例如,有效实施的问责机制将提高传染病的预防能力,同时极大地降低预防成本)。当然,这些改善可能仅仅是“边际”的而不是根本性的,但看似微小的边际改善在很多情境下仍是关键性的。当现实中的市场由于自身局限无法发挥其汇总分散信息的作用时,思想市场作为汇集分散信息的工具,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与改进风险防控方案同样重要的是:对话情境可以实质性地改善人们的信念。在对话和讨论开始之前,人们的相关知识是不足的,不但对一己之私的考虑经常压倒所有其他的考虑,而且,也没法比较准确地定义个人利益。不难想象,如果一项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提案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那么,即使它可能最终有利于所有人,也无法得到多数意见的支持,这无疑是“多数人暴政”的另一个看起来较为温和、实质上却可能带来更严重后果的版本。事实上,人们在对社会问题作出判断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动机在起作用:一种是对事关个人利益的特定结果的逐求,一种是带有社会视角和伦理动机的价值判断。如果人们只考虑特殊利益,那必然会使社会选择难以达成,最终也会反过来损害“明智的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利益。这是因为个体的信息与知识往往囿于一隅,而对话会打破“坐井观天”的状态,开启另一个视角。比如,在环保和经济利益的权衡中,当人们意识到“健康”和“子孙后代”这两项价值维度的极端重要性,原先的观念很可能会松动,从而为开启新的、更为安全的社会提供可能。
然而,“通过对话改进偏好”的可能性,取决于参与人是否虚心明理、善于听取并接纳不同意见。如果参与人一开始就是反智的,或为某种先入之见裹挟,那么,这种交流必然会变成自说自话,甚至会由于沟通中的争端而引致观点的两极分化乃至严重对立,这也是协商民主的质疑者和批判者们时常论及的话题②Gardner,James A,“Shut up and Vote:A Critiqu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Life of Talk”,Tennessee Law Re⁃view,1996,p.63,pp.421-451;Sunstein,C,Going to Extremes.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但实证研究表明,相较于那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比如“英国是否应当保留君主制”),人们在环保、科技、能源、健康之类的话题上更容易被说服,也更容易接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理性价值观①关于协商民主影响和改变偏好的实证研究,参见Fishkin,James and Robert Luskin,2005。“Experimenting with a Democratic Ideal:Deliberative Polling and Public Opinion”,Acta Politica,40,284-98;Farrar,C.,et al.(2010).“Disag⁃gregating Deliberation’s Effects:An Experiment within a Deliberative Poll”,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0):333-347;List,C.,et al.(2013).“Deliberation,Single-Peakedness,and the Possibility of Meaningful Democracy:Evidence from Deliberative Polls”,Journal of Politics 75:80-95。最后一篇文章展示了不同类型话题的对话效果的差异。。而上述话题涵盖了风险社会很大一部分风险来源。这意味着促进风险防控方面的理性对话,更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从常理也可推知,关于风险防控方面的话题,与人的内在信仰关联不甚密切,且往往与常识相关,易于从现实中得到验证,而非单纯取决于固有的信念,所以人们的偏好比较容易发生改变,并且这种转变大多是有益的。鉴于现实中有关风险防控的对话过程并不仅仅是认知过程,还涉及利益分配,并且与社会公众初始的科学素养与政治理念相互关联,故而,对话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选择难题,但它至少可以打破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改进其偏好结构。这对于良法善治的达成与推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风险社会立法中的程序正义
社会选择的多数规则、平等开放的协商对话,实际上指向一个问题:风险社会的立法仍然要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正义原则。关于程序正义问题,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是探讨司法程序中的公平正义,例如审判公开、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非法证据排除等。但实际上程序正义应当贯穿于法律程序的始终,立法作为法律的源头,也必须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司法中的程序正义,传统上认为必须满足两项源于“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第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第二,公正而充分地听取各方意见。其他的程序正义原则,例如说明决定理由、决定前后一致等,都可以看作这两个原则的拓展和延伸②Shauer,Frederick F,“English Natural Justice and American Due Process:An Analytical Comparison”,William &Mary Law Review,18,1976,p48.。实际上,这两项原则体现着更为基本的理性决策原理,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正确合理的公共决策,就必须尽可能地广泛收集来自各个源头的信息,并且尽可能地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决策。立法过程,作为典型的公共决策过程,也必然要满足这样的原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也取决于它是否汇集了多数人的意见。Amy Gangl 概括了立法中正当程序的三个特征:第一,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的立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表达;第二,人们必须相信决策过程是公正而中立的,所有的观点得到了平衡考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优势观点;第三,他们必须信任他们的代表和立法机构能够负责任地作出决策。这三个特征概括而言,即“无偏而负责任的立法者充分地代表公众做出立法决策”,这可以看作自然正义原则在立法过程中的对应。Amy Gangl 等人的实证调查表明,立法程序越能满足程序正义原则,法律的正当性就越强,也越能得到民众普遍而自愿的支持③Gangl,Amy,“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and Evaluations of the Lawmaking Process”,Political Behavior 25,2003,pp.119-149.。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选择的合理标准(例如多数决策规则),离不开实质意义上的公民理性判断,协商民主则是达成理性判断的途径,立法中的程序正义则可以整合协调这两者,并将之落实于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之中。
立法者尽量处在不偏不倚的位置,并且在立法中增进公众参与,原本是立法过程应当谨遵恪守的基本原则。但对于风险社会的立法,很多人会发生疑惑——这样的立法是否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同时放弃了效率考量?在绝大多数领域和绝大多数情境下,公正和效率并不存在冲突,公正可以看作在多个有效率方案中的筛选机制①Kaplow,Louis and Steven Shavell,Fairness Versus Welfare,Cambridge,Massachuset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4.。但是,在风险社会的立法过程中,程序正义则仿佛与社会的整体效率发生了冲突。比如重大灾难发生而无法可依之时,临时制定的法律规范维护了社会总体的防控效率,但势必无法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也无法进行充分的协商对话,由此出现某种程度的协调难题。但笔者认为,这种冲突发生的场合是有限的,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多种类型、多重层次,必须区别对待,分而治之。需要固守的要领仍然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因为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风险,例如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都不会在转瞬之间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基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立法之前充分的公开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那些事关紧急状态的预警机制、应急预案,也必须在平日经过精心设计,并非临时拼凑可以奏效。总体而言,即使是风险社会的立法,程序正义仍然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这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实现最优防控的效率要求。当然,对于那些极其重大、猝不及防的风险,如果没有任何预警机制可言,或者已经设计好的预警机制临时发现有重大偏失,则应在设计时就预留出必要的裁量权限和裁量空间,便于行政机关临机应变。这是合宜的权变之策,也应当同时成为立法者预先考量的要点。事实上,这也体现了更为广义的利益权衡,因为“事急从权”之时,讨论和商谈的成本变得十分高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紧急时期,尽管不可能像平时那样从容审议,立法机构也应当留出听取民意和商谈讨论的空间和通道,以使法律灵敏地应对情势的变化,修正可能出现的错误。
众所周知,程序正义必须在现实的法律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通观中国的立法体制,其正式规定和很多举措,合理地反映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原则②例如,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立法须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第三十七条规定了法律案必须向社会征求意见,且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第六十七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草案也应当公布并征求意见。这些正式规定都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并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不断得到落实。。但也不可否认,我国的“部门立法”“关门立法”的弊端比较突出,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也时常流于形式。然而在风险控制、新技术规制等领域的立法,“专家立法”“关门立法”致使法律缺乏充分的程序正当性,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比之西方式的由利益集团、院外活动主导的立法体制,我国的立法机制或许更接近协商民主和程序正义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必须通过合适的途径得以实现。具体到风险社会的立法,大致而言,我们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第一,及时广泛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是个体和机构之间交流关于风险信息的过程,公众在此过程中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也获得风险防控的信息与知识。它虽不属于正式立法过程,却构成了风险社会立法的背景。我国的立法机构、政府和媒体不能仅满足于突发风险事件中的“舆情应对”,而应当在平日就增进沟通,加强教育,促进对话。立法机关应当拓展立法公开渠道,保障公民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方便快捷地获得立法信息,由此促使人们更为理性地认知风险,于防御风险、个体利益、子孙后代利益之间权衡轻重,避免懈怠无知与过度恐慌等极端情形,为风险社会的科学立法与法律的有效实施,打下良好的认知基础。
第二,公正无偏的决策机制。我国的立法程序比较严密,法案审议步骤相对严格,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局部利益的牵扯,在环境保护、新技术规制等事关重大风险防控的领域,法律碎片化、部门主导立法的弊端时有发生。在这些领域,探索委托利益无关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并加强人大代表、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是比较合理的改进途径。对某些重要的风险防控法案,甚至可以委托多个竞争性的第三方起草,形成更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也必须注意:立法程序的公正无偏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还应当有类似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实质保障。因为风险防控的预防和应急措施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损失,而社会从这些应急措施中的获益将会大于相关利益者的损失总和(否则风险防控就失去了意义),于是,必须在立法中对这些损失者予以补偿,以昭公正。这种补偿,也会使风险防控的结果趋向于“帕累托改进”,体现出我国法律代表人民利益的本质属性。
第三,积极有效的公民参与。目前我国采用多种形式鼓励公民参与立法,例如公开征集立法建议,公布法律草案并征求意见,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然而公民参与的力度和影响力仍有不足,难免存在走过场、走形式的弊端。风险防控措施涉及众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更应在立法过程中坚持人民本位,广开言路、海纳百川、集思广益,逐渐树立起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范式。知情是参与的前提,立法在规划立项阶段就应当公开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立法知情权;改进立法听证会的运作模式,让公众在听证过程中真正行使话语权,提高立法听证的实效性;适当延长法律草案征集意见期限,对采纳或不采纳特定意见说明理由;改进立法后评估体系,构建公民对法律提出改进意见的常态化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改进公民参与的有效方式,相关改进还必须有制度化的落实机制。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和基本框架的论证。现实中立法程序的改进,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其本身也要经过社会选择和民主程序方能成立,笔者在此只能作“点到为止”式的一般性勾画。尽管让理想中的制度“一步到位”并不现实,然而我们的基本旨趣是清楚的:“正义的理念”必须有序地转变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必须确定的基本信念。
结语与展望
处在当今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通过预先立法、确立规则的形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与危机,是事关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大事。然而,这件大事同时也是难事,不仅是因为对未知之事立法的技术困难,更在于人们具有多元的风险偏好和利益诉求,集结纷纭不一的意见而形成统一的社会规则,仿佛难上加难,实为一个重大挑战。本文认为,在风险防控的立法过程中,社会选择、协商民主和程序正义三者应当协调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鼎之三足,相互撑持:专家给出初步的风险调控方案与损益估算,经由社会选择过程,立法机构可以集结多数意见,选择较为合理的立法方案;协商民主则通过广泛的对话协商,充分整合专家意见与大众智慧,更加深思熟虑地设定和改进风险防控规则,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愚蠢”;体现程序正义基本原则的立法程序,则为此过程提供制度保障与实施机制,以公正的立法程序保证法律规则的可接受性与可实施性。此三者相互协调,共同形成风险社会立法的法理基础。
当然,笔者提出的只是一个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初步构架,如何在现实中充分实现这一构架,则需要相当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具体的制度设计。例如,如何让专家、公众与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密切结合,公众的意见和评判在最终的立法过程中将被赋予多少权重。当公众认知发生严重错误时应当如何纠正,风险管理的成本和收益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风险防控中受损民众的损失补偿的具体途径,这些都是中国法治乃至世界法治必须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中国自身也进入了后工业时代的“风险社会”,并且在全球的风险防控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领域的立法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高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不可忽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风险偏好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社会成员之中,以传统意义上的“开门立法”,综汇其信息,表达其利益;以当代之协商民主,纠正其偏差,化导其分歧;以立法中的程序正义,取得其支持,巩固其信念。使得社会选择、协商民主、程序正义“三位一体”,融合、整合社会的多元利益、多维诉求、多重价值,于风险防御的过程之中,保持社会的良序运行,从而化危为机——化“风险社会”之“危”,为“有机社会”之“机”。这是在风险丛生的荆棘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必由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