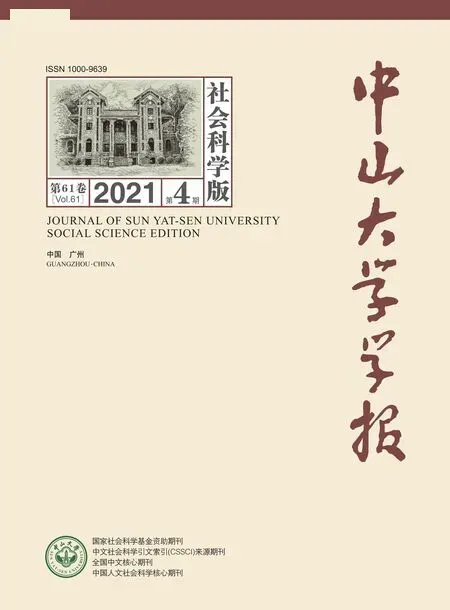编后记
本期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中国文体学研究”“文明与宗教研究”“大国治理的规模与效能”六个专题专栏,刊文凡19 篇。
从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这一百年既经历了中国的风雨与彩虹,也见证了世界的动荡与发展。本期刊发一组三篇文章,以为百年之庆留下深刻的学术印记。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于建党的纪念活动,纪念是为了不忘初心,纪念是为了总结历史,纪念是为了开创未来。而在这些纪念活动中,情感维度是始终贯彻如一的。对历史的敬畏,对英烈的敬仰,对人民的尊重,对政党的自信,对世界的感怀,构成了基本的情感意蕴。简言之,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也同时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情感史。这也印证了一个基本规律:情感不仅影响历史,也构建着自身的历史。政党、历史与情感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化和强化的学术领域。陈金龙的文章对此做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广州时期”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赵立彬的文章集中关注这一时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文学”大概属于可感知而难确定的一个概念,包涵着极大的弹性空间,所以喜爱“文学”的人可以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其实他们喜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至少有大量的非文学的东西被掺杂到“文学”的范围中了。这大概是文学研究者在直面现实生活中被标为“文学”的作品时深感不安甚至恐惧的原因之一了。大凡我们使用一种概念,敬畏是第一要务。如果概念本身在游离之中,则我们的认知和判断也必然是飘忽的。而要把敬畏落实,就必须对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进行精准的界定。至少名词的演变不等于概念的演变,文献的胪列不等于意义的剖析。一一勘察语境,把握同一系列概念之间的衔接点,才是界定概念的有效途径。就“文学”这一概念而言,古今中外皆在使用。中国最早的“文学”词源见诸《论语·先进》,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为“孔门四教”,“文学”一门的代表人物是子游与子夏。此后从范宁、皇侃到邢昺等人对《论语》的义疏中可知,“文学”一词大率以博通先王典文为要义。魏晋以降,相关辨析愈趋精微而各有其致,既有返归旧义,也有另立新说,当然也有弥纶群说者。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一文,立足“中国”的文学概念,但在梳理中国的“文学”概念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也时时参酌东西方对“文学”的种种界定,因此而带有一种兼具全球化、集成性与精准度的认知视角。这应该是“文学”研究中不可忽略、难以替代与值得敬重的成果。
2017 年深秋,我因为工作关系,曾到访巴黎,下榻的地方距离巴黎圣母院不过二三百米之遥。巴黎老城的建筑都已经有数百年之久,沧桑与古意酣畅而磅礴地弥漫在蓝天之下,令人震撼,恍然穿梭在老旧的时光之中,而我希望邂逅的就是雨果。我一直觉得,对巴黎而言,雨果就是沉淀在历史深处的一个精魂,氤氲着这个城市的气象和精神。而在广州的康乐园,就有个始终坚守着“我要回到雨果身边”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就是法语教授程曾厚。一个人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这是一种只有把学术当信仰的学者才有可能做到的。程先生早年求学北大,后来任教南京大学,侧重在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而他移席中山大学后,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对雨果作品的翻译、考订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上。他研究雨果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注重走进雨果的创作现场,将实地踏访、情感共鸣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所以他呈现出来的雨果是带着体温和鲜活的。他考订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的“巴特勒”乃是杜撰的收信人,连书信的撰写日期也是虚拟的。正在高城居埋头撰写《悲惨世界》的雨果对当时东方中国发生的圆明园劫难,并未及时关注,更遑论写这样一封书信了。他拍下了巴黎雨果故居“中国客厅”中诸多来自圆明园的陈列之物,他对《雨果和圆明园》一书的构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脚下到眼前再到书中的。
本期“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涉及碑文、传记、制义与小说四种文体,而跨文体研究成为值得注意之处。萧统《文选》收录的《头陀寺碑文》,内容上跨僧俗两界,中土建筑话语与佛教寺院、佛理结合,多种文化的介入,使寺碑文带着别样的风味。而传记文体与肖像画都以人物为中心,其间的关系乃是自然而当然的,尤其在内涵和功能上的重合更具意趣。胡大雷、赵宏祥二文于此各有专论。
“文明与宗教研究”专栏这次刊载了日本、匈牙利和美国学者的三篇文章,皆为专精之作,或探究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或评骘摩尼教审判绘画,或考订蒙古史书中提到的亦列、合答、豁孛格秃儿三位金朝将领的情况。选题冷僻一些,但三文并有发明。我读这三篇文章,竟然想起了1926 年9 月6 日王国维在陈寅恪到清华报到后致信罗振玉云:“顷陈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又《元秘史》原本本藏圣彼得堡者,今在伯希和处,拟设法照之,但所费甚巨耳。”元史、摩尼教、言语学、西学,这些关键词络绎奔会在一信之中,暗合本组文章者甚多,谅陈寅恪若在世,或因标题诱惑而略起浏览之心。
本质上说,要认知一流的哲学家,需要同样一流的哲学史家。因为面对思想的高峰,俯视的概率既然渺茫,仰视也同样失去部分意义,而平视的学术才有可能是端庄敬肃的。康德是西方哲学的永恒话题,其渊深博大的哲学思想令后人往往沉潜其中而难识东西,或窥其一鳞半爪而以为思致已尽,读不尽的康德大概是这样形成的。但学术史的格局从来就是多维的,对学术史的推进也需要多方合力才能完成,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责任和使命所在了。本期发表两篇康德研究的文章:一篇论康德对强化版本体论证明的系统批判;一篇疏解康德的意志理论。对康德研究来说,此二文是各照隅隙,还是偶观衢路,此当留待学术史的评判了。
中国是泱泱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大国与小国的治理模式肯定有异。其实不遑说国与国之间,即一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治理也存在差异。北宋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从滁州转知扬州,在扬州呆了一年多,因为深陷于当地各种政治纠纷之中而生厌倦之心,所以就以有眼病为由,管理不了大扬州,要求去小一点的地方,结果还真的如愿所偿去了颍州。看来地方大小对管理者的心态和能力也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国之大小也类此。本期由韩志明主持的专题“大国治理的规模与效能”刊文两篇,就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政府效能和政府规模之间的隐性张力展开论说,不仅契合历史,也契合当下,其意义是显在的。
时维七月,岭南暑气蒸腾。一期编讫,竟无诗兴,异哉!这让我联想起清人江弢叔有诗云:
我要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
今朝又被诗寻着,满眼溪山独去时。
我有“寻诗”之心,无奈诗无“寻我”之念,看来都市书斋终究难敌满眼溪山。下一期编后记当另觅林木水流胜处,待诗心涵养充盈,再把玩诸君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