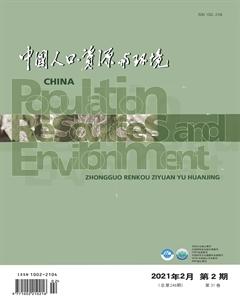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陈琦 胡求光


摘要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关键词 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制度互补;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2-0174-09 DOI:10.12062/cpre.20200615
随着海洋开发程度不断加快,海洋自然资源过度利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自然灾害等问题日趋严重,海洋生態保护逐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受传统“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中国近海以往长期处于“有人开发而无人负责”的状态,海洋生态损害成为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海洋生态问题从表象上看是工程、技术问题,而实质上是体制、机制和制度问题[1]。因此,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体系是有效遏制海洋生态损害的根本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尝试建立起从资源规划、监测督察到损害补偿等一整套的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体系。然而,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各类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法规不断增加,但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总体的治理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6]。
从制度视角,海洋生态保护低效的原因不外乎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三种类别。海洋生态损害涵盖陆源污染、填海造地、海上污染等多种类型,需要制定差异化、多样化的生态保护制度来适应不同生态损害类型的具体特征。制度缺失或制度不健全是早期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造成现实中的海洋环境治理实践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制度无效主要表现为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与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之间不相适应,制度设计初衷与实际结果出现错位、偏差。海洋的整体性、流动性与海洋管理的分散性、局部性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海洋环境治理失效的重要根源[7]。因此,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设计、实施难度大,需要兼顾陆海统筹的生态整体性和破除行政壁垒的管理可操作性两个方面。制度冲突则主要产生于制度体系逐步建成的后期,表现为不同管理制度间协调性不足甚至相互冲突,进而影响制度效应的发挥。从数量上看,中央及地方围绕沿海水域污染、海洋油气污染、海洋倾废管理、陆源污染、海岛保护等领域已经出台了多项管理法规和条例,海洋督察、海洋生态红线、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等制度已在沿海地区开展试点实践。这些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涉及了源头管控、过程监督、末端处置等多个环节,不同制度间能否有效融合从而形成全过程协同的治理合力尚有待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发展历程,挖掘其内在演进逻辑,在此基础上,从制度互补视角分析现有海洋生态保护制度间的互补需求,识别和诊断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现实问题,进而探究未来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无到有”“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
1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
1.1 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阶段划分
从中央及沿海各省市地区历年颁布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法规(表1)来看,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1)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74—1987年。受早期行政建制及“重陆轻海”传统观念影响,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由陆上相关职能部门兼管,尚未形成专门针对海洋的环境保护制度[8]。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后,日趋严峻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得到政府的重视,其中针对海上溢油污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于1974年颁布,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随后,1980年由国家计委、科委等五部委针对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开展了综合调查工作,拉开了中国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序幕[9]。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等沿海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专门从事海洋环境监管的厅(局)机构。1982年专门针对海洋领域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以该法律为核心的一系列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在此后5年期间相继制定,从而在法律层面初步确定了综合为导向、行业为基础的海洋生态保护基本格局[10-12]。
(2)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稳步推进阶段:1988—2017年。198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正式赋予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的职能,包括国家海洋局海洋分局在内的各地方海洋部门明确了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和监管的基本职责。此后,随着一系列涉及海洋倾废管理、海岸工程建设污染、陆源污染等具体海洋环境问题的管理法规颁布,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不断细化和完善。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制定了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海域使用统计制度等项重要法律规定,标志着海洋海域使用法律规范化管理的开始[13]。2006年“十一五”规划中,中央首次将海洋以专章形式列入,明确了保护海洋生态的总要求,海洋环境保护成为海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4]。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做出了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2014年以后,原国家海洋局专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海洋环境的有关保护、赔偿、监察等方面的政策文件,提出了包括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海洋督察制度、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一系列创新型管理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得到大幅完善。地区层面,以中央指导性规划文件为引领,沿海地区相继颁布了地方性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海域使用功能管理条例及海洋生态管理制度等相关政策文件。综上,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基础,1988—2017年期间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内容不断丰富,针对陆源污染、海岸工程污染、海洋倾废污染等各类生态损害的监管规范相继出台,同时涉及规划、督察及赔偿的一系列新制度手段逐步落地。
(3)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改革转型阶段:2018至今。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规范文件不断增加,但总体海洋生态治理效率依然偏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陆海分割造成的海洋生态监管职责不清晰、不协调,制约了地方层面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效果。为彻底解决海洋生态“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突出矛盾,2018 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原国家海洋局与水利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整合,新组建了自然资源部,同时将原国家海洋局对应的污染防治职能统一并入了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标志着海洋生态保护进入了陆海一体化治理的新时期。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湾长制”制度、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等陆海统筹治理方案逐步在沿海地方试点推广。例如,浙江省制定《杭州湾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了统筹陆域、海域污染物排放控制,实施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综合治理的总方针;山东省印发《山东省全面实施湾长制工作方案》,提出建立河(湖)长制、湾长制等统筹协调和联动机制,构建河海衔接、陆海协同的治理格局。总体而言,2018年以后,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开始由补充缺失向创新发展过渡,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成为新时期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
1.2 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趋势
纵观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总体呈现出三个趋势特征。
(1)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海洋环境问题主要涉及陆源污染、围填海、海上溢油等多种生态损害类型,其中以陆源污染最为突出。然而,长期以來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分别由负责河流排污监管的环保部门和负责入海排污口、海洋倾倒监管的海洋部门共同承担,这种两部门、两段式的监管模式导致污染防治责任主体不明确,海陆边界交错区域极易形成监管真空[15-18]。同时,环保与海洋部门间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缺乏有效的信息流动与共享机制,导致陆源污染治理效果大打折扣。为解决“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体制机制问题,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针对海洋环境监管部门进行改革,最终将海洋环境保护职能划归到生态环境部,为未来实现陆海环境一体化治理奠定了基础。
(2)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自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以来,一系列强制性较高、直接效果明显的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开始在中央及各地方层面广泛实施。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对于遏制中国海洋环境污染趋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行政手段过分依赖于政府的单一主导作用,存在社会参与程度不足、监管成本过大等突出问题,导致海洋生态损害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19-20]。基于此,自2014年国家海洋局颁布《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赔偿办法》以来,以生态损害赔偿为核心的市场激励手段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环境税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其他市场手段开始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企业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参与程度。此外,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作用,2016年国家海洋局颁布了《全面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海洋舆情常态化监测、预警、紧急应对和决策参考的一体化机制,为公众搭建参与海洋治理的平台,着力提升全民的海洋责任意识。
(3)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针对海洋事业方面制定了部分行政规范,但多属于对陆域经济活动的延伸管理,并未考虑海洋生态保护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上溢油污染成为影响中国海洋环境的突出问题,1974年国务院为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是中国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首部法律规定。1980年《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推动了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不断加快,海洋生态的损害程度持续加大,为此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提出在编制海洋功能区划基础上,明确海域使用的申请、审批程序,并对海域使用权管理和海域使用金制度做出具体规范,基本结束了海域使用 “无序、无度、无偿”的状况。此后,2007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首次明确海域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确立了海域使用权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从物权法这一基本法的层面保护了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合理开发海域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2009年和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相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海洋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颁布了地方性的海洋保护法律法规,成为海洋生态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动力
从外部来看,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变更受到资源环境压力、经济转型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社会角色转型、国际环保压力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从制度内部而言,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变实质上是需求-供给之间和成本-收益之间协调平衡的结果。
(1)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需求引致和供给滞后是促进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重要内在动因。纵览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一直在陆域,对海洋的开发程度十分有限,因此没有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客观需求,在此期间针对海洋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也基本属于空白。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对陆域资源的开发趋于饱和,开发利用海洋成为确保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一项必然战略选择,由此有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才开始引起政府管理者和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不断加快,海洋环境保护的客观需求与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现实中对陆源污染、各项海洋工程、填海造地项目、海上溢油事故等多种生态损害的监管迫切需要有标准化、强制性的规范制度作支撑,因而大量海洋生态保护政策及法律规范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
(2)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任何一项制度的变迁都涉及成本和收益两个层面,而制度的演进过程可被视为是成本制约和收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刺激大于预期成本带来的阻碍作用时,制度变革就会发生[21]。因此,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作是成本-收益驱动下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初始阶段,着力从海洋这一新领域中开拓经济利益是该时期的首要任务,而海洋生态保护问题尚未被提上议程,因而有关海洋的环境保护制度严重滞后于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负外部性逐步凸显,由于环保制度缺失,海洋粗放式开发所带来的大量环境成本只能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在此背景下,制定完善的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所带来的预期社会收益不断增加,中央及地方政府逐步改变过去片面追求海洋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导向,而开始重视海洋生态保护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绿色发展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针,保护优先、节约优先已经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海洋生态保护中存在的陆海分割监管、市场化手段缺乏、社会参与不足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刺激了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加快改革的预期,由此海洋生态保护制度迎来了从机构职能梳理到法律规范完善的一系列变革。
2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互补需求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元、复杂的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无效和冲突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尚有待进一步解答。按照制度互补性理论,制度往往不是孤立和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耦合与匹配,通过组合为“制度系统”而产生最大功效[22]。海洋生态保护问题涉及陆域和海域两个空间,受环保部门、海洋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多个行政机构管理,长期面临陆海分割、多头监管的现实困境。因此,海洋生态保护的客观复杂性决定了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互补尤为重要。这种互补性需求主要体现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
2.1 海洋生态保护主体的互补性需求
政府在海洋生态监管体制中扮演着核心引导作用。在十八大机构改革以前,中国海洋环境问题一直分属环保部门和海洋部门共同承担,造成现实中的污染监管责任主体不明确,各部门之间“各扫门前雪”现象十分突出。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政策目标导向差异,尤其在传统的“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影响下,地方政府往往纵容部分企业的污染行为,缺乏执行海洋环境保护的激励。以责任主体不清晰、污染边界难界定的陆源入海污染为例,在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条件下,参与陆源排污的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减排动力,同时在两部门、两段式的陆海分割监管模式下,陆海边界极易形成监管真空,最终造成陆源入海污染责任主体和治理执行主体的“双缺位”。为此,需要从陆海统筹理念梳理环境监管部门职责,依靠排污总量控制、“湾长制”等制度安排促进“上下游”不同政府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期形成陆海一体化的治理合力。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围绕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举措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解决陆海管理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明晰各部门间的职责,破除陆海分割下的行政壁垒,打造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补关系。现实实践中,中央层面的环境保护部制改革已经完成,但地方层面的陆域和海域环境治理职责仍有待进一步梳理。
另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式的传统环境监管模式存在“政府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监管成本巨大,因而鼓励企业、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研究表明,通过促进企业、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海洋生态保护,能够有效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环境决策的公共理性,降低海洋环境风险,减少在重大环境决策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抗争和社会不稳定风险[23-24]。从中国现有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来看,虽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已在政策规划中多次提及,但缺少具体的实施规范、激励措施。因此,总体而言,从主体互补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还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问题。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各类部门之间等政府主体职能关系,如何引导企业、社会公众等主体切实参与到海洋生态治理中,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的治理关系,这些核心问题均有待从制度层面解决和落实。未来亟须围绕地方海洋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海洋生态保护市场和社会主体培育等方面制定详细、具体的规划方案。
2.2 海洋生态保护手段的互补性需求
海洋生态保护手段可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社会参与型四个类别。其中,命令-控制型手段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传统核心模式,但海洋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现实已经证明单凭政府一己之力难以实现海洋生态的高效治理。海洋生态保护的市场激励性手段主要是通过向市场行为主体征收排污费而减少其污染行为,同时对于为海洋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资金补偿和支持。市场激励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政府所面临的监管压力,具有低成本、高刺激、灵活性强等优点,但同时也有间接性、无法清晰界定产权的缺陷。信息公开型手段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和环境信息公开两种形式。一方面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和环境监测数据统计能够为政府提供完备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及时公开海洋环境信息,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也是确保社会参与型手段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环境保护能够提高政府环境决策的公共理性,降低海洋环境风险,是传统政府环境规制手段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面临实施过程复杂、决策效率偏低的不足。因此,不同的生态保护手段既相互独立,各具优势,同时又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性需求,而单一的生态保护手段往往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问题,可能面临制度无效困境。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中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一直占比较大,存在“制度拥挤”的问题。尤其是在面临陆源污染、湾区环境治理等跨行政区的海洋生态问题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行政手段往往存在冲突,从而引发治理乱象。相对而言,其他三类政策手段则主要存在创新性和制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政策手段的适用情景、使用条件、执行流程等缺少清晰界定,导致海洋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监督治理等一系列市场、社会手段的实际执行率低,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5]。以海洋生态补偿为例,尽管山东、广西、福建等地方积极探索制定出台了管理办法,但相关规范文件仍停留在方向指導层面,操作性不足,缺乏具体配套的技术实施方案。例如,山东省于2016年印发《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系全国首个海洋生态补偿管理规范性文件,但2019年即被废止,与山东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制度的高效落地和广泛实践形成鲜明对比(自2014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以来,已连续5年完成空气质量赔偿资金缴纳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综上,中国海洋生态保护手段主要面临精准性、可操作性不足等困境,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海洋生态损害问题。未来应积极探索海洋生态保护政策工具创新,依据具体情景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搭配,推进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保障政策落地、落实。
2.3 海洋生态保护过程的互补性需求
海洋生态保护的过程可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个阶段,其中事前控制主要是对海洋生态损害的事前预防,包括海域使用规划、海洋生态红线、海洋排污总量控制等手段。海洋生态保护的事前控制能够有效降低污染的治理成本,是最直接、最经济的环境治理方式,然而由于企业行为的不可控性以及管理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事前控制实际执行的效果较差。事中控制主要是对围填海、近岸工程等海洋开发活动进行的实时监督、指导,以及时纠正、调整可能的生态损害行为,具体包括海洋环境监测、海洋信息收集与传递、海洋督察等。事中控制过程相对而言较为灵活,能够依据环境信息及时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但总体实施成本较高。事后控制是在海洋生态受损害之后,对生态损害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开展责任认定追究和生态损害赔偿,并采取措施加以修复。在海洋污染物中,除少数的近岸固定点源排污外,大量的污染物是以区域或流域的形式进入海洋,属于面源污染。现实中针对面源污染的事后控制面临责任主体不清晰的突出困境,相比较而言事前和事中控制往往更有效果。以杭州湾治理为例,毗邻长江口的杭州湾是一个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其陆源入海污染中大部分来自长江口的污染物输移,而长江流域沿线排污主体复杂且污染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因此,针对杭州湾海域的污染治理应重点做好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的协调配合,通过建立事前的河海系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同时加强事中的入河排污和入海排污实时监管及督察,打造河海联动的跨区域责任共同体,以此倒逼陆源排污地区自觉减排。
由于不同阶段措施相互联系紧密,在实施过程中,也应着力避免因制度冲突而影响环境保护的全局效果。例如,事后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应充分考虑事前的海域使用规划、海洋生态红线等,避免事前与事后执行标准相冲突;事中的海洋环境监测标准和评价体系应适应事后海洋生态补偿、领导环保责任追究的实施需要,避免事后处置环节的执行“无标可依”。总之,不同阶段的海洋生态保护控制过程各有优势和不足,具有明显的互补需求,在实践应用中要加强交叉配合,建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全过程协同的系统治理体系。
3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改革路径
立足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和互补需求,针对当前保护主体的制度缺失、保护手段的制度无效和保护过程的制度冲突等突出矛盾,对海洋生态保护制度进行梳理、改进和完善,做好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建立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主要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是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3.1 制度补充: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1)加强领导体制构建,尽快落实地方海洋生态监管机构改革。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落实党政主体责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受海洋公共性、流动性特征影响,中国海洋环境保护长期面临陆海分割、监管责任不清晰、部门间权力交叉重叠等突出问题。为此,一是对接“河长制”建立“湾长制”“滩长制”,逐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海洋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基于海洋生態系统管理理念设立总湾长,并依据地方行政层级向下逐级设立各级湾长,各级湾长则应由地方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兼任。二是加强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问责,以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为基准,围绕自然岸线保有率、海水质量、滩涂湿地保护等指标,建立以改善海洋环境为核心的专项目标责任体系,制定科学、完备的评价指标和考核方案,将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奖惩晋升的重要依据[26]。三是以中央部制改革为基础,立足垂直管理理念整合市、县级海洋环境监管机构,理清中央和地方的海洋环境监管职责,形成扁平的市县、省、中央三级架构,建立以各地方党委、政府为责任主体,以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为执行主体的海洋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管理体系。四是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理念[27],针对湾区、滩涂、入海口等特殊生境,由省级政府探索设立专门的环境治理机构,由其负责对所辖市县地方政府及环境管理部门进行统一调配,实现跨区治理,从而打破行政壁垒,推进从山顶到海洋的一体化监管[28]。
(2)建立海域使用权、排污权交易市场,激励企业自发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一是针对产权相对明晰的养殖海域,开展开放式养殖用海海域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试点改革,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规范企业、养殖户用海秩序,破解养殖用海乱象,实现“依法用海、有偿用海”目标。二是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陆海污染流动特征等客观因素,在污染排放配额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陆源污染重要源头地区收紧,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上游流域和下游沿海地区之间建立污染排放权一级交易市场,加强排放权在不同行政区间的流通。同时,探索开展跨行政区海洋生态转移支付试点工作,建立考核奖惩制度,让排污严重、考核未达标的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向达标地区进行补偿,提高地方海洋生态保护积极性。三是明确地区污染权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拍卖、挂牌为主要手段的二级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借助价格机制促进排污权的良性流通。四是健全企业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和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积极引入第三方开展生态修复,加强海洋生态补偿金使用和治理成效的公开透明性,借助市场激励作用引导企业自发减排。
(3)推动海洋生态治理重心下移,打造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机制缺失一直是中国海洋生态保护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是要适度放宽海洋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准入标准,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培育海洋环境NGO组织。二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制度,明确海洋环保组织及社会公众在环境诉讼中的主体资格,保障社会主体的环境利益维权渠道的后发通畅,确保海洋环保NGO的职能有效发挥[29]。三是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知识普及和公益宣传,提高全民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增强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环境监督、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2 制度修正:优化创新治理机制,提升制度适应能力
(1)创新完善市场激励型、信息公开型等政策手段,提升政策应用广度和深度。以往除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发挥较大效力外,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公众海洋污染检举等市场型、社会型手段普遍应用乏力。为此,一是要加快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建设,制定技术方案细则,借助环境税收、政策补贴及奖励罚款等手段为成本-收益市场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市场激励作用贯穿污染源头防治、污染过程监管及污染责任追究的全过程。二是依托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大数据信息平台,完善海洋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确保环境治理信息及时、高效传导,加强海洋环境质量信息和海洋生态治理信息的互联互通。三是要完善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公共区域或通过电子网络形式公开举报环境损害的投诉方式,扩大社会参与治理的范围,从制度层面明确社会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方式、渠道及程序。
(2)加强政策工具综合应用,探索政府-市场-社会立体式治理机制(图1)。从系统论视角,充分考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机制的职责分工及其相互制衡,灵活配置各类政策工具,实现规划决策的协同会商、环境信息的协同监督和污染防治的协同参与,建立扬长避短的治理体系。一是搭建海洋环境利益相关方的圆桌对话平台,开放环境决策过程,借助问卷调查、公开听证会、公众和企业代表座谈等多种方式听取决策意见,让海洋生态保护成为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事业。二是在环境信息的监督环节,引入环保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为第三方监督,建立问题报告、民意反馈及治理信息公示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协同监督格局。三是在污染防治层面着力打造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长效调节的协同模式,由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海洋环境状况和排污总量情况,做好海洋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的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内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市场化排污交易市场,以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倒逼污染企业减排。
3.3 制度协调:强化制度衔接配合,建立有机治理体系
(1)探索“海洋生态红线+海洋生态补偿”模式,促进事前和事后控制有效协同。事前的海洋生态红线区规划为区域间海洋生态补偿提供了基础性的参照依据,而事后的海洋生态补偿是促进海洋生态红线制度长效落实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建立“海洋生态红线+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模式的关键是将海洋生态保护的纵向和横向补偿手段融入受益区和红线区之间的利益平衡之中。一是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基准,参照“贡献大者得补偿多”的原则,确定海洋生态红线面积大的地区为优先补偿对象。同时参考红线区生态质量标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情况、产业发展受限程度、贫困情况等因素,从机会成本角度科学制定红线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二是依据未来的海岸带专项规划安排,建立健全重点海岸带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政策,结合中央与地方环境治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各地环境保护的减收增支情况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加大对偏远红线区、经济落后红线区的补偿力度。三是立足陆海统筹理念,建立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受益地区向生态保护红线地区进行资金和非资金的多元补偿。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面作用,探索资金补贴型、园区合作型、社会保障型、技术扶持型等多元补偿方式,实现红线区与周边地区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统一。
(2)探索“海域排污总量控制+海洋环保领导责任制”模式,推动防治职责统一。作为一项末端处置手段,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为逐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海域排污总量控制责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能够真正确保各地区排污总量控制有人负责、有人落实、有人监督。为此,要将海域排污总量控制责任纳入地方政府的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中,借助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引导地方政府落实排污控制计划。一是在各地方海洋环境保护目标任务中,增加海域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考评标准,确保与其他环境考核标准协调一致,避免重复与冲突。二是提高海域排污控制效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依据各行政地区年度入海污染排放控制情况,对减排工作成效显著地区予以奖励,对超标排放地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党政干部责任。三是完善责任逐级落实、监督逐级推进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省、市、县、区海域排污总量控制目标,逐级压实排污控制责任,通过任务分解将职责落实到各个涉海监管部门,同时省级海洋部门要做好對各市县级总量控制成效的评估和监督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3)探索“海洋信息服务+X”模式,打造网络化、智能化生态治理系统。无论是海洋环境治理的源头控制、过程监管还是末端处置过程,均离不开海洋信息服务的支持。推动“海洋信息服务+X”模式就是将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各海洋环境治理手段中,确保实施过程中资源环境信息和管理决策信息的有效收集、存储、加工处理和传导反馈,实现网络化、信息化治理。一是创新海洋信息传递渠道,为多主体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全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建立海洋环境治理信息平台,推动海洋信息传递大众化、扁平化发展,打造政府为主、公众参与的多元立体式治理体系。同时,搭建主体间的海洋信息传递、沟通渠道,增强主体间的互动性,打破信息孤岛怪圈,提升数据信息的使用效率。二是提高海洋信息传递技术水平,推动各环节海洋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化。通过建立海洋环境治理信息化平台,将公众、环保组织和企业的诉求、建议吸纳到海洋环境治理的决策中,增强数据采集、挖掘共享能力。开展跨部门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增强政府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的能力,在生态红线制定、海域排污总量评估、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等复杂领域建立“模型-数据-分析”的信息化决策模式,为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化、智能化、可视化的决策参考。三是延伸海洋信息传递服务范围,保障海洋环境治理的预测预警精准化。建立海洋环境治理大数据库,增强对海洋环境污染源、海洋灾害发生概率、海洋环境质量演化效应的研判能力,运用大数据融合模型对资源、环境和管理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优化、调整治理策略。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海洋环境污染信息进行动态监管和实时传送,确保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共享共用,推动海洋环境治理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变。
参考文献
[1]沈满洪.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治理创新[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84-91.
[2]王森,胡本盟,辛万光等我国海洋环境污黎的现状、成因与治理小.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6.
[3]李京梅,苏红岩.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评价[J].海洋环境科学, 2016,35(4):512-519,539.
[4]丁黎黎,郑海红,刘新民.海洋经济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评估[J].中国科技论坛, 2018(3):48-57.
[5]史春林,马文婷。1978年以来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J].中国软科学,2019(6):1-12.
[6]胡求光,沈伟腾,陈琦.中国海洋生态损害的制度根源及治理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7):113-122.
[7]巩固.欧美海洋综合管理立法经验及其启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3):40-46.
[8]张海柱.理念与制度变迁:新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变迁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6):162-167.
[9]仲雯雯.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的演进分析(1949—2009)[J].理论月刊,2013(2):121-124.
[10]翟勇.《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度设置对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贡献[J].海洋环境科学,2009,28(2):215-217,227.
[11]王刚,宋锴业.中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变迁、困境及其改革[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2-31.
[12]马英杰,赵敬如.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制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展望[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7(3):61 -67.
[13]YU J K, MA J Q, LIU 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in China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20,189: 105157.
[14]王印红.中国海洋环境拐点估算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8):87-94.
[15]SMITH H D, MAES F, STOJANOVIC T A,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land an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J].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2011, 15(2) :291-303.
[16]顾湘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府际协调研究:困境、逻辑、出路[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2):105-111.
[17]陈亮.我国海洋污染问题、防治现状及对策建议[J].环境保护,2016,44(5):65 - 68.
[18]姚瑞华,张晓丽,刘静等.陆海统筹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几点思[J].环境保护,2020,48(7):14-17.
[19]GRUBY R L, BASURTO X.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large marine commons: politics and polycentricity in Palaus protected area network[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4, 36:48-60.
[20]郑建明,刘天佐.多中心理论视域下渤海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2 - 28.
[2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45-47.
[22]MILGROM P, RPBERTS J. Complementarities and systems: understanding Japanese economic organization[J]. Estudios economics, 1994, 9(1):3-42.
[23]CHEN L, GANAPIN D. Polycentric coastal and ocean management in the Caribbean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harnessing community-based actions to implement regional frameworks[J].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6, 17(3):264-276.
[24]许阳.中国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概览、变迁及演进趋势:基于1982—2015年161项政策文本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65-176.
[25]杨振姣,吕远,范洪颖,等.中国海洋生态安全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研究[J].太平洋学报,2014,22(3):91-97.
[26]ZHAO P, LU W H, SONG J, et al. Natural coast protection and use in China: implications of resource protection ‘redlinepolicies[J]. Coastal management, 2016, 44(1): 21-35.
[27]孟伟庆,胡蓓蓓,刘百桥,等.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概念、原则、框架与实践途径[J].地球科学进展,2016,31(5):461-470.
[28]王琪,丛冬雨.中国海洋环境区域管理的政府横向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4):62-67.
[29]GUTTMAN D,YOUNG O,JING Y J, et 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20:126-135.
(責任编辑:刘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