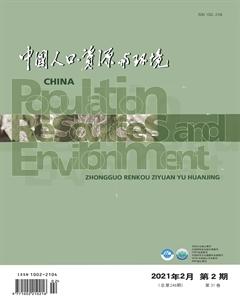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秦天 彭珏 邓宗兵 王炬



摘要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
关键词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2-0061-10 DOI:10.12062/cpre.20200613
在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实现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2011年“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农业源水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2014年原农业部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防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强调“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可见,中央政府不断提高农业环境规制力度,以实现农业经济绿色转型。然而,《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显示,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仅为38%左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也仅有64%,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收效甚微[1]。那么,为何中央政府如此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却未能实现农业面源污染的根本好转?不禁令人深思。环境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有利于因地施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我国环境事务管理权力逐步向地方政府倾斜,鼓励地方参与环境污染治理。但随着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晋升激励等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牺牲非经济职能目标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扭曲了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诱发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与“竞次”竞争,最终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率低下[2-3]。可见,环境分权可能是制约环境规制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那么,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关系到底怎样,环境分权又是否真的会弱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呢?若是,环境分权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促进环境规制倒逼减排?厘清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优化环境分权体系,提高环境规制效率,而且对实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形成了“抑制论”和“促进论”的观点之争,即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占优,还是“倒逼减排效应”占优。“抑制论”从静态视角出发,指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会造成生产者“遵从成本”的增加,不仅不利于生产者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减排,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反而扩大了污染排放[4-5]。“促进论”则从动态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减排效应,其中最核心的理论莫过于“波特假说”[6],该假说认为提升环境规制标准会倒逼生产者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创新,通过“创新补偿”抵消“遵循成本”,达到污染减排的目的。众多学者基于实证检验均支持“波特假说”[7-10]。此外,不少学者指出受产业结构[11-12]、对外直接投资[13-14]等因素影响,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门槛特征。
上述研究结论虽然莫衷一是,但多是基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假定政府始终将社会福利作为最高追求。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则摒弃了“福利政府”假设,提出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地方政府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征[15]。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与环境治理目标一旦出现激励不相容,往往会导致规制失效[16],而中国式分权改革正是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重要成因[17-18]。基于此,更多研究探讨了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但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部分研究指出在环境分权体制改革背景下,激励机制扭曲和中央政府约束力不足造成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存在策略互动甚至产生“逐底竞争”,弱化了污染防治绩效[3,19]。另一部分研究认为环境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间“争上游”的合作竞争,更高的分权程度带来更高的环境标准,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20-22]。
目前学界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绝大多数限定在经济因素的讨论上,其中包括化肥施用强度[23-24]、人口结构[25-26]、经济发展水平[27-28]等。然而,外在的经济因素不能独立于内在的制度因素。由于价格机制无法反映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成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常态,环境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但是,受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偏向的污染治理政策等因素影响,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29]。特别是,当政绩考核机制强调经济指标而忽略农业环境的刚性需求时,地方政府会为了经济指标而掩盖农业面源污染甚至袒护污染行为,造成不利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逆向选择行为[30]。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有進一步改进空间。第一,尽管上述研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方面考察,但对环境规制这一重要制度因素的研究有待深入,而国内研究更多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关实证研究仍显不足。第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集中于工业污染领域,二者关系多沿着“环境分权→政企合谋→环境污染”的逻辑链条展开。然而,由于农业面源污染隐蔽性、分散性等特征,仍沿用这一逻辑链条难以做到逻辑自洽,需要从理论层面重新审视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内在逻辑。第三,部分学者剖析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相互关系,但研究维度基本为两两关系分析,鲜有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进而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基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作用机理;二是实证检验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并探究可能存在的环境分权最优区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
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规制成为政府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必要手段。目前农业环境规制主要包括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种手段。就命令控制型手段来看,地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对化肥、农药、畜禽、秸秆等不同类型污染源提出了明确治理措施(如化肥农药登记制度、划定禁限养区域等),从源头上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同时,农业环境标准的日益严苛刺激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和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不断优化,驱动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即实现“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带来农业面源污染的降污减排。就经济激励型手段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各类财政补贴推进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补贴方案通常对绿色处理技术都有较高要求,驱使绿色金融和专业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3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激励的方法,采用“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农民朝着亲环境生产方式转变,营造农民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的良好氛围,有助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形成,降低隐性经济规模,从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因此,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得到有效缓解,污染治理效率得到显著提高。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利于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2.2 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
根植于财政分权理论的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指出,“用脚投票”机制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真实偏好,分权的环境管理体制更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居民偏好选取因地制宜的政策类型。因此,环境分权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效果[32]。然而,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模式(上级政府具有下级政府官员晋升的绝对权威)和晋升考核内容(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重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由于生产性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环保性支出的边际社会价值,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将“社会福利多任务委托”过滤为“经济增长的单任务委托”。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动机利用手中权力截留甚至挪用农业环保专项资金到其他生产性开支中,引发“粘蝇纸效应”,致使农业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凭借环境管理权力,降低利税多、吸纳就业强但污染严重的大型企业准入门槛,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也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从农业生产者转化为产业工人,而农业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化肥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村环保主体的“断层”,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高、周期长、难度大,地方政府为短期实现区域利益,多采取“重城市轻农村”治理策略。进一步地,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无法有效治污只能迅速移污,城市通过“污染下乡”和“绿化进城”等方式侵占农村环境资源,而环境分权赋予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自主权更成为污染转移的“助推器”,进一步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 环境分权程度的提升不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2.3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
环境分权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环境事务管理体制,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环境事权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受托方完成部分环境规制职能。就现实情况来看,虽然环境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决定环境规制水平的高低,但并未给予其相应的监管与约束,使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提升了环境规制弹性。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往往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渗透引起水质污染,因此其规制成效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搭便车”现象成为常态。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和自身本位利益,“我污染,你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策略,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上的策略互动,形成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地域邻近的地方政府不愿规制成效的正向溢出被无偿占有,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削弱了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导致省区、市区、县区交界处环境问题突出。而这些交界地带多散布农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居高不下成为必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地方政府出于自利性动机,对可能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的环境规制象征性执行,甚至消极执行,彰显地方政府的“牟利型”动机[3]。因此,牟利型动机辅之以环境规制执行上的自由裁量权,为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打开了“机会之匣”,从而弱化了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倒逼减排效果。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 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因具有“逐底竞争”的特征而不利于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引发“绿色悖论”效应。
3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3.1 模型构建
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滞后性,当期往往受到前一期的影响。同时考虑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EIit表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ER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EDit表示环境分权程度;Cit代表一组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业结构、人口密度和技术水平,μi、vt为地区和时间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为探究环境分权是否會影响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与环境分权的交互项,构建模型(2):
3.2 变量说明
(1)农业面源污染 (EI)。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残留于土壤的化肥或农药流失,农业畜禽养殖排污等,具有分布广泛、潜伏性强等特征,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难于统计和估测。基于清单分析的单元调查评估法由于形式简单、应用性强,成为大范围农业面源污染核算的一种重要方法,目前该方法已得到普遍采用。因此,本文借鉴清单分析的思路,对我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进行核算。核算污染物包括总氮(TN)、总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三类污染物,产污单元包括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和农业固体废弃物污染4个方面,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EI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代表农业面源污染在土地上的积聚水平。AL为研究区域的农用地面积;E为农业污染物排放量;q为产污单元的个数;EUi为i污染单元污染基数,具体为化肥折纯量、禽畜养殖量、农作物产量、水产养殖量;ρi是i污染单元的产污强度系数;ηi为相关利用效率的系数;EUi和ρi的乘积PEi指忽略外在因素时i产污单元的潜在污染产生量;Ci为i污染单元的排放系数,由单元和空间特征决定,表征考虑区域管理因素和资源利用对农业污染物排放的综合影响。各项指标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等取值重点参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源系数手册》以及吴义根等[26]、汪慧玲等[33]相关研究。
(2)环境规制强度(ER)。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相关数据较难获得,且数据质量相对较弱,学界对这一指标的测定方法尚未统一。目前研究主要从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个维度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前端治理维度主要包括环境法规颁布数量、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等替代变量,末端治理维度主要包括排污费收入、排污监察次数等替代变量。出于农业面源污染末端排放隐蔽分散的考虑,将规制重心放在可控的投入端成为目前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方向[1]。因此,基于指标完善性和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借鉴展进涛和徐珏娇[34]的做法,采用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额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3)环境分权(ED)。环境分权是一种以分权为基础的环境管理与事权划分机制。祁毓等[19]、白俊红和聂亮[20]指出,机构和人员编制是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和职能的载体,不同层级政府环保机构人员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环境事务权力分配,且不同层级政府环保机构人员占比的变动更能反映环境管理体制变动。因此,本文采用不同层级政府环保部门的人员分布特征来刻画环境分权指标。具体环境分权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Lepit、Popit和GDPit分别表示第i省第t年环境保护系统人员数、地区人口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Nept、Popt和GDPt分别表示第t年全国环境保护系统人数、全国总人口规模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加入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1-(GDPit/GDPt)]对环境分权指标进行有效平减。另外,本文将环境分权进一步细分为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三项细分指标的测算与式(4)相似,只需把环保系统人员数替换为细分指标相应的人员数即可。
(4)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选取控制变量如下: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各地区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城镇化率(URB)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农业结构(AS)采用牧业与渔业产值总和与农业生产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乡村人口密度(P)采用单位耕地面积上乡村常住人口数来衡量;技术水平(T)采用科技研发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3.3 数据来源
因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选取2005—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西藏及港澳台)作为考察样本。环境分权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科技研发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额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本文涉及的其他变量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针對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的问题,本文依照数据呈现的变化趋势进行平滑处理。为消除价格影响,本文对各省市人均GDP、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等数据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
前述计量模型属于动态面板模型,为了规避潜在的内生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联立偏误导致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农业面源污染可能存在的动态依赖性,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前述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引用农业面源污染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1报告了包含环境分权及其分解指标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AR(2)的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二阶序列不相关,模型设定合理。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总体上是有效的。列(1)~(4)中农业面源污染的一阶滞后项(EIt-1)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前期的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了当期的水平,即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估计系数均为负且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凸显,假设1成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矫正粗放式农业投入模式,驱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进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改善农业面源污染,假设2成立。比较各系数可以发现,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正向作用最大,影响系数为0.070 7。究其原因,环境监测分权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对本辖区的农业面源污染状况做出“自我评价”,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见效慢、周期长,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修改或者隐瞒对其不利的环境监测数据,不利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环境行政分权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行政分权有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行政分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达到人员与资金的有效配置。地方政府在地方环境事务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与信息优势,环境行政权力的下放有利于地方政府协调环保政策“本土化”,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为了考察环境分权是否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果,引入了环境分权及其分解指标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1中所示。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假设3成立,这与黄清煌等[35]的研究结论相似。环境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环境治理自由裁量权,出于“搭便车”的自利动机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惰性”,甚至引致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趋劣竞争”,不利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36]。从环境分权分解指标来看,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环境行政分权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地方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监察的具体机构,其预算和任命受制于地方政府,面临独立性缺失的现实约束。为避免环境监察与经济利益产生冲突,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监察可能会趋于表面化和形式化,使环境规制的减排绩效大打折扣。同时,在经济利益的约束下环境监测分权导致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降低,环境规制的着力点无法做出及时调整,降低规制绩效。
从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先增加后降低,呈现倒“U”型特征,EKC假说成立。城镇化(URB)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快速城镇化使大量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劳动力“过度”流失造成的化肥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源头排放。农业结构(AS)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农业结构是农业面源污染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依据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学特征,养殖业的污染排放强度高于种植业,养殖业比重上升必然带来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增加[26]。乡村人口密度(P)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乡村人口密度逐渐减小,农村出现“三留守部队”(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其环保意识较欠缺,往往导致畜禽粪便处置不当、过量施用化学品等行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严重失控。技术水平(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科技研发带来的绿色、清洁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污染治理效率,从而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4.2 区域层面的估计结果
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禀赋与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验证实证结果在不同区域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并设置地区虚拟变量,引入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深入讨论区域异质性影响。通过表2的实证结果对比可知,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成立。环境分权及其分解指标在东部地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为正,表明环境分权及其分解指标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则不显著。可见,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有限,地方政府无法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而将环境分权视为经济发展的“保护伞”,倾向于把更多精力投入对GDP增长贡献更大的非农领域,驱使地方政府非完全执行国家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政策,遏制了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减排效果,“绿色悖论”效应显著。
5 进一步讨论:基于门槛效应的再检验
5.1 模型设定
前文已初步证实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无法如期发挥,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是否因环境分权程度不同而具有非线性特征?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环境分权区间呢?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Hansen[37]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非线性门槛特征,以期获得最优环境分权区间,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经验性的理论支持。
本文在式(2)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以农业面源污染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环境分权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以探讨当环境分权大于或小于特定的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5.2 门槛个数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在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前,需要对样本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以确定门槛的个数。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F检验统计量,以及使用“自抽样法”(bootstrap)重复抽样500次计算概率值P值和临界值列于表3。可以看到,無论以总体环境分权还是分类别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作为门槛变量,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门槛变量存在三个门槛值。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模型应该设为三重门槛模型。
待门槛效应通过检验之后,需要对环境分权的门槛值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各门槛变量的门槛值和相应的95%置信区间。由表3可知,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的三个门槛值分别为0.848 5、0.938 3和1.107 8。
5.3 门槛回归分析
确定了门槛值之后,根据式(4)对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以环境分权(ED)为门槛变量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整个样本划分为四个门槛区间,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着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三重门槛效应。具体来看,当环境分权低于第一门槛值时(ED≤0.848 5),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在1%水平上为负但不显著;当环境分权跨过第一个门槛值并小于第二个门槛值(0.848 5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主要结论如下:①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环境行政分权则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负向作用。②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为正,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负转正,过高的环境分权程度将无益于环境规制减排效应发挥。
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①中央政府适度增加环境管理权力。本文核心结论显示,环境管理权力过多配置给地方政府会恶化环境规制减排绩效,中央政府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上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集权,但针对不同类型环境管理权力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度下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行政法规制定、农业资金配置和农业环境治理规划等方面的信息优势。环境监察权力和环境监测权力应逐步上移,保证环保督察的可靠性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地方政府因自利动机而造成的逆向选择行为。②制定差异化环境分权策略。地方政府环境事权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当地情况,因地制宜推动地方政府环保职能的发挥[40]。东部地区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较为明显,应适当加大地方环境自主权,进一步增加环境基层地区环保人员数,完善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职能,提高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率。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环保系统人员数不宜继续增加,并考虑进一步压缩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上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设定农业生态环境底线标准和奖励门槛,对区域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行为形成有效约束。③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体系。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这就要求各地区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统筹协调监测数据与监测手段两个方面,结合第二次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加密和固定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点位,整合完善已有监测体系。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溢出特征,地方政府应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区域协作,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数据共享、技术人员调配等多方面跨区域联防机制,形成“联防联控”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金书秦, 邢晓旭.农业面源污染的趋势研判、政策评述和对策建议[J].中国农业科学,2018,51(3): 593-600.
[2]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07,42(7):36-50.
[3]张华, 丰超, 刘贯春.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 财经研究,2017(9):33-49.
[4]GRAY W B, SHADBEGIAN R J. Plant vintage,technology,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6(3): 384-402.
[5]徐志伟. 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基于“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财经研究,2016,42(3): 134-144.
[6]PORTER M E,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7]李永友, 沈坤荣. 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8(7): 7-17.
[8]宋马林, 王舒鸿.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3(3): 122-134.
[9]RUBASHKINA Y, GALEOTTI M, VERDOLINI 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sectors[J]. Energy policy, 2015, 83: 288-300.
[10]于斌斌, 金剛, 程中华.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J]. 统计研究,2019,36(2): 88-100.
[11]原毅军, 谢荣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9.
[12]钟茂初, 李梦洁, 杜威剑.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 107-115.
[13]史青.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基于政府廉洁度的视角[J]. 财贸经济,2013(1): 93-103.
[14]吴伟平, 何乔. “倒逼”抑或“倒退”:环境规制减排效应的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J]. 经济管理,2017, 39(2): 20-34.
[15]BRENMAN G, BUCHANAN M.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6]QIAN Y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8, 88(5): 1143-1162.
[17]蔡昉, 都阳, 王美艳.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 经济研究,2008(6) : 4-11,36.
[18]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 经济研究,2010(8): 4-15,65.
[19]祁毓, 卢洪友, 徐彦坤. 中国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研究:制度变迁、数量测算与效应评估[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 31-43.
[20]白俊红,聂亮. 环境分权是否真的加剧了雾霾污染?[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27(12): 59-69.
[21]邹璇, 雷璨, 胡春.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29(6): 97-106.
[22]李国祥, 张伟.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J].当代经济科学, 2019,41(3): 26-38.
[23]侯玲玲, 孙倩, 穆月英.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分析:从化肥需求的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4): 173-178.
[24]史常亮, 李赟, 朱俊峰. 劳动力转移、化肥过度使用与面源污染[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6(5): 169-180.
[25]梁流涛, 冯淑怡, 曲福田.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理论与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4): 74-80.
[26]吴义根, 冯开文, 李谷成. 人口增长、结构调整与农业面源污染:基于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7(3): 75-87.
[27]颜廷武, 何可, 张俊飚.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 158-164.
[28]侯孟阳, 姚顺波. 异质性条件下化肥面源污染排放的EKC再检验: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组[J]. 农业技术经济,2019(4): 104-118.
[29]闵继胜,孔祥智.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59-66,176.
[30]袁平,朱立志. 中国农业污染防控:环境规制缺陷与利益相关者的逆向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2015, 36(11): 73-80,112.
[31]周力.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畜禽养殖半点源污染[J]. 中国农村经济,2011(2): 60-73.
[32]OATES W. 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33]汪慧玲,卢锦培,白婧. 中国农业污染物影子价格及其污染成本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 40-48,172.
[34]展进涛, 徐钰娇.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29(3): 167-176.
[35]黃清煌, 高明, 吴玉.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 33-42.
[36]田建国, 王玉海.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 28(10): 36-44.
[37]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345-368.
[38]朱小会, 陆远权.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 83-90.
[39]洪源, 袁莙健, 陈丽.财政分权、环境财政政策与地方环境污染:基于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40(7): 1-15.
[40]徐晓雯,孙超,王梦迪.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治污效应研究[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1(5):67-81.
(责任编辑:刘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