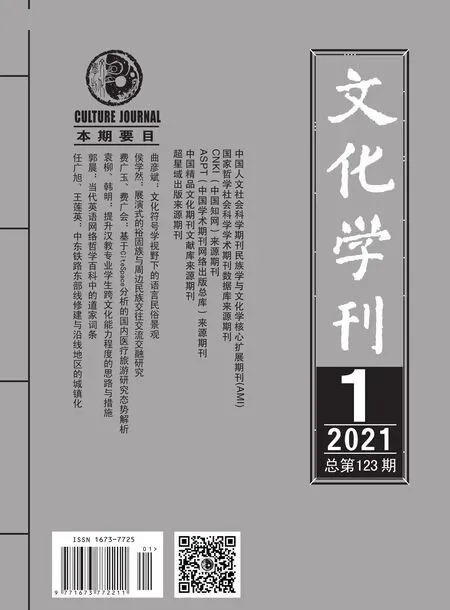浅析《史记·龟策列传》重视龟卜的缘由
李妮娜
《史记·龟策列传》是《史记》中记载龟策的一篇列传。“龟策”即卜筮,《礼记·曲礼上》云“龟为卜,策为筮”[1]。一般情况下,“卜”为用龟甲占卜,“筮”为用蓍草占卜。在西汉初年,“龟策”受到统治者的推崇。武帝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2]3224。武帝击匈奴,攘大宛,收百越时,“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2]3224。翻开《史记·龟策列传》,可以发现其中记载龟卜之处远远多于蓍占,基本可以称之为“龟卜列传”了。那么《史记·龟策列传》为什么会这么侧重描写龟卜呢?本文将通过分析龟卜的传统、西汉初年对龟和龟卜传达天命的神圣认识,对比当时其他占卜方法,从史学史的视角出发,结合作者和当时的写作背景,探讨《史记·龟策列传》侧重描写龟卜的原因。
一、龟卜的传统与神圣性
龟类为爬行变温动物,主要生活在热带及温带地区。温带地区的龟类在冬季寒冷时要冬眠,热带地区的龟类在夏季干旱、炎热时要夏眠,休眠期间不进食。龟类多杂食,耐饥力强,寿命可长达数十年至上百年。其中,半水栖龟类通常生活在河流、湖泊岸边的低地和沼泽中。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文明起源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温暖湿润。西周时期经过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后,至春秋时气候逐渐回暖。秦汉之际,温暖的气候和发达的水系为半水栖龟类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采集狩猎时代和农业不发达的史前时代,大量龟类很有可能作为食物为古人捕获食用。有学者依据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龟类骨骼,认为龟作为一种食物来源而成为先民的崇拜对象[3]。既然龟类在当时是可以食用的常见动物,那么作为猎物,先民必定仔细观察过龟类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以及生存环境。再结合史前时期流行的“万物有灵”思想,将龟的形象进行抽象并赋予其神奇的意义便成为可能。
在商代的占卜中,使用龟甲代替牛肩胛骨,可能有着实用与神圣的双重含义。一方面龟甲的产量比牛肩胛骨的产量高,另一方面很可能也是因为龟被人赋予了特殊的神圣意义。有学者认为,古人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龟的形态相结合,龟代表着宇宙:龟足立于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个方位,与“十”字形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结合,是为“八柱”,撑起圆形的天,龟背甲就代表天[4]。
龟卜自商代起盛行,至西汉初,依然流行于世。查阅《史记·龟策列传》的记载可以发现,西汉初流传着龟的种种神异。针对龟壳上的花纹,时人认为这些花纹与天象地理相应,所谓“八名龟”中有七种以天象或地理命名[2]3226。在龟的生存习性方面,古人认为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应四时变化甚至可以不食休眠[2]3231,且将龟不进食的原因归结为龟“行气导引”的结果[2]3228,于是,养龟被认为“有益于助衰养老”[2]3225。至于龟的生存环境,也充满着神秘气息:龟常伴莲叶、蓍草等灵物而生,在江南无毒蝎猛兽,野火、斧斤不及的森林中,择莲花所居[2]3226。龟在外观、习性、生存环境方面的神奇,都暗示着龟是与天相通、与天相感的灵物,它的出现自然被视为是天降祥瑞,人们认为龟作为天的使者,可向天子传达天命,代表天子受命于天。龟被古人视为“邦福重宝”,就连一国强盛的原因也归于龟之力[2]3227。在古人眼中,龟可以知利害、察祸福,言而当,战而胜,以此来安社稷,强国家[2]3231。普通人得名龟,可得财富[2]3226,甚者得到神龟,可为人君[2]3227,但也有人因为杀名龟而“身死,家不利”[2]3228。《史记》将“身死,家不利”的案例原因归为“人民与君王者异道”,普通百姓得名龟不能杀而用之,天子圣王却可以用它来占卜,且可以“十言十当”[2]3228,这与普通人得名龟后得财富和为人君的说法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出现的可能原因是:在统治稳定时,统治者利用当时龟与“天”相通的认识,为统治带来合法性,由此对龟卜的使用进行垄断;在政局不稳、改朝换代时,龟的垄断性削弱,为新君的上位提供“天人感应”的合理性,也为普通老百姓谋得的利益提供了一些合理的依据。这种矛盾也显示出龟的种种人为的神圣传说,其根本出发点是为现实形势服务。正因为以龟为宝、以龟为卜,时人争相得之,龟的数量由此减少。随着本来已是宝物的龟数量减少、使用减少,人们必然更加珍视龟,有利于龟及龟卜被渲染上更加神秘而又神圣的“天命”色彩。
二、龟卜与其他占卜方法
西汉初年,国家在长时间战乱后重获统一。经过几代的休养生息,民生得以恢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统一思想领域以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占卜的兴盛并非偶然。秦汉时方术流行,神秘信仰乃普遍的社会心理。当时的人们将“天”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天”具有了神格化的意义。“天命”是“天”做出的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决定,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人必须顺应“天命”,否则就会招来祸患。而天子为人君,当然也是因为“天命”所归。在当时,占卜被认为是知晓天命的一个有效途径。
卜筮是一种沟通天人、预决吉凶祸福的占卜方法。卜筮起源甚古,商周时期颇为兴盛,至春秋战国时期日渐衰落但仍不绝于世。《史记·龟策列传》载古代圣王皆以卜筮决疑[2]3223-3226。卜筮自上古时期起就受到重视,经过多代依旧保留了下来。所以,卜筮在西汉时期的兴盛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基础。
《尚书·洪范》记载了卜筮交相用的情况[5],以龟为工具的卜和与蓍草为工具的筮并用,故并称“卜筮”。蓍草也是一种神灵之物,班固《白虎通》载孔子云“蓍之为言耆也。老人历年多,更事久,事能尽知也”。之所以叫蓍草,是因其寿长而事事尽知,故称“耆”[4]。蓍草所生之处无虎狼毒虫[2]3225,生满百茎的蓍草,下面有神龟居住,上面有青云覆盖[2]3226。蓍草也可以与天感应,天下太平时蓍草可生百茎[2]3226。蓍草是灵性之物,常与神龟共生,与龟卜同用,占卜也相当灵验[2]3227。《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的记载明显多于筮占,原因有三。其一,蓍草虽然也是灵物,也可以感天,但不是天的使者,并没有被赋予传达天命的功能,在代表天意方面比龟对天的代表性逊色很多。其二,与龟在传统崇拜和占卜中的重要地位有关。从商代起,龟卜一直有着较高的地位。而龟作为动物,在远古时期可以作为直接的食物解决生存问题,相比于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的地位更为重要,更具有现实意义[3]。可以说,龟崇拜的传统根基深厚,延续日久,影响亦深远。其三,“物以稀为贵”心理的影响。龟数量较少、价格昂贵,出现即为祥瑞的征兆;而蓍草常见,数量多,方便易得,并非难得一见的祥瑞。如此一来,龟的神圣性比蓍草更强,在卜筮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
除了卜筮,星占、日占、梦占、鸡卜也是当时使用的一些占卜方法。关于星占,《史记·龟策列传》中载宋元王问卫平所梦为何物时,“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2]3229。可以看出,星占的体系较为复杂,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易经八卦。另外,天象只能显现国家大事,一般小事则不能显现。故星占占卜的是国家的军机大事,历来为官方垄断,民间几乎无人知晓[4]。而龟卜大事小事都能占卜,操作较为简易,流传甚广,民间也有运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操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易于被人们接受。
日占则是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位来占卜时间吉凶。《史记·日者列传》集解云:“墨子曰: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然则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记也。”[2]3215裴骃认为“占候卜筮”通称日者,可以说这是广义上的日占,狭义上的日占指“占候”。日占与龟卜相比,日占主占时,而龟卜主占事,占卜的理论不同,占卜对象各有侧重,日占不能传达天命。梦占与鸡卜前者是解梦,后者是利用鸡进行占卜,其神圣性远逊于龟卜,只能占卜小事,不能占卜大事,更不能传达天命,在《史记》中的记载也相当有限。
三、《史记·龟策列传》的背景
《史记·龟策列传》的作者背景和写作背景,在一定程度主导着其价值观。《史记·龟策列传》的作者是何人历来都有争论。《史记》在流传过程中遗失部分内容,故《汉书·艺文志》载“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注“十篇有录无书”,但未指明其缺补之处[6]。褚少孙增补史记,增补之处皆有“褚先生云”,经后人考证,多有疑云。《太史公自序》中载“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2]3225-3226。另《史记·龟策列传》索隐云“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所补”,正义云“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日者、龟策列传”[2]3223。所以,目前多认为《史记·龟策列传》亡佚,为褚少孙增补。也有学者认为《史记·日者列传》内容实为《史记·龟策列传》部分轶文,而现《史记·龟策列传》部分为司马迁所记,部分为褚少孙所补[7]。
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确有《龟策列传》一篇,无论作者是司马迁还是褚少孙,他们作史都不可避免带有当时官方的烙印。司马迁作《史记》本为私人修史,但司马迁官太史令,执掌史职,接触的人物以皇帝和各级官员为主,其所闻所见必然以官方的见闻为主。《史记》所用各种资料多为官方藏书,也正因为司马迁能够自由阅读官方藏书,《史记》才有成书的条件。《史记·龟策列传》载:“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2]3225-3226褚少孙本人不仅是郎官,而且增补《史记·龟策列传》的内容也是求访了当时的掌管卜事“太卜官”和掌管礼乐制度的“掌故”,至于“文学长老习事者”,则是当时有文化知识且深谙卜筮之术的人,这样的人绝非普通的平民百姓,应该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人物。
包括司马迁、褚少孙以及这些太卜、掌故、长老在内的人物,都与上层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许位于统治阶层的底端,但是他们所能接触的资料和信息都是官方的内容,浸染着官方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在那个“天”信仰根深蒂固的时代,在“天人感应”“天命至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下,统治者利用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社会影响力的、并带有强烈神圣色彩的龟崇拜和龟卜,宣扬王朝大一统乃“天命所归”,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了其统治的合理性,而且扩大了统治基础,使其统治有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色彩。因此,《史记·龟策列传》重龟卜,恰恰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当时统治阶级通过“天命”观的宣传来巩固统治。
四、结语
龟崇拜拥有悠久的社会文化历史,在诞生之初及历史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利用“龟”的祥瑞为自己的利益寻求合理性,赋予其神圣性,根本的作用是为现实服务。在西汉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龟”和“龟卜”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统治者借助“龟卜”宣扬天子天命所归的统治合法性。在他们的改造宣传下,“龟卜”作为新的“君权神授”工具而重获新生。从作者的身份背景和产生背景可以看出,《史记·龟策列传》不可避免地映射出当时官方的天命观念,正因为如此,“龟卜”才得以在《史记·龟策列传》中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