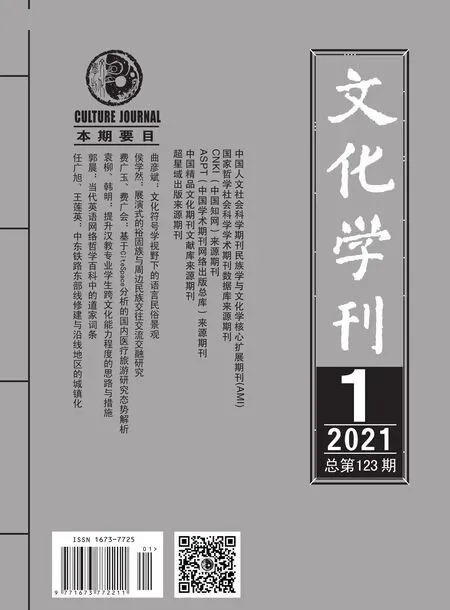关羽形象在朝鲜的接受及神化过程
赵婉彤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将德行兼备的英雄封神的习惯,关羽作为本土英雄,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对汉室的“忠义”,对刘备的“情义”,对曹操的“仁义”,对黄忠的“侠义”早已深入人心。他为大义牺牲小我的精神符合东方的审美,所以人们将关羽的形象“武将文雅化,英雄神异化”,称其为“忠义贯古今、神勇震乾坤”的民族武圣,使关羽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封神。
一、关羽中国本土形象的神化
关羽中国本土形象的神化主要体现在民间和统治阶级两个层面。民间层面的神化主要体现在民间传说、戏剧、文学作品的塑造上。一是民间传说中对“美鬓”和“红脸”的神化。《三国志平话》中将关羽的胡子称为“虬髯”,“虬”呈弯曲状,象征“龙的幼子”。传说中关羽有一根又细又长的胡须,是“黑龙”北海龙王的化身,龙王将自己的神力全部转给关羽,因此后世用“美髯公”指代关羽。《红脸关公》中称“关云长”是云间掉落的一滴血水长成,解释了关羽的脸谱是象征着忠勇侠义“红脸”的原因。除了形象方面细致入微的刻画,在《磨刀雨与晒龙衣》中,关羽以晒龙衣要挟海龙王借磨刀雨为人间解决大旱的传说,又使关羽被塑造成了福泽一方的保护神。二是戏剧上对关羽的神化。《花关索传》中,桃园三结义后为了却心中挂念,关羽、张飞分头杀死对方老小,与其子花关索构成了一个由剑神、水神与小童组成的完整神话象征体系[1]。三是文学作品上对关羽的神化。《东城关公庙记》《嘉兴县志》《寿春庵新建汉寿亭侯关王祠记》《常州新建关帝庙记》《五杂俎》《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等都重点描绘了关羽显圣护国保民的形象,将其塑造成“战神”。此外,晋商随身携带关羽的画像,将其视作“财神”;小孩子淘气夜间不睡觉的话,关羽还以“厉鬼”形象出现[2]。可以说,关羽的民间形象是多元有趣的,具有神话志怪的特点。
关羽形象统治阶级层面的神化主要体现在宗教和修建关帝庙上。儒教认为关羽夜读《春秋》符合儒家教义;道教将《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关羽列入祭祀行列中;佛教也为了立足于荆州,赋予玉泉寺“鬼助土木之功”的神话,铺垫了“关羽显圣”的故事。宗教本身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教化民众忠于君王,维系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目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建筑关帝庙宇,这些庙宇不仅气势宏伟、富丽堂皇,而且都使用了皇家专属的帝王黄色,体现了关羽在皇家帝王这些身份至高无上的人物心里的地位和荣耀,朝鲜顺安门外的关帝庙、中国地安门外的关帝庙皆是如此装点[3]。百姓捐资捐物修建关庙,祈求关帝显圣保佑,足见中国本土对关羽的喜爱与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关羽在中国本土的神化已经达到巅峰。
二、关羽的神化形象传入朝鲜
为进一步巩固与藩属国朝鲜的关系,明朝开始有意借“壬辰倭乱”向朝鲜传播关羽崇拜的思想,以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朝鲜认为,关羽虽然忠勇,但败走麦城,身死人手,并无丰功伟业存世,并不想大兴土木工程,劳民伤财地修建异国英雄的庙宇。明神宗于万历六年(1578)将关羽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比朝鲜国王的地位还要高出一等,这一行为更是激发朝鲜极其不满的抵触情绪。只不过迫于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不得已而为之,平定战事后修建的关帝庙也受到了朝鲜人民的冷落,可见接受新文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直到朝鲜宣祖时期,朝鲜遭遇倭寇入侵,连年的战事使得政局不稳,急需树立一个英勇无敌的形象,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共同抗击侵略者。关羽忠勇,又护国有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一方面,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关羽的保佑,希望借修建关帝庙犒劳关羽的显灵之功,继续保佑朝鲜的“运祚之绵远”;另一方面,为改变朝鲜重文轻武的风气,重塑朝鲜国家形象,恢复朝鲜士林的文化自信[4]。统治阶级规范全国各地的关帝祭祀活动,“捍灾御寇护国保民”体现了朝鲜政治方面的诉求,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亲至关帝庙祭拜。这从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那里也可见一斑。朝鲜学者李安讷《关王庙》中的“百战英灵凛九原”和“阴兵助顺神功着”,把将军关羽与战神关帝联系在一起,完成了朝鲜关羽由人到神的神化转变[5]。
朝鲜接纳关羽的形象后,关羽的形象发生了极大改变。俄国学者李福清在《关羽肖像初探》中指出:“韩国人画的关帝像都韩国化了,韩化的程度比蒙藏还多,与中国关帝像相较之下,韩化的关帝像画法不同,把人物扩大化了,服饰也不同。特别是1800年左右,全罗北道南原绢本唐彩画持青龙刀的关帝,完全不像中国关帝像。姿势、脸、眼睛、服饰都不像,只有青龙刀及帽上的绒缨与中国图相同。”[6]遭受“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后,朝鲜盛行“慕明恶清”力求“反清复明”的思想[7]。如果说纳贡给朝鲜经济上带来的负担尚能接受,那么背叛明朝投降清朝则是奇耻大辱。朝鲜文人阶层愿像关羽忠于汉室一样,忠于明朝,以表示对明朝的“再造藩邦”之恩。像关羽忠于刘备一样,恪守君臣之礼,忠于儒家君为臣纲的正统观念。
朝鲜使臣俞彦述的《燕京杂识》更是表现出对清朝将关帝像放在佛像中祭拜,甚至将关羽像放在“杂处于腥秽之中”的强烈不满,一方面体现了朝鲜对满清异族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说明朝鲜对关羽的神化已经达到顶峰,关羽的形象已经上升至朝鲜的自尊心。大韩帝国时期正式停止关帝庙祭祀,神化关羽的全盛时代结束了,但是民间祭祀活动没有停止,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朝鲜半岛的信仰文化。与中国将关羽的形象融入三教之中不同的是,朝鲜形成了只崇拜关羽的“关圣教”,至今仍把关羽作为忠义和财神的象征加以崇拜[8]。关羽能够得到朝鲜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喜爱,与其英勇无畏、忠肝义胆的特征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朝鲜获得如此广泛的喜爱,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
三、关羽形象在朝鲜的神化
朝鲜对关羽的崇拜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还逐渐渗透到了文学领域,分为对关羽的“显性崇拜”和“隐形崇拜”[9]。
“显性崇拜”主要体现在《壬辰录》《祀典典故》《敕建显灵关王庙》的关公显圣,以及《壬辰录》《天倪录·送使臣宰定庙基》《天倪录·见梦士人除妖贼》的三次托梦中。关公显圣的传说对鼓舞朝鲜士兵为国家的安定浴血奋战,以及在民众间形成同仇敌忾抵抗倭寇的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次托梦,第一次预示大难将至,第二次告知避寇之道,第三次向李如松举荐水军将领李舜臣[10],紧扣“壬辰倭乱”爆发、宣祖还宫、丁酉再乱爆发三个关键时间点。既塑造出关羽先知先觉的神通广大,又表现出关羽心系百姓的赤子之心。
“隐性崇拜”主要体现在将关羽的精神特质投射到朝鲜本民族英雄身上。例如,将《三国志·关羽传》中“刮骨疗毒”的故事移植到李舜臣身上,将“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投射到金应瑞斩杀倭将的片段中,暗示李舜臣和金应瑞就是朝鲜的“关羽”,以此凸显朝鲜民族英雄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形象。关羽经过朝鲜历代文人的虚构想象逐渐本土化,被视作朝鲜国家与国民的保护神。后期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关羽的神化对统治者的地位产生了冲击,《壬辰录》中关羽和朝鲜国王对话时不再自称“我乃上古关云将也”,而是有意将关羽描述成只能依靠神宗才能将倭寇驱逐出境的武将形象,使其恪守朝鲜的君臣礼法。即便地位有所下降,关羽的形象仍在朝鲜维持着极高的热度。不仅影响了朝鲜英雄类小说、野谈类小说、梦游录小说等,直到今天韩国的小说、漫画中还会出现关羽的形象,对韩国作品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实现、推动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中国本土对关羽的炽热崇拜是不难理解的,朝鲜对“关羽”这一异国形象的态度经历了从抵触到接受再到神化,最终有意贬低的复杂过程。对于当时的朝鲜,能出使中国直接感知中国文化的人还是少数的,大多数人要通过阅读或者其他方式接受外来文化,通过阅读记录使臣出使中国的文献和文学作品,想象并塑造着朝鲜人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所以,关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审判,原话语经过中间媒体的解构和合成,成为文化的变异体,文化的变异体已经不再是文化的原话语。有新文化文本的产生不是为了重复原话语,完全是为了本土文化的需要[11]。因此,朝鲜在特定的审美经验上,对关羽形象的价值和属性进行主动选择、接纳或抛弃,把握其形象背后蕴含着的民族情感和思想寄托,并顺应时代大环境的发展趋势,融入朝鲜本土化的特征,在文学领域进行再塑造,将对关羽的崇拜深深根植在朝鲜的政治文化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