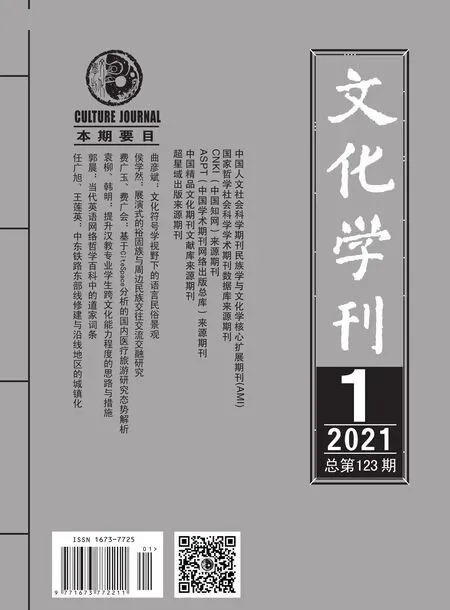浅谈雍和宫对清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凝聚力
于博洋
一、历史沿革——王府荣光
雍和宫前身为雍亲王府,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占地面积66 400平方米,是康熙皇帝为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修建的王府。1723年,雍亲王胤禛继承皇位,是为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三年(1725),雍亲王府改为行宫,敕名“雍和宫”。雍和宫的永佑殿曾是雍亲王胤禛的卧室和书房,雍正皇帝驾崩(1735)后,曾在这里停灵并悬挂影像。其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皇帝,为缅怀先父、体现皇家尊贵,在雍正皇帝驾崩后的半个月内,乾隆皇帝将雍和宫中轴线上主殿的绿色琉璃瓦全部换成黄色琉璃瓦,宫内殿堂一部分作为皇家祭堂,一部分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的诵经处所。由于雍和宫前身为雍亲王府,且乾隆皇帝也诞生于此,雍和宫实则出了两位皇帝,因此,雍和宫的建筑格局远高于其他皇家敕建寺庙,宫内殿宇黄瓦红墙,有着与紫禁城同样的规格。
雍和宫内的黄色琉璃瓦屋顶不仅是其出身王府、与清廷联系紧密的象征,而且彰显了它在全国喇嘛教寺院中的尊贵地位。公元1734年,雍正皇帝封章嘉活佛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乾隆皇帝继位后,封章嘉活佛为掌印喇嘛,主持雍和宫,使雍和宫成为掌管清政府喇嘛教事务的中心,标志着雍和宫正式成为藏传佛教寺庙,担当起联系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的桥梁纽带。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五年(1744—1750)的六年时间里,雍和宫完成了改建、扩建工作,建成了各类造像、陈设,以及僧舍、经史馆等。作为喇嘛庙的雍和宫,管辖着华北、内蒙古一带的喇嘛教寺院,并向这些寺院派住持喇嘛。“改庙后的雍和宫成为清廷弘扬佛法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亦是培养喇嘛的官方教育基地。”[1]至此,雍和宫的历史角色完成了由亲王府邸到清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中心的完全转变,奠定了雍和宫成为清政府以藏传佛教为纽带,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文化载体。
二、寺庙特色——汉藏融合
雍和宫在建筑布局方面展现出汉藏共生、汉藏互摄、汉藏融合的特色。
一方面,雍和宫的最南端以三座牌坊、一座影壁围成一个广场,其后为昭泰门(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整座殿宇坐北朝南,共有五进院落,具有布局规整、格局宏大、设置结构严谨的特点,体现了汉地佛教寺庙的传统布局:在雍和宫的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排列着五重大殿,即天王殿(雍和门)、雍和宫殿(大殿,又叫师祖殿)、永佑殿、法轮殿和万福阁。此外,还有由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戒坛楼、班禅楼、永康阁、延绥阁等组成的东西配殿。这些殿宇均由王府建筑脱胎而出,但又有所改造或扩建。雍和门、雍和宫殿和配殿,原是王府的正殿部分;寺东有太和斋、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则是王府的寝居部分。从整体来看,雍和宫受汉地佛教寺庙传统布局的影响颇深。
另一方面,作为全宫最大殿宇之一的法轮殿,则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艺术风格,该殿平面呈十字形,殿顶设有五座小阁,阁上饰小型喇嘛塔,状似曼陀罗的五塔构图,殿内存有藏文《大藏经》《续藏经》三百一十五部。大殿两侧为班禅楼和戒台楼,班禅楼展示雍和宫历代喇嘛的生活用品及法器、佛像近三百件展品;戒台楼展出金奔巴瓶(1)金奔巴瓶,即金瓶,系用来寻找蒙、藏地区活佛的转世灵童。清政府为防止蒙藏贵族操纵活佛转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意颁发两只金瓶,一只贮北京雍和宫,一只存拉萨大昭寺。和乾隆时期的部分文物。此外,雍和宫内一些佛像的造像手法也体现了藏传佛教的艺术特色。例如: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造像,其中东方持国天王像不在东方持立,而在西方的位置上,反映了藏族寺庙中以西为大,以右为上的思想,与中原汉族大部分历史时期奉行以左为尊的观念相反;雍和宫大殿中以佛教祖师释迦牟尼佛为中心的三世佛,左右两边不是汉地佛教寺庙中常供奉的西方阿弥陀佛和东方的药师佛,而是竖三世概念中的燃灯佛(过去佛)和弥勒佛(未来佛);法轮殿供奉的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像,头戴黄色尖顶僧帽,身披黄色僧袍,双手捻有两枝缠绕且开放着的莲花,显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师的独特风采;密宗殿里人身兽头、男女双裸相抱的欢喜金刚造像,是藏传佛教密宗区别于汉地佛教的一大造像特色。
三、大兴格鲁派——清朝统治者的怀柔政策
蒙古族人接触藏传佛教一般以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的会谈为开端。《新红史》记载,成吉思汗统治汉、吐蕃、蒙古及西夏之疆土,在位二十三年间均以佛法护持国政[2];《彰所知论》中记载,忽必烈即位后亦用佛法保护政权[3]。此外,元代统治者忽必烈汗接受灌顶、皈依佛法的历史事件,推动了佛教在蒙古传播的进程,抬高了佛教在元朝的政治地位,最终在元代统治者与藏传佛教首领之间搭建起联盟关系,并且一直将这种特殊的联盟关系延续到明清时期的整个蒙藏社会。
16世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他推行尊崇、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以交好蒙古族,推行修建佛寺、保护寺庙、优礼大喇嘛的政策,借此获取蒙古族的支持,为蚕食明朝所辖辽东进而统一全国积攒实力[4]。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入主中原,继续推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积极与格鲁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建立政治联系,公开宣布尊崇藏传佛教,以此赢得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支持。顺治九年(1652),迎请五世达赖入觐北京,赐予金册、金印,并以汉、蒙、藏、梵四种语言的词汇组合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又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承认其在西藏地区的统治,这是把固始汗当作有领地的汗王来对待的。康、雍、乾三朝皇帝在位时期,格鲁派的宗教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以北京为重心,辐射承德、五台山的三个由皇家出资修建的内地藏传佛教中心。
四、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索
在元代蒙藏关系建立、发展的过程中,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纽带的关键作用,这直接影响了后世清代满族统治者在处理蒙藏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并且反映在满族统治者自建立后金政权到康、雍、乾时期一直延续贯彻落实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怀柔政策上。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积极与蒙藏首领建立关系,得到了蒙藏首领的拥护,在民族关系上为统一中国做好了准备。满族统治者问鼎中原后,进一步扩大了元代的民族关系范围,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索,在汉族地区建成了以北京、承德、五台山为主的弘扬藏传佛教中心,并且优礼尊崇大喇嘛、广建寺庙、主持大规模编撰和翻译佛经的工作,加强了满蒙藏民族之间的联系与融合,使前朝面临的局部地区民族关系发展为全国范围下的民族关系问题。
“历史上的雍和宫,是清朝政府联系蒙藏地区的纽带和枢纽,政治地位极高。蒙、藏地区人民笃信藏传佛教,雍和宫自然就成为蒙藏宗教领袖、高僧大德在北京的活动中心……雍和宫实质上成为了联接中央与蒙古、西藏、青海等藏传佛教地区的政治通道,在密切满汉蒙藏民族感情、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5]为防止蒙古诸部因藏传佛教与藏区产生过密交往,使蒙藏民族情系清中央政府,根据乾隆皇帝旨意,雍和宫创立了显宗、密宗、医名僧院等,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使北京雍和宫成为中国内地组织完备、兼具培养蒙古藏传佛教人才功能的佛学学府。此举的深远用意,一是切断历史上蒙藏民族因弘扬藏传佛教之故建立起的过密交往,大大降低了清朝的边地隐患;二是借助藏传佛教怀柔蒙古诸部和藏族地区的宗教领袖,确定了雍和宫在巩固清政府封建专治王朝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三是以雍和宫为文化中心,形成了凝聚满、蒙、藏民族的向心力,加强了多元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此外,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多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持包容、尊重的态度,在“不易其俗”的前提下进行统治。乾隆皇帝曾学习多门少数民族语言,可与西藏高僧亲自交流,无需翻译:“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拉语。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不藉舌人传译……燕笑联情,用示柔远之意。”[6]乾隆皇帝以藏传佛教柔服蒙藏民族,在信众中建立起以雍和宫为中心的向心力,并且以身作则,注重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学习,通过吸引信众至雍和宫朝拜,明确了清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主权,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加强边疆与北京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举措。
元、清两朝如此重视藏传佛教在国家统治中的影响力,绝非源自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归根结底是统治者体察到了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民众中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利用藏传佛教可调和蒙藏民族间潜在的矛盾,通过抬高宗教领袖地位的政治手段来安抚、教化蒙古贵族和藏族信众,取得“胜于以兵戈相见”而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诉求,最终达到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雍和宫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庙,从雍亲王府敕建为清廷管理蒙藏佛教事务中心的过程,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蒙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亲和与重视,是清朝皇家意志反映在宗教方面的能动代表,是其以扶植藏传佛教为“标”,达到拉拢教化、团结交好蒙藏民族为“本”的政治手段,展现了清代统治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索成果。
——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创办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