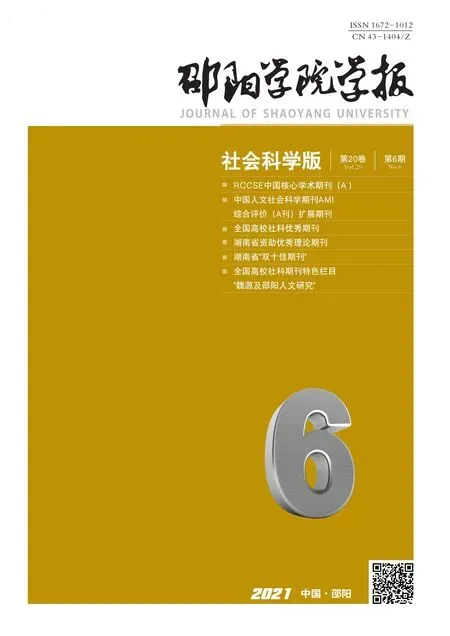邵阳布袋戏剧本词语特征分析
吕俭平
(邵阳学院 文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邵阳布袋戏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行于邵阳地区。由于老一辈布袋戏艺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条件进行剧本整理,邵阳布袋戏开始基本上是口耳相传,没有剧本。如果不把布袋戏的这些剧目、剧本及时记录下来,布袋戏就更加容易失传。因此,笔者先后联系布袋戏传承人刘永章、唐平清两位老人,把布袋戏剧本加以搜集、整理,对其中一些字词进行核实、改定,并得到老人的认可。在整理剧本的基础上,笔者对剧本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其特点。邵阳布袋戏剧本词语特征,主要表现为邵阳方言色彩浓厚、书面语色彩很强,在第一人称代词的运用上很有特色。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一、剧本词语的方言色彩
邵阳布袋戏剧本词语有不少是邵阳方言词语,带有比较浓厚的邵阳方言色彩。同时,笔者也发现,剧本词语还带有一些北方方言的色彩。
(一)比较浓厚的邵阳方言色彩
邵阳布袋戏的传承人是邵阳县人,因此布袋戏主要采用邵阳方言演唱。经过比较全面的梳理发现,剧本词语里存在较多的邵阳县方言词语与方言句式,剧本词语的邵阳方言色彩浓厚。下面结合剧本分类举例分析。
1.方言词语
(1)唐僧:(白)那里是什么东西在嚎叫?
张青:(白)老古猴在嚎叫。(《两界山》)
在邵阳县方言中,“老古猴”指成年的公猴。“古”,应写作“牯”。“牯”,本义指成年雄性的牛,也可引申为其他某些雄性动物。这种表示性别的语素在南方方言中一般后置,例如猪婆(母猪)、鸡公(公鸡)、鸭婆(母鸭)。邵阳方言有性别语素后置的情况,也有跟普通话一样前置的情况,比如龙狗(公狗)、草狗(母狗),“老古猴”属于性别语素前置的情况。
(2)八戒:(白)不要紧,不要紧,你又肥又大,像猪婆一样,有几百斤。来了又不发信。这下你来吧!(《两界山》)
在邵阳县方言中,“不发信”(不发出信息,不通知)可以看作“不发出信息”的省略。这是八戒的念白,属于口语语体,因此省略也就很正常。
(3)唐僧:(白)你愿不愿意学道?
孙悟空:(白)我爱得很。(《两界山》)
“道”,在普通话中有“宗教思想”的意义,做语素,如“布道、传道”。使用这个意义的语素“道”,在普通话中不能单独成词,在邵阳方言中能单独成词。“学道”,在剧本中是指学习佛教的教义、思想。
(4)太公:(白)请师父救救我的女儿。
孙行者:(白)师父,老太公待我们很好,他家中有难,我们一定要打救他。
太公:(白)妖怪凶神恶煞,你要小心才是。
孙行者:(白)哎!我老孙不怕。我还有马在这里。……如果是妖怪,将他收了就是。(《两界山》)
“打救”,就是“救”的意思。“打”是词头。“打”做词头,在普通话中也有这种现象,比如打坐、打听、打扫等。“打救”在普通话里没有,在邵阳县方言中有,类似的还有打住(住)、打流(流浪)、打比(比较)、打望(望)。
收,邵阳县方言词,即“收伏”,是“收伏”的省略。因为这是在念白中,念白口语化很强,容易省略为单音节。
(5)猪八戒:(白)可恼,真可恼!(唱“砣子”)听你言来心头恨,怒得我两眼冒火星。手提钉耙把洞门打,打破洞门捉拿妖精。(八戒连续数耙打破洞门)(下)(《青龙山》)
“可恼”,邵阳县方言词,“让人恼恨”的意思,多用于口语中。
(6)李:(唱“南路正板”)这奸贼眼力倒是狠,认出了我是李世民。双脚跨上龙驹马,手拿金箭弓在身,讲得真名也是死,不通其名死得成,当其问我名和姓,乃是掌朝天子李世民。(《乌泥河救主》)
“这奸贼眼力倒是狠”的“狠”,原剧本写作“很”,正确写法应为“狠”。“狠”,邵阳县方言词,“厉害”的意思。在普通话中的“狠”,本义是“凶恶、残忍”的意思,贬义色彩;在邵阳县方言中是“很勤奋、很努力”的意思,常常是做褒义词。比如,他做事蛮发狠(他做事很拼命、很努力)、他读书蛮狠(学习成绩优异)。
“其”,“他”的意思,邵阳县方言词,本字应为“渠”。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中“渠”,就是第三人称代词“它(方塘)”。
(7)娘:(坐在堂中)叫一声二孩儿,细听端详:(唱“二流”)你父亲去世早,母儿三人受煎熬。油盐柴米餐餐要,穿住两样不能少。孝儿上山砍柴卖,早去早回少挂牵。(《南山砍柴》)
“挂牵”,邵阳县方言词,“牵挂”的意思。它与普通话中的“牵挂”是同素异序词。邵阳县方言中同素异序的词语还有不少,例如闹热(热闹)、何如(如何)、钱纸(纸钱)等。
2.方言句式
(1)老妖:(白)好彩头。(下)
钻山:(白)大王呀,大王,彩头是蛮好的,那猪头的打法可好,杀法也厉害。我是杀他不赢,战他不过,这个买卖可要老成呃。(指着他自己头)(《青龙山》)
“动”“宾”“补”3种句法成分在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中的组合顺序有区别。在汉语普通话中,最常见的顺序是“动+补+宾”[1]76,例如“杀不赢他”“战不过他”。在一些汉语方言中,最常见的顺序是“动+宾+补”,比如在湘语沅江话[2]、湘语邵阳话中,采用“奈渠不何(斗不过他)”“杀他不赢”“战他不过”的方言句式。上述剧本中台词就采用了这种方言句式。
(2)八戒:(白)拿酒来,还要好菜。(扯着大妖衣服说)还要拜堂成亲。
大妖:(白)这酒很厉害,我要看到你眼睛吃。
八戒:(白)好,我猪老爷爱喝酒。(《渭水河》)
剧本中大妖的念白“我要看到你眼睛吃”,连谓句,符合普通话的正常语序。“眼睛”是名词,在句子中本应做状语,意思是“用眼睛”。看,当然是用眼睛的。说话人是为了强调“要亲眼看着”的语义而加上的,属于语用的羡余成分。为了强调亲眼看这种语用表达效果,剧本念白采取了移位处理:本该做状语的“眼睛”后置到宾语的位置。这种现象在邵阳县方言中不是孤例,最常用的“吃光饭、吃净菜”与此类似。“吃光饭”就是“光吃饭”,“吃净菜”就是“净吃菜”。普通话中,“光”“净”是做状语的,分别修饰“吃饭”“吃菜”的,应该位于动词的前面。在邵阳县方言中,“光”“净”移位到动词后、名词前,占据了定语的位置,说起来的停顿是“吃/光饭、吃/净菜”,给人的错觉就像是定语。
(3)唐僧:(白)老古猴叫多不多事?
张青:我听老前辈说的,不多事。(《两界山》)
关于“VO-neg-V”和“V-neg-VO”这两种反复问句,赵元任先生指出,北方话倾向于使用“VO-neg-V”格式[3]1531。朱德熙先生专门讨论过它们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在西南官话、粤语、闽语、客家方言等南方方言倾向使用“V-neg-VO”格式[4]181-202。邵阳县方言采用“V-neg-VO”格式,剧本里是“多不多事”。
好的戏剧语言都很重视口语,尤其是宾白的口语,这样才能通俗易懂,易于观众接受和喜爱。邵阳布袋戏是邵阳艺人演唱的,因此宾白口语化,带有邵阳方言的色彩就很正常了。
(二)一定程度的北方方言色彩
虽然邵阳布袋戏主要采用邵阳方音演唱,但是从词汇来看,我们整理出来的布袋戏剧本中不少词语不是邵阳方言。除了有不少书面语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参看下文)以外,还保留了比较明显的北方方言词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一人称代词“俺”。
第一人称代词“俺”,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方言词,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5]1《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6]4344和《现代汉语方言词典》[7]3228-3229这3种资料进行统计发现,第一人称代词“俺”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方言词,而且绝大多数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苏等地区。下面是笔者统计的使用“俺”的地区分布。
地点方言中说“俺”的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只说“俺”,标记为①;(2)“俺”“我”都说,标记为②;(3)“俺”“我”“咱”等都说,标记为③。资料显示,河南至少有25个县市,包括①类12个地点:新蔡、确山、西平、项城、扶沟、柘城、开封、民权、滑县、鹤壁、清丰、夏邑;②类13个地点:商城、社旗、镇平、鲁山、嵩县、洛阳、禹州、郑州、沁阳、获嘉、原阳、林县、商丘。山东至少有25个县市,包括①类9个地点:蓬莱、荣成、临朐、聊城、肥城、新泰、东明、成武、滕州;②类16个地点:苍山、郓城、兖州、沂南、夏津、临邑、济南、章丘、淄博、桓台、潍坊、诸城、青岛、利津、济宁、烟台。河北至少有18个县市,包括①类2个地点:故城、石家庄;②类16个地点:唐县、徐水、河间、黄骅、南皮、晋州、赞皇、冀州、隆尧、威县、永年、广平、沧州、邯郸、平山、阳原。安徽至少有7个县市,包括①类3个地点:利辛、濉溪、亳州;②类1个地点:阜阳;③类3个地点:灵璧、霍邱、滁州。辽宁至少有7个县市,包括①类3个地点:大连、张武、瓦房店;②类2个地点:宽甸、丹东;③类2个地点:辽阳、岫岩。黑龙江至少有4个县市,①类没有,②类有4个地点: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黑河市。江苏至少有3个县市,包括①类地点赣榆、②类地点泗洪、③类地点徐州。除了以上比较集中的省份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分布。比如陕西的西安,吉林的通化,山西的离石、忻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湖南的常德。以上是第一人称代词“俺”的共时分布。联系历史移民,我们认为“俺”分布的历史演变大致应该是这样:“俺”最早、最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与山东3省,辽宁、黑龙江、辽宁等东北省份的分布点很可能是“闯关东”的移民带过去的。山西、陕西、安徽、江苏,尤其是湖南常德等地,也是后面慢慢扩散过去的。
笔者认为,布袋戏剧本中的“俺”最早来源于北方方言。这个北方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俺”,也是通过布袋戏演唱者,在从北往南多次迁徙过程中进入南方地方戏曲的唱词中的。这就有必要分析布袋戏的来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
关于布袋戏的来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黄李娜指出,布袋戏的历史即为掌中戏的历史[8]。掌中戏作为与幻术一类的技艺最晚约在东晋之前由西域传入。孙楷第指出,唐贞元间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唐乾符年间安潜镇守四川时,在西安、四川都有布袋戏流行。孙楷第论及明朝中期山东的风俗,人死后会请一起偶戏前来娱神与娱人[9]40。黄李娜指出,陕西凤阳、河南新蔡在明清都有掌中戏表演的记载[8]。刘海潮专门考察了邵阳布袋戏的来源,他指出,在元末明初时,邵阳布袋戏是表演这种戏曲的艺人刘氏的祖先从江西移居湖南宝庆而带入的一门民间戏曲艺术[10]。这些资料大致能说明布袋戏(即掌中戏,属于木偶戏)东晋前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北方,然后随着北人南迁,流播到南方。邵阳布袋戏从江西传入邵阳。布袋戏传到南方,其剧本的宾白、唱词当然会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于是有的唱词有了变化,但有的唱词保留了下来,如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俺”保留下来了。笔者发现,北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俺”主要用于唱词中。唱词不同于宾白,它庄重、严肃,书面语色彩更强,更具有稳定性,师傅传授给徒弟演唱时,一般不会随意更改,这样唱词就一代又一代很好地保留下来了[7]。
二、书面语色彩很强
剧本中词语书面语色彩很浓,主要表现在唱词中运用了一些书面语色彩很浓的词语和句式。有时在宾白中,也有一些书面语色彩很浓的词语。例如:
(1)唐僧:(接唱)一见众徒出了阵,为师喜在眉头笑在心,回头来把沙僧讲,叫声沙僧听端详。(白)沙僧?哪里?
沙僧:(白)一听师父叫,面前问根苗。师父在上,弟子参详。(《青龙山》)
(2)孙行者:(白)我的师父是高道,能捉妖拿怪。
家人:在此巧机!(《高老庄》)
(3)孙悟空:(白)师父救我哪怕八件十件我都依从,请师父快快说来。(《两界山》)
例(1)中,唐僧的唱词中出现了“喜在眉头笑在心”“回头来把沙僧讲”“叫声沙僧听端详”“弟子参详”,其中把字句句式、“端详”“参详”书面语色彩很强。例(2)中“捉妖拿怪”书面语色彩较强,如果换成“捉拿妖怪”就显得比较口语化了。“在此巧机”程式化和书面语色彩较强,如果换成“这一下机会好巧啊”,就变得很口语化了。例(3)中“快快说来”的句式、助词“来”的书面语色彩都很浓。
邵阳布袋戏剧本语言为什么书面语色彩较强呢?笔者认为戏剧剧本的语言风格与剧本的内容密切相关,邵阳布袋戏也是如此。邵阳布袋戏的剧本大都是古代题材的,尤其是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的故事有关,比如《两界山》《高老庄》《渭水河》《青龙山》《关公战长沙》《武松打虎》,等等。古代故事中人物的语言不能太现代化、口语化,不能太通俗。剧本语言分唱词和宾白,唱词和宾白的语言风格有所区别。唱词的语言书面语色彩更强,而且在一代又一代布袋戏艺人的传唱中不容易改变,因此它书面语色彩更容易保留下来。像以上分析的剧本中“端详”、句末助词“来”,就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书面语色彩。宾白的书面语色彩要弱,口语化要强,而且不同的布袋戏艺人在传唱中容易改变,带有个人的色彩,随意性较强。
三、人称代词的使用很有特色
在整理的剧本中,我们发现第一人称代词有3个:我、俺、吾。就统计的数目来看:“我”最多,有1294个;“吾”次之,有55个;“俺”最少,只有24个。其中《关公战长沙》《黄河摆渡》两个剧本,刘永璋、唐平清两位老艺人都演唱了,本子不尽相同。唐平清版的这两个剧本都没有人称代词“吾”,刘永璋版共有3个,我们按照3个计入。人称代词“俺”的数目,两位艺人《黄河摆渡》的本子都为零;《关公战长沙》的本子有差异:唐平清版有7个,刘永璋版只有4个。我们按照7个计入。下面把3个人称代词在剧本中出现的情况分别加以叙述、分析。
(一)我
(1)飞:(岳飞出场,念)……我命岳云、张宪二儿校场操演人马,已有数天了,还未见二人前来交令,再待片刻或有信息。(《岳飞训子》)
上例中第一人称用“我”。这是岳飞出场的念白。
(2)白:只因我错饮雄黄朱砂,现出原形,吓死我夫许仙(郎)。(《白氏求草》)
上例是白素贞与白鹤神的对白,第一人称用“我”。
(二)俺
邵阳布袋戏中,“俺”使用数目统计有24个,用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做同位语;2.做定语;3.做主语;4.做宾语;5.做兼语。分别举例分析如下。
做同位语的,例如:
(1)魏:(白)呸!魏爷为的是谁?
黄:魏将军为的是俺黄忠。(《关公战长沙》)
(2)黄:多谢魏将军保我命,哪里还有黄将军。但你不该刺杀太守命,俺黄忠虽死足安宁。(《关公战长沙》)
(3)薛刚:(唱)……患难之中逢知己,俺薛刚从来不推杯。(《泗水拿刚》)
(4)薛刚:(唱)……俺薛刚待你哪有错?你反眼无情为哪般?(《泗水拿刚》)
(5)薛刚:(唱)恨太子在灯棚行为不正,抢民女欺百姓胡作非为。是小弟抱不平阻拦一地,小昏君反说我有意欺君。怒恼了俺薛刚心似懊气,踢太子惊老王一命归阴。……俺薛刚逃难无处躲避,唯望我宗兄来做解围。(《泗水拿刚》)
(6)云、宪:(上场唱“二流”)少年威武震华夷,英雄胆气举世闻。
云:俺,大元帅帐下大将军,元帅之子岳云是也。
宪:俺,大元帅帐下大将军,大元帅之婿张宪是也。
(云、宪圆场,剧中锣鼓点起)(《岳飞训子》)
上述都属于“俺”的同位语用例。我们发现,“俺”同位语用例大多用于人物唱词中,在宾白中用得很少。除例(1)是宾白外,例(2)—(6)都是唱词。经我们统计,“俺”同位语用例有:“俺薛刚”(4例)“俺黄忠”(2例)“俺悟空”(1例)“俺老孙”(1例)“俺武松”(1例)“俺,胡秀英”(1例)。“俺”还可以构成比较复杂的同位结构,例如“俺,大元帅帐下大将军,元帅之子岳云”,“俺,大元帅帐下大将军,大元帅之婿张宪”,“俺,长沙太守韩云”。
做其他句法成分的。做定语,例如“俺兄弟”“俺老爹”“俺性命”;做主语的,例如“若不是俺救你性命”,再如:
(7)魏:……适时,恰俺催粮回来,将韩斩了,救出黄忠,并劝他一起投汉。现呈上长沙官印,这些功劳都是我魏延的,师爷你赏罚分明,一定不会亏我的,哈哈哈。(《关公战长沙》)
(8)薛刚:俺只为这黄汤惹下是非,从今以后,我戒酒不饮了。(《泗水拿刚》)
(9)黄忠:昨日与关羽交战,他将俺拖下马来,不斩首于我。待我使用百步穿杨之箭,以报答关羽的不杀之恩。(《关公战长沙》)
做宾语的,如“将俺拖下马来”;做兼语的,如“待俺使百步穿杨……”。
(三)吾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吾”的第一义项:人称代词。我;我们(多做主语或定语)。笔者发现邵阳布袋戏剧本中的“吾”也主要做主语和定语,但只发现单数用例。如果要表示复数,就在后面加助词“等”,变成“吾等”。
(1)孔明:吾观魏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先斩之,以绝祸。(《关公战长沙》)
(2)官:(白)吾,乃上元一品赐福紫微大帝,又乃赐福天官星。奉玉帝圣旨下凡,前往各处向行善积德的人家赐福降祥。(向内喊)众神。(《天官赐福》)
(3)李存孝:(引)头戴飞虎盔,身穿铠子甲。胯下白龙马,手提笔砚抓。
(白)小王,十三太保李存孝,今领奉皇王圣旨,父查河南,吾巡查河北,今日黄道吉日,众将(有)人马可曾齐备?(《黄河摆渡》)
(4)官:驾祥云往红坐行走。(唱“起板”转“北路慢皮”)
乾坤大事记于脑,风雨雷霆任其飘。
鸿钧一道使此教,昆仑山上乐逍遥。
吾奉御旨谁知晓,巡查善恶奏天曹。
我在云端用目看(转“坨子”),上八神仙赴蟠桃。
神1:吾乃南极仙翁也!
神2:吾乃文昌开化梓童帝君也!
神3:吾乃送子观音大士也!
神4:吾乃赵公财神是也。
众神:是,天官大帝在上,吾神等叩拜!(《天官赐福》)
笔者发现,后面的神2、神3、神4圆场自我介绍时,人称代词都是用“吾”,跟前面是照应的。例外的是,神1后面再次出现时,自我介绍却用“我”,如原剧本所示:
(众神圆场,天官下场)
神1:待我前往(上前)(念)我乃南极仙翁,奉大帝钧旨,我把寿宴献上,唯愿为此寿比彭祖高,永享年华,此地之人好行善积德,因此把寿宴献上,学一个老彭祖儿其寿绵长。(《天官赐福》)
笔者觉得神1念白中的两个“我”应该改为“吾”,以使得前后一致,与其他3神的人称代词运用要保持相同,而且第二个第一人称代词可以省略。
以上用例的“吾”都做主语,我们发现做主语的共有17例,都是第一人称单数。剧本中人物做自我介绍时,多用“吾”,似乎显得庄重、严肃。下面我们看“吾”做定语的用例:
(5)李:吾的部下使用的武器都有六百有零。(齐备多时)兵扯河北(啊)。(《黄河摆渡》)
(6)白:本镇,薛义。
想夫妻俩进京前去投亲,谁知投亲不遇,偶遇奸贼张合得见吾妻有几分姿色。他想强逼为婚。吾妻不从,将我诳进府衙,用酒灌醉,将我送进县衙,一打一抬,定成死罪。多感得吾妻身背冤单叫冤。(《泗水拿刚》)
“吾”做定语的用例经统计有40例,分为称人和指物的两类。称人的有“吾皇”14例,“吾主”6例,“吾王”1例,“吾君”1例,“吾妻”3例,“吾等”3例,“吾神等”1例,“吾儿”2例,“吾父”1例,“吾兄长”1例,“吾女儿”1例,“吾的部下”1例。指物的只有3例:“吾心”“吾话”“吾心中”各1例。
“吾”跟“我”都能与“等”结合成“吾等”“我等”,表示复数。从我们搜集的剧本来看,“我等”用得较多,“吾等”用得较少。例如:
(7)神1:我等下凡有好些日子了,事情也做完了,该回天庭缴旨。(《天官赐福》)
(8)四神:吾等告辞了。(四神下)(《天官赐福》)
(9)众仙:娘娘,洞宾酒醉乃吾等之罪。(《蟠桃宴》)
(10)众仙:娘娘,我等喝够了,告辞了,娘娘万寿无疆!(《蟠桃宴》)
(11)内喊:“王爷在上,我等拜寿来了。“王”一齐进府。(《九锡宫》)
从用例看来,“我等”似乎只能做主语,“吾等”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定语。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了邵阳布袋戏剧本中词语的使用特点,主要是方言色彩和书面语色彩。其实,剧本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方言和书面语等语体色彩。“我”可用于方言和共同语,无所谓方言色彩。“俺”带有典型的北方方言色彩,“吾”带有典型的书面语色彩。方言色彩是相对于普通话色彩来说的,书面语色彩是相对于口语色彩来说的。邵阳布袋戏属于地方戏曲,是方言演唱的,剧本词语当然绝大多数是用当地方音演唱,但是它的剧本词语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方言词语。虽然剧本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地方言词语,带有比较浓厚的本地方言色彩,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剧本词语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话,有一部分是其他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