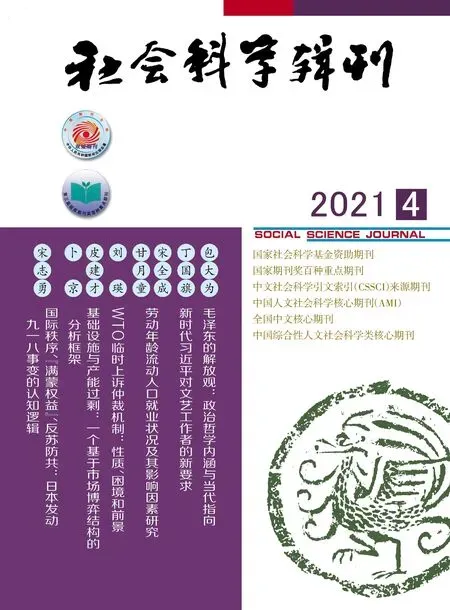《逍遥游》英译若干问题述论
于雪棠
一、《逍遥游》篇题英译对主旨的揭示
《逍遥游》是《庄子》首篇,重要性不言自明。国内古今学者对“逍遥游”的意旨多有探讨,英语世界对“逍遥游”的理解也多种多样,仅从篇名的英译就可看出端倪。19世纪有三种译法。巴尔福 (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 译为Wandering at Ease〔1〕,即自由自在地漫游,at ease有轻松、安闲、舒适的意味,这个译法颇能表达出“逍遥”之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 译为Transcendental Bliss〔2〕,超越性的极乐。transcendental意为超验的,尤其指宗教或精神方面的超验、玄奥;bliss是极乐、天赐之福的意思。这种译法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将“逍遥游”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精神体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译为Hsiao-yao Yu,or Eny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3〕①James Legge,The Texts of Taoism:The Tao Te Ching of Lao Tzu;the Writings of Chuang Tzu(part I),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62.此版本为牛津大学出版社1891年首版未经删改的重印本。,他采取了威妥玛音译和意译两种方法翻译。其意译强调的是不受打扰的安闲。理雅各还明确解释说:“逍遥游”的意思是根据郭象注解释的,是适性之逍遥,而非庄子的超越之逍遥。〔4〕这三种英译,都不包含近代以来流行的自由或精神绝对自由的意思。
20世纪《庄子》的全译本和节译本比较多,“逍遥游”的译法也多种多样。第一类是将“逍遥”译出自由义。这种诠释在英语世界中颇为常见。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的翻译是Excursions into Freedom〔5〕,即远游至自由之境。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 译为Free and Easy Wandering〔6〕,即自由安闲的漫游。山姆·哈米尔(Sam Hamill)和西顿(J.P.Seaton)的译本也采用了这一译法。〔7〕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的译本《要道:道德经及〈庄子〉内篇学说的道家核心思想启蒙》流传颇广,他直接将《逍遥游》译为Freedom〔8〕,即自由。大卫·辛顿(David Hinton)《庄子内篇》译为Wandering Boundless and Free〔9〕,即自由地漫游于无限。这一译法在自由之外多了一层意思,突出了逍遥之境的空间特征:广大无边。彭马田译《逍遥游》为Wandering Where You Will〔10〕,即漫游于你想去之所,这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汪榕培译为Wandering in Absolute Freedom〔11〕,绝对自由地漫游,很明显,译者采用了近代以来最广泛流行的“逍遥游”义。
第二类强调主体心灵或曰精神的状态。梅维恒 (Victor H.Mair) 译为Carefree Wandering〔12〕,心无挂虑地漫游。这一译法强调逍遥游的心灵状态,没有任何牵挂,无思无虑。还有强调主观感受的译法。冯友兰(Feng Yu-lan,1895—1990)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13〕,快乐的远行。林语堂(Lin Yutang,1895—1976)也采用了这一译法,只是稍有变动,译为A Happy Excursion。〔14〕冯家福 (Gia-Fu Feng,1919—1985) 译为Happy Wandering〔15〕,快乐的漫游。这三位华人或华裔学者都用happy来表达逍遥的意思,happy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是感到快乐或幸福。冯友兰首用excursion,突出逍遥游在空间上的特点,是远行之游,与《逍遥游》所写鲲鹏将从北冥徙于南海的寓言暗合。
第三类是突出精神之游,突出逍遥游的幻想特性。魏鲁南(James R.Ware,1901—1977)译为Let Fancy Roam〔16〕,让幻想漫游,逍遥游的主体是身心兼具或形神兼具之游,还是精神的逍遥之游?这个译法标示的是只在幻想中发生的游,不是形神兼具之游。这与其他译法明显有区别,表明译者关注的是逍遥游的空幻性质以及游的主体问题。
第四类是强调动词。“逍遥游”也写作“逍遥遊”,三个字的偏旁相同,都是行走义。现在理解的“逍遥”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类似“徘徊”“彷徨”“徜徉”义,而是指向了心灵的自在、自得的感受或状态。在原初意义上,“逍遥”与“游”是联合结构,不是偏正结构。有译法突出了这三个字的动词行走义。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译为Going Rambling Without a Destination〔17〕,漫无目的地闲逛,going和 rambling两个动词ing形式,突出了行走的不间断性。吴光明(Kuang-Ming Wu)的译法类似,即Hsiao Yao Yu,Soaring and Roaming〔18〕,翱翔且漫游。需要注意的是,葛瑞汉的翻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逍遥游的无目的性。这是哲学家观照下的意义,本土学者未曾明白指出,然而确实十分准确、深刻。一旦有目的性,便有束缚,则不可能逍遥。葛瑞汉的这一翻译思路并非首创。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将“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译为“aimlessly tread the path of Inactionbyitsside,orvacantlyliedreamingbeneathit”〔19〕,在其侧漫无目的地行走于无为之路,或者在其下神情茫然地躺着做梦。与葛瑞汉的翻译路径刚好相反,是将“逍遥游”译成有明确的目的。法国汉学家戴遂良(Leon Wieger,1856—1933)选译了部分《庄子》篇章,本是法语,转译为英文是Towards the Ideal〔20〕,即朝向理想,这个翻译已经偏离“逍遥游”了,尽管“逍遥游”确实是一种理想境界,然而直接译成“朝向理想”,这个目的性太强,而“逍遥”的意思又完全没有表达出来,这是所有翻译中离原义最远的一个。不过,这是由法语转译,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第五类,强调逍遥游的超越性。翟理斯译为Transcendental Bliss,超越性的极乐。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宗教学教授包如廉(Julian F.Pas,1929—2000)译为Free Flight into Transcendence〔21〕,自由地飞向超越。美国著名道教学者苏海涵(Michael Saso)在论文《庄子内篇:一位道教学者的冥想》中译为Journey to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ce〔22〕,前往超越境域之旅。不仅在篇题的翻译上明确“逍遥游”的超越性,文中还指出:这章的冥想的目的是要理解一个人是如何超越变化的世界,进入四海之外的永恒世界的。〔23〕爱莲心(Robert E.Allinson)也有类似的思路。他说:如果不只是考虑语言上的对应,而力求译出其哲学意蕴,“逍遥游”可以译为The Transcendental Happiness Walk(超验的幸福漫步)。〔24〕
尽管庄子所云“逍遥游”并非极乐、狂喜,更没有宗教意蕴,但文中所描述的实现逍遥游的境域乃无何有之乡,确实具有超现实的因子,翟理斯的译法在哲学层面而非宗教层面确实揭示了“逍遥游”的这一特质。包如廉和苏海涵继承了这种思考的方向,三位学者都有宗教学的背景,他们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发现了与宗教超越性相契合的因子,并将之特别提炼出来,启发了众多读者对“逍遥游”的理解。
21世纪以来对《逍遥游》篇题的英译,整体看没有新的思路。贤·霍斯曼(Hyun HÖchsmann)和杨国荣的合译本译为Wandering Freely〔25〕,自由地漫游;任博克(Brook Ziporyn)译为Wandering Far and Unfettered〔26〕,无拘无束地漫游至远方;索拉拉·托勒(Solala Towler)译为The Way of Free and Easy Wandering〔27〕,自由自在地漫游之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英译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逍遥游”的意蕴:一是游的主体,二是游的心灵状态,三是游的超现实性,四是游的空间特征,五是游的无目的性。篇题往往揭示篇章的主旨,对篇题的英译,绝不只是词语层面的翻译,还涉及更深层次的对文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多样的英译丰富了我们对《逍遥游》的理解。此外,还应当看到,在对古代文本进行阐释的时候,当然要力求揭示文本本来的意蕴,不过,不能片面强调以古释古,用古代的学术话语很多时候无法予人以清晰的认知。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运用现代学术术语去解析经典文本是必由之路。如何阐发古代经典的精微奥妙,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几个关键词英译的学术及文化语境
梳理过几种主要的译法之后,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和西方两类不同学术传统因子。首先看“逍遥”。采用了大量中国古代注疏的理雅各译为enjoyment,这与中国古代对“逍遥”的儒家化阐释一脉相承。理雅各的译法接近古人所云“自得”。“逍遥”一词,成玄英《庄子注疏序》引魏晋穆夜之说,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云:“《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这是以“自得”释“逍遥”,后代遵循此说者甚众,不复一一。理雅各所译enjoyment即源于这类解说。冯友兰以happy释“逍遥”,以乐作解,在中国古代的释读中也不乏其人。宋代理学家林希逸的《庄子》阐释在庄学史上踞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影响颇大。他解释曰:“逍遥,言优游自在也。《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只一‘乐’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台》曰‘乐只君子’,亦止一‘乐’字。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28〕林氏以儒释庄,用《论语》和《诗经》中的形容孔子与君子的“乐”,来解释“逍遥”的含义。二者实大相径庭,其间的偏失不必多辨。冯友兰以happy来译解“逍遥”,不难看到我国传统学术的影子。有趣的是,林语堂和冯家福两位华人学者,对“逍遥”一词也都采用了冯氏的译法,而英美学者则无人采取同样译法,其中确实存在中西学术传统的差异。
对“游”的翻译也蕴含着中西文化差异。冯友兰译为excursion,远足。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外出”这个意义上,“游”意味着去远方。比如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楚辞·远游》开首即云“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29〕,继而铺陈游于方外,与真人仙人为伴。结尾云:“经营四方兮,周流八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30〕所游之境超出人间,不可谓不远。从中国文化的传统语境看,应当说冯友兰的翻译揭示了“游”的一个重要意蕴,强调的是空间距离的遥远。
对照一下,从最早的《庄子》英译本开始,英美学者通常都用表达漫游、闲逛意思的词来翻译“游”,主要有wander、roam和ramble。这个译法揭示了“游”的另一层意蕴,即游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牛津词典中,这三个词的英文解释都提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学者的眼中,相比空间上的远,游的无目的性更重要。而且,这三个词也都包含“心情愉快地闲逛”这层意思,西方学者更重视游的主体的心理特点。
“化”是《庄子》的一个重要概念,首次出现在《逍遥游》开篇中。鲲“化而为鸟”的“化”有多种译法。翟理斯〔31〕、理雅各〔32〕均译为changes into,华兹生译为 changes and becomes〔33〕,魏鲁南译为evolves into〔34〕,巴尔福译为transformed into。〔35〕冯友兰〔36〕和梅维恒〔37〕都译为metamorphoses into。这些译词揭示了“化”的多重含义:进化、变化、变化而成、变形、转化等。metamorphose指内在的性质、结构与外表发生彻底转变,重在强调生物学角度的变化之态,意义单一。诸种译法中,笔者认为《庄子》全文首译者巴尔福的transform into最好。“化”是一个过程,change表达的变化意义比较宽泛,且侧重表明变化的结果,而transform除表明外形的转变外,还可以表达更多精神层面的转化。巴尔福对“化”的英译,在后来的研究者中得到了回应。爱莲心认为《逍遥游》运用了一些文学手法,它们说明《庄子》作为一个整体其主题是自我转化(self-transformation)。《逍遥游》以一个神话形式的转化故事开篇。鱼,就像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或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生活在无知之中。然而,鱼内在地拥有将自我转化为另一种生物的能力。鸟象征着让我们联想到自由和超越的生物。其中蕴含的主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内在转化的可能性,转化的结果是获得自由。〔38〕任博克也提出,鲲化为鹏的故事引出了《庄子》三个主题:化(transformation)、有待(dependence)及视角性知识的局限性(the limitations of perspectival knowledge)。〔39〕化,不仅是形态上的改变,还包含更多的内容。transform被更多地运用于解说“化”,这一现象说明研究者对“化”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庄子》之文奇幻多姿,多有特殊的名物词,《逍遥游》也不例外。篇中有些特殊的名词,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英文,有的译者采取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也有学者用接近的名词来翻译,这种译法有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魏鲁南把“鹏”译为Rukh〔40〕,这个词是指阿拉伯和波斯语传说中的大鹏。不过,这种译法很容易偏离原文的意蕴。最典型的是“鲲”,翟里斯译为Leviathan〔41〕,利维坦,这个名物在《圣经》中有时被用为描述象征邪恶的蛇,有时被描述为巨大的海怪。这在《以赛亚书》“以色列的救赎”一节、《约伯记》的第41节、《诗篇》第74节中都有描述。翟里斯有着深厚的宗教修养,他从自身的知识结构及西方文化传统语境出发进行翻译。这个译法的好处是能直接引起读者的想象,然而,其弊端亦显而易见。在《圣经》中利维坦是邪恶的海怪,是人们要想方设法铲除的对象。在《逍遥游》中,鲲化而为鹏,飞往南冥,是作者肯定的对象,在后世的接受中也把鲲鹏作为正面的、进取有为的象征。然而,翟里斯用这样一个海中怪兽翻译“鲲”,很容易传递给读者邪恶之物的印象,这与原作之意背道而驰,大相径庭。后来的译者应当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这一译法并没有为其他译者所接受。
另外,“至人”一词为《庄子》所特有,篇中反复述及,巴尔福〔42〕、华兹生〔43〕译为Perfect Man,完美的人,且首字母大写,是将“至人”视为专有名词。大多数译者选择这种译法。葛瑞汉将其译为utmost man〔44〕,极高远之人;梅维恒译为ultimate man〔45〕,终极之人。后两种译法更有哲学意蕴,更贴近原义,也更能表现出庄子“至人”一词的独创性。对“至人”“圣人”“神人”之“人”,苏海涵的解读异于众人且颇有启示意义。他说三种类型的人被定义为倾向于对不朽的沉思。〔46〕在英文表述中,“人”被译成man or woman,男人或女人,从现代学术角度看,这种解读似乎包含着女性主义的影子,其实不然。这是深深体会到道家学说独特性的一种翻译。《老子》以谦退为上,多以女性为喻,如谷神玄牝之说,而《逍遥游》所描述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也隐约有女性的特征〔47〕,因此,看上去不起眼的“男人或女人”,却是深得道家真谛之解。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8〕是《逍遥游》很重要的思想。无己,大多译为selfless或has no self。有的译者用动词来翻译。比如,翟理斯将“无”译为ignore,忽视、忽略,这三句他译为:“The perfect man ignores self;the divine man ignores action;the true sage ignores reputation.”〔49〕完美之人忽略自己,神圣之人忽略有为,真正的圣人忽略名声。苏海涵译为“the zhiren至人(man who seeks perfection)who transcends self(wuji无己)”,“the shenren神人(spiritual)who transcends meritorious acts(wude无德) ”①苏海涵的译文中明确将“无功”写作“无德”,不知何据。英语世界中可能流传着一种“神人无德”的中文版本。“神人无功”一句,华兹生的译文是“the holy man has no merit”,依据的原文可能也是“无德”。见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32。,“the shengren圣人(holy sage) who transcends good and fame(wuming无名)”〔50〕。将“无”译为transcend,虽然在字面上似乎并不相符,然而,在笔者看来,超越却最能揭示“无己”“无功”“无名”的深层意旨。苏海涵对这三个命题还有论说,认为这段文字的目的是将在人世间为自我完善而追求有为、功绩、好名声的外在努力,与个体寻找内在超越的统一性作出区分。因此,“无”这个词被译为相当于《老子》的无为之道。这种状态可以被描述为“专注于无名之道”即与道为一,志于道者通过对微宇宙中心内超验存在的冥想,以寻求消除“己”,消除“得”,消除追求名誉的行为。〔51〕笔者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庄子》中的多个“无”都可译为超越,如“无乐”“无情”等。“至乐无乐,至誉无誉”〔52〕,最高的乐超越快乐,最高的誉超越名誉、称誉。庄子与惠子辩论人有情无情,云:“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53〕无情,是超越各种情感。
此外,还有几个词语的英译也颇值得玩味。一是开篇所云“北冥”“南冥”之“冥”。冥,幽暗,又通“溟”,海也。在“北冥有鱼”的语境中,将“冥”译为“海”并无问题,英译多为ocean,19世纪的三个全译本及20世纪的有些译本均如此。如冯友兰译为Northern Ocean〔54〕,葛瑞汉译为North Ocean〔55〕,首字母大写,是将“北冥”视为专有名词。然而只译为“海”,失去了“冥”本字所具有的幽暗广远色调,以及道家特有的玄冥幽深之哲学意味。中文亦如此。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北海有鱼”,脑海中不会有幽暗广远深玄之联想。而《庄子》中言及海,并非均用“冥”,重要的《秋水》即言“北海”,因而,绝对不能简单地把“北冥”等同于“北海”。有译者注意到“冥”本字之义,将其译为黑暗。如华兹生译为NORTHERN DARKNESS〔56〕,所有字母均大写,表示专有名词。吴光明译为Northern Darkness,首字母大写,也是表示专有名词。〔57〕这种翻译自然会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和思考。然而,将“冥”仅译为黑暗,又失去了“海”的鲜明意象。有译者力图在翻译中传达“冥”的双重意蕴。如魏鲁南译为dark waters to the north〔58〕,梅维恒译为 darkness of the Northern Ocean。〔59〕这种译法兼顾了“北冥”所具有的“海”和“幽暗”双重意蕴,颇为传神。这也提示我们,当今出版的诸多古代文学作品选中,不应当只将“北冥”注释为“北海”,而应当将其特有的道家玄冥之意揭示出来,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体会《庄子》文字之妙。
“齐谐”的英译也寓含译者对《庄子》整体哲学思想的把握。齐谐,古注或云人名,或云书名,并无更多解读。诸多译本除译为书名,并意译为戏言集外,还有特别译出“齐”与“谐”之义者。如华兹生译为The universal harmony〔60〕,宇宙的和谐,吴光明译为Tall-tales of universal-harmony〔61〕,有关宇宙和谐的荒诞故事集。庄子倡导与道为一,消融自我于宇宙运化之中,《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2〕,“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63〕,《寓言》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64〕皆是此意。《逍遥游》所说“《齐谐》者,志怪者也”之“齐谐”,并无宇宙和谐之义,译者如此翻译,实为过度阐释。这个过度阐释虽然以《庄子》思想为背景,可见译者的精心覃思,但是也提醒译者,不宜将所有语词都看作与全书主要思想有关,有些词语并无深意,要与其用作特定概念时的意义相剖离,要在特定的语境中作具体分析,避免赋予普通词语以特殊意义。其实,不仅是译者容易产生此类误读,便是本土研究者,有时也难免产生这样的问题。
三、对《逍遥游》文本的删改及讨论
有的译者认为《逍遥游》文本存在重出或错置等问题,因而,在译文中做了改动。葛瑞汉翻译的《庄子内篇》一书从开篇到“圣人无名”一句〔65〕,中间有部分文句和文段被加了圆括号。在“圣人无名”后,他加了一段注释,云:加了圆括号的文字看似庄子后来添加的,或者是后来的注释,有三处在中文文本中似乎位置错乱,译文把它们挪后了一点儿。〔66〕全篇加圆括号的共有六处,对应的中文原文是:“南冥者,天池也”,“汤之问棘也是已”至“此小大之辩也”一段,“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还有三处被更改了文本位置,具体如下:
原文: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67〕
葛译对应的中文: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谐》之言曰:“……”(《齐谐》者,志怪者也。)
原文: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68〕
葛译对应的中文: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原文: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69〕
葛译对应的中文: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虽然,犹有未树也。)
葛瑞汉对《逍遥游》文本的这种处理,建立在两个认识基础之上,一是其《逍遥游》题解清晰表明的:《逍遥游》本来就是一些文字片段,它们被编辑者集结在飞翔于世界有限视角之上这一主题之下。〔70〕他在译本的“前言”中也提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写书,他们写下格言、诗句、故事、思想,到前3世纪,在绑在一起的竹片卷成的卷轴上写文章。《庄子》的一个章节可能是作为组成一个卷轴的条目或条目的集合而产生的。〔71〕二是译者有权对文本进行重新组合。“前言”指出,《庄子》经过了郭象的编辑,文本中混杂了魏晋新道家及佛教的注释,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就需要现代学术研究的全套装备,而中国、日本和西方的专家直到最近才开始运用现代学术研究的装备,以区分文字的不同层次,恢复损坏或错位的文本,增进对知之甚少的古汉语语法的理解,弄清楚哲学术语的意义。〔72〕葛瑞汉的译本力求标示出《庄子》文本中不同的文字层次,调整错位的文本,意图恢复一个更原始、更真实的《庄子》。
然而,这可行吗?其文本处理有没有合理性?这样的做法会导向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引出哪些问题?林顺夫详细分析并批评了葛瑞汉的这种译法。〔73〕林顺夫认为“南冥者,天池也”的确看起来像是在完成鹏的故事之后加上的文字,用以解释鸟所游之地。葛瑞汉的重新安排确实让整个段落看起来更有逻辑。然而,庄子会在意这种句子的逻辑顺序吗?有可能事实上更可取的是,当作者的思想浮现在其脑海中时,便将当前文本的开篇段落作为其思想的一种表达。“齐谐者,志怪者也”,属于这个语境,因为它与前一行在句法结构上是对称的。这两行起到连接两个平分的文段的作用,表达了作者的两组思想。将“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移至段尾,破坏了作者思想进程的呈现。文段语意的中断与转换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庄子抒情性想象图景的精确描述,葛瑞汉的重新编排彻底破坏了这一抒情特质。“汤之问棘也”一段在几个重要的细节上与前文鹏的故事不同。这两个关于鹏的文段建构了一个精确的例子,即在内篇中可以被称为“音乐结构”的组织机制,它可以被称为“音乐的”,因为它依靠“主题变奏”(variation on themes)来保持一篇散文的连贯性。“汤之问棘也”一段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篇首鹏之徙的变奏。
针对葛瑞汉对“宋荣子”一段文本顺序的调换,林顺夫评曰:“虽然,犹有未树也”一句,葛瑞汉调整插入的位置完全不合适,其对“彼此于世,未数数然也”一句的翻译也与原文意思恰恰相反。葛瑞汉对文本处理的结果成了聚焦于宋荣子和列子的比较,而原文是对在精神境界上升顺序中不同个性的列举,从自在的官员到游于无穷者。林顺夫还以钱穆《庄子纂笺》对《逍遥游》节段的划分为据,详细分析了六部分的意脉,认为这篇文章首尾呼应。在篇末,我们终于意识到对社会无用是庄子向往享有的绝对自由的基础,大而无用与逍遥游于此联结在一起。大树的意象、小动物和大牦牛也使人想起篇首的大鱼和大鹏。更重要的是,这篇的中心思想“逍遥”是在文本的最后几行植入的。这篇散文看起来随意的六个片段,内在是统一的,篇章结构确实清楚地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inner logic)。林顺夫强调了《逍遥游》文本自有的逻辑、作者特有的思考与论述方式,分析了葛瑞汉改动文本所存在的问题,其论说是令人信服的。
梅维恒的译本也直接删去了一段,用省略号标示出来。删去的原文是:“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74〕其译本在最后的附录中有一个“删去的文段”部分,将所删文段译出并集中罗列。他给出的统一的理由是:既因为它们是伪造的或是后来的注释,也因为一些其他类型的篡改误置入文本。〔75〕然而,他并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文献支撑或论证,这一做法颇为武断。
鲍则岳首先从文体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角度,详细分析了鲲鹏故事两段文本的结构问题,并将通行版本的下列中文文字重新删改排列。他引用了《逍遥游》开篇“北冥有鱼”至“而后乃今图南”一段中文原文,然后,不是在英译中做修改,而是直接更改中文原文。〔76〕对照如下:
原文: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改后: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九万里。去以六月息。
原文中加粗的文字,是被鲍则岳删改的。还有一段文本,也被做了一番改动:
原文: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改后:穷发之北有冥海,有鱼焉……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对于删改的原因,鲍则岳说,他认为“者”和“者也”删去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因而便删去了“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句尾的“者”和“也”,以及“去以六月息者也”句尾的“者也”。这明显是由于他对古汉语的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他还从表达逻辑连贯性的角度考虑,将原文中两次不同的鲲鹏叙述合并为一段,但是原文未必是无意的重复。显而易见,这种对文本重新编辑的研究方法,掺杂了很多臆测武断的成分,实不足取。
还有另一种对文本的改动。吴光明的译文分为七小节,前三个小节加了小标题,依次是:The big、The small、The big and the small〔77〕,这种处理是对主题的提炼,也是对文本的一种改造。小标题有将文本主题固化的作用,会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窄化甚至误导读者对文本丰富内涵的理解。
笔者认为,翻译应当忠实于原文文本结构,如果认为有问题,可以用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不宜直接改动译本。无论是直接删去某段文字或加圆括号,或加小标题,都是不合适的。《庄子》文本本身不属于主题单一类型的文本,无论是解读还是翻译,都应当充分尊重文本原貌,可以撰文讨论其文本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不能以某种尺度去衡量文本从而随意改变其结构。
19世纪的三个《庄子》英文全译本,都采用了中国古籍传统的正文夹注形式,对文本不做任何改动,有关探讨则在注解中说明,这是译者应有的态度。后来的译者也不乏这样的处理。同样是面对出现两次而文字有异的鲲鹏故事,华兹生的处理则异于葛瑞汉,他在“汤之问棘也是已”句后加了脚注,提出这个地方的文本可能有错误。注释引述了唐代神清的《北山录》所载文字:“汤问革曰:‘上下八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并说明某注释者认为《庄子》中有这个对话。华兹生的态度是:它是否属于《逍遥游》文本,是无法回答的问题。〔78〕这条注释虽不起眼,但足见译者对国内研究成果的采用以及对文本问题的审慎态度,值得肯定。
结语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非常重要的思想,篇题的英译集中反映了译者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从中既可看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也侧面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的过程。早期的英国译者并未将其与“自由”相关联,冯友兰初版于1931年的选译本“前言”中,明确运用了Absolute Freedom作为标题解说“至人无己”〔79〕,而这个“绝对自由”的概念,本是源自西方哲学。冯友兰以西方哲学视角审视《庄子》,之后,其说又为一些中西学者所接受。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在分析英译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给译者贴上任何文化标签,而应当作细致的辨析与甄别。
冯友兰以happy译解“逍遥”,快乐或幸福,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因素,也不乏西方哲学的影响。happy,既可译为“乐”,也可译为“幸福”。将其理解为“乐”则与我国学术传统相通,儒家特重“乐”,《论语》首章即是孔子所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讲君子有三乐。至宋,理学大儒推崇“孔颜乐处”,将其视为圣贤气象的要素。《庄子》并不标举“乐”,其“逍遥”的内核与儒家之乐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单纯以儒家之乐释“逍遥”,是以儒释道,并未得庄子之深意。比较而言,将“逍遥”译为happy,还不如理雅格所译enjoyment恰当。另一方面,如果将happy理解为“幸福”,则与西方学术传统一脉相承。在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西方读者看来,很自然会将happy理解为“幸福”。幸福,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以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康德等为代表的诸多哲学家均对此有深刻的阐发。冯友兰的译法并不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即使是深受其影响的修中诚也是如此。修中诚在其《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前言”中特别说明,他非常感激中国哲学家胡适和冯友兰。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2卷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冯著是其哲学教育的一个里程碑。〔80〕此后,修中诚英译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精神》〔81〕,但其“逍遥游”的篇名英译,取冯氏之excursion及freedom,而弃用happy。也就是说,在西方学者眼中,“逍遥”与happy并不对等,他们并没有把“逍遥”理解为幸福或者乐。可以说,冯友兰的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庄子》的旨趣,而其偏离,又是产生于深谙古代儒家学说又兼通西方哲学的知识背景下,这个现象颇值得玩味。进一步说,英译,不仅是文辞的对照,还涉及如何沟通古今中西学术的大问题。
在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上,可以看出,译者确实有其特殊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最典型的是将“鲲”译为Leviathan,这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会导致对《庄子》的误解。有的英译虽然有其西方宗教思想之源,却能超出中文字面的含义,深刻领会《庄子》的真精神,对学界颇有启示,比如将“无己”“无功(德)”“无名”英译为transcend。有的则能看出译者力求传达中文词语丰富意蕴的努力,比如“化”和“北冥”。
对《逍遥游》的文本,个别译者做了删改与移位,这一方面反映出对传世文献文本的态度,尊重其原貌还是断以己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西方在思维方面的差异。葛瑞汉对文本的改动,主要以逻辑的连贯性为标准,而《庄子》大部分篇章的行文并不在乎连贯性,卮言曼衍才是其典型的言说方式及文体形态,因此,这些对文本的改动颇有方枘圆凿之感。译者用富有西方学术特色的逻辑分析思维去改动具有随想录性质的《庄子》文本,其失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