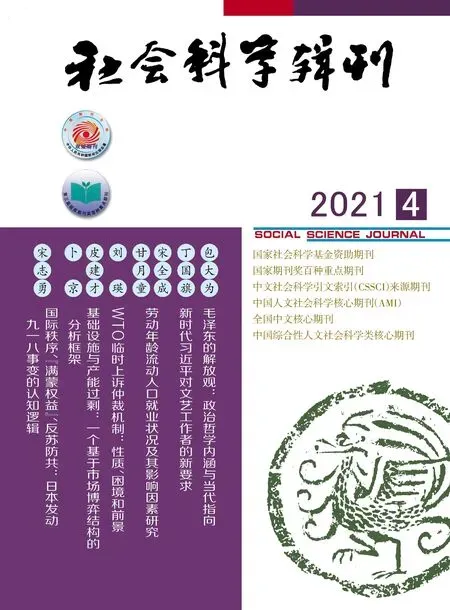情感的政治与道德生命的盈减之道
隋思喜
现代人在伦理实践中常常遭遇道德困境,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指导伦理实践背后的生命秩序观念出现了危机。现代性哲学将解决主客物我关系问题进而认识与征服客观世界视为自己最基本的思想特征和理论成就。在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统摄下,作为自我认识对象的人本身,也成为一种可以被剖析为物理、生理、心理等不同面向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之物。这种自我认识的思维方式依赖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导致人的客体化、对象化甚至工具化。而在这种客体化、对象化以及工具化的过程中,人逐渐丧失了他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深深陷入伦理实践的道德困境之泥淖中,成为现代性危机在生命问题上的根本体现。现代社会伦理困境的根本解决,需要一种在重思生命秩序的基础上借助道德教育来提供引导行动之思想洞见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什么样的生命秩序之思想洞见能够指导我们的道德实践并给予我们以积极的智慧?这种生命秩序的思想洞见如何形成?儒家的特点在于注重从道德的理路来认识世界并反思我们的实践活动。对儒家关于生命秩序问题的求索及其通过礼乐教化的方式而养成这种生命秩序的工夫论作反思性的重新理解与建构,能够为现代人的伦理实践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洞见。
一、儒学的道德生命秩序观
儒学之所以能够对现代人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及其难题的哲学反思提供有意义的洞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关于生命的哲学①在解释中国哲学具有怎样的思想特质时,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它的主要课题就是生命,即“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儒家哲学正是此生命之学问的典型代表。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能够为生命所面临的各种难题,特别是如何行动的实践难题提供一种观念和意义上的指南。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儒家把人的问题看作是第一问题,其主张的“反求诸己”思想,包含着将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对人的存在本身进行反思性认识的内容。这表明,认识自我以及成就自我,乃是儒学的最高目标。所以,儒学首先是一种“为己之学”。这种为己之学的确立,逻辑上奠基于人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儒家对自我的认识与理解构成了儒家的人性理论。就思想特征而言,儒家的人性论兼具知行并重的意义,既直接指向对生命秩序的认知与求索,又强调用求索出的生命秩序来指引人实现生命的自我提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人性论为思想主干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既是对生命秩序进行求索的自我认识之历史,亦是践履与养成生命秩序的道德实践之历史。因此,在儒家看来,首先实现对生命秩序的求索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关键的事业。
事实上,认识自我是一个东西方哲学都普遍关注的根本问题②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或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页。,而儒学也以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根本问题并参与其反思。儒学之所以为儒学,不是因为它发现了特殊的哲学问题,而是因为它选择了以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人类所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区分思想的永远不是思想所试图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即中国哲学通常所说的“观”。那么,儒学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生命秩序观?谈到秩序,儒家对秩序的理解包含三重维度:一是天地的秩序,即“自然”。所谓“自然”,是自己这样的意思,指天地自然运行所具有的自性本然的一种秩序,儒家称之为“天道”或“天理”;二是心灵的秩序,即“心性”。所谓“心性”,指人心的本来面目,即真心本性的意思,儒家称之为“良知”“良能”或“天地之性”,代表着人心先验具有的道德法则,即“性理”;三是身体的秩序,即“伦理”。所谓“伦理”,指人视听言动的身体化行为所应当遵守的礼法规范,包括个体的行为规范以及拓展此行为规范而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理论。整体地看,儒家关于秩序的三重维度之关系的判断是这样的: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
首先,《中庸》以“天命之谓性”的命题解释了天地秩序何以能够内化为心灵秩序。关于“性”,王夫之解释说:“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也。”〔1〕这意味着,“性”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关联“天”与“人”的关系性概念,隐喻天人交通时出现的生命秩序之奠基。天地秩序与心灵秩序由此互相渗透。在儒家哲学中,虽然“天”依然保留道德秩序之最高保证的地位,被视为道德之源头,但之所以能如此,儒者认为,这是因为“天”是我们的生命之本性,而非因为“天”具有神秘伟力或为人格神。儒家通过“天命之谓性”的言说方式,将“天命”内化为人的生命本性,即德性,而这一德性作为一种“道德的主体性”是显现于人心的。事实上,对于主体存在而言,“心”就成为一切道德秩序的生命本源和最高保证,最终由陆王心学以“吾心即是宇宙”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心灵在宇宙秩序之地位序列中的升格运动。
此外,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则以“心为身主”的命题得以确立。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秩序包括心灵秩序与行为规范两个基本层面。孟子曾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如果说儒家的生命秩序可以概括为仁义之道的话,那么分殊地看,心灵秩序可以用“仁心”来指称,而行为规范则可以用“义路”来表达。这两个秩序之间的关系,孔子首先通过“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命题实现了贯通。在这一命题中,“所欲不逾矩”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实践不逾越基本的行为规范,之所以个体能够自觉地遵守行为规范,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行为规范出自自己的心灵秩序,这就是后来孟子在“居仁由义”的逻辑中所发挥的“义内”思想——“仁”之人心外化为“义”之人路。在这种贯通中,儒家强调心灵秩序是身体秩序所代表的行为规范及交往理论的规范性来源。
虽然在学理上,儒家将对秩序的认识分殊为三重维度,但在精神上,三重认识维度都指向同一精神原则:将天地秩序、心灵秩序与身体秩序实现一以贯之的内在同一性原则是道德。正如方东美所指出的:“古代中国人的宇宙概念,乃是所有平等的存在者都能围绕最高的道德价值标准之中心而获得其自身生命的完成。”〔2〕在儒家看来,天地秩序是道德的,道德是宇宙的形上之道,谓为“天道”;心灵秩序是道德的,道德是心灵的存在本性,是为“仁道”;身体秩序也是道德的,道德是身体的行为之矩,故为“义路”。概言之,儒家的生命秩序是一种道德的秩序。
首先,于天地而言,这种道德的生命秩序源自天地生生不已的形上天道,因而人与宇宙具有最大的同一性,这是“因为生命的自然和道德秩序始自天的创造力,所以被儒家视为占据宇宙中心位置的人,能够匹配最高的创造能力。以这种方式儒家发展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作为价值中心的人生观之前奏”〔3〕。这种思想最终演变成为宋明理学的天人一体论。
其次,于万物而言,这种道德的生命秩序将人与其他存在者明确地区别开来,并揭示了人何以不同于其他存在。事实上,儒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与天地间的其他生命存在相比,人何以是最优秀的?关于这种“人是天地间最优秀的存在者”的观点,可以说是普遍地存在于儒学之中。例如,《尚书·泰誓上》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章第九》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祭义》中,乐正子春转述他从曾子那里所听到的孔子的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孟子通过对四善端的阐释回答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问题。荀子则通过与有气而无生的水火、有生而无知的草木以及有知而无义的禽兽相比较,突出人是兼备气、生、知、义四者的,所以“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被称为理学之开山的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在生成演化的宇宙论图式中界定与安排了人的位置,指出“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4〕。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儒家都站在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中的最特殊存在者这一自觉的立场上来追问人之为人的问题,并认为人凭借自己所特有的生命之道德秩序,能够辨别出自己作为万物中最特殊的存在者的特殊性所在,进而明确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由上述可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上,儒家都强调了人的道德性,把人视为一种道德的生命存在。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儒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实现道德生命的崇高与伟大。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在于“学”。从孔子开始,儒家明确地把“学”看作是实现自己、提升自己和发展自己的最主要的途径或手段,确立了“学”为儒家最高的纲领性精神,即朱熹所说的“故君子惟学之为贵”〔5〕。《论语》将孔子“学而时习之”一段话列为首篇的首章,并非随意编排,而是有认真考虑在其内的。事实上,孔子非常重视“学”①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而且将“学之不讲”视作自己生命之中最重要的四种忧患意识之一。②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也是在此种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他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这一生命事业昭示着,人的卓越性不受天赋禀性或地位财富等因素的决定,而由自己的努力,即学习来负责。所以“学”在儒家的生命实践中具有根基性的地位,无怪乎刘宗周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孔子一生精神,开万古宫墙户牖,实尽于此。”〔6〕此语深有见地。儒家用“圣人”来指称那些崇高与伟大的生命,通过对“圣人气象”的描述和刻画,为人的生命之自我圆成树立了一座精神“灯塔”,让每一个生命在人生之海航行时不至于陷入精神迷失而不知前进之方向的困境。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实现生命之崇高与伟大的学问便被称为“圣学”,即成圣之学。既重视“学”的工夫,又以“圣”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学以成圣”就成为儒者们眼中最辉煌的生命事业。希圣之学是实现生命的崇高与完满的自我圆成之事业。要建设好这一生命事业,关键的是要规划好建设道德生命事业的文化。在儒家,这种规划道德生命事业的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而养成崇高与圆满的道德生命之实践方式则被称为“礼乐教化”。
二、礼乐的盈减及其相须为用
儒家对秩序问题的理解,形成了以“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为主要观点的三重维度、两层关系之思想格局。这三重维度、两层关系的秩序思想表现于文化观念中,则为礼乐文化。具体而言:
首先,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的过程主要呈现为“乐”的观念与精神。一方面,因为乐与人心相通,“乐”是生命的心灵之精神状况的直接显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即“天命之谓性”的过程,正是生命之“德性”得以形成的过程,而“乐”是这种德性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礼记·乐记》将“乐”与“德”直接联系起来:“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的作者在上述这段话中对“性”“德”“乐”三者之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阐释:首先,“德”是“性之端”,指“德”是人之天性的端绪表现,即人所禀受之天命而表现于自我生命中的东西就是德性。其次,“乐”是“德之华”,这意味着乐是人之德性的成熟完美之直接表现形式。这也意味着“乐”与天命相通。如《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而《中庸》则说“天命之谓性”,天地之命即天命,天地之命即是性,可见,“乐”是直接与人的天地之性相贯通的。这一思想也渗透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命题中。“诚”与“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中庸》说“诚者”就是“天之道”。对于“诚”,朱熹则解释为“真实无妄”〔7〕。故与作为人为之“伪”的礼相比较而言,儒家认为,乐不可以为“伪”而是“诚”,即乐与天道以诚相通。所以儒家认为,乐是德性的直接显现方式。
其次,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礼”的观念与精神。前文分析秩序时指出,儒家的心灵秩序可以用“仁心”来指称,而身体秩序则可以用“义路”来表达。如果说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的过程确立了“仁”原则的正当性基础,那么,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的过程则确立了“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仁”原则的确立使得心有定主而依于仁,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义”原则的确立使得身有定矩而立于义,所以孟子说“义,人路也”。仁义之道也是儒家的生命秩序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于儒家的文化观念中,正是礼乐,如《礼记·乐记》中判断仁义与礼乐之关系为“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儒家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想,熊十力即明确地将礼乐视为人文教化之本源,并认为乐即仁,礼即义。①熊十力说:“《周官经》乃春秋拨乱之制,所以为太平世开辟洪基,其化源在礼乐。乐本和而忘人我,仁也;礼主序而人我有别。然治人必先治我,义也。礼乐修而仁义行,万物齐畅其性,方是太平之鸿休,人道之极盛。”见熊十力:《原儒·再印记》,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页。既然礼即义,则礼正是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的表现形式。故就三重秩序与礼乐之关系而言,《礼记·乐记》中“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一句是最好的概括。概言之,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的过程,就是“仁”的确立过程,“乐”正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的过程,就是“义”的确立过程,“礼”则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礼乐精神是道德生命之自我意识的彰显,本质上就是儒家的生命秩序之精神。
如果说礼乐文化凝结了儒家对人之道德生命秩序的理论认识的话,那么礼乐教化就彰显出儒家养成人之道德生命秩序的践履工夫。儒家经常说“成人”的话语,认为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养成的过程。当然,这种养成的过程,也是践履和落实自己本有的生命秩序的过程。儒家往往用“人道”概念来指称人的生命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人的不断被养成的历史,因此,“人道”概念表达了儒家关于道德的人及其道德实践过程的历史观念。在儒家,人的养成首先是个体的养成,然后由个体的养成达至群体的养成,这其实就是儒家的“修己安人”之学。这也正是《大学》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缘由所在。而在儒家看来,践履落实这种为学之道的最主要的实践方式就是“政”。在《礼记·哀公问》中,孔子明确提出了“人道政为大”的命题。①“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而对于鲁哀公继续追问的“何谓从政”问题,孔子则进一步解释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此外,《论语·颜渊》篇中也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的记载,而孔子的回答也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显然,以“正”释“政”,这是孔子的一贯之义和基本主张。这一解释主要是取得“端正”之义。在为政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为政者而言,首先需要端正的正是自己。所以在谈到“政”的问题时,儒家往往遵循孔子所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实践原则,强调一种“正人先正己”的政治实践逻辑。如果说儒家把个体养成的工夫称之为“正己”的话,那么,这种正己的工夫正是儒家所说的“政”这一概念的原初本义。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对“政”的理解,显然具有不同于现代之“政”的独特见解。在《中庸》中,孔子按照这样一种思考逻辑将政治与修身联系起来:要知道如何治天下国家就必须先知道如何治人,而要知道如何治人就必须先知道如何修身。②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当孔子强调知道修身就知道如何治人的观点时,显然,他所谓的治人主要指的是教导人如何实现修身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
儒家之政,就其思想的原初本义而言,最关切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如何实现所有人的修身。所以在儒家看来,“政”是有德之人所采取的一种最主要的道德实践方式。这种以实现所有人的道德养成为主要目标的儒家式之“政”,在实践方式上就首先表现为礼乐之治或礼乐教化。礼乐教化的“教”,含有《中庸》所言“自明诚,谓之教”的“教”之意义,而“化”也与《中庸》中所说“曲能有诚”则“形”“著”“明”“动”“变”“化”这一逻辑中的“化”相等。以《中庸》的“教化”思想来理解礼乐教化,礼乐教化具有牟宗三所说的如何来调节、运转和安顿我们生命的实践方式之意义。在论及儒家教化的功能时,刘子健说:“‘教’也不单指读书和育人,其含义是灌输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道德标准,并使之长存。相应的双语词‘教化’为‘教’的概念增加了‘化’的意蕴。儒家历经数百年之发展,其理想始终是对个人、社会和统治者进行管理、教育,使之转而向善。”〔8〕显然,正如学者们已经普遍指出的,就实践而言,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是在生命主体身上培养起一种道德秩序。作为自我教化的工夫,“乐”主要指向人心秩序的养成,而“礼”则关联着身体秩序的塑造。就生命之道德秩序的养成而言,儒家希望能够既养成人的心灵秩序,又养成人的身体秩序,然后合心灵秩序与身体秩序的内外通透而成就人的天地秩序。故而,在儒家看来,“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记·乐记》)。所以孔子有“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的思想。
因此,要进一步追问的就是:礼乐教化如何能在生命主体身上培养起道德秩序?这一问题也可以转化成如下的问题,即通过教化什么,礼乐之治才能在生命主体身上培养起道德秩序?儒家认为,礼乐教化的直接对象就是现实之人的“情”。按照《礼记·乐记》的说法,“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这表明,礼乐教化在具体实践上需要“管”的对象很明确,就是现实之人的“情”。那么,应该如何管治现实之人的“情”呢?儒家主张在涉及“情”概念时,主要区分为道德的“情感”和自然的“情欲”两种观念。针对“情感”与“情欲”的分殊理解,《礼记·乐记》提出了一种“盈减之道”:“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这里的“盈”“减”主要是在功能作用上说的,其针对的目标都是人本身。礼在人之外发挥作用,目的是减少人身上不好的东西;乐在人之内发挥作用,目的是增加人身上好的东西。具体地说,乐的主要作用是感动人心,存养人的道德情感,因为道德情感是使生命自然向善的本源脉动,对人来说当然是越丰盈越好,故“乐主其盈”。礼的主要功能是省察行为,克治人的自然情欲,因为情欲能遮蔽人的本真存在而使人陷入邪恶之泥淖,对人来说当然是越干瘪越好,故“礼主其减”。换言之,礼的功用在于“止邪”,即停止恶行,规范我们远离邪恶的事情,这当然是越少越好;乐的功用在于“章德”,即表彰德行,激励我们多做善良的事情,这当然是越多越好。①梁漱溟指出:“所谓‘礼主其减,乐主其盈’,大概礼是起于肃静收敛人的暴慢浮动种种不好脾气;而乐则主于启发导诱人的美善心理;传礼的自容易看人的不好一面。”既然传礼的容易看人的不好一面,则传乐的容易看人好的一面。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1页。所以儒家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辍淫也。”(《礼记·乐记》)凭借礼乐的盈减辩证作用,道德生命能够获得身心合一、内外圆成的完满人格之挺立。如荀子就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荀子·乐论》)这里的“志清”显然指的是人心意志清澈明白,而“行成”则指的是身体行动举止彬彬,“志清”而“行成”意味着道德生命之圆成发展的落实。正因为在生命之道德秩序的养成上,“礼”和“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功能,所以儒家主张“礼乐相须为用”(《礼记·乐记》),不可偏废或轻视任何一方,仅仅强调礼治抑或乐治,都不足以代表儒家在道德生命实践方式上的整全性观点。
三、情感的政治与生命秩序的养成
参照上述的分析,说儒家礼乐教化的实践始于现实之人的情感是可以成立的。虽然我们从“情感”与“情欲”的角度对现实之人的“情”进行了简略的分殊,但这种分殊主要还是侧重于从表现或作用上区分的。其实,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情欲还是情感,都可以说是现实之人的好恶之情,其差别只是表现或作用得适度与否。
在儒家看来,人的好恶表现出一种情感所具有的价值直觉之判断功能。例如,《大学》就将君子的好恶之情感视为“絜矩之道”。在解释“絜矩之道”时,虽然《大学》主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面来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②《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但我们知道,儒家也主张从“己欲立而立人”的积极面进行立说,所以“絜矩之道”亦可以从“所好于上,务以使下;所好于下,务以事上……”的积极面予以规定。显而易见,《大学》所强调的“絜矩之道”,具有行为之规范的意义,而就其判断准则言,所根据的正是人的好恶情感。当然,《大学》也进一步强调,真正能够理解和把握人之好恶的,只有仁人或君子,即“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这样,礼乐教化的对象就由人的情感进一步被明确为人的好恶之情。《礼记·乐记》中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在这里,《乐记》的作者将先王制作礼乐的目的归纳为“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强调礼乐的功用是“平好恶”。之所以特别强调要运用礼乐这样的方法来“平好恶”,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的好恶之情虽然能够自发地规范行为,但不能自然地成为一种正当的行为之规范。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提出“道始于情”①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这里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之说表明“道”始于情而终于义,与《礼记·乐记》“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说一致。转引自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的命题,而上述所引的《乐记》思想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命题的一种恰当理解,即人道实践从“教民平好恶”开始。前文中也指出,按照孔子“人道政为大”的说法,政治是人道最主要的实践方式,因此,依照“道始于情”的命题,我们也可以逻辑地说“政始于情”。
在儒学中,情感不仅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实践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之一。②蒙培元指出:“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哲学文化,必然要讨论人的存在的方式问题,情感便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因此,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便把情感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且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见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如果说情感是人的最主要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政治就是人的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实践方式,而实践方式的选择正是为了解决存在所遭遇的难题。作为一种道德生命的实践方式,儒家的整体主张是“礼乐教化”,而教化的直接对象是现实之人的情感,特别是人的好恶之情。礼乐教化,亦即礼乐之治,作为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实践方式,要解决的根本难题就是情感。当孔子说“有教无类”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人人都存在着相近的性情,他以帮助引导人们使人的性情臻于“中和”为己任,所以,就教化的实践而言,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递进工夫之路径。这一思想认为,诗教可以兴发人的自然情感,礼教可以端正人的自然情感,而乐教则完成由自然情感上升为道德情感的中和理想境界。③《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又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可见,儒家以在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这最基本的五伦关系中实现喜怒哀乐之情感的“和”为生命实践之理想境界。所以,把礼乐视为孔子思想之精髓的梁漱溟准确地指出:“礼乐是孔教惟一重要的作法,……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他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9〕
自孔子主张“重建礼乐”开始,在历代儒者们不断因革损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崇尚礼乐教化的思想观念和实践传统。礼乐教化奠定了道德生命的终极秩序、精神方向与实践路径,在道德生命的养成过程中具有一种实践本体论的性质。这一实践,以现实之人的自然情感为教化的对象,以去除情欲后的纯粹道德情感之真实呈现为教化的目标,即以情感的调节、运转与安顿为实践所要解决的根本难题。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儒家的礼乐教化称为“情感的政治”。当然,在儒家这里,礼乐教化并非解决情感的调节、运转与安顿难题的唯一实践方式,但却是最主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徐复观说礼乐之治是“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10〕。那么,以调节、运转和安顿人的情感难题为实践基本问题的礼乐教化,是如何实现这种调节、运转与安顿的?
按照儒家“天地秩序内化为心灵秩序,心灵秩序外显为身体秩序”的观点,在生命之道德秩序的三重维度中,心灵秩序事实上就处于关键的地位。早期中国文化,历经夏之巫觋文化经商之祭祀文化再到周之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11〕,在文化精神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人逐渐从把“神灵的启示”或“天命”视为道德秩序之最高保证的“幻觉”中走出来而实现人文道德理性化的过程。问题是,在这一人文道德理性化的过程中,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取代“神灵的启示”或“天命”的人文理性替代物?就儒家而言,孔子找到的人文理性替代物是“仁”,所以说“仁者爱人”。儒者以为“仁”是在心中实现的,所以“依于仁”其实就是依于心,孟子“仁,人心也”的观点最明确地点明了这一点。尽管孔子的话语体系里还保留“天命”概念,依然有“畏天命”“知天命”的说法,但孔子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真实本然的“心”看作是道德秩序的最高保证,这体现在孔子对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句,通行的句读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笔者以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更能体现儒家把“心”视为人之为人的道德秩序之最高保证的意义。的人生践履之体验反思中。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七十岁比五十岁的生命体悟境界更高,所以,五十岁所知的“天命”并不是孔子最终的追求,通过知“天”、知“性”进而知“心”,孔子最终追求的是从自己的“心”,当然这个“心”指的是真实本然的心,是王夫之所说的能够作为“人情天理合一之原”〔12〕的心。这一真实本然的心有它的真实性情与心灵秩序。概言之,作为秩序之本源,心不仅仅是道德秩序的最高保证,也成为生命实现自我安顿的主要场所,所以孟子把人心比喻为“安宅”,视为使人获得平静与安宁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强调人人具有的真实本然的“心”具有秩序之本源的意义,在探索道德生命的养成问题时,儒家特别聚焦于“心”上,主张养成道德生命的关键是端正人心。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的情感情欲,究其实都是由心而发的。例如,《大学》在解释为什么“修身在正其心”时说:“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很明显的是,这里所说的“忿懥”“恐惧”“好乐”与“忧患”,都是从情感情欲上说的。②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注解说:“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见〔宋〕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9页。为了端正人的这些情感情欲,就必须端正人心。只有端正了的人心,才有资格成为道德秩序的最高保证。③王夫之说:“正心者,过去不忘,未来必豫,当前无丝毫放过。则虽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有主者固不乱也。”见〔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页。因为,对于每一颗当下具体的现实人心来说,既有向善的可能性,亦有流于恶的危险。孟子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曾引用孔子“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孟子·告子上》)的话来解释人心的不确定性,进而强调了养心的必要性。关于现实人心的这种张力,朱熹也曾在《中庸章句序》中从“道心”与“人心”之别的角度进行了解释。④朱熹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见〔宋〕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5页。当然,朱熹所说的“道心”与“人心”,并不是真的指人具有两个心,而是指理解现实之人的现实心的形上与形下两种维度。朱熹正确地意识到,人的现实心确实会面临着陷溺于人欲之私而造成危殆不安的危险,故而需要对现实心进行省察克治;人的现实心虽然也愉悦于天理之公却也会有微妙而难显现的困境,故而需要对现实心进行涵养扩充。
就现实心同时需要省察克治与涵养扩充而言,礼治和乐治都是必要的。当然,在具体的实践方式上,乐治是一种直指人心的教化手段,而礼治则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而将秩序精神内化于人的心灵之中。礼乐教化实践的基本原则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坤·文言》):在人的内在心灵中建立起精神秩序,这是“敬以直内”的乐治;在人的外在行为上建立起伦理秩序,这是“义以方外”的礼治。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许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记·乐记》)
依照“动于内”抑或“动于外”的功能原则之差异,上述引文区分了乐的功能主要是“治心”,而礼的功能主要是“治躬”。概言之,礼治的目的是通过外在的习俗与制度建构一种规范行为的和谐秩序,经由对身体行为的规范将这种规范映射到心灵上,从而实现道德生命的自觉与自为,这种规范性的过程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这意味着礼治主要发挥克治人的自然情欲的功能;乐治的目的是通过内向的感兴与启发养成一种存养心灵的和谐秩序,进而实现道德生命的自发与自由,这样一种直指人心的教化方式是建立在存养扩充人之道德情感的基础上而实现人道之正的。这表明,礼治也好,乐治也罢,都承担着调节、运转与安顿人的情感难题的功能。就礼乐与情理之关系而言,儒家主张“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按照这一思想,乐的精神其实是那些具有持久性、稳固性特征的“情”,这样的“情”应该是指道德情感;礼的精神是不可易的“理”,此处的“理”可以理解为道德原理。那么,乐治事实上是通过感兴发动人的道德情感来调节、运转与安顿人的情感,而礼治则运用道德原理规范人的自然情欲来调节、运转与安顿人的情感。这意味着经过礼乐之治所培育的情感,是一种反思性的情感,亦即理性的情感。这正是本文将儒家的礼乐教化称为“情感的政治”的理由所在。这意味着在道德生命秩序的养成实践中,需要培养一种情理交融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的养成,需要从调节、运转与安顿人的情感开始。礼乐教化,正是这样一种以情感的盈减为实践原则,以“情深而文明”的生命理想为实践旨趣的调节、运转与安顿生命的“情感的政治”。
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儒学的主要目的是教会人们在面对日常生活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在培养指导行为背后的那种思想洞见。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教化,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人文化成的方式而实现人的有教养之发展的人生实践之路,其合理性在于引导人们凭借自身的良知良能而自觉地走上自我完善之路,这是《中庸》“修道之谓教”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深刻教义,也是中国礼乐文化赋予我们用来指导生命实践的最好的思想洞见。新时代,我们可以借鉴传统的礼乐教化实践来养成现代社会的生命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