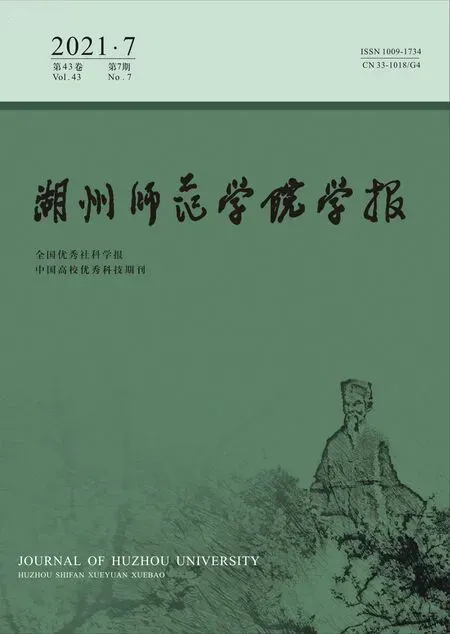略论《吕氏春秋》的伦理观*
张文渊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血缘为社会根基建立起来的,故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这样的社会里,思想家轻视对自然的探求,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1]200。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提倡“少私寡欲”“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用退守的办法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家则以重法、用术、运势来整合君臣、君民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作为一部综合百家之长的治国典籍,《吕氏春秋》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或者说它的伦理观,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学派属性。
一、以本能之性为基础
人性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先贤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先秦诸子争论的焦点。总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善论和性恶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家们的这些观点,在人性论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吕氏春秋》吸收并发挥了“生之谓性”的思想,认为性来自于天,生而即有,且不可改变,所谓“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2]388。“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2]1637在阐释具体内容时,它以情论性,主张性情统一,于此,书中这样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2]86。“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2]275所谓的情欲在这里是指生理机能,即人的各种天生的本能欲望,这种人性也就无所谓善与恶。《吕氏春秋》的伦理观就是基于这种人性理论而建立起来的。
《吕氏春秋》认为,人类之初并没有伦理道德可言,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吕氏春秋》看来,上古时期的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采取群居的方式来应对“禽兽”“狡虫”和“寒暑燥湿”等自然危害: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2]1330。
这种无别、无道、无礼、无便、无备的群居生活虽然抵御了自然界的危害,但他们并不具备文明社会的特征,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分,因此也就不会有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不过是出于本能的需要,“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3]668。为了生存,他们甚至还会“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2]1331。在《吕氏春秋》看来,这种不文明的社会是不能忍受的,也是必须改进的,于是天子、国君等官长也就应运而生了,“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2]1331。“置天子”“置君”的目的是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维护这些关系正常运转的规范、原则即伦理道德也就随之出现了。当人类有了伦理道德以后,人与禽兽也就区分开来:“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2]956。
二、以宗法制为原则
宗法制由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有很多争论,但认为其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发展于商代,成熟于西周的看法基本得到大家的认可。在宗法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何谓嫡长子(宗子)继承制,王国维这样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4]232对于其他公子来说,只能别为一宗,继而被后世奉以为祖。故,“公子不得称先君,因而别为一宗,为宗法之一义;始来在此国者,后世奉以为祖,为宗法之又一义。两义之中,后义实为尤要”[5]89-90。从这两段话可知,第一,嫡长子(宗子)继承制有以血缘身份行使族权的宗统和以政治身份行使行政权的君统之分,二者虽有区别,但联系也极为密切,因为族权和君权往往交织在一起无法明确区分。以殷周的天子为例,他既是宗族社会里最大的族长,又是国家政权中的最高统治者。于是,血缘和政治、政权和族权、君统和宗统交织在一起,他们既是政治上的君臣隶属关系,又是血缘上大宗和小宗的关系[1]36-37。第二,继承制中的嫡长子(宗子)相对于其他众子而言,从表面上看“不公平”“不合理”,但却能很好地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避免众子之间的争斗甚至杀戮,从而维护政治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进而保证社会的安定。
因此,宗法制的确立是出于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从血缘层面来看,是为了解决大宗小宗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各尽其职;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为确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隶属关系不可僭越。这样,宗统维护君统、族权强化王权,家规补充国法,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来调整统治者内部的君臣上下关系,掩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从而永保周天子处于天下“共主”和“大宗”的最高统治地位[6]24。
《吕氏春秋》肯定等级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指出“定分”是保护等级制度运行的重要方式。《吕氏春秋》认为天下、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乱源于“未定分”。关于定分,《吕氏春秋》引用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话:“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2]1120众人追一兔,并非这只兔子能满足所有追兔人的需要,而是因为此兔未定分之故,即此兔不属于任何人,大家都有得到这只兔子的权力与可能。与之相反的是,“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2]1120。大街上兔子多到满地跑,但看到兔子的人却不去抓,这不是说行人不喜欢兔子,而是因为这些兔子已经物有所属,名花有主,即所谓的“定分”。故在《吕氏春秋》看来,定名分、定上下是解决纷争的前提[2]1132,“分已定,人虽鄙不争”[2]1120。如何定分,该书从政治和血缘两个维度进行阐释。从政治维度看,定分就是给各种官职确立等级名分,“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2]1120。在《吕氏春秋》看来,天子、诸侯、大夫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下绝对不能颠倒,否则会引起混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2]1120。从血缘维度看,定分就是要处理好嫡庶之间的关系,明确长幼之间的秩序,“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2]1120。如果破坏这种制度,则会产生疑惑,“疑生争,争生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2]1120有了疑惑就容易产生争斗。因此,“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2]1120-1121。天下国家的安定与宗族家室的团结离不开定分。
《吕氏春秋》这种以宗法制为原则的伦理观,是对宗法制、等级制的肯定,是亲缘与政治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视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性[7]64。当然,如果把这种社会结构作为其伦理思想的出发点,甚至作为伦理思想的标准或者原则,则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以“十际”为内容
人伦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何谓人伦,潘光旦指出,要弄清楚人伦,首先要明白“伦”的含义,于是他用训诂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考证。他认为“伦”有“类别”和“关系”两义,“类别或差等的伦是具体而静的,要靠理智来辨认;关系的伦是抽象而动的,要靠情绪来体会与行为来表示”[8]27。在此基础上,他把人伦分为“静的人伦”和“动的人伦”,静的人伦主要是指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动的人伦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他说:“这动的人伦便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间分别应有的关系。”[9]115-116这种解释既指出了伦理道德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道明了处理这些关系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尚书》应该是早期对人伦关系记载较多的一本典籍。《尚书·舜典》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10]51“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10]75何谓“五典”“五教”,《春秋左传·文公十八年》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11]580。学界也因此把“五典”“五教”看作是“五伦”的源头,除此之外,《尚书·洪范》中还有关于“九德”“五事”“三德”等伦理道德的记载。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三代以来的人伦关系做了总结和发挥。在他的伦理观里面,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其讨论的主要内容。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2]5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26稍晚于孔子的另一思想巨擘墨子,则重点关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人伦关系。就先秦思想家而言,孟子提出了最为系统的五伦观念,他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3]114孟子的五伦思想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孟子的五伦是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1)这里的长幼是指兄弟。与“朋友”,父子一伦是排在五伦的第一位,而朋友一伦放在五伦的最后一位。第二,孟子指出每一伦之间没有必然的尊卑或者隶属关系,即每对人际关系的双方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以君臣关系为例,君有君的权利,君也有君的义务;同理,臣有臣的义务,臣也有臣的权利,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3]171。自此,五伦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正如贺麟所说:“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14]141
《吕氏春秋》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人伦“十际”是区别人与麋鹿虎狼的主要标志。该书这样说:“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2]1514就“十际”的内容而言,它是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2]1514。该书进一步指出,如果人类社会没有处理好“十际”之间的关系,社会就会出现“无安君、无乐亲,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的局面,进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甚至相互残杀的状态,故“十际皆败,乱莫大焉”[2]1514。从这里可以看出,该书把人际关系分为“十际”的观点明显继承了《尚书》尤其是孟子的五伦思想。
其次,《吕氏春秋》提出了保证“十际”关系得以正常运行的原则,“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2]1515。在《吕氏春秋》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十际”关系就不会得到有效的维护,人们也因此无所适从。于是,该书提出以“义”作为“十际”关系遵循的统一原则,“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2]1501。义就是宜,而宜的本意为合适、适宜,引申为适当、应当[15]6。《吕氏春秋》借用曾子之口来阐述圣王在义的原则下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2]737。
不管是“贵德”“贵贵”“贵老”,还是“敬长”“慈幼”,在《吕氏春秋》看来,这都是圣王协调人际关系时所采取的方式与手段,以达到安定天下治理国家的目的,之所以有“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之分,是因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针对不同的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即对合适、恰当即义原则的遵循。从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关于“十际”关系的运作虽然不如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样清楚,但其基本精神却是相通的、一致的。
最后,在人伦“十际”关系中,《吕氏春秋》特别重视其中的六际,即必须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它认为这六际处理好,社会就文明和谐。“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2]1678就这六际人伦关系而言,《吕氏春秋》又认为父子两际才是核心,是其他几际的前提与基础:
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2]514。
在《吕氏春秋》看来,父子两际不同于其他几际,原因在于从情感上来说,父(母)子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产生,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本能的体现。
总之,《吕氏春秋》的人伦“十际”,是在吸收前人思想尤其是孟子“五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与前人不同的是,它特别重视父子关系,并以此扩充到其他几伦,这种做法既符合人情,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四、以“孝”“忠”为根本
“孝”“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古代伦理观里最为重要的概念,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伦理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孝”与“忠”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一般来说,“孝”主要表现为子对父的伦理道德;“忠”则体现在臣对君的伦理道德。
儒家认为,父子关系是生而既有的天然形成的关系,故“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如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2孟子也说事亲是“人伦”之根本,“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13]164。关于孝德的践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有很多的论述,他认为尽孝就是要赡养好父母,但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敬重父母,否则与养动物有什么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2]14如果在赡养父母的过程中与父母发生了矛盾,子女也要做到“无违”“劳而不怨”。总之,子女尽孝就是要对父母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2]13。
《吕氏春秋》继承并发挥了前人的孝德伦理。首先,它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是所有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治国的原则,“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2]736。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这种观点与孔孟有所不同。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是“庶矣”“富之”“教之”[12]134-135,即在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实施教化;孟子也主张治国应该先让“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3]5。而在《吕氏春秋》看来,治理天下的根本不是让人们富足,也不是增加人口,而在于让治下的人们去践行孝德。其次,该书把孝推广到各个领域,它说:“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2]736在《吕氏春秋》看来,孝是所有人都要践行的道德,只是不同身份的人尽孝所起的作用不一样。以最高统治者天子为例,“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2]736。天子尽孝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利于社会秩序稳固,也利于天子的统治。故《吕氏春秋》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2]736最后,该书提出教化是培养孝德伦理最重要的方式。书中这样记载:“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2]738教化的目的是让民众知道尽孝就是赡养父母。在《吕氏春秋》看来,赡养父母是一个“养敬安卒”的过程,在赡养父母过程中要做到善始善终。该书更进一步指出,父母去世以后,子女也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让父母的名声受到玷污,如果能做到这些才能称之为孝,否则不能称之为孝。此外,《吕氏春秋》还讨论了仁、义、礼、信、强等五德与孝德的关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2]738。在《吕氏春秋》看来,孝在众多德目中处于中心地位,仁、礼、义、信、强等道德都是为孝德服务的。
我们也知道,宗法制度下统治者都具有双重身份:从政治层面上看,他们是君主;从血缘层面上看,他们是族(家)长。因此,对族(家)长的孝,就是对君主的忠,于是孝与忠便在这里打通了,即所谓的“移孝作忠”。
“忠”观念虽出现较晚,但含义却比较丰富,而把事君作为忠的主要内涵的思想家则是孔子。《论语》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知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2]30战国时期的荀子认为“忠”是作为人臣的核心道德,并在此基础上把忠分为“大忠”“次忠”和“下忠”。他说:“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16]300他主张臣要大忠,反对臣的次忠和下忠。韩非子认为忠有大小之分,作为臣子应该行大忠而拒小忠,“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17]59。
《吕氏春秋》的“忠”观念明显受到孔子、荀子和韩非子思想的影响。它首先强调“忠”的指向。“忠”是“至忠”“大忠”,而不是“小忠”。其次阐释彼此间的关系与内涵。关于“小忠”与“大忠”的关系,它说“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2]872。在《吕氏春秋》看来,小事上献媚是小忠,而它主张行大忠。何谓“大忠”,该书这样写道,“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2]594。“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2]1089“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2]1592最后突出“大忠”的重要。在《吕氏春秋》看来,“大忠”就是做臣子的为了国君,尤其是天下、百姓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应该牺牲自己的名利甚至是生命,它同时也指出,“大忠”并不是愚忠,“大忠”以义为指导,以安定天下百姓为目的。
由上可知,把“孝”“忠”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正好迎合了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特征,所谓“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2]198《吕氏春秋》强调“孝”与“忠”相通,其目的就是主张以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交互为用,治理天下[18]47。
倡导以德治国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会同先秦诸子,整合新的治国理念,在总结吸收先秦伦理与德治思想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了“孝”与“忠”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这种较为合理且实用的治国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以生而即有的本能欲望作为其伦理观的人性论基础,这让人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容易接受,进而便于推广。其次,因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故“孝”在《吕氏春秋》这里是所有道德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德性,由此扩充与推广,打通了“孝”与“忠”的界线。总之,《吕氏春秋》基于宗法制的伦理观,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规范。正如张光直所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