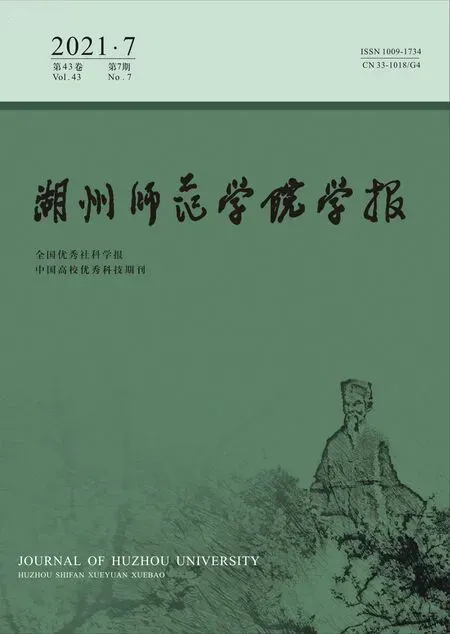“大上海”与“小南浔”:近代南浔绅商结社与区域互动*
郑卫荣
(温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近代社会,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商人开始由分散的个体走向联合的组织。最初的商人组织通常是与商人的自然组织——宗族亲缘组织相重合,再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了商人的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相对而言,由亲缘组织的宗族向地缘组织的会馆,再向业缘组织的行会、公所演变,是商人组织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72-89。虽然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依次取代关系,而是存在着时间上的交叉并存和组织上的相互重叠,但仍然整体性、趋势性地呈现出由旧趋新、以新摄旧的近代化特征。商人合群结社既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又对促进家乡本土和旅居地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以往研究的视角较多集中于旅居地社会,侧重从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的视角来关注商人社团组织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而较少探讨商人社团组织与本土社会的互动问题。(1)民国时期商人社团组织的重要成果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尤育号:《民国时期旅外同乡组织与家乡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等。少数研究探讨了商人社团组织与本土社会的互动问题,例如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本文将以晚清民国时期在江南地区颇具影响的南浔绅商群体为研究视角,对这一时期绅商的社团组织运作及其与家乡本土之间的双向互动作一考察。
一、近代南浔绅商的合群结社
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开启了江南地区生丝贸易国际化、近代化的进程。在当时苏嘉湖区域极为繁盛的“浔沪丝路”中,南浔绅商依托地缘、业缘、亲缘相交织的社会网络乘势而起,形成了一个以“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为代表的显著的绅商群体[2]124。自19世纪60年代起,寓居“小南浔”和旅居“大上海”的南浔绅商,相继在镇域组建南浔丝业公所(附设善举公所)、南浔商会、地方维持会等本土团体,在旅居地上海先后参与创建上海丝业会馆、圣寿庵、旅沪同乡会、湖州会馆、湖社、南浔公会等客地组织(见表1)。

表1 近代南浔绅商在沪、浔两地的合群结社
表1以时间为序,概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南浔绅商在沪、浔两地合群结社的情况。
从发展逻辑来看,无论是本土社团的创立还是客地组织的发展都根源于绅商阶层厚实的经济动能。作为上海开埠后江南地区湖丝贸易的中心地,“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六属丝行几皆为南浔人所包办,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浔为中心”[3]122。这一贸易格局使得南浔绅商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稳执沪上丝业贸易之牛耳。凭借这一行业地位,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南浔绅商顾福昌、陈煦元、刘镛、顾福昌、周昌炽等人就已跻身上海丝茶捐总局、上海丝业会馆等官方、半官方丝业征税及管理机构的董事之列,这一影响力也反映在后续成立的圣寿庵(1861)、浙湖绉业公所(1887)、无锡茧业公所(1900)、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2)、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1909)等行业组织的董事构成中。也正是倚靠丝业贸易领域积聚的经济实力,南浔绅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地方社会重建中展现出积极的主观意愿和强大的财力后盾。他们组织成立了战后首个地方性业缘组织——南浔丝业公所及其附设善举公所,以丝经附捐的筹资模式推进战后各项善举机构事务,扮演了社会重建的组织者、推动者的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社会重建成为了绅商阶层用以应对战后新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结构分化的社会策略,将自身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至参与地方事务、分享地方权力、树立地方权威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这一行动逻辑一直延伸至20世纪上半叶,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地方自治中得到了进一步地强化和体现。
从阶段特征来看,总的来说,在清末民初日渐趋新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地缘性的同乡组织还是业缘性的行业社团,它们在组织系统、价值取向、运行方式、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虽然联系到某一个社团组织在特定时期的动态发展时,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以20世纪20年代为界限进行前后比较,可以发现:在此之前,南浔绅商通常以湖州商帮或湖州同乡的身份参与旅沪浙江或湖州“大同乡”组织的活动,并在这些组织内部及其与客地、本土的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此之后,在旅沪“大同乡”组织持续壮大的同时,陆续出现了以南浔商会、南浔公会、南浔旅沪同乡会为代表的合镇性质的“小同乡”组织,这些组织均由南浔绅商独立创建和运营,凸显了南浔绅商与客地、本土联系的需求关注,也形成了与“大同乡”组织独立共存、网络交织而又功能互补的态势。这种变化既是社团组织在功能定位、地域层级、群体细分、需求关注等方面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近代南浔绅商群体规模扩张和心理整合的必然结果。相较而言,在诸多社团组织中,以湖社、南浔公会为代表的旅沪新式同乡组织所展现的活力,是同一时期南浔绅商参与或创立的其他社团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也从代表性个案的视角为我们解读蕴含其中的区域社会互动提供了典型例证。
二、“大上海”与“小南浔”的互动网络
由旅沪绅商及其合群结社建构起来的组织网络,在为旅外同乡提供组织平台、发展资源的同时,也搭建起了联结家乡(本土)和旅居地(客地)的社会支持系统。在这个社会支持系统中,以湖社、南浔公会为代表的同乡组织都处于客地上海,但又和本土社会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如湖社《章程》所表述的旨趣以及南浔公会《章程》所定义的宗旨。作为旅沪社团组织,这些同乡组织是如何保持客地与本土之间的互动的?换言之,以同乡组织为纽带的上海与南浔之间的互动网络是怎样运作的?在城与在镇的绅商是如何发挥各自作用的?下文拟通过有关湖社社务、南浔公会会务的具体分析来解答这些问题。
(一)联结旅外同乡的人脉关系网络
1924年成立的湖社是张静江、陈蔼士、杨谱笙等人在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会馆的基础上倡立的新式同乡会。(2)1920年代初期,旅沪湖州绅商群体中保守派、改革派关于改造和利用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会馆的态度分歧,成为了改革派另组湖社的重要契机。关于两派意见分歧的报道参见《湖州同乡会章起草续志》,《申报》1924年2月25日,第15版;《湖州同乡昨日开会》,《申报》1924年5月12日,第15版。湖社在实行理事制、委员制、三权分立制的不同时期,由社员大会选举2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构成了湖社的核心领导层。自1924至1937年间,南浔绅商张静江、张君谋、周颂西、周佩箴、周君常、张廷灏、褚民谊等人先后当选为委员,其间虽有个别成员进退流转,但大致维持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包括上述委员在内,湖社中已知的南浔籍社员还有王均卿、沈伯经、沈调民、沈石麒、周心远等人。(3)《历届委员表》,《湖州月刊》(湖社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年第1卷,第37-39页。这些社员大多出身绅商家族,或身为国民政府党政官员,或致力工商文教事业,在家乡和客地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很高的社会声望,为湖社谋求同乡公益事业提供了优厚的社会资源。这里以湖州旅沪中小学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作为湖社旅沪同乡会组织的唯一教育机关,湖州旅沪中小学始办于1907年。是年,旅沪绅商刘锦藻、庞青城、汤沧济等人为解决同乡子弟异地求学问题而醵资创办湖州旅沪公学,由南浔绅商刘锦藻出任首任校长。从公学“校史”纪录来看,名列创始人的有陈英士、汤济沧、韦文白、史赓身、杨谱笙、严浚宣、凌铭之、刘锦藻等人[4];在开办当年的各方捐款中,团体捐款者有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旅沪学会等组织;个人捐款者有沈协轩、王亦梅、沈谱琴、黄介绶、韦文百、汤济沧、杨信之、吴登云、刘承干、谢子楠、凌铭之、朱五楼、周少莱、史庚生、杨诚之、沈联芳、杨彬甫等人,汇集了当时湖州旅沪绅商的主要代表人物。(4)《历年捐款题名》,《湖社第十二届社员大会特刊·附湖州旅沪中小学卅周纪念刊》,1936年,第260页。他们或是从商、或是从政,或是城居、或是镇居,关心桑梓、热心公益的共同特点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开启了公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在开办之初,公学“订定两等各三年学制”,学生仅有20余人。在经费筹募上,“因半属义务教育之故,而经济之筹所取之诸乡父老,益诛求而无厌”。校董中,除首任校长刘锦藻“任巨款”“常年捐”以外,以庞青城、沈谱琴、沈协轩等人“捐助为巨,亦且关心于教育者为切”。1908年,刘锦藻去职,凌铭之(名祖寿)继任校长一职,克服诸重困难,“历办五年,迁地者三”,公学男女两校学生数在1912年增至500余人[5]40。至1925年,公学添办初级中学,发展至北浙江路、北长康里、闸北湖州会馆三个校区42所教室,2 200余名学生。(5)《湖州旅沪公学添办中学》,《申报》1925年7月20日,第22版;《湖州旅沪公学之发达》,《申报》1926年7月30日,第19版。1926年,在公学办校二十周年之际,湖社正式接办公学校务,公学随之易名为湖州旅沪中小学(简称“湖校”)。在湖社领导下,湖校改行私立学校校董会制度,推选“同乡之能筹划经济或热心教育赞助本校者”36人为校董,由校董会选聘校长一人总理校务,并分设教务、训育、事务三部主任。(6)《湖州旅沪公学校董会简章》,《湖州月刊》1928年第3卷第4期,第67页。在1928年的首届校董会中,南浔籍校董有周佩箴、周庆云、张君谋、张静江、褚民谊、刘承干、庞青城、庞元济等8人;(7)《湖州旅沪公学概况》,《湖州月刊》(中华国货展览会特刊),1928年,第122-124页。1931年第三届校董会中,南浔籍校董有周佩箴、周庆云、张君谋、张静江、褚民谊、庞青城等6人。(8)《湖州旅沪中小学概况》,《湖州月刊》(湖社第八届社员大会特刊),1932年,第23页。从南浔籍董事的构成来看,在以绅商为主体构成的校董会中,同时期新旧同乡组织中既存的派系歧见,已为同乡教育事业的最大共识所取代,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结成了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联盟。(9)在“湖校”之外,由于政治倾向和文化观念之差异,张静江、张君谋、周颂西等改革派加入湖社,周庆云、庞元济、刘承干等保守派继续留在湖州旅沪同乡会,周佩箴等人则两面参与。与此同时,从联系南浔地方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些绅商校董们几乎都是一身多任地参与了同时期南浔镇诸多中小学教育建设,尤其是对于地方私立学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6]144-154。在校董会的治理下,湖校的学生培养质量有了长足进步,学校声誉也广受赞誉,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福建等10省区生源不断汇入湖校,学生数在1927年增至3 000余人,成为当时“沪上私立学校中之翘楚”。(10)参见《湖州旅沪公学学生籍贯区域图》,《湖州月刊》(中华国货展览会特刊),1928年,第108-109页;《湖州旅沪中小学新易校长》,《申报》1935年2月4日,第4版;《湖州旅沪公学实行新学制》,《申报》1923年2月28日,第18版。
从湖州旅沪中小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湖社还是之前的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旅沪绅商从旅外同乡子弟教育的共性需求出发,以浓厚的同乡观念、广泛的人脉关系创设、经营旅沪中小学。这种同乡观念、人脉关系虽然根植于传统乡情的文化土壤,但在近代社会发展中也因势利导地促进了旅外同乡子弟文化素质以及同乡组织社会竞争力的提高。由于中小学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地位,它同时也成为了客地和本土绅商共同的关注重点,使旅外同乡团体的内部凝聚及其与家乡、旅居地之间关联变得更为紧密,而同乡教育所取得可观效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旅外同乡网络的内聚力和扩张力。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湖校声誉的提升和生源地的拓展,包括南浔绅商在内的湖州绅商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同乡绅董的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二)联结城乡、官民的联动机制
湖社事务尤其是社外事务侧重于关注湖属六县地方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问题。(11)有关湖社(1924—1937年)的主要社会活动,参见沈阶升:《湖社十年来社务一瞥》,《湖州月刊》(湖社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年第1卷,第1-3页;姜定宇:《湖社十年大事记(1924-1934)》,《湖州月刊》(湖社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年第1卷,第33-37页。湖社旅外同乡在处理事务时尤为注重对官民、城乡关系网络的利用(见表2)。

表2 湖社社务及其处理路线图(1928—1937年)
表2以部分社务为例,梳理了湖社在不同社务中与官民、城乡联动的路线图。为了便于直观理解,路线图选择以具体社务为中心,以湖社为始发部门(出发点),单向度地勾勒出湖社与主要关系部门或当事人之间的联动方式。事实上,这种简单化的联动方式在现实场景中很少存在,湖社的绝大多数社务都会同时涉及多个关系部门或当事人,而且还有诸多信息来回、人员往还的反复过程,各项社务的处理也并非是理想化的单线推进,而是多方力量、几条路线同时推进,最终共同促成某种具体的结果。下文将以“1934—1935年湖属六县亢旱赈济”为例,对湖社联结官民、城乡的联动机制作进一步分析。
1934年春夏之交,浙省亢旱酷烈,庄稼枯死殆尽,灾情遍及全省72县,灾民几达百万,其中,浙省灾区尤以湖属六县为严重,湖属六县中又以吴兴县灾民数量为最多。(12)《湖属旱灾写真》,《申报》1934年10月20日,第11版;《湖属灾况一览表》,《湖州月刊》(救灾专号)1934年第6卷第4-5期,第35页。由自然因素引发的亢旱与1930年代中期湖州蚕桑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相互交织,同时还滋生出了农民之间因戽水而引发的抢水冲突,农民与屠夫之间因祈雨或禁屠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民、商人与政府之间因请愿、抢米而激化的骚乱和罢市,进一步使得地方动乱不断升级。(13)《湖社救灾款事项案卷》,上海档案馆藏(Q165-4-22)。受灾及赈灾期间,湖属六县政府、党部、救济会、商会和各镇、区官员先后向湖社报灾请赈函电有22件。(14)《湖属救灾委员会工作报告》,《湖社救济灾款事项案卷》,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4-22)。从这些函电中可见以湖社为枢纽的湖属六县与上海客地之间的信息通达。湖社根据这些函请所述,在第一时间准确地了解到灾区实情,在此基础上,通过常委会讨论和决议,拟具复函,并根据各县来函请求或复函、或转函、或呈报、或请赈、或劝募,成为灾情汇总与分类处理、救灾处置与善后联络的中枢。举其大端者有:
成立专门机构。1934年9月,湖社成立湖社救灾委员会,推选王一亭为主任,陈勤士、沈联芳、钱新之、沈田莘为副主任,陈果夫、章荣初、沈阶升、潘祥生、杨谱笙、庞元济等46人为常务委员,分任总务、捐务、财务、赈务等事项。救灾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关于救济湖属灾荒之计划、建议、筹赈和调查及协助。(15)《湖社救灾委员会简章》,《湖州月刊》(救灾专号)1934年第6卷第4-5期,第83-84页。在救灾委员会之下,湖社还指导湖属各县设立旱灾救济委员会,专办救济事务,形成了对上联系浙省政府暨民政厅、浙省振务会、全浙救灾会以及中央义赈会,对下指导各县旱灾救济委员会,横向联合其他各类专门办事机构(如吴兴县平籴委员会)的立体式救灾组织体系[7]63。
吁请政府救助。湖属六县罹灾后,省政府暨民政厅、浙省振务会勘查各县受灾程度,将吴兴、长兴、德清三县列为乙等灾区,与三县受灾事实不符。湖社转呈三县县长来函,“由本会呈请省政府暨民政厅,及分函浙省振务会与全省救灾会,请将吴、长、德三县改列甲等灾区”,“又分函该三县县长,请迅将七月以后各该县灾荒严重情形据实补报省府,俾资考核”。(16)《第四次常务委员会》,《湖社救灾委员会议案、救济款案卷、救济款会议案卷》,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4-15)。通过系列函电往来争取,浙省政府暨民政厅最终批准三县改列为甲等灾区,三县才得以依据《修正刊报灾情条例》将征缓田亩造册呈报民、财两厅,派委复勘,缓催旧欠。(17)《函请吴长德三县以灾情据实报省》,《救济灾款案卷》,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4-17);《湖社第十一届社员大会报告特刊》,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1-61-13)。
募集急赈物资。湖社在呈请各级政府、浙省振务会拨款放赈的同时,还通过赶印募捐手册、举办演剧筹赈大会,在上海和外埠多地劝募粮食、衣物和捐款。(18)《湖属救灾委员会募捐启,湖属救灾委员会募捐册》,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5-132)。其大宗物资有1934年底急赈湖州各县面粉2 840包、寒衣4捆,采办并转赈麦粉5 000包;同时将募集的9 200元灾款分配至各县。(19)《第五次常务委员会,湖社湖属救灾委员会议案、救济款案卷、救济款会议案卷》,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4-15、Q165-4-17、Q165-4-22)。由于募款不足敷用,湖社提出,各县区要发挥地方自主性,“缩小区域,分头办理”,并强调“筹款之法,亦应城镇划分,自行劝募,庶办事人员均有切近之关系,不致敷衍塞责”,悉心筹划和指导着各县城镇乡村的赈灾事务。(20)张青士:《关于救灾意见》,《湖州月刊》1935年第6卷第4-05(专号)。
组织以工代赈。在发放急赈物资之外,湖社还联合“各县已有社会救济事业协会、水利工务所等机构分工合作”,“以浚河、筑路、修塘为主,务使四乡灾民均能就地工作,俾度温饱”。(21)《湖社主办湖属六邑工赈实施座谈会会议记录》,湖社湖属六邑工赈实施座谈会,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1-104)湖社制订以工代赈方案,组织“本地被灾农家之壮丁”参加工赈,“工资以土方计算,每一土方给工资大洋四角,每人以两日挑一土方为度”;工赈补助“分三期给付,开工时付三分之一,工程过半时付三分之一,工竣时由本会派员验收,将补助款全数付讫”。(22)《吴兴旱灾救灾委员会工赈办法》,《湖社救济灾款事项案卷》,上海市档案馆藏(Q165-4-22)。根据该工赈计划,湖属六县工赈总计36万余工,工赈补助款额达7万余元[7]55。
条陈防灾计划。鉴于湖属六县甲戌亢旱因“比年河道淤塞、蓄泄无由导致水旱交臻”,湖社为疏浚苕溪及湖属河道淤塞以利蓄泄,特函呈请浙省政府暨民政厅,条陈“防灾计划”四项,具体措施包括:东西苕溪上游择要筑坝蓄流,下游乘本年冬季征工疏浚;湖属六县政府将所属圩田多辟支渠小港;改造扩大公路经过之桥梁闸门;田赋附加税中治虫费一项积存之款移购戽水机,由各县分府分发各区领用。(23)《湖社条陈防灾计划》,《申报》1934年8月15日,第12版;《呈请浙江省政府疏浚苕溪暨扩大公路桥梁口门以利蓄泄》,《湖州月刊》(救灾专号)1934年第6卷第4-5期,第76-77页。“防灾计划”着眼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期达成标本兼治、防灾于未然的功效。
从上述五端可见,湖社在甲戌亢旱救灾中扮演了联络沟通各级政府机构、各界社团组织、各方救灾力量,指导建议湖属各县具体救灾工作的关键性角色,构成了湖属赈灾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合纵连横的中介和枢纽。在赈灾的具体策略中,以湖社及其附设救灾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绅商委员们心系灾区、情系灾黎,通过函电、吁请、筹赈、条陈等方式带动城乡、官民等关系的联动,既有效促进了荒政救灾体制中国家与社会分工协作的良性运转,也切实为湖属六县灾区争取到了有利的政策及物资援助。湖社在赈灾中采用的短期急赈募捐、中期以工代赈、长期防灾计划相组合的方式,注重救灾、生产和发展相结合,对维系灾区社会安定、城乡关系平衡与官民关系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联结客地与本土的互动机制
成立于1924年江浙战争初期的旅沪南浔公会,是一个横跨沪浔两地的地方自保机构。南浔公会“以犒师、筹款、御匪、集团为入手办法”,“以沪会总其枢纽”,以本土的南浔商会和“地方维持会”为策应机构,形成沪浔两地遥相呼应,联合处置战时紧急事件的互动机制[8]43。这一互动机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动荡岁月中,有效地凝聚了两地绅商力量,保全了地方安宁,尤其是在齐卢战争、孙传芳入浙等兵乱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24年秋,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抢夺沪松地盘和鸦片税收入而爆发江浙战争。9月,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浙东战事失利,下令驻扎于湖属长兴县的陈乐山一部撤退赴苏。陈军分批过境湖州,动辄向地方勒索军饷,若不遂愿则挑动部下祸乱地方。湖城以东的南浔,位于江浙两省接壤处,为各军进退之孔道,是年农历八月至九月,过境军队“相望于道”,“所有浙军、皖军、苏军经过镇上必欲借款,多则数万,少亦数千,络绎而来,闻南浔为浙西富镇,故有许多并非必欲经过,特绕远道过此为要钱地步”[9]第八册,2。为应对过境军队骚扰,谋划地方自保之策,南浔商会先是集议“急办商团,策武装卫护”,后因无处购办枪械而作罢[9]第七册,473-474;继而组织成立“地方维持会”,“设军事临时招待所于东、西两栅,招待军队,供应食宿”,“凡有往来兵士,务令安然出境,不致扰累我镇居民”。适值需款孔亟而金融阻滞的战争时期,商会一方面邀集四方捐款,另一方面迅速召集旅沪绅商成立旅沪南浔公会,订立《章程》六章二十九条,利用旅沪绅商的关系网络策应“地方维持会”的运转[10]494-498。
时任商会会长的庞赞臣记录了是年秋季(农历八月初四至九月初四)军队频频过境的紧张情形,以及商会五次应对军队索饷的沉着冷静,曾不无感慨地写道:“综计吾镇自有军队过往以来,均赖襄助招待,诸君踊跃将事,妥为应付,得免偾事,惟客军纷集,此去彼来,办理供应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物力既竭,心力亦疲,所幸秩序未至紊乱,地方得保安全”[10]757-758。相较于庞氏所述的概略,刘承干在《求恕斋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八月末浔沪两地绅商联合应对陈军索借军饷事件的始末:八月廿二日,索借军饷公函已由南浔商会电传至上海南浔公会。是日,邱寅叔、张墨耕至刘承干处,“出示浙江第四师陈耀珊(字乐山)师长派该师参议葛祖、赵庆华、赵铸三人率军队至浔欲向镇人借洋五十万元来电,请示办法。电系商会会长庞赞臣及庄骥千二人出名”。“前电正在传示各家,第二次催电又至。”是日晚,旅沪绅商庞元济、邢穗轩、周庆云、邱冰壶、邱寅叔、邱竹筠、张石铭、张澹如、张墨耕、邢复三、邢鼎丞、邱仲虎、梅仲泩、梅仲涤、刘锦藻、刘承干十余人召开绅商会议。由周庆云拟电复南浔商会庞赞臣、庄骥千,“告以银根竭蹙万状,勉筹五万元作为犒师费,镇上收括不足则由沪上划还之,下写‘旅沪浔人公复’”,“再由湘舲(即周庆云)主稿写一缘起,请各人落笔,以七万元作底,先以五万元应之,前途一定不肯,如欲再添,则以二万元为后盾”,“再由(张)墨耕写一信与(庞)赞臣,告以留出二万元为伸缩”。经各家凑款,最终筹集四万四千五百元[9]第七册,495-496,502。在这笔巨额筹款的背后,旅居客地与居留本土之绅商“同人眷怀桑梓,心窃忧焉”,即便是在“所筹之数,概作垫款,事定再议摊派”的情况下,仍以“治安所关,各宜慷慨”[10]758,周庆云、庞赞臣等主事者更是“电讯往还无虚日”,“焦心劳累谋善后”,足见诸绅商对故乡之地的深情厚谊[8]43。故乡情义固然是客地上海与本土南浔之间互动策应的牢固纽带,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纽带背后的制度层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正是《旅沪南浔公会章程》的系列规定,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了客地的旅沪南浔公会与本土的地方维持会、商会之间分工合作的科学与周密,才从根本上保障了旅沪南浔公会对地方维持会、商会的信任以及后者不负重托的信义。借助上述联结客地与本土的互动机制,南浔公会在江浙战争期间先后筹集军事招待费银约六万元,多次使得危如叠卵的地方局势归复安稳[10]758。地方各界感于祐护之德行,特为商会庞赞臣、旅沪诸乡老树碑立颂。
江浙战事敉平后,地方维持会及其下设的军事临时招待所虽然即行停止,但是旅沪南浔公会与南浔商会之间相互策应的临时动员、地方自保机制则一直延续。1926年冬至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入浙,军阀孙传芳指挥主力部队南返浙江,“联军纷调过浔”,旅沪南浔公会随即复办地方维持会,再次与南浔商会联合策应犒师、资遣等军事招待事宜,前后“共费六万六千余元,分三股派认,殷户二股,业户一股”,迭次化解了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24)刘锦藻:《自编年谱》,第56页,南浔图书馆藏。
三、结论
综上,我们以时间为序概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南浔绅商在“小南浔”社会和“大上海”舞台上合群结社的发展逻辑、阶段特征。通过对湖社、南浔公会的具体社务、会务的考察,分析了以绅商为纽带的新式同乡组织在“大上海”与“小南浔”区域互动中的功能及其效果。总而言之,依托近代同乡组织更为科学民主的组织架构、周密的制度设计以及充任同乡组织绅董、会员的绅商们所具有传统价值观、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和故乡情义,南浔旅沪同乡组织得以在客地扎根、生长,并借助联结旅外同乡的人脉关系网络、联结城乡及官民的联动机制、联结客地与本土的互动机制,在旅外同乡内部以及旅外同乡与客地、本土之间搭建起了多元的联通渠道和互动网络,使得遭受经济萧条、战祸侵害的故乡市镇与富庶稳定的上海都市之间形成了持续不断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以绅商为纽带的同乡组织实际上充当了平衡乡村世界和都市中国的桥梁[11]162。对于“小南浔”来说,绅商既是明清以来传统社会地方绅权的历史延续,又是民国以来日益新兴的城乡自治组织的主导力量。正是经由这一特殊阶层及其组建的社团组织,地方社会才得以构建起连接官府与民众、沟通城市与乡村、联系本土与客地的社会治理网络,形成了“官—民”“城—乡”“内—外”良性循环的互动网络[12]36-37。也正是由于这一互动网络,才使得市镇社会阶层内聚,地方机构运行稳定,社区族群保持着较好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绅权、普通民众在地方治理中相互认可、互相协调,进而使地方社会由传统时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破坏性冲击最小化,并与那些“生态不稳定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25)杜赞奇、李怀印、王先明等研究显示:清末民初地方实施自治以后,在诸如华北平原的冀-鲁西北、晋西北、湖南等地区,由于国家政权渗透基层社会、汲取地方资源力度的日益增强,削弱了地方社会传统的“保护型”领导,进而导致地方社群的瓦解和一批“掠夺型”劣绅、村霸的暴政。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942年的华北农村》,王富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年;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当然,文中引证的数例,无论是湖州旅沪中小学、湖社救济湖属甲戌亢旱等社务,还是齐卢战争时旅沪南浔公会与地方维持会的互动策应,只不过是从短时段的历史事件的视角对两地之间的互动网络作出的几个注解,而在时间稍长的南浔商会(1921—1949)、湖社(1924—1949)、南浔公会(1924—1949)存续期间,以及中长时段的近代城乡社会生活变迁中,以绅商为纽带的同乡精英团体控制乡村社会、主导城乡和官民互动的乡村社会控制网络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实为这一客观存在的网络的折射或呈现。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区域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互动区域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认知的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13]17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探讨的区域互动较为关注“大上海”对于“小南浔”的作用,而关于这种区域互动对于“大上海”的影响,虽为题中应有之义,但需另文专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