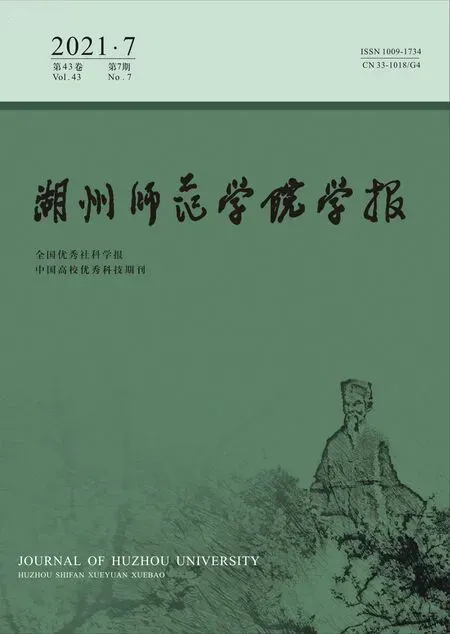论《尚书》文体的类型及其生成*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汉书·艺文志》指出《尚书》与记言传统有关,是在左史记言之基础上生成的,于是《尚书》通常被视为记言文献。对此,人们似乎很少有异议。然而,当进一步考察《尚书》文体类型时,争议就出现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尚书》文体类型到底如何划分,是“六体”“十体”还是其他类型。应该看到,《尚书》文体类型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文体的划分,其实还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尚书》文体生成及性质方面的认知。因此,厘清这个问题,对于《尚书》的认知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
就相关文献来看,最早对《尚书》文体进行划分的是传为孔安国的《尚书序》,其中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的说法。[1]10《尚书序》对《尚书》文体进行明确的划分,提出“六体”的观点,可惜它未能进一步明确“六体”所属之篇目。此后陆德明分析《尚书》百篇与“六体”之间的关系:“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十一篇亡。谟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摄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2]1377他不仅指出“六体”在《尚书》百篇中各自拥有的篇数,还从“正”“摄”的层面对“六体”各自篇数进行再次划分。不过,尽管陆氏明确“六体”的篇数,但同时也留下两个问题:一是何谓“正”“摄”;二是“六体”各自到底拥有哪些篇目。对于这些问题,宋末元初的学者熊朋来给出了答案:
典、谟、训、诰、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与摄之分。正者,有其义而正其名;摄者,无其名而附其义。正三十四,摄六十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尧典》、《舜典》;摄者十三:《禹贡》、《洪范》、《汩作》、《九共》九篇、《槁饫》。谟三篇,正者二:《大禹谟》、《皋陶谟》;摄者一:《益稷》。训十六篇,正者二:《伊训》、《高宗之训》;摄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周官》、《吕刑》、《典宝》、《明居》、《徂后》、《沃丁》。诰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摄者三十:《盘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将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秦誓》;摄者二:《胤征》、《汤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贿肃慎之命》;摄者六:《君陈》、《君牙》、《归禾》、《嘉禾》、《成王政》、《亳姑》。[2]1379
所谓“正”“摄”,熊朋来主要是从《尚书》篇名中是否蕴含“六体”之称谓来加以辨别的,有则为“正”,否则为“摄”。细论之,熊朋来对《尚书》百篇“六体”篇目的划分,实际上使用了两个标准:一是依据篇名之字,即“因名立体”;二是篇章意义的把握,亦即“因事立体”。就最终效果而言,依据篇名之字划分文体归属,这样做自然没有什么问题。麻烦的是第二个标准,尽管篇章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但对其把握则因人而异,于是难免会在篇目的具体归属上引起混乱。比如,同样坚持“六体”,有学者将《周官》《吕刑》视为诰体,[3]8-11而熊氏则视为训体。这种争议,其实只要把握“六体”各自的生成路径,就不难澄清。整体言之,熊朋来澄清了《尚书》百篇与“六体”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熊朋来之前,孔颖达《疏》业已将《尚书》文体与篇目联系起来了。不过,孔《疏》对“六体”表示异议,而是提出“十体”之说:
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录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戒王,亦训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训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1]19-20
孔《疏》增加贡、歌、征、范四体,将“六体”扩充为“十体”。对于新增的“四体”,孔《疏》指出《禹贡》为贡体,《五子之歌》为歌体,《胤征》属于征体,《洪范》属于范体。不难发现,孔《疏》固然新增“四体”,然而每体只对应《尚书》一篇。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一些学者的非议,比如林之奇说:“书有五十八篇,其体有六: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此六者,错综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会而不可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于篇名之间,其《尧典》《舜典》则谓之典,《大禹谟》《皋陶谟》则谓之谟,至于训、诰、誓、命,其说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也,故又增而为十:曰贡,曰征,曰歌,曰范。虽增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于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增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从也。《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学者知《禹贡》为典之体,则谟、训、誓、诰、命见于他篇,皆可触类而长。”[4]林之奇批评孔《疏》以篇名定《尚书》文体之行为,特别是“以一篇为一体”的做法。在他看来,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使“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不过,林之奇尽管否定孔《疏》,但同时又认可“六体”的价值,“《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此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4]应该说,林之奇对孔《疏》的批评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又表明林之奇对“十体”说缺乏全面的理解。林之奇指出孔《疏》“因名立体”,这没有错,“十体”说确实缘于“因名立体”,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尽管是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孔《疏》在提出“十体”说时还曾有一个说明:“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禹贡》即全非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以此禹之身事于禅后,无入《夏书》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1]19孔《疏》提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尧典》《舜典》以叙事为主,很少记言;二是《禹贡》并非王言。由此表明,孔《疏》在提出“十体”时其实暗含这些关键点,特别是王言与非王言之别。刘知几在讨论《尚书》时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5]1刘知几基本上将《尚书》视为“王言”,并且也发现《尚书》部分篇目游离于“王言”之外,其思路与孔《疏》有近似之处。有学者分析说:“孔颖达是因为《禹贡》《五子之歌》《胤征》《洪范》四篇未涉及‘君言’‘上言’才将它们独立出来。这说明在孔颖达心目中,《尚书》是记载‘王言’的书,而这四篇并非‘王言’,只能另体归之。从这个角度看,孔颖达其实是将‘十体’分为‘王言’与‘非王言’两部分,‘王言’中有‘六体’,‘非王言’中有‘四体’。”[6]71-83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观察。这就再次表明,无论是“六体”还是“十体”,单纯就体例论之,均体现“因名立体”的路数;然而,倘若将它们与《尚书》篇目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在建构“六体”“十体”的背后,其实还预设其它的前提。也就是说,它们并非依照单一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从“六体”到“十体”,并非只是单纯文体数目的增加,同时也折射出《尚书》文体类型划分标准的多元。这就表明,倘若秉持的分类标准不同,那么,对《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自然也就会出现差异。对此,潘莉、叶修成、吴志刚等学者均有讨论。(1)潘莉《〈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叶修成《〈尚书〉文体研究综述》(《嘉应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吴志刚《〈尚书〉誓体研究述论》(《天中学刊》,2019年第4期)。潘莉分析说,有关《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大体呈现三种路向:第一类是以篇名为依据,影响较大的是“六体说”和“十体说”,还有“三体说”和“四体说”;第二类是根据记叙方式将《尚书》文体划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蒋伯潜将今文《尚书》分为记事之文和记言之文,前者包括《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其余均为记言之文;第三类是将篇章名称和记叙方式相结合,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誓辞、文诰书札和记事的片段三类,陈梦家则分为诰命、誓祷、叙事三类。[7]3叶修成认为《尚书》文体分类的讨论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尚书》篇名进行划分,最典型的是“六体说”和“十体说”;第二类是依据记录的语言形式,将《尚书》篇章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如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三类是根据各篇所包含的德性,如伏胜《尚书大传》“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第四类是根据多重标准,如郑振铎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誓辞、文诰书札、记事的断片三类,陈梦家则分诰命、誓祷、叙事三类,李零分为典谟类(掌故类)、训诰誓命类(政令类)、刑法类(刑法类)。[8]77-82吴志刚也将历来有关《尚书》文体分类的讨论划分三类:一是以记叙方式作为分类的标准,将《尚书》的文体分为“记言”与“记事”;二是以功能与形式组合而成的多重标准作为分类依据,如郑振铎、陈梦家;三是以篇章名称与体例之关系为标准,于雪棠认为《尚书》文体源于篇章命名方式,而篇章命名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9]这些讨论在一些细节方面虽然有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呈现比较一致的认识。通过他们的分析,大致可以明了长期以来人们有关《尚书》文体分类讨论的各种看法,由此也可窥见《尚书》文体分类的复杂性。
二、“因事名篇”与《尚书》文体的生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人们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依据篇名,或者根据记叙方式,或者采取篇名和记叙方式结合的多重标准。就《尚书》文体的划分而言,人们选择多元标准,这自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上述标准是不是能够解释《尚书》文体的原初生成,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
对于先秦一些文献,当分析它们的文体时,关键应注意分清专书文体与篇章文体。比如《国语》《论语》,人们将《国语》视为“国别体”,这是就专书文体而言的;同样,《论语》之“语录体”也是如此。其实,无论是《国语》还是《论语》,它们还存在篇章文体。专书文体与篇章文体之间尽管存在密切联系,但也存在区别;专书文体可以容纳一种或多种篇章文体。分析《尚书》文体,需分清楚是谈论《尚书》整部文献的文体还是《尚书》具体篇目的文体,或者是兼而有之。这是因为,选择的角度不同,会影响到所得出的结论之差异。就《尚书》这部文献而言,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部记言文献。《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10]1715这就是说,早期社会非常重视对君主言行的载录,通常由左史专门负责载录君主的言论,这些言论最终形成《尚书》。应该说,《汉志》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根据对早期文献的考察,先秦社会很早以来就存在重言之风尚,由此形成记言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之下,出现大量的记言文献,《尚书》的编纂正是利用这些记言文献。不仅《尚书》,后来的《国语》《战国策》《论语》也都是如此。所以,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这部文献呈现记言的特征。
对于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刘知几曾提出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用来解释《尚书》《春秋》《左传》这些文献的生成,但是,它们也能够很好地阐释先秦时期记言文献内部的演变。先秦时期的记言文献,由于历经长时间的发展,从而衍生出很多次生文体。这些次生文体既包括专书文体,也包括篇章文体。先秦时期典型的记言专书文体有国别体和语录体;而记言篇章文体,具体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格言体、对话体在很大程度上与记言行为相关,而事语体的生成则是出于史官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就先秦专书记言文献而言,它可以容纳多种记言篇章文体。比如《国语》,它其实就包含对话体与事语体;而《论语》则蕴含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在《尚书》中,有对话体、事语体,甚至还有单纯记事的篇章。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比如《论语》除了记言之外,就还有单纯记行的。人们通常视《论语》为语录体,其实这种语录体并不单纯记言,还有记行,《论语》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因此,作为记言文献,《尚书》存在记事的篇章实属正常。那种将《尚书》记事篇章视为“为例不纯”的看法,其实是没有通盘考察早期记言文献的文体特征。
澄清了专书文体与篇章文体之间的关系之后,再来看《尚书》的文体。《尚书》的专书文体呈现记言的特征。在这种视野下,《尚书》的篇章文体又该如何划分呢?从记言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尚书》的篇章文体划分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种划分,其实大体可归属于前面提及的记叙方式标准。不过,这种划分,尽管也体现《尚书》篇章文体的特征,但未能完全揭示其文体特色,因为《国语》《战国策》《论语》这些记言文献也大都蕴含这些次生文体。那么,《尚书》篇章文体的特色还体现在何处呢?这种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尚书》篇名上。从《尚书》篇名的角度来讨论《尚书》文体,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一方面,《尚书》的篇名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体色彩,且反映它所代表之文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尚书》篇目的命名也很好地揭示这种文体的生成。在中国古代文体生成问题上,郭英德分析说:“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10]29其中所谓“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是指“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10]29“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是指一种言说方式“形成具有独特的文体形态特征的文本方式,人们就可以依据这种文本方式来进行篇章的归类,将文本方式相类似的篇章类聚到共同的‘类名’之中,‘以类相从’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文体,从而形成一定的文体序列”。[10]42在这些说法中,“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两点对于把握《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来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大体言之,“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有助于揭示《尚书》篇章文体的生成,特别是对那些篇名具有文体意义的篇目来说;而“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则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可以将《尚书》中那些篇名没有具备文体意义的篇目进行文体归类。对于《尚书》的篇名,孔《疏》指出“《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1]20章学诚也说:“《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11]7他们一致认为《尚书》的篇名均缘于“因事而立”“因事命篇”,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孔《疏》认为《尚书》篇名“既无体例,随便为文”,章学诚说“本无成法”,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对于《尚书》的篇名,于雪棠曾经做过细致地考察,认为《尚书》篇名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一,人(国)名:益稷、微子、太甲(上中下)盘庚(上中下)君奭、君陈、君牙、多士、多方。其二,人名+名词:尧典、舜典、高宗肜日。其三,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动词,其中包括:(1)人名+动词(动词性词组):大禹谟、皋陶谟、禹贡、汤誓、秦誓、汤诰、康诰、召诰、伊训、说命(上中下)毕命、冏命、胤征、吕刑、西伯勘黎;(2)地名+动词:甘誓、牧誓、费誓、洛诰;(3)人(名)+之+动词:五子之歌、仲虺之诰、康王之诰、微子之诰、蔡仲之命、文侯之命。其四,形容词、名词(文章的内容、性质)+动词:泰誓(上中下)大诰、酒诰、洪范。其五,其他(文章中心内容、议题、线索):咸有一德、无逸、旅獒、金縢、梓材、周官、顾命、武成、立政。由此可以看出《尚书》命名的特点:即特别重视以人和行动为中心。其中《尚书》篇名出现人名的有32篇,尾字是动词的有29篇,均超过半数;二者交叉的有l9篇。并且,篇名尾字名词或动词有的反复出现:典2次、谟2次、命5次、誓6次、诰9次,这五个反复出现的篇尾动词,恰为六体中的五个,唯独训在篇名中未反复出现,只有《伊训》一篇。“由于篇名本身末字动词有的多次反复,有类的归属,因而,这种命名方式实际上就启发、引导,甚至暗中制约、规定着人们以篇名末字来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并将所有篇章纳入到六体规范中。从现实操作角度看,这种分类法的确方便可行。在文类观念并没有特别确定之时,应当说,这种分类法具有很强的合理性。”[3]8-11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对于《尚书》文体的考察,可以从专书文体与篇章文体两个方面进行。《汉书·艺文志》从“左史记言”的角度突出《尚书》记言的特征,此后刘知几说:“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5]8则是对《汉志》观点的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不过,这些说法主要围绕《尚书》专书文体展开的。其实,《尚书》文体的特色还体现在篇章文体上。如何厘定《尚书》篇章文体,历来存在争议。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尚书》篇名大都呈现鲜明的文体性质。尽管《尚书》篇名普遍具有“因事名篇”的倾向,但整体言之,《尚书》篇目命名还是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主要体现在典、谟、训、诰、誓、命这些关键词上,此诚如林之奇所言,“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此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4]
三、《尚书》“六体”的内涵及意义
《尚书》篇名大都“因事而立”“因事命篇”,看似随便为文,没有体例;但另一方面,《尚书》篇名中典、谟、训、诰、誓、命这些词语出现的频率又颇高。这样,在貌似“随便为文”的背后又似乎隐藏某种定律。那么,《尚书》篇名为何会热衷于使用这些词汇,它们又具备怎样的特质,这些问题不仅关涉《尚书》篇目的命名,同时也与《尚书》篇章文体的生成密切相关。因此,揭示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内涵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二为“谟”体。张表臣谓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12]12薛凤昌认为“谟”是嘉谋嘉猷,指禹与皋陶、益稷等赞襄献替,君明臣良可为后世懿范。[13]22黄寿祺认为“谟”有嘉谋嘉猷之义,指禹、皋陶、益稷等赞襄之道。[14]37朱自清认为臣告君的话有称为“谟”的。[25]20刘起釪指出“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15]9夏传才以为“谟”与“谋”通,即谋议。[18]99谭家健也认为谟是谋议、谋略。[17]51他们的观点很一致,指出“谟”乃谋议,大臣汇集在一起商量国是。“谟体”确实是载录臣下的谋议,不过,载录臣下的谋议为何称“谟”,上述诸家似未加措意。《周礼·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郑《注》:“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图、比、陈、协,皆考绩之言。王者春见诸侯则图其事之可否,秋见诸侯则比其功之高下,夏见诸侯则陈其谋之是非,冬见诸侯则合其虑之异同。……《司马法》曰:‘春以礼朝诸侯,图同事。夏以礼宗诸侯,陈同谋。秋以礼觐诸侯,比同功。冬以礼遇诸侯,图同虑。’”[26]992-993“朝、觐、宗、遇、会、同”体现诸侯不同时节朝聘天子的不同仪式,《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26]464诸侯在朝见天子的“夏宗”仪式上就国家政事进行谋议协商,这种谋议亦即“谟”之行为最终演变为“谟体”的生成。再来看《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及《益稷》,序谓“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孔《传》云:“矢,陈也。陈其成功。……大禹谋九功,皋陶谋九德。”孔《疏》解释说:“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发端,禹乃然而问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陈,因皋陶之言,而禹论益稷,在《皋陶谟》后,故后其篇。”又说:“《益稷》亦大禹所谋,不言‘谟’者,禹谋言及益稷,非是益稷为谋,不得言《益稷谟》也。其篇虽有‘夔曰’,夔言乐和,本非谋虑,不得谓之‘夔谟’。”又说:“禹与皋陶同为舜谋,而禹功实大,禹与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异于皋陶,于此独加‘大’字与皋陶总言故也。”[1]85《大禹谟》《皋陶谟》及《益稷》记载大禹与皋陶在帝舜之前谋议,由此可知,这些篇目确实体现“谟体”的特征。
其三为“诰”体。张表臣以为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12]12薛凤昌指出“诰”为晓谕臣民之辞,[13]22黄寿祺以为“诰”即告,晓谕臣下之辞。[14]37朱自清认为平时的号令叫“诰”,[25]20刘起釪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15]9夏传才指出“诰”是告谕的意思。[18]99-100江灏、钱宗武将“训”与“诰”合并解释:“训诰,主要是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以及祈神的祷告。”[16]1谭家健认为训诰是训诫诰令,有上对下的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和君臣对谈。[17]51李零则以为“诰”是布政之辞。[19]65这些看法除少数地方存在异议,基本上认同“诰”为君对臣民或下对上的讲话。《尚书》篇名中含有“诰”字的有《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据孔《传》、孔《疏》的解释,可以发现:(1)就“诰”之发出者与接受者而言,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臣对君的诰辞,《仲虺之诰》为仲虺对成汤的诰辞,《召诰》为召公对成王的诰辞;二是君对臣的诰辞,《汤诰》为成汤对诸侯的诰辞,《大诰》乃周公以王命对各诸侯及大臣的诰辞,《康诰》《酒诰》是周公以王命对康叔的诰辞;三是君臣之间互诰,《洛诰》载录周公“陈本营洛邑之事,以告成王”及“王因请教诲之言”,《康王之诰》载“群臣进戒于王”及“王遂报诰诸侯”。可见“诰”并非仅限于君对臣民或下对上的讲话。(2)“诰”之创作缘由:《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1]196为了消除成汤的顾虑,仲虺作了这篇诰辞。可见《仲虺之诰》的创作,实缘于夏桀的放逐。《汤诰》乃战胜夏桀之后,成汤向诸侯阐述伐桀的重大意义。《大诰》为周公平定武庚叛乱而发表的诰辞。关于《康诰》《酒诰》,孔《疏》以为“以殷余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诰》、《酒诰》”。《召诰》载录洛邑营建过程及召公的诰辞。《洛诰》记录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与成王的谈话。《康王之诰》记录康王即天子位之后与群臣的对话。由此看来,“诰体”要么与战争有关,要么与即位册命有关,要么与营建洛邑有关,这意味着“诰体”的生成往往关联重大事件。“诰体”这种特质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孔《传》曾言“会同曰诰”,按《周礼·天官》载大宰“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郑《注》:“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大会同或于春朝,或于秋觐,举春秋则冬夏可知。”[26]49“会同”为诸侯朝见天子之仪式,上述诸诰确实也涉及天子与诸侯大臣,但孔《传》将“诰”领会为会同之仪式似乎也并未完全揭示“诰体”的真相。陈梦家对于“诰”有过这样的分析:
《大祝》六辞的诰、会即六祈的造、襘,……告为祷告、祈告之告,《说文》曰“祰,告祭也”,“诰,告也”,《大祝》注引杜子春云“诰当为告,书亦或为告”。六辞之诰是名词,六祈之造是动词,故《大祝》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礼记·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曾子问》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庙;诸侯相见必告于祢;反必亲告于祖祢”。《尚书·金縢》曰“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此告即祈告。卜辞之告皆告于祖先。[27]314
很清楚,“诰”是一种言辞,与“造”“告”“祰”这些祭祀祖先的行为相关。据卜辞有关殷人祭告祖先仪式之记载,“‘告’行于内祭与外祭,而其告于神灵的内容,则大致以方国的来寇、征伐、田游、出步、虫祸、水害、疾病、王尤为主。”[28]48由此可见早期“诰体”的特征。到了周代,《尚书》诸诰所告的对象已经指向生人,所告内容也多为现世人事。并且,《尚书》诸诰都是在各种特定的礼制仪式中生成的,这些仪式主要有赏赐、任命、册封、会同之礼。[24]比如《康诰》《酒诰》,《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29]1545-1549上面已经对《尚书》诸诰进行一些分析,可以说,《尚书》诸诰是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中生成的。
其四为“训”体。张表臣指出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12]12薛凤昌也认为“训”是诲导启迪之义。[13]22黄寿祺指出“训”有诲导儆迪之义,即敷奏陈说之辞。[14]3夏传才以为“训”是教诲的意思,[18]99江灏、钱宗武指出“训诰”主要是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以及祈神的祷告。[16]1谭家健认为“训诰”是训诫诰令,有上对下的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和君臣对谈。[17]51李零也主张“训”是教训之辞。[19]64他们大都将“训”理解为诲导、教训之辞。《说文》:“训,说教也。”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20]91可见“训”是一种言说行为,通过运用理义的方式去教导他人。就早期文献的记载而言,“训”这种行为的存在似乎比较广泛,《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在即位典礼上任命百官,要求他们要担负训导公卿子弟及部下的责任。[29]802-807这种“训”的教育意味非常浓厚。其实,不仅“训”之行为通常与教育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出现《训典》用作教材的情形,《国语·楚语上》明确记载“教之《训典》”。[22]528因此,“训”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一方对另一方所施加的一种特定的教导,就施训方而言,必须依托某种义理,为受训方提供可资借鉴的准则;受训方在接受这种教导时,能够从中获取某种收益,为以后的行为提供合乎规范的依据。“训”之行为侧重教育层面,其仪式意味相对《尚书》其他文体而言较为淡薄。当然,很多仪式场合也常见“训”之行为。《国语·鲁语上》说:“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22]153《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29]276“训上下之则”,就是训诫臣属要严守君臣名分,区别等级尊卑。这种训诫行为就发生在朝聘之礼上。《尚书》篇名中出现“训”字的有《伊训》,孔《疏》说:“成汤既没,其岁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汤之后,恐其不能纂修祖业,作书以戒之。”[1]202太甲即位之后,伊尹担心他不能很好地继承祖辈的事业,于是就写下此《训》来规训太甲。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30]98孔《疏》所谓“成汤既没,其岁即太甲元年”并不准确。不过,它们均认为《伊训》作于太甲元年。按《尚书·伊训》载:“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只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1]202-203此处不但明确《伊训》作于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而且还指明这一天祭祀先王,伊尹侍奉嗣王太甲拜见祖先,说明成汤的盛德,以此来训导太甲。通观《伊训》,伊尹都是用先王事迹进行说教,由此表明《伊训》的生成还是基于祭祀的背景。
其五为“誓”体。张表臣指出即师众而誓之谓之“誓”,[12]12薛凤昌谓“誓”为约束士民之言,[13]22黄寿祺认为誓即约,约信于士民之辞。[14]37朱自清认为有关军事的叫“誓”,[25]20刘起釪说“誓”是君主誓众之词,而且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15]9夏传才指出“誓”是约束的意思,多半指征伐交战的誓师词。[18]100江灏、钱宗武认为“誓”主要是君王诸侯的誓众词,[15]1谭家健也说“誓”是誓辞,指战前誓师词。[17]51不过李零认为“誓”是誓神之辞。[19]65归纳起来,一是认为“誓”是征伐交战的誓师词,二是指约信士民之辞,三是誓神之辞。《说文》:“誓,约束也,从言折声。”段《注》指出:“凡自表不食言之辞皆曰誓,亦约束之意也。”[20]92《说文》大抵侧重字面之义,很难看出“誓”的内涵,段《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誓”行为的内在意义。即使如此,段《注》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说明“誓”。《礼记·曲礼下》“约信曰誓”,孔《疏》说:“用言辞共相约束以为信也。”[31]141可见“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言语约信行为,段《注》所谓“凡自表不食言之辞”似乎只侧重单个人而言,并不全面。《诗经》毛《传》有“师旅能誓”之说,[32]199《周礼·秋官·士师》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26]920这些记载更突出“誓”与军旅之间的联系。一般而言,“誓”之用途并不限于军旅,比如侯马盟书,内容可分作5类:(1)宗盟类,要求参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2)委质类,参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3)纳室类,参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4)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5)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33]33-52“誓”与“盟”是两种不同的仪式行为,《礼记·曲礼下》云:“约信曰誓,莅牲曰盟。”[31]141但是,“盟和誓两者都是用语言向神以及人或者物宣誓将来自己必须做的,或者不能做的事情,以此来制约自己行为的一种方法。”[34]50所以,“誓”与“盟”常常连接在一起。这样,由侯马盟书可以发现,“誓”广泛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先秦的“誓”体存在祭祀之誓、会盟之誓、约剂之誓和军旅之誓。“盟誓”的仪式,据《礼记·曲礼下》“莅牲曰盟”的记载,孔颖达《疏》写道:“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31]141由西周青铜器所载“誓辞”来看,其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步是“立誓”。约剂之“誓”主要是调节因经济利益而引起的纠纷,有的纠纷只在利益双方的参与下就得到解决,而有的纠纷则不但有利益双方的参与,还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样,“立誓”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益双方协商,宣誓一方对于所立的违约之后的惩罚是出于自愿的;一是第三方的介入,使违约之后的惩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立誓”就不一定出于自愿。第二步是“宣誓”。誓辞一般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为宣誓方承诺今后履行某种行为,其二是在不履行誓约的情况下所应承受的处罚。[34]80-81《尚书》中的“誓”均与战争相关,属于军旅之誓。根据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等资料的记载,军旅之誓可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进行。[24]59《尚书》篇名中出现“誓”字的有《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其中《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属于战前之誓,只有《秦誓》一篇为战后之誓。
其六为“命体”。张表臣说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12]12薛凤昌指出“命”为戒饬臣工之诏,[13]22黄寿祺也强调“命”为戒敕臣下之言。[14]37朱自清认为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25]20刘起釪则以为“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15]9夏传才分析说:“‘命’,是‘令’的意思,所以命体是命令之词,多是君王奖赏臣子宣布的命令。”[18]100江灏、钱宗武指出“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16]1谭家健以为“命”是册命。[17]51李零认为“命”是命官之辞。[19]65《尚书》篇名中明确以“命”名篇的有《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孔《传》、孔《疏》对它们均做过解释。孔《疏》分析《说命》说:“此三篇上篇言梦说,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说既总百官,戒王为政;下篇王欲师说而学,说报王为学之有益,王又厉说以伊尹之功。相对以成章,史分序以为三篇也。”[1]246孔《传》以为《微子之命》乃“封命之书”,[1]352《蔡仲之命》是“册书命之”,[1]451《毕命》为“毕公见命之书”,[1]521《冏命》“以冏见命名篇”,[1]530《文侯之命》乃“平王命为侯伯”。[1]555至于《顾命》,王国维说:“《周书·顾命》一篇,记成王没、康王即位之事。……今以彝器册命之制与《礼经》之例铨释之,其中仪文节目,遂犁然可解。”[35]25-26这样,《尚书》中七篇以“命”名篇的文献在性质上均属于册命文献,也就是说,它们的生成均基于册命仪式。据分析,周王册命仪式大致包括如下环节:(1)周王即位。周王在某日之晨至宗庙太室,即位在中廷之北,太室阶上,户牖之间,斧依之前,南向而立。宣命史官在其右,书命史官在其左。(2)受命者入门。周王即位之后,受命者由一傧者导引,由右边入门,立于中廷,北向,面朝天子之位,等候册命,傧者在其右。(3)授书与册命。册命时,书命史官将命书授之于周王,周王复将命书授予宣命史官,由宣命史官南面宣读命书,册封受命者,受命者与宣命史官正面对着。(4)受命礼仪。史官宣命完毕,授册书于受命者,受命者行再拜稽首之礼,对扬王休。受命者受册以出,出入三觐。受命者受册以归,舍奠于其宗庙,或铭刻于彝器。“其它如王臣册命、诸侯册命的仪式,均与此相仿。”[24]其实,《顾命》就比较完整地呈现周康王册命仪式之过程,贾海生曾从十个方面加以揭示:(1)堂上户牖之间置屏风、幄帐,户牖之间、东西序、西厢夹室设成王生时四座,东西序、东西房及堂下两阶、左右塾前陈列宝物、兵器、辂车。(2)九名宿卫执兵器就位于门内、两阶东西侧、东西厢前堂、东西垂、北阶。(3)康王从宾阶升堂。太保奉介圭,太宗奉同(酒器)瑁从阼阶升堂;太史持命书从宾阶升堂;卿士、邦君入门就堂下位。(4)太史宣读命书,命康王继体为君。康王再拜,起立,答册命。(5)康王从太宗手中接过同,三次进酒祭神。太宗向康王进酒,赞王饮酒。康王尝酒,再拜。(6)太保从康王手中接过同,降自阼阶,将同放入堂下篚中,盥手,洗另一同,执璋升堂,酌酒自酢,将同交给太宗,拜神,告神已册命康王。康王答拜,敬受册命。(7)太保又接过同,祭神,尝酒,奠酒,拜神,告册命之礼毕。康王答拜,敬其告神。(8)康王、太保降阶下堂,有司彻去诸器物。(9)诸侯出庙门,康王出门立于应门之内。太保、毕公率东西方诸侯入即位,陈庭实,再拜稽首。康王答拜,受庭实。太保等戒康王要敬王位,继承先王之业。康王告群臣当辅己发扬光大先王之业。(10)群臣退下,康王复服丧服。[36]王国维说:“其册命之礼质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古《礼经》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35]26
通过对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的分析,我们发现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它们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仪式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具有可重复性。仪式的这种特性,也就是造成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尚书》中的根本原因。由于“六体”的仪式特征,这就为判断《尚书》篇目的归属提供依据。譬如《周官》《吕刑》,是诰体还是训体?周成王灭淮夷后回到王都丰邑,向群臣阐明周家设官分职用人的法则,这是《周官》生成的缘由,由此观之,《周官》归入“诰体”更符合实际。关于《吕刑》,周秉钧先生分析认为“是穆王的诰词”。[37]23还需说明的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在《尚书》中,两种行为往往相混于同一文体,若以行为分类,则同时可以归为两种文体,尤其是‘诰’的行为与其他行为相混。而且《尚书》中记言部分的篇章往往有叙事成分,内容相互掺杂,若以叙事分类,则也可分入‘典体’。再则《尚书》一篇章中往往包含几种文体,有记言的,也有记事的,若按孔安国六体分类标准归类,则难以辨别。”[38]24-29即是说,《尚书》存在文体相混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专书文体与篇章文体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前面已经指出,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呈现记言的特征。但作为记言文献,《尚书》存在记事的篇章也属于正常。从这个层面来看,就不能说《尚书》文体相混,因为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本身就是常态。至于《尚书》的篇章文体,大致有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自然也谈不上文体相混。因此,只要紧紧抓住“六体”的内涵,用它们来划分《尚书》文体类型并不存在难以辨别的问题;相反,也只有利用这一点,才能比较好地阐释《尚书》文体的生成及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