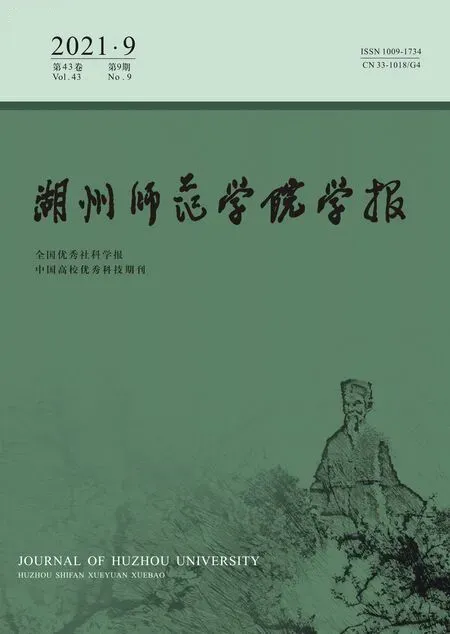“三言”异类爱情故事对《夷坚志》的改写*
王一雯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晚明思想史的变动加速了程朱理学的松动。这一时期,“理”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知识阶层对“情”与“欲”的推崇。因此,在文学中也形成了一股“尚情”的思潮。同时“情”也成为晚明,尤其是万历以后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作者对于“情”的态度却不可一概而论。
“三言”中有不少异类爱情故事,同时涉及人与妖、鬼之间的爱情。虽然“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有“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尚情观念,但这些爱情故事笔涉虚幻,又由文言本事改易而来,在口头流传中几经变异;同时,小说中的“爱情”主题又与其他主题相互交织,因此故事对“情”的态度变得相当复杂。
“三言”中涉及异类爱情故事共有十篇(1)《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卷十四《一窟鬼难道人除怪》,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卷二十七《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据谭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其中有五篇故事的本事与《夷坚志》相关(2)《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本自《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警世通言》卷二十七本自《夷坚支庚》卷七《周氏子》,卷二十八本自《夷坚志》戊卷第二《孙知县妻》,卷三十本自《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醒世恒言》卷十四本自《夷坚志》支庚卷第一《鄂州南市女》。。据此可知,“三言”中,异类爱情故事的本事半数都与《夷坚志》故事相关,这显示了编纂者在改写时的选材偏好。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对《夷坚志》中故事的改写情况。
“三言”的故事,大多经历了复杂的删改过程。《历代学者》在话本断代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胡士莹、程毅中等认为“三言”中存在宋代话本(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程毅中:《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章培恒、韩南则认为“三言”中的小说几乎都写定于元以后(4)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5-20页;(美)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页。。本文主要讨论冯梦龙对《夷坚志》故事的改编。虽然作品的断代有许多争议,但“三言”经由冯梦龙改编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冯梦龙将这些作品编入“三言”,即使他对文本没有做过多改动,也表示了他对所收作品的认同。因此可以推断,将宋元话本修改并编入“三言”的冯梦龙,认为这类故事符合“情教”观念,同时具有商业出版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故事虽然具有宋元时代“非主流”的思想特色,但却拟合了晚明“尚情”的思想潮流。
一、“情”“教”合一:晚明尚情思潮与情教观对改写的影响
晚明思想界经历了不少震荡,不少人秉持着“天下莫重于情”的观念,并将“情”作为至高的人生价值。他们对“生死相恋”的感情极端推崇,对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也同样看重,似乎“情感”的力量能冲破一切阻碍,改变人的命运。“尚情”派的文人将《牡丹亭》视为“至情”代表作。“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情节昭示着“情”可以超越生死,人鬼的身份差异不应该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的阻碍。在“尚情”派作者的眼中,爱情故事里,男主人公若怀疑人物身份,害怕女鬼,只因为爱人不是人就抛弃她,这并非“至情”,而是一种“无情”。
“三言”的编定者冯梦龙提出了“情教”的主张,奉行以“情”劝世的原则,他在署名龙子犹的《情史类略》序中说: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1]1
冯梦龙认同“情”的重要性,认为天地有情才能生万物,人死情不灭;“情”不仅是狭义的爱情,而是包含了天地间一切伦理情感。我们可以发现,冯氏也深受“尚情”思潮的影响。
在“三言”中,冯氏将文化意义上的“情教观”与“小说”的编纂观念,即创作目的、手段与原则等互相糅合:
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也。[2]1
这种病害主要危害的部位是果穗,一旦玉米植株受到感染,通常都会颗粒无收。对于玉米的危害性极大,针对这种病害的防治力度必须加强。玉米种子对于病害的抵抗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在土壤中非常容易受到土壤中细菌的感染,这样在植株不断生长的过程中细菌会进一步蔓延之果实,最终导致玉米减产,针对这种病变,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选用抗病性较强的玉米品种,同时也可以物理、化学及生物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针对玉米叶茎根等的病虫害要及时的喷洒适量的农药,缓解植株的病变情况。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着重强调了“小说”与史书间的关系,冯氏试图以“三言”为“六经国史之辅”,“情”不再居于文化中心的地位,而是成为小说功能的一种。冯氏认为,通过小说教化人心可以“导情情出”,引导读者积极向上。这段话表明,“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的“教化”观念是冯氏编纂“三言”的主要原则之一,而“触性性通,导情情出”是在“情教观”影响下,小说教化功能的具体表现方式。无疑,冯梦龙的“情教观”和小说的“编纂观念”互相影响,都体现在了“三言”的编纂策略中。
我们发现,“三言”在不改变《夷坚志》本事中主要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与“情”相关的元素。如《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主要讲述了靖康之变后,杨思温在燕京巧遇其友人韩思厚的亡妻之魂,便将此事告知韩思厚,二人一起寻找韩妻鬼魂之事。虽然在本事《夷坚志·太原意娘》和《杨思温》中,都提到杨、韩二人因为惧怕鬼魂而有所顾虑,但这并没有成为故事发展的阻碍。女鬼是在靖康之变中守节而死的韩思厚的妻子,因此“鬼”的身份没有导致任何道德问题。《太原意娘》中,韩生特地祝祷,对妻子的孤魂“感泣”并“誓不再娶”,但妻子的鬼魂没有要求一直跟随着韩生。与本事相比,《杨思温》中添加大量诗词,渲染韩思厚与妻子间的深情,如:
因感亡妻郑氏,船中作相吊之词,名《御阶行》……至楼上,又有巨屏一座,字体如前,写着《忆良人》一篇。[2]363-379
除此之外,故事还强化了妻子身份变化与丈夫情感转变的关系,强调了妻子对死亡会使夫妻感情疏离的担忧:“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温道:‘叔叔岂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时,他风流性格,难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随他去,怜新弃旧,必然之理。’”最后韩思厚因为背信弃义而死。《杨思温》在继承本事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信义、感情与性命的紧密关系,强化了《夷坚志》中“情感”的部分。
《警世通言》卷二十七《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其本事为《夷坚志·周氏子》。本事讲述了书生夜遇女鬼之事。周生与女鬼的情事被父亲撞破后,“父即日挈之徙舍,招医拯治”。故事并未提及周生与女鬼之间的感情,只提道:“女令周吹灯,解衣登榻。隐士绝迹,而女夜夜来”[3]1189。《假神仙》里,两人的感情变为两男一女三人的“情欲”。三人之间产生情感的方式延续了本事中的由“欲”生“情”,但将情感更加具体化:“一连宿了十余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诸多本事也都指向妖物对青年男性的威胁,但《李黄》和《夷坚志·孙知县妻》都未涉及感情,只是讲述男子被蛇妖迷惑的故事。《西湖三塔记》中未提及白衣妇人和许宣赞有任何的感情。《白娘子》中,许宣为色所迷。在他不断怀疑白娘子身份的过程中,二人却仍然“夫唱妇随,朝欢暮乐”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白娘子》中,白娘子的“情”变得较为显著:“情意相投,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难道走开了?我与你情似太山,恩同东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处,和你百年偕老,却不是好!”[2]420-448
上述故事在本事的基础上增补了很多“情感”细节,主要突出强调女主人公的“有情”,但也保留了本事中许多儒家的传统伦理,因此男主人公往往表现得十分“薄情”。如《假神仙》将“情欲”“长生”“死亡”互相联系。故事夹杂了魏生对成仙的渴望,以及三人的“情欲”,这使魏生一开始不愿意相信二位仙人是鬼怪,最终他选择了抛弃这段感情。《白娘子》故事的结尾再次明确了许宣对白娘子的情感是“被色迷了心胆”,否定了二人的感情。
由此可见,“三言”对于《夷坚志》本事中“情”的改写面貌与《牡丹亭》的主旨不同。“三言”中的一些故事汲取了志怪笔记中的“女鬼”故事,主题仍然围绕“守信”“戒色”等传统伦理,用以教化人心。但话本中对“情”的描写有所增加,迎合了晚明流行的“情欲”话题,并体现了冯梦龙对“情”的重视。
二、“情”重于“教”:情教观对果报结构的影响
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民间认为“善恶皆有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冯梦龙欲“以小说行教化”,所以因果报应在“三言”故事中并不少见。相比本事,“三言”中的因果联系显著增强,甚至体现出锱铢必较的特色。但在以歌颂女子“多情”为主题的《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和《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男主人公却没有受到任何“果报”,这一安排是比较特殊的。
以《闹樊楼》为例,《闹樊楼》讲述了男主人公与女鬼的爱情及其引发的公案。谭正璧的《三言二拍源流考》列举了其本事:《夷坚志·鄂州南市女》和《清尊录·大桶张氏》。在《鄂州南市女》与《大桶张氏》中,男主人公对死者“还魂”的认识都是单一的。比较《鄂州南市女》《大桶张氏》以及《闹樊楼》能发现不少相似的情节。三个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为情而死,遭遇盗墓,“复活”后被男主人公打死,引起公案。男子无故杀死一名女子,依据各朝法律都应被判死罪。而对盗墓罪的处罚,唐以来盗墓开棺见尸者均会被判处绞刑,法律上处罚的出入不大。
但《鄂州南市女》中,盗墓者“坐破棺见尸论死”,而“打死人”的彭生没有被判死,仅仅是“轻比”[3]1136。这说明在《鄂州南市女》中,死而复生的吴女的身份无疑是“鬼”,因此彭生不算杀人。而在《大桶张氏》中,“郑发冢罪该流”。按律,“发棺”应该判处绞刑。不判死刑的原因只能是判决者认为张女不是尸体,即使前文提到张女“俄顷即死”[4]193。而张生因杀人被判死罪,判决理由是“而张实推女而杀之,该死罪也”,张生“虽奏获贷,犹杖脊,竟忧畏死狱中”。也就是说,《鄂州南市女》中官员认为男主人公“打鬼”,《大桶张氏》中则认为男主人公“杀人”。
虽然在《鄂州南市女》与《大桶张氏》中,牵涉命案的男主人公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但他们都是依据律法被判决。刑罚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官方对女子身份判定的不同。《大桶张氏》中提到“张实推女而杀之,该死罪也,虽奏获贷,犹杖脊,竟忧畏死狱中”,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因果报应。结合《闹樊楼》中范二郎的结局,可以发现,它主要参考了《鄂州南市女》。在一系列的风波后,范二郎被无罪释放。
《闹樊楼》故事的前半部分显示了范二郎对周胜仙有“情”,但后半部分范生的种种表现,却暗示了他“无情”的一面,如他因为“遇鬼”而极度恐慌:
女孩儿移身直到柜边,叫道:“二郎万福!”范二郎不听得都休,听得叫,慌忙走下柜来,近前看时,吃了一惊,连声叫:“灭,灭!”女孩儿道:“二哥,我是人,你道是鬼?”范二郎如何肯信。一头叫:“灭,灭!”一只手扶着凳子。却恨凳子上有许多汤桶儿,慌忙用手提起一只汤桶儿来,觑着女子脸上手将过去。……酒博士看那女孩儿时,血浸着死了。范二郎口里兀自叫:“灭,灭!”范大郎见外头闹吵,急走出来看了,只听得兄弟叫:“灭,灭!”……良久定醒。[5]459-471
他的表现与周胜仙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胜仙“一心牵挂着范二郎,见爷的骂娘,斗别气死了”,做了鬼,是“因情而死”;而“死不多日,今番得了阳和之气,一灵儿又醒将转来”,得以重生,想和范二郎再续前情。范二郎怀疑她是鬼,将她打死。周胜仙向五道将军求情,“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将军,但耐心,一月之后,必然无事”。若范二郎没有打死人,她应向五道将军申冤,在托梦时不必言“求情”,在改判时不必判“打鬼”,直言“未死”即可。周胜仙人鬼身份的转变与范二郎的结局密切相关。范二郎最终因为周胜仙的求情,被判打鬼,免于处罚。
范二郎对周胜仙,从一见钟情到相思成病,无疑是“有情”的。但范二郎得知周胜仙病故后,又见她来店里找自己,判断其为鬼而失手将她打死。在今人看来,范二郎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鬼怪威胁不得已为之,这是一种真实反应,不能直接判定其无情。同时,已经成鬼的周胜仙选择原谅并助其摆脱牢狱之灾,表现了她用情至深。范二郎只是一个烘托周胜仙“多情”的配角。但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了“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似得便宜”的议论。这表明,与今人不同,作者认为范二郎后期的一系列表现是“无情”的。周胜仙一往情深,经历了生生死死,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般多情,却不得好死;范二郎所为,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他没能如柳梦梅一样为爱不顾生死,而是辜负了周胜仙的多情,就理应受到报应,不应该得到“便宜”。这句议论说明了作者对“情”的高标准与极端推崇,以及对故事不符合“因果报应”的质疑。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金明池》中。该故事本自《夷坚志·吴小员外》。《吴小员外》与《鄂州南市女》较为相似,没有描写“情”。《吴小员外》中缺少盗墓的情节,也没有对被击杀女子尸体的描述,虽然吴小员外看到女子倒地,但故事最后只有“流血滂沱,为街卒所录”[3]29这样模糊的交代,且根据“鞫不成,府遣吏审池上之家”,可以推测该公案故事因没有尸体作为证据,所以无法拘押他。志怪也选择了一个常见的结局,即开棺发现女子类似“尸解”,宣告这个女子不再是人,或者说之前击杀的不是人。因此吴小员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金明池》中的吴小员外,名“吴清”,似与“无情”谐音。该篇故事引用了诗句作为入话:“朱文灯下逢刘倩,师厚燕山遇故人。隔断死生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朱文”一句是宋元南戏中的人鬼恋爱故事,朱文夜遇女鬼,女鬼送他太平钱,后来几经周折结为夫妇。“师厚”句指代《杨思温》典故,主要是强调“意娘”的情切。说明该故事主题与“情”高度相关,并且主要强调的是“隔断死生终不泯”的深情,而非如《杨思温》中的负心情节。
《金明池》的前半部分,细致地描绘了吴清与卢爱爱两情和美:
那小员外与女儿两情厮投,好说得着。可知哩,笋芽儿般后生,遇着花朵儿女娘,又是芳春时候,正是:佳人窈窕当春色,才子风流正少年。小员外只为情牵意惹,不隔两日,少不得去伴女儿一宵。[2]260
当他得知卢爱爱是鬼后,也恐惧她的非人身份,并与道士商议,预谋杀死她,而不是选择求饶,展现了他在爱情中“无情”的一面。爱爱对他始终如一,在吴清入狱后,爱爱的鬼魂特来告别:“前夜特来奉别,不意员外起其恶意,将剑砍奴。今日受一夜牢狱之苦,以此相报。阿寿小厮,自在东门外古墓之中,只教官府复验尸首,便得脱罪。”由于女鬼的“多情”,吴小员外得以逃脱牢狱之灾。在这类故事中,只有女主人公的“多情”能够拯救男主人公,让他们免于因果报应。这样的安排,昭示了“情”的力量。
在本事中,因果报应仅仅和命案相关联。而在《闹樊楼》和《金明池》中,他们能免于因果报应是因为女主人公的“多情”,这表明“情”能够超越因果报应的结构。这与冯梦龙的“情教”观念有所抵牾。虽然“情”能超越因果报应的结果侧面说明了“情”的重要性,但因为多情者并没有得到庇佑,而无情者也未得到惩罚,“教”的部分在这些故事中就难以实现。
三、平衡“情”“教”:情教观与编纂观念对改写的影响
冯梦龙的“情教观”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冯梦龙把“情”当作移风易俗、人伦教化的重要手段,同时这种“情”是天地间的“泛情”,它包含了不同伦理关系中的情感。
但从《情史类略》收录的故事来看,冯梦龙对“情”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两性关系上。冯梦龙编纂《情史》而“事专男女”,独以男女情事为长,以阐发两性关系之微妙:“是编分类著断,恢诡非常,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1]1冯梦龙在卷首所述涉及“君臣父子”的“情教”观念与《情史》中收录了大量“男女情事”故事的行为有一些出入。冯梦龙在编纂《情史》时,绝大篇幅仍集中在女性群体上,主要是对女性事迹进行整理。“事专男女”,或者说着重描写女子,是为了迎合时人的阅读偏好。这说明冯氏在卷首所宣称的“情教观”和书籍具体的“编纂策略”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同样,在“三言”中,冯梦龙的“情教观”通过具体的编纂策略表现在文本中,但又受到其他编纂观念,如本事选择、故事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形成了一些叙事上的矛盾,这也使冯氏在改写时不得不进行“情”与“教”的平衡。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本文讨论的异类爱情“三言”故事并没有改动本事中基本的情节与故事的发展轨迹。话本小说基本保持了文言本事的结构,均保留了《夷坚志》故事的开头和结局中人物的处境,没有人为改变故事的因果,没有将男女主人公离散的结局扭转为大团圆结局。《夷坚志》本事中的开端和结局在“三言”故事中并没有发生完全“颠覆”式的改易。本事中男主人公的结局并没有由“生”到“死”的改变,即使他们做了“无情”之举。除了《白娘子》改编了《夷坚志·孙知县妻》中孙知县病亡的结局。但这一改写应是沿用了民间流传较广的《西湖三塔记》的结局。所以尽管白娘子变得“多情”,但仍然不能和许仙共结良缘。
而《闹樊楼》中出现了没有符合因果报应的情况。《闹樊楼》是融合《鄂州南市女》与《大桶张氏》而成,并非只取其一作为本事。《闹樊楼》中,男主人公认定女方是鬼这一情节,受到本事《鄂州南市女》的影响较多。《闹樊楼》综合了两篇本事,感情描写与果报观更加复杂。对比《大桶张氏》和《鄂州南市女》,会发现前者注重突出因果报应,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男主人公最终受到道德制裁;而后者侧重描写对鬼的恐惧,彭仆在道德上没有严重的过错。这两者都在《闹樊楼》里留有一定的痕迹。《闹樊楼》因继承、改编多篇本事,同时受到晚明“尚情”趋势的影响,前半段的感情描写显然迎合当时“尚情”的审美氛围,而后半段的范二郎的“无情”也是受限于本事情节的影响。因为《鄂州南市女》和《大桶张氏》中的男主人公都无意于女主人公。在《闹樊楼》中,叙事者对男主人公范二郎没有受到任何“报应”而感到不满,因此在故事的最后,有诗为证:“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似得便宜。”由这句叙事者干预可知,作者对该故事结局并不满意。但为何作者宁愿发出“无情翻似得便宜”来质疑故事的结局,也没有改编范二郎的结局让他获得因果报应呢?
如上文所述,强调“情”能够超越因果报应的结构是编纂者的目的之一。但作为编纂者,为人物添加或减轻一些果报也是可能的。在此,可比较“二拍”对《夷坚志》故事中因果报应的改写。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三的《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判溪里旧鬼借新尸》在参考《夷坚志·证果寺习业》时,“果”与“业”在话本中被重点强调。《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中添加了向官府告密的仆人胡阿虎以及其受到的报应:“‘那胡阿虎身为家奴,拿着影响之事,背恩卖主,情实可恨!合当重行责罚。’当时喝教把两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周四不计其数,以气绝为止。不想那阿虎近日伤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为奴才背主,天理难容,打不上四十,死于堂前。”[6]193然而其本事《夷坚志·湖州姜客》中并无此类情节。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的《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的“入话”故事受到《夷坚志》丁志卷十八《刘尧举》和《睽车志》故事共同影响。在本事中,刘尧举并未获得功名,而在《二刻》中则是将报应改为男主人公因“始乱终弃”而“迟了”功名,较本事稍稍减轻了一些报应。
相比凌濛初对因果报应的改易,冯梦龙没有按照“情教”的思想改易《闹樊楼》中的果报。究其原因,极可能是受到了本事结构,尤其是本事中男主人公结局的限制。《宝文堂书目》中并无《闹樊楼》,但谭正璧、欧阳代发、程毅中认为这是宋代话本小说,而韩南未将之归入1450年前的小说类别。但若该故事在宋代已有雏形和框架,或此故事是明代说话人仍然讲演的“说话”故事,那也就意味着当时的读者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或者熟悉这个故事的梗概。就像《白娘子》故事就极有可能受当时民间传说的影响。也因此,冯氏不能改易故事的结局,可能与当时读者的阅读经验相关。
异类故事中往往都添加了“情”的元素,充满了对“情”的崇尚;描写女性的“多情”也迎合了“尚情”的风气以及商业出版的需求。冯氏吸收、化用多篇本事改写故事,受到编纂观念的限制,不能过分改易故事的结局,但又要贯彻他的“情教”,强调“情”的力量,于是导致了“情”和“教”之间不能完全平衡的叙事矛盾。
但在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冯氏试图平衡“情”与“教”的努力。“情教”中所强调的“教化”,主要以另一种形式进行表现。《闹樊楼》与《金明池》中,男主人公没有受到“报应”,故事选择对女主人公进行一定的补偿。以负心为主题的宋代志怪中,对无情者的处罚相当严重。被负一方多亲自现身索命,如《夷坚志·陆氏负约》《夷坚志·太原意娘》等。《闹樊楼》中,道德无错的女子并没有获得感情上的回报。因此《闹樊楼》的主题——歌颂“多情”,“无情”会招致果报这一教化目的未能实现。最终编纂者只能用命运“前定”来解释结局,并给予了女主人公跟随神的补偿性回报:
奴阳寿未绝。今被五道将军收用。奴一心只忆着官人,泣诉其情,蒙五道将军可怜,给假三日。如今限期满了,若再迟延,必遭呵斥。[5]471
而本事《大桶张氏》中并没有关于女主人公结局的描写,《鄂州南市女》也只写了墓中无尸。
编纂者采用道教、佛教等民间元素,反复暗示女主人公成仙的结局。在《金明池》中,卢爱爱说大元夫人“怜奴无罪早夭,授以太阴炼形之术,以此元形不损,且得游行世上”。“太阴炼形之术”,是道家全真派法术,死后仅剩尸骨也可以修炼:“孙不二元君,所传女金丹中,有太阴炼形之道,为女子修真之捷径。若有童女,精进修技,可以立成神仙之果。”[7]183话本又将本事中“开棺”后只见到衣服如蝉蜕的情节改编为爱爱的身体仍然存在:
那爱爱小娘子面色如生,香泽不散,乃知太阴炼形之术所致。吴小员外叹羡了一回。改葬已毕,请高僧广做法事七昼夜。其夜又梦爱爱来谢,自此踪影遂绝。后吴小员外与褚爱爱百年偕老。卢公夫妇亦赖小员外送终,此小员外之厚德也。[2]193
而吴清用佛家之法超度亡魂,用道教之法指向成仙的结局。同时,相比“尸解”,卢爱爱肉体不腐更符合民间对仙人的想象,强调了她成仙的可能。
冯氏融合佛、道以及民俗对女主人公结局进行改易,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情教”的观念,展现了他平衡“情”与“教”关系的努力。
综上所述,“三言”异类爱情故事的文言本事题材多糅合《夷坚志》的相关故事,这显示了话本编纂者的一种选材偏好。这点在凌濛初的“二拍”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通过比较“三言二拍”对《夷坚志》故事的改写,可看出编纂者改写观念上的一些差异。编纂者对待本事的态度及其编纂理念,对改写文言本事、编定“三言”的影响颇大。而冯梦龙所坚持的“情教”的编纂观念与晚明“尚情”思潮存在一定的差异。冯梦龙虽然十分推崇“情”的地位,但在“三言”中,更倾向于将它当作一种“教化”的工具。但是,为了回应“尚情”思潮,以及迎合商业出版的要求,“三言”中以“教化”为主题的小说,也加入了一些“情”的元素。这些故事将“情”这一命题与“生死”“人鬼”身份转换及公案等流行题材结合,体现了符合晚明流行思潮的叙事特色。而基于对“情”的推崇,改写后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话本中的基本理念——因果报应的“教化”功能。因此,作品意涵与改编者的主观意图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情教”。编纂者在话本结构、故事来源、改写限制等方面受限,其编纂观念决定了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本事作出改易,力求在小说中达到贯彻“情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