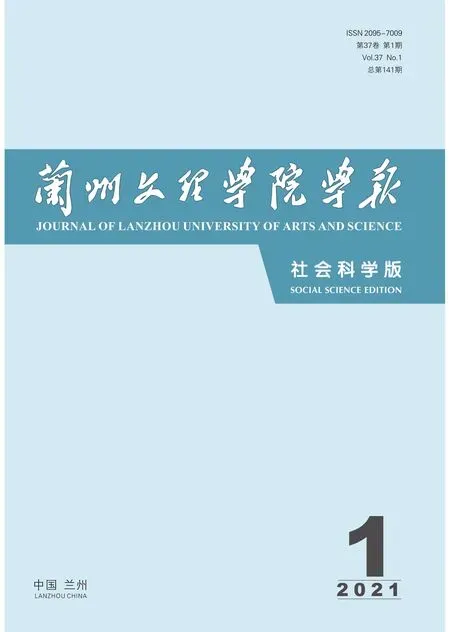论史部时令类典籍的独立及其原因
代 金 通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时令是按季节随时制定的政令,《月令》是上古时代这种时间观念的文本表达。李零先生认为时令是古人式图与原始思维的反映[1]127,葛兆光先生则将其归入与“天”有关的方术[2]2。余欣、周金泰先生认为:“时令上可为天子提供施政纲领,下可为四民提供生活指导,是集国家权威性、礼仪神圣性及民众世俗性于一体的复合知识。”[3]58诚如几位先生所言,时令知识包含多重内容,不仅具有较强的仪式性,也具有指导四民生活的实际功用。因时间知识在调节生产生活上的巨大作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对岁时民俗与节日的记述,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岁时月令文献。
一、时令类典籍的渊源
中国古代的时令文献发端甚早,《夏小正》即是上古时期前人对于物候历法与观象授时知识进行整合而产生的一部以记录动植物的物候为主的月令文献。笔者试按物候、天象、农事与社会四个类别对《夏小正》所载之内容进行分类,以探析其中所蕴含的时间观念。
《夏小正》折射出当时的时间观念较为朴素,以随时间流转而变化的物候,运行有常的天象作为时间的标尺,按照月份安排社会层面的活动与农事,未掺入关于五行的内容,这样的时间仅是一种具有标度意义的物候时间[4]154~155。
然而《礼记·月令》的内容则相对复杂的多,该篇依照春夏秋冬四时,再将四时分为孟仲季三月。试以孟春之月为例来探析该篇的内容: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眸,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民其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5]399~421。

物候天象农事社会一月启蛰。鹰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时有俊风。田鼠出。寒日涤冻涂。囿有见韭。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鞠则见。初昏参中。农纬厥来。初岁祭耒始用畅。农率均田。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獭祭鱼。鸡桴粥。二月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睇。有鸣仓庚。祭鲔。往耰黍。荣堇菜蘩。荣芸时有见稊始收。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士女。丁亥万用入学。剥蝉。三月越有小旱。螜则鸣。田鼠化为鴽。鸣鸩。拂桐芭。参则伏。摄桑萎杨。(羊韦)羊。采识。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颁冰。
可以看出,这一部分依照星象、太阳行度、朝暮星辰位置、天干、帝神、五虫、音律、成数、味臭、祭祀、物候、天子明堂位、礼器服制、天子命事与政令、时令变异与灾异告诫的次序以系时纪事。许迪先生指出:“‘月’为天时物候,‘令’为祭祀与政事,所以‘月令’者,即是将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时、五行、鬼神等加以关联,而最终归结到各种人事与政令上,使以物候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与祭祀、政令等社会人事成为有机互动的生命共同体,可谓‘观象于天,取法于地’。”[4]156
《礼记·月令》以十二月份为叙述框架,逐月安排活动,与《夏小正》按月叙述的框架相同,当是以《夏小正》为基础写成的。何以《夏小正》会演变为如此复杂的《礼记·月令》?这当与阴阳五行思想有关。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思想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此一时段,中国的先民们将世界的根本秩序归因为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因此,他们开始采用阴阳五行思想对传统的时间安排叙述进行系统的整饬,《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等篇章便是阴阳、五行结合以说明四时变化的尝试,《吕氏春秋·十二纪》则在此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整合[6]1~52。之后成书的《月令》略删《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部分内容,经马融整理进入《礼记》之中[7]72~81。《礼记》在后世成为儒家经典系统之一,《月令》篇也因《礼记》的流传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与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在秦汉时代曾作为时间规范普遍推行。
自然时序在掺入了阴阳五行思想之后,成为神秘威严的宇宙律令,王者依托神秘的“天时”,从治政的角度规定着人们的时间生活;而在帝王明堂月令制度之下,流动的自然时间转变为国家政治与社会人事活动的时间指南与规范,《礼记·月令》正是王官时代的时间表述,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制时间[8]123~141。正如冯友兰指出,在《月令》中:“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所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因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时间的架子,也是一个空间的架子,总起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9]437
尽管月令在中古以后失去了神圣的时间指导意味,但这种时间规范性的文献在后世却不断出现,如隋代的《玉烛宝典》、唐代的《御删定礼记月令》《唐月令注》、宋代的《国朝时令》、清代乾隆时期的《御定月令辑要》等。此外,诸多儒士大夫也仿照《月令》编纂了诸多文献,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宋周守忠的《养生月览》、明冯应京的《月令广义》、清李光地的《月令辑要》等,这些文献或是专于记录月份的养生行为,或是汇编古代的月令条文。这些按照月令“以时系事”模式而编纂成的文献形成了一个“官方时令”的文献传统。
二、时令类典籍的目录学独立
关于时令类目的设立时间,前人已有相关探讨。陈振孙认为始于《中兴馆阁书目》,《宋中兴国史艺文志》、李致忠先生《三目类叙释评》等从其说;姚名达先生则认为岁时与时令同为一类,“岁时”始于《崇文总目》,张子侠、张永瑾、何发延、徐有富等先生皆因袭其说。两种观点在目录学界皆有影响,但是两说皆值得商榷,在史部设立时令类的做法较早见于《龙图阁书目》,其史传阁下之“岁时类”即为“时令类”之权舆。
《宋史·艺文志》载:“杜镐《龙图阁书目》七卷。”[10]5146其书虽已亡佚,但是在《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都有记述,其基本分类情况仍可考知。《玉海》卷二十七记载了景德二年真宗幸龙图阁阅书一事,此条详细记载了各阁所藏书之卷数与阁藏书籍的分类。
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龙阁,阅太宗御书,观诸阁书画。阁藏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总五千一百十五卷轴册。下列六阁:经典总三千三百四十一卷(目录三十卷,正经、经解、训诂、小学、仪注、乐书。),史传总七千二百五十八卷(目录四百四十二卷,正史、编年、杂史、史抄、故事、职官、传记、岁时、刑法、谱牒、地理、伪史。),子书总八千四百八十九卷(儒家、道书、释书、子书、类书、小说、算术、医书。),文集总七千一百八卷(别集、总集。),天文总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兵书、历书、天文、占书、六壬、遁甲、太一、气神、相书、卜筮、地理、二宅、三命、选日、杂录。),图画总七百一轴卷册(古画上中品、新画上品。又古贤墨迹总二百六十六卷)[11]872。
《龙图阁书目》采用了独特的分类法,多有创新之处。“这些革新建立在唐宋社会学术思想急剧转型的基础上,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较大深远影响,通常我们以为由《崇文总目》开创的一些类例模式,实际上都是由此目所创立。从这个角度上说,《龙图阁书目》标志着宋代目录学的开始。”[12]169《龙图阁书目》在相对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的史传阁下开创性地设立了“岁时”一类。《龙图阁书目》成书于景德二年(1005年),而《崇文总目》则成书于景祐元年(1034年),可见时令类目当较早的设置于《龙图阁书目》。
时令类目何以在《龙图阁书目》中立类?乔好勤先生认为:“这是与中国古代农本思想、与北宋早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一致的。”[13]186李致忠先生认为,这是宋代目录学家注意到时令类文献的史学价值[14]184。徐有富先生认为:“这些书之内容上自国家典制,下至民间风俗,不专限于农事,隶于农家,实有不妥。故自《中兴馆阁书目》便一改前辙,于史部别立‘时令类’,以突现时令之书的丰富内容。”[15]306~307
三、时令类目独立的原因
(一)农业社会对于岁时知识的依赖
我国地处东半球,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西南距印度洋不远。国土幅员辽阔,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温度带。又因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季风气候明显,大部分地区受到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夏季风的影响,下半年雨热同期,温度和水分条件良好,为发展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这种气候特征也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研究表明,距今一万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交替阶段,我国大地上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主要劳动对象,依靠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来取得产品。
为了获得良好的收成,满足生存的需要,先民们必须对动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进行探索,对其生长与周围天文地理等自然环境进行细致的观察、思考和总结。人们直接观察到了某些动物草木的“生老病死”与气候冷暖变化有一定联系,与所种植的农作物共同变化,因而通过这些动植物的变化便能大致了解气候变化的脉动,进行农业生产的安排,于是产生了物候农时。在物候农时的基础上,先民们将此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与天象变化联系起来,观察到日影长短、昼夜盈缩、星宿的出没及在天空中位置的变化,将这些与一年气候的寒暖变化相结合,进而进一步以天象变化来确定四季变化,指导农业生产。到黄帝时代,诞生了最早的天文历。《史记·历书》载:“黄帝考定星历。”[16]1256当时的群落中出现了负责“占日”“占月”“占星气”和“造历”的专门人员,促进天文历的发展。
到帝尧时代,部落联盟扩大,设立“羲和之官”。同时岁时作为先民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正因此,岁时知识自然不能只为官方垄断,需要向社会民众普及,故而差遣一批专职天文人员分赴各地,向四方传播岁时知识,以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质性的指导作用。顾炎武所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17]1725即可看为岁时知识播布传递的结果。对于先民们编法制历,柳诒徵先生有言:
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躔度微差,无关大体。故觉天道远而人道迩,不汲汲于推步测验之术。不知邃古以来,万世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苟无法以贯通天人,则在在皆表枘凿。故古之圣哲,殚精竭虑,绵祀万年,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之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其艰苦愤悱,史虽不传,而以其时代推之,足知其常耗无穷之心力。吾侪生千百世后,日食其赐而不知,殊无以谢先民也[18]44。
进入夏代,从事天文历法的人员进一步专业化,将过去分散、零星的物候农时和观象授时知识加以收集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地观察计算,制订出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历《夏小正》。商代虽然没有像《夏小正》一样的月令类文献传世,但是商代农事与商代历法息息相关,不同的月份应有相应的农事安排[19]16。
周代祖先原以农艺见长,相传其祖先后稷生下不久,就能种植大豆、谷子、麻、麦、瓜等农作物,后来又教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使农作物生长良好。至周武王建立周王朝的时代,仍非常重视农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正是在西周时期确立了四分历与十九年七闰法,创立了二十八宿,逐渐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并形成了《诗·豳风·七月》和《月令》等月令类文献[20]3~25。
值得注意的是,因农业自诞生以来一直在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部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农业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需要能够不违农时,准确的把握季节时令的变化,以按时生产;土地的所有者为获取更多的收益,也必然希望能够对一年中的生产活动进行精密的安排,这就需要对一年的生产规划和逐月安排生产的进程予以关注[21]5。因而岁时知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被倚重与被依赖的位置,这使得“一方面,时人不断将当下的岁时知识和有关事象记述下来成为新的文本,另一方面,又不断有人对先前的相关记述进行抄纂、编述、阐释或引用,并形成新的文本”[22]42。
这样的文本至北宋初年已有一定规模。我们可以以《崇文总目》史部岁时类、《中兴馆阁书目》史部时令类、《直斋书录解题》史部时令类为例一探成书于北宋之前的时令类典籍的数量。三目此类计收《夏小正》《月令章句》《荆楚岁时记》《锦带》《玉烛宝典》《孙氏千金月令》《保生月录》《金谷园记》《四时纂要》《岁华纪丽》《四序总要》《四时录》《秦中岁时记》《周书月令》《月令小疏》《十二月纂要》《齐人月令》《唐玄宗删定礼记月令》《注解月令》《咸镐故事》《岁时广记》(徐锴)、《国朝时令》《国朝时令集解》《时鉴新书》《皇朝岁时杂咏》《备阅(注)时令》《岁时杂记》二十七部典籍,而其中除去《国朝时令》《国朝时令集解》《时鉴新书》《皇朝岁时杂咏》《备阅(注)时令》《岁时杂记》六书成书于天水一朝以外,其余二十一部均成书于北宋之前,此类文献虽然不能多至称为“大国”的程度,但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二)北宋初年的重农业、重农时
时令类文献数量的增多是设立“岁时类”的文献基础,而宋初重农业重农时的政策、对于典籍搜集整理的重视也是“岁时类”单独立类的重要现实条件。
北宋承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混战的局面而立,北宋初期的帝王们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看作重要的事务。“国家每下诏令,必以劝农为先。”[23]1129建隆三年(962年)正月,宋太祖下《赐郡国长吏劝农诏》曰:“诏郡国长吏劝农播种。”[24]658乾德二年(964年)春,再下《劝农诏》[24]658。两年后,又再下《劝栽植开垦诏》,强调:“庶几畎亩之间,各务耕耘之业”,并声明“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不征收荒田的税,以此来调动人们开荒拓植的积极性,改变五代以来“围桑柘以议蚕租,括田畴以足征赋”的局面。对于能够招复在逃、劝课栽植的诸县令佐也进行奖赏,“旧减一选者,更加一阶”[24]658。
太宗继承乃兄重农政策,设置农师指导生产[25]807。至道二年(996年),设置劝农使。为了使地方官积极推进重农政策的落实,太宗还将“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与“催科不扰,税赋无陷失”及户口的增加等都作为考核知州政绩的重要内容[26]3722。
宋真宗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在位期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诸如保护耕牛、引进优良作物占城稻、刊印农书等,为北宋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了便于百姓垦田,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年)诏:“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25]1307“以兵罢,民始务农创什器,遂权除生熟铁渡河之禁。”[10]4162景德三年(1006年)设置劝农使,并根据劝勉农事的政绩决定官员的奖惩,进而达到催促官员重视农业生产的效果。
帝王发布诏令并非难事,其效果如何,关键在于上行下达,落到基层实行要靠各级地方官员的执行。北宋前三帝的重农诏书,必然有些变成了纸上谈兵,未能发挥激励劝勉的作用。但是帝王屡发布诏令,显示出帝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会对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将农政效果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依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级官员尽心于农事。
此外,北宋初期几任帝王也多次强调农业生产不能违背农时,禁止在农忙时节征调农民服徭役。真宗曾屡次强调尊重农时,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自京城至永安沿路州县,因为修建皇后陵园的限期将至,官吏征调农民修道,真宗了解后认为:“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三,至时量以军卒给役。”[25]1457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乙未,真宗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今每岁十月至正月以旬休日召集校阅,免夺农时。”[25]1594皇帝关心农时,臣僚也尽心于遵守农时。天禧元年(1017年)二月乙未,宰臣王旦说:“缘路州县调夫治道。臣以方春农事初起,悉已罢遣。”[25]2045~2046同年十一月壬寅,真宗至太一宫,当时大雪盈尺,他对大臣们说:“兹固丰稔之兆,但虑民力未充,失于播种,卿等其设法赈劝,毋遗地利。”[10]163告诉臣子们要积极督促,以免百姓因耕种误时而影响生产的进行。仁宗时也曾下诏重视农时,庆历二年(1042年)八月乙酉,仁宗下诏:“河北诸路州军,自修城籍强壮、刺义勇,颇妨农时,应见役去除,并令放免。”[25]3288北宋帝王屡下诏令不违农时,显示出对于农时和农业生产的重视。
(三)北宋初年的蒐书、藏书与校勘
宋初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国家藏书总数不过一万二千余卷,宋初统治者为彰显国家之盛,稽古右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采取了诸多措施充实国家藏书。
其一,接受前朝及割据政权藏书。宋朝承后周而立,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周朝藏书。而五代诸多的割据政权,凡据富庶之地,都能聚集典籍。因而宋初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政府也将南方诸国的图籍收归中央。如:“太祖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26]2237又如:“(乾德)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书经籍印篆赴闕。至四年五月,逢吉以伪蜀图书法物来上。其法物不中度,悉命毁之;图书付史馆。”[26]2237
其二,宋朝还通过诏求图籍的方式蒐集图书。诏求图书,就是利用政权力量,采取适当的奖励办法征集图籍的方式。即所谓:“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27]1300私家藏书家,在这种情况下,也迫于无奈,献出自己的藏书,一来可窥得入仕门径,争取功名,甚至得到皇帝的赏识;二来献书也可以获得政府的赏赐,对于士人来说莫不是无上的荣光。至于赏赐的丰薄,主要依据政府当时的财力和图书本身的价值来确定。

年代[28]47-49献书情况赏赐情况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凡献书者送学士院考试,堪称馆职者,具以闻名。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三百卷以上宋学士院考试,选任馆职;不堪任者,量才安排。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三百卷以上赐给千钱,量才求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凡献书者进纳入官,优给价值;若不愿得官与钱,赐给御书石本。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赐给出身、酬奖,若不亲儒墨,即与班行内安排。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五百卷以上优其赐,能可采者,别奏候旨。
其三,编修新著。利用馆阁藏书编修新著,也是宋代馆阁藏书的重要特色。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正月编《唐会要》一百卷,三月编《三礼新图》二十卷,八月编《周世宗实录》四十卷,乾德元年(963年)七月编《刑统》三十卷、《五代会要》,开宝六年(973年)四月编《开宝通礼》二百卷,开宝七年(974)编《五代史》一百五十卷,都入藏馆阁,这仅是太祖一朝所编修。宋太宗时四方太平,修文止戈,三馆秘阁基本上聚集了天下图籍,宋代闻名于世的四大部书,有三部皆是太宗朝所编,《册府元龟》是真宗朝编撰的,它们的编纂反映出北宋初年政府藏书的丰富,同时这些典籍也充实了北宋的政府藏书。
经过北宋前三帝的不断蒐书,北宋馆阁藏书不断增加。根据相关史料,北宋前三帝时期馆阁的藏书量大致为:太祖建隆初年(约960年)三馆藏书一万二千余卷[29]251。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继位,太平三年(978年)建成三馆,三馆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30]393。宋真宗景德年间(约1004年至1008年)昭文馆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卷,史馆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卷,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30]394~395。而三朝馆阁藏书的总量则达三千三百二十七部,计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10]5033。
北宋藏书之府虽有多处,但是整理官书的人员,却仅仅设立于崇文院。而具体从事官书整理工作者,不止有修撰、检讨、校勘、校理、直馆、直院以及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等,两制学士及其他官吏也被选调来做整理工作。而其地点则一律在崇文院,崇文院负责秘阁图书的整理和校勘,并且负责内府藏书的整理。因而,崇文院既是当时的国家藏书中心,又是国家的官书整理中心[31]34。
北宋初期三帝都有一定整理官书的活动,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史馆新定书目》四卷[10]5147。又据王应麟《玉海》卷五二引《国史志》云:“乾德六年,《史馆新定书目》四卷。”[11]877这说明太祖时已有整理三馆图书的活动,而且已经编制了藏书目录。太宗朝宇内基本统一,注意力转向内部,在三馆之外又兴建秘阁。“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画百四十轴,尽付秘阁。”[26]2778前文述及太宗朝也编修了大量官书,真宗称太宗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则刊广疏于九经,校缺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11]970~971应该说这大体上反映出太宗朝整理编纂官书的成效。及至真宗时期,馆阁藏书开始转化为内府藏书。据《宋史·艺文志》,咸平二年(999年)时:“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10]5032至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直秘阁黄夷简等上书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二卷,称校勘新写定御览书籍[11]870。景德二年(1004年)四月,真宗说:“龙图阁书籍屡经校雠,最为精详,已传写一本,置太清楼。”[11]872可见,三馆秘阁之藏书经校勘,转换为太清楼、龙图阁等内府藏书。以上可见,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时期对于图书的收集与内府馆阁藏书的整理,而这些藏书经过整理,不仅成为精校精勘的善本,而且为了利于校勘,宋代馆臣必然要对藏书进行一定的分类,这样的分类为《龙图阁书目》创新图书分类法打下了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对于时令类典籍的渊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自《夏小正》诞生以来,时令文献屡有发展,然而及至宋代,该类文献始终未能在古典目录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书于景德二年(1005年)的《龙图阁书目》当是时令类典籍独立的滥觞,彼时彼刻,时令类典籍终于获得了独立的目录学位置与学术地位。宋初大量蒐书、藏书,并对图书进行精校、精勘,这一过程对于藏书的分类有重大意义,也为《龙图阁书目》开启新的图书分类法打下了学术基础。而历代以来的重农政策,尤其是北宋初年,皇家对于农业、农时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使当时的学者必然也重视农业、农时。编纂《龙图阁书目》的杜镐、戚纶等儒士大夫,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在为龙图阁编纂藏书目录时,便应时而为的设置了“岁时类”,以备帝王咨询查阅,同时也是对时令类文献增多的合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