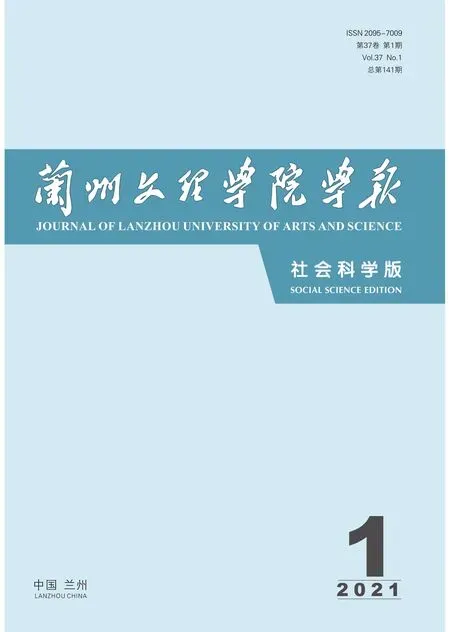唐代丝路审美文化熔铸研究
——以西安何家村窖藏典型金银器为例
王 辰 竹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张骞凿空西域”常被认定为丝绸之路的初始,其意义实则偏重于汉朝与西域诸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丝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和物质的对话远先于此。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上延续千年的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融通之路,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当时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于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唐代金银器作为丝路审美文化的物质性载体,始终以“未完成”和“不完整”的姿态向社会开放,是大唐盛世和丝绸之路诸文化交流和对话的物质见证。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发现有三批,即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和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1]。其中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大多数属于唐鼎盛时期,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可以说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陈列于博物馆中的金银器是已死的辉煌的过去,但若将它们镶嵌回特定的空间,它们就会成为那个空间的一部分。此时的金银器便不再是单纯的器物,而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与意义载体,反映了盛唐时期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和社会背景。本文选取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鼎盛时期的典型金银器: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鸳鸯莲瓣纹金碗、银盒一组、葡萄龙凤纹银碗、唐代金银带把杯一组,探讨唐代金银器在内外双向开放交流过程中金银器上的工艺、纹饰和审美观念方面的熔铸共生,对丝路沿线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智慧结晶的深入挖掘,亦是探索物质交流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一、金银器物构造工艺的糅合熔铸
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原材料或工艺的缺乏都会阻碍一些形式的出现。唐初时期,金银制造业本身并不发达,器皿较少,发展较慢。秦代以前的金银工艺主要包括熔炼、范铸、焊接、镶嵌、鎏金等,但仍基本处在青铜器铸造工艺范围内;到了汉代,金银工艺已渐渐脱离青铜工艺传统,金珠焊缀技术、掐丝、錾花等工艺的运用也日渐独立[1]24。自南北朝始,进入中原的马上民族将贵金属铸造工艺和审美需求一并带入,对中原的金银器工艺产生初步影响。唐初,官府作坊主要传承了南北朝以来北方系统的金银制作工艺,而北方系统的金银工艺一直深受西方影响,不但有西方输入的器物和技术,而且金银工匠中有一大批来自西方[1]20。背靠雄厚的社会物质财富,本土与西域的金银制造工艺随丝路的融通不断结合熔融,中国自行制造的金银器皿渐次焕发光彩,至唐朝达到巅峰。
唐代边陲外族以承认中国皇帝为“天可汗”的方式,在名义上归属中原,开放的天下秩序使唐朝的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弹性,为丝路商贸的畅通提供了前提条件:来自西亚、中亚的金银器在唐初随着商贸大量涌入,造型独特,纹饰新颖,满足了包容开放的唐王朝求新的审美需求及高层贵族奢靡猎奇之风;丝路的畅通也使大量外族人内迁,其中不乏金银器工匠。各族和平共处使中原与丝路接壤的边缘地带成为了外来技术与本土技法融汇贯通的空间,也为工艺的熔铸改进创造可能。
唐代金银工艺的具体记载虽已佚失,但从明代人引用的《唐六典》中提及的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十四种分类可见曾经辉煌[2]。齐东方先生在对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进行研究,将金银工艺用现代技术用语分类并概括:打作与锤揲、鎏金与镀金、掐丝与金银珠焊缀、钑镂、錾刻和镂空[3]。唐代金银工艺充分利用金银材料质地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物质材料的特性与精湛工艺结合,实现了金银器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目标。

图1①

图2②
体现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当属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内层机环、外层机环、金香盂之间用直径0.1厘米的银铆钉分别在90°的位置连接,连接时各层之间垫有外径0.2厘米、孔径0.15厘米的管形垫片,这样各轴既转动灵活,又都互相垂直,使里面的香盂始终保持中心向下[1]224。香囊科学地利用了现代所称之的“陀螺仪技术”——多环嵌套,多轴稳定,重心中置,自然平衡。无论怎样转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香料稳稳置于内而不会撒落,十分精妙。香囊外壳运用錾刻手法,在设计的花纹中将不需要的部分去掉,以形成天然的滤香口,外壳精巧俏丽,又满足日常实用的需求。香囊盖顶上部铆接有环钮,上套接链条,其上连接环钩弯曲,这样既可悬挂室内,又可作为装饰品佩带于身。白居易在《青毡帐二十韵》中将香囊的用法交代得颇为清楚:“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寒冷的冬日里,这位大诗人携带银香囊,住进圆顶青毡帐内避寒。他将银香囊吊挂在帐顶下,炭火的红光从精致的镂空花纹里隐隐透出,不断散逸香缕。外来工艺与本土技术的融通对唐代的金银工艺也有极大的推进。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1]109。该碗整体锤揲成型,又在碗体腹部锤揲出略微起伏的双层莲瓣。莲瓣中的纹饰细密,錾刻在莲瓣间的奔跑的动物和飞舞的珍禽,如同线条素描,艳丽夺目。圈足和碗底应用了传统焊接技术,底部联珠纹金珠规整,大小均匀。整件器物华美富丽,宛如盛放的金莲。

图3③

图4④
丝路文化交流频繁引入的大量外来器物和技法,对传统工艺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我国锤揲工艺历史悠久,但更多处于从属地位。在鸳鸯莲瓣纹金碗制造过程中主要采用的锤揲工艺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技法,其中许多源自波斯、中亚和拜占庭。锤揲,即在软物或置于模具上衬以金银片锤击成型,器型与图案均可。唐代对金银器的巨大需求,使经济实用的锤揲技术的运用达到极致。
物的存在不仅是由物质属性来界定的,而且是由其在技术、文化、经济、政治等社会话语所规定的叙事和逻辑系统中的位置所界定的[4]。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和亮丽的天然色泽使其注定成为工艺品的良好材料,但使金银器璀璨生辉的则是技术本身。在物质主义的世界中,技术是一种“最常见的常见之物”,技术的进步能使我们面对和克服遇到的时间、空间和自然元素等任何问题,使我们程式化地去完成和实现自身难以完成的目标[4]110~111。在金银工艺的融会贯通中,西方金银工艺对唐朝的影响,以粟特地区最为重要,西亚的萨珊或东罗马的影响,大多通过粟特人转化而被唐代工匠所接受。锤揲技法在粟特的银器中极为常见,通常以凸瓣装饰的形式出现在器物上。5、6世纪时,粟特银器上的凸瓣分瓣多且细密,带有希腊装饰遗风;至7、8世纪,部分粟特银碗上的凸瓣慢慢接近莲瓣,而这种形状在传入中国时被唐代金银工匠吸收效仿并加以改进。与粟特银器相较而言,唐代金银器的凸瓣大多较平整,多为隐起图案,有的仅起分割装饰区域的作用,颇有“压地隐起华”之意。除鸳鸯莲瓣纹金碗外,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白鹤莲瓣纹弧腹银碗、白鹤缠枝银长杯等唐代绝大多数器物均由锤揲制造而成,器物中的纹样亦然。
自丝路传入的西方器物所具有的崭新样式和工艺,为唐王朝手工制造业注入全新的活力。工匠们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地学习外来工艺,最终变为己用。至开元盛世,位于安南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官员还兴“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5]——波斯僧不但带入新颖器皿,更引进西方先进的金银工艺并参与制作,极大地推进了唐代金银工艺的发展。正如佩尔斯所言:“物要有象征性意义的构造,要有故事线并能承担人的代言人的角色以获取社会生命;社会关系和实践反过来也需要具有物质基础以获得时空上的稳定性。”[4]185物的象征效力使精湛的金银工艺成为唐代文化秩序的重要部分。处于唐代时空的人们正是凭借精湛的工艺,尤其是在对金银器的纹饰的建构和塑造中,将丝路文化在物与物的糅合中熔铸升华。
二、金银器物纹饰审美的融通互鉴
装饰在金银器上的纹样属于附加性装饰,其本身具有独立的艺术意义,有一定的纯欣赏价值。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丝绸之路的通畅使西域文化不断与本土文化交汇融通,作为纹饰的艺术题材纷纷涌现并被匠人付诸实践; 生活的富足让普通民众有余力参与美的创造,对贵族阶层的审美情趣也有所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于丝路文化的交互影响中悄然建构,金银器的纹饰也在潜移默化中变得华美富丽。
唐代工匠追求奇巧,善于创新,将外来风格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熔铸成受到当时人们喜爱、反映人们审美情趣的新的纹样。除鸟兽等动物传统题材外,花鸟植物纹成了唐代装饰纹样主流。唐代金银器纹饰整体舒展大方,自由挥洒,富丽堂皇。纹样题材的变化也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变化轨迹。
在唐代金银器物上,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和谐共处,繁而有序,富有情趣。根据装饰部位,金银器纹饰可分为主题纹样和附属纹样。主题纹样装饰在器物的显著部分,非常醒目,直接体现装饰风格,主要包括忍冬纹、葡萄纹、缠枝纹、宝相花纹、团花纹、折枝纹、绶带纹以及莲叶纹;附属纹样饰于器物的口沿、底边、转角等处,展开后呈条带型,包括了联珠纹、三角纹、缠枝纹、绳索纹、卷云纹、云曲纹、半花纹、小花纹、叶瓣纹[3]131~158。唐代金银器大多采用通体装饰纹样,这些图像点缀、装饰着金银器物的空间,大多以满幅的、去中心化的、形式重复的布局,将完全等同或非常接近的因素编织在同一平面之上,运用节奏、对称、比例等抽象形式造就强烈的节奏与韵律,从而满足欣赏者视觉观感和审美需求。
唐代银盒大多带有纹饰,花纹与器型精巧结合。以何家村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为例,盒盖面中心錾刻一只口衔绶带的双翼平角牡鹿,环镜以一圈连心结,周围是八朵莲叶忍冬组成的石榴花结[1]130;盒底中心是一只凤鸟,该凤鸟头戴胜,嘴喙向下内勾(很像鹦鹉的嘴喙),喙衔长长的绶带。胸上挺,左右两翼向两侧舒展[6]。凤鸟周围是圆形连心结和八个忍冬花结,盒沿饰以流云飞鸟组成的二方连绩图案,花纹平錾,纹饰鎏金。

图5⑤

图6⑥
文化交流频繁的唐代,中原特色与西域风情紧密结合,装饰构图中常常闪现着外来纹样组织方式的身影。在何家村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上,正面的主纹是想象中的带翼之鹿。鹿在唐朝被视为纯善之兽,而为动物添翼的作风来自西亚,带有表示希望的含义[7];背面主纹为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之鸟。《说文·鸟部》有言:“凤,神鸟也……见者天下安宁。”[1]130翼鹿与凤鸟寓意吉祥,又均口衔绶带——在唐代,因“绶”“寿”同音,口衔绶带的祥瑞禽兽纹样带有长寿之意。主纹之外依次环绕了麦穗连心结和忍冬花结作为装饰。银盒上装饰的有翼动物如飞狮、天马、翼鹿,周围绕以麦穗纹圆框的作法在唐代并不流行,仅出现在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几件器物上[8]。这种纹饰被称为“徽章式纹样”,在萨珊银器上最为常见。银盒上出现这种纹样,显然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影响。在同批次的银盒中,鎏金飞狮纹银盒、鎏金犀牛宝相花纹银盒、鎏金翼鹿宝相花纹银盒等均有祥瑞的动物装饰在顶部或底部中心。“徽章式纹样”进入中原后逐渐受唐朝本土审美影响,首先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代之以唐人喜爱的宝相花类,有的银盒盒盖与底上动物和宝相花两种风格的纹样并存(如鎏金翼鹿宝相花纹银盒、鎏金鸳鸯纹银盒);稍晚一些的银盒,圆框中心则是一朵宝相花(如鎏金团花纹银盒),后又取消了圆框。八世纪中叶后,唐代金银器上基本不见这种徽章式装饰,转而被本土所喜爱的图像取代。鎏金鸳鸯纹银盒上纹饰的排列组合便是这一过程的体现——盒面上的鸳鸯与桃叶、忍冬、莲叶花结之间,还留有可以容纳绳索纹的空隙,应该是它消失不久,原来占有的空间还没有被他用[1]193。

图7⑦
饱含异域文化的纹饰元素随先进工艺一并传入,打造出具有生命力和动感的形体,显示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一过程不仅是金银器器物的交换,更有纹饰本身作为物质的对外开放与接纳。从物质诗学的角度言说,文化植根于社会,这使得文化本身就是物质实践。尽管无法独立于物质世界,但文化本身的物质性和文化生产的物质特性无可忽视。物质文化向来以叙事、符码和象征等形式呈现,这也使得作为符号的金银器纹饰必然具有象征意义。唐代金银器的纹饰造型与丝路上金银物质的流通、艺术文物的接触紧密相关,植物、动物纹样写实逼真、种类繁多,且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纹饰装饰随着文化交流发生相应的改变。
唐代社会对外来动植物接受和再创造,包括造型上改造为唐代民众更习惯接受的形式以及纹样寓意的转化。 唐代金银器上的写实性图像——如狮子,自汉代以来长期是外来朝贡的动物,一向被认为具有祥瑞之意。 受到印度和吐蕃艺术的影响,其形态往往为卷发,呈现“狗化”趋势。 南北朝时期,佛教等外来文化的进入使具有宗教色彩的莲花、忍冬纹样作为新颖的艺术题材进入中国。至唐代,植物纹和动物纹摆脱了宗教信仰等约束,在器物上大量出现。除忍冬和莲花纹的大量使用,大量花卉题材如牡丹、芙蓉、茉莉等层出不穷, 华丽饱满而富有生气的卷草纹和团花纹尤其体现唐代纹饰繁复的特点。 外来动植物纹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融合,自然而然成为中华文化语境的一部分,亦是丝路审美文化熔融互通的具体表现。
包容多元的唐代文化推动了金银器纹饰艺术的发展,而纹饰艺术的不断发展也令作为物质性文本的唐代金银器发展繁荣,成为适宜观赏的艺术品。丝路时空中,纹饰不是静止的,其演变瞬时和当下都在发生。纹饰时间和空间中向其他文化开放,不断生成、变化的文化寓意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异域文化衔接熔融,作为物质文化的唐代金银器,尝试解读其纹饰创造过程和演变的可能性,无疑展现了唐代审美优越性和经典性,使丝路文化大放异彩。
三、器物融通与审美文化的交融互铸
作为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何家村金银器展示了唐代文化强大的包容力,外来的器形、纹饰、中西结合混搭的装饰风格兼容并蓄,实则为丝路审美文化的交融互生的体现。金银器器型与纹饰的变化体现了唐代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融通,是某个文化片段或观念意识的记录,反映了唐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唐代金银器是丝路不同文化交互熔融的艺术结晶,其文化含义和蕴含观念不断生成延发, 更多的时候不是纯粹的审美观念的交互,而是从金银器本身出发,追溯、探讨其在那个时代的自然形态、物质形态、技术形态、社会形态和人的思想观念形态综合生成发展。 绚丽夺目的金银器不再单纯是反映文化交流的历史的物质,其本身就是历史。
于马上民族而言,金银器象征权力与财富。马上民族将对金银器的热爱带入中原,唐代皇室贵族延续了这一狂热追求。这不仅因为金银器昂贵的价值和华美的外观,还与汉代以来对金银所持有的神秘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太平御览》珍宝部银条载:“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李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不死。’”[9]汉代方士们推崇的“金银为食器不死”的长生之术令追求金银器在唐朝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尽管价值崇拜与命运向往结合使得金银器皿风靡,但金银器并非人人有资格使用。《唐律疏议》明确了纯金食器的使用要求:“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10],明确金器为受法律规定的等级标志;《唐会要》杂录亦载:“神龙二年(706)九月,仪制令著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11],也再一次强调了银器的使用等级。对金银器使用的法律规定和一再要求,使世俗权力在金银器上有所反映,深切影响了当时对器物和纹饰的审美。在何家村窖藏银器中,一件7世纪后半叶制作的葡萄龙凤纹银碗引起学者注意。制造龙凤之瑞来粉饰太平或自应天命向来为历朝统治者所青睐。但本件银碗凤在碗心居上,龙在碗底居下,这使学者不得不考虑武则天称帝的背景。据《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高宗上元三年(675),“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武则天抓住这个“凤瑞”,改元“仪凤”;高宗死后,武则天称制,头一年就把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1]172。武则天煞费苦心地以凤自比,不应只在政治活动上有反映,物质文化上应有证据。故有学者推断,此物为当时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亦是武则天称帝时权力的象征。
社会观念的更迭对唐代金银器审美特性的影响不容忽视。熔铸了中亚、西亚复杂的历史背景,这注定了金银器本身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丝绸之路被谈及时,往往会被默认为是地理意义上的点对点,面到面的路线,呈现的是平面式的地图,而丝路文化所构成的活态空间却被忽视。“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12]唐代金银器是以固定形态保存和遗留的丝路文化,精湛工艺在器型和纹饰上所留下的痕迹难以用文字抒写,其本身构成了一种活态文化(lived culture),停留在唐代的时光中。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从金银器物质本身出发,借助先进的科技和技术不断加以发掘、整理、分析和阐释,将对金银器的审美在唐代语境内进行重构。
丝绸之路本质上是文化存在生发的空间,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尤其需要重视。宗教往往构成艺术的主题和动力,这使得艺术与宗教往往相伴相生。除佛教在唐代得到极大发展外,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也随外族人深入内地得到了广泛普及。唐代皇室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使得唐代艺术也呈现兼容并包的特点。正如文化组成是包括在人的组成之中,个体组成实则也包括在文化组成之中,文化的交融互铸使得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引导在丝路共同体上的人们逐渐形成相似的审美观,为丝路审美文化进一步的交流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8⑧

图9⑨
丝路空间中,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使其在实用和观赏上更加符合唐代本土的需求,是唐代接受外来文化的特点。外来文化的渗入推进金银器新的器类和器型出现,无疑是丝路审美文化交融的展现。在考古学领域里,器物形态的相似往往是归为同一类型的理由。金银带把杯的演变渊源在中国传统中近乎于无,却在粟特器物中常见,故对唐代金银带把杯的研究往往纳入了唐朝与粟特的文化交流中来考虑。 游走于欧亚大陆上的粟特人以经商和手工业闻名,粟特人东迁入唐,工艺与文化的双向融入为唐代金银器的创新创造了基础。粟特地区的带把杯迄今为止只有银器出土,但唐代带把杯金银器均有,造型与粟特各种带把杯基本相同,只是把手样式更丰富。中国境内出土的带把杯包含了输入品、仿造品、更有外来影响下的创新作品。在何家村出土的一组带把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伎乐纹银八棱金杯、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便是体现粟特特色与唐风逐渐融合的产物。

图10⑩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素面罐形带把银杯与其他大量的唐代金银器风格迥异,却与粟特7世纪至8世纪流行器型类似,被认为是粟特输入品;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伎乐纹银八棱金杯以中国传统的铸造工艺做成,但因杯底焊接的联珠纹样式及其上具有浓烈西域风格伎乐纹饰,且人物的浮雕式做法为西方特点,被认为是在粟特工匠的参与下,对粟特带把杯较为忠实的模仿;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息更为浓厚的则是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唐代典型的八曲葵口和环底碗形,指垫上的鹿与指环吸收粟特银器的特点,内底的摩羯纹又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狩猎图中的猎人又是突厥人的形象,仕女游乐又是盛唐时期的典型题材,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特点[1]67。年代更晚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杯体为筒形,其杯把不同于前几个带把杯:用银条做成的“6”字环形,指垫直接从环形把上部向外伸出,并微向上翘,无装饰,无指板这一特点不见于粟特和西方银器,却在汉晋时期的器物上有所出现[1]42。此带把杯的形制及其装饰具有明显的唐风,被认为出自唐代工匠之手。
从传统类型学的研究出发,我们常常难以捕捉制造者及产地的时空的细节。丝路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交往使风格交融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传统手工业时代,每一件器物都是单独制造,同类型器物很难有全然一样的造型,而文化背景各异的工匠的迁徙则使器物的器型与纹饰拥有更加复杂的底蕴。唐代金银带把杯形态的变化是唐代与西域在审美文化方面的融通与创新过程的显现,在考察其器型变化时,工匠或艺术家的自我发挥以及创造性发现,区域间的相互影响和历史演进,对深入探讨丝路文化的熔铸生成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后来者了解金银器背后的制造历史,了解审美的需求变化对制造工艺影响。
在丝路文化领域中,人们所展示的审美偏好实则基于丝路文化间交流、碰撞后所产生的审美价值的共鸣,这使得丝路审美文化具有活态性的特征。唐代金银器作为丝路审美文化的物质性载体,其本身不是丝绸之路各门艺术的简单相加组合,也并非丝路艺术现象与成果的静态呈现和归纳,而是丝路多元文化在交融互渗中持续产生“审美的附加值”,生成新的审美意义,最终呈现出符合丝路沿线多元文化的审美形态和文化含义。
四、结语
丝路文化作为一种由不同国家、民族和个体所共同参与和建设的文化综合体,其在空间中熔铸生发的文化心理需要和审美价值,势必在物质文化的熔融互通中展示。作为唐代物质文化的代表,何家村金银器在丝路空间与多种文化和合熔铸,其在丝路文化时空中的意义远超物质财富本身。若将金银器当做特殊的“文本”,其向内和向外双向开放的交换过程,让作为艺术作品的唐代金银器在反映物质世界各方面力量的影响更加有力,是丝路文化的熔铸生成的重要的见证。从何家村金银器出发,探索物质文化在“文明互鉴”和“人文化成”中的作用,必然为当今文化的和合给予更深刻的认知。
【注释】
①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影像图(外)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M].文物出版社,2003,第223页(以下注释均出自本书,仅在注后标志页码)。
②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透视图 第225页。
③鸳鸯莲瓣纹金碗影像图(外)第110页。
④鸳鸯莲瓣纹金碗影像图(底)第112页。
⑤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影像图(盖)第131页。
⑥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影像图(底)第132页。
⑦鎏金鸳鸯纹银盒影像图(盖)第194页。
⑧葡萄龙凤纹银碗透视图 第174页。
⑨葡萄龙凤纹银碗影像图(底)第173页。
⑩素面罐形带把银杯影像图(外)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