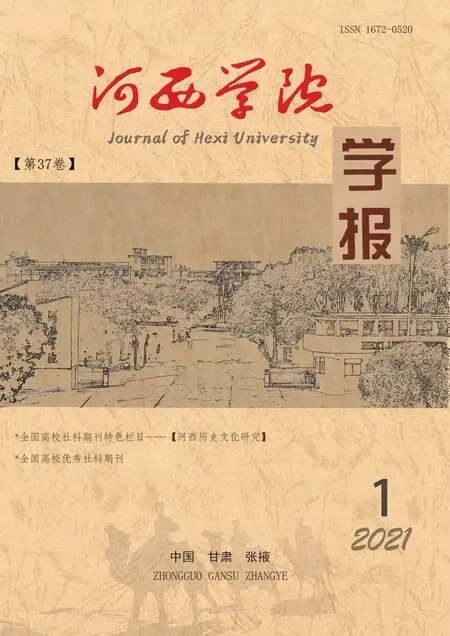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
——李学辉《国家坐骑》探析
马云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 合作 747000)
《国家坐骑》是武威作家李学辉继《末代紧皮手》和“小麦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品延续了李学辉以往的创作风格,以凉州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为核心,展现了河西走廊地区奇特而又浪漫的风俗习惯,以及善良、诚挚的乡村民众简单而又厚重的生命意义。但是,较之以往的作品,《国家坐骑》不再仅仅哀叹乡村文化的消逝,而是将已逝的乡村文化与国家民族大义相结合,显示出了作家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和创作格局。以“义马”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和以“义马”所象征的民族精神,共同担负和承载着中国西部乡村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在历史和文学的书写中人民似乎和国家息息相关,但是却又似乎很远,自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先生怀着对于国民深切的爱进行国民性批判,首先对于国民的精神和灵魂进行了剖析。其后也有很多的作家也不断的尝试写底层的民众,展示底层文化,但是都难以触及到底层民众的精神和灵魂。因此,在乡村文化逐渐衰落的今天,李学辉笔下“义马”这一搁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有了关照当下现实的时代意义。像李学辉《国家坐骑》这样既能立足地域文化,又能将地域民间信仰升华为国家大义的作品,足以显示出当代作家为时代书写,心怀民族国家的担当意识。
一、地理人文景观中的西部情怀
地理文化基因是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里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区域和生活经验,这些都对于作家的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每一个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作家更是如此。来自甘肃武威的作家李学辉就是一位以地域风貌为写作动力和写作源泉的作家,他以故乡凉州这一西部重镇作为自己情感表达和情感寄托的载体,创造出了独属于李学辉的文学空间-巴子营。凉州今名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下,这里云淡天高,山峦巍峨,平原肥沃,是西部戈壁沙漠上较为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带。寒冷的气候,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给西部打上了落后、贫穷与苦难的印记,以苍凉、辽远、悲壮、沉重、坚韧、虔诚为标志的西部精神,成为了西部文学书写的主题。就如诗人张子选所说:“我一直相信,有一种真实的西部面目,是与各种困难做斗争以求生存发展中培养起来的勇敢、刚毅、吃苦耐劳与自主精神,以及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不屈不挠、忠于友情的行为准则。这些,就是所谓的西部魅力之所在。”[1]28西部作家在书写时为了凸显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精神价值,他们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都会带上这样一种特殊的西部地域情怀。《国家坐骑》中李学辉对于西部的深情厚谊,体现在他对于故乡凉州地理景观和历史事件饱含深情的书写中。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凉州地势平坦辽阔,是西北最大堆积平原,自古就是控制三大高原和西域的中心城市;从历史沿革来讲,凉州一度是西北的军政、经济、文化中心;从族群构成来讲,凉州地处三大民族走廊之西北走廊中心地段,汉羌边界,因此形成了这里民风剽悍,悍不畏死的特点。并且,自古以来凉州精骑便横行天下,西晋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因此,马成了凉州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以此延伸出了马神信仰、马户头、马户们、圉人、相马师等一系列与马相关的人物群像,以及以马场、马户街、马神庙等与之相关的地理空间景观,这些现已消逝的文化群像在李学辉的《国家坐骑》中以“义马”为中心得以展现。
李学辉的作品都是以地理行政空间中的凉州为对象,建构出了“巴子营”这个标示性的文学空间。每一个乡土作家笔下的文学空间都是有其相对应的地理空间生成的,例如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乡、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等。李学辉以“义马”的诞生到义马的最终逝去,剪影似的为我们展现了巴子营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在《国家坐骑》中李学辉从不同侧面的描述了巴子营的自然风貌,文中以巴子营草场的草为对象展现了巴子营不同季节的美。“九月的巴子营,天稠的像韩骧妻子的奶汁。一到冬天,天若下雪,雪顶在草上,努力出一朵一朵的绒花。待到春风一拂,固有的草身一夜间变绿,绿出别样的一个春天。”[2]4作品中作者还为我们展现了马神庙、以及凉州的七寺、八庙、九台等人文地理景观。①七寺、八庙、九台体现了凉州地区佛道儒三教相融合的信仰形式。“巴子营”这一文学空间的塑造是李学辉展示西部重镇“凉州”的文学载体,同时也成为了李学辉表达西部情怀的情感寄托。
二、历史剪影中的乡土挽歌
李学辉对于西部的深情厚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凉州乡土文化的书写上。“地方叙事或地方色彩则是乡土文学的美学原则。地方色彩具有特别重要的叙事功能,不仅是文学想象其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还是文学建构其艺术魅力的特殊路径。它在为不同地域的作家提供文学书写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地方色彩的呈现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意义。”[2]64《国家坐骑》延续了他以往的乡土色彩,融合了流传于民间的历史事件,使他的作品在乡土奇异色彩之外又与大的历史社会背景相呼应,多了一丝历史的厚重。就如作者自己所言“2000年之前,我一直抱着“本土的乡土”不放,抒写的东西基本被人打上“乡土”的烙印。在发表若干小说后,自己突然醒悟了一点。我觉得自己抒写的乡土尽管有粗砺的诗意,但有些单薄,缺乏历史的支撑,于是我便翻看多年的“行走积累”,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在我心里激起了震撼。[3]《国家坐骑》围绕凉州地区的“马神”信仰展开,将反映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民间信仰和大时代相结合,使凉州的乡土文化与宏大的社会历史相碰撞,在时空的交织中展现出了一幅幅生动的西北生活图景,以历史的转折来推动故事中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不再局限于乡土文化和地方色彩的展现,更多了一种扩大历史空间和丰富历史文化的色彩。并且,作品中还涉及到了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审美价值,这也是李学辉《国家坐骑》较之以往乡土作品的突破。
“小说在本质上都是回忆性的,所叙述的在逻辑上皆是过去时态的事情,而最后一个是一个人或一件事或者一种生活,生产方式的完结也是属于过去时的,且由于是最后一个,所以抒发感慨和寄托情思的空间都变得更大,与小说回忆状态下的叙述本质恰好相吻合。大凡写最后一个的作家,都会有末世人情怀,或者说挽歌情怀,也就是说最后一个作为原型,可以和作家的考察联系起来。”[4]李学辉的人生经历和对于乡土的热爱铸就了他小说中的挽歌情调。李学辉把周末的时光变成了探求凉州野史的战场,他把这些民间野史融入了他所熟知的凉州,为我们建构出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富于神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乡土文化是李学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次聊天中,幽默的谈吐,爽朗的笑声让我对这个作家充满了好奇。谈论中他告诉我们,他至今保留着时不时回乡间劳作的习惯,他说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每次谈到凉州文化或是对于乡土的守护,这个看起来憨厚而其貌不扬的西北汉子眼睛里都仿佛透着神采。从李学辉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凉州作家深厚的乡土情结和故土情怀。他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更是将这种乡土文化消亡的惋惜之情,融入到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就如他的《国家坐骑》中的“义马”,最能体现作者的一种末世情怀,这一形象中既包含着作者对于马神信仰这一民间习俗消逝的惋惜,又有着一种在时代交替之际,国家危亡之时的一种精神消亡的悲叹之感。这些复杂的感情以及对于凉州民间文化的热爱杂乱的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作家真挚而强烈的挽歌情调。“挽歌情调是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挽歌性叙事往往更具有绵长的艺术魅力,它常常体现着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历史思考:批判与惋惜、同情与无奈、憎恶与向往常常交织并行。”[5]31现代生活中的丑陋和欲望与乡土生活的古朴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乡土如何抗拒,现代生活依然如期而至,因此美好的乡村回忆与充斥着焦虑与丑陋的都市在对比中,愈加显得美好。李学辉的小说以对于乡土的惋惜与眷恋记录着曾经盛行于凉州大地,以现在逐渐消亡的民俗活动为立足点,展现着在凉州大地上这些活态民俗的鲜活与生动。在这些已经消亡的民俗活动中展现的是底层民众顽强的生命力,以及他们朴素而又崇高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李学辉将自己对于乡土的热爱与眷恋融进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在《末代紧皮手》中,以挽歌的形式,记录了最后一位紧皮手余土地的故事,讲述了“紧皮手”这一职业的消亡,作品细致入微的描述了“末代紧皮手——余土地”他短暂的一生,以及他对于土地信仰的坚守。余土地的悲歌,何尝不是作者对于乡土文化衰落的哀叹。《国家坐骑》更是继承了《末代紧皮手》以乡土和民俗为主题风格,但是较之以往的作品而言更为恢弘大气。作者以时代更替为历史背景,描绘了边缘小城凉州特有的马神信仰,以沉重而悲凉的笔调写了最后一位“义马”奇特的人生经历。作品以“义马”的一生贯穿全文,围绕义马展示了义马周围这些为国家民族大义而献身的人物群像,最后小说以“义马”的死去,和盛大的祭祀仪式而告终,宣告着一种文化的消亡,宣告着一种信仰的消逝,就如文中李德铭所说:“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但是再也无法复制在这个时代消失的东西了。你我此生,可能也就睹此一回壮观景象了。”[1]228这些挽歌式的叙述中,蕴含着作者对于乡土文化逐渐消亡的悲叹和留恋。时代在变化,我们所熟悉和留恋的很多乡土文化都在逐渐消失,很多的作家,民俗文化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他们的“乡愁”,也都在以他们的形式保护和保存着民间文化。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李学辉的挽歌情怀似乎也有着历史的必然。
三、图绘边地民众的家国意识
在这部作品中,除了对于西部地理人文景观和乡土的描写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深切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杰缅季叶夫指出:“民族情感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民族性是个人终身的和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和心里滋味特性越强,民族情感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就越鲜明。”[6]在《国家坐骑》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和杰缅季叶夫所阐释的民族性一致,是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李学辉细致的为我们展现了历史更迭时期底层民众的家国观念。这部小说中以“义马”的一生展开,“义马”的形象延续了传统古典小说中半人半神形象的塑造。作品中“义马”这一半人半兽的存在,似乎就像是一个展览物一样,作者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展示了“义马”的外形和动态,为了凸显马的特征,义马是无声的,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献祭者”,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转化为国家之马”这一使命。作品中通过不同的群体对于“义马”的态度,展现着底层民众形态各异的家国观念。
首先,“义马”的孕育者——韩骧及其妻子。韩骧和妻子对于“义马”的不同态度,体现的是在家庭内部情与理的对抗。韩骧的妻子作为这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她体现的是母性的光辉,以及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人性最为柔软的部分。她在文中多是伴着眼泪而出现,在“义马”刚刚被确认身份时,“圉人让韩骧把圉床搬进屋中,把孩子塞了进去。韩骧的妻子要在圉床上铺点衣物,被圉人阻挡。她把眼泪夹在眼眶,用手搓摩圉床,从里搓到外,床面和扶手绸缎般光滑。夹板夹在孩子脸上时,她撕扯自己的头发,韩骧拉住她的手,让她搓夹板,她搓出了奶汁的芳香。”[1]27-28“妻子放下义马抹泪出门了”[1]45等。国家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其实是很抽象的存在,它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却看不到,摸不着,韩骧的妻子不懂“义马”所代表的意义,也或许是懂得,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和她作为母亲的力量相抗衡。她从不把“义马”特殊化对待,于她而言义马不是“义马”这个抽象的国家精神的符号只是她的孩子,她无法阻止丈夫、圉人以及相马师对于义马残酷的训练,只能以她自己的方式给义马带去温暖和关爱。作为父亲的韩骧对于“义马”则更为理智,他不是不爱义马,而是在亲情和国家民族大义中,他选择了国家。文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韩骧用一把大铁锁锁上门,把韩义马的哭音关在屋里。哭声像猫,抓不开铁锁。就着豆油灯,韩骧看到了妻子眼里的幽怨,便侧身睡去。
“把义马抱过来吧,他还那么小。”
“不行”韩骧的身子如山,妻子撼不动。
“反正没人知道。”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谁说没人知道。”
“睡在那样的床上,他不舒服。”
“舒服便做不了义马了。他不是我们的,是国家的。”
“国家是什么?”
“我也说不好。他也是光绪皇帝的。”
“光绪皇帝那么远,他能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生下来是义马,死了转生后就成了国家的马了。”
“你信?”
“别乱问,这不是信与不信的事。这是规矩,这是他的命。”[1]3
从韩骧的冷硬和妻子的感性中,透漏出了韩骧和妻子对于国家的不同态度。韩骧的坦荡和妻子的自私对比,既是在面对抽象而宏大的问题时性别间差异的体现,又是传统“严父慈母”家庭伦理模式的体现。其次,从他们的对话中,清晰而明确的展现了韩骧和妻子对于国家概念的模糊,他们都不清楚国家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这样的乱世,韩骧们的心中是有国家的,也愿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对于国家是什么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让我不禁会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 对于革命的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一系列形象体现的是底层民众最深层的悲哀,他们本是国家民族的主体却在时代的沉浮中成为了尘埃。从韩骧和妻子的这段对话中反映出了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底层民众整体的家国观念。
其次,“义马”的守护者和殉道者——圉人和相马师。在《国家坐骑》这部小说中李学辉倾注笔力描写了巴子营中义马的守护者们,展现他们对于义马的敬畏,以及他们为守护义马而做出的牺牲。最为典型的守护者应数圉人和相马师,他们似乎是为义马而生,又为义马而死。相马师的出场本身就带着沧桑的意味,“多年未出龙驹,相马师手中敲骨的木槌失了光泽,懒懒地躺在匣中。”[1]15相马师的死更是苍凉,因梅知县要收马户们的租,义马也在其中,相马师带着不甘和悲愤想去阻止,最后在义马过火关的现场,带着遗憾死去。就如韩骧问圉人“梅知县为何要薄待相马师,圉人摇头哀叹:忠也,运也;义哎,命哎。”[1]97圉人的这四个词精准的概括了相马师的一生。展现出了相马师对于国家的忠,对于义马的义,相马师是幸运的因为有生之年见到了可以转化为国家之马的龙驹,可是他又是不幸的,因为生在这样的乱世,他想为国家培养国家之马的道路是艰辛的。为了守护义马,相马师含恨而终,他的不甘与遗憾未尝不是国家和民族的遗憾。圉人的出场平静而又淡然,他似乎像是相马师的影子,和相马师一起陪伴着义马成长,在相马师死后,他带着义马完成了义马该做的一切,最后在义马死去之后,在义马的葬礼上,圉人投身火海彻底成为了义马的殉道者。圉人和相马师伴随着义马的诞生而出现,随着义马的死去最终消失,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义马,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
再次,作者又塑造出了清末国家的代表“梅知县”,以及民国时期西北军阀的代表马廷勷——马军长。梅知县对于义马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庙祝体现出来:“庙祝又甩了一下拂尘:扯吧,扯。国家都四分五裂了,还国家。满凉州,就你圉人领着这几个人还在嚷嚷国家之马。你看梅知县吧,这应该是他管的事,连义马他都收捐。国家的官都变成这样了,国家的马又会成什么东西?”[1]120。庙祝冷眼旁观又极尽嘲讽,他对于梅知县的嘲讽,一方面告诉了我们梅知县这样的国家形象的代表者就像国家的蛀虫,在这样的乱世只会引发民众对于国家的不满和失望;另一方面,作为反面的梅知县和马军长的存在进一步衬托了“义马”,以及他的守护者们的崇高。
马军长对于义马缺少敬畏,他觉得自己手中有枪炮,他就是老大,对于圉人他们所坚守的家国精神嗤之以鼻:
马军长伸长脖子,望着马户头和义马,哈哈大笑。
“这两个扁头一站,有趣;两个扁头一站,也有意思。你们说的这国家之马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好笑不好笑。”
圉人正色答道:“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一点也不好笑。”
马军长沉声问道:“蒋委员长是不是国家?东北的张少帅是不是国家?我西北的马家是不是国家?”
圉人昂首争辩:“不是,你们都是军阀。”
马军长拍了一下椅前的方几:“现今的中国没有军阀何来国家?”[1]235-236
马军长的嬉笑、沉声等形态的描写显示出了他的自负以及对于义马的不以为然,与圉人的正色和昂首争辩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展现了在这样的乱世“义马”这一凝聚着国家精神的符号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义马”精神的阐释者——李德铭。底层民众对于国家的概念似乎既具体又抽象,局限于他们有限的视野,不能完成对于“义马”精神的最终概括,所以只能借助有国家民族情怀的李德铭来完成这一使命。在马军长因为圉人的争辩而恼怒降罪时,李德铭站出来挡在圉人和义马前面,说:“这是一种精神。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我们民族的属相是马。精神要留给国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张少帅远避北京。中国缺的就是这种刚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义马不是单纯的马,他体现的是国家性格的一部分,这是现在我们最为缺乏的。我们这辈子如果传承不了,还有下一辈,所以义马的转世就有了特别的意义。”[16]在李德铭对于马军长的这一段辩述里我们看到了李德铭他对于国家民族精神的坚守与传承决心。对应前面圉人所说的军阀都不能代表国家之言,我们可以获悉,不管是对于圉人、相马师还是李德铭而言,所谓的国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扩展版图而不顾民众意愿的军阀们,而是能够承担起更大意义上的民族期望的政权。加之后面所提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德铭的红色革命者的身份也呼之欲出。较之以梅知县为代表的腐败且破败不堪的清政府和以马军长为代表的残暴且血腥的军阀,以李德铭为代表的始终坚守民族精神的红色政权似乎更符合民众对于国家的期待。在这篇小说中以“义马”为线索,既有地域文化的展示,又有对于国家民族大义的探究。在历史的书写中完成了从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义马”这一半人半兽形象的塑造,从巴子营的历史变迁探究了红色政权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李德铭使“义马”的形象最终得以升华,使我们明白义马不仅是凉州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更是承载着国家民族精神,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符号。
在《国家坐骑》这部小说中,李学辉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展开叙述,小说核心的主人公义马,似乎既是一个真切存在的人,又是一个象征物。在全篇小说中,义马没有任何语言,作者为了塑造出这样一个半人半神的象征体,没有让义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它在沉默中,完成了它“献祭者”的一生。看起来充满了崇高,但是在这种崇高中又有着对于生命畸形存在的悲哀。在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崇高和个人悲剧的矛盾中,恰恰反映的是大时代的变迁中个人命运的沉浮。
注释:
①文中提到的七寺分别是:海潮寺、永安寺、竹林寺、相国寺、罗什寺、地藏寺、安国寺。八庙分别是:玉皇庙、阎殿庙、三官庙、大庙、白云庙、勒马庙、小关帝庙、老君庙。九台:松林台、大云寺台、清应寺台、灵钧台、皇娘娘台、凤凰台、张轨祠宫台(雷台)、东岳台、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