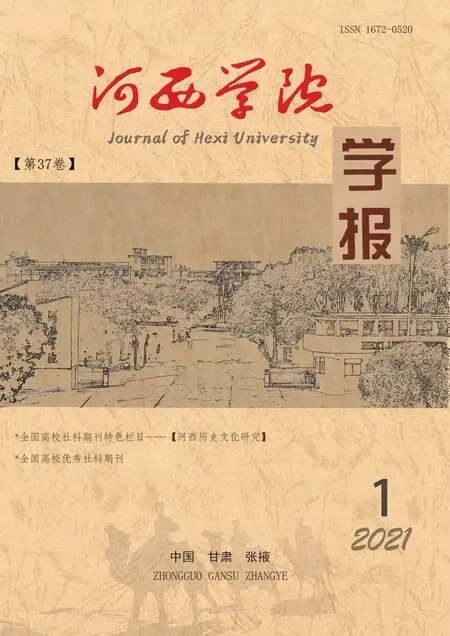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述论
——民间文书与明清以来甘肃社会经济研究之一
谢继忠 罗将 毛雨辰
(1.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河西学院法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近年来,学术界对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河西走廊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的破坏与沙漠化、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与环境变迁、清代基层官民环境意识及行为、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环境资源保护、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变迁、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及其实践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的环境保护思想再作些探讨。
明清以来甘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方面受干旱少雨、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人口增长、战乱、对森林滥砍乱伐、对水源的破坏、对草场的滥垦等都有直接关系。吴晓军认为:“在西北地区,由于人口增长特别是清代以来人口暴增,造成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本来就稀疏的山林被砍伐殆尽,大面积地表植被被开垦和滥挖,干旱风沙、水土流失日趋肆虐,所以,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密切的直接关系。”[1]王利华认为,清朝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人口持续增加,盲目毁林开荒、导致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水旱灾害日益频繁,环境——经济——社会关系严重失衡,这些意味着已经持续几千年的人口(劳动力)增加——农区扩张——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虽然“朝廷和地方官府推行不少举措禁垦禁围,鼓励植树造林,各地护林保水、限樵禁猎的乡规民约大量涌现,但并未遏制环境恶化趋势。”[2]上述论述对我们认识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对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清代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与河西走廊生存发展关系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宁夏将军兼甘肃提督苏宁阿,他在《八宝山来脉说》《八宝山松林积雪说》《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说》中集中阐述了祁连山水源保护与张掖生存的关系,提出“永远保护”祁连山森林的深刻见解。
嘉庆七年(1802年),宁夏将军兼甘肃提督苏宁阿在《八宝山来脉说》中云:“故八宝山为西宁、凉州、甘州、肃州周围数郡之镇山。山生杉松、穗松,山之草木、牲畜、禽鸟,人无敢动者,动则立见灾祸。附近蒙古熟番,以及牧厂人等,俱皆敬畏戒守,不敢妄行。……黑河流出北雪山,开渠五十二道,灌溉甘州水田,为甘郡黎庶生计。是以八宝山之积雪,其功大矣!雪融助河,收水利以敷灌溉之用;若雪小水歉,则五十二渠,大有艰涩宭乏之害。甘府之丰歉,总视黑河雪水之大小。……考诸山川来脉形势,周围数百里之山,再无与八宝山齐高者,是知其为西凉甘肃四郡之镇山也,所以永远禁止樵采。盖为四郡风水攸关,司兹土者,当何如敬慎欤。”[3]苏宁阿对保护祁连山森林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祁连山主峰之八宝山作为镇山,人畜都不能进入,一旦进入,就会有灾殃。这种“镇山”的神圣性,有效限制了人们伐树、放牧的范围,使人们产生了“敬畏”祁连山之心,客观上有利于森林和水源的保护。
苏宁阿在《八宝山松林积雪说》中云:“一斯门庆河,西流至八宝山之东,汇归黑河而西,绕过八宝山而北流出山,至甘州之西南,灌溉五十二渠。甘州人民之生计,全依黑河之水。于春夏之交,其松林之积雪初溶,灌入五十二渠溉田,于夏秋之交,二次之雪溶入黑河,灌入五十二渠,始保其收获。若无八宝山一带之松树冬雪,至春末一涌而溶化,黑河涨溢,五十二渠不能承受,则有冲决之水灾;至夏秋二次溶化之雪水微弱,黑河水小而低,则不能入渠灌田,则有报旱之虞。甘州居民之生计,全仗松树多而积雪。若被砍伐,不能积雪,大为民患。自当永远保护。”[4]苏宁阿在《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说》中云:“黑河出山后,至甘州之南七十里,上龙王庙地方,即引入五十二渠灌田。甘州永赖以为水利,是以甘州少旱灾者,因得黑河之水利故也。黑河之源,不涸乏者,全仗八宝山一带,山上之树多,能积雪溶化归河也。河水涨溢溜高,方可引以入渠;若河水小,而势低不高,则不能引入渠矣。所以八宝山一带山上之树木积雪,水势之大小,于甘州年稔之丰歉攸关。”[5]苏宁阿重申,保护祁连山与甘州民众生存攸关,应“永远保护”祁连山森林,是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系统功能的深刻认识。
至近代,由于河西走廊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对河西走廊环境保护的认识也随之深化。成书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的《新修张掖县志》收录《富甘之畜牧谈》一文,涉及到张掖环境保护的若干内容,其中有“种树”“保护野畜”“禁挖草根”诸条。“种树”条提出“种树以养牲畜”。“查种树之利,可以招雨泽,可以滋草木。各国皆属要图,而甘肃尤为亟亟,以其与牲畜大有关系也。但人民不明此理,有斩伐而无种植,以致各地林木濯濯俱空,不惟缺养牲之原料,即燃料亦觉为难。此近年以来各地牲畜渐少之所由来也。故欲事养牲宜先种树。”“保护野畜”条提出“严禁用毒品毒杀狐狸等野畜。”“据近年来之调查,所产野兽之数已不敌十年前之十一。恐再越二三十年,野牲恐将绝种。且此种毒品,不惟直接及间接毒野兽,并能毒家畜,所关甚大,宜呈请官厅力加禁止,不准再用毒捕,只许用旧法以捕获之,庶可保无穷之利。”[6]“禁挖草根”条提出“禁挖草根、改良草种”。“查张掖煤矿甚少,民间烧燃半用薪柴。而近年以来薪柴亦缺,故常有于冬日挖取草根之事,已成为习惯。须知草根既去,则明年即不能发生,牛羊食料即因之不足,此于畜牧事业大有妨碍。欧洲各国所有喂牲之草,半恃种植。我国地广,全恃天然。近来又加以挖根之弊,则草必日少,虽欲多养畜,而不能,此不可不严禁者也。欲改良草种,最好向外洋购买草籽,自播种之,则其地全生养畜之草,而牲畜自可增多矣。”[7]这里提出“种树以养牲畜”“严禁用毒品毒杀狐狸等野畜”“禁挖草根、改良草种”等,都是建立在对破坏环境具体行为的切实认识之上,也是对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的长远思考。
二、碑刻所见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
水源是河西走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因子。由于河西走廊属于干旱区,降水稀少,故保护水源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而言,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明清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祁连山水源的重要性。
祁连山为河西走廊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水源涵养区,河西民众赖内陆河灌溉农业而生,故祁连山森林的保护对河西走廊民众而言,性命攸关。《创修民乐县志》云:“祁连山一带,极广大之杉林、柏林、柳林,及补达河、马蹄河、香沟河畔之山白杨林,皆天然生成之旧林区。因森林繁茂,山谷不干,冬可以藏冰积雪,夏可以调节气候,增加雨量,水利攸关,保护自昔周密。”[8]
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之东乐(今甘肃民乐县)有同治元年(1862 年)保护水源碑刻,如例1:
例1 东乐县同治元年“保水源事断案碑”
为遵照断案,公立界碑,以垂久远,而保水源事。案据咸丰十一年有番目庆木厥多布旦等,在府具控东乐六大坝土民王执中等攘夺番地等情一案,蒙批本县讯断,详报随卷。查道光十四年前,府宪奉各上宪批断详报,有生员韩景泰者,与洪水番目铁令多尔吉控争水源,曾经断定下横路以南,作为番目游牧,汉民水源;下横路以北,只许番目自耕自种,有案可稽。今番目庆木厥多布旦,系铁令多尔吉之子,将下横路以南游牧之地,以至于中横路,亦(并)租于张应时任意开挖耕种。是以王执中等查知有伤水源,致起争端。经本县秉公酌断,饬令张应时等,此后不准耕种番地,只准庆木厥多布旦等在下横路以南游牧,下横路以北自耕自种,永不准汉民耕种番地,亦不得番、汉交趾,致滋事端。倘蹈故辙,按律究办。两造各具遵结完案,并令交界之处立碑打墩,防微杜渐,以垂久远。详蒙府宪批准,尔士民自应照此断案,立碑打墩,免滋事端,永远遵守毋违,须至勒碑者。同治元年三月二十日立。[9]
该碑立于同治元年(1862 年),清代东乐(今甘肃民乐县)属甘州府(今甘肃张掖市),地属祁连山北麓之黑河流域。道光十四年(1834年)前,生员韩景泰,“与洪水番目铁令多尔吉控争水源”,官府判决:“下横路以南,作为番目游牧,汉民水源;下横路以北,只许番目自耕自种”。咸丰十一年(1861 年),番目庆木厥多布旦等控告“东乐六大坝士民王执中等攘夺番地”。而“王执中等查知有伤水源,致起争端”。县府“秉公酌断”,“饬令张应时等,此后不准耕种番地,只准庆木厥多布旦等在下横路以南游牧,下横路以北自耕自种,永不准汉民耕种番地,亦不得番、汉交趾,致滋事端。倘蹈故辙,按律究办。两造各具遵结完案,并令交界之处立碑打墩,防微杜渐,以垂久远”。最后府宪批准县府断案,并立碑晓谕各方。这桩诉讼案,历时近30年。可见,保护黑河流域水源,是生活在祁连山区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
光绪二年(1876年),“番目”与东乐民众就水源保护再起纠纷,甘州府根据同治元年(1862 年)断案,了结此案。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争夺双寿寺山地木植、水源,山丹县属南滩十户庄民与东乐属六大坝民,“在府县衙门互控”,张掖县、山丹县分别作出判决,并刻石立碑,如例2:
例2 东乐县光绪二十七年“保水源烟火事断案碑”
谨按:洪水河,出西水关口,两岸均系草坡旱地,往往为黠(黑)番偷租于汉民耕种,坝民以水源所关,屡与构讼。盖以泉水微小,春资雪液,夏恃天雨,地一犁熟,雨尽渗入土中,不能聚而成流也。此案系清同治元年甘州府鲍、山丹县熊所断。至光绪二年,该番目又翻控一次,蒙甘州府龙仍断如前案。又于光绪二十七年,山丹县属南滩十户庄民,借采薪之名,私入西水关口,偷伐水源大木,坝民与该十户庄民,互控府县各衙门,有甘州府诚、张掖县杜、山丹县郑、东乐分县蒋断案。碑文照录:
为照录断案,公立界碑,以垂久远,而保水源烟火事。案查光绪二十七年,据山丹县属南滩十庄士民何其隆等,与东乐属六大坝民刘应试等,在府县衙门互控,争夺双寿寺山地木植、水源各等情一案,由府饬县会同秉公讯断。旋经张掖县堂讯,查双寿寺距西水关有十五里之谱,既不可碍东乐民人(人民)水源,亦不可断山丹人民烟火。除西水关以内,林木甚繁,自应严禁入山,以顾水源;自西水关以外以五里留为护山之地,不准采薪;尚有十里至双寿寺,即准采薪,以资烟火。此十五里山场,作为三分,以二分地顾烟火,以一分地护水源。打立界碑,永远遵行。并令采薪人民,入山时只准用镰刀,不准用铁斧,如有砍伐松柏一株者,查获罚钱二十串文,充公使用,并照案出示晓谕,以使周知。该两造士民,当堂悦服,各具遵结,附卷完案。详蒙府宪批准,并移东乐、山丹存案。嗣又控经山丹县断令两县分界,仍照大河为准,所有老林树,两县均不准砍伐,以护水源。尹家庄、展家庄用镰刀砍伐烧柴,只在老君庙以下;老君庙以上,无论何县田地,均应保护林木,不准砍伐。如有犯者,从重处罚。各具有遵结完案。尔士民等,自应遵此断案,公立界碑,以息讼端,而垂久远。其各懔遵毋违,须至勒碑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立。[10]
该碑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代山丹隶属甘州府,属黑河流域。山丹、东乐(今甘肃民乐县)互控案,经张掖县判决,划定保护山林区域和水源地,并规定使用采薪工具和违规惩罚细则。“采薪人民,入山时只准用镰刀,不准用铁斧,如有砍伐松柏一株者,查获罚钱二十串文,充公使用”。山丹县判决,“两县分界,仍照大河为准,所有老林树,两县均不准砍伐,以护水源。尹家庄、展家庄用镰刀砍伐烧柴,只在老君庙以下;老君庙以上,无论何县田地,均应保护林木,不准砍伐。如有犯者,从重处罚”。同时,“打立界碑,永远遵行”,并刻石立碑。如果从道光十四年(1834年)算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东乐与山丹的水源保护纠纷,历近70年时间,这也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
进入民国时期,疏勒河流域党河的水源也出现了被少数民族“蒙人”牛羊践踏、“屡致湮塞”的情形,敦煌县长赵晋芬令农会会长樊兆麟疏浚泉眼,并与“蒙人”交涉,划定水源边界,不准“蒙人”越界放牧,同时签订协约。为记其事,赵晋芬写了《入山疏凿党河源悬匾龙王庙以志神庥序》,如例3:
例3 赵晋芬《入山疏凿党河源悬匾龙王庙以志神庥序》
敦煌农田灌溉,夙资党河,迩来河流曰尠,农业之仰给不足,晋芬职司民牧,惄焉心忧。爰集邑人士,议所疏通而张大之,农会会长张君惟俊,樊君兆麟,以疏凿河源请,众议赞成,即以樊君任其役。斯役也,共派民夫二十人,以四月入山,履拉排沟,桥头子河,鳖盖。峩博沟、小牛沟、清水沟、野马河,需时三十日,疏凿泉大小四百三十眼。其尤益者,各处泉眼,被蒙人之牛、羊践踏,屡致湮塞。樊君至与蒙人交涉,划鳖盖为界,嗣后不准蒙人游牧,由蒙人××等与樊君双方书名签字,立卷在案。由是河流渐增,农田利赖。虽曰谋人,抑也神明之默护也。爰题“溥洽渊泉”四字,用答神庥兼志不忘云耳。
民国二十年 月 解梁赵晋芬题并序[11]
该序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敦煌属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其灌溉主要依赖党河,党河源头在祁连山,故党河源头水源保护,与敦煌灌溉农业密不可分。赵晋芬任敦煌县长时,“派民夫二十人”,“需时三十日,疏凿泉大小四百三十眼”,属较大规模水事活动。同时,与“蒙人”交涉、划界签约,“不准蒙人游牧”,有效地保护了党河水源,其效果立显,“河流渐增,农田利赖”。赵晋芬题“溥洽渊泉”四字,“用答神庥兼志不忘云耳”。这篇序文虽未刻石立碑,但对党河水源的保护作用,也显而易见。
总之,上述2 通碑刻和1 篇序文,从地域分布来看,涉及祁连山北麓之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基本涵盖了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从时段来看,最早者为同治元年(1862年),最晚者为民国二十年(1931 年)赵晋芬的《入山疏凿党河源悬匾龙王庙以志神庥序》,时间跨度达70年。它们的基本思想都是保护水源,不许滥垦和越界放牧,划定禁区,严禁人畜进入等,这些认识和做法,不但反映了当时人们保护祁连山环境的思想,而且反映了人们对祁连山环境功能及其保护措施的理性认识。这些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河西走廊民众的经验总结。
三、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
明清以来,河西走廊滥砍盗伐、滥垦等破坏环境行为,屡禁不止,旋禁旋犯,这主要是源于生态恶化,资源匮乏,人们生存艰难,也与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有一定关系。探讨环境保护思想,必须提升认识,即环境保护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思想认识方面,更应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对河西走廊而言,植树造林,培育林木,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当地干旱少雨、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也是人们的必然选择。
早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镇番(今甘肃民勤县)教授彭相,“倡率在学生员每人植树二十棵,栽柳五十株。”[12]在学生员植树颇有成效。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镇番名士“孙克明等募赀修葺苏武庙,筑土屋数间,佣人看守,专行种植树木之责。是年栽植香椿二十株,土榆五十株,紫槐三十株,杨树二千株,沙枣二千株。”[13]康基渊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肃州直隶知州(今甘肃酒泉市),他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地方的措施,其中有专论植树条目。“劝民广种树株”,“种植杨柳十万余株,引各坝灌田余水浸浇”,使肃州百姓“均沾惠利”,[14]此举受到普遍赞誉。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在河西走廊已经形成了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
清末,左宗棠从同治六年(1867年)起督办西北军务、兼陕甘总督,至光绪六年(1888年),主政陕甘十余年,号令军队植树,据张玉山统计,“在平番、狄道、大通、皋兰、董志、环县、会宁等一些州县,种植树木约三、四十万株。从长武到会宁有一条六百多里的道路,历年来沿路种活的树木有二十六万株以上。如将河西走廊和新疆所栽种的树木加在一起,大约为一、二百万株。”[15]后人对左宗棠在甘肃植树的功绩多有评论,大加赞赏。《创修民乐县志》评价曰:“清光绪元年,左文襄平定甘肃,自西安以至酒泉,夹道遍植杨树,至今树大数围,材木不可胜用,号称‘左公林’,为西北第一建设,载之青史,万古常存。”[16]左宗棠在甘肃大规模的植树,是对甘肃历代植树造林传统的继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左宗棠在甘肃植树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民国六年(1917 年),镇番知事周树清“力倡植树,以为:镇邑之存亡,多系于草木之盛衰有无,既与夫生民生活之有关者,安可熟视而无睹者欤?是年,仅城内植树近万株。”[17]1942 年刊《创修临泽县志》记载:临泽“南山番地,森林饶富,山谷沟壑间,松柏丛生。”“明、清时为保护水源,严禁砍伐。甘州提督铸有铁牌,悬为厉禁。迨后禁令废弛,滥伐为虑。各乡镇沟沿河岸、庄宅四周、沙漠边缘、道旁,杨、柳、榆、椿以及桃、杏、果木随处皆有。……近来注重民生,国家提倡林业,不遗余力。公有林除昔年左文襄公在东西大路栽植者外,迩来所栽者多在城关周围。”[18]
在20 世纪40 年代,位于祁连山区的民乐县坚持植树,并采取有效措施护林。《创修民乐县志》记载:“三十五年度(1946年),遵奉郭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笔者注)电令,每口各栽十株,计全县共栽三十余万株,并令各村住户自栽自护,长成后仍归自用。法良意美,造福非浅。”“曾于各山口附近,各组设保林公所,委有所长、稽查、巡丁,负责巡查,严禁偷伐。故近数年来,凡一切活松、湿柳,一概不准入山采伐;除连年砍伐电杆,略有损伤外,更无人敢犯禁者。而农林部所派之林警队,又时常会同警察及地方保林人员,轮流入山,认真巡逻,保林之策可谓至周至密矣。”[19]
从明万历年间至20 世纪40 年代末,河西走廊各地官府严禁砍伐林木,动员民众植树造林,体现了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形成了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无论怎样整治,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
四、余论
通过对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的分析,使我们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环境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视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官方与民间通力合作,才能收到实际效果。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保护祁连山森林和水源,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祁连山水源保护的碑刻,体现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形成了保护环境的合力;利用八宝山“镇山”的“神圣性”,增强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保护水源的碑刻中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效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持续不断的植树造林,体现了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这都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它们既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第二,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是对中国“道法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发展。乐爱国认为:“现代生态学是基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提出来的,道教的‘道法自然’,就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言,也与当时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联系。但无论如何,道教的‘道法自然’要求以自然规律的优先为原则,要求顺应天地自然的自然而然,反对过度地开发自然,主张适宜开发,必然是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应当可以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原则之一。”[20]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虽然没有直接阐述“道法自然”的内涵,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完全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
第三,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与当代学者解决西北生态环境问题的主张有“共通性”。当代学者在研究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时指出:“由于多年来的毁林、毁草、滥垦、滥伐、畜牧超载等原因,致使西北地区各高大山系山区的森林面积减少,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山区的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和减少,浅山区几十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森林已荡然无存。残留的森林已经退缩到远山地带,并呈现出不连续的块状分布,开始失去其‘天然水库’的作用”。[21]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学者们也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如石生泰等人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加强西北地区各高大山系水源林区的建设,保护与治理、发展并重”。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大力度,实行封山育林,不断扩大森林资源的面积;要科学研究、科学管理,保护与治理并重,提高林木质量,增强其水源涵养功能,充分发挥水源涵养林区的多种效益,缓解水源林区的严重生态危机。因为,在自然生态环境综合平衡系统中,遏制森林草原地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是西北地区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亦是其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22]如果我们把上述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学者对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相比较,那么,就会看到二者之间的“共通性”。由此可见,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环境保护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历史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对地方性环境知识的研究,对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不无借鉴意义。正如袁超等所说:“在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充分挖掘多样的地方性环境知识无疑会为当下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相关研究表明以往农民、土著的地方性环境知识是有助于生态环境维护的,只是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尺度上,地方性环境知识被掩盖与边缘化了。”[23]因此,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环境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还需学术界做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