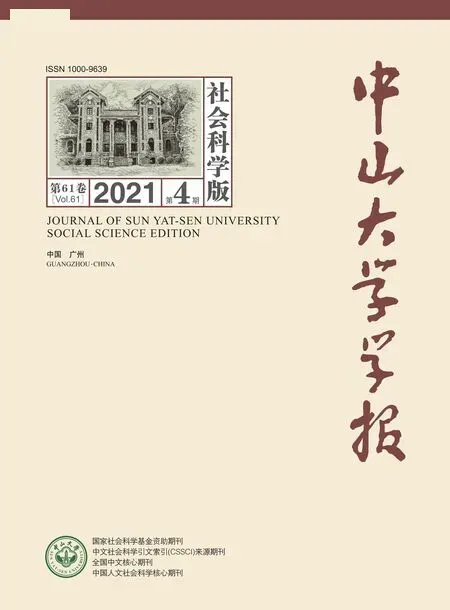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董滨宇
一直以来,康德伦理学以其极具代表性的理性主义特征而受到情感主义者的攻击。在情感主义这一广泛的流派中,亚里士多德与休谟的相关学说往往被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德性”或者“美德”视为幸福生活的根本,而“德性”的本质则是理性与情感的内在和谐状态。休谟则指出,“同情”是道德行为的根本动机,而理性只是负责提供适当的指导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美德伦理学可以说是情感主义发展至今的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学说。很多当代美德伦理学学者都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康德,其中,康德将道德动机的根据视为“理性”而非“情感”,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是错误的,这必将导致道德主体及其行动的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偏激的,情感主义者们未能看到的是,康德伦理学虽然以道德义务为中心,但就道德动机这一概念而言,它既是理智化的,也是感性化的。准确地说,它的理论根据是“理性”,但它的现实根据是以“敬重”为核心的实践性情感。在康德复杂的理论术语中,它们其实都相当于其所说的“意志”乃至“理性”。对此,我们将结合文本做出深入的分析。
一、情感主义者的不满
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情感主义者早就认为,感性情感或者欲望才是道德的根源与动力,而理性只是提供具有指导作用的原则而已。“同情是我们对一切人为的德表示尊重的根源。”①[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0页。当代美德伦理学继承了这一观点,其中一些学者指出,康德将道德动机的根据置于“理性”之中,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它将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认识与行动上的难题。尤其是,由于理性与情感的分裂,康德式的道德主体将会遭遇严重的内心冲突的麻烦。
康德将行为者的道德动机仅仅视为对于道德法则的尊重,这在一些情感主义者看来很可能导致行为者动机与信念的不一致,斯托克尔(Michael Stocker)将此种情况称为一种“精神分裂症候”。伦理规则表达的是“应当”,而它未必与行为者的动机是相一致的。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的理性认可一个道德法则,但是它并不构成你的真实的欲望。由此将产生两种后果,要么你的信念并不能促成真正的行动,要么就是你表面上依照法则的要求这样去做了,但其实内心情感是与之对抗的,从而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分裂”。
斯托克尔的这一批评与威廉斯关于“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观点相关。威廉斯指出,所谓“内在理由”,是指行动者出于内心的真实欲望而行动,在这里,动机与理由是相互一致的;所谓“外在理由”,是指行为者的动机与理由相分离,此时,作为外在理由的规范性原因无法作为行为者的真实动机①[英]伯纳德·威廉斯著,徐向东译:《道德运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无论是在斯托克尔还是威廉斯那里,作为休谟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只有情感、欲望等这些经验性要素才能作为行动的内在理由,然而,像康德那样将实践理性及其法则作为动机,其实就会导致一个无效的结论。因为仅仅作为一个“外在理由”,它缺少转化为行动的“内在理由”的根据。理性主义者以实践理性及其法则作为行动的理由,在斯托克尔看来是不够的,因为前者错误地以为道德上的良好意图就会自然地转化为行动上的动机。恰恰相反,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现象:一个所谓的出于义务的要求而行动的人,其内心里却充满了抵触。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斯托克尔坚定地认为,理性与情感、动机与理由必须统一协调起来,由此才能激发真实的行动,而且只有如此,行动者才不会陷入二元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斯托克尔进一步指出,只有那些基于爱、友谊、同情、和谐亲善等自然情感的行为才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行动的动机就是理由。
斯托克尔以及威廉斯的观点激发了很多讨论。从道德动机问题出发,情感主义者否认理性及其规则有资格作为行动的原发性力量。他们站在休谟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对于激情只是起到调解作用,而真正激发行动的则是欲望或者情感。斯托克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以情感为依据,由“理性至上主义者”所导致的这种“精神分裂”才能得到治愈。首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好人就必须拥有正确的情感,它能够指导人如何行动与如何生活。其次,像康德等理性主义者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认为情感、欲望仅仅是盲目的本能冲动,它们并不具有任何鉴别与判断的能力,而只有理性才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相反,斯托克尔认为,情感本身拥有评价性功能,即能够产生认知性行为。他以亚里士多德关于“愤怒”的论述为例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轻视就是被否定了适当的重要性与适当的尊重。因此,无须特意证明,愤怒之人必然会认为自己由于被否定了适当的尊重而受到了道德性伤害。因此——假设我的愤怒完全像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被轻视,那么我的愤怒就表明我仍然在意你是我的朋友。相似地,我在音乐会上感到厌倦,可能就表明我并不重视音乐或者这场演出。因此,情感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评价的信息。它们与评价本身也有着系统的、认知性的联系。”②Michael Stoker,How Emotions Reveal Value and Help Cure the Schizophrenia of Modern Ethical Theories,in Roger Crisp,Michael Slote,ed.,Virtue Eth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4-125.可见,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无意识的情感,其实都是在某种理由的基础上发生的,而这就意味着情感本身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评价性功能。这一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认同,他们认为,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冲动,它能够通过自身的敏锐感知而针对复杂的情境做出相应的判断,甚至这种判断比理性更加准确。
二、欲求、任性与意志
面对情感主义者们的强烈质疑,现在的问题是,康德真的是将道德动机的根据视为与情感完全相对的理性么?事实并非如此,在康德那里,理性与情感并未分离开,相反,就作为一种实际能力来说,它们共同居于“意志”之中,在康德的语境里,它也相当于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同时,它具体地表现为“对法则的敬重”这一情感状态。
首先,应该说,康德确实主要是将纯粹理性以及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以及根据。不过,文本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表述。一方面,“法则是独一无二的动机”(Rel:37)。“道德法则作为动机的作用仅仅是否定的,而且作为这样的动机,这动机是能够被先天地认识的。”(KpV:72)另一方面,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中,康德又表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惟一的、同时无可怀疑的道德动机”。(KpV:78)要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阐释,就应该依据《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那句著名的表述:“欲求的主观根据是动机,意欲的客观根据则是动因。”(GMS:427)①本文所依据的中译本是李秋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简称《全集》)。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如《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简写为GMS)出自《全集》的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实践理性批判》(简写为KpV)、《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简写为Rel)、《道德形而上学》(简写为MS)出自《全集》第6 卷(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同时,本文还参考了剑桥版的英译本(Immanuel Kant,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Greg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与英译本都是依据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康德全集》译出。为方便起见,本文所用引文仅标出康德著作的简写形式及其编码。这里,“动机”(Triebfeder,ince⁃tive)实际上就相当于“对法则的尊重”,因为它只能是一种主观性的感性情感,是促使道德行动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动因”(Bewegungsgrund,motive)则相当于作为意志的根据的道德法则,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产物。理性存在者是在认识到法则的正确性与权威性之后,出于对它的尊重而决定有所行动,即“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一种通过一个理智根据造成的情感”(KPV:73)。然而,正如贝克所注意到的,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混用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在“动因”的意义上使用了“动机”一词。显然,康德本人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②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91.。贝克又指出,在雅培(T.K.Abbott)的译本中,“动机”被译为motive 或者Spring,这是一个不错的翻译,因为德文Feder本身指的是钟表的主要发条③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91.。这一看法在恩斯特龙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将“动机”译为incentive 是不对的,难以准确地表达出康德所赋予它的精微涵义。因为在英文中,incentive是有外在对象或者目的存在的前提下所发生的一种效应,而康德所说的“动机”(Triebfeder)更主要地是作为选择或者行动的内在源泉,它具有潜在的活性力量,因此,最好译为“规定性力量”(determining force)或者“促发力量”(motivating force∕driving force)。恩斯特龙同时还建议,在第二批判中,Triebfeder在康德那里既包含着作为促发力量的“动机”,也包含着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动因”。前者是一种主观状态,具体表现为情感,后者是一种客观原因,具体表现为法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康德借此是要解决“是”与“应该”的问题:“客观原则是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依据,而就它是一个既定的主体的确这样去行动所依据的原则来说,它又是一项主观性原则或准则。同样,我主张,被视为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的道德法则就是意志应该被如何规定的表象;这一法则也被视为一个给定的主体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它是实际地规定主体意志的同一个表象。”④Stephen Engstrom,The Triebfeder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in Andrews Reath and Jens Timmermann,eds.,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A Critical Gui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90-93.这篇论文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康德义务论的动机理论。
在这里,要准确地理解康德的“道德动机”概念,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把握“欲求”(Begehren,desire)或者“意欲”(Wollen,volition)的真实涵义。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具体阐述了这种“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gen,faculty of desire):“就是通过自己的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之原因的能力。”(MS:211)作为一种因果性活动,欲求能力能够自己产生对象,可以说,它就是人的一种主观的意愿能力。而且,欲求能力与情感有着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把与欲求(对其表现如此刺激人的情感的那种对象的欲求)必然相结合的那种愉快称为实践的愉快。”(MS:212)康德又将它特意与“情欲”(Konku⁃piszenz,concupiscence)做了区分,后者是一种单纯的感性能力,能够作为“规定欲求的诱因”,不过,由于只是毫无理性的感官冲动,因此并不能够像欲求能力那样在心灵上规定行动(MS:213)。可见,相对于情欲,欲求能力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蕴含着潜在的理智性功能;其次,作为“一种根据喜好有所为或者有所不为的能力”,欲求能力又分为两种形式:“如果它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做任性(Willkür,choice)。但是,如果它不与这种意识相结合,那么,它的行为就叫做一种愿望(Wun⁃sch,wish)。”所谓“任性”,是指“虽然受到冲动的刺激,但不受它规定,因此本身(没有已经获得的理性技能)不是纯粹的,但却能够被规定从纯粹意志出发去行动”(MS:213)①关于Willkür,韩水法译为“意愿”,([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相当于英文的volition,邓晓芒译为“任意”,([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实践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秋零则译为“任性”。笔者认为,“意愿”更符合德文的原意,因为它更加具有中性化色彩,而另外两个词都偏重于主观性的自由活动,与理性相去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在康德那里,Willkür 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而只是在与Wille 相互区别的意义上,指并不依照纯粹理性来行动,然而,它却仍然离不开慎思理性或技艺理性,以便实现主体的目的。显然,“意愿”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这种一般性的欲求能力。为求表述上的一致,本文仍然主要使用“任性”一词,然而其间的差别,却不可不察。另外,Gregor 的剑桥版英译本则译为choice,相当于中文的“选择”,也比较准确地表达了Willkür 的中性化涵义,而且顾及了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不过,相对于汉语的“意愿”,choice 丧失了其中所蕴含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choice其实不如volition(意愿)更加准确。。重要的是,康德又提出了一个与“任性”直接相关的概念,就是“意志”(Wille):“如果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根据,因而喜好本身是在主体的理性中发现的,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意志。所以,意志就是欲求能力,并不(像任性那样)是与行动相关来看的,而是毋宁说与使任性去行动的规定根据相关来看的,而且意志本身在自己面前真正说来没有任何根据,相反,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MS:213)这里,康德把意志与任性区分开了,但是,接下来他似乎又把二者等同起来:“就理性能够规定一般欲求能力而言,在意志之下可以包含任性,但也可以包含纯然的愿望。”(MS:213)贝克认为,意志和任性都属于一种统一性的意愿能力,而我们通过对于任性的“回溯”,能够获得对于意志的理解。有时候,康德将二者区分开,而有时候又将它们统称为“意志”。然而,具体来说:第一,意志属于立法能力,而任性属于执行能力,意志是由纯粹理性加以规范的任性。第二,由于不涉及行动,意志不包含动机要素,而任性则必然蕴含着动机。第三,意志是本体性的概念,任性则是这一概念在现象界的表现,所以会受制于经验要素的影响,因此有时候是不自由的。第四,意志产生法则,而任性产生准则,不过,在隶属于意志时,它也会成为服从法则的纯粹实践理性。第五,任性是自由的,它有两种情况:消极的与积极的,消极的任性是指独立于感性冲动的规定,而积极的任性是指作为纯粹理性,它本身能够产生实践活动。在意志之中,两种任性的自由能够达到统一。第六,在贝克眼中,意志是“自律的”,而任性则是“自发的”②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176-208.。伍尔特则认为,意志相当于西季威克所说的“善的或理性的自由”,即主体只有在遵守道德法则的情况下才会获得的自由,而任性相当于西季威克所说的“中立的或道德的自由”,即主体在道德与非道德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由此,西季威克对于康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即“中立的或道德的自由”)的批评是不成立的。而且,伍尔特认为通过“任性”这一概念,康德引入了意志主体在进行选择时所必须具备的经验性的情感要素,如尊重、愉悦等①Julian Wuerth,Kant on Mind,Action,&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36-243.。
欲求能力和情感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康德在“导论”中指出,所谓的“情感”,是指一种与欲求或憎恶相结合从而产生实践性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感受。同时,愉快的感受并不总是由欲求所产生的,而可能是通过鉴赏活动所产生的纯然沉思的或者无为的愉快。不过,康德认为,就欲求而言,既存在着一种感性偏好的愉快,也存在着一种“近似于”鉴赏活动的“无为的愉快”,康德称之为“理性兴趣”,它是纯粹的、无关乎功利的一种“继欲求能力的先行规定而起”的理智的愉悦(MS:212)。这种愉快的感受既可以作为欲求的根据,也可以作为欲求的结果。结合康德以往的见解,前一种情况下将产生他律的行为,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是以道德法则为根据,以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行动,那么所产生的就是自律者的纯然愉悦的感受。
以上的论述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道德动机”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康德显然意识到道德行动的促发力量与运行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一项正确的法则如何转变为实际行动。然而,在情感主义者看来,真正能够促发行动的动机只能是作为感性情感的同情或者仁爱,康德主义者试图以理性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是并不成功的。而且,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它具有一定的认知性功能,相比于理性,它是更加原初的能力,甚至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道德判断。然而,站在康德主义立场上的学者们认为,理性能够作为道德动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对法则的敬重”这一基本情感表现出来的。重要的是,正如康德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是盲目的、无知的感性冲动,而作为一种思维能力,只有理性才能够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道德法则。我们则进一步认为,情感主义者的批评主要源于他们并没有完全了解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者说他们忽视了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含义,尤其是“意志”与“理性”的真正内涵以及二者的内在关系。
首先,在“意志”这一概念之外,康德其实将“欲求能力”视为更加一般化的心灵活动。在初始意义上,意志就是一种欲求能力,只是它与理性法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正如我们此前所分析的,在康德那里,意志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作为规定性根据的“意志”(Wille),二是指作为实际选择能力的任性(Willkür)。二者最明显的差别是,相对于前者,后者具有“动机”的功能,即将法则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不过,二者通常是作为一个概念——“意志”(Wille)而被康德加以运用的。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康德其实是通过具有统一性内涵的“意志”(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意志Ⅱ,而将它所包含的只作为规定性根据的意志称为意志Ⅰ)来指称一种既能够确定法则又能够以此为动机而产生实际行动的能力。而且,康德有时也将这种统一性“意志”(意志Ⅱ)与“理性”等同起来,即理性也是一种欲求能力:“自身幸福的原则,无论在它那里使用了多少知性和理性,对于意志来说毕竟只包含有与低级的欲求能力相适合的规定根据,因而要么根本不存在高级的欲求能力,要么纯粹理性必须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仅仅通过实践规则的形式就能够规定意志,无须以任何一种情感为前提条件,因而无须惬意或者不惬意的表象,惬意或者不惬意是欲求能力的质料,这种质料在任何时候都是原则的一种经验性的条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惟有为自己本身来规定意志(不是为偏好效力),才是在病理学上可规定的欲求能力所从属的一种真正的高级欲求能力,并且现实地、甚至在种类上与前一种欲求能力有别……理性在一个实践法则中直接规定意志,并不借助参与其间的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哪怕是对这一法则的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而是惟有它作为纯粹理性就能够是实践的这一点,才使它有可能是立法的。”(KpV:24-25)
显然,在康德那里,已经对于欲求能力做出了低级与高级之分。只要是实践规则将其根据设定为纯粹的形式,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是高级的,而如果设定为经验性质料,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是低级的。前者就是以道德法则为动机,而后者则是以情感或者欲望上的愉悦与满足为动机,前者属于将任性置于意志之中的活动,而后者则只属于任性的活动(KpV:24)。作为高级的欲求能力,意志Ⅱ同时就相当于理性①康德在很多地方都表明理性(实践理性)就是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Ⅱ。“既然为了从法则引出行为就需要理性,所以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理性。”(GMS:412)“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MS:213)。
据此,可以说,康德的“意志”(如不做特别说明,以下都指的是意志Ⅱ)与“理性”首先都是一种“欲求能力”。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即意味着依据法则而行动的意愿。正如康德所一再表明的,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种实践性:“纯粹理性单凭自身就是实践的,并给予(人)一条我称之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KpV:31)纯粹理性既能够产生行动,也能够产生行动的原则。同时,它也是纯粹意志:“因为纯粹的、就自身而言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意志作为独立于经验性条件的,作为纯粹意志,被设想为被法则的纯然形式所规定的,而这个规定根据则被视为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KpV:31)可见,应该时刻注意到,在康德的文本中,意志与理性拥有着不同层次的涵义,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理解。由于理性相当于意志,因此,我们也应该对其做出进一步区分,即作为仅仅确立原则的理性(理性Ⅰ)与既能够确立原则也同时具有行动能力的理性(理性Ⅱ)。也就是说,理性Ⅱ和意志Ⅱ也是等价的。在康德哲学的概念体系中,正像“意志”既包含着意志Ⅰ(纯粹理性及其法则)也包含着任性一样,“理性”也由于拥有实际的执行能力而能够成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康德在《奠基》中的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人在自己里面确实发现一种能力,他凭借这种能力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事物区别开来,甚至就他被对象所刺激而言而与它自己区别开来,而这就是理性。理性作为纯粹的自动性,甚至在如下这一点上还居于知性之上:尽管知性也是自动性,并且不像感官那样仅仅包含惟有当人们被事物刺激(因而是承受的)时才产生的表象,但他从自己的活动出发所能够产生的概念,却无非是仅仅用于把感性表象置于规则之下并由此把它们在一个意识中统一起来的概念;没有这种对感性的应用,知性就不会思维任何东西;而与此相反,理性在理念的名义下表现出一种如此纯粹的自发性,以至于它由此远远地超越了感性能够提供给它的一切。”(GMS:452)
可见,康德所说的“理性”其实是一种具有“纯粹自发性”的实践力量。而休谟式的情感主义者的误解就在于,在他们的概念体系中,“理性”只是一种能够产生理由或者原则的推理能力,至于经验性的实际行动则必须用与这种“理性”完全判然有别的情感或者欲望去推动。这种观点在威廉斯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他看来,只是作为“纯粹的理性思维过程”,康德的“定言命令”属于“外在理由”,而不是能够促发行动的“内在理由”,因为只有情感或者欲望才能作为这种“内在理由”。
按照情感主义的见解,只有感性情感,或者康德所说的“偏好”才能够真正地促发行动。但是,在康德那里,任何感性要素都不可能被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与动机,否则就丧失了行动的道德属性。对于这种深刻的对立,本文认为,康德通过“意志”与“任性”确实提出了一种具有独特含义的“理性”的概念,也就是以上所说的理性Ⅱ(或者意志Ⅱ),由于必然与情感相关,作为欲求能力的“理性”或者“意志”,既是一种理智性活动,也是一种情感运作,因此,它既属于本体世界,也属于现象世界。按照先验哲学的观点,它体现着人的“理智性品格”与“经验性品格”的统一。
在《奠基》的第三章,康德区分了“两个世界”:对于人而言,“就纯然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把自己归入感官世界,但就在它里面可能是纯粹活动的东西(根本不通过刺激感官、而是直接达到意识的东西)而言把自己归入理智世界,但他对这一世界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GMS:451)。这种区分是基于康德在其理论哲学中所确立的“现象∕物自身”这一对概念所做的进一步阐述。康德认为,由于受到先天的感性形式的限制,我们只能够认识现象世界,而对于作为其根据的物自身却无法形成知识。某种意义上,物自身相当于“本体世界”。对于理性存在者来说,他的品格同时对应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首先,就它属于感官世界而言,它服从自然法则(他律);其次,就它属于理知世界而言,它服从不依赖于自然的、并非经验性的、而是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GMS:452)只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现象的与非现象的,即本体的)来说,“两个世界”对于理性存在者才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称其为“经验性品格”与“理智性品格”。重要的是,主体由于拥有统一性的理性而能够将两种品格同时置于自身当中。因此,理性存在者既能够作为现象世界中的主体,通过理性(知性)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而掌握经验性规律,又能够作为本体世界中的主体,通过理性(意志)形成道德法则并且产生相应的行动。在前者那里,人是受因果性法则所支配的不自由的主体;而在后者那里,人是能够以自己的意志作为原因从而“开启”一项行动的自由的主体。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统一性能力,理性以其认识性功能与实践性功能将主体同时确立为本体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存在。从思维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自由的,但对这种先验理念我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认识,然而,它可以反映到现象世界中来,即通过道德行动证明这种本体性自由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就把自己作为成员置入知性世界,并认识到意志的自律连同其成果,亦即道德性;但如果我们设想自己负有义务,我们就把自己视为属于感官世界,但同时也属于知性世界。”(GMS:453)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可以认为,康德所说的“理性”,其在本体世界拥有着作为行动指导原则的理由,而在现象世界则仍然呈现为一种具体的感性情感。也就是说,这种统一性的“理性”(理性Ⅱ)在两个世界中分别拥有两种状态,而后者是前者在经验性条件下的“映射”,即作为根据的理性(理性Ⅰ)及其原则,它必然将以感性的方式表现为行为的动机,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最为重要的道德情感—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前一个世界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知性世界”或者“本体世界”,后一个世界属于“感官世界”或者“现象世界”。同时,作为理性Ⅰ,康德将其称为纯粹的、认知性的理智能力,而作为理性Ⅱ,它不仅包含了理性Ⅰ,也同时具有实践性的执行能力。作为一种欲求能力,理性Ⅱ或者意志Ⅱ,将本体与现象、理智与情感连接起来,规定了道德主体的统一性的品格。
三、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理论的与实践的①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在不做特别说明时,一般所说的“理性”就是指理性Ⅱ,它既具有理性Ⅰ的认知能力,又具有能够促发行动的、作为“敬重”的情感能力,而在与“情感”相对的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理性”则指的是仅仅作为认知、推理能力的理性Ⅰ。
贝克指出,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并没有清楚地区分出“动机”与“动因”,因此给我们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区分至少对于康德来说并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同一于“理性”之中,或者说,只是理性在不同维度的表达。因此,几乎在同一处,康德既说道德法则是动机,又说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惟一的道德动机(KpV:78-79)。其实,正像本文所一再论证的,如果说道德法则是客观根据,那么敬重就是主观根据。不过,一些学者仍然认为,有必要在根本层面上说清楚,究竟何者在康德那里才是真正的道德动机。麦卡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解释,像瑞斯就认为:“是敬重的理智性方面在促发道德行动时发挥着作用,然而它的情感性方面,即敬重的情感,则是这一理智性方面对于某种感性倾向的效果。”“当道德法则规定意志时,那么尊重的情感就产生了,然而并不是这一效果产生了动机。”②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70.其中,麦卡蒂所引用的瑞斯的观点出自Andrews Reath,Kant’s Theory of Moral Sensibility:Respect for the Moral Law and the Influence of Inclination,Kant’s-Studien,1989,Vol.80,pp.284-302,p.287,p.290。第二种解释也属于理性主义,是由斯特拉通-莱克(Stratton-Lake)提出的,他和瑞斯一样,认为只有对于法则的认识而非敬重的情感才能够作为根本性动机。不过,二者的区别集中于这种情感与“关于道德法则的认识”的关系上。瑞斯认为尊重是由这种意识所引起的,二者是因果性关系;而斯特拉通-莱克认为二者是同一的,即尊重不是这种认识的附带产物,而是它的另一种描述。
麦卡蒂进一步表明,第三种解释是情感主义的,以格瓦拉(Guevara)为代表,他认为尊重的情感就是道德动机,它既是由对法则的认识产生的,又是与这种认识同一的。对于麦卡蒂来说,他更支持第三种解释,因为在他看来,仅仅以具有约束性作用的道德法则为动机,而忽视了主观性的情感,对于行动本身来说力量有些太弱了。不过,格瓦拉的解释中蕴含着一个观点,即尊重的情感被视为由道德法则规定的本体性的意志在感性世界的对应物,然而,这将导致理解上的困难:我们该如何解释道德上的软弱?这种现象是否也意味着某种本体世界中的道德软弱?也许,人们会猜想,是因为本体世界在表象为现象时某些东西丧失了,或者在本体世界中,意志是绝对地、充分地被法则所规定的,只是现象世界对它的模仿太过于粗糙了①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麦卡蒂认为,这些解释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他的观点是,并不应该将尊重的情感视为由道德法则所规定的本体性意志的感官表象。所谓本体、或者物自身,是就对象而言的。然而,尊重却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它并不关乎被表象的对象。“在表象一个对象时,我们所感到的愉悦并不涉及作为一个对象的自身。也就是说,我们感到愉悦与否并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意志作为一种观念。情感可能是包括身体或者精神活动在内的感官显象的主观反应(reactions),也可能是物自身理念的主观反应,但不是这些事物的显象(appearances)。因此,康德并不认为尊重的情感就是本体性意志的显象。他的主张是,这种是否愉悦的情感起源于一个行动是否符合道德法则的认知。”②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麦卡蒂指出,作为实践情感的敬重,就是一种“启动性”的力量,它是基于主体对道德法则的认识。首先,客观性法则提供了动机的方向;其次,主观性的敬重情感提供了力量。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客观性方向是同一的,但主观性力量却有可能是不同的,有的人会感到快乐多一些,而有的人则会感到痛苦多一些。对于此前的三种解释,他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更为正确,因为它们都主张尊重只是由法则所规定的意志的效果(effect)。然而,它们的不恰当之处在于,第一种解释否认了敬重所具有的“动机”角色,而仅仅把它当作理性认知的附带效果;相比而言,第三种解释正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但它一方面将意志与情感的关系解释为本体与现象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相比于同样可以作为动机的偏好,这种情感所具有的多变性的动机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③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可见,麦卡蒂的观点与我们之前的分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主要是,他反对将受到法则所规定的自由意志与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解释为本体与现象的因果性关系,而且,两方面若是完全对应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作为现象的情感的多样性变化。不过,如果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实际上与我们此前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麦卡蒂首先承认,本体性的自由意志是必然的存在,只是它如何具体转化为实际的动机,其中的机制由于超出了人的认知界限而无法被真正地说清楚④在“现象∕物自身”的问题上,麦卡蒂不是“一个世界、两种视角”的支持者,他批评了科斯嘉、阿利森等人的这一立场。后者主张只存在一个“中性的世界”,只是我们从肯定与否定的两种视角来考虑,才产生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概念,也就是说,“物自身”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意义。麦卡蒂认为,这种解释无法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提供有效的说明。只有承认本体世界的实存性,人才会是绝对自由的,而这要通过道德的行动加以实现。本体决定了现象,但是其中具体的运行机制是难以被领会的。经验性品格不可能赋予人以自由,我们必须承认理智性品格的首要性(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05-145)。。而麦卡蒂否认了自由意志与敬重之间存在着像本体与现象那样的因果关系,因为在他看来,情感不是由作为某种物自身的对象的刺激而引起的显象,而是生发于主体自身之中的感受。然而,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很可能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因为在康德看来,情感属于我们的内感官,与外感官一样,它是由某种作为物自身的对象刺激后所产生的显象。“关于内感官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只是像我们在内部被我们自己刺激的那样通过它来直观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就内感官而言把我们自己的主体仅仅当作显象、而不是按照它自己所是的东西来认识。”(KrV:B156)本体性的自由意志能够产生一种内感官,它呈现为经验性的品格,在第二批判中,康德继续说道:“主体的每一个行动的规定根据都处在属于过去的时间而且不再受它控制的东西里面(必须归于此列的也有他的已经做出的行为,以及在他自己的眼中作为现象对他来说可以由此得到规定的性格)。但是,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自己是物自身的同一个主体,却也把自己的存在本身就其不服从时间条件而言仅仅视为通过它凭借理性本身给自己立的法则可被规定的,而且在它的这种存在中,对它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先行于它的意志规定,相反,任何行动,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存在的任何按照内部感官变更着的规定,甚至它作为感性存在者的实存的整个序列,在对它的理知存在的意识中都必须仅仅被看作后果,而绝不看作它作为本体的因果性的规定根据。”(KpV:97)当本体性的自由意志反映为作为敬重的道德情感时,由于主体自身特殊的感性要素的影响,将呈现为有所不同的情感现象,但是,“敬重”始终是最为根本性的情感,否则就不会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总之,本文认为,即便是麦卡蒂本人也承认,在理论上,对于法则的意识是敬重的情感产生的原因,但在实践中,二者是同时发生的一种活动。在这一点上,理性主义解释与情感主义解释并不存在明显的对立。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始终基于康德所说的这句话:道德法则是作为客观根据的动因,而敬重是作为主观根据的动机。二者的区别其实只具有描述的而非实际的意义。对此,可以借助康德关于“知识”的分析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解。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我们没有任何先行于经验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却并不因此都产生于经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先天知识的纯粹的知性范畴所导致的(KrV:B1)。在现实中,我们必然要同时凭借感性经验与范畴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但是,在逻辑意义上,范畴起着根本性作用,即范畴先于感性经验,因为如果不以这些先天的概念为前提条件,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是经验的客体”(KrV:B125)。通过对于意志的规定,理性不仅产生道德法则,而且理性及其法则就是道德行为先天的根据与动机,但在实际的意志活动过程中,它必然呈现为对于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康德也将其称为“理性的兴趣”或者“道德兴趣”,它是促使行动发生的经验性的表象与力量。纯粹理性既是认识的、也是实践的,它与敬重的情感是“二而一”的关系,在道德主体那里是同时发生的,但类比于范畴与经验的关系,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是在先的,而敬重是在后的。
其实,相对于其他三种主张,麦卡蒂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从而使其最终的解释更为“精致”而已。不管怎样,麦卡蒂也一再表明,对于法则的意识与尊重的情感是同一的,它们统一于既具有理智性品格也具有经验性品格的主体之中。而在我们看来,它们就属于“理性”或者“意志”,即理性存在者所拥有的既能够立法也能够同时据此产生实际行动的能力。
结语
在康德那里,由于“理性”与“意志”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情感要素,因此,并不存在情感主义者所批判的理由与动机之间的割裂,道德主体对于理性法则的认识必然要体现为内心的敬重,从而促使主体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其中,康德通过“任性”这一概念,实现了“意志”从“理智性品格”向“经验性品格”的转换。并且,原来只具有认知性功能的“理性”拥有了实践性能力。然而,情感主义者未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眼中,康德的“理性”仅仅是一种认知推理能力。但实际上,康德的“理性”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在道德主体那里,它体现为整体性的“意志”。另外,正如我们此前所介绍的,情感主义者们断定只有情感(同情、仁爱)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根本性动机,因为它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知的冲动,相反,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性功能,从而能够形成更加合适的道德判断,而且只有这种纯粹的情感或者欲望才能够产生形成行动的促发性力量,这样的论断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康德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认知性功能只能来源于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理性(理性Ⅰ),作为低级的欲求能力,情感或者欲望只属于感性冲动,康德称之为“病理性的”,它们所产生的是心理上或者身体上的单纯的知觉,其中不可能包含任何有意识的判断。只有在理性的参与下,某种判断才可能发生,而即便是那种极为“薄弱的”判断,也必然是理性发生作用后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实践中,理性必须通过感性情感的方式被实现出来。也就是说,二者同一于一种心理活动中,由此才能促使相应的行为实际地发生,从而这种道德情感也具有认知与判断的功能。作为一般性的欲求能力,康德将其称为“理性”(理性Ⅱ)或者“意志”(意志Ⅱ)。如果仅仅就自由意志的表象来说,康德其实与休谟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能够作为行为动机的必定是一种情感或者欲望①盖耶指出,休谟与康德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一方面,休谟确实认为我们的目的总是由激情(passions)所决定的,但他也认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最终是由平静或者自由的激情所促动的。至少在否定的意义上,它摆脱了欲望的纠缠。因此,理性虽然可能是激情的奴隶,但我们也有一种根本性的成为理性的(reasonable)激情,并且享有它所带来的平静。另一方面,对于康德而言,道德的最终目的也是自由,尽管他对自由的理解比休谟更充分。而且,至少在经验层面,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认为,没有一种原初的对自由的激情,我们就不可能是道德的,尽管这种激情必须由拥有力量的理性(这种理性源于从我们的自由到所有人的自由)重新确立方向。因此,两个人都将道德的内容和可能性置于对自由的激情中,尽管在休谟那里,这相当于倾向理性的激情(a passion for reasonableness),然而,在康德那里,我们原初的对自由的激情必须被理性所驯服,而一旦如此,康德就不会将其再视作一种激情。”(Paul Guyer,Passions for Reason:Hume,Kant,and the Motivation for Morality,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86,No.2,2012,pp.4-21,p.5)盖耶进一步认为,由道德法则所规定的意志属于本体性自我,但在我们有意识地进行决定与推理的时候,它必然显现于经验性自我中,即愉快或者痛苦的自然情感之中。但是,他也指出,这种“本体性的选择”与“现象性的效果”之间的具体联系,是难以被说清的(Paul Guyer,Passions for Reason:Hume,Kant,and the Motivation for Morality,p.15)。盖耶试图将康德与休谟的分歧消弭到最小程度,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对的。但是,本文的观点更为细致:在理论意义上,康德坚持只有理性及其法则才是道德行为的客观根据,也是根本性的动机,而情感作为它的表象,只是实际的动机。休谟及追随他的情感主义者们,并不持有这一立场。。但是,与休谟不同的是,康德认为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其内在根据是理性及其法则,而非任何一种感性质料或者能力。理性与情感,都居于这种整体性的“意志”之中,而至于本体性的纯粹理性具体如何发生作用并形成敬重的情感与行动的意愿,则已经超出了目前的知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