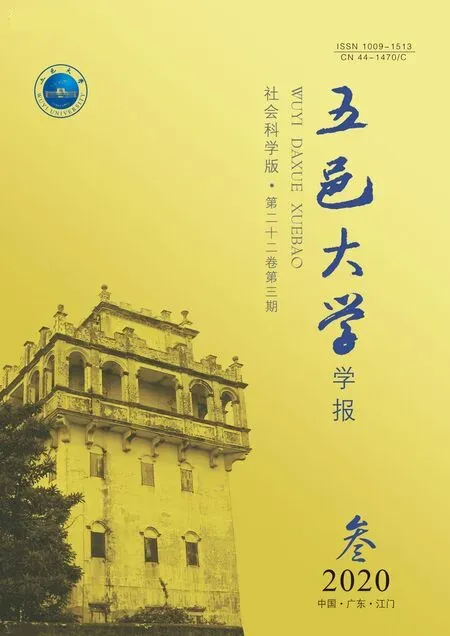四库“提要”对《圣谕广训》的历史书写
——基于学术与政治视角的考察
余志刚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自明代宣讲《圣谕六言》发展到清代宣讲《圣谕广训》(以下简称《广训》),封建社会“君师一体”的中国帝皇教导“愚夫愚妇”的圣谕文本及其宣讲制度,至此也发展到历史顶峰。雍正帝在推衍112字“上谕十六条”将之制成万言“广训”的过程中,特别撰写了一篇《圣谕广训序》(以下简称《广训序》),言简意赅地交代了他的用意。其子乾隆帝在下令编修《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时,将《广训》收入,要求撰写的“提要”也很好地反映了清帝的意志。以往的《广训》研究,只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文渊阁本或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中的《广训》“提要”,且多仅将其当作文本材料进行使用,而对各四库本《广训》“提要”中的文字异同及其原因,以至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内涵并未给以专门阐发①。基于此,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各本《广训》“提要”何以不同
翻检今日留存下来的《荟要》、《全书》以及殿本《四库提要》,不仅可以发现《广训》在收入《荟要》、《全书》各部类中并不一致,而且它们的“提要”文字也有差异。摛藻堂《荟要》本《广训》被归入《荟要》“史部”“诏令类”,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广训》被归入《全书》“子部一”“儒家类”,文溯阁本《广训》“提要”、殿本《四库提要》《广训》被归入“子部四”“儒家类四”。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同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差异较大,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同殿本《四库提要》所刊“提要”相同,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提要”同《荟要》本大体相同,文溯阁本《广训》“提要”同文津阁本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首先,《荟要》本、阁本《广训》被相应收入不同部类,显然同政治相关。自表面观之,由《荟要》本的“史部”降到阁本的“子部”,其地位似是降低的,然而,《荟要》本一开始预定的对象就是清帝,阁本的读者对象则经历由国家向社会(“南三阁”)的转变,而《四库提要》则是专门面向社会,一旦明晰《荟要》本与阁本《广训》所面向的对象之不同,就能洞悉其间的关窍远非表面那么简单。
其次,现存各种《广训》“提要”之所以不同,也同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大有关系。“四库全书馆”与“四库全书荟要处”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后,撰写书籍“提要”迅速成为编修《全书》《荟要》的一项重要工作:“编纂《四库全书》,悉仿刘向、曾巩等序录之例……《荟要》亦如其例。”四库馆臣在修书流程中各循其职,“提要”的撰写大致经过这样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们对所分担的书认真审核校理之后,按要求写出一篇提要,并提出入选……意见,然后由总纂官复核,有时意见不一,便由总纂官审定。”[1]经审定的“提要”同各书一样由不同的人抄录,形成两种《荟要》本、七种阁本。同时在各书已撰成“提要”基础上单独辑出《四库提要》,经由纪昀等人再三删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体完成并在五十七年(1792)交付武英殿刊刻。这样,《荟要》本、阁本与殿本《四库提要》“提要”都得以完成。但乾隆帝很快发现《全书》内容存在问题,“提要”亦然。尤其乾隆五十七年纪昀覆勘文津阁库书,“查出提要内删节、改窜及遗失私撰各篇页,与《总目》不符”,军机大臣阿桂等上奏,建议对此情况“要求一律赔换以臻完善,均应如纪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为换写……俟写毕后,仍责成纪昀带领官匠将文渊、文源二阁换写篇页,逐一抽换完竣,再赴文津阁,抽换整齐,免致歧误”②。存世的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同《四库提要》《广训》“提要”相同,而与它种阁本《广训》“提要”不同的原因初步“浮出水面”,这也给解释各四库本《广训》“提要”异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可即便如此,《四库提要》《广训》“提要”有无在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基础上撰成的可能呢?当无此种可能。比照今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广训》样式,可对此做实。首先,就书迹而言,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同排在其前的《广训序》、目录,排在其后的正文书迹显然非出于一人之手。其次,就原式而言,虽然“提要”在排序上是紧随目录之后,而非今日可据之断为撤换证据的在目录之前,并且其署恭校上年月日也在本分库办竣年月之前,但其版心题“提要”两字显然同“文渊阁库书”“原式”“所在的书版,版心仍题‘目录’”不同。再次,一般认为,其他六阁本是在文渊阁本基础上抄录而成,不仅有乾隆帝题诗可资佐证③,而且在修订《四库提要》之前,阁本提要一般较短,而现有文渊阁本《广训》“提要”较文溯阁本、文津阁本篇幅长得多(见下文)④。
再据《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与《荟要》本三种《广训》“提要”互勘,前二者文字一致并与《荟要》本(恭校上呈御前时间“记为”乾隆四十二年)文字大体相同,区别仅在前二者在后者文本上同加增“而于朔望日今有司合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一句(见下引文)。这种情况容易理解,原因当在三者“提要”底本皆本于一个,基本可推就是纪昀等定夺的《荟要》本《广训》“提要”,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提要”为陆续抄出,两者所据底本相同也不存在疑问,唯一的疑问是三者中前二者所据底本上因何加添上述一句的情形目前还不清楚。总的来说,虽然前二者何以加此一句目前未找到史料待考,但上述事实却给揭开三种阁本以至各四库本《广训》“提要”何以不同进一步提供了线索与支撑。
同为阁本,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恭校上呈御前。文渊阁本《全书》完成在前,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全书》完成在后,照理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提要”当同文渊阁本,但现在前两种阁本“提要”同文渊阁本不同,则应有全书抄成完竣后的撤换。在撤换前,三种阁本《广训》“提要”文字应该一致。
据上述基本可推,《荟要》本《广训》“提要”先出,文渊阁本《广训》“提要”次出,但很可能在乾隆五十七后进行过“换写”。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提要”依次继出,但文津阁本《广训》“提要”在文渊阁本相关“提要”“换写”后并未照阿桂等奏议进行“换写”,文溯阁本《广训》“提要”也未“换写”。《四库提要》所收《广训》“提要”最后完成,它当是纪昀等的手笔。现存各本《广训》“提要”行文不同的原因当在于此。
二、《广训序》与《广训》“提要”
雍正帝给一部由皇考同自己两代协力完成的政治读物作序,其御笔亲撰的最高权威性使《广训》“之所由作”的政治内涵不同寻常。《广训序》文曰:
《书》曰: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记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实之道,为牖民觉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圣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万物,义正万民,六十年来宵衣旰食,祗期薄海内外兴仁讲让、革薄从忠,共成亲逊之风,永享升平之治。故特颁上谕十六条,晓谕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视尔编氓诚如赤子,圣有谟训,明征定保,万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诰诫以示提撕,谨将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往复周详,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无非奉先志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愿尔兵民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嗣子孙并受其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理岂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2]
从行文逻辑看,“序”文首先将谥号“仁皇帝”的康熙帝之仁德及其推行的《圣谕十六条》宣讲统绪,直通到《尚书》《礼记》所载的“道人以木铎徇于路”与司徒修六礼、明七教,用意无非论证大清继统之纯正,乃接续三代之“统”,兴仁行教一本于三代。其次,雍正帝自序自证自己得统之纯正,以“三年无改先王之政”仁孝面目出现在臣民面前,“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这符合雍亲王在康熙晚年塑造的形象;紧接着,在以亲身示范给军民人等以表率便于树立“以孝治国”理念的同时,表示要在治下继续大力推行宣讲,经由步步演绎,使紧密相连的合法性层层递进。最后,以《易经》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来期许家国安吉、共臻升平之治,这是论证完成的结语。《广训序》层层递进的政治意图不言自明,它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构成一个严谨的论证逻辑链:论述圣谕宣讲的传承,重点在论证雍正帝自身的合法性;论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重点落在将大清的统绪接续到三代(主要在可考的周朝)。
乾隆帝在下令编修《荟要》《全书》时,将《广训》收入,要求撰写的“提要”也很好地反映了清帝的意志。存世的《荟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广训》“提要”文曰:
《圣谕广训》一卷 臣等谨案:《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以晓谕薄海臣民垂教万世;而《广训》万言则世宗宪皇帝因而阐发之,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而绍闻善述之模亦亘古为昭矣。是书简帙虽约义蕴实宏,方今布在学宫,著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合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加此一句——笔者注),盖所以陶成民俗袛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3]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1]426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4]
存世的文渊阁本、《四库提要》《广训》“提要”文曰:
《圣谕广训》一卷 臣等(《四库提要》少“臣等”两字及恭校上年月——笔者注)谨案:《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广训》一万馀言,则我世宗宪皇帝推绎圣谟以垂范奕世者也。粤稽虞代,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当时必有诰诫之文,今佚不可考。周礼,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又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教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其法今亦不传。然而圣帝明王膺作君作师之任,其启迪愚蒙,必反覆丁宁,申以文告,则其制章章可考,故书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也。惟是历代以来,如家训、世范之类,率儒者私教於一家。琴堂谕俗编之类,亦守令自行於一邑。罕闻九重挥翰,为愚夫愚妇特撰一编。独明太祖所著《资治通训》诸书,具载《永乐大典》中,而义或不醇,词或不雅,世亦无述焉。洪惟我圣祖仁皇帝体天牖下民之意,亲挥宸翰,示亿兆以典型。我世宗宪皇帝复钦承觉世之旨,郑重申明,俾家弦户诵。圣有谟训,词约义宏,括为十有六语不为少,演为一万馀言不为多。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而皓首不能罄其蕴。诚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矣。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5]
抛开体例的差异,在内容上大体可断定上述“提要”为同一底稿的产物,彼此的共性大于差异性。《荟要》本《广训》“提要”当是其他“提要”撰写的基础。文渊阁本《广训》“提要”的“换写”与《荟要》本《广训》“提要”的未予“换写”体现了朝廷内外有别的方针。区别于上列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尤其是深藏宫中的《荟要》本《广训》“提要”,文渊阁本行文中添加的“粤稽虞代……世亦无述焉”、替换的“诚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矣”等内容,显然是总纂官纪昀等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同样是将圣谕宣讲制度接续到三代圣王,纪昀等充分运用朴学的传统,使文渊阁本《广训》“提要”在行文措辞上拿捏的分寸更适中,既没有背离雍正帝所撰《广训序》的论证逻辑(《四库提要》《广训》“提要”刻意模仿《广训序》文路),又保证了所论论据的严谨,还不忘迎合今上乾隆帝的“文治”虚荣心。文渊阁本《广训》“提要”所反映的强化统绪之正的自洽路径就在于此。
首先,四库馆臣将圣谕宣讲的源头追溯至史籍有载、后世无传的虞夏时代的司徒“敬敷五教”,以及《周礼》州长、族师月吉读法及其劝善纠恶上;同时将此中反映的清帝“君师一体”的统绪,接到《尚书·洪范》语境中的古圣王“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馆臣的行文比《广训序》更有说服力。其次,馆臣以古者圣王“膺作君作师之任”“启迪愚蒙”相号召,追溯与评价历代以来效仿其意的家族及地方性实践,感慨罕有可匹接此正传者,唯一法此遗意的明太祖还学得粗糙,进而得出有且只有伊等躬逢的圣清才得纯正之统绪。这一拉一伸、一抑一扬以“舍我其谁”的气势抬高皇清,同时还不忘借此贬低《永乐大典》而自抬身价吹捧一下在纂修的《全书》。此处馆臣不仅充分运用朴学传统论证严谨,而且格外注意迎合乾隆帝“盛世”大兴“文治”的虚荣心。最后,既然大清得中华之正传,借烘云托月的手法,馆臣一鼓作气将康雍两代接续而成的《广训》推到“世为天下则”的地步不亦宜乎!经由替天子代言的便利,馆臣将《广训》的政治地位一并上升至《圣谕十六条》“纲”的高度。《荟要》本的“史部”与阁本及《四库提要》的“子部”部类差异,并不影响这种“纲”的认定。士子岁科两试需要默写《广训》一两百字、军民人等每月朔望需参加讲读活动等,更在政治实践上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三、《广训》与“祖宗家法”
雍正朝“万言谕”《广训》虽维持着“上谕十六条”是“纲”、“广训”是“目”的布局,但至迟在乾隆朝《广训》的政治地位一并上升为“纲”,后继之君效仿先帝经由乾纲独断的绝对权力从容地完成这项政治认定。乾隆五年,清帝下令敕修并作序刊布的《世宗宪皇帝圣训》(后收入《全书》)将《广训序》收入卷九“法祖”内(正文未收入)[6]。这同雍正年间将“上谕十六条”收入《圣祖仁皇帝圣训》的做法如出一辙。到乾隆中,不仅《广训》宣讲收入《学政全书》等典制书,而且《荟要》《全书》皆收《广训》,这正说明朝廷将《广训》及其宣讲当作“世为天下则矣”的“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只能继承而不能更张。乾隆帝在《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中对清室“圣圣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大加推崇的同时,是这样看待“上谕十六条”与《广训》同孝道的关系的:“……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上谕十六条》,以敦孝悌、重人伦为首。及我皇父,嗣登宸极,迪光继述,衍《圣谕广训》之书于敦孝悌、重人伦,反覆开明,惟恐人之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7]既然人伦以孝悌为先,帝王莫能外之。难怪乾隆二年汪漋请就《广训》颁“简要训谕”被清帝无情拒绝:
……皇祖皇考洋洋圣谟,字字切于民生日用,诚使讲明切究实力奉行,自有革薄从忠之效,朕即颁谕旨,其简切明要,该括无遗,岂能加于《圣谕十六条》。其谆切周详,知愚共晓,岂能过于《圣谕广训》。若奉行不力,不过地方有司多一具文而巳,汪漋所请不必行……[8]
嘉庆五年(1800)在要求官场遵行雍正帝“正百官”“特颁训谕”的同时,针对某御史请朕躬“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论”“条陈”的请求,同先帝一样嘉庆帝以《广训》对此内容皆备而给以拒绝:
……再各省颁行《圣谕广训》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挈其纲,皇祖世宗宪皇帝详其目,牖民觉世,剀切详明,近有御史条陈,请朕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论,宣谕百姓,朕思《圣谕广训》纲举目张,朕即别制训辞,亦断不能出圣祖世宗范围。至于整饬百民,朕亦惟有禀承前志,以期实力奉行大小臣工,但能恪守彝训,即不殊听朕诲言……[9]
道光十九年(1839)针对两江总督“陈銮等奏,请饬下儒臣推阐《圣谕广训》颁发各省”建议,道光帝独具匠心(在今日看来尤其意味深长)地命儒臣“推阐圣谕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颁发全国:
……向例各直省地方官,于朔望宣讲圣谕广训……良法美意,允宜永远遵行。惟州县地方辽阔,宣讲仍虑未周,著照所请嗣后各省学政到任,即恭书圣训广训,刊刻刷印,颁行各学……并著翰林院敬谨推阐圣谕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拟撰有韵之文进呈,候朕钦定颁发各省……[10]
自乾嘉以来,各地官员多有衍释《广训》的作品,这条建议本无特殊之处。但从道光帝煞有介事地仅要求单独将《广训》第七条“崇正学以黜异端”撰成有韵之文,并须“朕钦定颁发各省”来看,这种举动颇不寻常。嘉庆元年至八年白莲教起义蔓延川、楚、豫、秦四省,(保守估计)朝廷耗费白银1.2亿两才将之镇压下去;嘉庆十九年天理教起义曾试图攻入皇宫,时为亲王的道光帝甚至举枪“击匪”。在国势转衰、痼疾丛生、各种社会矛盾频发、民间宗派“异端”蜂起的情况下,加之嘉庆十一年新教已进入中国,中西文明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日渐增加,此时钦定颁发“四言韵文”,实在是颇有预见性的。咸同二帝继位之初,一再诏举国宣讲“四言韵文”不是偶然的。
“庚子之变”后,朝廷意识到变更成法已迫在眉睫。在新政中,以汇成一股潮流的设立宣讲所为例,朝廷的限度是允许添加开民智的内容,但“忠君、尊孔”必须置于首位,任何违害朝廷统绪的讲演均不得涉及:“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学部颁行宣传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但“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不得涉及政治演说及一切偏激之谈”。甚至为防范进行革命演说或革命党渗透,要求“凡宣讲时,巡警官得派明白事理之巡警员旁听,遇有妨碍治安之演说,可使之立时停讲”。[11]添加新思想新内容甚至采用新方式的宣讲,依然保持着“老大帝国……风行草偃、以上化下、以长化少”[12]规训(启蒙)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其逻辑及其形成逻辑,共同论证着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特色。
结 语
清室有“法祖”传统,雍正帝亲撰的《广训序》在整体上建构了朝廷圣谕宣讲制度的合法性。乾隆帝钦定的各四库本《广训》“提要”则对之给以强化,以充实“祖宗家法”的形式稳固了这一教化方略。就四库馆臣所撰“提要”对《广训》的书写而言,各本《广训》“提要”的撰写、润饰与“换写”服从于这一政治意图的实施。《广训》“提要”的撰写虽说出于学术目的,但在乾隆朝日益增长的政治高压下,其政治考量压倒学术考量,在文化工程领域起着配合政治思想控制的作用。在内外有别的政治语境中,儒臣代帝王而作、以帝王钦定形式颁行的各本《广训》“提要”给雍正帝所撰《广训序》及其颁行全国的《广训》作了坚实有力的注脚。
注释:
①学者们在研究《广训》时,多将文渊阁本或《四库提要》所收相关“提要”作为材料进行使用,而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详见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廖振旺:《“万岁爷意思说”——试论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圣谕广训〉的出版与认识》,(台湾)《汉学研究》2008年第3期;姚达兑:《〈性理精义〉与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 8期;等等。或注意到《荟要》本、文渊阁本、《四库提要》相关“提要”不同,但其政治文化内涵还有进一步解读空间,见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4—65、477页。
②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07页。
③详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影印本,第697、815页。
④关于鉴别七阁本“提要”是否原文,详见刘远游:《〈四库全书〉卷首提要的原文和撤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