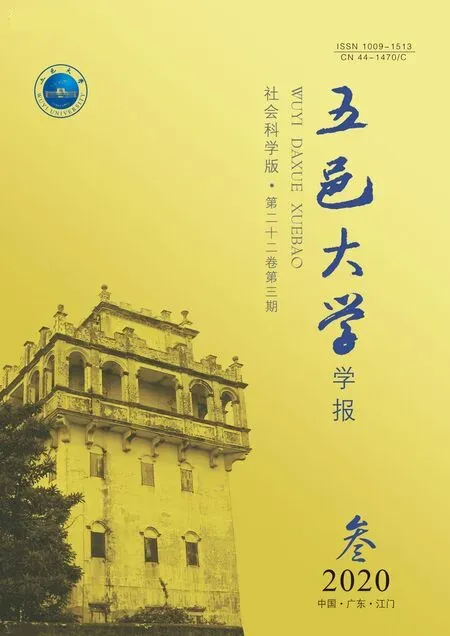陈澧批点《日知录》述论
邹 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陈澧,字兰甫、一字兰浦,号东塾,广东番禺人,清代著名学者。其学所涉颇广,于诗文、经史、乐律、算术等方面均有建树。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陈澧批点本《日知录》八册,涉及《日知录》相关内容的评述、辨析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批语字迹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陈澧手稿《东塾杂俎》字迹完全一致。此外,有批语见于陈澧《东塾读书记》,如《日知录》卷三《韩城》篇“梁山、韩城皆有,不言其地”句,眉批:“《毛传》云:禹治梁山,据《禹贡》‘治梁及岐’之文也,安得云《毛传》不言其地乎?”(十九页)亦见于《东塾读书记》卷六,云:“王肃自谓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毛传云:‘禹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贡》‘治梁及岐’之文也。”[1]115所以,此本当为陈澧亲笔批点无疑。
一、陈澧批点本《日知录》概况
《日知录》三十二卷,索书号:1249,凡八册,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上刻卷数,下刻页数。是书第一册封面有“番禺陈氏东塾藏书印”朱文方印,扉页题“《日知录》,顾宁人先生著,经义斋藏板”。篇首有潘耒序,钤“潘耒之印”白文方印、“学于旧史氏”白文方印,第八册末页有“陈庆龢字公穆”白文长印。
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已有初刻八卷本行世,康熙九年始刻,康熙十年完成。[2]8潘耒《序》称:“耒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缮写成轶,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王悔斋赠以买山之资,举界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2]2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去世,潘耒从顾家求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编辑,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始刊刻,为三十二卷,文字约多八卷本五倍。《日知录》亦是三十二卷,当出于潘刻三十二卷本,扉页题“经义斋藏板”,“经义斋”为嘉、道间苏州胥门书坊[3],但所刻年月不详。
封面“番禺陈氏东塾藏书印”朱文方印为陈澧藏书印,末页“陈庆龢字公穆”白文长印为陈澧长孙陈庆龢印。陈庆龢,字公穆,一字悟庵,号容园,光绪十七年副贡,历任广雅书院分校菊坡精舍学长,内阁额外中书。入民国后历任国务院咨议,外交部秘书兼参事,驻檀香山领事。建国后聘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述训》《蓉园杂钞》等。
二、陈澧批点《日知录》的特色
陈澧批点《日知录》的百余条批语,在评述内容上,将直接评判、结合现实评点、补充评述三者结合;此外,辨析发微、驳问质疑、正讹文补脱文、注释音义亦是其批点特色。解析如下:
(一)评述内容。陈澧对《日知录》内容的评述可分为直接评判、结合现实评点、补充评述三类:
1.直接评判。如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句,眉批:“此论稍偏。”按,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云:“汝成案,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係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2]1486陈澧认为“此论稍偏”,或与黄汝成合。又如卷二十七《杜子美诗注》:“《行次昭陵》诗‘威定虎狼都’注引《苏秦传》:‘秦,虎狼之国’,甚为无理。此乃用《秦本纪赞》‘据狼、弧,蹈参、伐’”句,眉批:“此似不然。”按,“虎狼”到底出自何处,历来有争议,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虎狼都,关中也。谓太宗之取天下,先以神武定关中。《苏秦传》,‘秦,虎狼之国也。’”[4]《杜诗镜铨》云:“顾炎武曰:‘《天官书》,西宫参为白虎,东一星曰狼’,《秦本纪赞》:‘据狼、弧,蹈参、伐’,乃是秦之分野,旧引《苏秦传》未当。”[5]《杜诗详注》则备二说:“张延注‘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据关中’,《苏秦传》:‘秦,虎狼之国也’。顾炎武《日知录》以虎狼为秦分野,盖据《天官书》,‘西宫参为白虎,东一星曰狼’,《秦本纪赞》:‘据狼、弧,蹈参、伐’,此另一说。”[6]陈澧云“此似不然”,或是赞同“虎狼”出自《苏秦传》。
2.结合现实评点。陈澧读书,多会结合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来进行评点,如卷八《员阙》:“不过索一丁忧之缺”句,眉批:“近时外官有病危者,则群起而谋其缺矣。”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始出补外”句,眉批:“今则外官不称职,入为京官。”按,以上两条批语,可见晚清官场风气不好,病危的官员早就被同行虎视眈眈欲谋其缺,无能之人却能为京官。
3.补充评述。补充评述又可分为引用解释、自我阐发、补充说明三种:
(1)引用解释。如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古者郎官出宰”句,眉批:“《韩非子》曰:‘宰相必出于州郡。’”按,此条见于《韩非子·显学》,原文云:“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7]此处强调文臣武将的选拔应注重基层工作经验。又如卷二十三《已祧不讳》:“宋真宗名‘恒’”句,眉批:“《论语·南人》章,《集注》讳‘恒’为‘常’。”按,此条见于《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朱熹《集注》云:“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国之人。恒,常久也”[8]。
(2)自我阐发。如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题上眉批:“愚谓道者,生死之道。有生必有死,有寿亦有夭。知此,则夕死可矣。”按,陈澧认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指生死之道,即要认识到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事情。
(3)补充说明。如卷十三《重厚》:“今之词人”句,眉批:“袁简斋是也。”按,袁简斋,即袁枚。袁枚的诗作被一些人认为是“淫词艳曲”,陈澧亦认为如是。
(二)辨析发微。如卷三《韩城》:“世谓‘寒号’非也”句,眉批:“王肃好与郑立异,因《潜夫论》有韩侯国近燕之说,遂以当时所谓‘寒号’者当之。郦道元又因王肃之说而以高梁水所出者为梁山,其实皆由于《潜夫论》之谬说耳。”按,《潜夫论》所谓“韩侯国近燕之说”,见于卷九“志氏姓”第三十五,云:“昔周宣王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9]《水经注》云:“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动迁也。’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之寒号城。’”[10]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云:“原注:《魏书·地形志》‘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杨氏曰:‘据《水经注》,则周有两韩国,不可不变。’”[2]167陈澧此处辨析“寒号”城错误根源,认为来自《潜夫论》的谬说。
(三)驳问质疑。如卷三《韩城》:“岂有役两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句,眉批:“燕师至韩,当时必有其故,但不可考耳,不能悬断其必无也。《崧高》诗云:‘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召伯可以营申伯之城,燕师不可完韩侯之城乎?”按,召伯,即姬奭,封地在蓟(今北京)。申伯,姜姓,封地申国(今河南南阳)。二人封地距离较远,但召伯却谋求申伯的城池。陈澧以此来驳斥《日知录》“岂有役两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
(四)正讹文,补脱文。如卷三十一《邹平台二县》:“晋囗梁邹入邹县”句,眉批:“‘晋’下当是‘省’字。”按,陈澧批点本《日知录》“晋”后脱去“省”字,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囗”作“省”。卷三十二《而》:“故后汉督邮斑碑柔远而迩”句,眉批:“‘而迩’之‘而’当作‘耐’,即‘能’字也。”按,《日知录集释》作“而”。
(五)注释音义。如卷三十二《巳》:“今人以辰巳之巳读为士音”句,眉批:“‘士’字本上声,今读去声亦误。”《元》:“汉‘原庙’之‘原’,皆作‘再’字解”句,眉批:“‘原’即水源之‘源’,作本字解未为不可。”按,陈澧认为“原庙”之“原”可作本字解,《说文解字注》云:“‘原,水本也。’各本作‘水泉本也’。今删正。月令《百泉注》曰:‘众水始所出为百源。’单呼曰‘原’。累呼曰‘原泉’。”[11]又如《豆》:“《史记》作饭菽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称‘豆’”句,眉批:“古音‘菽’与‘豆’同,故以同音假借用‘豆’字”。
三、从批语看顾炎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对陈澧的影响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即提倡学术应对社会产生实用价值。潘耒《日知录序》云:“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土风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2]2“匡世”“救世”是“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特征。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多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着力在学术中实现“匡世”和“救世”。
作为晚清岭南的大学者,陈澧十分推崇顾炎武,这从其《日知录》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例如卷七《听其言也厉》:“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句,眉批:“《正义》名言甚多,自采无人拈出,惟亭林先生耳。先生之读书,真不可及也。”他曾把顾炎武比作孟子,《东塾读书记》云:“孟子论‘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振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矣。”[1]63又《学思自记》云:“顾亭林之学,能有效之者乎,吾老矣。”[12]759可见陈澧十分推崇顾炎武。
陈澧尤其重视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他在《与胡伯蓟书》中说:“《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天下,此其在数十年之后者也。”[13]陈澧所指的书,即其所著的《东塾读书记》(又名《学思录》),他在《读书记序》中说:“生平敬慕顾氏《日知录》,顾氏书毕载天下事,今惟读书一事而已,不敢窃比也。”[14]又说:“《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12]758可见《日知录》对陈澧《学思录》的成书具有重要影响,陈澧推崇顾炎武并重视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陈澧《日知录》批语多体现“经世致用”,如卷九《京官必用守令》,题上眉批:“京官必用守令,是也。然亦有籍者守令称职则当久任,不称职即当降黜矣。当如何而入为京官,宜更酌之。”又如卷十六《拟题》:“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句,眉批:“不可太难,科场但取天下之中材,不可太难。”再如卷二十二《郡县》“秦始皇议封建”句,眉批:“亭林先生欲使县令世袭,余亦以为县令最高之选,不过道士而已,而使世袭,太过优矣。”以上皆可看出陈澧“经世致用”的思想。
四、结 语
《日知录》自成书以来,阎若璩、沈彤、杨宁、钱大昕均对其有过校勘和研究,嘉定黄汝成博采诸家疏解,对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本《日知录》逐卷校释,成《日知录校释》三十二卷,此后其又经过详加审校,在撰写《日知录刊误》《续刊误》时,对原刻做了修正。至此,《日知录》资料可谓大备。陈澧批点本《日知录》的发现,在诸家之外,可为《日知录》研究和陈澧学术思想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日知录》陈澧批语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