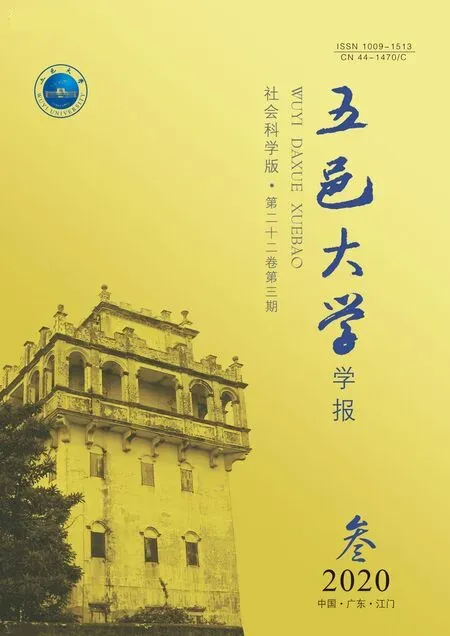互助·启蒙·焦虑
——1940-1960香港小说中“作家”的生存境遇
王 琨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0)
1940—1960年代的香港现代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作家形象,如侣伦《穷巷》的高怀、舒巷城《太阳下山了》的张凡和刘以鬯《酒徒》的酒徒,他们是作家对时代文化、社会人生、理想价值的多重思考和表达的化身,同时也是彼时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黄继持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小说有着“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1]三部小说中的作家活动背景是1940-1960年代的香港社会,他们都是苦闷、彷徨不得志的失意文人,但又因为个人际遇与时代环境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高怀与他人的互助友爱、张凡与少年林江的相互启蒙,以及酒徒对自我的迷失与放逐,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存姿态,他们既有自己的文艺原则需要坚守,也要适应香港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以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在二者的权衡中确认自我的艰难历程,揭示了在商业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变迁。
一、《穷巷》里作家的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侣伦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生于1911年,对于香港半殖民地文化有着切身体会。他的小说是香港本土叙事的重要源头,也是香港都市书写的范本,其早期创作总体上呈现出华洋杂陈的香港都市浪漫风味。创作于1948年的《穷巷》,属于侣伦后期的创作,在风格上趋于现实主义,小说除了对香港本土人们的生活进行写实呈现以外,更注重对彼时香港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失业、经济复苏、拜金主义等现象的展露,进而强调这些现象对个体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影响。小说最初连载于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热风》上。作为一个左翼刊物,文艺的现实干预功能和民族化、大众化方向是其主要办刊宗旨,而《穷巷》的成功是侣伦深入开掘香港文化资源而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的结果”,[2]31侣伦的《穷巷》因为其对香港底层的关注,“作品流露出来的‘社会主义’倾向,也使得‘当年左翼文坛许为同道中人’。”[3],侣伦虽然思想立场上偏向左翼意识形态,但在具体文学创作上的左翼文学痕迹却相对淡泊,《穷巷》的成功之处在于对香港商业社会中本地乡土意识的表现,人物命运较为集中客观地反映了港人在1940年代转型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穷巷》所书写的“无论是战后经济表面的繁华和大批难民涌入的困窘交织而成的香港历史的变迁,还是由衣食住行琐细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市民日常生态,在小说中都有极为真切的描写”[4]。战后的香港在迅速地复原繁荣,也在迅速地复原丑恶,小说采用写实手法,以抗战胜利后的香港为背景,反映底层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生活,讲述他们在拥挤、逼仄的穷巷里乐观互助,共同抵御贫穷和黑恶势力,怀着坚定的信念迎接未来生活的挑战,这些自然符合左翼文学的叙事模式。但左翼文学所持有的人生关怀,在侣伦的笔下不是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来完成的,而是将草根阶层的自在自为状态进行集中展现,体现出香港1940年代的社会风貌。战后香港失业现象普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部分就是失业者,只有作家高怀和教师罗建以微薄的收入供给大家日常开销,他们随时有被包租婆驱逐的可能,但他们之间建立起了可贵的联盟,能够同甘苦、共患难,齐心协力面对外力的打击。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下,他们仍然收留了失足女白玫,五个人融洽、乐观地互相帮扶、鼓励着渡过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他们之间的情谊是香港工业社会到来前的最后一曲乡音。小说在讴歌底层民众间人情美的同时,强调善与恶、美与丑、穷与富的对立,无情鞭答了人性之恶。作者以强烈的憎恶和鄙视,刻画了嗜财如命的阿贞之母,冷漠自私的包租婆,残忍暴虐的黑恶势力,这些人性有亏的形象,从反面衬托了高怀等五人品格上的高尚与无私。这样一种善恶分明的创作立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侣伦的价值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于人物性格、行为的描绘,更着重从人物内心出发,如高怀对白玫的救助、贡献自己稿酬去维持大家生计的慷慨,都是一种自发行为,包括罗建为了维持家人生活任劳任怨地工作,都是个体忠于自我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生存表达。这些在无形中削弱了左翼文学所强调的反抗社会体制、表达底层民心的创作意图。
在小说结尾,杜全因为恋爱失败、求生无门而跳楼自杀,另外四人因无钱续租被赶上街头,但高怀仍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强忍着悲痛,安慰其余几人:我们是有前途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与香港的时代风潮相应和,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尚未来袭的四五十年代,作家知识分子的个人物质欲求较低,更重视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价值的界定标准则是能否有益于他人与社会。高怀作为一名在内地参与过抗日战争的记者,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体察到人民的疾苦,因而更加珍惜自我与他人的日常点滴,在细微处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关怀,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总要有所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4]33高怀的独立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他对周围人的同情与身体力行的帮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现实情怀。
高怀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侣伦的人格投影,体现了侣伦的文化人格与道德理想。他们有着共同的内地参战经验,战乱和流亡,使他们在思想上倾向于左翼,注重对社会底层和弱者的关怀,对小人物的关怀和书写充溢着民间生命力。“《穷巷》的成功是侣伦深入开掘香港文化资源而超越当时香港 ‘政治化’状态的结果”[2]32。高怀所置身的香港正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期,文化风气浮噪,纯文学写作在商业社会的立足之地越来越狭小,在文学与商业联系越来越密切的香港社会,三毫子小说、报纸副刊、天空小说等不同传播形式的通俗文学的受众越来越广。在这种趋势下,高怀纵使被贫穷逼迫,仍有着君子固穷的高尚节操,孜孜不倦地进行自我的严肃文学译著工作,正像高怀开导杜全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做事只要合道理,只要对得住良心,旁人怎样看法怎样想法都不必管。高怀对于自我内心的坚守,如作者侣伦一样,从来不迁就时尚,不肯媚俗去写迎合地方性的流行趣味作品,他们对文艺范式的执守,延续了传统知识分子清明秉正、独善其身的优良传统,并在香港文学商业化的趋势中,使得现实主义等小说传统得以延续发展,并深刻影响了后代香港本土作家创作。
二、《太阳下山了》中作家与少年的双向启蒙
战后香港小说中的本土化书写得到了长足发展,相比较于《穷巷》对香港社会中底层人物间贫富差距明显、善恶两极的对立描写,舒巷城的《太阳落山了》摒弃了人物形态的两极分化写法,对香港下层生活状态和草根阶层的生活状态进行自然的呈露,“在情节结构、叙述文体及地方性各方面”突破了“左翼文学模式”,[5]开始初现香港乡土书写的特色,以香港民众所长久生活的里街小巷、渔村码头为背景,对平凡小人物的喜乐哀愁进行自然状态下的呈现。与侣伦在《穷巷》中着重强调社会矛盾和善恶两极分化的写法不同,《太阳下山了》被称为香港乡土书写的典范,淡化了阶级对立观念,以平民角度讲述平民故事,对边缘个体生存状态的体察,对香港世情的书写,彰显了作者浓厚的地域情怀。小说用舒缓的笔调对香港底层社会进行从容展露,谱写出一曲独属于香港的田园牧歌。
小说中的张凡是一位具有小资情调的作家,他因为情感与生活的双重受挫,搬到贫民窟成为少年林江的邻居。张凡的出现对于林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十二三岁的林江正属于叛逆期,因为家境困难只能离开学校,在社会上游荡,沉迷于街头讲古和武侠小说,他的文学资源和生存哲学皆源于此,如他对《水浒传》如痴如醉的阅读,欣赏水浒英雄的侠义精神和快意恩仇的性情,他在生活中对江湖义气的奉行、对英雄主义的自我实践,体现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在香港社会的生命力。但林江纵有一腔古道热肠,无奈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个人生的节点上,稍微走错一步都有可能自毁前程。对于林江的英雄梦,张凡提醒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并非只有除暴安良才叫英雄,张凡在恰当的时候给林江以人生的引导,小说中也不断穿插讲述林江对阅读的痴迷、对写作的神往。张凡欣赏林江的文学天赋,乐意于培养他的文学爱好,介绍林江读巴金、老舍、高尔基等具有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作家,因而林江的文学视野进一步扩大,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更为具体,也更加充满向往。小说中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经济迅速起飞的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快,纯文学创作的前景日渐没落,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文人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将写作与商业联姻成为作家的生存方式之一,但张凡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孤守清贫,当投机文人唐仲廉专程赶到西湾河,邀请张凡写低俗小说以谋取利润的时候,张凡断然拒绝了这种金钱诱惑。林江在旁边目睹了这一过程,并获得一定的人生启迪,这一启迪的意义不止是让林江明白文学的尊严,更影响了林江的金钱价值观,对一个少年来说具有极为可贵深远的意义。张凡对林江的启蒙,并非高高在上的概念式宣讲,而是在身体力行中让林江受到教育,感悟到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如何尊严地活着。
在张凡的影响下,林江渐渐能够认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莫基仔的相识,是他自我交际范围的一次拓展,也是成长的一次远行。通过对莫基仔遭遇的旁观与悲痛体验,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比自己不幸的人有很多。林江尽己所能地帮助莫基仔一家。他的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乐善好施、除暴安良的美好品质。小说的最后,林江得知自己的孤儿身世后,毅然担当起生活的重担,带着养母与非亲非故的弟弟,一起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对亲人的责任感,成为他坚守的人生法则。他对于责任的勇敢担当,显然秉承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中的孝悌观念,在张凡的启示下,“林江经历了‘隔离’到‘启蒙’到‘回归’的成长模式,从蒙昧无知的街童,成长为对人生理想充满憧憬的少年”[6]。
张凡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他所推崇的作家中鲁迅、巴金、老舍、杰克·伦敦都是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这些作家的人文视野无形中构成张凡的创作和思想底蕴,他在现实中奉行脚踏实地的处事原则,对身边人一视同仁,没有阶级观念。他与林江之间的启蒙是双向的,在与林江接触的过程中,张凡也在更新自我。在情感失意和现实受挫后,张凡失意地独自搬到贫民区去隐藏自己,在熟悉了林江的生活圈子之后,他无形中被底层民众的生活气息和坚韧精神所感染,被林江身上所赋有的正义感所吸引,并以莫基仔的遭遇为素材创作出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这与以往他习惯的沉溺于自我情感的小资产阶级写作风格大相径庭。张凡渐渐此走出小我的迷茫,迈向更加广阔的现实。《太阳下山了》“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底层,不仅是为了表现乡土社会在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动荡,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那里寻找温暖而坚强的人性力量,作为对城市文明消极意义的反拨。”[7]张凡亦是作家舒巷城的艺术投影,寄予着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理想主义精神,正是因为舒巷城看到了战争中生命的脆弱,看到了战争中人性恶的一面,他才在《太阳下山了》中,通过张凡眼睛去感受和鉴证下层美好和谐的人性,进而谱写了一曲和谐美好的乡曲。
三、现代人“酒徒”的存在迷思
《穷巷》和《太阳下山了》中的作家都有与底层民众长期相处的经历,与他们共情于日常伦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义德所寄予知识分子关心穷人和下层社会、参与解放和启蒙的理想姿态,他们在与民众的良好互动中完美诠释了士人兼济天下的情怀与启蒙立场,同时二人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坚守自我信念,拒绝为了金钱从事出卖灵魂的写作。而在1963年出版的小说《酒徒》,虽然其中的主人公酒徒同样身为作家,但酒徒的文学信念、人格理想、价值原则等已濒临被城市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主义击碎的边缘。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中,作为南来作家的刘以鬯比本地作家更面临商品化、个体表达的文学困境,他1948年移居香港,在这座殖民性与商业性交织的现代都市定居,他的过客心态、家国之思渐渐演变成对于文化本身的思考、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找,体现了作者努力摆脱文学商品化的诉求和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自我调适过程。《酒徒》写于1962年,以1960年代初的香港为背景,刻画了一个小知识分子作家在香港谋生过程中的挫败与内心体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五四后的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在香港得以继续流传与发展,“香港现代主义思潮是香港城市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内容,它明显地延续了‘上海——香港’的脉络,是战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离散至香港的最重要部分。”[2]64《酒徒》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香港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转变。
在《酒徒》的序言中,刘以鬯自言《酒徒》的写作是为了表现身陷时代苦闷之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以自我虐待的方式求取生存。酒徒是一位南来香港的作家,在香港文坛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香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商业文化占主导地位,文学创作被纳入现代商业社会的生产、分配机制中,文学表达方式成为商业筹码,创作者不再着重考虑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动机,而是将商业利润放在首选位置。在缺乏价值引导的情况下,读者的诉求成为文艺市场创作的风向标,如大量不加规制的低俗色情文学应运而生,极大地制约了严肃文学创作的空间。文中多次提到的三毫子小说,便是其中一种,内容多为言情,鲜有文学价值,但这是一种阅读趋势,为读者所普遍欢迎。酒徒本是一位吸收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汲养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状况,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对自我的创作有着极高的要求,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怀有极大的包容和肯定。酒徒到了香港后离自己所热衷的严肃文学创作越来越远,最后自愿彻底沦为低俗小说的写手。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情感的挫折与写作的挫败,同时在金钱势力主宰一切的情况下,目睹了人性被金钱扭曲的人间乱象:交际花张丽丽为了钱财与酒徒窜通去算计一个富商;受流行文化影响的少女司马莉,不加辨别地接收流行文化,她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也因此而改变,在堕落纵欲的道路上一去不返;年轻的包租婆明知丈夫有许多情人,仍然不去反抗或者挽回,因为只是需要他的豢养;年老色衰的私娼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文化投机者莫雨公然剽窃“我”的剧本等等乱象,都是人性在资本市场中被扭曲、被异化的表现。置身其中的酒徒不能够清醒地绕过所有的欲望泥潭,如他也参与“捉黄脚鸡”,也曾与包租婆有肉体关系,但他能够及时地进行自我审视。他意识到在香港这个社会,个体人已经沦为欲望的机器,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与传统人伦道德的规约,在金钱势力下,所有由有原乡意味、高尚情操的东西皆败下阵来。
酒徒最大的失落来自整个社会对他作为一个“人”的疏离和漠视,“伴随着香港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个人的生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人的真正本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抑,人渐渐成了物,像工厂流水线上的部件一样,成了没有自己灵魂的、无法支配自己的零配件。”[8]他所置身的社会只是将他当作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意识、没有尊严的零配件,置身其中他很难获得一种立身凭证,于是只能从酒精的麻醉中寻找自我存在的证明。酒神精神所指向的是非理性,在混乱中,试图呼唤人类的本能,自古以来,酒在骚人墨客的生活中,被他们视为寄托感情、言述抱负的载体。嵇康的时代,名士饮酒放达以图忘忧,摆脱现实中名教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回归;20世纪的酒徒,在酒里的自失与寻找,也彰显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即自由而无法自主的存在悖论与焦虑。以创作界来讲,在看似自由的保障下,作者和读者都有自由去选取适合的生存方式,但经由酒徒的所见所闻我们知道这份自由太不健康,人性的恶在低俗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被无限纵容和放大,个人也只会在虚空中更加孤独与渺小。文艺创作自由氛围下诞生的文学,成为供大家消遣娱乐的商品,缺少应有的艺术价值。作者刘以鬯借助于酒徒所表达的,正是像他这样的南来作家,到香港后的写作困惑和内心的焦虑。
在麻醉中,酒徒一再对自我、对社会、对文学进行拷问,其看似颓废堕落的行为隐含着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他借醉酒抒发己志,抨击香港社会和文坛的乱相,对拜金主义、文化荒漠等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至的批判;但当清醒以后,他却不能置身事外,仍要为了生存去躬行于文艺市场的商业法则,去写作出卖灵魂的连载低俗小说。酒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酒鬼,世人皆醉我独醒中,酒徒醉后吐的真言具有超凡的智慧。他明明知道黄色小说、三毫子小说是只有价格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他却不得不操持这营生来养活自己,这就是酒徒最深重的身份焦虑。当麦荷门邀请他一起创办纯文学杂志的时候,酒徒考虑再三予以拒绝,因为在香港整个文学氛围太淡,在所谓的文学圈子里,他所看到的全是虚假和做作,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宁愿放逐自己,也不愿与那些文学掮客为伍。他的存在焦虑在与日俱增,只能用酒来排解。
小说中酒徒最后一次搬家,是做了一户老实人家的租客,老太太精神失常将他当作逝去的儿子,并给以疼爱和关怀。她母亲般无微不至的温暖,给酒徒漂泊已久的心魂以短暂的慰藉,但是酒徒终于无法再消受这种具有原乡意味的情怀,灵魂的负累使他终于不愿再做他人的替身,在一次醉酒后,他向老太太揭开了真相,直接导致老太太绝望地自杀身亡。酒徒被现代社会异化的生存焦虑只能靠酒的麻醉来承载,在小说的结尾,经过反复戒酒的他,最终决定去喝一杯,这意味着他将重新开始自己的迷醉之旅。酒徒的存在是一种悖论,印证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的真实,即人无法超越自身,更无法超越时代。酒徒通过自我的“改造”,来迁就市场的审美趣味和大众对文学趣味性、煽情性的追求,他的颓废,他对理想主义立场的扬弃,表面上是一种个人行为,背后却有着深厚的社会底蕴,是社会体制的弊端导致他的自我放弃。酒徒用退守自我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怀才不遇,但他最终还是无路可退,在酒里寻找那个理想的世界,从侧面揭示了现实中自救的不可能,是自由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迷茫的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香港1940-1960年代文学中作家的生存境遇,反映出商业文化背景下现代都市中知识分子作家生存境遇的变迁,他们从与民众之间亲密融洽的互助、互相启蒙到孤独的自我放逐,呈现了都市化进程中个体生存空间从外向内的转变历程,形象揭示了现代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本雅明说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从高怀、张凡和酒徒的生存轨迹、价值选择和立身方式,可以看出作为本应拥有独立精神空间的作家,在一点一点地遭受商业化社会的挤压,高怀与张凡凭着顽强的毅力得以胜出自己的时代,但对于酒徒来说,灵魂日渐趋枯竭,三位作家与时代不同程度的张力关系说明,对于作家来讲,在所置身的现实中找到适宜自身的文化实践形式,灵魂才能重获失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