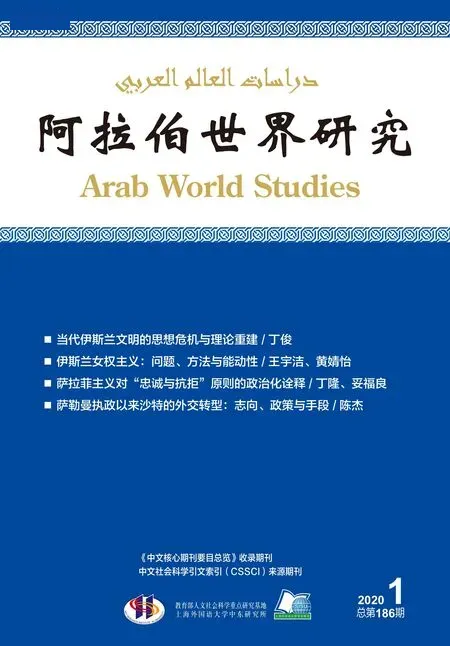伊斯兰女权主义:问题、方法与能动性*
王宇洁 黄婧怡
穆斯林女性的权利与地位问题,是伊斯兰研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外界有关伊斯兰教压制甚至迫害妇女的认知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有穆斯林以文化的纯正性为由,主张穆斯林女性有权通过与非穆斯林社会通行的不同方式来主张并实现自我的权利。西方国家对穆斯林女性问题的认识常常受制于固化的思维模式而局限在对特定领域的批评上,如伊斯兰教强调性别隔离,穆斯林女性的人权难以得到保障,伊斯兰世界内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频发,等等。还有一些人将穆斯林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之根源归咎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引发了各种解读和争论。可以说,“许多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试图透过(女性权利问题)这一棱镜来审视和评价伊斯兰教”(1)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8.。
当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团面临各种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其中既涉及穆斯林女性的教育、就业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又包括穆斯林女性的宗教领导权和解释权。这些问题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内部和西方伊斯兰学界的广泛讨论。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发表了多种见解,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试图通过发布法特瓦(fatwa)(宗教法令)来表达自身立场,但这些观点和立场有时却相互矛盾和对立。伊斯兰女权主义(Islamic Feminism)(2)中文学界对于“Feminism”一词,常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译法。在伊斯兰的语境中,这一思潮更多地强调伊斯兰世界内部对穆斯林女性赋权的呼吁。本文据此采用“女权主义”的译法。的思潮便是伴随对伊斯兰教妇女问题的讨论而兴起的。在伊斯兰文化的背景下,这股思潮主张重新解读伊斯兰教经典、反思伊斯兰传统,鼓励对伊斯兰教倡导的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是否与传统的父权制规范相容等问题展开讨论,推动社会各界围绕与穆斯林女性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提出新见解、发出新声音,促进穆斯林女性获得平等权利。本文主要考察具有强烈宗教认同、主张在伊斯兰框架内解决女性权利问题、反思与挑战伊斯兰传统的伊斯兰女权主义,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示传统宗教回应现代问题的不同路径与可能性。
一、 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伊斯兰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在过去30多年间,其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明显变化。1995年出版的《牛津现代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一书将“伊斯兰女权主义”定义为穆斯林女性对抗父权制霸权,争取在现代家庭、社会和国家中更加平等的性别安排的思潮和力量。该词条主要关注伊斯兰女权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及其与后殖民抵抗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之间的关系。(3)John L. Esposito,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23.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主体的复杂性。前述词条的编写者玛格特·巴德兰(Margot Badran)对相关定义进行了修订,强调伊斯兰女权主义是全球“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网络的组成部分。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不仅有来自亚非地区的穆斯林女性,也有来自西方的穆斯林移民和改宗伊斯兰教的女性,伊斯兰女权主义正是在全球“乌玛”网络中加速循环。(4)Margot Badran, Feminism in Islam: Secular and Religious Convergences,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9, pp. 243-245.而随着伊斯兰女权主义的思想主张逐渐为人所知,诸如“伊智提哈德”(ijtihad)(5)也译作“创制”。等阿拉伯语词汇也进入了英语世界。
这种定义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伊斯兰女权主义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的扩张。当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开始使用英语来传播和表达自身观点和立场时,便意味着她们已实际参与现代西方社会关于性别平等、妇女权益等议题的讨论之中。由此,伊斯兰女权主义不再是特定领土范围或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而是致力于融入21世纪初形成的新型全球社会的话语体系,借助各种要素跨国流动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将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话题纳入公共空间的讨论。(6)关于“大众媒体化的全球化宗教情感”的论述,参见[德]乌尔利希·贝克:《自己的上帝: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李荣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1页。正是在此背景下,如同个体自由、社群价值、动物权利、环境问题等议题一样,女性的权利与自由问题因其缺乏固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空间中促进思想交锋和知识生产的重要议题。
随着伊斯兰女权主义在全球层面动员能力的增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注重将其置于世界女权主义的语境下予以考察。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持续至20世纪初,聚焦女性的投票权等基本权利;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则在社会制度和知识构建层面对父权制度的批判进一步理论化和具体化。以“文化女权主义”为主要标识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反思和批评早期女权主义中充斥的白人至上主义,以此呼吁对非西方的、缺乏权利的女性的关注,构建所谓的“妇女主义”(womanist)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女权主义,是第三波女权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伊斯兰女权主义思潮的渊源而言,其初期形态,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女性为争取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等个人权利而发起的社会运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妇女在当时通过批判阿拉伯文化,对伊斯兰的宗教权威发起挑战。此后,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由穆斯林女性学者直接参与的对伊斯兰宗教文本进行阐释和探讨的学术运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以全球女权主义者和文化女权主义者的面貌贡献了诸多理论代表作,包括法蒂玛·美尔尼西(Fatima Mernissi)(7)法蒂玛·美尔尼西(1940~2015),摩洛哥社会学家和作家。曾在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任教。美尔尼西经常参加有关穆斯林女性问题的公共讨论,她的作品广泛涉及性别意识形态、性别认同、社会政治组织和伊斯兰世界妇女生存状态等问题。的《揭开面纱:穆斯林社会中的男女动态变化》(BeyondtheVeil:Male-FemaleDynamicsinMuslimSociety)和蕾拉·艾哈迈德(Leila Ahmad)(8)蕾拉·艾哈迈德(1940~ )出生于开罗,1999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神学院,是该系第一位教授宗教和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她对美国穆斯林女性佩戴“面纱”的问题进行过深刻论述,并因此获得格文美尔大奖(Grawemeyer Awards)。的《伊斯兰教中的妇女与性别:当代论争的历史根源》(WomenandGenderinIslam:HistoricalRootsofaModernDebate)等。持文化女权主义立场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意识到,自己仍是传统女权主义者群体中的“他者”,并逐渐将注意力转到对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构建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批判上。同时,她们还注重展现穆斯林女性的尊严和活力,强调以符合伊斯兰教精神、具有伊斯兰特色的话语体系阐述自身主张。
无论是针对西方社会中与伊斯兰教相关议题而发声的穆斯林女性,还是接受现代价值观和改革主义思潮的穆斯林女性,女权主义是她们重要的话语工具。对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而言,保留“女权主义”的话语标签,其意义在于将穆斯林女性置于世界女权主义的整体语境下,实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与其他女性群体间的互动与联合。(9)Ednan Aslan, Marcia Hermansen and Elif Medeni, eds., Muslima Theology: The Voices of Muslim Women Theologian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2013, pp. 16-18.在这个意义上,米里亚姆·库柯(Miriam Cooke)认为,只要穆斯林女性参与围绕穆斯林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分配和权利的公共争论,对有损于她们的解释宣战,哪怕只是说句“不”,那么她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站在伊斯兰女权主义的立场。(10)Miriam Cooke, Women Claim Islam: Creating Islamic Feminism Through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57.因此,当穆斯林女性声称自己是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时,这并不是一个“伊斯兰”和“女权主义者”简单混合而成的身份,而是穆斯林女性寻求公平正义和公民权的意图和态度,是一种全新的、持续性的主体性意识。(11)Miriam Cooke, Women Claim Islam: Creating Islamic Feminism Through Literature, pp. 59-61.对坚持这一立场的穆斯林女性而言,纠结于伊斯兰是否与女权主义相容并不是一个有足够建设意义的问题。在她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穆斯林女性本身就具有成为强大女性的权利和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意味着,穆斯林女性既不需要刻意迎合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压迫性想象,也不必依赖于某位宗教权威对性别角色分工的“合理解释”。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最著名的伊斯兰女权主义学者主要活跃于欧美国家,她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对那些对宗教经典所做的性别主义和男权主义的解释进行反思和批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里法特·哈桑(Riffat Hassan)和阿齐扎·希比里(Azizah al-Hibri)是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阿米娜·瓦杜德(Amina Wadud)(12)阿米娜·瓦杜德(1952~ )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1972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理学学士,同年皈依伊斯兰教。她先后在利比亚、埃及等国游学,1988年获密歇根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瓦杜德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于我而言,早年对伊斯兰教、公平正义和性别问题的关注继承自我父亲的信仰之光。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牧师,他出生的年代正值致死的贫穷、黑暗和压迫的种族主义遍布美国。但我却在父爱的指引和信仰的保护下成长……我的道德意识兴起于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的顶峰时期。……身为穆斯林的我,无论何时何地遭遇不公平、歧视和压迫,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古兰经》中不断重复表达的‘真主不会压迫’的观点。”在此背景下,“公正”成为瓦杜德的伊斯兰观中的核心追求。和阿斯玛·巴拉斯(Asma Barlas)(13)阿斯玛·巴拉斯(1950~ ),巴基斯坦裔美国作家,1976年在巴基斯坦驻外事务处(Pakistan’s Foreign Service)工作,后因批评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政权遭开除。1983年,她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并获准前往美国,现任教于美国伊萨卡学院。是活跃于90年代的代表人物,凯西尔·阿里(Kecia Ali)(14)凯西尔·阿里(1972~ )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历史学和女性主义研究,获学士学位本,后在杜克大学获宗教学博士学位,自称是“进步的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凯西尔·阿里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宗教学系,主攻伊斯兰教法和女性问题。此外,她还是美国乐施会(Oxfam America)理事。和阿伊莎·希达亚图拉(Aysha Hidayatullah)(15)阿伊莎·希达亚图拉曾获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宗教学博士学位,自2008年起任教于旧金山大学,兼任美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性别—女性”项目负责人。希达亚图拉在其博士论文《〈古兰经〉的女权主义边缘》序言部分提到, 20世纪90年代她在求学过程中目睹了伊斯兰女权主义思潮的繁荣,阿米娜·瓦杜德和里法特·哈桑等人都对她思想的形成产生过较大影响。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身份背景来看,北美国家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一部分是来自亚非拉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学者,如来自埃及的蕾拉·艾哈迈德和来自巴基斯坦的阿斯玛·巴拉斯,另一部分则是北美本土皈依伊斯兰教的学者,如阿米娜·瓦杜德和凯西尔·阿里,后两者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浪潮中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
在伊斯兰女权主义成为具体理论和进入实践阶段之前,20世纪中期移民到北美地区的一些男性穆斯林学者同样也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性别观。其中,法兹鲁尔·拉赫曼(Fazlur Rahman)和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Fadl)等学者的学说对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兹鲁尔·拉赫曼注重运用解释学理论来阐述性别问题,他从一夫多妻制与公正无法相容这一角度出发,对《古兰经》中的相关经文予以重新阐释,对一夫多妻制进行了解构。哈立德·阿布·法德尔则认为,伊斯兰教是永恒的资源,但在不同时空中产生了具有历史特征的观点和话语。他提出,诵读《古兰经》时要伴之“审慎的停顿”,即读者在诵读《古兰经》的过程中,当价值观遭受冲击时,应暂时停止诵读,尽可能地跟随内心、而非文本本身去理解经文。(16)Roberto Tottoli,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Islam in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397-400.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和一些男性穆斯林学者具有类似的立场倾向。
不论作为移民群体、少数族裔,还是改宗者,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往往与欧美社会所关心的各种身份政治问题相互交叉。她们既要通过理性化的宗教表达以寻求跨文化的理解,也要通过对伊斯兰宗教话语的重构,为解决当下穆斯林社会中的“变”与“不变”提供可行性建议。经训阐释和宗教领导权,是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在建构理论体系过程中处理的主要论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穆斯林社会业已存在的老问题,也涉及因全球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伊斯兰女权主义者采用了不同于研究性别问题的男性穆斯林学者的研究方法。
二、 伊斯兰女权主义对宗教经典的自主性诠释
对于坚持自身宗教精神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而言,在处理性别问题时无法回避“伊斯兰教是否压迫女性”这一辩题。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传统中确实存在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性别话语。以现代视角来看,作为伊斯兰教经典的《古兰经》中提及的女性多以妻子或亲属形象出现,除先知尔撒的母亲麦尔彦外,其余女性都没有具体的姓名。这一现象似乎坐实了父权制社会中穆斯林女性的从属地位。此外,也有不少经文强调性别隔离,认可一夫多妻制和男性在家庭生活、法律地位方面之于女性的优越性,这些内容与现代价值观念存在明显差异。当代女权主义者寻求在伊斯兰的话语框架内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如何使对经文的具体阐释符合穆斯林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不可回避的重要挑战。
对于这一挑战,当代伊斯兰女权主义者首先试图对《古兰经》的传统解释进行解构。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宗教权威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穆斯林社会规范的合法性来源,但这些解释是人为的知识,与不可更改的经训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由此入手,认为历史上男性学者对《古兰经》中有关女性地位的经文存在误读,中世纪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是造成这一误读的主要原因。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男性穆斯林垄断宗教学者这一职业,他们在对《古兰经》进行注释和编纂教法学著作的过程中,将当时的父权制度及其规范进行了制度化改造。而这些男性宗教学者又因自身所处的父权制语境,再一次强化了《古兰经》文本的父权色彩。(17)Ayesha S. Chaudhry, “Women,” in Gerhard Bowering, ed.,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66.由此,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不同的诠释,成为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解释宗教经典、阐发自身观点的常用手段。(18)Ednan Aslan, Marcia Hermansen and Elif Medeni, eds., Muslima Theology: The Voices of Muslim Women Theologians, pp. 81-82.
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对宗教经典的诠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历史上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女性有必要参与对经训的解释。在她们看来,伊斯兰教强调的女性价值已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甚至连穆斯林女性也常常忽视这种价值。换言之,伊斯兰女权主义不仅寻求介入解读《古兰经》和“圣训”文本的过程,也重视经过历史积累形成的伊斯兰传统,即伊斯兰社会常常使用的“遗产”(turath)一词。对具有“改革”倾向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言,“遗产”的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传统伊斯兰的思想中,“遗产”常与“持续”“稳定”“确定”“权威”等概念相联系。在广义上,“遗产”可被视为一种以《古兰经》、“圣训”及其相关的哲学、神学、伦理学、教法学、神秘主义和社会政治规范等学说为核心的,且具有动态性和层累性特征的宗教历史建构。(19)Adis Duderija, “Toward a Scriptural Hermeneutics of Islamic Feminism,”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Vol. 31, No. 2, 2015, p. 46.这种对历史的层累性的理解类似于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关于“文化”和“传统”的观点,即“文化”是一种“重写行为”,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张力促进了“文化”本身的活力。但“传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传统”只与传承、接受以及被接受事物的持续性相关。“传统”即使具有可想象的动力,也不过是存在于文本之中,通过一种可控的、自觉的方式释放出来。(20)[德]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当然,“遗产”一词的本意远不止于此,但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过程中,当“遗产”与人们通常所认知的具有权威意义的宗教“传统”建立起联系时,实际上很容易被推导为一种基于信仰体制的“有形的宗教”,其对立面则是基于个人认同的“无形的宗教”。因此,即便“传统”的结构性张力仍然存在,但在人们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预期面前,一种通过自身的行为参与,使解释范式由观念转化为实在的“无形的宗教”,似乎更值得受到鼓励。正如穆罕默德·阿尔孔(Muhammad Arkoun)所指出的,伊斯兰文化总存在一些人们“未加思考”的问题和认为“不可想象”的问题。(21)Khaled Abou El Fadl, Speaking in God’s Name: Islamic Law, Authority, and Women,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1, p. 207.一些致力于穆斯林女性问题研究的学者亦会通过对那些“被遗忘”的伊斯兰/穆斯林文本资源进行再度开发,来重构传统的伊斯兰性别话语。费德瓦·马尔蒂-道格拉斯(Fedwa Malti-Douglas)认为,在重构性别话语的过程中,《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品和其他口传文学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在传播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22)Fedwa Malti-Douglas, Woman’s Body, Woman’s Word: Gender and Discourse in Arabo-Islamic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5.
如今,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并不必然会强调“阿拉伯”因素,但在诠释伊斯兰性别问题时仍要面对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并在“未加思考”的问题和“不可想象”的问题之间谨慎探索。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虽然对诠释的目的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诠释资源的合法性方面,各自有其不同的认识角度。
阿米娜·瓦杜德最早在《〈古兰经〉与女性:以女性视角重读神圣文本》一书中,试图对如何解释《古兰经》中人们普遍认为的贬抑女性的经文段落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她认为,《古兰经》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歧视妇女的倾向,主要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解释者狭隘地理解经文,断章取义的解读凸显了他们的个人想象和对妇女的偏见;二是《古兰经》是在父权制时代的阿拉伯半岛降示的,当时妇女因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而受到歧视,这一现实制约了《古兰经》的表达。但瓦杜德也认为,这并非《古兰经》的全部本意,《古兰经》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公正、平等、互相尊敬和道德责任,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平等才是对《古兰经》原则的真正体现。她在书中对被认为承认男性优越地位的经文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她看来,这些经文段落包含了两个经常被用于彰显个人或群体间功能性价值的术语。第一个术语是“达拉杰”(darajah),原意为“级别”、“程度”或“水平”,但该词并不仅指社会地位和品级,而且指穆斯林今生和来世之间、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阶层。第二个术语是“法达来”(faddala),即真主对一些受造物的偏爱。在回应《古兰经》是否暗示“男性优于女性”这一问题时,瓦杜德指出,阿拉伯语词汇中的阳性/阴性单词复数形式并不是全称指代的,“他们比她们更优越”的原文不是简单地意指所有男性比所有女性更优越,只是表达一些男性在某些方面会胜过女性而已的含义。同样,一些女性也会在某些方面胜过男性。“不管真主到底偏爱了谁,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优越而已。”(23)Amina Wadud, Quran and Woman: Rereading the Sacred Text from a Woman’s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6-71.
阿斯玛·巴拉斯指出,对《古兰经》的诠释实际上涉及伊斯兰思想和实践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即神圣与世俗、启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巴拉斯认为,真主的启示是不可改变的;但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的持续性和普遍性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只要保持合适的阅读方法,《古兰经》经注学的合法性便不容置疑。她认为,针对父权制认识论这一问题,诠释《古兰经》的过程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神学原则方面,从诠释学的原则出发,对《古兰经》的阅读在本质上是真主向读者“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的过程,巴拉斯将这种“自我表露”总结为为真主的独一、公正和不可描述性三个方面。二是在方法论方面,诠释《古兰经》的过程应强调对宗教经典的整体性阅读,不鼓励对《古兰经》进行碎片式、断章取义的阅读。三是在伦理方面,应明确阅读《古兰经》的方式和方法存在差异性,对经文进行阐释需要将经文置于特定的语境和降示背景中,这既是天启宗教内在的多义性使然,也是读者的道德责任。四是诠经的权威性问题,即谁有权利解释经文和谁的解释更加权威的问题。巴拉斯认为,诠经的权威性来自《古兰经》本身,而非源于公众的认可或理性,也不源于宗教学者现行的权威解释结构。事实上,正是现行权威解释结构和公众认可度导致了《古兰经》对女性进行隔绝的普遍观点。对此,巴拉斯引用先知穆罕默德与妻子乌姆·萨拉曼(Umm Salama)的一段对话予以阐释。乌姆·萨拉曼曾问先知:“《古兰经》为何只提到男人,而没有提到我们(女人)?”萨拉曼提问的实质是寻求“《古兰经》是否与女性有关”这一永恒的话题。在巴拉斯看来,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是一项“未完的宗教功修”,如果穆斯林女性不能直接参与对宗教经典进行解释的过程,穆斯林女性就无法期待得到符合女性需求的回应。(24)Kari Vogt, Lena Larsen and Christian Moe, eds., New Directions in Islamic Thought: Exploring Reform and Muslim Tra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9, pp. 17-22.
阿伊莎·希达亚图拉在发展伊斯兰女权主义理论时,注重对现有经注工作进行批判性梳理。她敏锐地指出了女权主义者在开展《古兰经》经注工作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巴拉斯等人所提倡的整体性诠释方法和现代主义者的解释方法一样,强调要在语言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古兰经》经文使用的天启语言。同时,为区别于传统的解释模式,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又强调《古兰经》优于“圣训”的地位,认为“圣训”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值得怀疑的。其结果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权主义者们甚至不愿意承认《古兰经》存在性别歧视的可能,而只强调对“圣训”的曲解和误读。比如里法特·哈桑就曾宣称《古兰经》拥有绝对权威,误解都源于解释者对“圣训”的曲解或误读。阿斯玛·巴拉斯也认为,《古兰经》经文本身就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性,因此强调读者有责任正确阅读《古兰经》。(25)Aysha A. Hidayatulah, Feminist Edges of the Qur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6-128.直到2006年凯西尔·阿里的《性别伦理与伊斯兰教:对〈古兰经〉、“圣训”和教法学的女权主义反思》(SexualEthicsandIslam:FeministReflectionsonQur’an,Hadith,andJurisprudence)和阿米娜·瓦杜德的《在性别吉哈德内部:伊斯兰教中的妇女改革》(InsidetheGenderJihad:Women’sReforminIslam)两部著作先后出版,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才开始正视上述这些问题。希达亚图拉认为,女权主义者对平等、公义和性别三个术语的使用常常是含混不清的。她指出,平等是一个当代的概念,女权主义者不应将平等视作是不证自明的、与历史无关的公义标尺。在她看来,读者在阅读《古兰经》的过程中,必须区分作为当代概念的两性平等与《古兰经》对两性理解之间的差异。(26)Ibid., pp. 126-134.
凯西尔·阿里在如何诠释《古兰经》的问题上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观点。她指出,在现代道德的语境中,诠释学致力于维护宗教文本永恒性的方法,却在性别伦理层面遭遇了挑战。进步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将《古兰经》视作区别于其他宗教文本的经典,认为它不同于“圣训”,《古兰经》是纯粹的、不可侵犯的、神圣的宗教文本。但当学者面对奴隶制、肉体惩罚、一夫多妻制等《古兰经》中提及的那些令当代社会难以接受的内容时,他们又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对穆斯林生活适用性的角度来看,《古兰经》所有的指示都是一成不变的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凯西尔·阿里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她认为,改革主义方法的问题在于,他们将《古兰经》视作超越任何文化实践永恒的、至高无上的文本,但如果对《古兰经》的解释没有触及其中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地“超越”文本中的这些道德挑战的。(27)Kari Vogt, Lena Larsen and Christian Moe, eds., New Directions in Islamic Thought: Exploring Reform and Muslim Tradition, pp. 91-92.凯西尔·阿里进而指出,当人们试图从文本中提炼原则时,他们必须理解文本所能提供的原则是有其限度的。换言之,对性别关系而言,《古兰经》所关注的是一种纯洁合法的合作关系,但这并不代表原则之外的性别关系就不会存在。因此,如果女权主义者一味地强调平等主义原则,却不对诸原则的源头进行辨析,就很难不陷入对文本的曲解。(28)Ibid., p. 98.
凯西尔·阿里的女权主义研究聚焦性别伦理问题。她坦言,从性别伦理的角度来看,女性的从属地位并非穆斯林社会的特有现象。通过对伊斯兰古典文献进行阅读和分析,她意识到学界正在陷入一种“对女性的压迫是伊斯兰教特有现象”的危险刻板印象。“穆斯林的性别伦理问题要比其他宗教传统都棘手”已成为学界对伊斯兰教的一种“普遍印象”。(29)Kecia Ali, Sexual Ethics and Islam: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Qur’an, Hadith, and Jurisprudence,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 2006, p. xviii.不可否认的是,贫穷、战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对穆斯林女性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对穆斯林社会性别问题的分析,不能忽略考察这些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对伊斯兰国家而言,贫穷和战争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贫穷限制穆斯林女性实现婚姻自由和处理婚姻问题的同时,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和工具化也从政治层面限制了穆斯林女性的权利,尤其是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家庭事务的介入,加重了穆斯林女性处理性别问题时的压力。
将对伊斯兰教法问题的讨论与对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相结合,这是凯西尔·阿里一直倡导的伊斯兰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在她看来,如果将“伊斯兰教法”视为一套伦理体系,那么对其进行现代性解读不应采用“义务的行为”和“禁止的行为”的简单二分法,因为这套伦理体系自形成以来就还包括了“嘉许的行为”“应予谴责的行为”“漠视的行为”等其他类型。在北美和欧洲等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地区,穆斯林较少受到伊斯兰传统体制的束缚,因此这些地区的学者应更加重视运用这些学术资源。(30)Ibid., pp. xviii-xxi.凯西尔·阿里还指出,伊斯兰教法的确为处理穆斯林伦理问题提供了法理根据,但如今部分女权主义者和萨拉菲主义者一样,都只强调回归经训,却忽视从传统的学术资源中探寻伊斯兰教法传统的历史依据。对于传统学术资源持忽视态度,似乎是为了回避中世纪以来在穆斯林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规范,实际上却忽视了早期穆斯林学者在处理社会风俗和宗教经典之间关系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原本可以为穆斯林处理当代问题提供极其丰富且权威的宗教解释。(31)Kecia Ali, Sexual Ethics and Islam: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Qur’an, Hadith, and Jurisprudence, pp. xxiii-xxiv.
不少伊斯兰女权主义学者对自己著述的立场归属仍持谨慎态度。例如,凯西尔·阿里认为自己并不是教法学家,也不是《古兰经》经注学家或伦理学家,她强调自己只是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性别伦理问题尝试性地提供解决建议,而非制定一套关于宗教和教法的完整改革方案。她曾坦言自己“在阅读这些(宗教)文本时感到非常愉悦”,但大量穆斯林女性没有机会去阅读、书写和讨论现有的教法学文本。她承认自己并不打算在“制度性的、男性的伊斯兰”和“模糊的、伦理的女性的伊斯兰”之间建立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致力于使穆斯林女性获得阅读“文本之愉悦”,在她看来,这是“穆斯林女性体会生活之愉悦的一个过程”。(32)Kecia Ali, Juliane Hammer and Laury Silvers, eds., A Jihad for Justice: Honoring the Work and Life of Amina Wadud, 48HrBooks, 2012, pp. 133-134.其他女权主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巴拉斯指出,在“《古兰经》没有提出一种性别平等的理论”和“我们仍能从《古兰经》倡导的教义中获得支持性别平等的理论”两大命题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是因为,《古兰经》并未提出明确的性别观,既没有提供关于性别的社会功能的描述,更没有为性别的生理特征赋予任何社会层面的内容和意义。(33)Asma Barlas, “Secular and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Qur’an: Anti-Hermeneutics as Liberation?,”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Vol. 32, No. 2, 2016, pp. 111-121.上述观点反映了当今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发展趋势,即穆斯林女性不仅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争取话语权,而且致力于使这一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在阐释伊斯兰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主体性和自主性,而不是以单纯的受压迫者的形象出现以寻求社会的同情。
三、 伊斯兰女权主义对公共领导权的探讨
女性在宗教生活中的角色问题是伊斯兰女权主义者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伊斯兰教认可男女两性在宗教上享有同等地位,但传统观念认为,去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不是穆斯林女性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对于穆斯林女性能否像穆斯林男性那般担任集体礼拜,特别是有男性参加的集体礼拜的领拜人,更持不赞同的态度。即便是那些被公认为思想开明的现代穆斯林思想家和宗教学者,对此也多持反对态度。例如,英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剑桥大学蒂莫西·温特(Timothy Winter)教授承认,《古兰经》和“圣训”中并没有明文禁止穆斯林女性担任男性穆斯林的领拜人。但温特和优素福·格尔达维、阿里·葛玛阿等许多传统主义的宗教权威和改革者一样,仍依据逊尼派伊斯兰教法的经典公议原则,认为男女共同礼拜时,领拜人即伊玛目必须由男性担任。(34)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p. 124.即便是那些长期在美国生活、对宗教持有开放包容观念的穆斯林宗教人士,也倾向于认为女性领导男女混合的礼拜“是不可接受的”。这些人并不认为女性是具有精神缺陷的次等性别,他们承认女性应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受到尊重和获得荣耀,但他们也认为穆斯林女性只可以担任仅有女性参加的公开宗教仪式,或在家中带领家人履行宗教功修,而不适合担任男女混合的公开礼拜的领拜人。
在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看来,上述学者的立场显然有失公允。法蒂玛·美尔尼西在研究中强调,穆斯林女性无法担任领拜人的论断凸显出女性在伊斯兰教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事实。在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社团领袖在周五聚礼日的演讲中可以直接和穆斯林信众进行沟通,借此向穆斯林传达重要信息。然而,对于权力弱化的担忧导致哈里发很快切断了社团与清真寺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其统治领域内竖起一道道帷幕。(35)Fatima Mernissi, The Forgotten Queens of Islam, Mary Jo Lakeland, tran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 79.结果,曾经和穆斯林男性一样进行政治参与的穆斯林女性,逐渐被剥夺了担任军事和政治首领的资格,更无法成为杰出的宗教领袖。法蒂玛·美尔尼西坚信哈里发和穆斯林女性两种身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兼容性。在她看来,“正统”的意义会随着不同的文化和权力关系而发生变化,但伊斯兰教历史上始终存在一种“正统”,即女性对权利的要求总是被视作对权威的侵犯。(36)Ibid., pp. 20-21.
摘掉头巾(hijab)通常被认为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进行抗争、体现主体性的主要手段。但在欧美穆斯林社群中,抵抗的手段和内涵发生了微妙变化,穆斯林女性往往通过佩戴头巾来抵抗主流社会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少数群体的不公平待遇。(37)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2-123.蕾拉·艾哈迈德曾采访过一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穆斯林女生安妮亚·拉贾(Annia Raja)。拉贾表示,佩戴头巾增强了她的自我意识,即她是代表伊斯兰进入公共场域的,以此告诉公众“什么才是真正的伊斯兰”。与此同时,头巾也“解放”了她,帮助她在校园里创造出一种强大的美国穆斯林身份。(38)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pp. 207-211.然而,选择佩戴头巾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教义教规的认可,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仍将清真寺里的性别隔离制度和对女性领拜人角色的限制视作不公平待遇。在解释这种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上,她们认为,在穆斯林社区内部,穆斯林女性缺乏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她们被紧紧地限制在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这种限制并不必要,针对穆斯林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试图不断证明穆斯林女性在社区中可以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同时,穆斯林女性公共角色的缺席严重损害了女性为社区服务的能力,限制了该群体谋求自身福利的机会。(39)Katherine Bullock, ed., Muslim Women Activists in North America: Speaking for Ourselv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 xvii.加拿大穆斯林女导演扎尔卡·纳瓦兹(Zarqa Nawaz)曾执导过纪录片《我与清真寺》(MeandtheMosque),她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来反映穆斯林女性对北美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的重要性,以及她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她看来,穆斯林女性在社区内部,哪怕是在清真寺中获得平等地位,也是推动公平和正义的一小步。穆斯林总是谈论外部的不公平待遇,但却很少谈论穆斯林社区内部的不公平现象。在清真寺中,穆斯林女性通常被隔离在一间小房间进行礼拜,穆斯林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被剥夺,这是穆斯林社区内部不公平现象的典型表现。(40)Juliane Hammer, American Muslim Wome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Activism: More Than a Pray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p. 12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跨国交流的日益频繁,穆斯林妇女组织在欧美国家穆斯林社区中逐渐兴起。穆斯林女性表现出参与政治的积极态度,这与其在公共生活中受到的排斥和不平等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不平等待遇不仅反映在性别层面,也受到种族、信仰和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对此,阿米娜·瓦杜德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打破这种现状。瓦杜德挑战了长期以来只有男性穆斯林领拜周五聚礼日集体礼拜的传统,开展了一项大胆的行动。2005年3月18日,瓦杜德在美国纽约发起了一场男女混合的集体礼拜,她在这场集体礼拜中担任领拜人,带领一百多名穆斯林男女做了聚礼。聚礼地点设在纽约圣约翰教堂(Synod House of the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瓦杜德在聚礼日演讲中选择《古兰经》中具有代表性的章节,尤其是体现“认主独一范式”的章节,来阐述她的宗教观和对“认主独一”的理解。
这场周五聚礼的组织方包括“进步穆斯林联盟”(Progressive Muslim Union)、“纽约穆斯林改革运动组织”(Muslim Reform Movement Organization of New York)、“伯克利灵性进步网络”(Network of Spiritual Progressives in Berkeley)和“穆斯林妇女自由之旅”(Muslim Women’s Freedom Tour)等宗教非政府组织。“穆斯林妇女自由之旅”的负责人阿斯拉·诺曼尼(Asra Nomani)在此前出版的《独自站在麦加》(StandingAloneinMecca)一书中记录了她在麦加朝觐期间的经历,声称朝觐之旅激发了她对穆斯林女性身份的反思。完成朝觐后,她在纽约城发起了一系列礼拜活动,参加了瓦杜德担任领拜人的男女混合集体礼拜。她认为,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穆斯林女性在宗教场所和整个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然而,这场活动也给诺曼尼和瓦杜德带来了负面影响。瓦杜德任职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对其采取停职措施。瓦杜德本人虽然并未将此次聚礼活动视作其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的重心,但仍因此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41)Juliane Hammer, American Muslim Wome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Activism: More Than a Prayer, pp. 148-164.穆斯林社区和宗教界内部围绕穆斯林女性领拜权是否符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产生了激烈争论。
阿斯拉·诺曼尼早在2003年就筹建了一座清真寺,并试图在清真寺内部恢复女性穆斯林对宗教事务的领导权。她在一篇题为《身为领袖,我想在世界上看到……》(Being the Leader I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的文章中称,自己一直对女性在社区、家庭甚至社会上担任领袖抱有期待,但她最终意识到,这些领袖都没有达到女性平权的要求。经历这段令人痛苦又失望的坎坷后,诺曼尼决心不再寻求从外部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诺曼尼和瓦杜德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女性对于宗教权威和宗教事务领导权的要求常被认为与其宗教虔诚度呈负相关。明确提出这些要求的穆斯林女性,往往被指责站在了“伊斯兰的对立面”,这成为“阻碍穆斯林女性公开参加伊斯兰解放事业最强大的胁迫策略之一”。(42)Ibid., pp. 134-135.虽然2005年瓦杜德领拜的聚礼不是穆斯林女性第一次领导男女混合的礼拜活动,但这次活动仍引起了全球宗教学者和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宗教领袖的谴责最为严厉。时任爱资哈尔大教长阿里·葛玛阿先是发布宗教教令支持瓦杜德的领拜行为,但迫于压力随即又澄清这一教令只是重述历史上宗教学者对穆斯林女性领导礼拜的许可,并不是批准穆斯林女性领拜周五的聚礼。(43)Ayesha S. Chaudhry, “Women,” pp. 263-272.
在哈福德大学任教的北美伊斯兰协会主席英格里德·马特森(Ingrid Mattson)支持穆斯林女性对政治和宗教事务的领导权,但不支持瓦杜德和诺曼尼的激进行为,她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改良手段。针对男女混合礼拜的问题,她在《女性能成为伊玛目吗?》一文中对穆斯林女性领导权的形式与功能进行了探讨。(44)Ingrid Mattson, “Can a Woman Be an Imam? Debating Form and Function in Muslim Women’s Leadership,” Ingrid Mattson, June 20, 2005, http://ingridmattson.org/article/can-a-woman-be-an-imam/, 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4日。她指出,《古兰经》本身并没有对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的界限作出清晰划分。穆斯林女性担任宗教领导人的意义,首先在于保障穆斯林女性在社团中的代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穆斯林女性都能感受到社会以伊斯兰之名对其实施的不公平待遇和束缚。问题在于,大多数穆斯林女性既缺乏对于伊斯兰教法术语的熟练掌握,也缺乏愿意为她们说话的宗教权威的支持。其结果是,鲜有人为她们作出改变,这进而导致穆斯林女性对于公义的内在需求受到抑制。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的匮乏,将导致穆斯林女性的诉求和权利难以被充分代表。从这个意义上看,确保穆斯林女性的领导权确有必要。
但是,穆斯林女性担任宗教领袖的重要性是否等同于其成为宗教权威的重要性?梅特森试图通过在概念上区分宗教权威与宗教领袖来回答这一问题。她指出,并不是只有担任正式宗教领袖职位的穆斯林才具有宗教权威。实际上,这种正式的职位有时反而会消解宗教领袖的权威性。如果认为美国穆斯林社区的领拜人同时具有宗教领袖和宗教权威的双重身份,信众可能会对伊斯兰教宗教领导权的动态演变出现认知偏差。反过来看,这种认知偏差会极大地削弱那些对性别问题具有包容性的穆斯林成为宗教领袖的可能性。如果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穆斯林社区的宗教领袖,人们会发现美国大部分穆斯林对社区宗教领袖的满意度并不高。相比普通女性,担任宗教领袖的穆斯林女性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具有包容性的代表权只是善治的必要条件,这无法保证女性担任宗教领袖后就可以代表其他穆斯林女性的所有需求。反过来讲,穆斯林社区必须拥有负责任的宗教领袖和包容性的决策机构,才能以社区意志来代表个人价值和关切。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确保宗教领袖责任到位的最好方法是允许宗教领袖根据普通穆斯林信众想要的方式开展工作,并最大限度地确保男性和女性同等参与社区的宗教事务。(45)Ibid.
梅特森的分析也暗示了另一个问题,即围绕女性宗教领导权的争论不仅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更是由欧美穆斯林社区的发展现状所决定的。换言之,努力与欧美社会现行宗教体制相适应,是以移民和改宗者为主体的欧美穆斯林社群必须面对的挑战。北美穆斯林社群开展宗教实践的组织形式,大多以“北美伊斯兰社团”“美国穆斯林促进社”等宗教社团为主。这意味着在美国,作为领拜人的伊玛目在角色上更接近于为社区服务的“穆斯林牧师”(Muslim chaplaincy),这与穆斯林世界的伊玛目具有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意义存在较大差异。“穆斯林牧师”既是社区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社区教育工作的服务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培养水平合格的本土宗教人士,远比基于宗教经典开展论辩的“宗教权威”,更有利于支持穆斯林女性担任领拜人的合法性。
总的来看,穆斯林社会内部女性地位不平等的现象长期存在,如部分组织仍不接受穆斯林女性从事宗教职业、不接受穆斯林女性对佩戴头巾的选择权、不支持不会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女性担任教职,(46)Shenila S. Khoja-Moolji, “An Emerging Model of Muslim Leadership: Chaplaincy on University Campuses,” The Pluralism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http://pluralism.org/affiliate/former-student-affiliate/shenila-s-khoja-moolji/, 登录时间:2019年8月10日。但是梅特森对欧美社区女性领拜人角色的功能主义解释,仍为实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的诉求提供了有效策略。
四、 伊斯兰女权主义的能动性: 复古与改革
如今,穆斯林女性的形象或多或少会成为具有政治意涵的话语媒介。穆斯林女性问题既是外界用来测量伊斯兰教“进步”与否的标尺,也是一些伊斯兰政权或是伊斯兰主义者所坚守的“真正的伊斯兰价值”的象征。(47)Ayesha S. Chaudhry, “Women,” pp. 263-272.穆斯林女性的境遇常常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辩论中被提及,这些话题旨在说明伊斯兰国家的“进步”或“落后”。当有学者试图为这种对穆斯林女性处境进行的政治化解读“松绑”时,其态度并不是简单否认女性在穆斯林社会中遭受的痛苦和不平等待遇,而是超越现象本身,指出宗教不应成为被同质化的打击对象,进而指出必须审慎对待与妇女解放相关的进步主张。例如,莉拉·阿布-卢古德(Lila Abu-Lughod)指出,所谓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关注穆斯林女性受压迫的故事时,真正的穆斯林女性的声音却被忽视。这种现实使得西方国家的民众倾向于认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女性缺乏婚姻自由,但埃及乡村的现实却能有力驳斥这种偏见。在埃及乡村,穆斯林女性通过研习宗教,使用伊斯兰教法的知识来挑战当地的包办婚姻。(48)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 199-200.
阿布·卢古德曾多次反思“穆斯林女性是否拥有主动挑战社会规范的行为能力”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使得所谓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宗教是压迫性的,一个在宗教上虔诚的女性缺乏任何的能动性。(49)Sara Salem, “Feminist Critique and Islamic Feminism: The Question of Intersectionality,” The Postcolonialist, Vol. 1, No. 1, 2013, http://postcolonialist.com/civil-discourse/feminist-critique-and-islamic-feminism-the-question-of-intersectionality/,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9日。针对这样的观点,有不少学者指出,这是女性主动做出的选择,使用宗教来替代社会规范的女性,本身就反映出一种行动能力。萨巴·马哈茂德(Saba Mahmood)基于对埃及开罗的实地调研,重新思考了宗教复兴运动中女性的主体性意义。在她看来,这些在清真寺里开展宗教活动、组织研习班的穆斯林女性,并没有将权威的道德模式视作束缚个人自由的外在社会干预,而是将践行这一模式视为基于个人意志的潜能。(50)Saba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8-32.
在西方世界,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同样表现出类似的追求回归宗教传统的倾向。她们往往强调宗教本身并无不利于女性的明确规定,历史环境影响下的宗教传统发生变化,是导致穆斯林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主要原因,如中世纪父权制对伊斯兰教的纯正性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为维护真正的宗教精神,信众应以宗教经典和早期史料为基础,溯其本源。这种追求改变的形式自然是“复古”的,但并不意味穆斯林女性内在地接受父权制传统的压迫,也不意味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采用的种种方法充分体现了其能动性。一方面,她们以极高的热情阅读和诠释宗教经典,通过学术阅读和社会活动的体验不断转变自身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另一方面,她们无不把对经训和教法的传统解释模式视作一种社会建制,为构建性别平等的宗教话语,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尝试性地选择那些有利于性别平等的解释传统,坚决否认或“脱离”明显带有父权制偏见的压迫性话语。
在各种争议和讨论的背后,如今伊斯兰女权主义的思想体系内部充斥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得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以构建更加平等的性别话语体系为动力,但是平等和平权在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及表现存在差异,宗教话语对公共生活的介入程度也不尽相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女权主义是社会公开辩论的一部分。(51)Jocelyne Cesari and Jose Casanova, eds., Islam, Gender, an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2.例如,同阿米娜·瓦杜德有过合作关系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姐妹”组织(52)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姐妹”成立于1988年,其主要宗旨包括发展和提高穆斯林妇女的权利;促进改变男尊女卑的观念和行为,消除对妇女的不公正和歧视;提高公众意识,依据伊斯兰教倡导的平等、公正和民主的理念推进法律和政策领域的改革。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公共教育、舆论宣传、向政府和立法机构递交备忘录、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开展穆斯林妇女的维权行动。法律援助一直是“伊斯兰姐妹”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宰娜·安瓦尔参与了审理一桩穆斯林男性娶二妻的案件,出庭为该男子的首任妻子辩护。领导人宰娜·安瓦尔(Zainah Anwar)曾宣称:“身为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我之所以关心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实践,是因为女性正在遭受打着伊斯兰名义的不公正待遇。在公共领域,穆斯林女性尚能够在一个发展和现代化的世界里大步向前。但在私人领域,在宗教权威和个人身份法的压力下,穆斯林女性经常要遭受打着伊斯兰名义的歧视。”(53)Zainah Anwar, “Negotiating Gender Rights Under Religious Law in Malaysia,” in Kari Vogt, Lena Larsen and Christian Moe, eds., New Directions in Islamic Thought: Exploring Reform and Muslim Tradition, p. 177.对于生活在欧美的穆斯林女性而言,穆斯林是少数群体,少数群体本身的生存压力和“9·11”事件后兴起的“伊斯兰恐惧症”,使她们要为消除社会偏见和不公正现象而斗争。蕾拉·艾哈迈德、阿米娜·瓦杜德和凯西尔·阿里这类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大多在北美大学里教授宗教学和性别研究课程。但在阿米娜·瓦杜德的自述中,在北美大学中教授伊斯兰教研究课程并非易事,她最早在基督教氛围较浓的美国南部教学,既要在教学中努力寻找到一种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解说方式,又要随时面临不同的文化挑战。(54)Amina Wadud, Inside the Gender Jihad: Women’s Reform in Islam,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 pp. 65-66.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欧美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多么具有争议性,她们的声音仍然只代表社会少数边缘群体。她们塑造的话语与其说是一种激进的改良呼声,不如说是少数群体寻求社会理解其信仰的一种表现。但无论如何,不同背景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均认为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与对宗教精神的追求是一致的,或至少是相容的。
无论是伊斯兰世界还是西方社会,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大多是社会活动家。曾任美国《伊斯兰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和北美穆斯林社会科学家协会副主席的凯瑟琳·布洛克(Katherine Bullock)(55)凯瑟琳·布洛克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就将自己的人生视为同倡导公平、中正和同情的伊斯兰相一致的“行动主义生活”(56)Katherine Bullock, ed., Muslim Women Activists in North America: Speaking for Ourselves, p. 70。瓦杜德本身就是有政治远见的,她秉持“没有父权制的伊斯兰教”这一观念,针对北美穆斯林社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她称之为“性别吉哈德”的活动。这些活动受到了“进步穆斯林联盟”和“纽约穆斯林改革运动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支持。(57)Jocelyne Cesari and Jose Casanova, eds., Islam, Gender, an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2-123.
伊斯兰女权主义活动家活跃于高校、媒体等公共空间,她们试图为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为穆斯林女性的权利发声。但正如玛丽·比尔德所言,大量事实表明,将妇女的声音完全排除在公共讨论外的“特拉马库斯式企图”(58)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特拉马库斯是奥德修斯与佩涅罗珀的儿子。在佩涅罗珀对吟游诗人歌颂希腊英雄们归家之路上遭遇的重重磨难的吟唱表达不满时,她的儿子特拉马库斯说:“母亲,请回到楼上你自己的房间,纺纱织布才是你的分内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此时此刻,我是一家之主,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佩涅罗珀于是离开大厅,回到了楼上。始终存在,即民众尚不习惯将女性的声音视为具有专业能力的声音。(59)[英]玛丽·比尔德:《女性与权力》,刘漪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0页。被视为“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也面临相似的边缘化处境,女权主义活动家虽积极投身公共领域,但外界要么给她们打上“虚假意识”的标签,要么就根本不和她们打交道。当今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依然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强烈形塑。穆斯林女性文化身份的体验、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以及伊斯兰世界冲突频发的现实及其与西方的紧张关系,都会对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发展及走向产生影响,亦会影响到其他穆斯林对伊斯兰女权主义的认知和反应。
总而言之,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挑战,使得这一群体的主张虽然表现出改革主义的倾向,但更多是处于如履薄冰的尝试状态。对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而言,在不断变化、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经典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古兰经》永恒的特质与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实践《古兰经》道路之间寻找平衡,以平等主义的姿态来重申穆斯林女性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自身传统中获得平等与权利,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