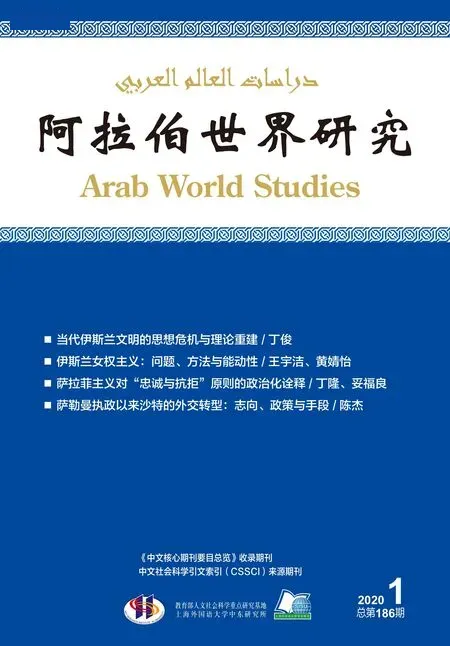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国内根源析论*
熊 亮
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既是一场由该国内部矛盾升级引发的战争,又是地区和国际力量在黎巴嫩扶植代理人、以黎巴嫩为主战场的代理人战争。黎巴嫩内战的爆发,是内外因素相互叠加、互动和影响的结果。本文通过考察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历史背景,梳理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国家认同危机、教派政治动员与政治力量重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等问题及其对黎巴嫩政治发展的影响,分析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国内根源。
一、 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成
黎巴嫩虽然是一个现代独立国家,但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种超越社会、能够缓和冲突并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之内的政府力量。这种现象是由黎巴嫩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黎巴嫩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巴勒斯坦毗邻,靠近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黎境内多山谷,居民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各教派社群杂居、割据的传统。黎巴嫩的与众不同还是其几个世纪相对与世隔绝的环境使然,崎岖的黎巴嫩山为国内的少数社群提供了天然庇护。(1)Bruce Borthwick,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0, p. 124.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前的30年间,黎巴嫩一直处于一种内外部因素的微妙平衡中。一方面,黎巴嫩作为一个人为划定的国家,其人口构成复杂,政治基础松散,时刻处于被外部敌对势力破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黎巴嫩的政治体制是中东地区独一无二的多元政体。(2)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7.
黎巴嫩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最早出现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1861年。黎巴嫩政治实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1975年至1990年内战的爆发,都与当时黎巴嫩的领土范围、人口构成和政治制度息息相关。黎巴嫩山是黎巴嫩最重要的地理标识,最初指的是黎巴嫩北部山区。随着天主教马龙派人口的增加以及由此带动的由北向南的人口迁徙,黎巴嫩山的概念扩展至整个黎巴嫩山区。居住在黎巴嫩山区的主要社群除天主教马龙派外,还有长期在此聚居的德鲁兹派。与此同时,不少东正教徒和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社群也在黎巴嫩酋长国时期(3)1516年至1697年曼家族统治时期和1697年至1841年谢哈布家族统治时期。在此地区定居。(4)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 18.
在德鲁兹派曼家族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统治的巅峰时期,黎巴嫩以德鲁兹派和天主教马龙派的合作关系为基础,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框架下实行事实上的自治。这一时期,黎巴嫩同欧洲天主教国家发展关系,逐渐向周边的叙利亚行省拓展势力范围。17世纪末曼家族衰落后,逊尼派谢哈布家族取代曼家族,德鲁兹派的地位逐渐下降。当时,得益于经济地位的改善,天主教马龙派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导致占统治地位的谢哈布家族也改信马龙派天主教,德鲁兹社群则向叙利亚南部地区迁徙。埃米尔巴希尔二世(1788年至1840年在位)在黎巴嫩山区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巴希尔二世倒台后,黎巴嫩进入了长达20年的社会政治动荡,其间爆发了马龙派农民针对封建领主的暴动和德鲁兹派与马龙派之间的冲突,后者强化了黎巴嫩的教派认同和社会分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5年黎巴嫩内战期间,在1984年至1990年黎巴嫩山战争中有突出体现。1860年德鲁兹派和马龙派之间爆发冲突,马龙派社群在法国远征军的帮助下避免了毁灭性结果的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黎巴嫩政治实体中,基督徒社群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派社群在其中分享权力。一个自治的黎巴嫩政治实体在这一时期能够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下建立,一方面是得益于欧洲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基督徒社群的人口数量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开始对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委任统治当局支持马龙派社群,视其为抗衡日益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社群、强化委任统治的可靠盟友。委任统治当局认为,应当对马龙派社群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为此在1920年9月1日颁布法令,将奥斯曼时期原属于叙利亚地区的部分疆域划给了黎巴嫩,这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大黎巴嫩国”。的黎波里、赛达和提尔等重要沿海城市以及利塔尼河和贝卡地区就是在此时被划入黎巴嫩的。黎巴嫩的疆域逐渐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然边界”。此后,法国开始根据自身对黎巴嫩社会的理解,着手重塑黎巴嫩的政治文化。法国人将黎巴嫩视为一个由多个宗教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根据这一观念来设计黎巴嫩的政治架构,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就此在黎巴嫩建立起来。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看,政治职务是根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社群的。(5)[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0页。
然而,在国土面积大幅增加、经济发展成果得到巩固的同时,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却出现了:一是大叙利亚主义的兴起;二是黎巴嫩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的大幅增加,使黎巴嫩原来基督教徒占多数的状况转变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口大体平衡的状况。(6)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9-10;季国兴、陈和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435页。在黎巴嫩山地区,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的76%,但在新并入的沿海城市以及东部的贝卡和东黎巴嫩山等地区,基督徒仅占人口总数的58%。由于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异,这一比例在日后持续下降。(7)[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第281页。黎巴嫩的人口结构由此发生了重要变化。
1943年,比沙拉·扈里领导的以马龙派社群为核心的基督徒社群,与里亚德·苏尔赫领导的以逊尼派建制派为核心的穆斯林社群同意分享权力,达成《民族宪章》,黎巴嫩现代国家的框架和教派分权体系得以确立。《民族宪章》的达成使黎巴嫩事实上成为不同宗教社群实行自治的联邦国家,国民向各自所属的社群效忠,社群—教派领袖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教派内部裙带关系成为制约国家政治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无法反映真正的人口构成,议会成为具有高度排斥性的政治利益网络。宪章实际上将法国为实行殖民统治所推行的“社群主义”原则神圣化,进而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间分配权力职位,导致国家难以实现真正的政治融合。法国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遗产,其危害的持久性远超法国人统治的历史。(8)同上,第316页。
然而,占人口比重越来越高的什叶派社群因其经济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偏低且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员,在分权体系中未获得与其人口比例相匹配的权力。根据1943年《民族宪章》,黎巴嫩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由马龙派人士、逊尼派人士和什叶派人士担任。但实际上,什叶派的政治地位明显低于马龙派和逊尼派。这凸显出黎巴嫩政治体系的先天缺陷,为日后国内的政治动荡和内战冲突埋下了隐患。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改革派等不同意识形态集团而言,各自的政治议程在这一制度安排下难以推进,他们纷纷将教派主义政治制度视为践行其政治理想的障碍。而对于叙利亚、埃及、苏联等外部势力而言,只要投入有限的资源扶植特定派别,便能削弱甚至打击其他外部势力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黎巴嫩的政治体系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局面:对内封闭且缺乏活力,对外过于开放而缺乏对外部影响的抵抗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黎巴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正视教派差异,使各派别减少教派敌对情绪、发展竞合关系;而不像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刻意漠视教派差异。这一多元政治安排使黎巴嫩成为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唯一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制度的国家。(9)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24-26.
1958年,黎巴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部危机(10)也有史学家将其定义为内战,本文统一称为“1958年危机”。,凸显了黎巴嫩政治体系的先天缺陷和改革困境。当时,黎巴嫩穆斯林相信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强烈要求获得更大政治权力。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未再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又反过来加重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不愿分享权力。黎巴嫩穆斯林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要求赋予他们更多的政治话语权。(11)[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第409页。
总的来看,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是黎巴嫩立国和发展的基础。对黎巴嫩而言,这一制度既是最不坏的选择,又是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政治制度的僵化为黎国内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 黎巴嫩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认同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对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作为天主教社群的长期庇护方,法国始终将确保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属性”(12)同上,第280页。作为其在黎利益的重要落脚点。二战后,法国在黎巴嫩影响力大幅下降,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头渐起。1943年,穆斯林社群与基督徒社群达成《民族宪章》,基督徒社群受制于自身不再具备人口优势的现实,不再强求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属性,承认黎巴嫩在一定程度上是阿拉伯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在欧美国家的支持下保持自身的传统支配地位;逊尼派建制派力量则清醒地认识到,在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与马龙派妥协几乎是最大程度维护逊尼派自身权益和影响力的唯一选择,遂不再坚持黎巴嫩与叙利亚合并的主张。
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尔·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对黎巴嫩内战中不同阵营的政治目标曾有如下论述:以基督徒社群为代表的守成派,得到了部分逊尼派建制派力量的支持,其目标在于维护黎巴嫩现行政治体系,特别是基督徒社群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以穆斯林社群为代表的修正派,其骨干力量是德鲁兹派和什叶派,该群体致力于改革或颠覆现行政治体系,提升穆斯林社群地位。(13)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 45.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黎巴嫩政局主要由支持现行体制的守成派主导;修正派在政府和议会中被普遍边缘化,无法谋得一席之地。但与叙利亚和埃及军人执掌政权以及约旦阿卜杜拉国王遇刺等周边国家面临的危机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黎巴嫩仍能通过宪政体系应对国内政治危机。然而,1958年危机成为改变黎巴嫩政治生态的分水岭。这场危机是在一系列内外矛盾交织激化的背景下爆发的。冷战时期,由埃及总统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整个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黎巴嫩亦受到波及。主导政局的基督徒社群对日益兴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态度暧昧,这引发了作为黎巴嫩“二等公民”的穆斯林社群的反思。后者认为,穆斯林拥有人口优势,应赋予该群体更多话语权,黎巴嫩的对外政策也应与纳赛尔的主张合拍。(14)[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第409页。
面对这一局面,黎巴嫩基督徒社群领导层内部出现了立场分裂。一派主张采取灵活的安抚政策渡过难关;而以总统夏蒙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与西方和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浪潮。然而,夏蒙通过修改宪法谋求连选总统的尝试,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逐渐朝着对其不利的方向发展。1958年2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最终引发了以长枪党代表的支持夏蒙的阵营,同以穆斯林社群为代表的、主张黎巴嫩并入叙利亚的反对派阵营之间的武装冲突。在此过程中,黎巴嫩政府军在福阿德·谢哈布将军领导下保持中立,按兵不动。事情的结果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应黎巴嫩政府要求在贝鲁特登陆,而夏蒙则被迫放弃连任诉求,谢哈布在美国和埃及的支持下当选新一任黎巴嫩总统,既有政治局面得以维持,内阁人员构成进行了相应调整。
这场冲突本质上反映的是黎巴嫩自《民族宪章》达成以来,基督徒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对黎巴嫩国家属性的一种勉强认同。(15)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27-28.虽然这场冲突表明,黎巴嫩的政治制度和黎巴嫩人生活方式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同胞而言仍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任何企图改变黎巴嫩既有政治安排的极端措施,都将导致暴力危机的发生,这种制度安排仍然只是最不坏的选择。1958年至1970年间,黎巴嫩基督徒社群仍采取维持现状、拒绝改革的立场。对基督徒社群而言,改变以自由主义经济、低税收、小规模官僚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现行社会经济体系,以及限制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都是难以接受的。享有支配地位、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基督徒社群担心,任何改革措施都有可能使穆斯林社群受益,并带来一系列可怕的政治后果。(16)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29-30.这种担心或许可以理解为,维持本社群支配地位和特权的诉求,始终是影响基督徒社群认同黎巴嫩国家属性的消极因素。
黎巴嫩穆斯林社群对平等的政治参与的诉求,实际上意味着穆斯林建制派开始脱离长期以来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影响,转而采取《民族宪章》所倡导的黎巴嫩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以长枪党、自由国民运动为代表的马龙派等基督教政治力量,显然没有意识到穆斯林社群的变化,仍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地位。1974年秋,黎巴嫩基督教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长枪党面临来自三大政治战线的挑战:巴勒斯坦拒绝阵线、黎巴嫩修正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建制派。当时,长枪党同时反对黎巴嫩修正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建制派,其后果是使二者走近、修好,而后者实际上有可能成为长枪党对抗修正派的盟友。(17)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Delmar: Caravan, 1977, pp. 83-84.
黎巴嫩是一个由不同宗教社群组成的国家,每个社群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历史属性和利益诉求,教派忠诚十分强烈且突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在黎巴嫩建立一种将教派忠诚排除在外的政治制度是难以想象的。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民族运动等修正派力量自196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主张修订《民族宪章》、变更选举法、废除公共职位和议会中的教派代表制。民族运动宣称,《民族宪章》笼罩下的黎巴嫩国家统一是虚假的,国家真正实现统一需要摒弃教派因素,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公正。与民族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反对《民族宪章》不同,以萨义布·萨拉姆、拉希德·卡拉米和大穆夫提哈桑·哈立德为代表的逊尼派阵营主张黎巴嫩穆斯林应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力,这实际上是希望马龙派将自己的权力让渡一部分给逊尼派社群。但马龙派大权在握,特别是牢牢占据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公安总局局长等职务的现实,导致逊尼派社群难以实现上述诉求。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为整合政治立场和统一军事指挥,守成派力量代表、前总统卡米勒·夏蒙领导的自由国民党、杰马耶勒家族领导的长枪党和弗朗吉亚集团于1976年组建了黎巴嫩阵线。黎巴嫩阵线于1980年12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想要建立的黎巴嫩》的文件,阐述了其指导路线。文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在基督徒社群不占人口主体的黎巴嫩实现该社群对国内政治的支配地位。黎巴嫩阵线认为,尽管基督徒社群的人口规模已不占优,黎巴嫩阵线仍以基督徒社群的名义,要求该社群在黎巴嫩享受特殊地位。黎巴嫩阵线的理由是,黎巴嫩基督教徒在国家的历史形成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属性应当得到保护。
综上,黎巴嫩穆斯林社群和基督徒社群对该国国家属性的认同均持保留态度,其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黎巴嫩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教派主义政治制度造成教派间的割裂状态,使得国家认同危机不断发酵,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制度的负面效应。
三、 黎巴嫩教派政治动员与政治力量重组
天主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派政治动员是影响黎巴嫩内战爆发和走势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黎巴嫩政治力量重组的关键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黎巴嫩面临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1958年危机一方面导致了黎巴嫩政治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也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员提供了空间。这一时期,黎巴嫩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伴随贝鲁特、赛达和的黎波里等城市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是大批沿海城市,特别是贝鲁特城郊贫民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甚至有来自乡村的穆斯林移民直接将房屋建造在原属房地产开发商或基督教修道院的土地上。可以说,贫民区是黎巴嫩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副产品。一方面,公立教育系统的扩大为更多农村人口前往大城市谋生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谢哈布政府着力打造的乡村道路网络,为农村居民进城提供了极大便利。这带动了贝鲁特郊区什叶派贫民区人口的迅速增长。(18)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p. 7-8.同一时期,马龙派农村居民也在向城市大量迁移。从迁移方向来看,一般是北部地区农村人口向的黎波里迁移;中南部地区农村人口大部分向贝鲁特迁移,小部分向南部沿海城市赛达迁移。在此过程中,贝鲁特周边马龙派和什叶派的新聚居区逐渐相互毗邻。
来自天主教马龙派的皮耶尔·杰马耶勒于1936年成立的黎巴嫩长枪党是基督徒社群的代表性政治力量。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激进的青年运动,主张“腓尼基主义”,初期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受到同时代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军事色彩和马龙派民粹主义特征,同时还纳入了贝鲁特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强调黎巴嫩实体的思想。该党从最初的反对法国殖民、支持黎巴嫩独立,到黎巴嫩独立后转变为反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政治上比较务实。
杰马耶勒来自贝鲁特附近的黎巴嫩山马腾地区北部的布克菲亚镇。当时的布克菲亚镇是黎巴嫩山区中具有国际化氛围的一个村镇。杰马耶勒家族系当地名门望族,拥有“谢赫”头衔,他本人早年从事药剂师工作。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几大群体:马腾地区和贝鲁特东北部的农民;从山区迁居至贝鲁特、赛达和的黎波里并逐渐丧失传统教区归属的马龙派;具有政治诉求的基督徒,该群体将拥有严密政党组织、与政府联合的长枪党视为争取更大政治资源的渠道。杰马耶勒以马龙派社群的中下层为主要政治动员对象。1958年危机爆发后,长枪党选择与谢哈布当局开展合作,成为谢哈布主义的支柱之一。但相当一部分基督教派,特别是东正教派则因此不再支持长枪党,导致其地位受到削弱。在他们看来,长枪党是奉行机会主义的“谢哈布主义者”,粗俗且乡土气浓重,其民兵组织更令人反感。(19)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 4.
成立伊始的长枪党为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反对黎巴嫩基督徒社群的穆斯林团体,曾试图与当权派建立良好关系,使自己在黎巴嫩政坛中保有一席之地。在领导长枪党的40余年间,老杰马耶勒在坚守建党初衷的同时,展现出与时俱进的魄力以及进行政治参与和调整政治策略的务实性。20世纪50年代长枪党赢得议会席位后,开始以议会政党的身份参与黎巴嫩的政治进程。在这一时期,长枪党有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精心设计的领导层级和官僚体系。同时,长枪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方面具有极强的灵活性。杰马耶勒的侄子莫里斯·杰马耶勒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莫里斯·杰马耶勒主张政党应超越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的敌对竞争关系,倡导“黎巴嫩主义”和社会经济改革,在发展党员时注重吸纳非基督徒和非马龙派人士加入长枪党。然而,从该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此举更多地是长枪党采取的权宜之计。本质上,长枪党仍是一个具有马龙派教派属性的政党,其强调的“黎巴嫩主义”实则是基督教属性。当危机爆发之时或黎巴嫩政局不明朗时,长枪党扮演的历史角色仍然是在充满敌意的穆斯林汪洋中,以武力捍卫黎巴嫩基督徒社群的保护者,充当黎巴嫩基督教国家属性的最后屏障。(20)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61-62.
什叶派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并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定居,也为其日后进行政治动员奠定了基础。当时黎巴嫩议会按照基督徒与穆斯林6:5的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已难以充分反映黎巴嫩真实的人口现状,选举的结果更无法代表黎巴嫩社会的真实情况,议会代表的有效性与社会舆论、民众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至1970年3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袭击的报复性打击波及至黎南部地区,当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村庄遭受严重破坏,这导致大量村民流离失所,被迫北上迁移至贝鲁特郊区聚居。然而同一时期,黎巴嫩的基督徒社群和执政当局却乐见贝鲁特郊区贫民区中什叶派人口的迅速增加,想当然地认为贫民区什叶派人口是他们的天然盟友,不会与城市逊尼派为伍。无论是卡米勒·夏蒙还是雷蒙德·埃代,都拥有各自的什叶派拥趸;杰马耶勒领导的长枪党此时也招募了不少什叶派成员。从当时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伊朗是黎巴嫩基督教派的盟友,而伊朗极易对黎巴嫩什叶派产生政治影响,这无疑使黎巴嫩基督徒社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逻辑判断。但现实情况是,相似的经济社会境遇使黎巴嫩城郊贫民区居民和毗邻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共生关系,双方彼此同情对方的遭遇。当时基督教派领导人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在什叶派政治动员发生的初始阶段,未能将局势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法当局利用黎什叶派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不信任感来稳固委任统治,给予了黎什叶派社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不具备的权利。1926年,为体现黎巴嫩的制度优越性,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赋予了什叶派社群独立的司法地位。1967年,什叶派成立该教派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穆萨·萨德尔于1969年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在当时众多激进群体中,什叶派已成为第一大社群,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萨德尔在谢哈布执政初期回到黎巴嫩,凭借其睿智、个人魅力和灵活的手腕迅速成为引人瞩目的穆斯林政治领袖。(21)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p. 61-63.萨德尔曾在伊朗和伊拉克求学,父亲是黎巴嫩人,他与伊朗王室有着复杂且密切的关系。他一手创建“阿迈勒运动”,为什叶派社群的利益代言。萨德尔主张什叶派应在黎巴嫩政治体系中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职位,要求政府保护什叶派聚居的南部黎以边境地区,并向什叶派聚居区拨款实施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打击腐败。(22)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 38.
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力量重组是在一系列社会因素、地区冲突和国内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黎巴嫩什叶派人口的大幅增长。20世纪70年代初,黎什叶派平均每个家庭拥有9口人,同时期的基督教家庭人口只有6人。即便在穆斯林社群内部,什叶派妇女平均要比逊尼派妇女多生一个孩子。拥有十多个孩子的什叶派家庭在当时的黎巴嫩并不鲜见。(23)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ezbollah: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黎巴嫩建国后的十年间,人口流动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人口从穷乡僻壤向贝鲁特或海外迁徙,甚至远及美洲和非洲地区。当时,侨汇是黎巴嫩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为什叶派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资金支持。内战爆发前,黎巴嫩什叶派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较低。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来到黎巴嫩后,其意识形态对黎巴嫩民众具有较强吸引力,参与巴解武装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用于养家糊口,这对于缺乏经济机会的什叶派群体非常有吸引力。正因如此,黎巴嫩内战中什叶派人口的损失远超过其他任何派别。
但是,此时的什叶派建制派已与大众脱节,群众基础几乎丧失殆尽。实际上,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早在1926年叙利亚反法暴动期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承认什叶派社群拥有独立的司法地位,黎巴嫩南部和贝卡地区的什叶派政治领袖对该派获得大量权力和财富颇为满意,并没有对相关政治安排提出异议。什叶派社群政治和宗教领袖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度十分有限。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动员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社群内部政治力量重组的过程。
综上所述,人口比例的不断变化使马龙派社群的担忧不断积聚,该社群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持续发展,长枪党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政治力量。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地位的不满,什叶派为改变自身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政治动员,进一步刺激了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徒社群的反弹。两大教派及所属社群之间的矛盾又反映在教派主义政治制度上。马龙派认为,确保该制度的存续是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关键,也是其政治动员的最主要动机;什叶派则认为,该制度是阻碍其发展的桎梏,其政治动员的目的在于修正这一制度。二者的动机和目的之间的矛盾成为催化黎巴嫩政治形势不断恶化的主要因素。
四、 黎巴嫩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
1975年4月,黎巴嫩内战爆发。这场内战发生在黎巴嫩独立以来最后一支外国武装部队撤离29年之后。(24)黎巴嫩于1943年独立,法军于1946年撤离。1946年至1975年间,黎巴嫩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使其以贸易和服务业为主的私营经济蓬勃繁荣。黎巴嫩政府采取不干预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当时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的财政政策,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这一举措促进了黎巴嫩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与当时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成为黎巴嫩在整个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刺激下,黎巴嫩不仅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同时还实现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这为进一步吸收外来资本尤其是来自美国和南美洲国家的侨汇奠定了基础。(25)参见Samir Makdisi, “Flexible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The Lebanese Experience, 1950-1974,” World Development, Vol. 6, No. 7, 1978, pp. 991-1003.据估算,1950年至1974年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约7%,1974年黎巴嫩的人均收入达1,200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450美元,在阿拉伯国家中排名第7。(26)Robin Bar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1950-19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4, No. 2, May, 1982, pp. 129-157.1971年前,黎巴嫩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在2%至3%,在内战爆发前三年增至8%。1970年至1974年间,黎巴嫩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2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1965年至1969年数据涨幅达45%。1970年至1974年间,黎巴嫩人口增长了10%。内战爆发前,黎巴嫩本国人口约300万(27)Samir Makdisi and Richard Sadaka, “The Lebanese Civil War, 1975-1990,” Lecture an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3, p. 28.,首都贝鲁特是内战期间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空港。
上述经济成就的取得与谢哈布时期的政策密切相关。1958年至1964年间出任黎巴嫩总统的谢哈布,被不少学者和黎巴嫩普通民众视为黎独立后最杰出的政治家。谢哈布拥有其他政治家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本:权威地位、家族声望、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在1958年危机中坚守中立而塑造的“救世主”形象等。作为马龙派的政治领袖,谢哈布采取温和路线,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身份认同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两股力量中游刃有余,在现实政治中采取了略倾向于纳赛尔主义的外交政策。围绕他个人形成的“谢哈布主义集团”致力于加强黎巴嫩中央政府权威,严把情报系统,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黎巴嫩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国内广泛的人口流动,其间开展的社会、政治动员相对削弱了守成派的影响力。
研究内战问题的科利尔和霍夫勒将导致内战爆发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大变量:社会分化、族群优势虚拟变量、收入和经济增长、自然资源财富以及人口规模。根据这一模型,黎巴嫩内战前爆发冲突的风险并不高。1970年,黎巴嫩爆发冲突的概率仅2.6%,远低于同时代没有经历内战冲突的国家(5.8%)。由于该模型采取的数据以5年为一个周期,因此无法掌握单个年份的准确数据。但从该模型几大变量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内战爆发前的1974年的冲突发生概率较1970年并无太大变化,其间黎巴嫩国内的相关变量因素都未发生显著变化。从族群角度来看,黎巴嫩国内人口属于同一族群,国内的社会分化更多表现为宗教和教派层面的分化。根据科利尔和霍夫勒构建的模型,一国如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45%~90%)的族群,则国内冲突的风险将增加,而黎巴嫩实际上没有占人口支配地位的单一族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科利尔和霍夫勒模型中关于经济变量对冲突爆发风险的影响并不适用于解释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根源。繁荣的经济极大地满足了普通民众的获得感,但这种获得感并不平衡。黎巴嫩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拥有不同的幸福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不平衡在教派因素的叠加下更加突出。更严重的是,政府缺乏解决问题的意愿和措施。(28)掌权的基督徒社群担心穆斯林社群通过改革获益进而威胁自身地位。从社会经济地位看,基督教徒普遍比穆斯林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穿着更讲究,居住条件也更好。各宗教社群的经济社会状况存在明显差异:非天主教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处于顶端,德鲁兹派位于中间位置,逊尼派处于中下层,什叶派则处于最底层。(29)Michael Curtis,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 243.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73年至1974年间,黎巴嫩国内54%的人口属于相对贫困阶层,25%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21%的人口属于富裕和非常富裕阶层。(30)B. Labaki and K. Abou Rjeily, Bilan des Guerres du Liban, 1975-1990, Paris: L’Harmattan, 1993, p. 182.虽然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但如果综合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教派因素来考察黎巴嫩的经济发展状况,便能窥见推动黎巴嫩国内冲突爆发的相关因素。以首都贝鲁特为例,在内战爆发前已逐渐形成以基督徒社群为主的东区和以穆斯林社群为主的西区,(31)贝鲁特东区是指1975年内战爆发后贝鲁特东部由长枪党及其领导的联盟控制的基督徒聚居区。1975年至1976年间,长枪党驱逐了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仅有少量非基督徒被允许在此居住。贝鲁特西区是指1975年内战爆发后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聚居区。在此期间,一些基督徒仍居住在这一区域,主要集中在拉斯贝鲁特地区(Ras Beirut或Tip of Beirut),即贝鲁特西北角临近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濒海区域,这是贝鲁特的文化和知识中心,黎巴嫩不少显赫家族在此定居。贝鲁特东西区由绿线(Green Line, 又称Demarcation Line,即分界线)分割开来,然而实际上两区之间并没有一条实际存在的分割线,绿线基本上指由贝鲁特由北向南延伸的大马士革大街,最醒目的标识是各民兵武装林立的哨卡。绿线得名于被遗弃和损毁的街道、建筑物附近肆意生长、无人打理的绿色草木。战争期间,各派民兵在贝鲁特实行割据占领,将本派人口迁入各自占领区,绿线附近的建筑物损毁最为严重。1990年10月,时任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将东西区合并统一。参见Asad AbuKhali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ebano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1998, pp. 65, 225。高度发达富裕的区域毗邻极为贫穷落后的区域,中间星罗棋布的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飞地。黎巴嫩南部地区巴解组织武装对以色列突袭招致以军报复性袭击,导致大批黎南部居民涌入贝鲁特避难和谋求生计,其中不少居住在南郊贫民区。涌入的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其中又以什叶派人口居多,窘迫的经济状况导致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进而改变了贝鲁特的政治生态。无论是传统的守成派政党,还是新兴的修正派力量,都通过激进化的言论和立场来吸引支持者,传统建制派政治领袖的地位受到削弱,原有的政治共识不断遭到蚕食。同时,大部分中产阶级生活在贝鲁特(主要由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组成)和中部山区(主要为基督徒),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黎巴嫩南部、贝卡谷地、东北部和北部阿卡地区,当地的中产家庭少之又少。这一现实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被烙上了一层教派色彩。
除大力发展经济外,谢哈布总统在任内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实行严格管控。当时的黎巴嫩面临在黎巴勒斯坦人可能建立政治、军事组织的巨大压力,埃及纳赛尔总统对此更是推波助澜。(32)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 10.除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外,当时的黎巴嫩还面临其他诸多挑战。1958年危机后,黎巴嫩军事情报局已关注到国内涌现出一批逊尼派黑帮,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支持纳赛尔主义。为了将他们从逊尼派政治强人赛义卜·萨拉姆身边拉走,军事情报局雇佣了他们,并赋予其一些特权。1961年,萨拉姆因反感谢哈布总统的强势作风与其决裂,导致部分逊尼派人士对总统不满。但客观而言,谢哈布政府对待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对逊尼派还是什叶派的政策和态度都是妥当的。谢哈布在叙利亚与埃及关系破裂后并不急于背弃纳赛尔而与叙利亚修好,这很大程度上平复了纳赛尔主义者的情绪,缓解了他们的焦虑。(33)Ibid., pp. 11-12.
在谢哈布时期,黎巴嫩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持续完善。谢哈布严格践行《民族宪章》,在各教派间公平地分配行政权力。尽管如此,黎巴嫩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是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穆斯林社群中,什叶派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其政治权力份额无法如数兑现,不少权益被逊尼派和德鲁兹派瓜分,其中也不乏什叶派整体受教育程度低导致的缺乏担任要职的资质等原因;在基督徒社群中,马龙派明显挤占了希腊东正教等其他教派的份额。如前所述,谢哈布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国家路网、公立教育、自来水、电力和医疗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覆盖乡村地区的公共设施网络。新的社会保险方案的实行,获得了国内民众的普遍赞誉。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对后继政府的治理构成挑战。
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为出发点,谢哈布最初打算收拢传统分肥政客的权力。但谢哈布逐渐意识到,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谢哈布仍信奉民主制度,珍视黎巴嫩的独立性,只有政治上的妥协才能使这一制度为建设独立的黎巴嫩继续发挥作用。向传统政客低头意味着对官僚系统的腐败持纵容态度,这使得谢哈布政府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被腐败所拖累。尽管他曾竭力打击腐败,但腐败问题始终未根除,底层民众——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马龙派的被剥夺感不断累积。(34)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p. 18-19.尽管谢哈布总统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和调停者,但他并不是改革者,缺乏正视、解决黎巴嫩根本性问题的勇气。这些问题包括黎巴嫩的国家认同危机、社会现实与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错位状态、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能力薄弱等。
同一时期,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杰拉勒·卡瓦什之死迫使黎巴嫩当局不得不放松对巴解组织的控制。卡瓦什死前居住在赛达外围的艾因哈尔瓦巴勒斯坦难民营,据悉他因制造事端被黎军事情报局逮捕,后死于监狱中。黎军事情报局长期以来被视为谢哈布主义集团最重要的堡垒,这一事件无疑为反谢哈布势力提供了借口。一时间,黎巴嫩各种政治势力对此兴师问罪,卡迈勒·琼布拉特挑头,联合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中反谢哈布集团的势力,对军事情报局施加压力。经过这一事件,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对巴解组织武装进行有效监控的军事情报机构遭受严重的信任危机。为谨慎处理与巴解组织的关系,黎军事情报局只得默许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境内扩大活动范围。(35)Ibid., p. 28.
1970年9月,约旦开始压制国内的巴解组织武装,当局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基本控制了该组织在约旦境内的活动。当时人们普遍预测,弗朗吉亚治下的黎巴嫩也将采取类似措施抑制巴解组织的活动。实际上,黎巴嫩与约旦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约旦,王室哈希姆家族的权力源自由外约旦人组成的军队,他们对巴解组织武装在约旦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军方与政府紧密团结。在黎巴嫩,军队主要官员系马龙派人士,陆军军官主要来自基督徒社群。但由于当时的黎巴嫩实行志愿兵制,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基督徒进入军队服役的人数逐年减少,而经济条件较差的穆斯林进入部队的人数则逐步增加,这些穆斯林士兵大多都来自贫穷的什叶派聚居区。
1958年危机爆发时,军队在谢哈布的领导下展现出了不俗的团结,但当军队与巴解组织武装的关系不断恶化乃至产生冲突时,军队将势必遭到国内穆斯林社群的反对。在黎巴嫩,巴解武装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穆斯林社群的安全保障,压制巴解组织武装意味着对整个穆斯林社群的打压。尽管此时黎南地区已经遭受以色列针对巴解组织袭击进行的报复性打击,南部居民甚至不得不忍受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国土上的高调军事行动,但没有人愿意公开反对巴解组织的存在。在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政坛,打击巴解组织极易造成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形成对抗进而酿成政治危局。(36)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p. 52-54.
总的来看,尽管内战爆发前黎巴嫩经济形势整体向好,但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和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失能,使得黎巴嫩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无法达到预期,这导致黎巴嫩的社会矛盾在原有教派割裂局面的基础上因阶级对立而进一步尖锐化。与此同时,谢哈布政府自身治理能力危机和反谢哈布主义势力影响的上升,对黎巴嫩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构成了严重阻碍。这一局面导致内战爆发前几乎黎巴嫩国内各社群和阶层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和焦虑之中。
五、 黎巴嫩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上述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黎巴嫩的政治形势持续恶化。在谢哈布总统明确表示不寻求连任后,夏尔·赫卢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赫卢出身巴卜达地区马龙派名门,1929年毕业于圣约瑟夫大学,早年在黎巴嫩当地一家法语报社任记者,与皮埃尔·杰马耶勒等人共同创建了黎巴嫩长枪党,后因与杰马耶勒意见不同而退党。赫卢曾于1949年参与了同以色列的停战协议谈判,先后担任黎巴嫩驻梵蒂冈大使、司法部长、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赫卢在任期内继续采取谢哈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中东国家民众经常将黎巴嫩称为“东方巴黎”或“中东瑞士”,这种称法大致就是在此时流传开来的。
但是,赫卢的任期并非一帆风顺。 他先后经历了1966年国家商业银行危机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最严峻的挑战是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持续增加。这些武装人员越境袭击以色列,同黎政府军发生冲突。赫卢抵制巴勒斯坦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但迫于各方压力难有作为。随着谢哈布主义集团逐渐失势,议会中马龙派三大政治集团——皮耶尔·杰马耶勒的长枪党、夏蒙的自由国民党和雷蒙德·埃代的民族联盟,联手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占得先机,继而又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中凭借微弱优势击败谢哈布主义集团。1970年,黎巴嫩北部地区马龙派保守派领袖苏莱曼·弗朗吉亚击败谢哈布主义集团候选人埃利亚斯·萨尔基斯当选总统,(37)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p. 29-31.而谢哈布集团势力随着1973年谢哈布的逝世有所弱化。
弗朗吉亚家族是北方兹加尔塔地区的马龙派望族,苏莱曼·弗朗吉亚的哥哥哈米德·弗朗吉亚早在黎巴嫩独立后的扈里政府中便担任外长一职,1952年成为总统候选人。1958年,哈米德曾是继夏蒙之后的总统热门人选之一,但他因中风瘫痪最终被迫退出。此后,苏莱曼成为弗朗吉亚家族的旗帜性人物,并以强硬作风著称。1970年,苏莱曼和谢哈布、夏蒙、埃代及杰马耶勒一起被视为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在谢哈布明确表示不参选后,谢哈布主义集团候选人萨尔基斯也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萨尔基斯是谢哈布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能力卓越。1966年国家商业银行倒闭后,黎巴嫩社会出现恐慌情绪,这一状况直到萨尔基斯就任央行行长后才得以缓解。萨尔基斯的短板在于其仅拥有职业官僚履历,缺乏政治领袖背景,这导致他在与弗朗吉亚的最终较量中以极微弱劣势败北。(38)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 50.
苏莱曼·弗朗吉亚当选总统后任命自己的逊尼派盟友萨义布·萨拉姆为总理并成功组阁,政府面貌一度焕然一新。但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弗朗吉亚政府先后经历药品丑闻、教育改革方案实施受阻、税收改革推进不力等不利局面,内阁多名部长辞职。改革受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建制派和垄断资本家不愿放弃特权,而海湾产油国热钱的流入以及本国贸易商、零售商的贪得无厌,使得黎巴嫩出现通货膨胀,物价、房租快速上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局面成为修正派批评黎巴嫩体制弊病的口实,政府被迫重组。(39)Ibid., pp. 54-57.
萨拉姆组建的首个内阁为数不多的“政绩”是对军队改组,改组对象主要是军中的谢哈布主义集团成员。由谢哈布主义者主导的军事情报局被解散,由亲政府的陆军军官情报机构替代。在黎巴嫩迫切需要规制和监管巴解组织武装、国内激进分子、阿拉伯和外国谍报人员活动的时期,拥有12年相关经验的军情局被毫无经验的陆军军官情报机构所取代。后者试图通过重建情报网络来应对国内危局,但因情报机关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局势迅速失控。与此同时,政府中去谢哈布化进程基本完成,仅有萨尔基斯留任央行行长一职。在改革无望的情况下,新总统任人唯亲,导致腐败丛生,民众极度愤懑。(40)Ibid., pp. 59-61.黎巴嫩底层民众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日益加重,而代表这部分人利益、主张改革的修正派却在议会选举中表现令人失望。修正派指责黎巴嫩的选举制度服务守成派的利益,提出重新举行大选,扩大选区规模,降低选民年龄,废除按照教派划分席位的安排。
1973年6月,塔吉丁·苏尔赫出任黎巴嫩总理,将政府的主要任务设定为净化政治环境,缓解国内紧张局势,与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建立稳定关系。但此时的黎巴嫩物价飞涨、劳工诉求无法被满足、学生示威时有发生、以色列对黎南地区袭击不断、黎巴嫩国防体系无力,国内局势急剧恶化。以保护基督徒社群为由而迅速崛起的马龙派长枪党民兵武装(41)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p. 36.,以及什叶派及逊尼派穆斯林社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倾向。当时黎巴嫩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已难以应对国内政治极端化带来的挑战。各社群之间的合作愈发困难,这突出体现在政府组阁和1972年的议会选举中。大批老派的政治领袖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缺乏缓解紧张局势的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政治良性运转的障碍。(42)Ibid., pp. 39-40.
1973年秋,黎巴嫩国内秩序逐渐失控。10月18日,3起连环爆炸事件先后破坏了贝鲁特和马赛的水下通信线路,黎巴嫩与欧洲和美国的通讯被迫中断。同日,“阿拉伯共产党”组织的5名武装人员袭击了贝鲁特美国银行,将银行工作人员和客户扣为人质,勒索1,000万美元用于阿以战争。次日清晨,黎巴嫩内部治安军突入银行,事件导致2名武装分子被击毙、3名武装分子投降以及2名人质死亡。此后,左翼激进力量持续发力。同年12月,一群思想激进的学生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黎巴嫩之际组织罢课。不久,贝鲁特的学生组织示威活动,抗议物价高企,3名学生在事件中受伤,1名警察遇害。(43)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 73.
1974年,贝鲁特还发生了多起学生罢课事件。当时,贝鲁特的消防员等发起为期3周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2月初,学生和工人在贝鲁特、赛达和提尔等地发动罢工,抗议物价上涨,威胁发动更大范围的罢工。2月底,学生再次罢课抗议基辛格二次访黎,并与内部治安军发生冲突。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生会由激进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学生把持,这批学生也发起罢课,抗议学费上涨,呼吁由学生参与管理学校。内部治安军随即进入学校,逮捕涉事学生,却又造成贝鲁特更大范围的学生示威游行。黎巴嫩国内社会运动的发展态势与当时整个世界政治激进化的形势相符。1974年9月,塔吉丁·苏尔赫因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辞去总理职务,总统弗朗吉亚遂任命拉希德·苏尔赫担任总理,再次引发混乱局面。一个由拉希德·卡拉米、萨义布·萨拉姆和雷蒙德·埃代组成的反对派阵营逐渐形成,这个被称为“新三方联盟”的反对派以反对政府现行政策和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为主要目标。(44)Ibid., pp. 85-86.在拉希德·苏尔赫上任前后的数月间,黎巴嫩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爆炸、抢劫、谋杀、绑架和政治暗杀频繁发生。1975年1月,苏尔赫政府着手打击和清剿的黎波里的恐怖分子,但其他地区的行动并未跟上,北部山区阿卡和兹加尔塔地区都爆发了冲突。不久后,黎南地区持续遭受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巴解组织武装与黎巴嫩政府军再次爆发冲突,前者向政府军营地发射了6枚火箭弹。事发后,杰马耶勒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抨击巴解组织武装在黎南地区的存在,敦促其解决内部各派别的无序状况。杰马耶勒不久便向总统弗朗吉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对巴解组织武装在黎巴嫩的存在等事项举行全民公投。
数日后,赛达地区爆发冲突。此前数月,赛达等黎巴嫩沿海地区的渔民都在为即将成立的渔业公司——“蛋白质公司”而担忧。这家公司由黎巴嫩和科威特合资建立,旨在将黎巴嫩的渔业机械化,公司董事长是自由国民运动领导人卡米勒·夏蒙。在黎巴嫩共产党等其他修正派别的诱导下,黎巴嫩的渔民将该公司的成立视为对黎巴嫩渔业的垄断。尽管公司方面尽力安抚渔民并许下各种承诺,但形势未见好转。1975年2月26日,赛达当地渔民举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吊销“蛋白质公司”的营业执照。示威活动逐渐升级为骚乱,并造成1名黎军下士死亡,赛达工会领袖马鲁夫·萨阿德中弹后不治身亡。事件的发生原因难有定论,事态尚未平息,贝鲁特激进派别便于2月28日组织了罢工和示威,部分道路被封,车辆遭人为纵火。次日,赛达地区民众指责军方应对马鲁夫遭枪击负责,在城中再次举行示威抗议,阻断了赛达通往提尔的道路。军队赶到现场后,在清除通往南部黎以边境的海岸公路的路障时遭遇武装平民持枪袭击,袭击者中包括数名临近艾因胡尔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人员。冲突导致5名政府军士兵和11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3月2日,赛达民众同意停火,政府军从城中撤离。尽管赛达冲突事件与巴解组织武装无直接关联,但却促使黎巴嫩各派别采取行动。激进派指责黎巴嫩当局是“法西斯分子”,联合资本家压榨工人阶级。(45)Kamal S. Salibi, Cross Roads to Civil War: Lebanon 1958-1976, p. 93.赛达事件也被学术界普遍视为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序幕。至此,黎巴嫩国内局势已接近内战爆发的边缘。
六、 结语
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国内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黎巴嫩国家的历史形成来看,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黎巴嫩。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既是黎巴嫩立国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各种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影响因素,僵化的政治制度为黎国内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黎巴嫩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便是改革甚至废除教派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对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基督徒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围绕国家属性分歧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深受黎巴嫩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正是这一政治制度造成了教派间的割裂状态,进而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持续发酵,反过来加剧了这种政治制度的脆弱性。
再次,人口构成的变化加剧了马龙派社群的担忧。马龙派通过长枪党,对本社群的中下层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与此同时,心怀不满的什叶派为改变自身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政治动员,进一步刺激了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徒社群。两大教派各自的关切也由此映射到教派主义的政治制度上。马龙派认为,确保该制度的存续是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关键,也是其政治动员的主要动机。什叶派则认为,教派主义的政治制度是阻碍本派别发展的桎梏,其进行政治动员的目的在于修正这一制度。二者的动机和目的之间的矛盾,成为黎巴嫩政治形势恶化的刺激因素。
最后,尽管内战爆发前黎巴嫩经济形势整体向好,但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和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失常,导致民众难以获得符合预期的幸福感,黎巴嫩原有的社会矛盾在教派割裂局面的影响下因阶级对立而进一步尖锐。与此同时,反谢哈布势力的持续坐大使得黎巴嫩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不升反降,社会运动和巴解组织武装活动愈演愈烈,内战爆发前几乎所有社群和阶层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和焦虑之中。
尽管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先天缺陷,但由于历史所致,它在客观上仍属于符合黎巴嫩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政治制度设计,并在黎巴嫩独立后的十余年间维持了国家政治的脆弱平衡,因此,如果武断地将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显然有失公允。实际上,一旦调整和改革适当,国家仍有机会使该制度继续有效运转。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国内根源在于过于僵化的政治实践和封闭的利益链条。政治精英阶层缺乏对制度进行调适和变革的意愿、智慧和勇气,以至于在迅速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国家认同危机加剧、教派政治动员与政治力量重组无序进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水平持续走低,一系列因素的交互叠加,使得黎巴嫩逐渐滑向了内战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