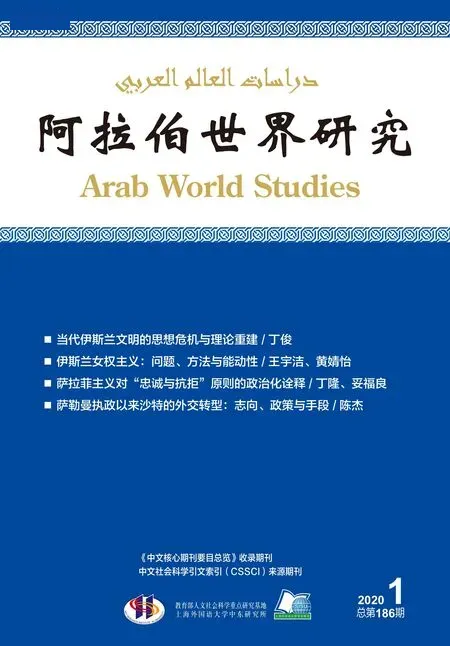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的安全治理*
李竞强
长期以来,突尼斯由于缺乏自主防御能力,一直被视作安全治理公共产品的消费者。(1)Ian O. lesser, “Security in North Africa: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Rand Project Air Force, 1993, p. 59.2011年以前,突尼斯虽重视安全问题,但与国际社会主流的安全观存在差异。在欧盟与北非国家的互动中,双方对安全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对突尼斯而言,安全意味着国家不受外部侵略和政权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融入欧洲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在欧盟看来,安全则意味着通过鼓励人权和民主实践,提升治理水平以及实现法治,进而促进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稳定。(2)Said Haddadi, “Political Securit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in the Maghreb: Ambiguous Discourses and Fine-tuning Practices for a Security Partnership,” Working Paper, No. AY0403-23, eScholarship, March 23, 2004,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8qm646tx, 登录时间:2018年6月20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欧盟加强了推进北非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力度,但效果不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在内的北非国家更倾向于保持政治稳定、维护政权安全,从而实现经济发展,而不愿为了经济发展的利益牺牲政治稳定。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并扩展至整个中东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突尼斯的传统安全观,使其安全治理陷入新的困境,反过来又制约了其民主转型。
一、 突尼斯的多重安全困境
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政权垮台,突尼斯进入了民主转型时期。经济重建、政治改革、社会发展成为转型时期突尼斯面临的艰巨任务,突尼斯的安全局面也不容乐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突尼斯受到了多重安全威胁,经常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一) 恐怖主义威胁
2011年以来,恐怖主义是突尼斯面临的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意识形态层面,突尼斯国内的恐怖主义主要属于圣战萨拉菲主义。突尼斯国内萨拉菲主义者大致可分为虔敬派、政治参与派和“圣战”派。(3)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9, No. 4, 2012, p. 144.突尼斯革命后,“圣战”思想(4)法哈德·霍斯罗卡瓦尔(Farhad Khosrokhavar)认为,自2011年以来,“圣战”思想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11年底前,和平示威是主流,“圣战”思潮处于低潮,示威民众的诉求集中在获得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等世俗领域,“圣战”分子的激进做法在民众当中缺乏吸引力。2011年底至2013年前,利用阿拉伯民主转型时期国家的安全真空和社会危机,“圣战”思潮再度兴起。2013年至2014年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伊斯兰主义者的激进活动趋向暴力,与政府的对抗日趋激烈。2014年6月底“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后,“圣战”组织的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该组织以扩张领土和建立“哈里发国”为宗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地区进行“圣战”。参见Farhad Khosrokhavar, “Jihadism in the Aftermath of Arab Revolutions: An Outcome of the ‘Failed State’?,” in Emel Aksali, ed.,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Palgrave, 2016, p. 86。摆脱了政治高压的束缚,泛滥成灾,导致萨拉菲主义者重新分化组合,温和派和激进派分野明显,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第一,温和派萨拉菲主义者表现不佳,难以发挥政治参与作用。突尼斯革命后,老一辈萨拉菲主义者组建政党,参与民主政治。穆罕默德·赫乌贾(Mohammed Khouja)创建了“改革阵线”(Jabhatal-Islah);萨义德·贾兹里(Sayd al-Jaziri)创建了“仁慈党”(Al-Rahma);穆勒迪·穆贾希德(Mouldi Mujahid)创建了“真实党”(Al-Asala)。在政治领域,上述萨拉菲政党的领导人都是萨拉菲主义者,其政治纲领都坚持建立“伊斯兰国家”,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取消利息,恢复“天课”制度;在文化方面,他们主张重启“创制之门”,引进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在社会领域,萨拉菲主义者谴责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行为,主张恢复一夫多妻制,取消男女平等的规定。(5)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p. 145.这部分萨拉菲主义者选择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治进程,是温和的萨拉菲派。其中,“改革阵线”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萨拉菲政党,但在2014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席位,之后影响力渐趋弱化。因此,从总体态势看,温和派萨拉菲主义已无力吸引大量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民众。
第二,激进派萨拉菲主义者力量持续壮大,并不断制造暴恐袭击。激进派萨拉菲主义者的代表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al-Sharia)组织,该组织是2011年4月由阿布·阿亚德·突尼西(Abu Ayyad al-Tunisi)(6)突尼西原名为赛义夫拉·欧麦尔·本·侯赛因(Sayf Allah Umar bin Hussein)。此人曾经参加过阿富汗抗苏战争,2003年从土耳其被引渡回国,2011年获释。创建。该组织鼓吹萨拉菲主义观点:号召支持者集体前往突尼斯圣城凯鲁万朝觐;占领清真寺,反对亲政府伊玛目;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伊拉克监狱的“圣战”分子等。“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反对世俗政府的各项政策,认为世俗政权背叛了伊斯兰教。(7)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p. 144.2013年2月和7月,“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刺杀了两位主张世俗化的左翼议员。此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加大了发动暴力恐怖袭击的频率和力度,对突尼斯国内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该组织尤其擅长利用互联网招募穆斯林青年和宣传极端教义,导致大量失业青年受其蛊惑参与境内外的“圣战”。据估计,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突尼斯籍“圣战”分子数量一度高达6,000人,另有约12,000人因被突尼斯安全部门拦截而未获准出境。(8)Stefano M. Torelli, “Tunisia’s Counterterror Efforts Hampered by Weak Institutions,” Terrorism Monitor, Vol. 15, No. 4, February 2017, p. 6.2014年底,“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内部发生分裂,部分成员开始隐藏身份,在本·古尔丹口岸从事走私活动,而另有部分激进分子则加入“奥克巴·本·纳法旅”(Okba Ibn Nafaa Brigade)组织(9)“奥克巴·本·纳法旅”由回国的“圣战者”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指导下于2012年12月建立。,继续对突尼斯政府发动“圣战”,袭击平民和政府目标,(10)Anouar Boukhrs, “The Geographic Trajectory of Conflict and Militancy in Tuni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20, 2017, p. 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313_Boukhars_Tunisia_Final.pdf, 登录时间:2019年9月18日。先后制造了巴尔杜博物馆恐袭案(2015年3月)、苏塞海滩枪击案(2015年6月)以及总统卫队遇袭案(2015年11月)等。(11)Djallil Lounnas, “The Tunisian Jihad: Between al-Qaeda and ISI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2019, p. 104.活跃在突尼斯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是“哈里发战士”,该组织在2018年共发动12次恐怖袭击,共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12)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 “Africa:Tunisia(January 8,2019),” https://www.acleddata.com/curated-data-files/, 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
第三,恐怖组织建立据点,招募人员。2011年以来,恐怖组织在突尼斯西部、中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地区先后建立了训练基地,并以此为据点,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威胁突尼斯国家安全。
在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西部边境地区,主要受到“基地”组织的威胁。在突尼斯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始终是困扰政府的主要难题。本·阿里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国家的资源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尤其是突尼斯城。东部地区以56%的人口创造了92%的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达85%,西部地区拥有突尼斯30%的人口以及整个国家55%的贫困人口。(13)Anouar Boukhrs, “The Geographic Trajectory of Conflict and Militancy in Tunisia,” p. 13.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治安混乱,安全问题较为突出,对中央政府也颇有微词。同时,由阿尔及利亚的“圣战士组织”演化而来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这一地区影响较大。突尼斯政权更迭后,此前长期盘踞在阿尔及利亚山区的恐怖分子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阿突边境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突尼斯“圣战”分子的接纳和培训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进一步威胁突尼斯边境安全。
在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失业青年成为恐怖组织招募的新目标,恐怖主义威胁也逐渐上升。中南部地区素来就有反抗中央政府的传统,如1980年加夫萨(Gafsa)暴动,1984年加夫萨事件,2008年加夫萨盆地抗议和2010年西迪·布吉德省的自焚事件。2016年,突尼斯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激发了新一轮抗议,加之工作、医疗和社会保障缺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普遍缺乏公平,该地区失业青年成为极端组织招募成员的重要来源之一。(14)Georges Fahmi,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alafism in Egypt and Tuni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15, 201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 ̄tions/?fa=61871, 登录时间:2019年3月4日。而在东南部地区,除了地区自然条件差、部落政治文化浓重等因素外,利比亚内战爆发后突尼斯大量劳工和部分利比亚难民进入突尼斯境内,打破了原先存在的边境秩序,出现毒品和枪支泛滥、大批“圣战”分子回流等情况,为恐怖组织的跨国联动提供了沃土,对突尼斯边境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凸显。(15)Djallil Lounnas, “The Tunisian Jihad: Between al-Qaeda and ISIS,” p. 107.
(二) 多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同样面临困难和挑战,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首先,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尚未实现政治稳定。突尼斯在发生变革之后,国内出现“权威真空”(16)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第15页。,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激烈,政局变动频繁。2011年至2016年,突尼斯先后更换七任总理,历届政府维持的时间都很短,很少超过两年。这表明突尼斯的政治体系尚不健全,现有政治制度无法应对复杂的局势,消耗了原本可以用于建设的大量精力和资源。突尼斯虽然重新制定了宪法,但宪政的推行并不顺利。
其次,突尼斯经济发展缓慢,复苏艰难。转型时期的突尼斯经济已经完全丧失了之前5%左右的高速增长。2011年以来,突尼斯经济增长率最高时也只有2.4%,2015年以来更是在2%的低位徘徊。(17)“Tunisia Overview,”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nisia/overview,登录时间:2018年6月20日。受安全局势的影响,作为突尼斯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变得萧条,来突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大幅减少。这不仅导致突尼斯旅游收入锐减,而且使许多人失去了生计。另外,随着外资撤离,国内投资不景气,突尼斯重振经济的努力迟迟不能收到实效,通胀率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接连探底。如果不是外部援助的补充,突尼斯经济或许已经崩溃。2018年4月,突尼斯政府虽然通过新的《启动法案》(Start-upAct),推进经济创新政策,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颓势。2018年突尼斯GDP在缓慢中增长,第一至四季度增长率分别为0.7%、1.0%、0.6%和0.5%,通胀率则为7.1%,外汇储备下降到了2005年的水平。(18)“Tunisia,” Trading Economics,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tunisia/gdp-growth, 登录时间:2018年3月23日。突尼斯经济持续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补贴过高,税收不足,并长期陷入以税收资金偿还债务的恶性循环。
最后,社会安全不容乐观。在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民众虽然获得了更多自由,但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要求改善社会处境的各类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近几年来,突尼斯政府强力推行激进经济和社会改革,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政治反对派的抨击,进而加剧了社会动荡。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突尼斯上规模的社会抗议和示威游行高达500余起,涉及出租车司机、记者、反对党、突尼斯总工会、律师、少数族群、失业毕业生和警察等。(19)“Africa 1997-Present(February 28, 2019),”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https://www.acleddata.com/data/, 登录时间:2019年3月5日。
突尼斯“革命”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旧有秩序遭到了严重冲击,原先的安全机构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但重组安全力量和安全制度建设等进展异常缓慢,导致安全困境突出。
首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互动。突尼斯警察和军队既要解决国内各类治安问题,又要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现实中难以兼顾。在突尼斯边境地区,检查站和海关接连遭受攻击,其中既有传统的反政府武装袭击,也有恐怖主义袭击,很多时候恐怖分子与其他反政府势力之间界限模糊。例如,突尼斯西部山区一直对中央政府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抱有成见,在布尔吉巴时期和本·阿里时期,突尼斯政府都试图通过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来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但事与愿违,导致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这进一步给了恐怖分子和反政府势力以可乘之机。在突尼斯与利比亚交界地区,部落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反政府势力相互勾结、互相借重,不仅从事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而且发动恐怖袭击和从事其他反政府活动,使得突尼斯警察和安全部队防不胜防。
其次,国内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合流。从恐怖主义的发展特征来看,国际恐怖组织与突尼斯境内恐怖组织已形成合流之势,这在突尼斯历史上比较罕见。更为严重的是,突尼斯情报机构实力有限,难以对大量突尼斯籍“圣战”分子的境外活动实施监控,使得突尼斯面临恐怖分子“回流”的巨大压力。(20)Ralph Davis, “Jihadist Violence in Tunisia: The Urgent Need for a National Strategy,” Crisis Group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riefing, No. 50, Tunis/Brussels, June 22, 2016, p. 15. https://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tunisia/b050-jihadist-violence-in-tunisia-the-urgent-need-for-a-national-strategy.aspx,登录时间:2018年6月22日。2015年,巴尔杜博物馆恐袭事件、苏塞海滩袭击案等发生在突尼斯核心地带的恐怖袭击事件均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21)尽管突尼斯官方认为这两次恐袭事件是国内极端组织所为,但“伊斯兰国”组织公开宣称对这两次事件负责。
最后,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成为困扰突尼斯政府的突出问题。突尼斯革命后,国内反对派力量不仅质疑突国内长期形成的世俗政治传统,而且对新政府的治理模式表示强烈不满。在制宪过程中,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爆发了数轮冲突。双方最终在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人权联盟、突尼斯律师协会和突尼斯雇主协会等市民社会组织的调解下达成和解,但萨拉菲派组织始终不支持新宪法,认为执掌过渡政府的复兴运动党背叛了伊斯兰教。(22)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p. 141.2017年9月,突尼斯议会通过的《行政和解法》再一次撕裂了民意,即使在突尼斯议会内部,议员们对曾经犯过腐败和镇压罪行的本·阿里旧部予以豁免也感到非常失望。非政府组织的反对则更加强烈,例如,突尼斯人权组织接连发声,谴责该议案。普通民众则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在突尼斯,关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难题一再出现,不仅政治人物难以展现其治理能力,法律文件的颁布也数次延宕。
二、 突尼斯安全困境的成因
突尼斯安全困境形成原因极其复杂,既包括国内结构性原因,也有国际政治的间接影响,该国威权主义政治传统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 结构性原因
突尼斯是夹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之间的一个小国,国土面积狭小,人力资源有限。突尼斯的军事支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不到3%。(23)Anthony H. Cordesman, A Tragedy of Arm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the Maghreb,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2002, p. 252.从根本上而言,突尼斯长期以来实施的“安全外包”(24)“安全外包”主要指依赖西方强国以维持某种特殊关系、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参见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第21页。政策导致其自身安全应对能力相对有限,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维持国家稳定和应对外部威胁。众所周知,突尼斯自独立以来通过维持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来换取这些国家对本国安全的保障和武器装备的供应,并提供军事和安全培训。但是,突尼斯过分依赖外部力量使得其在单独应对本国安全问题时力不从心,如2012年9月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遇袭时,突尼斯普通军警的训练不足彰显无遗。此后,恐怖袭击在突尼斯接连发生,再次证实了突尼斯应对恐怖主义袭击不力的说法。可以说,短期内突尼斯很难迅速提升安全部队的有效能力,这是导致现有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
人口结构问题是突尼斯安全问题爆发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在突尼斯,青年群体的人口占比达40%,2018年曾有高达35%的突尼斯青年处于失业状态,(25)王琳:《突尼斯骚乱背后:年轻人失业率超35%》,第一财经网,2018年1月15日,https://www.yicai.com/news/5391923.html,登录时间:2019年9月8日。失业青年成为恐怖组织潜在的人员来源。突尼斯青年虽然没有阿富汗战争的记忆,但对“9·11”事件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有较多认识。突尼斯变革期间,突尼斯青年展现出与政府斗争和周旋的能力,但直到过渡政府建立后,他们的自身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挫折感仍十分强烈。据统计,在突尼斯,从事恐怖袭击活动的群体大都来自边缘地区和家庭,其中90%以上受过中等教育。(26)“Three-quarters of Terrorists Returning from Conflict Zones Are Single, 90% of Them Have Medium Level of Education (Study),” Agence Tunis Afrique Pres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tap.info.tn/en/Portal-Politics/10168263-three-quarters-of,登录时间:2018年9月22日。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突尼斯有68%的城市青年和91%的农村青年对现行政治制度表示不满。(27)Anouar Boukhrs, “The Geographic Trajectory of Conflict and Militancy in Tunisia,” p. 6.显然,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突尼斯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当政府难以满足青年的基本诉求时,后者便可能选择暴力手段表达不满。2019年10月突尼斯大选期间,平民政治家凯斯·赛义德(Keas Saed)出人意料地击败其他有名望的政治家,当选突尼斯总统。可以说,突尼斯青年不满现状,最终以选票“惩罚了体制内的政客”(28)“The Bird Will Not Return to the Cage: An Analysis of Tunisian 2019 El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October 25, 2019, https://www.ictj.org/news/‘-bird-will-not-return-cage’-analysis-tunisia’s-2019-elections,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30日。。
(二) 周边国家动荡
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深刻改变了突尼斯的外部安全环境,对突尼斯本国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利比亚战乱的长期化给恐怖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训练场所以及武器来源。利比亚“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突尼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之间联系密切,前者为后者提供训练营和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叙利亚为突尼斯籍“圣战”分子提供了从事暴恐活动的天然实战场地。马里内战进一步扩大了利比亚战争的影响,打破了萨赫勒地区的旧有秩序。2017年以来,马里北部仍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Coordination of Azawad Movements)的占领下处于自治状态,(29)“Mali: At Least 30 Dead in Clashes Between Tuareg Groups in Kidal,” The North Africa Journal, June 14, 2017, http://north-africa.com/mali-at-least-30-dead-in-clashes-between-tuareg-groups-in-kidal/, 登录时间:2019年6月22日。虽然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冲突并没有完全平息,其溢出效应仍对周边地区造成威胁。
(三) 威权统治时期的遗产
本·阿里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坚决镇压,虽然打击了其极端行动,但由于未能甄别恐怖分子与一般犯罪人员,将后者与前者一起长时间关押,“制造”了大量的“圣战”分子。本·阿里时期,突尼斯被捕入狱的伊斯兰主义者数量据称有3万人左右。(30)Anne Wolf, “An Islamist ‘Renaissa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ost-Revolutionary Tunisia,”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4, 2013, p. 505.突尼斯安全部门对伊斯兰主义者的粗暴对待,导致许多原本对极端思想不感兴趣的犯人对世俗政权产生了敌对心理。对于可疑的伊斯兰主义者,或者伊斯兰主义者的家属,突尼斯政府也严加防范,采取特殊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犯人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事实上处在“社会死亡”(Social Death)的状态。(31)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p. 143.因为现实中伊斯兰主义者很难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受限,发展前景黯淡。突尼斯政府在处理伊斯兰主义者与一般犯人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是威权政权时期经常采用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潜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基数。时至今日,突尼斯的“转型正义”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本·阿里政权时期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补偿,新的“革命烈士”也没有得到抚恤,这些利益受损者大量存在,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转化为极端分子,进而将对突尼斯的安全治理造成更大困扰。
三、 突尼斯的安全治理及其成效
突尼斯作为一个小国,时刻面临各种安全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突尼斯维持了国内相对稳定,但以“安全外包”为主的安全治理模式始终无法解决根源性的安全问题。在新的安全形势下,突尼斯政府被迫对其安全治理模式进行了调整。
(一) 变革前的安全治理
突尼斯曾经是北非地区最稳定的国家。本·阿里时期,突尼斯安全治理的逻辑是“宪政民主联盟主导的多元主义、受控制的选举和选择性压制”(32)John P. Entelis, “The Democratic Imperative vs. the Authoritarian Impulse: The Maghrib State Between Transition and Terroris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9, No. 4, Autumn 2005, p. 540.。突尼斯政府维持一党制统治,采用半开放的方式应对国内外要求其推进民主化的压力,将防范潜在的伊斯兰革命和恐怖主义袭击作为安全治理的首要目标,对伊斯兰主义力量采取高压政策。具体而言,突尼斯在安全治理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第一,以经济发展换取民众支持。新宪政党(1989年后改称宪政民主联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是突尼斯政权获得民众长期支持的重要基础。正如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所指出的,突尼斯维持政权稳定的关键手段是维持经济的顺利发展。(33)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Stability and Reform in the Modern Maghreb,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62.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与多数中东国家相比,突尼斯的经济发展优异,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5%以上,出口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再加上比较优厚的投资条件和人力资源优势,每年有将近10亿第纳尔的投资涌入突尼斯。(34)Kenneth Perkins,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2.突尼斯在推行私有化改革政策后,外债有所下降,其GDP占比从56%下降到51%,因此在2000年被世界银行评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追求社会成就方面取得最好成绩的中东北非国家”(35)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Stability and Reform in the Modern Maghreb, p. 85.。2002年至2005年,突尼斯人均GDP增长40%,人均收入水平是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贫困率降到了4%,人均寿命提高到73岁,妇女占劳动力的1/3,95%的居民使用水电设施,初级教育的入学率接近100%,突尼斯跨入了世界银行评定的较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36)Ibid.
第二,突尼斯努力稳定国内局势,通过提振旅游业拉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突尼斯对国内以优素福分子(37)优素福分子是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政治对手,新宪政党前总书记萨拉赫·本·优素福(Salah Ben Yusuf, 1910~1961)的支持者。参见Kenneth J. Perkin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nisia, Lanham: Md.& London, 1997, p. 35。、自由派、伊斯兰复兴运动等为代表的挑战威权政治的反对派予以坚决压制,使政治反对派始终无法形成气候。这一政策使得本·阿里政权维持了多年社会稳定,为旅游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提升了突尼斯的国家形象。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来看,突尼斯旅游业共吸引游客680万人,创收达30.77亿突尼斯第纳尔,占世界旅游业份额的0.8%,(38)Mounir Belloum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Receipts,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uni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Vol. 12, No. 5, p. 552.旅游业也因此成为突尼斯第一大外汇来源,从业人口高达35万,解决了12%的劳动力就业问题。(39)《突尼斯旅游业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9年2月18日,http://tn.mofcom.gov.cn/article/ddgk/zwjingji/201902/20190202835076.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5日。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国内收入,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有能力为营造稳定的旅游环境在安全方面加大投入。
第三,以“安全外包”策略应对外部威胁。“安全外包”策略的制定出于突尼斯避免其现代化建设受军费支出掣肘的考量。与邻国相比,突尼斯是地区小国。从邻国的人口规模来看,阿尔及利亚人口达4,220万,军队人数达20.45万人;(40)《阿尔及利亚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18/1206x0_677320/,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0日。利比亚人口规模达647万,军队人数约76,000人(2001年数据)。(41)《利比亚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018/1206x0_678020/,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0日;Anthony H. Cordesman, A Tragedy of Arm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the Maghreb, London: Preager, 2002, p. 220。自布尔吉巴时期以来,突尼斯主要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安全装备、军队训练和安全保障。为此,突尼斯一直与西方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其中,突尼斯与法国保持特殊关系,并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在安全领域优先选择法国机构和人员对突尼斯安全力量进行培训。法国因此成为突尼斯安全领域长期依赖的外部保障。此外,突尼斯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曾在突尼斯与法国交恶时免费为突尼斯提供过武器和安全援助。
第四,强有力的安全力量是维持威权统治的重要支柱。2002年恐怖袭击发生后,突尼斯政府加强了边境管控,注重打击国内和边境地区的极端组织。突尼斯政府主要依靠警察、国民卫队和军队来维持国内治安。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一定作用。然而,布尔吉巴和本·阿里对军队的信任度都不高,尤其是本·阿里更加倚重警察部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突尼斯政府通过警察系统直接压制群众暴动和恐怖袭击等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击政治伊斯兰等不同政治力量,以维护政权稳定;二是突尼斯政府通过情报部门对反对派形成威慑。20世纪90年代,政治伊斯兰力量在蛰伏期间,安全部门长期对其代表人物及其亲属进行监控,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世俗反对派也迫于压力选择与威权政权开展合作。
(二) 变革后的安全治理
在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国内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这迫使政府改变了安全治理理念和模式。一方面,复兴运动的上台改变了伊斯兰主义者在国内的地位,使得安全治理的对象从笼统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进一步缩小至伊斯兰极端势力;另一方面,民主转型扩大了国内政治动员,被赋予更多政治自由的突尼斯民众逐渐倾向于公开表达政见,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有所增加,导致安全治理面临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前述安全治理机制虽仍在沿用,但效力已大不如前,在民主转型时期经常左支右绌。总体来看,革命后的安全治理手段主要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通过频繁实行紧急状态来扩大安全治理的适用范围。根据突尼斯宪法第80条规定,在国家制度或国家安全、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以及国内秩序难以维持时,突尼斯共和国总统与行政机构首脑、议长进行沟通后,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必要的非常规手段。(42)John P. Entelis, “The Democratic Imperative vs. the Authoritarian Impulse: The Maghrib State Between Transition and Terrorism,” p. 540.2011年3月,突尼斯首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先后持续三年之久,直至2014年3月才解除紧急状态。(43)“Tunisia Lifts State of Emergency, Three Years After Revolt,” Haberler News, June 3, 2014, https://en.haberler.com/tunisia-lifts-state-of-emergency-three-years-after-390315/, 登录时间:2018年6月22日。2015年苏塞恐怖袭击事件后,突尼斯再次宣布实行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44)Harriet Alexander, “Tunisia Declares a State of Emergency,” The Telegraph, July 4, 201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fricaandindianocean/tunisia/11718196/Tunisia-dec ̄lares-a-state-of-emergency.html, 登录时间:2018年6月22日。2015年11月25日,突尼斯总统卫队遇袭后,埃塞卜西总统又宣布突尼斯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此后,突尼斯的紧急状态几经延长,一直持续至2018年3月。2018年3月12日,迫于形势的压力,埃塞卜西总统再次宣布延长紧急状态7个月。(45)“State of Emergency Extended by 7 Months from March 12,” Agence Tunis Afrique Press, March 6, 2018, https://www.tap.info.tn/en/Portal-Top-News-EN/9931455-state-of-emergency, 登录时间:2018年6月22日;Querine Hanlon, “Dismantling the Security Apparatus: Challenges of Police Reform in Tunisia,” p. 193。在屡次实行紧急状态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行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但突尼斯民众的自由尤其是集会自由却受到了极大限制,从而引起了普通大众对紧急状态下安全治理的不满。
第二,通过改革安全机构来整合国内安全力量,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突尼斯安全力量主要包括警察和军队。警察分为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城市安全力量以制服警察为主,农村安全主要由制服警察中的国民卫队负责,偏远山地的安全任务基本上由便衣警察执行。此外,突尼斯还设立了法警、特勤人员和其他治安力量等特殊警种。在变革之前,突尼斯有着“警察国家”的名号,号称拥有20万名警察,而政权过渡时期突尼斯包括行政人员和后勤支援力量警察在内的警察总数缩水至11万人左右,但突尼斯总统卫队却从原来的400人扩充至2,300人。突尼斯军队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目前三军总人数已从革命前约27,000人增至约4万人(46)《突尼斯国家概况(2019年12月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98/1206x0_678600/,登录时间:2019年12月5日。。此外,2011年12月,突尼斯新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改革安全部门的计划,旨在提升警察形象、改变警察行为方式、提高安全机构透明度、增强情报收集能力和提升对视频监控和电子监控等技术的运用等。
(三) 突尼斯安全治理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安全部门的一系列改革,突尼斯国家安全治理的能力得到了一定提升,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队角色发生变化。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军队更加注重形象塑造,其角色开始从“镇压者”向“服务者”转变,从“政权保卫者”向“公共秩序维持者”变革。具体而言,军队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通过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来确保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实现,在执法过程中尊重法治和民主价值成为突尼斯安全机构的新指针。(47)Malik Boumediene, “Armée, Police et Justice dans la Tunisie Contemporaine,” Pouvoirs, No. 156, 2016, p. 111.
第二,安全机构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在本·阿里时期,突尼斯安全机构人员冗杂、结构复杂,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指挥权掌握在总统本人手中。为建立效忠于自己的安全力量,本·阿里通过各种手段使不同的安全部门之间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各安全部门的官员承担相同的任务,但往往互不隶属。突尼斯新政府成立后对内政部进行了重组,将安全力量统一置于内政部的指挥之下,警察部门和军队构成了突尼斯安全部门对内和对外的安全应对机构,总统只掌握有限的警察管控权。
第三,警察内部变革效果初步彰显。变革之后,突尼斯安全部门进行了一次内部大调整。一方面,大量安全机构人员离职使得突尼斯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征召新人加入安全机构。虽然这批新人训练不足,但突尼斯政府在培训过程中加入了保障人权等执法理念,更加符合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对警察的资质要求。另一方面,突尼斯安全力量也开始注重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各方面待遇保障。突尼斯安全部队成员成立了工会,要求提高安全部队人员的各项待遇。由于警察职业的高风险,突尼斯政府增加了对执勤警察的补贴力度。此外,突尼斯政府对安全部门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对安全系统和海关系统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进行了大规模整顿。自2016年以来,突尼斯对本·古尔丹口岸海关官员的整顿最为典型。(48)本·古尔丹口岸位于突尼斯和利比亚边界处,是连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重要通道。长期以来,该口岸存在大量的非正式贸易,因而形成了国家管辖治理之外的灰色地带,滋生了腐败现象。Sarah Yerkes, “Marwan Muasher, Tunisia’s Corruption Contagion: A Transition at Risk,” Carna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5,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0/25/tunisia-s-corruption-con ̄ta ̄gion-transition-at-risk-pub-73522, 登录时间:2019年6月26日。
在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安全治理实践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内政部改革缓慢,这为恐怖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空间。近年来,突尼斯恐怖袭击频发,安全部门改革被迫放慢步伐,以集中精力打击恐怖分子,但突尼斯监狱继续充当着恐怖分子“孵化器”的角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艾米诺(Emino)(49)此人原名毛鲁瓦尼·杜伊里(Maurouane Douiri)。。此人在监狱里服刑18个月后,从一名世俗的说唱歌手转变成为“圣战”分子。2015年3月,他在网络上公开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而此前他是一名在社交网站上十分活跃、经常上传自拍照的自恋歌手。(50)Tom Wyke, “Tunisian Rapper Who Regularly Posted Photographs of Hhimself with Scantily Dressed Women Becomes the Latest Failed Hip-hop Wannabe to Join the Ranks of ISIS,” Daily Mail, December 17, 2018,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000855/Tunisian-rapper-Emino-latest-failed-hip-hop-wannabe-join-ISIS.html, 登录时间:2018年6月26日。
其次,军队与警察分工不明,相互间竞争激烈。突尼斯剧变改变了该国军队的地位,但却没有改变军队的作用。在突尼斯的政治体制中,军队的作用并不突出,但是突尼斯剧变改变了军队的地位。奥马尔将军拒绝执行本·阿里镇压群众的指令,并迫使后者离开突尼斯,这在该国现代史上尚属首次。此外,军队在民主转型时期维护了国内社会秩序,及时退回到兵营,此举被认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军队在突尼斯民众心中的威望。但在民主转型时期,军队的作用虽然日益凸显,职责界定却不甚清楚。如前所述,恐怖分子主要盘踞在边境地区,边防部队和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边境安全。其中,边防军的任务主要是应对外部入侵,警察的任务主要是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反恐则属于警察分内的特别任务,但在实际反恐行动中,突尼斯军队承担了重要任务。因此,突尼斯警察虽然被寄予完成反恐任务的厚望,但其不论在整合资源还是装备方面,都面临困难,难以迅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最后,突尼斯社会各界对政治伊斯兰的威胁估计不足,这导致突尼斯成为国际恐怖分子重要的来源国。复兴运动上台后,因对安全形势估计不足,在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一方面,复兴运动以受害者姿态自居,同情宗教运动,对宗教极端化问题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导致其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短暂纵容,使得后者影响力迅速上升,即使在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遭到冲击后,复兴运动政府也没有进行正面回应。另一方面,复兴运动政府缺乏经验,在无法沿袭旧政权应对措施的背景下对国内安全问题应对失当,反而受到了安全部门的掣肘。突尼斯军队回到军营,虽然避免了军人干政的威胁,但对反恐本身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突尼斯安全力量不但不配合复兴运动,反而进一步消极对抗。之后,呼声党执政后,尽管加强了安全治理的力度,但治理思路和手段缺乏新意,以频繁实行紧急状态来应对安全威胁,这既不利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也不利于民主转型。
四、 安全治理对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影响
安全治理的成效关系到民主转型的成败,这既是突尼斯新秩序建立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兴业的基本保障。突尼斯已在民主转型方面树立了较好的榜样,是阿拉伯变局后在民主转型方面进展较为理想的国家。但是,安全治理一旦难以解决恢复稳定的重要任务,国内民主转型前景必将蒙上阴影。
(一) 安全治理是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
2011年以来,国内乱局使得解决安全问题、稳定局势成为民主转型时期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突尼斯的政治活动中,安全问题显然成为主要议题。过渡时期突尼斯的几任总理都是强硬派,如阿里·拉哈耶德(Ali Larayedh)和哈比卜·埃西德(Habib Essid)总理都有主管内政部的经历。2016年3月,埃塞卜西就任总统后成立了直接对其负责的“国家反恐和反暴力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20名部长,涉及青年人、文化、安全、宗教、人权等多方面事务。(51)Ralph Davis, “Jihadist Violence in Tunisia: The Urgent Need for a National Strategy,” p. 11.但是,突尼斯政府加强安全治理与民众的民主权利产生了冲突。突尼斯民众争取的自由民主权利在屡次紧急状态中已受到严格限制,由此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14年市政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68.3%,2018年大幅降至34.4%。(52)Lamine Ghanmi, “Tunisia’s Independents, Islamists Come Ahead in Low Turnout Vote,” The Arab Weekly, May 8, 2018, https://thearabweekly.com/tunisias-independents-islamists-come-ahead-low-turnout-vote,登录时间:2016年6月26日。不难看出,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而言,民意如果不能通过明确的政治活动来表达政治诉求,便只能转向通过这种“无声的反抗”来表达。
(二) 安全治理是影响民主转型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民主转型时期,民众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扩大,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使得安全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加强,推动了制度革新。因此,罗伯特·达尔认为,民选政府对军队和安全机构的绝对控制权是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53)[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126页。突尼斯革命后,军队回归到军营,民选政府保持对安全机构的领导,安全部门成为民主转型时期秩序的重要保障,这无疑是突尼斯民主转型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突尼斯新政府的合法性虽然有所提升,但在解决危机方面却难有作为。一方面,极低的投票率难以完全反映民意;另一方面,重组后政府相对软弱。安全困境加剧了突尼斯民主转型的风险。突尼斯安全治理的实践直接影响该国的民主转型,失业和恐怖主义威胁仍然考验着人们对民主政府的信心。另外,突尼斯安全力量粗暴对待关押犯的做法仍大量存在,这影响了安全部门的正面形象。因此,很难说民主力量已经控制了安全部门,使其为人民服务。
一般认为,民主转型包括政治转型和民主巩固两个阶段。突尼斯转型后的全国大选将赋予新政府合法性。(54)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2002, p. 15.从这个意义上看,突尼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步入民主巩固阶段。民主巩固的标志是政治制度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体系的变革,(55)陈尧:《新权威主义的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但这一切都将建立在安全治理成功的基础上。安全治理的失败不仅影响政治制度的巩固,而且影响政治文化的转向。市民社会文化难以建立,威权政治复辟,这将使民主转型功亏一篑。突尼斯转型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成就固然可喜,但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转型极有可能发生逆转。历史经验表明,面包问题才是根本,只有解决了就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突尼斯的政治发展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五、 结语
在民主转型时期,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的叠加,突尼斯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安全困境突出。突尼斯的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威权体制时期的经验,创新性不足,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环境。
从历史经验来看,突尼斯如果能实现稳定和发展之间的良好互动,就能实现安全治理。突尼斯只有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凝聚民心,打消民众对新政权的疑虑,阻止突尼斯青年被恐怖组织招募,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威胁。只有这样,突尼斯才能再次实现繁荣,民主巩固才能真正实现。2014年1月,突尼斯新宪法颁布后,新的宪政民主制度已基本确立。这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半总统制的确立,在经济发展上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推行,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并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以圣战萨拉菲主义者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威胁仍持续存在。总体而言,突尼斯的民主巩固严重依赖安全治理,如果国内安全得不到保障,突尼斯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将无法维系;如果安全治理难以实现,突尼斯温和、包容的政治文化将发生根本性逆转,强人政治很可能再次出现。因此,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这种转型或将迁延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