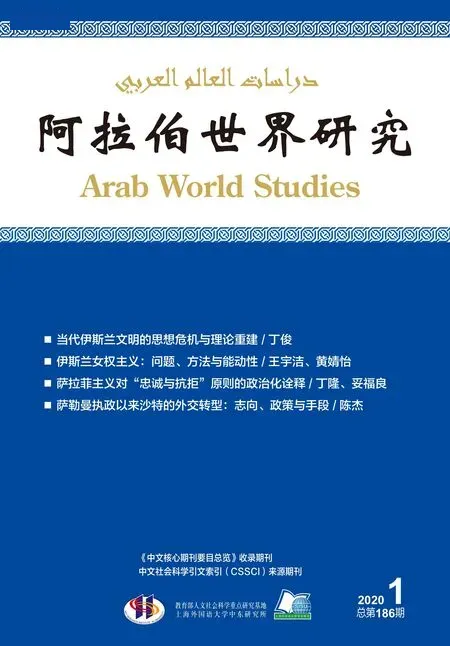南苏丹分离运动的逻辑分析:1972~ 2011*
周光俊
2011年1月9日,南苏丹举行独立公投,98.83%的选民支持独立。(1)《南苏丹国家概况(2019年8月)》,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nsd_678308/nsdgg_678310/, 登录时间:2019年9月20日。同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南苏丹共和国,并加入联合国和非盟。南苏丹的独立事实上改变了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和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一届首脑会议确立的关于“边界不可更改原则”,该原则明确指出,非洲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证、边界不可改变。(2)[埃及]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仓友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南苏丹作为一个新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出现,是非洲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被视为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或者是未来的先例”(3)Anthony J. Christopher, “Secession and South Sudan: An African Precedent for the Future?,”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93, No. 2, 2011, pp. 125-132.。
南苏丹的独立源于南苏丹分离运动,后者导致的第二次苏丹内战是苏丹历史上最严重的内战之一,对苏丹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南苏丹为何能够实现独立?独立后的南苏丹内部的族群关系、南北苏丹关系如何影响南苏丹的政治走向?本文以第二次苏丹内战作为分析对象,考察南苏丹问题的成因以及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的原因,探究南苏丹分离运动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判未来南苏丹的族群关系与政局走向。
一、 学界对南苏丹问题的研究与认知
现代苏丹的地理疆域与政治安排是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这造就了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苏丹。“苏丹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崛起,是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它不是通过自身内在动力和其人民的素质来实现的,不同民族是受大国殖民后被迫加入苏丹民族国家的”(4)Girma Kebbede, “Sudan: The North-South Conflic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ributions in Black Studies, Vol. 15, No.3, 1997, pp. 15-31.,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人为结果”(artificial products)(5)Tina Kempin Reuter, “Ethnic Conflict,” in John T. Ishiyama and Marijke Breuning, eds., 21st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A Reference Handboo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1, pp. 141-149.。作为地理概念的苏丹是由英国殖民统治者建构的,但这一概念却没有培育出苏丹人民的国家意识。相反,部落意识在苏丹仍然占据着上风。(6)刘辉:《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1956年,苏丹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独立后的苏丹陷入了南北双方仇恨与不满的历史困境中,北南双方以饱含贬义和敌意的“奴隶”和“掠奴者”称呼对方,(7)Oduho Joseph and William De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ern Sud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53.这一源自北方奴隶贸易时期(8)19世纪,埃及以奥斯曼帝国的名义征服苏丹北部,并在当地建立了土埃政权。该政权在开展贸易活动的过程中以奴隶去支付相关费用,并将奴隶贩卖至埃及等中东国家,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的称呼将历史仇恨传承下来。此外,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始终实行限制南方发展的政策,南方也因此未能作为一个整体同北方进行斗争,力量的分散导致南方的抗争举步维艰。在易卜拉欣·阿卜德(Ibrahim Abboud)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北方完全占据了国家教育资源,南方的诉求基本遭到忽视(见下表)。
资料来源: Joseph Oduho and William Deng,TheProblemofSouthernSud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6。
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Gaafar Nimeiry)通过政变上台。在南方问题上,尼迈里在推行泛阿拉伯主义的同时,承认南苏丹问题的存在,并与南苏丹开展谈判。1972年,双方经过一系列谈判后达成《亚的斯亚贝巴协议》(AddisAbabaAgreement),南苏丹历史上首次获得自治地位。该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17年的第一次苏丹内战,标志着以北苏丹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和以南苏丹为代表的非洲文明之间关系的缓和。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南北双方的和解,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可能。(9)Francis Deng, War of Visions: Conflict of Identities in the Suda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 362.然而,南北双方因自治地位、石油资源、文化冲突等问题产生的矛盾持续激化。在此背景下,南北苏丹从协议签署之日起,便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再次爆发冲突的困境,而新一轮内战彻底改变了苏丹的政治格局和国家走向。
第二次苏丹内战是整个非洲大陆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之一,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涉及程度之深是非洲国家内战中极为罕见的。据统计,第二次苏丹内战共造成200万人丧生,400万人流离失所,57万人沦为难民,大量道路、桥梁、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被摧毁,苏丹的发展至少停滞了十年。(10)王猛:《苏丹民族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解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74页。
关于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国家建构、历史遗产、族群文化冲突、经济利益冲突等视角予以阐释。
就国家建构视角而言,苏丹国家建构的背景是南部政治边缘化、经济遭忽视和北部伊斯兰文化主导。(11)Cleophas Lado,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Oil Industry in the Sudan Problem or Resource in Development,” Erdkunde, Vol. 56, No. 2, 2002, pp. 157-169.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认为,苏丹独立以来的各届政府将阿拉伯伊斯兰化视为国家建构的唯一范式,(12)Francis M. Deng, “Identity in Africa’s Internal Conflic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40, No. 1, 1996, pp. 46-65.北方试图将其宗教和语言传播到南方,而南方一直抵制这些努力,(13)Francis M. Deng, “Sudan-Civil War and Genocide: Disappearing Christians of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8, No. 1, 2001, pp. 13-21.这导致了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
就历史遗产视角而言,殖民时期遗留的历史怨恨成为南苏丹分离的重要背景,尤其是南方人怨恨北方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14)Francis M. Deng, “Sudan: A Nation in Turbulent Search of Itself,”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03, No. 1, 2006, pp. 155-162.历史上的黑奴贩卖、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第一次内战的恩怨最终导致南方选择分离。(15)杨勉:《南苏丹独立的背景与前景》,载《学术探索》2011年第10期,第30页。
就族群文化冲突视角而言,南北苏丹巨大的宗教、历史、族群、语言等差异,成为南苏丹分离的重要文化背景。安德斯·布雷德利德(Anders Breidlid)在解释南苏丹人民反抗伊斯兰政府的原因时指出,苏丹政府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初等教育体系未能充分考虑国家的多元文化和宗教背景,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教育则以世俗课程为主。(16)Anders Breidli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udan’s Civil War,” Prospects: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3, No. 1, 2013, pp. 35-47.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认为,南北苏丹族群与宗教的对抗以及英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酿成了南方的分离倾向。(17)Douglas H. Johnson, The Root Cause of Sudanese Civil Wa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6-40.
就经济利益冲突视角而言,罗杰·邓恩(Roger Dean)指出,宗教不宽容对苏丹内战爆发的影响很小,而地区和全球政治以及食物和水资源等基本问题才是内战爆发的主要因素。(18)Roger Dean, “Rethinking the Civil War in Sudan,” Civil Wars, Vol. 3, No. 1, 2000, pp. 71-91.杰弗里·海恩斯(Jeffrey Haynes)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内战是经济资源的竞争,宗教和族群等重要因素决定了各方可以获得的资源。(19)Jeffrey Hayne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Civil War in Africa: The Cases of Uganda and Sudan,” The Round Table, Vol. 96, No. 390, 2007, pp. 305-317.除此之外,大卫·希罗基(David S. Siroky)和约翰·卡夫(John Cuffe)从行动者的角度考察了南苏丹在自治期间领导层与地区议会经验的获得,与分离运动所需要的集体行动问题之间的关系。(20)David S. Siroky and John Cuffe, “Lost Autonomy,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8, No. 1, 2015, pp. 3-34.
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历史传承、行政区划、宗教冲突、族群对抗等单一角度进行的考察,各自有其合理性。然而,一场持续三十年的内战并非单一的过程,而是一种复杂过程。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涉及1981年内战后苏丹南北政治的发展,也将考察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后苏丹的政治制度、资源分配、宗教政策等。此外,内战中代表南方自治与独立利益的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作用,以及政治精英在分离运动的组织、动员上的作用,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 断裂型制度安排: 苏丹自治的消逝与资源不公平分配
离心型民主政体(centrifugal democracies)与向心型民主政体(centripetal democracies)是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等人提出的一种衡量政治制度特征的两分法,其考察的对象是政体的离心与向心程度。(21)Arend Lijphart,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d Politics, Vol. 25, No. 2, 1969, pp. 207-225.南苏丹分离问题不仅是政体问题,也涉及政体之外的政治权力分配、政治权利机会等问题。断裂型制度(22)关于断裂型制度与弥合型制度的划分,参见周光俊:《族群分离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基于过程论的分析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5期,第77页。表明,分离族群与中央政府(主体族群)之间存在分歧,权力获取、利益分享、权利机会三者在任一维度上的缺失,都可能导致中央政府的族群政策的失效。运用断裂型制度与弥合型制度的二分法考察苏丹政治制度安排中南北双方的政治地位、政治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后果等,有助于解释苏丹断裂型政治制度安排带来的苏丹南北冲突的原因。
《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签署结束了苏丹自独立以来的内战状态,赢得了十年的和平。对于北方而言,尼迈里在执政初期并不依靠伊斯兰主义力量,然而,苏丹民主统一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进入政权后,开始要求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这也是尼迈里逐步破坏协议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尼迈里逐步撕毁协议,使得协议所规定的南方的自治权逐渐被侵蚀,直至南方自治地位被取消,在此过程中,南方的石油资源也就自然地被北方所侵吞,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带来了南方的不满与敌视。南方权力获取方面的弱势地位与利益分享上的不公正状态最终形塑了苏丹的断裂型制度。
(一) 南方自治的消逝
1972年2月28日,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相关规定,南苏丹自治区宣告成立,这是南方历史上为自治权奋斗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根据协议,南方地区自治由人民地区议会(People’s Regional Assembly)和高级执行理事会(High Executive Council)组成,前者是地方代议机构,后者是具体执行和管理机构。其中,高级执行理事会的主席由人民地区议会选出,由总统任命。但南方自治政府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它不断遭到侵蚀,以致最后被废止。尼迈里有意借助南方自治政府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将之作为与政治对手进行谈判的筹码。
首先,尼迈里不经南方人民地区议会的选举就直接任命南方高级执行理事会的主席。南方自治政府组建以后,原本最有希望出任高级执行理事会主席的约瑟夫·拉古(Joseph Lagu)未能如愿,尼迈里任命副总统阿贝尔·阿里尔(Abel Alier)为主席。此后几任主席多是在南方自治政府与尼迈里的博弈中出任的,且多是尼迈里的意见占据上风。
其次,1977年尼迈里在获得与乌玛党(Umma Party)的和解后,不再需要南方的支持,遂开始收回南方部分自治权。以马赫迪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进入政府后,尼迈里显示出抛弃南方,转而依靠伊斯兰派系的倾向,逐渐缩减南方的自治权。“对于尼迈里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他的宗教投机(religious bids)用在了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方向上,而在于1971年后他压制伊斯兰组织的历史使其对手(马赫迪和巴希尔)相对容易地批评他是伊斯兰教可同甘而不能共苦的朋友。”(23)Monica Duffy Toft, “Getting Religion? The Puzzling Case of Islam and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4, 2007, pp. 97-131.
最后,解散南方自治政府。阿里尔离任南方高级执行理事会主席后,拉古接任主席一职,尼迈里乘机解除了拉古的军职。由于拉古本人与以色列等国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加之拉古任人唯亲的作风受到南方的批评,尼迈里在面对北方伊斯兰势力的施压后逐渐倾向于解散南方议会。1980年,南方提前举行了第三届议会选举,阿里尔在随后的高级执行理事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主席。1983年6月5日,尼迈里签署《六五总统令》,解散南方地区议会与高级执行理事会,同时将南方地区分为加扎勒河省、赤道省和马拉卡勒省等三个省,建立省议会,将行政长官的任命由地方议会任命改为总统任命。这一系列决定表明,尼迈里“傲慢地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24)[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徐宏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此后,无论是阿卜杜勒·拉赫曼·苏瓦尔·达哈卜(Abdel Rahman Swar al-Dahab),还是阿卜杜拉·法迪尔·马赫迪(Abdullah al-Fadil al-Mahdi),抑或是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在取得政权后未再提及南方自治的问题。直到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议》达成后,南方才再次获得自治权。
(二) 石油资源分配与争夺经济利益
一般而言,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会对中央政府(主体族群)与地方少数族群的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族群冲突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支撑,因而占有资源的一方占据优势。在此背景下,冲突就变成了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之争。另一方面,作为在分配中受到歧视的少数族群,资源的分配状况事实上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空间,尤其是当受到主体族群威胁时,少数族群更倾向以集体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苏丹先后在南方或者南北交界的本提乌(Bentiu)、科尔多凡(Kurdufan)和上青尼罗河(Upper Blue Nile)等地勘探出了可供开采的石油。《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给予了南方政治自治地位,但却没有赋予南方多少经济权力,这显然是南苏丹面临的不利因素。即使和平协定持续下去,围绕政治权力和资源分享的分歧也将成为和平的主要障碍。(25)Bona Malwal, Sudan and South Sudan: From One to Two,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14-115.事实上,南方并没有预料到油田的发现,而尼迈里为实现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北油南运。政府决定在产油地400英里之外的北方库斯提修建炼油厂;同时建设一条长达870英里的石油管道,将南方的石油运往苏丹港,进而运往国际市场。这一舍近求远的举措激起了南方的激烈反抗。
其次,在石油管理机构中排除南方势力。为加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尼迈里调集由绝大多数北方人组成的北方部队,以替换萨尔瓦·基尔(Salva Kiir)驻守在本提乌的南方卫戍部队。同时,南方的石油管理权被完全排除,改由总统直接定夺,后者否决了南方人要求平分财富的提议。
最后,重划行政区域。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南方的石油财富,尼迈里采取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措施,试图削弱南方通过地区自治获得新的政治潜力,但却进一步加快了和平的崩溃。(26)Carolyn Fluehr-Lobban, “Protracted Civil War in the Sudan: Its Future as a Multi-Religious, Multi-Ethnic State,” The Fletcher Forum, 1992, pp. 67-79.尼迈里将南方地区分为加扎勒河省、赤道省和马拉卡勒省,在本提乌地区设置统一省(Unity State)并亲自监管,将此地视为西苏丹南部,旨在将石油资源纳入北方管辖范围内。尼迈里的上述措施激起了南方的强烈反抗,南方高级行政理事会领导人多次表达不满与反对。南方出版的《为什么必须拒绝重新划分南方地区》一书就曾阐明了反对尼迈里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主张。(27)[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第152-153页。然而,尼迈里不顾一切地逮捕南方反对者,强力推行重划行政区的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南方无暇兼顾,此后北方主导的历届政府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尼迈里时期的石油资源分配政策。
三、 强力政党: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组织建设与内战进程
对当代族群而言,政治组织化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族群政党或准政党(quasi-party)、类政党(similar party)组织(28)类政党在法律程序上或手续上并不是正式政党,但它们在政治功能、组织特征、活动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政党类似的特征,能够在一定的政党体制框架内生存与活动。准政党是即将成为政党的组织,主要是以一般社团的形式存在却以政党方式活动的政治组织。参见金安平:《简论政党政治中的“类政党”与“准政党”现象》,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22页。本文为了表达方便,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这样的准政党通称为分离主义族群政党。。对于分离运动而言,族群政党的意义在于提供平台、筹募资源、建构认同、协调行动等。有了族群政党,分离主义者就能够依赖于群体认同的建构,利用精英团体的叙事能力,保持族群政党较强的影响力,在关键节点开展公投、武装斗争等活动。族群是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是族群的政治代言人,族群政治往往呈现出族群政党化和政党族群化的趋势。因而,族群政党是排他主义者,常常通过极化政治诉求导致社会分裂甚至崩溃。(29)Richard Gunther, Larry Diamond, “Types and Functions of Part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22.对于南苏丹分离运动而言,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就是分离主义族群政党。
苏丹独立后,南苏丹境内的游击战持续不断,南北双方也在战争中进行过多次和谈。然而,南方力量的分散使得南方始终不能以一个整体与北方抗衡。仅以1965年为例,在南北联合政府组建后,流亡海外的南方政治家受邀参加圆桌会议,南方武装力量代表中甚至出现了卡克瓦人埃利亚·鲁佩(Elia Lupe)代表的境外苏丹非洲全国联盟(Sudan African National Union-outside,SANU-outside)、丁卡人威廉·邓(William Deng)代表的境内的苏丹非洲全国联盟(SANU-inside)、境外的阿尼亚尼亚解放阵线(ALF)和苏丹非洲解放阵线(Sudan African Liberation Front/SALF)的阿格雷·杰登、南方阵线(Southern Front)等多个团体。(30)Ibid., p. 95.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南方力量的高度分散化。
有鉴于此,1983年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后,南方独立派代表人士约翰·加朗(John Garang)为整合南方势力,于同年5月成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其武装力量是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成员主要是非穆斯林和南方黑人。1983年7月31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公布《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宣言》,主张以全苏丹的名义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一个全新的苏丹。在此后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过程中,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逐渐将目标调整为实现南苏丹的独立。虽然此举并没有得到加朗的公开支持,但《全面和平协议》的签署仍标志着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致力于南苏丹独立的目标被正式公之于众。1985年7月8日,加朗在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交的备忘录中提到,除非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宗教偏见不再存在,否则战争仍是苏丹唯一的选择。(31)Douglas H. Johnson, The Root Cause of Sudanese Civil Wars, p. 71.战争作为唯一的手段不仅是加朗的结论,也是南方其他抵抗力量的一致看法。此后,在北南双方断断续续的和谈进程中,战争始终是重要的斗争手段。
战争期间,如何将其他势力汇聚成统一的抵抗力量成为加朗的重要任务,这事关南方能否以统一的组织、行动与北方抗争。在整合南方势力的过程中,加朗通过多种手段和策略将南部统一纳入他的领导之下。为此,作为政治组织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与作为军事组织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内战中不断加强组织建设,确立了加朗的领导地位,整合了南苏丹的各种政治势力。
第一,将南方其他抵抗势力拉拢进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以统一的旗帜行事。南方的其他抵抗势力有的独自行动,有的支持加朗,也有的反对加朗。经过8年的努力,至1991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完成了军事化过程,并且呈现出专制主义军事等级的特点。(32)[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第232页。1994年4月,加朗在南方召开南部苏丹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在历经十几年的内战后,南方抵抗力量纳入加朗的统一指挥。在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优势面前,其他抵抗力量相形见绌,不得不同意以加朗的“新苏丹”为奋斗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大会通过的南方自决目标是南方独立的前奏,大会也成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革新的序曲,加朗成为南部苏丹的合法代表。(33)同上,第241页。
第二,面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与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分裂,加朗采取果断措施对有关方面予以打击或联合。1991年5月之前,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这不仅是为方便接受国外援助,也是避免被苏丹中央政府所清剿。随着苏丹人民解放军将总部迁回国内,南方内部矛盾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置于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1991年8月,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发生分裂,主张南方分离的里克·马查(Riek Machar)、拉姆·阿科尔(Lam Akol)等人叛变,组建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纳赛尔派(SPLM/A-Nasir)(34)后更名为“南苏丹独立运动”。。这不仅在军事上重创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也在战略上暴露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分裂意图。引起南方警觉的是,1997年阿科尔与苏丹中央政府展开谈判,达成《喀士穆和平协定》(KhartoumPeaceAgreement),致力于通过军事行动创建一个独立南方的加朗对此予以谴责。直到2001年,加朗和马查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化解,第二年马查再次回归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马查具有标志意义的回归不仅确认了加朗作为南方统一领导人的角色,而且也带动了2003年阿科尔的回归。阿科尔的回归宣告了加朗代表的丁卡人与阿科尔代表的努尔人的和解,两个族群通过和解致力于实现南方的共同事业。
第三,面对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主张彻底独立的力量和其他分离组织,虽然加朗也致力于南苏丹独立,但为了避免破坏非洲边界不可更改原则从而招致非洲国家的反对,加朗决定将内战的目标定位为建立“新苏丹”。考虑到非洲各国的情绪,加朗强调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将南方分离出去,而是建立“所有苏丹人的‘新苏丹’,一个其中央政府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与部落制度的联邦政府”(35)[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第162页。。加朗在1987年的备忘录中明确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目标定位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非地方性的叛乱或外部势力的工具。在访问美国、赞比亚等国时,加朗也重申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致力于建立民主、世俗和统一的苏丹的目标,以此赢得外部势力的同情。
四、 文明冲突: 伊斯兰化、苏丹主义与新殖民叙事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提出,主宰全球政治的范式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3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以2011年前的苏丹为例,南北苏丹之间的文明冲突集中于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南方的非洲文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引发了南苏丹对非洲主义和作为整体的苏丹国家主义的想象,进而塑造了南方对北部苏丹的殖民者形象的叙事。一方面,北方精英试图将整个国家阿拉伯化,将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南方等边缘地区持续不断地反抗北方的同化政策。(37)Gunnar M. Sørbø and Abdel Ghaffar M. Ahmed, “Introduction: Sudan’s Durable Disorder,” in Gunnar M. Sørbø and Abdel Ghaffar M. Ahmed, eds., Sudan Divided: Continuing Conflict in a Contested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3.这一基本矛盾使得苏丹南北围绕着族群、宗教、语言等议题冲突不断。为了应对北方的同化政策,南方针对性地提出了苏丹主义的概念,以对抗北方的伊斯兰化。不仅如此,南方更是将北方视为新的殖民主义者,认为独立后的苏丹面对的只是将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换成北方帝国主义而已。
(一) 同化政策: 北方的伊斯兰化努力
虽然独立后的苏丹经历了议会民主制与军人政权的反复,但都毫无例外地奉行将阿拉伯语定为官方语言、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致力于在南方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政策。无论是苏菲派、哈特米教团、萨曼尼教团掌权,还是由马赫迪主义演变而来的乌玛党、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民族阵线等力量,都主张实行全面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并将这一政策作为解决南苏丹问题的关键。自独立以来,北部苏丹痴迷于将苏丹建设成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一个拥有一种语言(阿拉伯语)、一种宗教(伊斯兰教)、一种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种族(阿拉伯人)。(38)BGV Nyomb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Rac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the Sudan,” Frankfurter Afrikanistische Blatter, No. 6, 1994, pp. 9-22.北方对南方的同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伊斯兰教为依托的阿拉伯文化的入侵。如同当年欧洲殖民者那样,北部阿拉伯人将未能接受伊斯兰教的南苏丹视为“黑暗的大陆”(dark continent)。
纵观北方推行的同化政策,无论是将阿拉伯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还是排斥打击南方基督教和原始宗教,都带有明显的宗教歧视色彩。多数苏丹领导人都认为“伊斯兰教在非洲具有神圣的使命,南部苏丹则是这一使命的开始”(39)Gabriel Warburg, Islam, Sectarianism, and Politics in Sudan Since the Mahdiyy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3, p. 167.,南部的文化真空等待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来填补。(40)Dunstan M. Wai, “Revolution,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Suda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7, No. 1, 1979, pp. 71-93.可以说,宗教问题是苏丹内战与南方分离运动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北方伊斯兰教和南方基督教的冲突是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宗教冲突激化和延续的结果与表现便是南苏丹的分离运动。(41)姜恒昆:《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30页。南方的原始宗教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相对比较温和。当然,这与南方族群的部落化有着直接联系。而基督教却是由殖民者引入的,且在南北分治时期受到着力扶植,基本上处于一种独立发展的状态。在被引入之初,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外来宗教,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入侵,也承担了南方教育的重要责任。正是对南方教育的贡献,使得基督教在南方获得了扎根的机会。此时的基督教更多的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塑造了南方说英语的习惯和文化。然而,北方伊斯兰化的政策逐渐使南方人将基督教会作为反抗不公正和压迫的政治联盟。(42)Amir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Sud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67.
1972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并未能获得北方伊斯兰教激进主义者的同意和认可。马赫迪的苏丹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加入政府改变了尼迈里之前的和平政策。为拉拢苏丹民主统一党,尼迈里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伊斯兰化政策。1977年,尼迈里成立“基于伊斯兰原则的苏丹法律修改委员会”,旨在修订苏丹法律以使之符合伊斯兰教法,并任命穆兄会秘书长哈桑·图拉比为委员会主席。这一任命为伊斯兰教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此后,尼迈里政府强行颁布《九月法令》,在全国推行伊斯兰化运动,将伊斯兰教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律法。《九月法令》的实施不仅是对1973年宪法的背叛,事实上也标志着《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破产。尼迈里还对基督徒实行史无前例的打压,将教堂视为非政府组织,甚至建立了名为“正义裁决法庭”的机构来督促《九月法令》的实施。此后,苏丹执政者不遗余力地推行伊斯兰教法,强力推行国家伊斯兰化政策。
(二) 意识形态: 从非洲主义到苏丹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主义和阿拉伯主义之间的界限是流动且模糊的,在全球化、移民和社会联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的身份认同可能出现。通过解构苏丹身份的主导概念和纳入有关身份认同新概念,有助于理解影响冲突的社会动力。在此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帮助适应国家多元身份和促进稳定的模式。(43)Abderrahman Zouhir, “Language Policy and Identity Conflict in Suda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4, No. 2, 2015, pp. 283-302.
南北苏丹在文化上的鲜明差异主要表现为,“非洲主义和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两种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身份,并引发了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导致南北战争的升级以及其他武装冲突”(44)Amal Ibrahim Madibbo, “Conflict and the Conceptions of Identities in the Sudan,” Current Sociology, Vol. 60, No. 3, 2012, pp. 302-319.。“南苏丹人共享欧洲和阿拉伯商人发动的具有破坏性的奴隶贸易以及外国统治和镇压的历史。这使得他们加深了非洲人的意识,并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即接受并将他们居住的领土作为一个明确且专有的非洲实体。”(45)Dunstan M. Wai, “Pax Britannica and the Southern Sudan: The View from the Theatre,” African Affairs, Vol. 79, No. 316, 1980, pp. 375-395.无论是1962年成立的“苏丹秘密地区国家联盟”(46)1964年更名为“苏丹非洲全国联盟”。,还是1966年成立的苏丹非洲解放阵线,南苏丹的反抗都表现出一种“非洲主义”情结。(47)刘辉:《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第75页。“来自北方的威胁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感,即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理念,与最近获得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非洲主义。”(48)Francis Deng, War of Visions: Conflict of Identities in the Sudan, p. 494.历史地来看,在苏丹,种族和族群身份都是斗争的结果和后果,它们是动态的。后殖民时期,苏丹的政治发展主要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所倡导的“新苏丹”或“苏丹主义”(Sudanism)的结果。政治主题的转换将苏丹的冲突从种族与族群的问题转移到民族与公民的议题上来。(49)Amir H.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Sudan, p. 105.
“苏丹主义”的提出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南北关系的长期演化和斗争中诞生的。北部将南部界定为“南部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歧视。约翰·加朗并没有坚持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重新将苏丹危机界定为“南部问题”,而是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引入了苏丹主义的概念。苏丹主义的概念拒绝了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而寻求整合阿拉伯人、非洲人、基督徒或穆斯林身份的可能。(50)Amir Idris,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Violence in Two Sudans: Reimagining a Common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98.“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分离主义者的南苏丹民族主义者在苏丹人民解放军的统治下成为顽固的‘新苏丹民族主义者’……‘新苏丹’的口号由此变得更加根深蒂固。”(51)Bona Malwal, Sudan and South Sudan: From One to Two, p. 165.
(三) 新殖民主义的叙事: 怨恨与不满
南北苏丹的交往历史曾是血腥的、暴力的、痛苦的奴隶贸易。(52)刘辉:《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第19页。南北双方共同的美好记忆可能止于马赫迪起义,然而,马赫迪起义终究是由伊斯兰主义者发起的。待马赫迪起义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进入南方的马赫迪主义者开始在当地大肆劫掠,甚至开展黑人贸易,这极大地刺激了南方的怨恨与不满情绪。南北双方巨大的历史和现实差异,使得双方都难以接受彼此。北方在政治上的强势使得南方不得不接受被统治的事实。但这种统治在南方看来是不合法的,尤其是南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遭到了北方的歧视与压制,这导致南方的怨恨与不满不断加剧。“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认为是自由的、优越的,而且是奴隶主的种族,而黑人和异教徒则被认为是(合法的)奴隶。”(53)Francis Deng, War of Visions: Conflict of Identities in the Sudan, pp. 4-5.
纵观苏丹历史,北方是特权阶层,南方是低等阶层,被称为奴隶。(54)Mohamed Ibrahim Nugud, Slavery in the Sud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translated by Asma Mohamed Abdel Halim, edited by Sharon Barn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61-149.“苏丹北部被认为是‘东方的’,南部则被视为是‘没有历史的人的居住之地’。结果,北苏丹被贴上了阿拉伯、穆斯林、文明开化的标签,而南苏丹则被贴上了黑人、异教徒、原始人的标签。”(55)Amir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Sudan, p. 13.不难想象,苏丹南方人有充足的理由去仇恨穆斯林和说阿拉伯语的人,历史上,北方人是抓捕奴隶(slave-seizing)的组织者。(56)Hugh Seton-Waston,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Methuen, 1977, p. 345.“在苏丹,暴力和种族主义两种历史特质被嵌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之中。当暴力深嵌入国家的基础结构成为种族化的制度时,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赖于暴力的使用,暴力被视为获得合法性和实行迫害的终极手段。”(57)Amir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Sudan, pp. 54-55.当权力为北方所拥有时,南方因其历史上与北方的敌对关系而势必遭到种族主义歧视和暴力镇压。
南苏丹人的身份是基于混合的种族、文化、宗教、地理环境、历史、教育,是和阿拉伯苏丹作为一个外围集团的存在而共同产生的。(58)Alexis Heraclides, “Janus or Sisyphus? The Southern Problem of the Suda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5, No. 2, 1987, pp. 213-231.南苏丹的民族主义是以下因素的混合产物:一是极端的不平等;二是北部阿拉伯人强加的同化威胁;三是喀土穆政权反对南苏丹联邦制地位、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要求。(59)Ibid.这种夹杂着对北方仇视的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将怨恨与不满定位为南北关系的主基调。这也就不难解释,南方为何坚持认为独立后的苏丹只是政权的变化和统治者的变更,只不过是将“英国帝国主义换上了北方帝国主义”(60)杨灏成、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五、 南苏丹的族群冲突及未来走向
独立后的南苏丹并没有从苏丹分裂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占统治地位的丁卡人和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并没有给独立后的南苏丹带来稳定和繁荣,南苏丹依然面临严重的族群冲突。与此同时,南北苏丹关系仍然被历史遗留问题所羁绊。
(一) 《全面和平协议》与南苏丹独立
2005年1月9日,南北双方在肯尼亚的内罗毕签署关于苏丹南北问题的一揽子协议,即《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PeaceAgreement)。协议的达成结束了苏丹长达23年的第二次内战,缓和了苏丹的外部压力,为巴希尔当年的再次连任赢得了政治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南方由此获得了和平,饱受战乱的南苏丹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契机。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和2005年苏丹临时宪法,南北苏丹关于南方自治、权力分配、石油财富分配、宗教语言等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南苏丹在政府设置的6年过渡期内享有充分的自治地位,苏丹第一副总统由苏丹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或其继承人担任,同时兼任南苏丹政府主席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统帅。这一职位最早由约翰·加朗担任,然而仅一个月不到,加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转由萨尔瓦·基尔继任。
第二,关于中央政府权力分配问题,除第一副总统由苏丹人民解放军统帅担任之外,南北成立团结政府,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所占比例进行划定。其中,北方占比70%,南方占比30%,具体分配为:全国大会党占比52%,其中北方人为49%,南方人为3%;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占28%,其中南方人为21%,北方人为7%;北部其他政治力量占比14%,南部其他政治力量占6%。
第三,关于石油资源的分配问题,成立国家石油委员会,总统和南苏丹政府主席共同担任主席,南北各派4个代表作为常任理事,石油州派3个代表作为非常任理事,负责制定石油发展战略与计划。
第四,关于宗教和语言问题,宪法第一条即明确了苏丹作为多文化、多语言、各种族和宗教并存的国家,政府确认各种宗教和文化是其力量、和谐、天启的来源。联邦政府明确了阿拉伯语与英语作为政府官方语言的地位,不得歧视任何一种语言。同时,政府尊重、发展和提高土著民族语言。(61)《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973页。
《全面和平协议》和苏丹临时宪法都得到了双方的一致维护,即便是在加朗不幸遇难给南北和平增加变数和南北因阿卜耶伊地区爆发冲突(62)南北苏丹分家后对盛产石油的阿卜耶伊地区存在争议,2011年公投对该地区归属权也未明确,南北双方在公投后为此爆发了冲突。的情况下,巴希尔仍然坚持尊重协议和宪法。根据协议和宪法安排,南苏丹在6年过渡期后举行独立公投,最终实现独立。南苏丹独立后,北方仍然沿用了“苏丹共和国”的国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名与地理位置存在着对应关系。然而,南苏丹的独立并没有改变北方保留原有国名的态度。“也许,这是一种不情愿的怨恨,即北方的苏丹人没有将他们的国家重新命名为北苏丹。”(63)Bona Malwal, Sudan and South Sudan: From One to Two, p. 65.不管原因是什么,北方不得不承认的是,南苏丹已然独立,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对于北方而言,在国家建设上所能做的是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如何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避免下一个南苏丹的出现。
(二) 再陷困境: 南苏丹的族群冲突现状
独立后的南苏丹仍然面临族群冲突与南北分裂后的遗留问题。南苏丹的独立激化了丁卡人和努尔人的矛盾,此前为共同抵抗北方所缔造的利益共同体崩溃,原本隐藏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南苏丹仍面临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南苏丹以黑人为主,尼罗特、尼罗哈姆、班图和努巴构成了该国的四大族群,四大族群下还有丁卡人、努尔人等众多部族,但却没有一个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部族,最大的丁卡族的人口占比也只有15%左右。除复杂的族群结构外,南苏丹语言、文化和宗教也呈现多样性,并非一个统一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南苏丹的族群结构、语言矛盾、宗教冲突等比苏丹还要复杂。客观而言,很难得出南苏丹居民组成一个民族、共享统一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归属感的结论。换句话说,南苏丹人似乎分成了无数个个体和部落成员。(64)Milena Sterio,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165.
在关于南苏丹的新闻报道中,“群尸坑”、难民、种族屠杀、部落冲突等负面消息不绝于耳,族群冲突成为南苏丹民族国家建构中难以回避的问题。(65)关于南苏丹的族群冲突,参见唐世平、张卫华、王凯:《中国海外投资与南苏丹族群政治》,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5期,第60-63页;刘辉:《南苏丹共和国部族冲突探析》,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3期,第31-39页。2013年12月,丁卡族总统基尔解除了努尔族的副总统马沙尔的职务,导致丁卡族与努尔族之间爆发族群冲突,并牵涉到其他部族,南苏丹内战随即爆发。时断时续的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2015年8月,各方才达成《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次年4月,南苏丹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成立,但协议的执行仍然不容乐观。不合时宜的权力下放、权力分立和国家能力的孱弱,导致南苏丹再度陷入了严重的冲突。
南北遗留问题主要指阿卜耶伊问题,这一地区甚至可能变成第三个苏丹。(66)Abdel Ghaffar M. Ahmed,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Borderlands: Emergence of a Third Sudan?,” in Gunnar M. Sørbø and Abdel Ghaffar M. Ahmed, eds., Sudan Divided: Continuing Conflict in a Contested State, pp. 121-139.历史上的阿卜耶伊一直处于南北苏丹冲突的前沿,后因石油资源的发现而变得更加敏感,即使是在《全面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也曾遭到战火肆虐。根据《全面和平协议》和南苏丹临时宪法,南苏丹实行联邦制,领土范围是原加扎勒河省、赤道省、上尼罗省以及1956年1月所建立的疆界范围,包括阿卜耶伊地区。阿卜耶伊是2009年《阿卜耶伊仲裁法庭仲裁书》所确认的在1905年从加扎勒河省转移到科尔多凡省的9个恩格克——丁卡酋邦的领土。(67)有关南苏丹宪法的相关规定,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第719-746页。按照计划,阿卜耶伊地区与南苏丹于2011年同时举行公投,或是选择加入北方保留其特殊的行政地位,或是加入南方成为加扎勒河省的一部分。然而,直到2010年12月该地区的划界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各方围绕谁有权利参与公投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未能于2011年如期举行公投。未来,阿卜耶伊问题将成为影响南北苏丹关系走向的焦点,同时也考验着南北领导人的智慧。
六、 结语
族群分离运动作为次民族(sub-nation)运动,是“民族国家构建与族群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68)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是国家建设过程中族群关系张力的集中表达。可以认为,“族群分裂说明国家建设或国家建构的过程尚未充分完成”(69)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6页。。南苏丹分离运动与苏丹的分裂表明,作为一个族群和文化异质的国家,在面对南北双方巨大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以单一文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行的。面对多族群、多宗教、多文化的人造国家,苏丹的执政者并没有深刻理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复杂性。南苏丹的分离运动是南北双方关系持续破裂的产物,苏丹以武力镇压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族群分离问题。令人唏嘘的是,独立后的南苏丹仍然没有吸取教训,仍在沿用苏丹的治理模式,这导致南苏丹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进一步紧张,族群冲突不断,使得南苏丹成为世界上族群政治激化的新国家。南苏丹的民族国家建设尚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南苏丹的发展道路仍然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