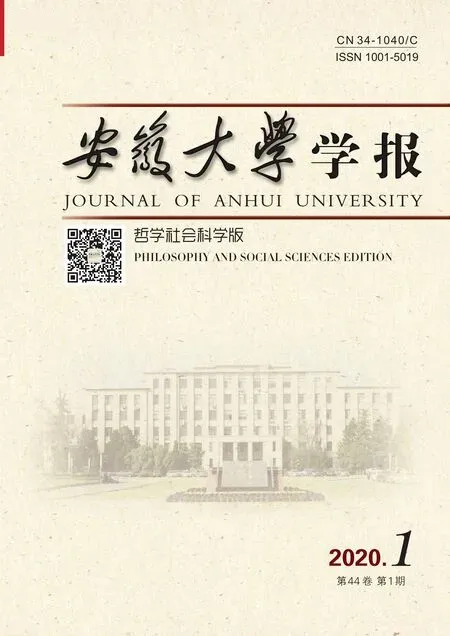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林 凯
魏晋清谈自高平陵政变之后一度沉寂,直至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年)才再度复兴,并形成继正始之后的第二次高峰。乐广与王衍作为当时清谈领袖(1)《晋书·乐广传》记:“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本文所用《晋书》版本为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引领一股好谈虚无之风;其中又以家世显赫并高居要职的王衍影响最大,“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这一股虚无之风,自统治高层刮起而遍及士夫群体,不但席卷学术领域,更扩及人伦礼法以及行政作风,影响甚为广泛。在此情境之下,不但清谈圈外的保守儒士对虚无之风发起抵抗,就连清谈圈内热心世务的名士对此也有所反感,其中代表即为当时朝廷重臣裴頠。裴頠善谈名理,但推宗儒术,其价值理念不同王衍之徒,故两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崇有、贵无的论辩。此论辩成为元康清谈中最重要的思想事件。
现代魏晋玄学研究普遍重视裴頠对贵无论的批判,即使《崇有论》残篇的思想深度有限,其依然被当成魏晋玄学两大中心主题发展逻辑中的重要一环。如冯友兰主张“王弼贵无论—裴頠崇有论—郭象无无论”构成了“有无之辩”主题的逻辑发展闭环(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4页。;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肖箑父、汤一介、余敦康等人(3)参肖箑父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71页。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I页。从“自然与名教之辩”的角度,将裴頠思想当作对嵇康、阮籍以及元康放达派“反名教”的纠偏之论(4)应该指出,将裴頠思想视作自然与名教关系问题中的重要一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裴頠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汤用彤的玄学分期就没有提到裴頠。参见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这样的思想建构有着宽广的玄学史视野,然而其思想还原又不免有逻辑先行之嫌,未能完整而细致地展示裴頠的思想与贵无论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他并非一味否定贵无,而是试图对有无关系进行更融贯的处理(5)裴頠实际著有《崇有论》与《贵无论》,就在《崇有论》中他已对老子贵无有所认可,那么在已佚《贵无论》中他可能会对贵无论有更多肯定。参许抗生等著《魏晋玄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8~279页。。进一步从玄学史视角看,后世史书和裴頠著论表明,裴頠的崇有仅为对治当时的贵无,并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6)杨立华认为裴頠的批评乃针对整个贵无思潮整体(参见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3页),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而牟宗三认为裴頠所论之有无与道家之有无不在同一个层次,不构成真正的批判(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但其观点在目前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并且在学理上,裴頠思想其实也无法对后者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
一、从史料说起
学界倾向认为,王衍之徒的贵无论来自王弼、阮籍等人,故裴頠的崇有论实际也针对王、阮等人。这个判断首先出于《世说新语》《晋书》等记载的影响。然而,仔细分析相关史料,这个判断不无可疑。有关记载如下:
1)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世说新语·文学》)
2)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敳之徒皆希慕简旷。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诸公赞》)
3)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晋书·裴頠传》)
4)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晋书·王衍传》)
由材料2和3,裴頠作文首先出于“疾世俗”“患时俗”,即针对所谓“王衍之徒”,他们包括作为首倡者的乐广、刘汉、王衍、戴奥,以及后进的庾敳之徒(即所谓“四友”“八达”)。而裴頠实际论战对象则主要是王衍(材料1、3、4),次之有乐广(材料2),以及其他时人。结合文本内证,如《崇有论》明确批评当时的“薄综世之务”者以及“放者”,则裴文确实直接针对王衍、乐广以及元康放达派等人。
而至于王衍之徒的思想来源,材料2追溯至夏侯玄、阮籍,材料3则及何晏、阮籍,材料4又至何晏、王弼。王衍之徒的思想跟这些前辈当有关联,但他们是否完整继承了前辈思想则不无可疑。这些追溯,可能是史家对照时人与前人理论后作出的准确评价,但更可能是史家根据王衍之徒所自称的来源进行的推测。如材料4说王衍“甚重”何、王之论,王隐《晋书》也指出当时放达派乃“祖述于籍”(7)见《世说新语·德行》第23条注引王隐《晋书》。,可见,借重前人之风在当时颇为流行。所以我们应该有意识区分王衍之徒的贵无与前人的贵无,前后之间可能存在曲解。而进一步,我们能否认为裴頠也有意针对这些前人的贵无?考虑到《崇有论》无法给出文本内证,我们最多可认为裴頠对王衍之徒所宣称的何晏、王弼、阮籍有所回应(然而连这一点也颇为牵强);至于裴頠是否针对真实的何、王、阮本人,则难有依据。
总之,魏晋史料倾向于认为裴頠针对王弼、阮籍,但未能给出充足证据,所以,我们必须依据对裴文的分析,才能辨清裴頠是否以及能否回应整个贵无思潮。
二、裴頠对贵无论的批评
裴頠以崇有批评元康时期的贵无,然而,王衍之徒的贵无论究竟是怎样的主张,而裴頠借以批评的崇有论又是如何之面貌?以往研究往往零散地提到贵无论的多点内容,但较少以一种体系性结构去呈现它。然而,这种贵无论即使在裴頠《崇有论》看来也是“上及造化,下被万事”,其应当被把握为一种包纳形上与形下、本体与人事诸层次的体系;同样地,裴頠的崇有论也应当在一种体系性结构中得到呈现。如此,我们才能在崇有、贵无两种理论之间进行较完整的层次对照,从而说明裴頠如何批驳以及能否驳倒当时的贵无论。
(一)贵无论体系
贵无论的阐发首先起于人事关切,如裴文指出,正是为对治人类情欲,王衍之徒才提倡贵无贱有之说: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晋书·裴頠传》)
由于对治“欲衍、情佚、擅恣、专利”一类人欲,贵“无”贱“有”之“有无”首先当是“有欲、无欲”之义。贵“无”首先是贵“无欲”。“无欲”如果只是否定过分之欲而非绝欲,那它其实与儒家传统中的“节欲”观念有相通之处。不过在裴頠看来,王衍之徒的“无欲”已然极端化,如其后指出“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8)《晋书》版本原作“故”,但《资治通鉴》有另一版本的《崇有论》在此处作“累”。笔者以为取“累”为佳,即明形体欲望之累。,盛称空无之美”(《晋书·裴頠传》),也即王衍之徒为了解决“有形之累”而主张“空无”,也就是一种彻底的无欲。这种彻底的无欲会引发人事实践层面的诸种问题。
首先引发的问题是行动上的“无为”,因为无所欲求将会取消行动的动力;个体可因此摆脱名利之累,但也将无所作为,无益于社会整体的福利。裴文谈道,当时便流行这种追求个人解脱的无所作为:“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晋书·裴頠传》)。进一步,“无欲”将导致“无礼”,这在裴文首次谈到贵无论时便已指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晋书·裴頠传》)由于有欲源自有身,则贱弃有欲将导致忽略己身(即“外形”),如此建基于规训身体的礼教便无必要(即“遗制”“忽防”“忘礼”)。这种贱有一旦极端化,就将对抗一切实有,“忘礼”将变成“违礼”,如裴文其后描述放达派的表现:“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亡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晋书·裴頠传》)
如此,在人事层面,王衍之徒主张“彻底无欲—无为无礼”的内外结构。值得指出的是,人事方面的说明又可区分个体视角和整体的政治视角:前者侧重谈一般个体如何进行内在修养和实施外在行动,从而实现个人欲求;后者侧重谈治政者采取怎样的方案进行治理,为所有个体的欲求满足提供外部保障。显然,王衍之徒的贵无在人事上过分关注个体视角,而忽略从政治角度谈无为之治。
除“下及万事”,王衍之徒是否还“上及造化”,即从本体论或宇宙论(9)中国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笔者这里是从基础的构成论的意义上说本体论。而宇宙论则从生成论角度去说,说明万物由何产生和如何化成。等形而上层次去论“无”?按史料记录,上文中材料4提到王衍对何晏、王弼“以无为本”这种本体论很重视,那么王衍贵无应该有某种本体论上的主张(即便他照搬了王弼)——当然 “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参照裴文,文中有批评后人贵无是对老子贵无本义的扭曲,将“以无为辞”执着成了“以无为宗”。那么史料与文本互参,《崇有论》的批评应当就是史料所谓“著论以讥之”,即裴文批评“以无为宗”就是直接针对王衍的本体论。不过,由于王衍之“无”是彻底的“空无”,则其“以无为宗”乃“以(空)无为本”,与王弼的“以(道)无为本”实际有所出入。
综合起来,王衍之徒的贵无论从本体到人事、从个体到政治,包含了这样的层次:“以无为体—(个体)无欲—(个体)无为无礼”。然而,这个结构实质还缺乏两个重要的层次。第一,它没有谈“以无为用”,也即它说了本体和人事,但本体如何发用而为人事实践所模仿,它没有说清楚;而从体到用的转换却是王弼贵无超出传统崇有的关键所在。如果吸取了这一点,王衍或许不会走向彻底空无。第二,它在人事上没有考虑整体政治。而如何创造一个良善环境以保证个人与他者不相冲突显然对个体欲求的实现极为重要;裴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贵无论导致“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并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补充。
(二)崇有论体系
参照对手的理论结构,裴頠的崇有论同样可被把握为一个“上及造化,下及万事”的体系,以对贵无论作出相应的批驳。
1.形上的探讨
对应贵无论体系,我们先看裴頠关于形而上层面的探讨。裴文最后一段指出: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晋书·裴頠传》)
此处“至无者无以能生”有回应《老子》“有生于无”的意味,但考虑到句中的有无只具有实在论层面的意义(如“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则此句文义应当被理解为:空无(非存在)不能产生实有(存在)。它实际属于此物生彼物的宇宙论探讨,而非在本体论层面探求万物生化之基础。当以宇宙论模式追溯那个最初源头,就会陷入无限倒退的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裴頠主张的“自生”才能得到较为适当的理解,也即他实际主张“无”或“有”均非最初来源,万物不过自然生化。
“自生”概念早已见于庄子、严遵、王弼和向秀的论述(10)王葆玹:《玄学通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6年,第498页。。就从魏晋学者看,王弼言:“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11)《老子》第10章注。本文所引版本为《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向秀言:“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12)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这里,“自生”乃自然而然生化的意思,与某种有意志的主宰方式相对,它甚至不当被理解为“自己”主导生化。并且在王弼、向秀这里,事物“自生”需要一个基础,即句中所谓“原”和“生生者”,也即“道”。考虑到“道”生万物是本体论的论述,而裴頠谈“无”或“有”均不能生万物却是宇宙论的论述,二者并不冲突,并且裴頠自生论还有可能吸取了王弼的相关思想。
有学者会特别关注“自生而必体有”一句,以及开篇“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和“理之所体,所谓有也”两句,从而强调裴頠主张“以有为体”(13)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第153页、154页。。这里应该是受到有无对立结构影响而对其有所误读。“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和“自生而必体有”所说的“体”并非本体论之体,而只是牟宗三所谓“凭借”之义(1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316页。,只是说明凡物之生、凡条理之显示都需要以实有为载体。而“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一句,也不是说“整个无分别的群有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道(本体)”(15)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第153页。,它不过在说“总混万物而探其本,是建宗立极之道”(16)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316页。詹雅能则依从牟宗三观点对此有更为详细的文句辨析,参詹雅能《裴頠崇有论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第24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45~46页。,其表明探求道的方式,而非以有为道。所以,认为裴頠在本体论上主张“以有为体”,并构成对王弼“以无为本”的反动,在文本上并无充足依据。相反,裴頠只是在宇宙论上否定“有”或“无”作为终极来源而主张“自生”,至于本体论上他具体如何主张却未可知。
2.事理的探讨
由上,在形上层面裴頠并无强调“以有为体”。他之论“有”(实有)其实主要在事理层面展开,强调的是“有”的存在性和“有用”“有为”的必要性。这种强调主要体现在《崇有论》首末两段:
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晋书·裴頠传》)
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晋书·裴頠传》)
首段指出凡物之生必以实有为存在载体(即“体有”),由此也便须择取外在物质以资生存(即“用有”);而末段也提到事物“体有”,并进一步指出要养育和管理已生之万物则必须“有用”“有为”。
“体有”,即在肯定事物的存在性,对治彻底空无。“用有”,在首段主要从个体角度谈一般个体需要有所作为去利用实有之物,才能满足生命需求;在末段则主要从政治角度说治政者需要利用他物和有所作为,才能满足万物之需求。总之,事物是实有性的,为满足其生存则(无论个体自身或治政者)必须利用外物,故而实践上“有为”是必要的。
然而,裴頠所论“有”之存在和“有为”之必要,偏重“有”之静态层面而忽略“有”之运作层面。已经存在的“有”应当如何去利用,必要的“有为”又当如何去展开,这些关乎“有”之运作机制的问题对于实现生存目标甚为关键,但裴文未能深入。所以,如果说王衍贵无只谈“体”而未谈“用”,对王弼贵无之体用有所曲解,则裴頠崇有既不谈“体”也不谈“用”,其论“有”之存在与必要尚属浅显层次,甚至都没有推进到王弼考虑“有”之运作的层面。
3.人事的探讨
在人事上,王衍之徒主张个体的“彻底无欲—无为无礼”而缺乏政治层面的考虑,相较之下,裴頠则较为全面,主张个体之“有欲—有为”以及治政上“有为”“用礼”。
裴文指出,“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晋书·裴頠传》),他充分肯定人类的欲望,主张节欲而非绝欲。既然人欲本有,为了满足生存欲求,个体显然需要“有为”。裴頠主张:“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晋书·裴頠传》)也即个体必须有所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有所为(“躬其力任,劳而后飨”),行美德(“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并有节制(“志无盈求,事无过用”)。这是一种关于个体内外兼修的主张,充分肯定某种适中的“有欲—有为”。
不过,裴頠更侧重补充王衍未能考虑的政治层面,指出治政必须有所作为,积极施用礼教。如其言:“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晋书·裴頠传》)也即君王要建立秩序,制定礼教刑法,大臣则要积极推行这些礼法,辅助教化。总之,统治阶层应当积极发挥其引导作用,实行以名教为基础的有为之治。
裴頠肯定“有欲”并主张(个体或治政的)积极“有为”,显然是基于其论有之存在性和必要性的原理。但其问题也正如前文所表明的,他没有深入考虑“有”之运作机制,也就忽略了名教实现过程中存在的美丑、善恶辩证转化问题。他对有为教化过于自信,认为“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晋书·裴頠传》),似乎百姓任随教化去改造,竟有意忽略东汉末年名教虚伪问题的教训。
总结裴頠的崇有论体系,它同样包含本体与人事、个体与政治的多层次结构:宇宙论的自生论—“有”的存在与必要性—(个体)有欲—(个体)有为—(政治)有为之治。对照王衍的贵无结构,裴頠从本体论转向了宇宙论,强调了实有的必要性,并且在人事方面增加了政治考虑;但同样地,裴頠的崇有论还是缺少了体用之“用”的关键层次。如此,这一崇有论虽然在实有的必要性上对极端空无构成反驳,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层次,不推进到事物运作层次,任何预景美好的行动方案都无法得到有力的辩护。
在这里值得补充的是,裴文笼统地批判王衍之徒,似乎当时贵无论是一个整体,但实则不然,当时贵无论内部已有所分化。比如面对放达派的无礼,连乐广也要批评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晋书·乐广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中区分出“无为派”(如王衍、乐广)与“无礼派”(如西晋“八达”)。像王衍和乐广两位清谈领袖,他们只是喜好清谈,“宅心事外”,并无越礼;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尚非完全不作为,而只是不主动用力,比如乐广“所在为政,无当时功誉,然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晋书·乐广传》),王衍“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晋书·王衍传》)。不过由于他们影响巨大,后来模仿者将其思想极端化,出现裴文批评的那种彻底无为;而西晋“八达”则放浪形骸,藐视一切世俗名教,这又将被动的无为推进到主动的对抗作为上。在这里,模仿越来越表面化、极端化,已偏离了原先“贵无”理念所着意的相对融贯的内涵。如要批评这种极端,重返名教立场不失为一种有效策略。但相比原先融贯的理念,它本非更好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裴頠崇有论受限于对治空无,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
三、裴頠对贵无论的肯定
(一)老子贵无
裴頠批评王衍之徒彻底空无的贵无论,但这并非他对整个贵无思想的态度。就在《崇有论》中,裴頠对作为当时贵无论源头的老子贵无依然持有某种肯定,并据此批评时人对贵无之曲解。某种意义上,当时的贵无可谓“假贵无”,老子贵无本义则是裴頠肯定的“真贵无”。
裴頠在个体视角的全性保生问题语境中把握老子贵无的内涵,认为其须区分字面义和深层义。字面上,老子“以无为辞”,大谈“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其直接意思为“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晋书·裴頠传》),即主张去欲守静。对此字面义,裴頠认为其属与“有”相对的“虚无”(也即空无)。而裴頠心中最完善的思想却是整全的易学,它既包含损欲的哲学,又包括事功的哲学,足以融通有无。相较之下,字面义上的老子贵无只能符合易学一部分的意思,即“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晋书·裴頠传》),只是“偏立一家之辞”(《晋书·裴頠传》)。所以就字面义看,老子贵无是不完善的。但深层里,老子之辞乃为对治欲望,本义却是“旨在全有”,也即恢复仁义德行(17)即裴文所言“存大善之中节”“反澄正于胸怀”(《晋书·裴頠传》)。,绝非一味主张彻底空无、无为、无礼。这样看,老子贵无本非偏执一方,其实际在借助某种特别的表述方式来整合有无,最终意思当又符合那整全的易学。而当时的贵无论主张彻底空无,却是不解文本的语言技巧,固执老子贵无之字面义而错失其深层义。如此则知,裴頠对老子“真贵无”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可,只是对其表达方式有所非议而已。
不过,裴頠如此以易学统贯老学,这是否妥当?不可否认,欲望问题始终是古典哲学的核心关注,易学、儒家、道家均主张减损欲望,最终非为走向空无,而为实现更大的事功作用。所以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融贯有无的意味。问题是,易学的“节欲”能替代老学的“无欲”吗?“节欲”往往以礼法、理智对已经产生的过分欲望进行抑制,而老子谈“无欲”则更倾向在源头上消解非分之念,使适度的欲望自然流露。故而在修行上,“节欲”要求名教辅助,而“无欲”要求专气虚静。这样看,在融贯有无上,易老的方式实际有所差异,易学并不能直接替代老学。除非像王弼那样,将欲望的节制往“自然”上靠拢(18)王弼注《周易·艮卦》曰:“夫施止不于无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则奸邪并兴。”见王弼《周易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3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易老贯通。然而裴頠依然强调名教抑制,则看不到他对王弼的吸收。这样,裴頠虽然站在融通有无的高度道出了老子贵无“旨在全有”的内涵,但他对老子贵无本义依然有所遮蔽。
(二)无为之治
前面提到裴頠在《崇有论》中谈论治政策略时主张积极有为的名教之治,似乎是对王弼无为之治的一种倒退,然而,裴頠在另文却又主张“无为之治”,如其言:
臣闻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侵官为曹,离局陷奸,犹惧此法未足制情。以义明防,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然,故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19)严可均辑:《全晋文》,何宛屏等审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6页。
裴頠认为尧舜盛世实属“无为而治”。此“无为”乃针对君主而言,贤臣则要积极作为;并且此“无为”也并非无所作为,因为君主实际有所“劳”。其劳在三事,即“设官建职—选贤举善—委任责成”。“设官建职”“委任责成”这些制度和法规是前期已经完成的,而“选贤举善”则需后期持续用力,所以尧舜主要“劳于求贤”;不过,由于君主的这些工作都是在为具体治理奠定基础,而非参与具体治理,故而尧舜又“逸于使能”,可谓“无为”。此模式有类黄老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之治”。
《上疏》所谈“无为而治”与《崇有论》的积极“有为”,在概念形式上似有相悖,二者如何统一?汤用彤指出裴頠“虽崇有亦不放弃无为之论”(20)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但尚未对二者整合;余敦康则干脆认为裴頠的崇有违背了其《上疏》本来的“无为之治”理想(2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这里笔者且作一番辨析。
实际上,《崇有论》以名教为基础的有为之治,在形式上并不违背《上疏》“无为而治”中“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构想。无论圣人“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或者“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崇有论》都在强调君主要建立整体秩序,利用礼教政刑等手段实施治理(具体执行当在臣不在君),这符合《上疏》所谈君主的三种职责。而我们之所以会对二文的一致性产生疑惑,则在于,我们误以为《上疏》之“无为而治”直接等同了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后者与儒家精神是有所出入的。
“君无为而臣有为”理论首先处理的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君臣关系,试图建立一个完美的秩序制度,使君臣各司其职,发挥最佳的整体效应。然而,治政还有更重要的一环,即处理臣民关系。各司其职、积极有为的官僚治政,是否就能引导百姓进行和谐的生产生活?儒道在这里发生了分歧。儒家相信,预先完美的秩序设计加上良好的礼教引导和法制禁防,足以成就社群之和谐;但老庄警惕其中的劝与禁对人欲的扰动,一旦动欲则容易导致智巧与虚伪,真正的和谐便不可能。积极入世的黄老道家吸取了老学精神,他们在“君无为而臣有为”结构中进一步内置了一个基础原则,即“因顺”,无论君治臣的“无为”还是臣治民的“有为”都需要因顺而为。所以,在黄老道家那里,礼教刑法至少要在“因顺”百姓性情意义上建立才可能消除扰动——这个原则使得它与传统儒家刻意劝禁的名教方案有了根本区别。但这个尊重百姓性情的因顺原则在裴頠这里并未得到论述,他在《崇有论》中更倾向认为百姓有如器中之水,是容易为教化所改造的,其根本精神还是儒家名教式的。所以,在文本统一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裴頠在《上疏》中只是在形式上使用了流行的黄老道家“无为之治”的话语,而其内在精神依然是传统儒家的。
总之,就具体行文看,由于受限于对治彻底空无的贵无论,裴頠偏重于从另一极端即实有的角度去进行批判,这造成其发挥出来的崇有理论层次有限;但就其隐而未发的理想哲学看,他真正推崇的当是那种融贯有无的整全哲学。这种整全理想使得他能够包容老子的真贵无,以及黄老的无为之治。当然,由于其对老子和黄老的理解还有一定偏差,裴頠的实际践行并未真正遵从这些即使是“真贵无”的方式。
四、裴頠与玄学贵无思潮
上文说明了裴頠崇有论的理论层次以及其对贵无论的复杂态度,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裴頠与整个玄学前期的贵无思潮之关系。鉴于史料本身不充足,我们显然不能轻易说裴頠意在批评整个贵无思潮;并且即使他有意于此,其批评能否真正有效又是一回事。整个玄学思潮中有多种不同的贵无主张(22)严格地说,这些主张并未直接使用“贵无”一词,但都对“无”的观念有很大推崇;参照裴文将重视“无”但并未使用“贵无”一词的老子思想也定位为“贵无”,笔者认为这些主张在宽泛意义上也可以归属于“贵无”。,这里我们将辨析它们与裴頠崇有之间的关系。
(一)王弼贵无
魏晋时期最具理论深度和影响力的贵无论,无疑来自王弼。研究者也特别关注裴頠之批评与王弼贵无的关系,大多会认为裴頠表面批评王衍,实际却将矛头对准王弼。但结合史料和文本,这种判定并无可靠的依据。理由一:前文所举材料4虽提到王衍很重视王弼的“以无为本”而裴頠却非之,但裴頠首先非议的当是王衍而非王弼;并且前文的分析表明王衍彻底空无的“以无为宗”实际曲解了王弼本体论,那么裴頠是否连同王弼贵无也有非议就不无疑问。理由二:《崇有论》也无法提供明确论及王弼的文本内证(23)杨立华认为裴頠批评“以无为宗”是明确针对王弼的(参见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第93页),但此词其实更应被理解为针对王衍的本体论。。理由三:裴頠在不少地方反而对王弼思想有所吸收,比如其宇宙论的“自生”概念很可能吸收了王弼的说法,比如裴頠解老使用的得意忘言方式以及其谈“旨在全有”的“全有”实际也来自王弼解老(24)王弼注《老子》第40章曰:“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再比如其形式上主张的无为之治也可能与王弼有一定关系。所以笔者认为,王弼贵无未必不能归入老子那样的“真贵无”,从而得到裴頠的认可。
退一步说,即使裴頠不认可王弼贵无,他的崇有主张能否对王弼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先看王弼贵无论,如果我们体系性地去把握,它显然也“上及造化,下及万事”。概括地说,它包含了“以无为本—以无为用—(个体)有欲—(个体)有为有礼—(政治)无为之治”的完整层次,并且其所谈之“无”并非彻底空无,而是“无形无名”和“无心无私”。比照之下,裴頠的崇有论体系很难对它构成有效批判。
首先,王弼本体论之“无”乃是无名无形之道而非空无,它作为万物生化之基础,更像一种存在“背景”,而非宇宙论意义上直接产生万物的终极某物。而否定实有或空无作为终极产生物的裴頠“自生论”就只是宇宙论的阐发,不构成对本体论的真正批评。其次,王弼“以无为用”并没有否认“有”之存在与必要,而是试图在运作层面思考如何让“有”充分发挥其功能,最终在更好实现“有”的意义上突出“无”的重要性,即其所谓“将欲全有,必反于无”(《老子》第40章王弼注)。然而,裴頠忽略“用”的层次,其对“有”之存在与必要的强调未能推进到“有”之运作层面,如此又不及王弼深刻。再次,王弼认可百姓有自然情欲以及本具仁义,故而百姓必将有所作为并能遵从礼法,这一点同于裴頠;不过,王弼强调百姓性情应当自然发用才会复诚从礼,而裴頠推崇礼教却更加强调个人节制,反而阻滞了自然过程,容易产生玄学家警惕的虚伪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裴頠落后于王弼的反思。最后,王弼主张政治上的无为之治,认可“立名”(也即建立秩序制度)的必要而否认“用名”(即“任名以号物”)(25)王弼注《老子》第32章曰:“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防止治政者对百姓情欲有所扰动而破坏了其自然发用过程;裴頠形式上也认可无为之治,但实际操作还是偏重“用名”,主张积极的名教之治,那么他显然也未能吸收玄学家对传统儒家名教方式的批判反思,故也落后于王弼。所以总体看来,王弼贵无体系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程度(26)不少研究肯定王弼注解《老子》《周易》意在融贯有无,但为了说明其与后来嵇康、阮籍、裴頠等人的思想构成一种发展逻辑,他们又论证王弼之有无实际存在着分裂。如汤一介认为王弼哲学存在“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矛盾(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第45~47页),余敦康认为王弼体系中“有与无仍然分为两橛”(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第292页)。这些理解有刻意构造发展逻辑而误读文本的嫌疑。笔者以为,王弼贵无论在融通有无方面其实已有相对完善的论述,可谓“贵无而全有”。其不足只在对个体逍遥方面关注不够,而这却是后来嵇康、阮籍大力阐发的地方。, 裴頠崇有论不但没有对它构成实质性批评,甚至在某些地方与其相比还有所倒退。
(二)阮籍贵无
对元康名士生活方式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是阮籍,特别是后期的阮籍。后期阮籍居职朝廷,却口谈玄虚,不遵礼法,仕无事事;然而阮籍竟得司马氏宠信,在社会获得很高声望,直接诱发世人的效仿。比如西晋初期玄谈家王戎曾在丧母时“鸡骨支床”而有“死孝”之称(27)《世说新语·德行》第17条。,便有效仿阮籍之嫌;前文所举材料3,东晋史家将王衍之徒与阮籍关联了起来,王隐《晋书》亦记元康放达派“皆祖述于籍”,则我们可以认为元康名士实际就在效仿阮籍。不过,元康名士能否完整继承阮籍精神,却又可疑。比如东晋戴逵认为他们并没有继承真正的玄学精神:“然竹林之为放, 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 无德而折巾者也, 可无察乎!”(《晋书·戴逵传》)所以,裴文虽对元康效仿者的无为无礼有激烈批评,但考虑到他们可能曲解了阮籍,那么裴頠是否对阮籍本人也有所非议,便难以确定。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思考,就(后期)阮籍贵无的本义看,裴頠之崇有能否对其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
且看阮籍贵无。相较王弼,阮籍的思想体系要简略不少,他少谈形上理论而侧重形下之人事。首先,他基本不谈本体论“贵无”而只在宇宙论上坚持传统的“元气自然论”(28)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331页。。“气”作为万物基质,并非产生彼物的此物,则它并非回答终极产生者问题,故与裴頠的“自生论”不冲突;相反,阮籍言气化之“自然”,却又与“自生”接近。而由于他不谈本体,也便不会去谈论体用之“用”,这一点也同于裴頠。所以在形上层次,裴頠当无意批判阮籍,二人的理论甚至有所相近。
其次,论及人事,阮籍对个体逍遥和治政策略都给予了很大关注。
从个体视角,阮籍肯定人的自然情欲,他不同裴頠之“节制”,而是主张“无心”(只是无人为刻意而非彻底空无),从而保证本具之性情的自然发用。应该说,阮籍关于个体内在修养的根本精神乃对王弼性情自然之论有所继承,吸取了玄学家的反思,不是裴頠节制之论能轻易驳倒的。而为保持这样的无心自然,在外在行动上,阮籍既不取礼法君子的为名利而纠缠俗务,也不取隐士的清高遁世(《大人先生传》),因为他们在心灵层面始终有私心有二分,从而违背了自然。阮籍所期待的是游心人世,身不离世但心灵超脱,实现在世之逍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阮籍提倡入世的“无为”,而非隐遁不为。不过,由于无意追求名利事功,在现实效果上他也确实无主动作为而只是被动随从;进一步,阮籍又化被动为主动,坚持任情自然,结果竟不时与现实礼教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基于无心自然的根本精神,阮籍构想了一种“无为、无礼”的行动方案;他以为这样能与世俗和谐相处,但实践效果上却表现出对抗。可以说,阮籍的个体理论存在某种实践困境。元康名士直接效仿阮籍,也就同样继承了其与世俗的对抗;甚至他们还将阮籍无心自然的根本精神转换成了彻底的空无,加剧这种对抗。裴頠重新要求个体有为有礼并与名教相符,对彻底空无进行批评,如此他消解了个体与名教的对抗,但却是以牺牲个体生存的逍遥追求为代价,这样他实际没有回应阮籍关于个体逍遥问题的困惑,并没有为阮籍理论中的对抗提供有效的解决。
从政治视角,后期阮籍批判名教的态度非常激烈,其主张彻底的“无君论”,将名教施行视为对人类自然性情的残害。这里,他将王弼对名教的反思推到极端,将保存自然生命视为首要目的,而排斥一切形式的名教治政方案。如此他也正合了裴頠所说的“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阮籍这种只有批判而无建设性的极端说法当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裴頠倒退回传统儒家有为之治的应对策略,却又只能造成有无两个极端的继续对立,而无法真正解决阮籍的质难。对此,裴頠最应该去吸收王弼的无为之治思想。
所以,总体上看,后期阮籍确实在人事方面逐渐走向极端,但他的这种取向应该从玄学方向去理解和批判,而不可能被裴頠所倒退回的传统儒家立场所驳倒。
(三)其他贵无
史料还提到了何晏和夏侯玄对贵无论的影响,这些影响同样是无法得到史料和文本的坚实论证;但我们依然可以考察裴頠崇有是否对他们的贵无构成真正有效的批评。
前文所引材料3将何晏和阮籍并说为“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这个描述或适阮籍,却未必符合何晏。何晏喜好清谈,这是公认;但说其无礼、无为则并无依据。先说其作为,在其真正有高名于世的正始时期,何晏担任吏部尚书而主选举,其成绩在某些史书看来是值得肯定的,如《晋书·傅咸传》说:“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再加上他积极参与正始期间的改制活动,则何晏当非“尸禄耽宠,仕不事事”。又看其对待礼法,《晋书·五行志上》有记何晏喜欢穿女人衣服,有悖礼节;但除此以外,史书难见有关何晏“不遵礼法”的记录。如此,何晏对元康名士的影响当在谈玄而已。
何晏喜好谈玄,并以其才智与地位促成了正始玄谈的繁盛。而正始玄谈中最重要的成果则是何晏、王弼共同主张的“以无为本、以无为用”,这一点在前文所引材料4中已有所体现。王晓毅指出何晏贵无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早期《无名论》的用词和论证方式都还不成熟,经过吸收王弼解老后才达到王弼这般圆融(29)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27页。。但即使他在《无名论》中用并不成熟的原表空无的“无所有”去形容“道”,他的整体思想却还是想说明“用无”(30)何晏《无名论》:“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 参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下,马志伟审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1页。,也即“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这样,在根本意思上何晏早期的论“无”同于其后期吸收王弼解老后的论“无”。前文谈到王弼的贵无论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非裴頠所能批判,这一条应当也适用于何晏。
至于夏侯玄,前文所引材料2提及他时并非要针对其行为,而是针对其玄谈。就行为看,史料有记其任贤得当(31)《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用《世说新语》之言:“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且其应答司马懿之问时事时也表达了积极改制、简政敦教之主张(《三国志·夏侯玄传》),可见夏侯玄实属积极有为者。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何晏等人阐扬玄风、肆力清谈之时,出身将门的夏侯玄则更为留意经世实学”,而这在整体上是与夏侯氏“崇实忠烈”的家风相一致的(32)束莉:《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故其行为方面当不为裴頠非议。而夏侯玄同时是正始玄谈的重要人物,著有《本无》《道德论》;其谈玄论文已佚,仅见何晏《无名论》一句引用:“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33)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下,第411页。。仅由此句也可见,其所关注乃“有”之运作的基础问题,也即体用之“用”层面,与王弼主张相类,亦非裴頠崇有所能批判。
总之,正始玄学之贵无,无论夏侯玄、何晏还是王弼的思想,都有极其相近之处;他们在反思传统有为之治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倡“本无”,更加注重“崇本举末”而非偏重一端,这样的贵无论非裴頠之崇有所能批判,况且裴頠对他们的思想还有不少吸收,应当也无意去批判。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风行魏晋的贵无论思潮在其内部实际存在多种具有微妙差异的主张,不可笼统等同,裴頠明确批评的只是西晋中期已偏空无化的贵无论,而非针对整个贵无思潮。裴頠提出的崇有思想在理论层次上不够完整,也不够深入,因为它原本只为对治层次浅显的空无论;而在最高精神上,裴頠其实又推崇一种融贯有无的整全哲学,老子贵无甚至王弼贵无在很大程度上便与此相通。所以,裴頠对整个贵无思潮实质有着复杂的态度。同时由于崇有论的理论局限,他想要却未能对当时的贵无论进行充分有力的反驳,他无意并也不能对王弼和阮籍的贵无构成真正有效的批评。
若从魏晋玄学史的角度去看待裴頠的崇有论,其地位与价值应当如何衡量,当前研究的评价似有一定夸大,或认为它构成对王弼贵无的反动,或认为它构成对整个贵无思潮的反动,这在事实和学理两个层面都难以成立,它最多对作为贵无论末流的元康阶段之贵无有所反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适合被整合进“有无之辩”的正反合逻辑闭环之中。而按玄学史梳理,王弼贵无论其实已经相对完整,只是在个体修养全生方面论述不够;嵇康、阮籍则沿个体方向作了很大推进,即使其理论内含某种实践矛盾,他们在总体上还是期望一种自然与名教相契的个体逍遥;但元康末流则走向极端,直接逼显了二者冲突。裴頠的崇有论作为对治元康时期极端化的贵无而出现,它本身并未化解这种冲突,反而站在传统名教立场加剧了冲突。所以,虽然元康时期的崇有、贵无之争在思想史上不可忽略,但就裴頠理论本身的深度看,它实际是对相对完善的王弼理论的一种倒退,并且它也未能为新阶段的自然与名教冲突(特别在个体逍遥方面)提供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崇有论在“自然与名教之辩”的主题发展史中的地位也不宜夸大。
或者更好的处理是,我们并无必要给特定的一段思想历程强加某种类似正反合的逻辑结构,而只需客观描述思想发展本身固有的起与伏、常与变,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呈现特定思想事件的意义。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我们需要回到裴頠文本本身,回到当时论争的历史语境,才能准确把握崇有贵无理论的实质内涵。基于这种把握,再进一步结合整个玄学史的理论背景,裴頠崇有论所内含的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关切或能得到更好揭示:它意味着,东汉末年以来名教遭遇的挑战由内部的道德虚伪变成了外部的放达无为,原来其所承受的“改良”压力变成了“革命”压力,于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重建名教便成了新的问题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