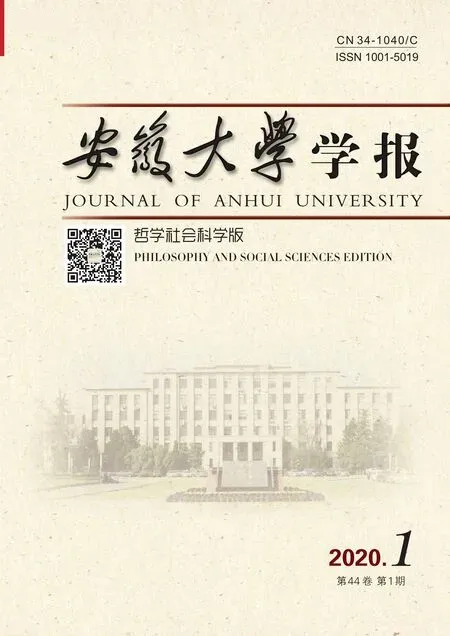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杜勇涛
地方史研究近几十年来已成西方汉学界的显学,其最大命题之一便是所谓“地方主义转向”(localist turn),即中国士大夫至少自南宋以来在其安身立命的考量中便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意识,而乡邦所在的郡县在他们的家国情怀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这方面的著作较多,经常引用的例子可参看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Peter K.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4. No. 2 (Dec. 2003), pp. 1-51.。然而直到今天,在这些有关“地方主义转向”的学术讨论中,“地方”的规模大小等级问题却鲜有明确讨论。“地方”有时指“府”,有时指“县”,有时也指涉包括多个府在内的较大区域(2)关于县级地方认同分析,参看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and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府级地方认同分析,参看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 No. 1(2001), and 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涉及多个府分析的著作,参看Steven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这种在规模上的模糊应该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地方史研究的初始阶段:最初地方史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的,它要克服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常见的,以整个中国为对象的泛泛而论和大而化之的倾向,它的主要对策因而就是将考察对象的地理范围缩小,提供更多的细节,从而在细节基础上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也往往能得出更新颖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规模的“地方”都总要比整体的中国更小,更便于操作;而“府”“县”这些既存的地方行政单位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史研究的选择对象。在古老中国大地上最有效、影响最深远,也最为人所知的地域划分方式毕竟还是行之千年的郡县体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方主义转向”之说兴起时,多数研究士大夫地方主义倾向的学者在此形势之下,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府”或者“县”作为考察的对象。因为“地方主义转向”说强调的是士大夫与国家之间“离”(separation)的因素,所以此处虽然对“地方”的规模仍未作明确定义,但对其立论则不形成妨碍:国家是明确的,由朝廷代表,地方则不管是府是县都可以和前者形成鲜明对比。但是随着“地方主义转向”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地方性”不仅牵涉到士大夫在国家和社会(宽泛而言,即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之间的位置,也牵涉到其在全国和地方(具体一地)之间的位置(3)Peter K. 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Steven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Chen Wen-yi, Networks, Community,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7).。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清楚地界定“地方”到底是什么、在哪里。从前那种出于方法论考量的,模糊地等同于府或县的“地方”概念,已经难以为继了。
定义地方的规模大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士大夫如何界定哪里是“国”、哪里是“家”,以及他们在地方主义的考量中如何划定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担当的范围。从明清时代的士大夫在地方社会里的诸多事功上看,“地方”的规模又从未一成不变过。既有的研究也充分表明,士大夫的地方身份认同,可以在包括府和县在内的多个规模层级上都有很活跃的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国家与社会、全国与地方等诸种关系的微妙所在。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深入考察应当是我们理解明清士大夫地方性的一个关键。在此意义上,1577年(明万历五年)徽州府各县之间的税赋纷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地方”规模的变动性及其背后原因的良机。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自宋至明,以府为单位的文集和方志持续不断地营造一种对徽州的自豪感。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居住在徽州府歙县(实为新安卫籍)的某人突发奇论,认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一场歙县和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由此引发。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双方互有攻防,请愿上书不断升级。而此案最终的判决中因为有歙县出身的朝臣的明显参与和影响,更导致其他五县士大夫的强烈抗议,最终在1577年导致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此案因此可以看作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认同感对于阖府地方认同的一次挑战。这个挑战如果和此前几百年徽州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以及此后徽州文化认同的强势恢复放在一起考察,应当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分析士大夫如何理解地方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徽州形象之构建与阖府认同
徽州府作为被地方行政体系所定义的一个单位,自北宋以后开始稳定下来。其边界、名称,作为“府”的级别,以及其所属六县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都未曾改变(4)徽州作为地方二级行政区划,所辖范围自公元771年(唐大历六年)起稳定为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和祁门6县,历宋元明清一直未变;“徽州”之名始自1121年(北宋宣和三年,见罗愿《新安志》卷1《州郡·沿革》),此后一直未变。。但是被徽州士大夫所感知、认同,并作为乡邦存在于他们的言说之中的徽州则经历了更长更复杂的变迁。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1577年的税赋纠纷爆发之前,徽州的形象伴随着一次次地方主义活动的兴起已经经历了数次调整(5)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转型”,参看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en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 2.关于这一时期徽州的地方主义活动,参看Harriet 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Prefecture 800-1800 (Leiden: Brill, 1989); Keith Hazelton, “Patri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Lineages: The Wu of Hsiu-Ning City, Hui-chou, to 1528”, i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37-169; and Liu Hsiang-Kwang, Education and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Hui-Chou, 960-180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徽州方志对这些活动的记载,见弘治《徽州府志》卷5。。南宋士人多以水土论徽州,即把徽州的独特之处建立在其山形水势以及由此决定的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元代道学大盛于徽州,道学学者们打着程朱故里的旗帜,把徽州重新定义为“东南邹鲁”。明代中期,日兴的宗族建设和宗族活动逐渐成为士大夫徽州论说中新的主题。1566年版的《徽州府志》最终将宗族作为徽州地方的另一形象标识正式载入方志。这些徽州形象的构建是叠加式的(6)杜勇涛:《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后来者,比如徽州作为道学或宗族活动大盛之地,在明清两代徽州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无疑最常提到,但是最初的徽州水土独特之论并未完全消失(7)参看弘治、嘉靖、康熙、道光各版《徽州府志》的“风俗”部分。。徽州的形象构建也并未在16世纪中期停止:1577年的税赋之争所发生的年代正是徽州商人渐兴,并即将在天下为徽州赢得“富名”之时。用西人包弼德(Peter K. Bol)的话来讲,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有其特色”(8)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pp. 52-53. 徽州士人对家乡形象建构的详细分析,参看Yongtao Du, “Locality, Literati, and the Imagined Spatial Order: the Case of Huizhou, 1200-1550”, Th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012: 407-444;杜勇涛《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前述徽州形象在晚明和清代文献中经常被提到,并有相当的一致性。可见徽州士人对其乡邦的形象构建是比较成功的。这个过程有两个特点和后来的税赋之争关系尤为密切,一是徽州形象的构建由阖府士人共同完成,并未见某一县独领风骚的局面;二是在徽州士人的乡邦想象中,国家与朝廷呈日渐后退之势。
(一)阖府共建的徽州认同
南宋时与基于水土的徽州论说同时兴起的,有一系列由地方士人主导的具体的乡邦建设工程(比如修建社仓、祭祀乡贤等)和对于“地方”本身的接近于理想化的热情颂扬。比如现存最早的徽州方志《新安志》的作者罗愿就认为地方对于人物的操行有最终的发言权,而以朝廷为中心的“天下”则不过是一个名利场:
壮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显名于时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乡百世思之者鲜矣。中古以来相矜以权利,有啮臂而去其亲,为间而焚其孥,临陈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顾所厚。其威则伸于敌矣,而不见信于族党。其位则列于朝矣,而不见誉于州里。激扬人主之前,矜视同列,得志富贵矣。而不可以见故乡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随宦留止,不能复还,使其子孙为羁人于四方。数世之后燕秦楚越矣,而况能使其乡百世思之者哉?(9)(南宋)罗愿:《罗鄂州小集》卷3《程仪同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87页。
稍晚的方岳(1199—1262)更进一步,认为地方内在必然地在道德上较朝廷或天下更具优越性:
圣有大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蛮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难。独何与?州里得之于其常,蛮貊得之于其暂。暂者易勉而常者难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贵,而不为乡士大夫所齿者矣。月旦之评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则愈难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妇子也。夫子之所以圣,不过乡党一书,而所谓治国平天下者无余蕴矣。(10)(南宋)方岳:《休宁县修学记》,(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209页。
这些有关地方的大胆言论或许正表现了“地方主义转向”初始时期,士大夫刚刚发现“地方”这个新的社会空间时无法掩饰的激动。这些言论的倡导者和发布者基本上都是有功名的士人,比如歙县罗愿(1136—1184)、休宁程泌(1164—1242)、祁门方岳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徽州的水土本身便很独特,并足以令他们感到自豪。罗愿在《新安志》中就认为徽州山高水急,故而士人适合做谏官;山限水隔,故而男子耐劳女人守节。程泌则认为,徽州“其山峭刻而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灵而吞水液也,往往方严而劲正,耻谀澜而疾回奸,其民则尚气好斗好讼,其士大夫则尚气好义,可杀可僇,而英气毅概凛然而莫干。故其出任于时也多为材御史,否则为真谏官。此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独今为然也”(11)(南宋)程泌:《洺水集》卷12《祭汪给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391页。。罗愿在《新安志》中也提到徽州六县风土人情的差异。但是宋代其他的文献中鲜有论及各县自身的特点及各自的身份认同(12)宋代徽州的县志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后来的县志有追述,可参看道光《婺源县志》序。。我们没有见到现存的宋代徽州县志,如果后来的县志中提到的宋代县志可以为据的话,则或许宋代徽州真的有过县志,但是至少不是所有的县都有自己的县志(13)休宁和歙县宋代就没有县志。。最大的可能是宋代徽州各县基于县本身的认同感尚未起步,而地方意识仍多以徽州府为附身。所以朱熹虽然出自婺源县,却总是称自己为“新安朱熹”,在给徽州士人的信中也以“同郡朱熹”落款(14)参见朱熹《求放心斋铭》,《新安文献志》卷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593页;朱熹《与汪伯虞书》《答汪太初书》,《新安文献志》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151页、152页。。
元代徽州“东南邹鲁”的言论多以徽州是程朱故里为立论根据,同时强调徽州士人对程朱理学的笃信和守护。诸多论说中以赵汸(1319—1369)的阐述最为精简:
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15)(元)赵汸:《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287页。
这一轮徽州形象构建的背景是元代的异族统治和多数汉人士大夫入仕机会的丧失。在此情况下,他们作为士人的身份不得不依赖于“学”。元代徽州最举足轻重的学者,也是对此期徽州形象构建出力最大的学者,都被载入了明代第一部《徽州府志》的“儒硕”一门(16)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儒硕》。更全面的徽州道学学者名单,见(明)程曈《新安学系录》。。这些学者多出自休宁和婺源,正是后来1577年人丁丝绢案中领头和歙县对抗闹事的两县,比如陈栎(1252—1334)、程若庸(js.1268)、倪士毅(fl. 1330s)、朱升(1299—1370)、赵汸 (1319—1369)皆出自休宁,胡炳文(1250—1333)、胡一桂、胡方平皆出自婺源(17)当然,其他县也有道学学者,如歙县的郑玉(1298—1358)、祁门县的汪克宽。。他们对朱熹的称谓(“郡先师”),和对自己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命名(“新安”),都说明这些学者认同徽州府,而非某县。婺源县有数量可观的道学追随者,或许可以借着朱熹的大名标榜一种基于婺源县的地方认同,但是这种潜在可能性并未被挖掘利用。阖府认同在元代徽州仍是主流,至少在其最有影响的士大夫中是如此。
以宗族论徽州的兴起当然也和道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但是前者涉及更多人物、更长时间,上述主要道学学者多数本人就是积极的宗族活动家。更为重要的是,宗族建设和宗族活动从道学运动中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引导,从而越发迅猛。到明代中期,诸如请名人为族谱作序以显亲扬名,或以一族为单位与他族展开词讼等宗族间的竞争已经非常频繁。此类现象正契合于韩明士(Hymes)对宋元时期江西抚州的宗族文化所做的描述,即族群意识从前是私事,现在则变成了公开领域内讨论、评介并宣扬的事情(18)Robert P. Hymes, “Marriage, Descent Groups, and the Localist Strategy in Sung and Yuan Fu-chou”, i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Watson (Berkeley, CA:1986).。在徽州,此类竞争尤其激烈,而其最明显的证据则是通过编纂《新安大族志》之类的书对本地大族进行排名。最早的《新安大族志》由陈栎在1316年编定成书,以后二百多年又有多种版本继其后(19)陈书直到明代中期才付印。有关其付印问题的详细讨论,参看Guo Qitao, “Genealogical Pedigree Versus Godly Power: Cheng Minzheng and Lineage Politics in Mid-Ming Hui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31, No.1 (June 2010), pp.28-61. 继陈栎而出的大族志或以续修陈志为目的,或模仿陈氏体例,但实施于较小范围。前者如郑佐于1549年编成《实录新安世家》,程尚宽于1551年编成《新安名族志》;后者如曹嗣宣仿效程尚宽于1625年编成《新安休宁名族志》。。
正式将宗族活动作为徽州的形象和特征接受下来是在16世纪,1502年版《徽州府志》已经在其“宫室”一门包括了徽州重要的宗族祠堂。关于徽州以宗族活动见称之类的言论到嘉靖年间也已经出现,当时的文人吴子玉就写道:
大江之南宗祠无虑以亿数计,徽最盛;郡县道宗祠无虑千数,歙最盛……姓必有族,族有宗,宗有祠。诸富人往往独出钱建造趣办,不关闻族之人。诸绌乏者即居湫隘,亦单力先祠宇,勿使富人独以为名。由是祠宇以次建益增置矣。(20)(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22《 沙溪凌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11页。
到了1566年,新版《徽州府志》增加了大量宗祠记载,并明确提出“惟宗祠以奉尝祖祢,群其族人而讲礼于斯,乃堇见吾徽而它郡所无者”(21)嘉靖《徽州府志》卷21《宫室》,《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该卷列出的宗祠数量超过200座,而其他类型的建筑总共才几十座(第420~424页)。。
到了明代中期,基于县的地方认同显然已经抬头。婺源县已有四部县志:元代两部,正德、嘉靖年间各一部(22)光绪《婺源县志》卷首《修志源流》。。休宁县也有了至少两部县志,最近的一部由原籍休宁、生长于北直隶河间府的程敏政执笔写成(23)程敏政提到“休宁旧有海阳诸志,多详于宋元略于本朝,本朝所修者又多附于府志,其势益略”。见弘治《休宁县志》凡例。。但是以宗族论徽州仍然是阖府士人的共鸣之作。上述第一部以徽州府为单位的宗族志《新安大族志》为休宁陈栎所作,前面引到的吴子玉也出自休宁。再后来有一部《新安名族志》,编撰者为戴廷明和程尚宽,参与编撰过程的10位学者涵盖了所有徽州六县(24)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次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台北:台湾大学,2004年,第237页。。受徽州知府之邀主撰1566年版《徽州府志》的是汪尚宁和洪垣,分别来自歙县和婺源县,在府志里正式将宗族活动接受为徽州的标志性形象应当是此二人的决定所致(25)康熙《歙县志》卷7《选举·进士》、卷9《人物》;道光《婺源县志》卷15《儒学·洪垣》。。所以应该说直到16世纪中叶,人丁丝绢案爆发前夕,徽州士人有着强健的阖府认同。没有迹象表明歙县作为附郭县在徽州形象的构建过程中一枝独大,也没有“县”“府”认同冲突的迹象。1492年版《休宁县志》的编撰者程敏政在1498年也编撰了著名的《新安文献志》, 收集大量徽州文人论著和外人论及徽州的文章。“府”“县”认同可谓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
(二)朝廷之渐退
考虑到徽州的名称、行政级别、地域范围,以及其属县构成都是由朝廷所定,我们必须说王朝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徽州的地方认同之中,为后来所有的关于徽州特性的论说定下最基本的框架。实际上,在《新安志》中,罗愿除了赞颂徽州的山水和风俗,也说到徽州近代以来“名臣辈出”,并且将徽州税额与邻近府县对比,试图说明朝廷对徽州征收赋税之重(26)(南宋)罗愿:《新安志》卷1《风俗》、卷2《贡赋·税则》,《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04页、7624~7626页。。其他跟朝廷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建制沿革、科举仕宦人物等在《新安志》和后来历次重修续修的府志中都居于显要位置。
但是宋明间徽州士人对于乡邦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又呈现出一个与朝廷拉开距离的趋势。南宋士人对地方热情洋溢的歌颂通过对朝廷在道德上的贬低来达到。甚至对于徽州山水地势的歌颂,虽然看起来和政治无关,却也可能导致淳朴的徽州百姓和昏庸的朝廷官员之间的对比。元代程文曾经对新任徽州府绩溪县主簿揭西斯作如下忠告:
惟其民风土俗则不可以不察也。徽之为郡,在万山中,地高而气寒,其民刚而好斗。绩溪当宣歙之交,尤为阨塞险绝处。国初有司者乘其新附,虎视而鹰攫之。民不堪命,遂起为乱。朝廷命将出师以讨之。堑山垒泽以为固,攻之不下。其人曰,吾非敢反也,纾死也。若许侯来无事兵矣。许侯者名楫,尝守徽,有惠爱于民。是时迁他官,诏召以来。许侯掉臂入其巢穴,众皆罗拜而出矣。人皆谓许侯贤于三军之师,而不知绩溪之民可以义服而不可以威屈也。(27)(元)程文:《送揭主簿之官绩溪》,《新安文献志》卷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275页。
元代徽州士人建构徽州本地之学统并用它来定义徽州形象之努力,和包弼德所发现的同时期浙江婺州士人的努力如出一辙,都是企图一方面“在朝廷之外寻找道德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为乡邦在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寻找支持(28)Peter K.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pp. 27-32.。在这些情况下,士大夫都是以在野的儒者身份出现的,虽然不处庙堂之高,却要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们称徽州为“东南邹鲁”,也是将其与先儒圣地并列,从而使它在文化上和道德上都更接近天下之中的地位。总之,“地方”是要在道德的权威上和国家分庭抗礼。
宗族建设看起来似乎纯属民间活动,并不对朝廷的权威形成任何威胁。但是如果宗族活动浸染了整个地方社会,地方上的大族之间不遗余力地争夺在本地的名望,则宗族活动也会进入“公”的领域,如同前引韩明士所说的那样。在徽州,宗族之间名望争夺的重要阵地之一便是通府的氏族志。一般情况下,每个宗族都立足于其所居之村,并以村名和姓氏共同定义该族。但是宗族之间争名夺利的大舞台却是整个地方社会:所谓名望是给通府的士人看的,也要由通府士人评说。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常用的一个比喻,即“人是生活在由他自己织出的一张网上,他对事物的理解亦由这张网规定”,我们可以说徽州士人的宗族活动就是他们织网的行为,而徽州作为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织出的网(29)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5.。
要使得宗族活动保持活力,这网必须能够给予人们足够的象征性的回报,从而使人们在宗族建设中有持续的孜孜不倦的热情,否则他们必将迁居到其他的“舞台”上,比如像中古豪门一样聚集在京城附近。所以徽州作为一个“地方”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立的社会空间。而《新安大族志》这样的给全郡大族排名的行为则证明徽州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与中古官修氏族志覆盖全国不同,徽州的这类大族志只管本郡,不及其他。其编纂指导思想一般是收录越多越好,所收大族一律以迁入徽州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名。所以一个宗族只要居地在徽,就有资格被收录;在徽时间越久,其排名就越靠前。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未必能够严格遵行,但这个编纂思想背后的理念则是各族只在徽州“地方”范围内进行相互间的比较,“地方”以外的涉及国家的因素诸如仕宦科举成就等于此无涉。换言之,“地方”欲将“天下”搁置,而使自己成为象征性资源的掌管者。徽州士大夫以本郡宗族之盛相标榜,其实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声明,他们认识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和朝廷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中心“本郡”,并且至少部分地将其关注的重心移向后者。
至此,徽州形象构建的过程与其他地方史研究已经验证的主题——地方精英与朝廷之间的“离”——大体契合。但是也必须指出,此处的“离”绝非彻底分离。宋代高喊地方之道德优越性的士人都是在朝官员。元代“东南邹鲁”的称谓之所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熹在全国范围内的崇高声望。而朱熹的声望,则又与1315年之后程朱理学被朝廷纳为官学密不可分。宗族建设和宗族活动作为道学学者们所推崇的道德践履,亦受到官府的提倡和保护。在徽州以及在别的地方,致力于宗族研究和宗族活动的士大夫很多都将他们在宗族事务上的努力视为“齐家”之属,亦即实现“平天下”理想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朝廷和国家在徽州士人的乡邦想象中确实逐渐退却,但却从未彻底消失。1577年的人丁丝绢案即将证明,它随时可能重新出现在前台最显要的地方。
二、徽州认同的危机
(一)作为事件的徽州府“人丁丝绢”案
实际上,在1577年的人丁丝绢案爆发前几十年,徽州府的人丁丝绢问题已经于1522年和1534年至少两次被人提及过。但其真正作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出现并导致重大后果则自帅嘉谟始。帅是新安卫籍,居歙县。万历《歙志》说他“少有心计,析入毫芒。精通巧历,稍稍猎经史诸书,略知梗概”(30)万历《 歙志·传》卷7《良民·帅嘉谟》,《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524~525页。。他在研究了天下各地户口税粮之后,发现合计8780匹、折银6147两的徽州府人丁丝绢在《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在徽州府项下,但是自明初以来却为歙县一县所承当(3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倡议首呈按院刘爷批府会议帖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2~253页。。震惊之余,他将这项发现公之于众,并在本县士绅的支持下开始了漫长的上书和告状的过程。
1570年,帅开始了第一步,上书“按院”(巡按御史衙门)和“抚院”(应天巡抚衙门),要求六县平摊人丁丝绢。两衙都很快批复,要徽州府调查此事(3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复呈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7~258页。。徽州知府则顺理成章地要求六县知县召集“耆民”“里老”商议如何应对帅的难题(3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倡议首呈按院刘爷批府会议帖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3页。。但官僚机构办事拖拉迟缓,徽州府的指示只在绩溪一县得以执行,而绩溪耆老商议的结果是对帅的要求一口拒绝(3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绩溪县查议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4~255页。。这样到了1571年,帅决定进京告状。户部对他的案子做出回应,仍是要求徽州府调查(35)(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复呈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8页。。但是也就在此时,帅自己也成了其他五县攻击的对象。他后来指证说自己自京返乡的路上遭遇袭击,于是为安全计决定暂不回郡,而是在外躲藏(36)(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复呈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8页。。接下来的三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1575年春,徽州府再次指示六县就帅案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讨(3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8页。。这一次六县均迅速做出反应,歙县当然衷心拥护,而其他五县则竭力反对。六县的反应都由县衙代表阖县“士民”向府衙提交(3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歙县士民交呈本府批县转申鲍院公文》《兵道奉按院鲍爷批府查议牌面》《婺源县查议申文》《绩溪县查议申文》《休宁县查议申文》《祁门县查议申文》《黟县查议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9~270页。。但是双方似乎都意识到争端不会在本郡内顺利解决,因为到了年底双方“士民”都向兵备道衙门呈递了状子(39)(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歙民陈良知等赴兵道告词批府行县帖文》《婺民具告都院宋爷批府行县帖文》《绩溪县士民具呈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71~273页。。同年九月间,双方又都有“县民”为此案进京呈状(40)(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江子贤等妄诋黄册奏疏帖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14页。。
从技术上讲,纷争的焦点是赋役征收以何为据的问题。歙县方面认为应该以《大明会典》为依据,因为《会典》明确指出人丁丝绢属于徽州府项下丁税,而没有指明必须由歙县承担,所以人丁丝绢当然要由六县分摊。歙人并且提供佐证:大明别处府县凡是人丁丝绢列在某府项下的,必由阖府各县分摊;若征于某府内具体某县的,则《会典》必有明文。不仅如此,户部勘合下到徽州府时,都将此项写明“人丁”字样,但本府文移却莫名其妙地将“人丁丝绢”改作“夏税丝”,然后“一并于歙征纳”,但是最终移文户部时又重新改回“人丁丝绢”(4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具呈本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5页。。所以,帅嘉谟最初的上书以及后来歙人的状子中都指出,此项征收在其肇始之时必有蹊跷。至于蹊跷为何,据歙县里老回忆,是国初阖府人丁丝绢征收甚急,知府情急之下请歙县暂时代为缴纳。哪知后来府衙书手俱出五县,遂上下其手,将此做成永役(4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歙县士民交呈本府批县转申鲍院公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9~260页。。
而其他五县则要求以黄册以及传抄自黄册的府志为据。他们坚称歙县人丁丝绢载于黄册,征收二百余年,已成“祖制”,不得更改。至于此项征收诸多可怪之处及其缘起,五县人亦自有源自五县里老的说法:国初查勘赋税,歙县比附元代定额亏欠正耗脚麦若干石,故按亩科丝,以补亏麦(4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绩溪县查议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63页。。
如此看来,要解决此案,必须探明该项人丁丝绢的起征缘由。而唯一可能存在的能证明该项起征缘由的证据,是南京后湖所存的黄册原本。因此到了1576年初,双方都已经摩拳擦掌,上书请愿,要求到南京后湖开库查册(4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帖歙县查册公文》《五邑赴都院告准查册词》《帖五邑查册帖文》《兵道奉都院委官查议牌面》《五邑奏查黄册疏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94~295页、296~298页。。双方请愿经由徽州府上达户部,经户部批准,由歙县、休宁和婺源共同派员三人于1576年夏天到南京查册(45)(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委官查册牌面》,《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99页。。
同年秋天,查册结束,所得结果报回徽州。但是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黄册上写明“丝绢”在歙县的开征时间是1382年,但并未说它到底算是丁税还是夏税,或者为什么只在歙县一县开征(46)(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户部查回后湖六县黄册》,《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06~309页。。这就把丝绢问题带进了死胡同。然而大约就在此时,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歙县殷正茂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刚刚上任的殷尚书将丝绢案上奏天子,请旨(其实当时是张居正当国)后责令应天巡抚、巡按及兵备道各衙门与徽州邻府协调,共同派员,先将徽州府各项钱粮“总算总除”,然后再照各县人丁数和地亩数决定丝绢负担。殷的处理原则是“赋役均平”:“如六县照各丁粮俱已均匀,而丝绢之坐歙县者已在均匀数内,则丝绢应征歙县一县”;“若歙县各项钱粮已抵过各县均平之数,而丝绢独累在均平数外,则合行均派”(4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户部借户科条陈事宜议行均平疏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11~313页。。
所谓“赋役均平”是当时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的总体原则,所以徽州府的人丁丝绢纠纷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赋役改革的一部分(48)[日]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4~156页。。这样看来,此案牵涉到对黄册记载的质疑和修改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黄册所载仅为实际征收数额,本来就和“均平”无关。在徽州,关于人丁丝绢的纠纷很快就变成关于“黄册所载能否改动”的问题(49)(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帖歙县查册公文》《五邑赴都院告准查册词》《帖五邑查册帖文》《兵道奉都院委官查议牌面》、卷4《江子贤等妄诋黄册奏疏帖文》《五邑乡宦辩江子贤妄诋黄册呈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94~295页、314~319页。。五县士民指控歙县“以一豪权敢扰乱而诋毁”祖宗成法,并将殷正茂和帅嘉谟同时列为攻击指责的对象(50)(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五邑乡宦辩江子贤妄诋黄册呈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18~319页。,其用辞则日趋激烈,甚至出现“誓死不代歙纳税”之类的话(5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五邑人民惊派均平急告院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21页。。
对徽州府各项钱粮的“总算总除”和“通融均派”在邻近的太平府进行,并于1577年的春天结束。核查的结果是:根据赋役均平原则,歙县在丝绢项外已经多负担2657两,若加上丝绢,则在此基础上更多负担3300两(5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各官会议均派回院申文》, 《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26页。。抚院按院两衙建议从歙县其他各项负担中转移3300两至五县,从而歙得减负之实,而不动丝绢之名。如此处理,本案几乎可以结案了。但是户部不同意,其理由也堂堂正正:歙县争的是丝绢,又不是别项!若照此议实行,岂不导致更多赋役不均?所以户部议定,将歙县多负担的3300两丝绢悉数抽出,分加给五县(5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户部坐派丝绢咨文并府行县帖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28~330页。。
这一决定可谓歙县的完胜。帅嘉谟最终荣归故里,被歙县士民“花红迎导”,受到英雄般的欢迎(5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2《叛民帅嘉谟倪伍徐宗式朱汉卿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68页;(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报舒府台揭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5页。。然而1577年夏天,户部咨文发到徽州府并由府转发到县时,骚乱很快便发生了。在婺源县,部文到达时正值暂时署理县务的徽州府通判徐庭竹上京进表。于是当地士民“一时愤激,簇拥县衙,连名具告,乞求申达”。聚集的人群有“大书歙某变乱版籍,横派丝绢,贻毒五县”者,所谓“众情汹汹,奔走呼叫,自暮达旦”(55)(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报舒府台揭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5页。。次日,徽州府推官舒邦儒自府城起行前往婺源县代理县事。行至休宁县,被“合县里排耆老民人”拥堵在路上,并被迫接受他们的联名上书。书中称休宁“通县人民耕者弃农贾者罢市”,以及“五县会议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甚至威胁“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56)(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休宁县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1页。。几天后舒推官到达婺源,又被五千余婺源士民“遮道哀告”(5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舒爷署县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8页。。与此同时,徽州知府徐成位闻变后亲赴休宁。此时休宁县城已经聚集了几万人,“鸣金约党,竖旗结盟”,导致“道路禁阻,文移隔绝”,甚至“该府一申一揭,众必索验之而始发”(5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礼科等给事中彭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2页。,形势几乎失控。
婺源县的形势更有些变幻莫测。舒推官到县刚刚两天,便有谣言称歙人买通婺源县吏员,欲将无理丝绢正式“认纳”。于是群情激愤,拥入县衙,捉人扭打。本县生员数人甚至占领紫阳书院成立议事局,并酝酿在全县筹措经费备用(59)(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7《抚按题覆招拟并刑部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82页。。郡内其他地方亦有暴力事件发生:五县之人在歙县遭打,而歙商店铺在五县者也屡屡被抢(60)(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本府禁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40页。。
据形势看,民变已然形成。情急之下,徽州府和兵备道都发表文告,对各县士民晓之以理,戒之以罚。休宁婺源两县领头闹事的生员连同歙县帅嘉谟一同被抓。同时朝廷也勒令府道各衙严查五县骚乱中的幕后乡绅。但同时,各级官员也很快协调行动修正前令,杜绝乱源。到了1579年,虽然抓捕幕后乡绅黑手的行动不了了之,对于人丁丝绢纠纷的全新解决方案却已出炉。按照新的方案,原有歙县人丁丝绢不动,但是歙县项下其他赋税酌减2000两,而五县亦不加赋(6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奉院道豁免均平公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6~407页。。归根到底,是朝廷承担了一个损失,摆平了各方。就纷争各县而言,可谓皆大欢喜。
(二)徽州认同的破裂
放在徽州地方主义的历史背景中看,丝绢事件可以说是徽州认同的破裂。如果把被地方行政体系所定义的徽州比作“(政治经济)基础”(infrastructure),再把被感知、认同的徽州比作“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这个上层建筑显然是比较脆弱的。丝绢案发展的初期,双方还多少存有一些同袍之感。1575年帅嘉谟上书中仍提到“六县犹六子”,而将均输比作诸子共赴家难(6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复呈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8页。。五县上书中也常引用同样的比喻,但得出相反结论:兄弟分家有多有少本是常事,歙县承担丝绢既已日久成习,不妨就此担当下去(6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2《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91页。。显然,此处同袍之义已成讨价还价之资。随着纷争的持续发酵和冲突的升级,仅存的一点阖府认同感迅速消失殆尽。五县上书请求后湖查册时就提出要求,若是查到最后丝绢确属歙县本分,“乞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6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2《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祁门县里排黄邦泰等呈府揭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76页、285页。。最后户部主导的解决方案从上压下引发民变之时,五县与歙县几成死敌。歙商店铺在五县被抢,其情形和徽商在江南各地因富名遭嫉妒被抢如出一辙(65)Yongtao Du, “Lesson of Riches: Mercantile Culture and Locality in Late Ming Huizhou”, Ming-Qing Studies, Spring 2010, pp.33-59.。如果民变的几天内所发生的暴力行为尚属形势突变、群情激愤所致的话,后来的几个月内追捕幕后黑手的运动则充分表明双方之间怨恨之深。揪出五县幕后乡绅黑手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上层,最终可追溯到张居正。张欲利用此案除掉他在朝中的政敌、前几年刚刚被他逼迫致仕的余懋学(66)[日]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7~123页。。徽州知府虽然不愿为张所用,竭力将事件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歙县士绅却不断煽风点火,逼迫府衙彻查(6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歙民架诬倡乱告词》《歙县生员呈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8~360页。。婺源县领头闹事的生员何愧吾事后被捕,最终死在狱中。他死前留下遗言,说“死不足惜,而歙仇之未复则可惜也”,要五县士大夫“与歙人鸣不戴天之仇”(6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何愧吾临终说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8~409页。。
随着阖府认同的破裂,过去构建徽州形象和徽州认同的历史突然之间也成了问题。丝绢纷争爆发前夕,徽商行迹已经遍及四方,徽州的富名也正冉冉升起。这些在徽州士人笔下一般都是阖府的特征(69)Yongtao Du, “Lesson of Riches: Mercantile Culture and Locality in Late Ming Huizhou”.,1566年版《徽州府志》也将“以货殖为恒产”列为整个“徽郡”的风俗之一(70)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第66页。。现在,徽商的富名忽然变成了拖累,双方都把它扔向对方(7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五邑乡宦尊制呈词》、卷4《江子贤等妄诋黄册奏疏帖文》、卷8《乡宦奉都院宋爷书》, 《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05页、316页、396页。。而历次由各县士人共同编撰的《徽州府志》也从阖府认同的化身变成了争议所在。1502年版的府志,因为是入明后的第一部府志,记载着(由黄册转抄而来的)人丁丝绢份额,所以它的可靠性忽然遭到歙县士人的质疑。歙人给出的理由是该志主撰汪舜民为婺源人,所以很有可能捏造故事,歪曲丝绢事实,陷害歙人(7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3《帅嘉谟诋蔑黄册告词》、卷4《江子贤等妄诋黄册奏疏帖文》, 《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10页、315页。。1566年版的府志中有一处言及丝绢之可怪,但毫未提及六县均摊的要求(73)嘉靖《徽州府志》卷7《食货志》,第179页。。现在事态变了,五县士人也开始质疑其可靠性:该版府志总裁汪尚宁是歙人,所以这一处言及丝绢的必是总裁“附入私议”(7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休宁县查议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66页。。
因为丝绢之争关乎六县赋役分担,所以这个事件似乎可以理解为六县各自因为物质利益相争不已导致阖府认同的破裂。但是如果细究所争的具体问题(即丝绢),则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所争的税额并不高。对歙县而言,即使得到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即丝绢由六县分摊,则歙县能少交3300两丝绢银。这在嘉靖年间只占歙县正常赋役的3%左右(75)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列有徽州府及六县的税收定额表(第208~210页)。。但是歙县在此期间又常负担一些“不时坐派”,比如所谓“新增军马钱粮以防虏患”一项,在1552年一年就征银11577两(76)嘉靖《徽州府志》卷 8《食货志》,第190页。。无怪乎五县乡绅在和此案有关的一封信里坦陈,单就银两数量而言,所争胜负之间确实出入无几(7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湖广等道御史唐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4页。。南京湖广道御史唐裔,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在奏议里发出类似感言(7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湖广等道御史唐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4页。。即使是歙县的很多“缙绅先生”“三老豪杰”等等,在最初听到帅嘉谟有关丝绢的发现时也都反应冷淡,以为不值得一究(79)万历《 歙志·传》卷7《良民·帅嘉谟》,《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4册,第526页。。
另一方面,丝绢事件中所见“县的意识”也有些不平常,因为纷争的一方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县,而是五个县因为暂时的公敌歙县站到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五县的民变(尤其是在休宁和婺源)是由躁动的生员阶层挑起的(80)这一现象很契合明末士风, 别处另作讨论。。在婺源,挑事的两个生员“妄写小贴百十余张,书开‘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等语,遍贴乡市”(8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7《抚按题覆招拟并刑部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82页。。就歙县而言,本县意识当然更明显些。但是即使如此,帅嘉谟个人出风头的因素也很明显。殷正茂力挽狂澜,歙县取得完胜之后,帅嘉谟结束自我流放,凯旋归里。虽然帅本人连个生员都不是,却“以本邑津贴之资,输纳冠带,妄自夸张,使合邑士民鼓乐彩仗道迎于白昼通衢,以炫耀梓里”(8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抚按会题疏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0页。。所以整个事件所展示的与其说是“县的意识”之强大,倒不如说是徽州通府认同之虚弱:只不过一点微小的物质利益,一个未必强大的竞争对手,加上几个近乎滑稽的挑动者,就将它颠覆了。
(三)朝廷挽救地方认同
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徽州士人(以及民众)阖府认同的危机中,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了彰显。帅嘉谟最初的上书中即高调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帅嘉谟具呈本府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55页。。歙县士民后来的请愿上书中更殷切地呼吁“六邑之人皆国家赤子”,所以在赋役征收上要一视同仁(8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歙县士民交呈本府批县转申鲍院公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260页。。类似的用词在五县的上书中也屡屡出现(85)(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乡宦送本府萧爷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90页。。
各级朝廷命官在丝绢纷争过程中也很乐意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1576年年末,对于徽州府赋役的“总算总除”正在邻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的时候,都院(即巡抚衙门)向徽州府发文即指责纷争双方“以同郡之民自分胡越”(86)(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都院行府均派宪牌》,《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19页。。从都院衙门的角度讲,徽州六县当为一体。徽州知府徐成位对此当然毫无异议。民变之后不久徐即提请上司,在重新考虑丝绢问题的解决方案时,要把徽州当作一个整体考量:“均徭者乃一郡之利非独一邑之利。”(87)(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徐太爷复请改议均平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68页。参与善后过程的各衙各官亦多持此见。比如户科都给事中光懋的条陈中就说到“休歙等六县同一府治,并称饶沃,岁办钱粮岂可有过多过少之弊”。抚院按院在协商之后也回复户部,认为解决丝绢纷争,必须公平地考虑双方的利益和情感(8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7《抚按会题丝绢疏并户部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73页、375页。。
在民变爆发的1577年夏天,面对急迫的形势变化,各级官员都呼吁徽州士民以徽郡“东南邹鲁”的声名为念,保持克制。(徽饶道)兵备副使冯某在初闻徽州骚乱的消息后,立即发布出巡徽州的告示,文中委婉地劝慰当地民众,声称虽然对报告所说事件“未委虚的”,但是“谅尔乡号称邹鲁,宜不至此”(89)(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兵道出巡告示》,《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40页。原文未注明此兵备副使之衙属。按《明史·职官志》有“徽宁池太道”,但未明言有兵备职责。康熙《徽州府志》卷1《舆地志上·建置沿革》载,嘉靖四十五年“四月,改广德兵备道为徽饶兵备道,分司于衢州”(《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212页)。据此臆补,可再考。。为了给事件降温,徽州知府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写给五县某乡绅的信中表达了对徽州“以礼乐之乡而蒙不韪之名”的忧虑(90)(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徐太爷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97页。。
如此,当徽州士民对阖府认同弃之不顾的当口,各级官员却呼吁他们珍惜共同的经历和处境。当然,此处官员们试图挽救的徽州阖府认同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他们是出于维持“纪纲”的考虑,所欲挽救的也更应该算是地方行政单位意义上的徽州(9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礼科等给事中彭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2页。。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公平”“同郡之民”等等都要服务于“治”的目的;拯救“东南邹鲁”的声名是为了把徽州更牢靠地固着在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要抬高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出于同样逻辑,基于山形水势的徽州风俗,比如“刚而好斗”“不可威屈”等等,也都在民变后官府高层讨论对策的时候,被引为必须谨慎行事而不可轻易弹压的依据(9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抚按会题疏文》《南京礼科等给事中彭一本》《本府回无豪右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0页、352页、371页。。
所有这些略带讽刺的言论和考量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在丝绢事件中徽州又被缩减到它最初所是的状态:王朝国家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地域单位。地方士人的“上层建筑”虽然轻易地崩塌了,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却站立得很牢固。如此一来,宋元明徽州士人苦心经营的、以地方为着眼点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经历几百年之后,一夕之间便又翻转过来。现在政治上的权威和道德上的优越性都转到朝廷手里了。在此形势下朝廷命官的自信,活灵活现地体现在对徽州赋役的“总算总除”结束之后“各官会议”以解决徽州问题的“申文”中:“一郡犹一家然,歙其长子也,五县其众子也;有司其父母也,院道其大父母也。”(9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各官会议均派回院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27页。
三、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
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规模上的可伸缩性。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上生成。在徽州,“县”和“府”最终都成为士民地方性认同的载体,和他们的热情所钟的对象。此事件过程中当事人所用的“桑梓”一词,在规模上从未有过清楚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它和现代汉语中的“乡土”一词一样模糊)。这种语义上的模糊甚至令很多当事人都产生迷乱:整个纷争过程中殷正茂都是以歙人身份出现的,也被纷争的双方都认作歙人。但是骚乱之后问责过程中,却有御史上奏,指责殷“陷害乡曲”,显然是把他算作徽人了(9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殷尚书自陈疏》,《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4页。。当下我们在地方史研究中对“地方”规模大小的模糊,看来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上的当事人!
这种模糊性也是一种可变性。这对于出门在外的“乡人”来说,当然可以在构建“同乡”网络方面提供诸多便利。比如说,清代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的一个在外侨寓的人,至少可以在省、府、县三级的同乡组织里寻求帮助(95)Peter K.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p. 42.。明末北京的“歙县会馆”在清初改为“新安会馆”,但是到了乾隆年间又改回“歙县会馆”。甚至在最终改名“歙县会馆”之后,它仍然接受徽州其他五县侨寓商人的捐赠(96)Yongtao Du, The Order of Places: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the Huizhou Mercha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chapter 3.。
但同样是这种可变性,也使得地方认同很难被固着在任何规模层面。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如果有机可乘,“乡人”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的地方认同从一个层转移到另一个层,或者让几个层面上的地方认同互相冲突。正因如此,在徽州,并不太强的“县的意识”就可以轻易地颠覆经营了几百年的阖府认同。这种地理上的模糊有可能是“地方”在政治上长期积弱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因为不管“地方”落脚在哪个规模层面,这个“层面”本身都是国家提供和界定的。像作为地方行政体系单位的“府”和“县”,其名称、边界、行政级别等等都是由国家设立、从国家获得的;在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里,国家又都设置了各不相同的赋役数额、科考员额等等。这样,至少对于同居一府一县的士人来说,他们在赋役、科举这样的大事上被国家的建构与政策绑在一起。如果考虑到宋明期间“府”和“县”在地方行政中体系中“临民”的角色,士大夫的“地方主义”长期附着在“府”或“县”的架构上其实也不奇怪。另一方面,在“省”一级,因为行政上的整合度较低,省级地方认同也比较微弱。这种状况直到18世纪中期“省”变成一个更加整合的行政单位(territorial entity)之后才开始改观(97)Kent Guy, Qing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所以地方认同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搭台、士人唱戏”的过程。“搭台者”在长期的地方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被“唱戏者”想象为不受欢迎的角色,并且在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日渐低调,但是它却从未消失。在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中,最后由朝廷出面收拾残局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我们认识到纠纷最初的起点(即丝绢)本就是朝廷制造的一项赋役的话,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朝廷在此注定要充当最后的问题解决者。
丝绢纷争以县为单位爆发的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在这个事件中的影响力。歙县的人丁丝绢负担并非由其所属的15个乡平均分担,而是有多有少,有的乡则全无。这一点,在事件当中休宁民众将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拥堵于路的时候,在某一个休宁乡绅给舒的上书里已经明确指出了(9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舒爷过休宁准休民告词申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1页。。显然,乡一级的地方认同和动员机制在当时即使存在,也不足以引发乡与乡之间因为丝绢负担分配不均而导致冲突。之所以如此,国家制度的建构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明代地方行政系统中,“乡”并不是一级行政机构,所以它也不具备“县”和“府”所具有的,能使得地方意识附着于其上的基本架构:乡一级的政府,乡一级的生员名额,或者乡一级的官学等等都不存在;“乡”从“县”所分到的赋役负担在县志府志里也不记载,所以也不算是正式的税额。与“府”“县”相比,乡一级的方志在明代很少,清代有所发展但绝不普及。其建制上的差异显然是原因之一。
在“县”一级,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所有可能导致群体性的政治行动的因子,比如县衙门、赋役数额、生员员额、方志,尤其是县学等等,在此都具备了。在丝绢案中民变最激烈的婺源和休宁两县,正是县学的生员充当了骚乱群体行动的组织者,而生员所依托的“学校”也正是他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寻找到的最大的道义支持(99)(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赴太平上各府诉冤说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5页。。这些因子具体强弱如何当然很难说清,至少就徽州府各县情况而言,在丝绢纠纷爆发之前它们也未必很强大。但是丝绢案充分证明它们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由此看来,国家和地方在帝制时代后期并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不是国家强地方必弱,地方强国家必弱,而是地方认同沿着和国家建制相同的方向发展,并且被国家建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国家不但从上面控制了地方,也在下面造就“地方”的根基。
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虽然丝绢事件中不乏打着“乡邦”旗号的激烈言论甚至暴力行为,但不管是“府”还是“县”都从未对任何人提出过绝对的“效忠”要求。“桑梓之情”虽然可以很强烈,但是相比士大夫对于朝廷的忠诚,从来都是退而居其次的。这在丝绢事件过程中的上书、奏议以及双方的往返信件中都有清楚的体现。民变爆发之前,双方士大夫都以其对于“乡邦”的责任感来为他们参与纷争提供道德依据。殷正茂在事后上奏中回忆自己当初涉足此事的动机时写道:“里巷亲邻呼号偏累,虽欲避之而不可得。”但他同时又说参与此事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赋役均平”,这和他作为户部尚书的职责并不冲突。事情发展到失控,归因于他在具体问题处理时考虑不周,是技术性失误(100)(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户部尚书殷自陈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6页。。从殷的辩解来看,桑梓之情虽然不能为他的错误开脱,至少可以使这些错误具有一些“人情味”。桑梓之情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同样的,在纷争的初期阶段,刚刚被迫致仕回到婺源乡居的余懋学也代表乡邻向徽州知府写信求告。余也用了桑梓之情来解释他写这封信的动机,信中引用当时著名学者罗洪先的话来说明这种责任的无所不在和不可避免:“所以应酬乡人之见责者,不于朝则于夕,不为之慰遣,则为之饮食。”(101)(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乡宦送本府萧爷书》, 《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93页。
随着事件的发展和冲突的升级,原本无辜无害的桑梓之情渐渐获得一些负面形象,成了朝廷命官履行职责(即其对于朝廷的义务)的干扰甚至阻碍。1576年秋,当“总算总除”工作在太平府进行之中的时候,五县士民显然预感到事情可能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是五县“乡宦”联名“辩述”,在其“呈词”中以极重的言辞指责殷正茂“知有乡邑而不知有朝廷,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102)(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4《五邑乡宦辩诉均平呈词》,《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24页。大致同一时间,一位退休官员在给都院的信中也提出类似批评,见《丝绢全书》卷8《乡宦奉都院宋爷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9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辩述”中,“乡邑”已经被贬低到“私”的地位,从而成为以朝廷为代表的“公”的领域的对立面。
到了骚乱发生的1577年,双方关于“乡邦”以及“桑梓之情”的言论已经处处蕴含着一种前设,即它必须服从于一种更高的道德命令。例如苏邦儒署理婺源县事,一路惊恐,刚刚到任便有当地乡宦汪文辉揭帖呈达。帖内汪乡宦先以“不忘报主廊庙”和事关“朝廷之法纪”解释自己拜揭之由,然后指责殷正茂“于歙宦虽为桑梓,而尚书则国之大臣,朦胧乱制”(103)(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报舒府台揭帖》,《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35页。。
是年秋季,局势稍微稳定,双方情绪也略趋平静。歙县乡宦于是联名致书五县乡宦,提议双方心平气和地讨论此事。信中说到:“孰无桑梓里族之心?”可见是把桑梓之情看作人之常情,故而又说到对此正确的态度是“以理酌情”(104)(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歙宦遗五邑士夫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89页。。这里提到“理”字,似乎使得关于“乡邦”的讨论多了一些学究气,但是这并不改变王朝国家在事件中的位置,因为双方都把所据的“理”等同于国家。歙县乡宦认为理就是国家之“典”:“苟出于典,虽始自今日亦不可改。”而五县方面,则有程任卿的自白。程是婺源民变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也是事后唯一被定死罪者。程在狱中写的自白坦陈整个事件虽有情绪因素,但最终必须遵循“理”:“理苟是也则在朝而公言之可也,在野而私言之可也。”至于理是什么,程则说“盖维持乎理,所以维持乎国是也”(105)(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乡宦上徐太爷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3页。“理”的辩论并未解决争议,因为歙县士绅认为《大明会典》是国家之“典”,而其他五县士绅则主张黄册是国家之“典”。。同样,事后御史参奏问责殷正茂,多指出他突破了界限,“为桑梓地过耳”(106)(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湖广等道御史唐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354页;(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2《叛民帅嘉谟倪伍徐宗式朱汉卿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68页。。可见对于士大夫而言,“乡邦”和“桑梓”属“情”,朝廷国家属“理”,前者对于后者居于次要地位,是普遍而且从不质疑的观念(107)这一观念在中国语境中是天经地义的,但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其差异就很明显了。此问题别处另论。。
略具讽刺意味但也发人深省的是,事件以双方皆大欢喜的方式结束之后,五县士绅上书抚院衙门请求对陷狱的生员从轻发落时,又说到若能蒙恩“斯民不胜幸甚”(108)(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8《乡宦上抚院胡爷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01页。。“斯民”这个词在《孟子》中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的,代表了具有政治诉求的百姓。此处用了这个词,不禁令人遐想:自从秦汉一统天下千年以来,不断在政治地位上遭到贬抑的“地方”,是否在宋代以后兴起的“地方主义转向”中又被重新赋予政治上的新含义?(109)参看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3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年)。汉代对地方风俗常有歧视,认为风俗只关乎一地,故而难免偏狭。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Mark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192-212.但是即便有,应该也是很小的。丝绢案冲突的生死关头已经过去,士大夫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提出带有政治意味的“斯民”二字,显然已经无关大局了。
四、最后的讨论
人丁丝绢案当然没有彻底摧毁徽州的阖府认同,此后不久它便恢复,并且似乎更加强壮。明清易代之际,凤阳都督马士英曾调贵州兵入卫,途经徽州时,因军纪溃烂几成兵痞洗劫富郡之势。危急时刻,休宁乡宦金声联合各县士大夫组织民兵,以“徽郡”之名抵御黔兵,救乡郡于危难(110)关于徽州士民在明清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之中展现出来的阖府认同,参看Yongtao Du, “Lesson of Riches: Mercantile Culture and Locality in Late Ming Huizhou”.。清代徽商极盛时期,侨寓各地之徽州商人也常常以徽郡之声名互相砥砺,互保互助。从人丁丝绢案之前徽州形象的建构,之后阖府认同的恢复,甚至纷争期间六县士民对于乡邦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徽州地方认同显然对于徽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人丁丝绢事件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比如发生了利益的冲突,则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
帝制时代后期的乡绅和国家对于社会秩序常常享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看法,乡绅也常常协助朝廷拓展其权威和影响。而乡绅和朝廷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性当然得力于宋代以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比如触角伸到县的发达的科举考试制度等。在这种情况下生发出来的地方主义,很难相对于国家保持独立。尽管地方主义的言论有时把地方的地位抬到很高,但是士大夫的地方主义活动其实都只是在国家认可、提倡,但又力不能及的地方施展一下。徽州在宋明间的形象构建正可以印证这一规律。
对于国家而言,上述情况无疑有利于其权力整合。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于是,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一种王国斌(R. Bin Wong)所说的“同构性”(fractal)特征,即同样的社会秩序可以在任何规模的空间层面上确立或重建,而在所有的层面上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精英分子都掺杂在一起(111)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1.。地方精英和国家之间当然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些分歧都不大,都可以调和。研究“地方主义转向”的学者们所发现的国家和地方士绅间的分歧大都属于此类。这类分歧有时候会很显眼,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用王国斌的话说,就是士大夫从未“清晰地划定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空间”(112)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p.107.。于是,“地方”成为一个士大夫自发地,以或多或少被国家认可的方式,实施执行早已被国家倡导的各项事业的社会空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性,加上制度上对地方和全国的整合,使得地方不仅是构建帝国大厦的砖瓦,而且成了帝国“具体而微”的缩影。所以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