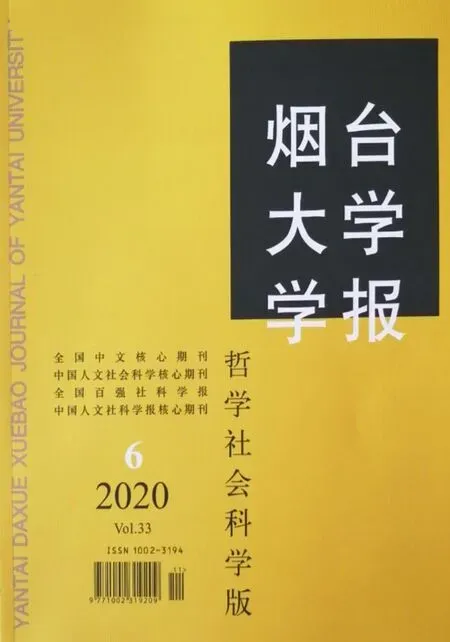康有为智性论统摄下的成圣理路及其困境
钟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一、积微成智:作为人性根基的智与学的工夫
晚清是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之时,清中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识时大多是抵触、被动的。经过顽固派、洋务派大员对西学态度的逐渐转暖,维新士人们大多主张积极采纳西学作为强国手段。在物质救国论影响下,西学中的物理、格致等实用科学尤受知识分子追捧,康有为也不例外。康有为以古代“气”论为参照,“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冻者为阴”(4)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33页。, 在“以元统天”思想之下借用西学概念,细化出气、力、质、形、光、声、体、神八种性质作为物之理,杂糅出一个以天为根本、以热为动力来源的类气宇宙观。“凡物热则生,热则荣,热则涨,热则运动;故不热则冷,冷则缩、则枯、则夭死,自然之理也。”(5)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演说》,《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59页。冷热既是气的属性,又是天理本身,在万物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热生物、冷枯物的生命力。人作为宇宙间一物也受此生成方式影响:“湿则仁爱生,热则智勇出。积仁爱、智勇,而有宫室、饮食、衣服以养其身;积仁爱、智勇,而有礼乐、政教、伦理以成其治。”(6)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5页。这类物理生成性对人性发挥着“如磁之引铁,芥之引针”的功用,具体表现为热力涵有多,人便义、信、勇,冷力厚人则退缩、怯懦。这样的湿热之气甚至能造就三皇五帝。与此同时,仁与义还能反过来成为热之生生能力的源动力。天道的生生在人道表现为对仁的普遍追求,仁义作为热力增长的动力因又进一步促进宇宙的和谐生生,最终,天—热(气)—人形成一个开放链环。之所以是开放的,是由于存在多种因素对链环产生影响。康有为将这种因素指向人,亦即人性,他认为正是人对“性”做的工夫胞育出改造天人关系和世界状态的可能。
早期康有为的人性论经历了试图消解对立的阶段,他意欲弥合自孟荀以来形成的人性善恶二分。“人之有生,爱恶仁义是也……爱恶皆根于心……存者为性,发者为情,无所谓善恶也。”爱恶只是人类欲求满足或不满足时的情感表现,在本质上并未触及人性层面。康有为这一观点并无太多新意,他接着指出“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将人基于欲求表现出的爱恶之情归结为“智”的选择。“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无智则无爱恶矣。”(7)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0-102页。智是人性的内在依据,爱恶是人性的外在表现。那么作为性的智如何影响作为情的爱恶?康有为指出,人性特征是善辨、善思的,这是判定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差别的标准,智是决定人善思善辨的人性基础。人类社会初期,“羲圣首出,创作八卦,包象蕴教,开物成务,民物之理备矣”,这时的“备”仅停留在嫁娶、渔佃等口腹层面,人智还“不能自已”。(8)康有为:《民功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68页。直到黄帝时期人类的智运用在“治”的事业上使得“民治大齐”时,智性水平才得到相应地提升。提升后的智又内在地影响着人对爱恶的判断及情感表现,是现实的、发展中的智在引导人性面对欲求时作出合宜的选择。从康有为的推演可以看出,他将性的善恶论简化为“爱恶论”,爱恶为情不为性,“智”能够引导爱恶向符合道德要求的方向发展,这为其后来“学”的成圣工夫预设了前提。
中期康有为秉承董仲舒关于性的“中庸”观念,他指出:
人之材性万品,略区为三:自上智、下愚外,皆中人也。如是者多,立教者因材而笃,当因中人之材性而教语之。(9)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21页。
性,中民之性……初禀天然之姿,受纯一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中人之性,在所习然。(10)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28页。
这时的康有为一改早期将性的善恶论简化为爱恶论的做法,开始以发展视角从人性本质来思考善恶的表现。他再度阐发孟荀性善恶论的精义:“盖善言性恶者,乱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检制压服为多,荀子之说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11)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4页。他将“性”理解为“名”的提法,名是“立教化之始”,立“性”是圣人为开展后续理论与制作而进行的名词建构。在人性的层级划分上,“性”特指相对于圣人之性与斗宵之性而言的中民之性,中民才是更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表现。在天然本质上,性无善恶的区分,一切分别只依赖后天教训使然。善恶只是性的表现,不可笼统地说性善、性恶,如卵可为雏,但不能说雏就是卵。性与善的本质区别在于:性是天然的质朴状态,善是王道教化的结果。性与善经过教化后表现为互显关系,无质朴之性则教化无果,无教化之工则质不能善。虽然性具有天然的质朴,但若没有后天的雕琢成善,其在名的层面也是“不真”,不能达到康有为所理解的真义、真情标准。这样,康有为几乎赋予了性善以绝对的后天工夫论特质。不过康有为人性论并未停留在对性之善恶的讨论上,后期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提升“智力”来引导性表现为善,以便在最终结果上帮助人类修性成圣进入大同乐园。
儒家传统中的智作为知识一直从属于仁、义等道德概念,康有为在“五运”皆重的同时将智的地位提升到仁义礼信之上,以智统仁义礼信,智作为人性天然具有的品质成为其人性论的根基所在。
研究工具为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被试个人信息、中文版的英语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量表和两个开放式问题。英语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量表由Dornyei(2005)编制,包括25个题目,分为四个维度:教师因素(题1-10)、学习者因素(题13-21,除去题18)、社会环境因素(题12、18、24、25)以及学习环境因素(题11、22、23)。开放式问题为“你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曾经采取何种动机调节手段?”
首先,智是天道对人性的赋予。康有为的宇宙观中不乏阴阳、理气:“阴阳者,气也;道者,兼理与气之名也。舍阴阳无以见道,舍气无以见理,而理则实宰乎气,人得是理以生。”(12)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31页。人得理即得气,即得阴阳,人的智也是理、气与阴阳所赋予,即“智也者,外积于人世,内浚于人聪,不知其所以然,所谓受于天而不能自已”(13)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0页。。
其次,康有为以智来容纳孟子的四端。“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智愈推而愈广,则其爱恶愈大而愈有节,于是政教、礼义、文章生焉,皆智之推也。”他还将仁智并举,指出“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仁智终始有其阶段性,上古以智为重,三代以礼为重,秦汉至今以义为重,后世将回到以智为重。康有为将仁智关系套用到体用公式中得出两种结论:一为就人之本然而言的智体仁用论,一为就人之当然而言的仁体智用论。就体用关系看,他把智与仁分别为认识力与实践力,智中蕴藏着“为我”的义,仁中包含了“为人”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最终“为人”克服了“为我”,表现为“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故人宜以仁为主,智以辅之”。(14)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2、108、109页。
再次,康有为的“智”能力极强,不仅是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动力,还是神秘的生成力:“人之能横六合、经万劫、证神明、成圣哲者,皆智之力也。”(15)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28页。康有为自诩在穷极万理获得极高智性后便独得天下无限之全权,集邃古圣英之神明。可见他的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智识水平,还具有由凡入圣的神秘性。
最后,康有为指出智在各个人身上表现出差别性。智性作为天性之赋予,在获得之初便各有短长。智性获得不均衡的根源在于“气”的薄厚不一,这使得个体获得“气”的禀赋有差等,愚者与智者的分别也由此产生。在结果上,“愚者可以与知能,智者可以参化育”(16)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31页。。智性水平低者将患“愚蠢之苦”,无法进入大同乐园。后来康有为在大同世界中设有“奖智院”作为促进智力发展、鼓励智力创新的奖励机制。智人徽章是评判智力的标准,在层级上有智人、多智人、大智人、上智人、哲人、圣人,智性发展水平再度与成圣境界相连。虽然康有为的智性论是对前人观点的批判和超越,但其修养人性的终极目标仍然落在圣人境界。这也与他早期提出的“合智言圣而圣为如神,舍智言圣而圣为偏至”(17)康有为:《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页。观念相吻合。
在交代智力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后,康有为又“人道”地提出弥补智性先天不足的工夫,即“学”。康有为的“学”可以溯源至荀学的直接启蒙。他认为孟子重于心而荀子重于学,孟子言大同而荀子言小康,两派俱是孔门圣学不可偏废。从当下的时代境遇出发,康有为欣赏荀学的实用性。在荀子那里,学是促进性情转化的方式,亦是士君子的标志。康有为认同这一点,他在善恶“非性也,习也”(18)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页。的基础上将性的善恶显现归结为后天习染,顺而为“学”的相对合理性搭建平台。他强调学的重要性,指出“美质好学,则穷极天人,而为神圣”(19)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15页。,将学作为追求智乐、超凡入圣的手段。“学”是后天工夫。“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20)康有为:《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41页。圣凡差别即在于“学之至极与不至”,圣人也正是由于智性涵有丰厚才能防患于未然。普通人如果能够自不学而学,就会“心智万变。积微成智,闷若无端,而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也”(21)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0页。,最终达成“学为圣人”的目标。以学为改善智性的方法来求得积微成智的结果,这也是康有为求变逻辑的应有之义。
康有为认为学是实现智强的路径,智强是国强的必要前提,“争新竞智,而后百事皆举,故国强”(22)康有为:《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87页。。 为学之志在于“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制之精,达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23)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25页。, 学与智均为社会治理服务。在订立学的目标后,康有为制定了为学的指导性原则。其一,为学须得合“时”。“礼时为大,故学亦必随时而后适。”“时”有两层含义:一为时时治学,学以养智是终身之事;一为合于时遇,“合时”需以“时时”为基础。学如鸟之数飞,熟练而后贯通,最终才能在时势中怡然理顺,逢源自得。其二,为学重在“合群”。康有为提出“群人共学”的设计,把群体性的学与社会性的人结合,认为仁智兼修是拯救群生的方法。合群首先要求个体找到自身的身份与角色所属,继而摸索规范的身份性伦理和适宜自身发展的群居合一之道。在此基础上,各个人“学”的水平可以真实地反映在层级化的身份结构中。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因材施教”地探索适宜各类群体的有针对性的学习模式。康有为的“群”还有大小之差,低水平的小群通过学可以向较高水平的大群转化,“合小群不如合大群,其学愈高,其用愈远”(24)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79页。。 在大同世界的“大学院”中,康有为架构起培养智力的学习框架。“大学之教,既以智育为主,此人生学终之事,不于此时尽其智识,不可得也。”(25)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09页。大学教育安排在德育、体育之后,专以智育为主,人人各从所志,学的内容有专门化趋势,包括光、声、电等。最终,他还是将学的目标落在救国上,在中西结合的倾向中一步步偏离他早期学以积微成智的成圣理路。
二、博文约礼:作为学之对象的礼及其节性工夫
为学始于“扞格外物”,继而“厉节”“辨惑”“慎独”,终于陈白沙之潇洒境界。这反映出康有为对于格物与养心两种工夫论的调融,即“苦身力行,以明儒吴康斋之艰苦为法,以白沙之潇洒自命”(26)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63页。。 康有为业已指出人天生的智愚殊异、质类不齐会使得人际关系在竞争中走向不睦,进而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这类不平衡在根源上虽然是“天造之”,但在发展中“平均者圣人调之”,孔子即是圣人形象的典范。“孔子之道全在六经”,礼作为六经之一是学的重要内容,圣人所创的制度礼义由此展开调节功能,“趋平而后止”(27)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83页。成为礼调节智的总目标。
与学对智性的积累工夫不同,礼之于智的功用见长于对智的葆有持中。康有为的成圣理想发端于圣人制礼。“圣人者,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竭其耳目心思焉,制为礼乐政教焉。”(28)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84页。人要成圣须以知命为本,“知礼知言”才能处人间世而无碍,践履圣人之礼即是追求圣人境界的基准。正如《荀子》中所论:“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29)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4页。
康有为以“智欲崇而礼欲卑”(30)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23页。来刻画智与礼间的生克关系。“惟其智者,故能……节文以为礼……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智是礼产生的认识力支持,同时也高于礼,在重要性上表现为“智为上,礼次之,义为下”(31)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8、109页。。 康有为指出,智如同“机轴转运,不能自已”,虽能“周乎八表之外”,但须得“躬循乎规矩之中”,博学而约礼才能避免放荡纵肆,进而合于天时。礼作为人道之节文,严而泰、和而节是合于礼的自然状态。礼制虽严,但据其初创时的人本性,用礼时也应当遵循人情之自然方能刚柔相调而不乖。
节用的“礼”有其人性论根源。康有为既认同“礼法天地”,又强调“礼为人设”,在将天地作为礼产生的客观条件的同时,还将人的主体需要作为礼产生的主观依据。汪学群先生指出,康有为强调的“礼”的节欲抑恶功能是从节制“人的身体”和“人的欲望”着手的。如“禁酒戒杀为仁之至,不能骤行,以饮酒食肉而为节度,制定饮酒礼;戒淫立约为义之至,不能骤行,制定昏礼”(32)汪学群:《康有为〈礼运注〉的礼学思想》,《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等等,礼制的定性皆是为满足人合理的生理需要服务。康有为也确曾指出人如果“投于声色臭味之中,则为物交所蔽。薰于生生世世业识之内,则为习气所镕”(33)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26页。。沿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出,康有为视域中为礼所“节”的对象首先是作为天性外求之必然表现的“欲”。欲是人性触角的向外探求,本身是内在于人性的,对于欲的追求程度是决定“性”表现为善或恶的依据之一,于是康有为直接将“节欲”阐发为“节性”。“性何以节?恃有礼而已……所以范其血气心知,以渐复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矫揉造作,理以为质,礼以文之。”(34)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29页。这不仅指明成圣理想在工夫层面由义至礼进而于智的修养次第,还表明智作为礼产生的认识力来源能通过礼的节欲功能来保有其天然性,即智性。在这一层面上,康有为将智、性、学、礼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体上能够自圆其说的以智性为人性论基础、以礼为学的工夫论实践、以成仁成圣为理想人格境界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康有为看来,礼之节用可以将智的使用框范于“中”的状态。“谓之中者,指性体也。性体既得其中,则发而为喜怒哀乐。”(35)康有为:《中庸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370页。康有为将智之“中”的标准定为“博闻强识,守之以浅”(36)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39页。,“义不讪上,智不危生”(37)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页。是智持中的理想状态。智性中有“不待学而知”和“待学而后有验”两部分,前者指向义理,惟义理是神灵光明的运行结果。后者指向礼乐,“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38)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30页。。
礼功能在智性上的发用分为外部影响与内在塑造两个环节。在外部环境影响方面,康有为认为礼在生命的孕育与诞生阶段便已存在于生命流转中,针对人从受孕到出生、渐长等阶段,他提出塑造外部环境来培养人性的主张。妇女受孕后要即刻入住胎教院,胎教院应选址于温冷、平原、有水环绕地带,以从外部环境“改良人种”;妇女胎妊之时,感人最易,因此要“教之治之”。“教”需要“知人道之治,风俗人心为先矣,则谆谆于教化,摩之以仁,渐之以义,示之以信,齐之以礼”,这指明了齐之以礼作为胎教的内容和方式之一在“性”层面孕育出合于大同之智性的可能;妇女产子后,需“抱子于户内,与官行礼,奏乐诵吉词而为之名”(39)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93、102页。,以示重人之生。康有为在生命孕育阶段设计的礼环境与《大戴礼记》中援引的《青史氏之记》注重母亲以礼节制自身来影响胎儿的记载有相通之处。“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40)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60页。进入小学院,康有为将人性培养目标落实在强调人道之始以德育为先。小学院亦择山水佳处,使“非礼不祥之事不接于耳目……保其静正之原,乃可广其知识之学”,以礼为规矩摒除非礼之事,使性保持静、正状态,以“合礼”的外部环境提升学的效果来补益智性。
在内在精神塑造方面,康有为强调中学院阶段学礼的重要性。礼在中学院成为贯穿生活各方面的准则,它能对学的结果做出规范性判断,以便从源头上培植出适合智性显用的环境。人十一岁至十五岁间学于中学院,在经过小学院阶段体育、德育的炼养后开始学习礼乐,以礼“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节,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还要自觉以礼律为准绳,“导之以正义,广之以通学,绳之以礼法”。(41)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07页。中学院阶段不仅注重学的博与精,还要求依礼慎行守约,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之“有若无,实若虚,不以学问自矜,而行礼至谨”(42)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98页。的谨慎、从容态度一般,以合中之智探寻物理、人事发展的适宜尺度。康有为中学院阶段的学礼设计再度与他认同的董仲舒思想相呼应。董仲舒曾言:“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即是“质”,与“文”相对而言之,“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43)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页。。康有为从内在精神层面设计的中学院学礼内容即是从质层面培养人的守礼自觉。同时,按董仲舒“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的思想看,康有为设计的婴幼儿时期“合礼”环境的外部熏陶和中学院时期学礼、守礼的内在建构,就是从质文两向着手以求最大化发挥礼的节性修身功能。
如多数前代思想家那样,康有为也为其以礼节欲进而增智的成圣工夫寻求神性佐助。礼作为圣人制作的结晶在与时空相契后达成与天道的联结,在时间上有“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空间上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44)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6-347页。礼之本是与天秩天叙的匹配合宜,康有为指出“礼法不能治者,以刑罚治之,刑罚不能治者,以鬼神治之,所以救礼法之穷也”(45)张伯桢整理:《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17页。,礼的权能在神性力量注入之后获得额外的威严,“人畏神谴,则咸循法度,此礼达于下之效也”(46)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91页。。 在鬼神之外,康有为还将“本诸天”的“数”作为宫室、饮食、衣服等礼仪典制形成的根本性依据。依托于数“始于一,由一生四,四生八”(47)张伯桢整理:《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226页。的“生生”之天理,人才能接触到数在推演过程中的伴生性产物“礼”,个人也在学礼、守礼中获得“测天穷地,察物究人”的可能。
三、始智终圣:学与礼的成圣理路及其困境
“若当太平之世,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淘汰,胎教修明,人之智慧、澹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而后为天生之成人也。”(48)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91页。这是康有为对太平世人全面发展的过程和理想状态的想象,基本总结了其学礼成圣的路径和理想。礼乐教化是促进智性提升的方法,胎教即是从“合礼”的外部环境着手开启了人生第一扇教化之门。人种淘汰是智性提升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趋于太平的必要牺牲。无论是学还是礼,种种手段的终极目标皆是使人成为“成人”。可以看出,康有为以智为性的人性论中蕴含着人类社会向美好状态发展的可能,在人表现为圣人境界,在世界表现为大同理想。这种可能性建基于“学”对智性的积累,落脚于“礼”对智的葆有以使智性在“中”的原则上发挥最大效用。学的人本性与礼的宗教性从人道和神道二重向度对人性发展予以引导,由此实现康有为成圣的人格向往。但这两种工夫有其天然张力存在。
康有为业已指出人性的本质特征在于“智”。智“受于天而不能自已”,属于人性中的天然部分。内在于人性的智生发出辨别心,爱与恶是智分别的第一对范畴。爱的表现有程度上的递增,起初表现为想要得到的“欲”,接着是得到后的“喜”,“喜”再进一步深化即是“乐”。由此类推,恶的表现有程度上的递减,起初表现为想要而不得的“怒”,“怒”又演化为“恶之极至而不得”的“惧”。若要使爱恶合矩就得提升智性水平,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消除分别爱恶的辨别心。康有为据此强调后天的“学”,以学作为亲近物理的路径,“穷物理之所以然”进而亲近“人理之当然”,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亲近与贯通。然而他又讲善恶“非性也,习也”,矛盾在于,他既将爱恶的分别归结于天然智性的辨识,又要凭借后天的“习”来取消先天的爱恶分别心,并意图以此强调爱恶并非人性的内在之质。这样,爱恶的分别心就同时具有先天与后天两种性质。若爱恶来于先天智性的辨别后果,那么由不可变的智性衍生出的爱恶又如何能通过后天的学扭转?康有为对爱恶来源划归的混乱,导致他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他又说“性识早定于童幼,如旭日初出,已自皎然大明;其后之进……虽有增益,非如常人之性识”(49)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88页, 实质已从性分上否定了后天工夫对智性的作用,学的工夫在其人性发端处便被斩断了生长根基。就康有为智性论的思想视域看,他未能“就‘性无善恶’作更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没有很好地回答后天的‘善’的来源问题,这就使其人性思想的某些方面说服力打了折扣”(50)张恒:《康有为人性论研究》,《当代儒学》2019年第1期。。 他短暂提及的“存者为性,发者为情”的无善恶说法最终也落入了“爱恶存者名为性,爱恶发者名为情”(51)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页。的窠臼之中。
康有为学以积微成智的成圣工夫还与其大同理想相抵牾。在康有为自制的“人类平等进化表”中,他将智与愚作为人种差异的天然标志。据乱世中黄、白、棕、黑四人种的智性水平有着天壤之别。进入升平世,按照康有为的通婚等“沙汰”之法,棕、黑人种将逐渐减少,人种间的智愚差距也相应缩小。在最终的太平世,棕、黑人种将被完全同化,到那时“诸种合一,并无智愚”。他甚至直言,“生同为人,而所知那与牛马等,不得一接其同类先哲之奥妙懿伟以沃其魂灵……况脑根熏浊,必少高明光大之神,势必嗜利无耻,少礼寡义,留此人种以传家则俗不美,以传种则种受害,以此愚根流传不绝,是犹在黑暗地狱”。智力赋有的强弱直接成为他判断人种优劣的标准,这在根本上是对其自建的平等而自由理想世界的背叛。此外,康有为对智的评价似乎全然积极。“人类以智自私,则相与立文树义”,于万物仅爱其同类,于自然则以人类的智力为判断依据,“衣鸟兽之皮,剥削草木,雕刻土金”(52)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9、29、50页。, 这种智的运用在根本上违背了仁的原则。从另一角度看,康有为宁愿给予恶兽毒蛇以进入大同世界的权利而主张强制淘汰棕、黑人种,这样的仁爱从本质上就是狭隘的,背离了“施与人民,救济众生,广博普遍,无所不及,庶得为仁”(53)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24页的仁道初衷。
作为“节智”工具的礼在演绎时亦有其理论困境,这体现在康有为架构的仁智与礼智关系上。张昭军先生指出:“仁、智、礼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对他们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54)张昭军:《康有为与儒学的近代转换——以仁、礼、智为例》,《理论学刊》2004年第1期。在康有为划分的由天界、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组成的大宇宙中,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55)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64页。。 五运是为实现群居和谐状态而设立,按康有为推演的五运机制,小康世仅有礼运,在礼运推动小康世向大同世转化后,智运才能在大同世全面实现。学对智的助益、礼对智的葆有持中,皆是为促进智运在大同世更全面地发挥权能所做的铺垫。康有为早期有着“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现实理想,主张智体仁用。仁作为成圣境界和大同之爱生发的泉源,其实现的可能性依赖于礼的践行度。但在康有为的小康世中,礼运统摄于智运之下且为智运服务,智性水平深刻影响着守礼程度与成仁进度。康有为强调智的认识力对礼与仁的直接塑造,这实际是在伦理概念知识化的过程中将仁与礼的本质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后来他只能不断强调仁与礼在各自三世进化线上的阶段性来自圆其说。同时,在智性生礼原则统摄下,智性的低水平意味着守礼的低水平。在本质上,智性水平的先天性也必然将一部分智性水平较低的人群阻隔在大同世界之外。最终,以智为基础产生的礼与作为智性发展终极目标的仁在人道与仁道两个层面均发生断裂,作为人性根基的智破坏了人性的平等、自然状态,成圣的“礼”路也因此失去根基。
礼的困境还表现于礼制本身对普遍人性的压抑上。礼在漫长的制度化和刻板化过程中已发展出其自身的异化物——礼教。清代的反礼教情绪自清初已有之,清中叶礼学家如凌廷堪等人对“礼者,理也”的扬弃将礼的本质复归至人情导向,讲求“称情而立文”。康有为指出:“性尊己而卑人,礼教人卑己而尊人。”(56)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61页。他认为尊人虽有益于忠恕之道的推行,但卑己导致的主体压抑却成为长期以来内化于人们精神深处不自由的枷锁。且“名分太严,则有暴殄压制之患。性情强合,则失自立自由之本”。(57)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556页。这种过度的“节”不仅不能保有智,甚至还遏制了智用巧思的发用。认识到这一点后康有为在大同世界为变革的礼留有余地。按其前期设想,包含礼制在内的孔门圣“学”业已完成引导人性完满发展、进入太平世的历史任务。随着太平世中家庭的取消,个体“复为独人”,礼失去其赖以生存的伦常体系,这恰是改革礼的最好时机。康有为主张革除与近现代世界文明不相容的拘束迂腐之礼,省去繁礼意味着省去传统伦常的硬性约束,这不仅能打破人际关系的僵硬状态,还能改善因伦常、礼制过紧而被抑制的人之独立性。太平世的礼就此被改良为符合现代社交仪节的礼仪、礼貌,只是已全然背离传统礼学意义上的礼义、礼制。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在其大同世界设计了“一个没有君主的文明”,他将礼之三本中的“君”从天人图景中抽离出去,进而消解了君君臣臣的“必然性伦理”,同时也翻转了儒家“因德性之差立礼义之等的逻辑”。(58)参见宫志翀:《“人为天生”: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根基》,《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康有为看似批判了蹈礼以修身的内在逻辑,实则提升了个人凭自力修身成圣的可能性,也将个人从固化的等级秩序中解放出来,与其历来鼓吹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一脉相承。
四、结 语
智是康有为人性论的基石,智性禀赋的天然差异为学的实用性埋下伏笔。学与礼是积智修性以成圣的工夫手段,为此,康有为对传统人性标准作出调整,他将仁智并举,勾勒出人格渐进式完满的发展过程。同时,为促进学对智的补益来实现人性善端的显扬,他将礼调整为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学出发的积微成智与从礼出发的博文约礼成为两条并行的工夫手段,在智性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直至达成太平世的智运时,学与礼合二为一。康有为看似设计了一个具备天命佐助、人道进益的合神道与人道为一体的具有实践性和可实现性的修身成圣理路。但在其性—智—学—礼的链环中,智既是礼产生的智力支持,又是最终导致礼消亡的关键因素,学也在此过程中失去支撑,因而其成圣工夫在源头上就埋下了无果的伏笔。康有为或许也意识到自己的成圣理路有粗陋之处,他自圆其说道:“治起于衰乱之中,治法不能不粗。”在“三世可为九世……由九世可变通之至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可推至无量数之不可思议之世”(59)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7页。的世界循环发展过程中,学、礼工夫虽能推进智性发展,促成仁智终始的前进模式,但仁与智的发展势必又在新世界产生新问题。推动世界发展的人性基础“智”与推动智性提升的学和礼将因此陷入无尽的循环,成圣理想也变得遥遥无期。
有学者给予康有为的人性思想及工夫论以较高评价,认为康有为“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60)王玉彬:《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哲学动态》2016年第4期。。 不过,康有为以智性为基的成圣工夫正是在其注意力全盘转移到政治理想时失效。在对政治改良运动彻底失望前,康有为的思想理论一直为其社会理想服务,因而其思想的矛盾性也源于他在刻意使思想与改良事业相匹配时造成的理论的牵强。他曾认同“西学中源说”,认为“凡生民千制百学,至黄帝而大备……四千年神圣之教不传,而令裔夷得窃其绪”(61)康有为:《民功篇》,《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75页。。可以想见,当他将西学中的物理概念加入到其人性论中时,或许还存有一丝将西方“窃”走的中国思想“拿”回来的自得。此外,援经议政的理论目标也使得康有为在运用古人思想时过分依准“为我所用”原则,有时甚至对一些古代思想结晶做了无根据的指责与批判。1898年,《中国邮报》记者在采访康有为后这样评价他:“康有为是一个像貌聪明、中等身材的中国人……他具有惊人的现代知识。而且较之大多数他的同国人更能掌握情况。虽然他的某些见解似乎不免近于幻想,但他的态度无疑是真挚的。”(62)《答〈中国邮报〉记者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19页。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康有为在守古与纳新之间摇摆不定。虽然他摆脱古老力量的羁绊因犹豫而无果,在无根的文化土壤中强行培植的思想花朵也宣告枯萎,但走在时人前列的康有为终因其探索精神和成绩被书写在历史的纪念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