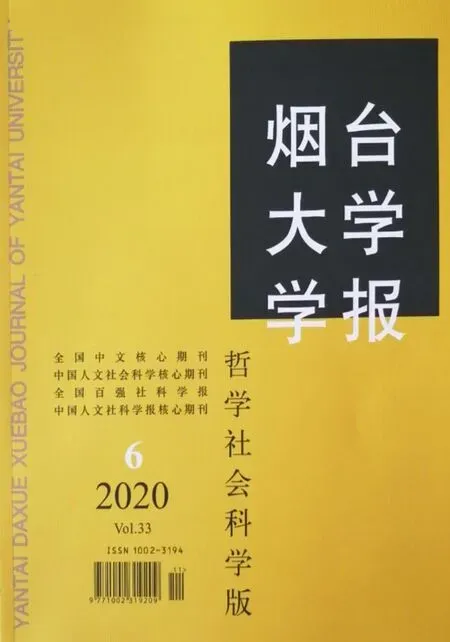流寓中的锐意丰盈
——论黑塞作品中“乡愁”的意涵与嬗变
郭利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年生于德国南部小镇卡尔夫,1912年流寓瑞士伯尔尼,1919年移居瑞士乡村堤契诺,后终身居住于此。在作家的代表作《荒原狼》中,赫尔米娜这样抚慰遭遇精神危机的荒原狼:“哈里,我们不得不越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历这么多的荒唐蠢事才能回到家里!没有人指引我们,我们唯一的向导是乡愁。”(1)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作品中作家还多处以“失落的故乡”“梦中的家”“漂泊的灵魂”等字眼来寄寓“乡愁”,“乡愁”成了贯穿作家一生创作的情感线索。生于市井之家的黑塞,终其一生走在还乡的路上。对黑塞流寓瑞士的经历及其作品中的“乡愁”意绪进行梳理和考察,有助于整体把握其创作的诗学意蕴和哲理内涵。
一、“乡愁”的自我之源
“乡愁”是一种关涉根脉、灵魂、记忆的情感状态,“乡愁”的生发牵涉着时间的迁移、空间的转移、情感记忆的转变及文化的归属等重要因素。对于黑塞来说,“乡愁”是一份刻着“自我”印记的、包蕴着动态的思想轨迹和执着精神的独特情感。作家在少年时就显现出不服从外部势力的个性特征。他十四岁时被送到修道院学习,由于无法忍受压抑个性、枯燥沉闷的学校生活,只待了七个月就逃走了。在家长施加压力强迫他重返修道院学习时,他曾两次割腕以示抗议,并被两次送进精神病院。作家在其《生平简述》中忆及少年时期经历时写道:“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都在所不计。”(2)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谢莹莹、欧凡、胡祖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页。黑塞逃离学校的结果是以退学告终。之后青年作家是缘何流寓瑞士的?流浪又可以给予他何种宽慰呢?下面着重通过作家创作来寻找其异乡而居的根源,并试图发掘出流寓前后其作品中“乡愁”意绪嬗变的轨迹。
“我不服从”“我是人”的呐喊声几乎贯穿作家一生的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1904)可以说明黑塞流寓瑞士的原因。小说描写一个偏远山村里的少年彼得,不爱学习,崇尚大自然,长大后他离开闭塞的小山村,前往使他感觉格格不入的城市。大学毕业后他对城里人们虚伪的生活不屑一顾,于是不停地游走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对生命的反思、对自然的感悟让他逐渐明确了自己将要选择的人生道路——成为作家,而他也终于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并衣锦还乡。在乡下照顾年迈父亲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乡亲们和善的目光和淳朴的民风民俗,突然领悟到所有的远大志向都将归于平凡的生活和内心的安宁。黑塞曾这样评价笔下的主人公:“他要走的不是多数人的道路,而是固执地走自己的路,他不想随波逐流,不想仰人鼻息,而是要在自己的灵魂中反映自然和世界,在崭新的图景里体验它们。”(3)转引自马剑:《寻求“自我”之路——论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显然,这部小说契合了作家反抗教育、神权,隐遁于瑞士乡村写作并如愿成为作家的经历,反映出作家渴望自主选择生活,希冀在繁复机械、唯图功利的现代文明中保持自我的心理动机。
1914年,德国作为同盟国成员卷入一战。面对整个世界陷入疯狂的战争罪恶,作家在创作与行动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反战呐喊。他在《啊,朋友们,不要用这种调子》的散文中写道:“爱高于恨、互相理解高于愤怒,和平高于战争,正是这场不幸的世界大战使我们比以往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4)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第173页。在散文《我的传略》中作家又无奈地说:“一九一五年的一天,我公开说出了关于这场灾难的认识,而且表示遗憾,因为连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知所措,只晓得宣扬憎恨,传播谎言,还赞颂这场巨大的灾难。我这些相当谨慎小心的控诉引起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5)赫尔曼·黑塞:《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张佩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后来,黑塞参加了德国战俘救济会,在英、法、俄、意等国家出版战俘杂志,为几十万德国战俘提供思想援助。黑塞始终站在被强权奴役的士兵和人民的立场上,对他们遭受的危险处境和精神困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侵略者的强权意志和战争暴力表达强烈的愤怒。但令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份忠诚和奉献却被德国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曲解为叛国之举。
一战后,德国政权落到纳粹希特勒手里。希特勒利用德国贸易大力发展军工业,利用外交手段尽力减小一战带来的经济损失,逐步将德国推向了新一轮的世界大战。1919年4月,结束了德国战俘救济工作后的黑塞面临着沉重的人生遭际:在瑞士伯尔尼的生活异常贫困,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夫妻关系冷漠隔绝,妻子精神分裂住进精神病院,三个儿子只能寄养他处,自己也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不得不多次接受荣格精神分析治疗。1923年,黑塞下定决心加入瑞士国籍,从此他便再不为德国人所原谅。可以看出,黑塞流寓瑞士实是无奈之举。他在瑞士乡间的生活饱受经济拮据和被同胞背弃的身心折磨,但这种与人隔离的生活能最大程度上使他保持独立。他立志要做一个独行者,在孤独和宁静中进行忠于自我、深入内心的灵魂写作。黑塞曾在散文《树木》中谈及自己每每凝听晚风中树木的沙沙声时,对故乡的眷念就会撕扯他的心。这种撕扯是一种渴望找回自我、逃离痛苦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一直牵引着他。
“没有人曾经完全发挥他自己,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做到那个地步”(6)赫尔曼·黑塞:《德米安》,丁君君、谢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2页。,黑塞终生企盼的正是这种自我完整的价值意义,“乡愁”的情感记忆由此而生。机械刻板的现代文明和战争罪恶使作家在流寓中上下求索,梳理他流寓前后的作品,可以发现作家经历了从分裂到融合、从索求到服务、从注重主体自我到强调“交互主体性”(7)“交互主体性”这一概念最早由胡塞尔提出,用以指不同心灵之间的共享互动与传播沟通。人生活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之中,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交互主体性,这是一种“构成主体性普遍网络的交互主体性”。见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人文主义向人道主义情怀转变的心路历程。他带着“乡愁”一路艰苦卓绝地探寻,最后终于打破了自我与世界的隔膜,走出身心分裂的困境,找到了刻着自我印记的、永恒的“阿特曼”(Atman)(8)“阿特曼”概念来自古印度梵文,汉语意思相当于“真我”“纯我”“神我”“自我”“灵魂”等。印度最古的《歌者奥义》将普遍人的共同本性(阿特曼)抽象出来,发现了它与宇宙本体“梵”的同一性,即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与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阿特曼”是统一的。黑塞受印度哲学影响很深,因此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内倾性、内向性很明显。。
二、“乡愁”的形而上之维
黑塞曾一度被认为是德国的“叛徒”。从一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对德国的批判,因此饱受朋友、同胞的埋怨和讥讽。但他在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却说:“把文学奖颁发给我也意味着对德语和德国在文化贡献上的承认,我认为此举体现了和解并重启各个民族间精神上合作的良好意愿。”(9)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第173页。这一肺腑之言体现出作家的“乡愁”情结,他极为重视德语文化的世界形象以及德国与世界的和解、交融。
黑塞青年时便离开了故乡,但德国古典文化精神几乎成了他所有文学创作的精神来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自我”的重视以及对理想人性的追求是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黑塞笔下的人物大多选择离开安逸的生活,去往自然和社会当中,通过体验世间百味来寻求更加完善的精神境界。如作家早期的作品《彼得·卡门青》(1904)、《盖特露德》(1910)体现出对人之天性、权利和尊严的强调。卡门青在远离都市文明的山村重新找回诗性自我,在自然的怀抱和纯朴的民风中得到精神慰藉。他抛弃了唯美主义的不成熟的幻想产物,在意大利和瑞士山村旅行之后,写出彰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优美诗篇。《盖特露德》中的库恩放弃死板的校园生活,遵从自己的内心学习音乐,但伴随其青春成长的还有狂妄、无知、失恋和自卑,滑雪事故造成的残疾让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奔跑、追逐。所幸他能在无数孤独的日子里学会接纳现实,终于在友谊和音乐的天地里创作出无数凝聚着青春激情、孤独和情感的音乐篇章。黑塞在早期的创作中流露出逃离陈规陋习、不断向大自然或艺术王国挺进的强烈意欲。他意识到只有在淳朴的自然天地和诗性的艺术王国里才能实现灵魂的自在和天性的恢复。
然而,作家也意识到这种古典人文主义思想重视的是理想信念的构建,缺乏在现实中生根发芽的实践维度。黑塞在1932年的随笔《感激歌德》中表露:“在所有德国诗人中间,歌德是让我最感激、最费神、最苦恼、最受激励的了,他逼使我去追寻或者去抗拒。我与歌德却总是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和思想上的斗争。”(10)《世界文学》编辑部:《布拉格一瞥》,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的确,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带有市民庸俗气和软弱性,他们所倡导的追求知识和灵性的完善,充实的、富有美和感受力的生活只是一场虚幻的道德说教。用光明的精神遮蔽鄙陋的现实,用人性善掩盖人性恶,用自我的精神满足代替扎根现实、服务世界的实践自我,这其实只是沦入了风光无限的精神大海。黑塞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古典精神中纯朴、旺盛的热情,一方面也看到了这种光明背后的阴影。
对德国古典文化精神的继承、反思和超越使黑塞的“乡愁”意绪得到了升华,使其对自我的认知增扩了形而上的超越之维及形而下的实践之维。他勇于打破民族藩篱和精神乌托邦的拘囿,努力探求一种更为博大、普世、开放的文化信念,一种和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互动的新的价值观念。这种探索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超越宗教一元论及德国民族主义、德国古典精神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理想,其二是立身现实、服务现实的“人的自由本质”观的构建。
“世界主义”发轫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的“世界理性”观念。该思想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人类世界是一个整体,个人可以通过与体现神性本然的理性一致来实现世界公民社会,即世界城邦(Cosmopolis)。这一思想在18世纪启蒙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康德曾提出建立一个各民族联盟的“世界主义秩序”。在康德看来,残酷而紧张的战争正像事实上呈现出来的一样, 能够使人类“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所有的战争就都是要——尽管这并不是人的目标,但却是大自然的目标——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并且是要通过摧毁或者至少是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而“每一个国家,纵令是最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须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须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页。。歌德及19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也分别在文学和宗教领域内提出“世界主义”的观念,而黑塞作为德国古典精神的继承者以及饱受世界战争之苦的知识分子,也呼唤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理想。
黑塞认为老子、佛陀、耶稣在追求最高精神境界上是同质的。他在其散文《我的信仰》中表达了这种多元统一的信仰观:“我体验过两种宗教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就是奥义书、博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极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袭击了我……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12)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第54页。黑塞认为,应将道家“无为”的思想用来弥补欧洲理性型文化的不足。我国道家思想中,“无为”即不逆“道”而为,“道法自然”才能实现最高限度的“有为”,此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而西方文化崇尚浮士德式的欲望范式,明知有限永远不会成为无限的伙伴,也依然要走向生命毁灭的终点。这种不可为而为之价值取向的过度张扬,会导致人类耽于物质追求和物欲享受而精神衰颓。作家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推崇,是对现代社会中践踏人的生命和尊严、束缚人性自由等不合理存在状况发出的抗议。
黑塞对道家思想的接受着重体现在他对“道”这一核心概念的内化。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庄哲学将“道”上升为宇宙的本源,将“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是故得“道”即得“一”,得“一”才得“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第三十九章)黑塞将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引入人的认识论领域,重视个人内心的悟“道”,认为得“道”即实现最高程度的圆融、自由。例如他在其长篇小说《德米安》(1919)、《悉达多》(1922)、《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以及短篇哲理小说《内与外》等作品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悟“道”而“一”,“用东方智慧打破二重镜像”(13)张弘、于匡复:《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26页。,寻求内在和谐的文化思想。在《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中,修道院学生歌尔德蒙也听从朋友纳尔齐斯的劝说:
像你这一类的人,天生有强烈而敏锐的感官,天生该成为灵感充沛的人,成为幻想家、诗人和爱慕者。比起我们另外的人来,比起我们崇尚灵性的人来,几乎总要优越一些……你们生活在充实之中,富于爱和感受的能力。我们这些崇尚灵性的人,看来尽管常常在指导和支配你们其他的人,但生活却不充实,而是很贫乏的。充实的生活,甜蜜的果汁,爱情的乐园,艺术的美丽国土,统统都属于你们。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14)赫尔曼·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杨武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这里提到了两类人:拥抱大地、追求感官享受之一类和崇尚灵性、精神之一类,后者会因生命太过拘谨而窒息在灵魂的真空地带。歌尔德蒙由此放弃苦修,开始长期的流浪。凄美沧桑的爱欲情感和优美惬意的自然风光使他迸发出智慧与灵感的火花,终以恋人丽迪亚为原型雕刻出圣母玛丽亚雕像。歌尔德蒙在内外合“一”中才实现了精神世界更高程度的“丰盈”。
“一”的本质是超越种族、地域以及信仰差异,全世界人们在和而不同中实现更高阶段融合的美好愿景。黑塞“乡愁”所念的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心灵深处的安顿之地。这一包蕴着多重复杂情感的意象,既体现出作家对德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继承,还寄寓着他跨越民族、包容不同文化的世界主义理想。不难看出,流寓后的黑塞在他乡抽绎出更为扎实的精神冠冕,一定程度上为人类减轻了欧洲中心主义“烈日”的暴晒。但这种理想终究仍只是形而上的精神超越,缺乏现实的土壤以及对“生活世界”(15)胡塞尔在《生活世界现象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同自然科学对象领域的理想化概念相对立的日常实践语境,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具有直接发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二是具有非对象性和先在性的原始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黑尔德曾明确指出:“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构造思维所始终涉及的那个“世界”,“世界的整体并不是各个独立的对象领域之总和,而是一个对所有视域而言的普遍视域。即是说,它是一个绝然全面的我的各种权能性的活动空间”。见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61-274页。的切实参与。
三、“乡愁”的内向之路
通过努力追求,黑塞实现了成为诗人的梦想,并获得一时的温暖和满足。但随着世界战争以及流寓生活危机的爆发,黑塞在其《传略》中写道:“我再度成了问题,和周围世界发生了矛盾……我必须再一次以自己为满足,而忘却周围世界,正是这一次经验,我才跨过门槛进入了生活。”在遭遇世界及朋友的背弃时,他感到“悲伤”,也“由于烦恼而感到十分孤独”,但他认为这同时也“成为我抵御外界的甲胄和铁罩”,“常常因而更坚信自己所走的路”。在“充满间谍行为、行贿技巧和投机艺术的政治环境里”,作家意识到“每一个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16)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第470-472页。。“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的理解。”(17)赫尔曼·黑塞:《荒原狼》,第5页。作家在升华形而上超越思想的同时,开始转向对内在自我的剖析:“谁能找到向内之路,/并能于沉思中/将智慧核心感悟,/即:要将世界与上帝/当做典故与图画。/那么,他的每个思想和行动,/便是与自己心灵之对话,世界与上帝尽于心灵中。”(18)赫尔曼·黑塞:《诗话人生——黑塞诗选》,郭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02页。继而推己及人去探讨现代人生命普遍存在的疾病和危机,并试图以“永恒和生之本相”(19)赫尔曼·黑塞:《漫游者的寄宿所:黑塞诗选》,欧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来整合被物质文明所腐蚀的生命碎片。
创作于1919年的《德米安》是黑塞向内转的开端。该作品讲述的是少年辛克莱内心发展变化的经历。童年辛克莱生活于学校、家庭和教会所描绘的伊甸园世界,但后来的经历让他感悟到客观世界和描绘世界的巨大差别。邻人克罗默是“恶”的典型人格,辛克莱却被他吸引。克罗默多次在梦中教唆辛克莱犯罪,甚至促使他杀死亲生父亲。“弑父”之梦预示着辛克莱认识另一世界的必然:他觉察到克罗默正是自身“阴影”的投射,现实同时存在着光明、秩序、亲切的和黑暗、喧嚣、邪恶的两种世界,两者的矛盾集中作用于人,让人在善与恶、灵与肉、光明与黑暗的规定下决定自己的归宿。德米安作为辛克莱的精神导师,引导他应正视“内心的该隐”,明白对世界一元的、非此即彼的看法只会走向分裂。
黑塞对现代人内在矛盾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荒原狼》一书中。主人公哈勒“失去了职业,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故乡,游离于所有社会集团之外……时时与公众舆论、公共道德发生激烈冲突……宗教、祖国、家庭、国家都失去了价值……科学、艺术故弄玄虚,装模作样”(20)赫尔曼·黑塞:《荒原狼》,第2页。。他同时承受着内心的分裂与焦灼:既是具有理性信仰的知识分子,崇敬以“莫扎特”“歌德”等为代表的精神乌托邦,孤立地与四周的暴力机器做斗争;又是冲动直率的荒原狼,忍受着兽性本能的冲击以及善恶两级力量的冲撞对峙。在依稀获得拯救而又重坠鄙陋现实的深渊时,他终于“兽性”大发举刀杀人。黑塞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哈勒心灵上的疾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怪病,是哈勒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21)赫尔曼·黑塞:《荒原狼》,第3页。哈勒是20世纪“世纪病”患者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类造成的沉重影响,异化、分裂、焦虑成了这个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普遍的精神病症。
黑塞的流寓经历伴随着他对主体内在两面性的深入思考,彰显出作家对普遍人性的热爱与敬畏,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与反思。这一点是作家在价值论层面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做出的全新注解:不仅表现人的内在情感——人的青春激情、爱情的甜蜜与痛苦、对生命有限的感怀忧伤等,还着力于探索现代语境中人的精神危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世界的碎裂等问题,力求在诗意语言和灵魂喻象的诗化王国中对刻满创伤记忆的人的心灵予以抚慰,为现代人类指引可资思索、前行的方向。作家的创作对在已被战争和工业文明破坏的现代世界中的人该如何坚守灵魂阵地,如何在分裂与荒芜的颓圮世界实现诗意筑居等问题做出了重要思考。作品中“乡愁”弥漫的诗意氛围以及作家对现代人精神危机、心灵孤寂的深刻表达,使几乎已然绝迹的浪漫主义诗学重新迸发出绚丽的艺术魅力。
黑塞于1932年创作的小说《东方之旅》,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古“黄金时代”“东方”所象征的超时空精神文明的向往。“东方之旅”实质上也是知识分子的内向之路,旅途中所描述的经历与困境是现代人痛苦焦虑、心灵空虚的象征暗示。作品中对尼采超越精神和老庄文化思想的融合则显示出作家力争超越自我,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弥合”现代世界人性分裂、追求精神世界和谐、统一的价值主张。总而言之,对爱与美的澄净追求、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切使作家的创作具有“永恒价值”⑤的艺术形态。
四、回归“生活之母”
黑塞艰苦内向的创作方式曾遭到一些批评家的诟病,认为他通向内心的道路过于深邃,缺少映射外部世界的现实维度及自我与现实矛盾关系的切实思索。关于这一点,黑塞在晚期创作中做了反思与调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极端独裁和对外侵略恶行,黑塞开始扎根于现实,让自己走向真正的“生活世界”。
作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创作于二战时期。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虚构了一个精神温室“卡斯塔里亚”,这一艺术象牙塔是对现实恐怖世界的有力嘲讽。这个教育王国专门培育玻璃球游戏大师,玻璃球游戏“采撷自不同领域的思想精华予以集中归纳后,再进行排列、整理、组合与互相对比,无不是对一切永恒价值和形式的迅速回溯,无不是一次穿越精神王国的技艺精湛的短促飞行”(22)赫尔曼·黑塞:《玻璃珠游戏》,张佩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4页。。主人公克乃西特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之后,意识到这个远离世俗的精神王国缺乏对于现实的体悟和参与,预见到纯粹的精神世界是缺少生命力的,于是他毅然舍弃了赖以生存的精神乌托邦,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他做了一名教师,充当学生们身心发展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引导者。
克乃西特的成长历程体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他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是对过去的否定和超越。这一形象的成长轨迹象征着作家打破个体原初的自适满足,战胜成长过程中身心分裂、纠结的困境,并在服务社会的行动中实现自我本质和身心和谐的观念转变。黑塞的这一观念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这一思想反对主客体间的二元对立,强调身体—主体的不可分割与互为存在,认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是对话、共在与交流的关系,而人只有在与世界、自我的和谐统一中才能实现最大的自由。黑塞以毕生的创作实践完成了从“自我”到“身—心统一”,再到“立身世界”、超越自我的“人的自由本质观”建构。这一内化与外化的双重努力,进一步彰显出作家对碎裂世界复原、追求心灵宁静的强烈渴望。
黑塞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处在孤独、流浪、怀乡的征途上。在现代社会中,功利主义的思想渗入世界的每个角落,唯独那些不肯被习俗同化的硬汉还在孤独地徘徊、流浪着。有研究者认为,黑塞一直在寻找的其实是“生活之母”,正如作家在作品中透露:“人类之母不是思想,……在她身上,慈爱与残忍合而为一”(23)赫尔曼·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第200页。,“母亲”就“是作为人类之母的生活本身”(24)赫尔曼·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第182页。。根据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思想,人应该放弃一切偏见和习惯看法,按事物直接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去把握,也就是说,人的使命就是要寻找生活与生命的本原。再回到《荒原狼》中赫尔米拉说的那句话“我们唯一的向导是乡愁”,就可以发现黑塞的“乡愁”所归不仅是德国故乡、德国古典精神,或是艺术、宗教、哲学所代表的超越精神王国,抑或是超越民族藩篱的形而上之世界主义理想,“乡愁”最终的归宿乃是“生活”。黑塞晚年时的宏愿就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它可以“赋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义。我要赞美自然,描述它的发展,后者到了某一时刻就会被命定的痛苦驱向精神,即自然的遥远的对极,而摆动在自然和精神这两级之间的生命就应该像彩虹横空那样绚丽多姿和尽善尽美”(25)赫尔曼·黑塞:《朝圣者之歌》,第48页。。这里自然、精神两级间绚丽多彩的生命,就是立足于“生活世界”之上勇敢追求真、善、美的生命。“生活之母”能以包罗万象的慈爱糅合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性分裂,能以甘于奉献的切实行动引导人战胜孤独,以新的自由而完整的“身体”形象参与到世界中来。
总体而言,黑塞的整体创作就是其终身追求“生命本原”、回到“生活之母”怀抱的路线图:早期,作家杂糅中国儒学与道家思想、佛教、基督教等多重宗教于一体,通过追求信仰、艺术等精神活动去寻找自我,希冀理想人性的养成和塑形。中期流寓瑞士之际,因受现实拘囿甚重,作家以自身为参照探究普遍存在的灵肉冲突困境,并在作品中进行多层次的身心对话交流。晚期的作家不再眷恋自我的精神象牙塔,在希特勒对全世界进行军事侵略的逼人局势中,他终于冲破灵魂困境,在作品中使人物置身“生活世界”的基石,并使其充分参悟人生的多重选择、多元意义,最终以贡献自我、服务社会的行动来实现人的积极自由。
在作家晚年的创作中,“乡愁”意绪中的孤独与惆怅转变成了灵魂的宁静,凝化为纯美的文字沉淀下来。作家晚年为其生活的瑞士乡村堤契诺写了散文集《堤契诺之歌:散文、诗与画》,在其中称堤契诺为“第二个故乡”(26)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散文、诗和画》,窦维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页。,这是“乡愁”落定为诗意现实的写照。在一篇名为《山隘》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不再欢呼雀跃,但却会用眼睛、心灵和每一寸肌肤微笑。面对香气袭人的土地,自己比当年邂逅时更加优雅、内敛、沉静和洗练。对故乡的思念,已经转化为所见的事物,世界因为自己会看了,也变美了。”(27)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散文、诗和画》,第6页。这样的文字透着历经艰难后的洒脱与宁静。他不再想和别人分享快乐,但却能由心而发、由内而外地感受美。在经历过战斗、分裂和痛苦的纠结后,他真正在孤独中丰满、净化了自己,实现了灵魂的“诗意栖居”。“乡愁”犹如灯塔般为他指引“归家”的路,使其能够在艺术创作的征途中,始终秉持“人”的核心要素及美的诗意追求,坚持将其作为与一切非正义、非人化现象进行斗争的精神力量,从而使他的创作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保持不衰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