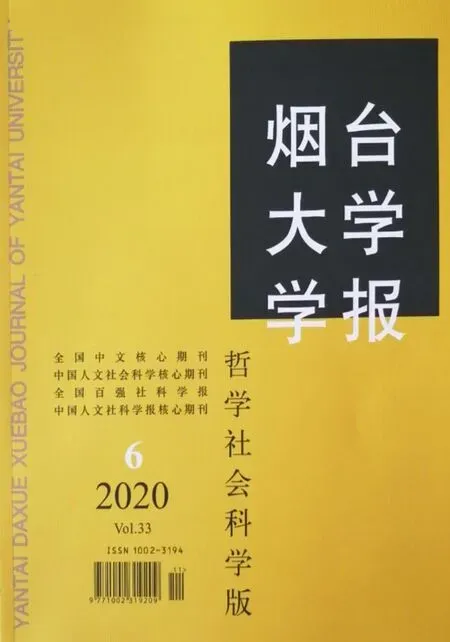“箫剑”与“鹏蝶”
——龚自珍对庄子美学的接受实践
杨艳秋,刘东影
(1.黑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9)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衰败,使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难以解答时势的难题,无法给予人们应对动荡和苦难的精神力量。龚自珍是集诸子新释、思想启蒙、中西交融三点于一身的近代学人,他既渴望向诸子学寻找经世之法,又不断自我颠覆向内寻求新生,并能积极打开视界,寻求来自外域的启示。
庄子是龚自珍的重要思想渊源。在近代学人涌向诸子学之时,庄子的思想以强烈的批判意识、自由洒脱的人生境界、自然恣意的文风、隐逸而又不可忽略的姿态,回归士人的视野。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具艺术气质的哲学家,《庄子》一书中既有绵里藏针的批驳,也有大张旗鼓的赞誉;既有奇特瑰丽的想象,也有寄寓深远的哲思。这促使龚自珍从人性之理的高度抓住人性新方向,以愤激辛辣的诗文慨论天下事,在反复求索中,其尊剑弃箫、志为名儒名臣的人生追求转化为箫剑并举、实为名士名家的现实选择。龚自珍承前启后之功,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上由古代向近代转折的标志地位。李泽厚先生认为:“龚自珍思想的特点和意义,主要是在于那种对黑暗现实(特别是对那腐朽至极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种种)的尖锐嘲讽、揭露、批判,在于那种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社会讥评,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之音。这种声音在内容上触及了最易使近代人们感到启迪和亲切的问题——如君主专制、如个性的尊严和自由、如官僚政治的黑暗;而在形式上,这种声音又响奏着一种最易使近代人们动心的神秘隐丽、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色调。”(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1页。李泽厚先生的分析指出了龚自珍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重要特征:批判精神、自由意识及其浪漫主义特色。这些特征既是他接受庄子的契合点,也是他实践庄子思想的重要表现。
一、龚自珍接受庄子的内外缘起
如开篇所述,晚清经学资源被开掘殆尽的现实促使学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领地,“当后来的学者试图在传统学术中寻找自己施展才智的领域时,不免眼光溢出经典之外,找到了同样可以施展文献功夫的诸子”(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1页。。 一种情况是如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用治经之法来治诸子,把诸子书当作解读经典的辅助资料。另一种情况是在治经的过程中把诸子书作为思想和文化资源,以表达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学术需求为先秦诸子成为考据学的中心内容提供了契机,此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将视线转移到诸子学上。在庄学方面先后出现了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和《庄子解故》,严复的《庄子评点》等著作,这些成果从文本层面唤起人们对庄子及诸子学的关注,肇始了近代美学启蒙的晞光。
伴随这一学术发展脉络,经世致用思想渐盛,以龚自珍、魏源为引领的一代先觉和启蒙者摒弃空洞的理学和繁缛的考据学,渴望激发主体自身的革新力量,以超出世人的眼光和魄力向僵化的儒学传统宣战,向被儒学挤压的道学、佛学以及外来文化求援。关于龚自珍经学之家学渊源,历来论述甚多,不再多议。而他接触西学的时间没有确切的史料记录,在1819年与魏源相交之后尤为重之,在《定庵文录序》中,魏源对此讲到,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龚自珍文集收入其增强国力、抵御外敌的论述《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多篇,均有吸收西学之处。
如果说龚自珍经学功底来源自家学传承,吸收西学是受衰世所迫,那么他发掘庄子思想的近代气息,对庄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则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心理禀赋和学术敏感,其思想似箫之悠长,剑之犀利,更如风雷卷动,有力地推动庄学在近代中国的活跃和复兴。
在美学层面上,龚自珍对庄子思想的吸纳与接受可以用两人具有代表性的意象“鹏蝶”与“箫剑”来表达。“鹏蝶”本身是自然界中独立的生命客体,没有束缚与牵绊,具有独特的自然属性和美学意味。从意象分析,“鹏蝶”是庄子自然美学、自由哲学的化身,是庄子思想物化的承载。而龚自珍的“箫剑”呢?在中国乐器史上,对箫的起源较有影响力的说法便是源自《庄子·齐物论》之中的“女(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郭象注此曰:“籁,箫也。”箫,既有源于自然的材质,也有源于自然的美妙声音,是审美化的产物,用以传达某种情感或意趣。而剑有着明显的社会化、功利化印迹,其工艺需经过烈火锻造,其功用是为着某种涉及利害的目的——防御抑或是攻击,而且剑还是一种身份象征。中国自先秦起便有尚剑的传统,在楚地道教发展中形成了法剑的信仰和佩剑的风尚。在《庄子·说剑》篇中也曾论及剑术与佩剑人之别,“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天子之剑……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也”;“庶人之剑,蓬头突鬓……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此篇与《应帝王》篇呼应,旨在说明为政当无为而治。这里所言之剑并非仅指有形之剑,实则指礼法制度、军事防御、外交政策等无形之剑,这是龚自珍褒贬时政、倡导改革的焦点问题。
据统计,龚自珍诗词中“箫”“剑”出现四十余次,并且连用时居多。箫剑之解,便如龚自珍的人生,建功立业的抱负与悠远缠绵的情思相生相悖。据说龚自珍在很小的时候曾患过一种奇怪的病,听到箫声就会发作。“黄日半窗煖,人声四面希,饧箫咽穷巷,沈沈止复吹。小时闻此声,心神辄为痴;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行处迨壮盛,此病恒相随。”(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4页。以下所有《龚自珍全集》引文,为行文方便,只注出书名和页码。儿时的病痛使他对箫产生了较为特别的感触,也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宿命。而从家学传承和家庭期待上,他从出生便背负龚、段两家的儒学标签与世族压力,几经官场消磨、世事沉浮,他的内心更加焦灼。“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在他的一生里,箫与剑是两种理想的化身,“一箫一剑平生意”,但这两者又难以相融。早年龚自珍并不满足自己的诗名:“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在32岁的时候,他就感慨这一箫一剑让他“尽负狂名十五年”(《漫感》)。“检点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气寒西北”,指在边疆的建功立业,“声满东南”便是他的文人诗名。辞官归去之时,他也自嘲道:“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己亥杂诗》第一七八首》)年岁增长,阅历增多,失败迭至,他渐感“剑气箫心一例消”,路过清江浦,龚自珍对灵箫的痴迷,源于他心中数十年不散的“箫剑情结”。而在他蓦然转身欲退而求其次时,却骤然而逝,其一生被箫魂剑气所系。由种种相生相悖的人生际遇所见,龚自珍一生在针砭时弊中思考,在颠狂叛逆中追索,其人格理想、美学思想虽受庄子影响较深,但始终未达到涤尽尘虑、自由逍遥的境界。
二、龚自珍对庄子美学思想的接受
龚自珍对庄学的吸纳与接受如庄学的隐逸一般,并不易察觉。但转换到文人、诗人的角色上,细读他的诗文,便显露出庄子美学的主导地位,其纵情自然的美学观念正是对庄子美学境界的追求。“自然”是庄子审美趣味积极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最早直接提出以自然为美的是庄子。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从审美主客体、人的思想情感到行动实践方面,“自然”都有所指涉和涵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天地有一种大美,有天地所孕育滋生的自然万物也是美的:“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庄子·列御寇》)“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庄子·秋水》)庄子认为,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热爱,应该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因此将这种审美感受具象化到文学作品之中也是自然而然的。艺术之中的自然不能以功利的心态去看待,而要采取一种“不以物累形”的超功利状态,以求得心理上的寄托和自然交融的情感,他所持的这种审美态度正是与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界定是一致的。(4)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页。他把“不以物累形”称为“游”,所谓“游心适性”就是要顺适人性的本然状态,让心灵处于虚静清明的境界,不因外物的变化而受到波动,不受任何羁缚地遨游在自然与宇宙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心灵与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龚自珍将庄子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与其“尊情”与“童心”的哲学思想融合,把天地万物化作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345页。。在《黄山铭有序》一文中,他通过对著名的黄山风景的描绘明确申述了自己的审美取向:“予幼有志,欲遍览皇朝舆地,铭颂其名山大川。甲乙间,滞淫古歙州,乃铭黄山。我浮江南,乃礼黄岳。秀吞阆风,高建杓角。沈沈仙灵,浩浩岩壑。走其一支,南东磅礴。苍松髯飞,丹朱饭熟。海起山中,云乃海族。云声海声,轩后之乐。千诗难穷,百记徒作。”(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15页。龚自珍把黄山作为自然美的典型代表,并置于天地之美的层面上加以赞美歌颂,俨如庄子容纳宇宙天地的审美气度。美的事物应该符合自然之规律,借助任何事物来表达意旨也需自然而然,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而经过矫饰、加工而变得扭曲的事物是丑的。正如《庄子·天运》中著名的“东施效颦”寓言,那种扭捏作态使人更加丑陋。对这一点,龚自珍也给予同样的贬斥,他在《病梅馆记》中斥责了文人画士“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的审美标准,使自然生长的梅树被斫直、删密、锄正,遭到人为的迫害和改变。
与道法自然的思想相协调,龚自珍主张文学创作要保护和展现人的自然本性,要“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庄子·天地》),这也回应着庄子对人们恶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庄子指出大言气势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使人们在睡梦中神魂交错,醒来时又身心不宁,人的心灵时刻遭受着各种纷扰和压制,难以自由发展,这是人生的悲哀。那么,如何摆脱这种悲哀呢?庄子提出的办法是在外要“无撄人心”,在内要“游心适性”。龚自珍也指出,人心受到摧残是社会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6页。。他把童心作为情感人格的立论之本,高扬具有主观精神的“人心”思想,热切追求纯真的心灵,赞许光明磊落的行为:“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太常仙蝶歌》),“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梦中作》)。其童心便是求真、尊真,简单地说就是要遵从自己的本心,以自然之道为尺度,不伪饰不造作,绽放生命本身的色彩。龚自珍倡导文学从自由的情感唤起人们的爱、真和对生命的尊重,这是龚自珍在求道体道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龚自珍既尊心、尊情,又善于移情,把自己内在的情感投入到客观对象上,把“我”之心志寄托于物,对象便从主体接受一种精神灌注,反过来主体又通过被观照的客观对象传达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在《己亥杂诗》中,龚自珍写心、梦的诗句俯拾即是,开篇三首诗均在反观内心。“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在这315首诗作中,有60余首诗发出追问、反问,甚是诘问,“千言只做卑之论,敢以虚怀测上公?”“呤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自别吴郎高咏减,珊瑚击碎有谁听?”“银烛秋堂独听心,隔帘谁报雨沉沉?”这些诗句反映出龚自珍对世事得失所做的观照、追索的心理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要摆脱外界的纷扰,进入虚静自由的审美境界,对龚自珍来说并非易事,他的内心经受着一番番挣扎。如同齐克果所言: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进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龚自珍的生命就是这样矛盾地存在,他烧诗、戒诗,主要是因为当他以审美身份欣赏的时候,强烈的痛感从主体中释放出来,他把诗文当作这种情感本身,烧诗文就是烧掉情感,是为了烧掉社会强加给他的角色和形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内心的真实自我,正体现着他的痛苦与悲哀。另一方面他又醉于诗,以诗文为武器,以诗文证明自己,像庄子一样,龚自珍中年以后诗文的锋芒并没有多少收敛,而在思考的深度上却有所加强,还写了不少讽刺性很强的“寓言”文章,如《捕蜮》《捕熊罴鸱鸮豺狼》等(8)邹进先:《龚自珍论稿》,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第19页。。他将自己鄙视的官场小人比为“蚊虻”“熊罴”等动物,经常是“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嗔”(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63页。,发出一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10)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第7页。,表现了他深恶痛绝的心理。魏源说“其道常于于逆”,“逆”意味着背离、叛逆、抗争和新生。(11)邹进先:《龚自珍论稿》,第23页。“慷慨、怅惘、悲愤、凄婉,完全适应和投合开始个人觉醒的晚清好几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绪和意向。从公羊到佛学,从浪漫诗文到异端观念,都是与封建正统的汉学考据、宋学义理相对抗着的。它们无一不开晚清之先声,为中国近代思潮奏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前奏曲。”(1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3页。在《宥情》一文中,龚自珍通过甲、乙、丙、丁、戊五人相互诘难的对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情有欲,他所说的情欲,实则依然是指童心,即是“童心来复梦中身”。心、梦、身、我交感,进入到了物即我、我即物、物我两忘的浑融境界。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在诗作中写出物我不分、物我相融之感,如同庄周与蝶之梦,鲲鹏与鯈鱼之乐。这种“移情”与庄子的“物化”极为相似,即在虚静的状态中,审美对象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心理毫无距离,由虚静的审美心理到通感和移情的艺术思维,这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也就如神工造物一般,不露雕琢痕迹,具有自然天成之美。
三、龚自珍诗文对庄子美学风格的实践
龚自珍以庄子的自然美学思想指导诗文创作,首先体现在诗歌中多用取于自然的意象,化用《庄子》表现手法之处也较常见。庄子擅长通过纵横无际的想象、奇丽变化的笔法、犀利有力的讽刺,把自然意象转化为抒发内心胸臆的载体。龚自珍也常把以神山、仙人、飞鸟、奇兽、异草为代表的意象转化成胸中的遐思,诗句充溢着生命的灵动和鲜明的情感。龚自珍爱花惜花,“不看人间顷刻花,他年管领风云色”(《己亥杂诗》第二○三首)。他写海棠、写丁香、写鸾枝花,细细品味,物态自成,栩栩如生,好似走进了它们的生命和情感世界之中,写水仙花宛如仙子,把宅中古桂“辛丈人”视为知己,形成了艺术上“倏忽万匠”“应物无穷”的神妙境界。在龚自珍写花的诗歌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是“落花”。在现实生活中,“落花”带着凋零衰飒之气,通常是用来表达失落、萧条的意象。但龚自珍抓住了“落花”能够因时因地而生或败的特点,其与时俱化的本性就是顺其自然的本真表现,把“落花”的意象变得更加复杂多义。龚自珍在身世飘零时自喻“落花”,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减字木兰花·人天无据》);同时他又借“落花”诠释他内心顽强的生命力,“难忘细雨红泥寺,湿透春裘倚此花”(《己亥杂诗》第二○七首)。在龚自珍眼中,这就是鲜活之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维摩昨日扶病过,落花正绕蒲团前”,又有向死而生之感。这些“落花”不仅没有因自身离开根茎的滋养和支撑而失去生命,还甘心把自身化为滋养新生命的泥土,延续生气,提升价值。当他呼朋唤友去城郊赏花,面对落花满地的枯败景象,却写出了“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西郊落花歌》)的气势。“落花”的强大生命力,犹如“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如雾”(《金缕曲·赠李生》),被赋予了新的审美意义。与“落花”同样具有这一特质的意象是“枯树”。“西墙枯树态纵横,奇古全凭一臂撑”(《己亥杂诗》第二二一首),一棵枝叶枯败的老树,它的枝干虬曲盘绕,似乎在尽力伸展双臂准备迎接岁月的磨炼和风雨的洗礼。它虽然失去了葱郁色泽,但姿态依然纵横挺拔,凭着钢筋铁骨在顽强地支撑,而这正是它的生命之根,绽放着生命的光彩,诠释出自然神奇之美。
其次,为达成自然之美,龚自珍不但强调意象的选择,更注重表现自然的本真之气。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这是说,生与死、美与丑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气。有气,则生则美;无气,则死则丑。这里的“气”是一种先于人和人性意识的自然存在,即便在世人的眼中被看作是丑的事物,如果它能葆有这种自然而生的天性、散发出一种鲜活顽强的生命力,那么,它就是美的。因此,庄子在《德充符》中塑造了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以及闉跂支离无脤、甕大瘿等一系列外貌异于常人或有明显身体缺陷的人,但从内在修养上他们却是充满德行、智慧和生机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命“通天下一气”,是由宇宙之气凝结而成的。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简单的美丑判断问题,而是一种天然旺盛并自我修为的境界,这种境界使丑向美转化,变臭腐为神奇。前段所论龚自珍诗中的“落花”“枯树”意象,便有此种深意。
再次,龚自珍践行“尊情”的文学主张,将真情融入诗文创作之中,强调:“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1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1页。因为有情才会有其哀其歌其痴其梦,“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半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第一百七十首)。其生命历程的风浪与点滴也因情而化成诗意,“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题红禅室诗尾》其三)。无论是想象的繁华、现实的冷遇,还是挫败中的深冷无望,在艺术的心境中,他总是能触到生命的本然,触及哲人的本思,触碰一种融现实与体验为一体的存在,达到无我、无旨、无哀乐的境界,有时他因狂喜而作,“下笔情深不自持”;他又不断地烧诗、戒诗,“此事千秋无我席,毅然一炬为归安”(《己亥杂诗》第六十首)。然后又破戒复作,且很有雄心壮志,“安排写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己亥杂诗》第二一一首)。他沉陷矛盾之中,一面追求经世伟业,“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另一面表露清游于“木樨风外”的心迹,想要“洗尽东华软红尘土”。他深感现实的嘲弄,“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一日所履历,一夕自甄综。神明甘如饴,何处容隐痛?沉沉察其几,默默课于梦。少年谰语多,斯言粹无缝。患难汝何物,屹者为汝动?”(《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六)对于这种现实处境,他一方面有乐观倔强的性格,“世事沧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己亥杂诗》第一四九首)。官场上的闪跌在他看来也不完全是坏事,“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寒月吟》)。“惠逆同门复同薮”更是体现了道家自然辩证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有盲目执拗的缺点,“终贾华年气不平,官书许读兴纵横”。乱世之中的龚自珍,不想逃避命运,面对人生厄运,他始终在守望新生之花。
复次,如何实现这种道法自然的境界?龚自珍关注语言表达的艺术,他在《己亥杂诗》开篇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这是他辞官后写下的第一首诗,意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走向,开篇两句将道、佛、儒三家思想融入其中,既想著书立说,又愿内观而得悟解,而这些感受要如何表现出来呢?即以卮言的方式,似泉水一般,自然而然且出之不尽地涌出。卮言,是庄子最核心的表达方式,“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寓言》)。每天在生活体验中顺其自然产生的思想和所作的表达,是最合乎自然本性和人性规律的。龚自珍强调文学语言要质朴平易,“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1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87页。。这里的“俗语”特指相对于“六经”典奥艰深之语而言,是不加修饰与雕琢的文字。在《题王子梅盗诗图》中,他又说:“菁英贵酝酿,芜蔓宜抉剔,叶翦孤花明,云净宝月出。清词勿须多,好句亦须割,剥蕉层层空,结穗字字实。”(1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505页。所有蕴含着精华的东西必有足够的酝酿期,在表现时又必须简单明了;繁冗芜杂的雕琢修饰,反而破坏了真正的美感。龚自珍在其文章中常常借用庄子的名句、典故,如嘉庆九年写《水仙花赋》多处借用如“姑射肌肤”“不事铅华”“是幻非真兮降于水涯”“写淡情于流水”“翩若自超尘”(1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09页。等等,明显可见龚自珍对质朴平淡的追求。他将水仙花写成一位仙子,亦有庄子文风的影响,与《逍遥游》中对姑射山神人的描写遥相响应,此之谓“淡然无极”的“至美”与“大美”。
最后,在诗文鉴赏中,龚自珍直截了当地批评那些鄙俗的艺术内容,毫不掩饰对浮华虚伪的厌恶。“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由艺术到社会,他以丰富的经历切身感受到充斥上层社会的虚伪阿谀、营私逐利的丑恶形态。他身为其中一份子,对此也在不断地忏悔,“忏悔首文字,潜心战空虚”(《戒诗》)。要把心空出来,不思虑任何事物,可是却“入定又出定,万虑亦纷纷”,不只是消除不了,还必须不断地写,才可以把甘辛全部写出来。这和庄子反对“乱五色,淫文章”“饰羽而画,从事华辞”的审美观是一致的。龚自珍对庄子“言不尽意”的语言观也十分尊崇,他认为世间的美难以用语言表达,想要通过文字领受这种美,也是极难实现的。因此面对眼前美不胜收的黄山景色,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慨叹,这既是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又与庄子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学理念相契合。
远承庄子“自然”美学之真谛,是龚自珍的诗文能够超越桐城派的重要原因。但同时,龚自珍还有兼容并包的可贵态度,他提出“莫从文体问高卑”(1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66页。,“骚香汉艳各精神”(1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443页。,以豁达的胸襟博采百家之长,因而他的文字具有一种大气磅礴的力度美,这种特质亦来源于其作为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庄子用“天籁”“昭氏鼓琴”抒发追求自然、平淡、无为之理想,龚自珍亦明确在诗中表达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所以志为道,淡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丁亥诗六十一首》)。龚自珍希望将自己的“箫”与“笛”化作“太古琴”,其“微吟”能如“天籁”一般能够拨动人的心弦,从而达到庄子“淡然无极”的审美境界。龚自珍有对外界的深刻认识,也有清醒的自知,他在诗词中引用过洪子骏《金缕曲》词:“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侠骨幽情、箫心剑态应是他的完美自况。
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开山人,龚自珍对庄子的接受与阐释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但从庄子思想和美学特质上说,他始终与庄子“隔”着一层,庄子以鹏、蝶的典型意象言志论道,反映着坚定自适、解放自我的哲学思维,呈现出崇尚自然、标举自由的美学特征,泽润了两千余年中国美学的心脉。而龚自珍过多地追求价值实现,他以庄释己、以庄解惑、以庄救世,有过多人工雕琢、人为渴求的成分,而未能实现更深的契合与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