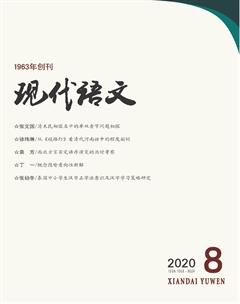民国时期东南亚华语学校国语文各分支的教学设计研究
摘 要:对民国时期东南亚华语学校国语文的四个分支——说话、读文、作文和写字(书法)的教学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教学语言广用国语的前提下,说话教学虽不单独设课,但比较重视,讲国语的气氛较为浓郁,而训练项目不全。读文教学教化色彩逐渐弱化,教学方法相对粗放,和国内的教学体例、教学内容基本一致。写字(书法)教学虽然一般不单独设课,但是常抓不懈。作文教学分值最重,形式多样,不仅目标明确,标准恰当,而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关键词:华语学校;国语文;分支;教学设计
研究华文教学史,就要研究民国时期的华文教学史;要研究民国时期的华文教学史,就要研究华语学校国语文的教学设计。这是因为教学设计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确定合适的教学起点与终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优化地安排,从而形成的教学总体规划。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方面的成果较少,只有《民国时期华校国语文考试研究》[1]、《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国语课程研究》[2]等涉及到这一话题,因此,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通常来说,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民国时期华语学校的国语文教学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语文教学基本一致,也是分为说话、读文、作文和写字(书法)四个分支。下面,我们就对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国语各分支的教学设计进行考察、分析。
一、说话教学
(一)不单独设课
在1941年颁布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中,目标的第一项就是“教导儿童熟练国语,使其发言正确,说话流畅”[3],并且规定六个学年都要开设说话课。在“初级各学年教材内容范围”的附注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说话课”的要求:“一,第一、二学年说话、读书、作文、写字四项作业,以混合教学为原则,每周教学时间共四百二十分钟”;“二,第三、四学年说话、读书、作文、写字四项作业,仍可混合教学,每周教学时间共四百五十分钟。如分别教学时,说话各三十分钟,读书各二百七十分钟,作文各九十分钟,写字各六十分钟”。在该课程标准的“高级各学年教材形式”附注中又提到:“上表说话类各项教材都应注重练习。‘教育部将编订高级小学‘说话教材纲要,以供参考。”[3]
就目前的相关文献来看,在东南亚华校国语科的教学中,单列“说话”的很少,就笔者所见,只有印尼的直葛学校开设了“说话”。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只安排“读文”“作文”和“写字”教学,有的也称作“读法”“作法”和“书法”。比如,马来西亚宽柔学校将国语文科的教学目的设定为:“读文——了解通常语言文字,引起读书兴趣,并涵养性情,启发其想象及思考;作文——养成儿童使用文字或语言发表之能力;写字——养成儿童有书写普通文字之知能”[4](P13)。这里对“读文”“作文”“写字”都有明确规定,却唯独缺少了“说话”教学。
至于东南亚华校当时为什么不将说话课单列,我们推测,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首先是受传统语文教学的影响。至圣先师孔子就倡导“讷于言而敏于行” “辞达而已矣”,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也不包括说话。先秦时期以来,语文的传统教育便体现出重书面表达、轻口语表述的倾向,主要是采取读文和作文两分法。其次是受国内教育方式的影响。如前所述,当时的教育机构为小学说话训练制订了相应的课程标准,不过,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全部贯彻执行,更多的情况是以混合教学为原则,将国语课分为读文、作文两块,或者是分为读文、作文、写字三块。再次是与东南亚汉语学习者的特殊身份有关。有学者指出,典型的传承语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水平表现为:发音、重音、语调等接近母语者水平,不过其发音系统可能是方言的;词汇丰富;能恰当地使用大部分语法;掌握与家人和社区成员之间语言互动的相关语用规则[5]。这里的典型的传承语学习者是指窄式定义的继承语学习者。而按照Fishman关于继承语的定义,民国时期华校的汉语教学应属于宽式的继承语教学。可以说,作为继承语学习的华族学生,从出生再到华校接受汉语母语教育,实际上是一直没有中断汉语的习得和使用,其语言水平是应该接近母语者的水平的。既然学生的说话能力普遍较高,因此,再单独开设“说话”课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二)普遍比较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多数华校的国语文教学并没有开设“说话”课,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是相当重视这方面的训练的。比如,马来西亚宽柔学校的国语文教学只有读文、作文、写字三门,但在“教学方法”中却明确规定:“在任何课文中,尚未开始教学前,须引起儿童学习之动机,其办法不外下列数种:(1)从谈话入手;(2)从布置环境,揭示挂图,提供直观物入手;(3)从时事或偶发事项入手;(4)从种游戏活动及模仿动作入手;(5)从他科作业,与本科教材有关处入手;(6)从观察自然现象入手。统上数法,完全在乎教师与儿童之谈话。”[4](P26)由此可见,宽柔学校虽然没有对“说话”单独设课,但却把教师与学生的谈话看作教学的一项基础工作。宽柔學校还在教学方法中将谈话的方式分为甲、乙、丙三级,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
甲 高级段——务求清晰自然,多采成语或典句,使儿童对过去所读之文字词句,知所应用。
乙 中级段——多用完整语句,但不拘文字修饰与词句结构,使儿童对事实发生兴趣,进而授以课文。
丙 低级段——务求浅现明白,引起有多闻多问之机会,如遇形容字眼,不妨加以表演,使儿童易于了解,按教学取材,以实物证明,最合方法。[4](P36)
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初级小学的国语课程也明确规定:“第一年,简单演进语法和会话的听取与练习;口述童话、物话、神话的听讲;故事的诵读和表演。”[6](P23)同时,很多华校每年都要至少举行一次国语演讲比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
有些学校还将国语视为语言统一的必要手段,要求学生无论是课堂交流还是课下交谈,都要使用国语。如马来西亚钟灵中学训导处为统一学生的语言,特意发布公告:
南洋教育之特色厥为语言统一,本校学生有千余之众,来自各地,方言各殊,彼此谈话当然以国文最最合。惟以地处英属,对于英语之练习亦关重要。本校有鉴于此,爰规定统一语言办法。凡在校学生限以国语或英语谈话,绝对不得夹用其他方言,以避免同学间之误会。考欧美各国凡二人在人群之中,以不通用之方言讲话者,即为最不礼貌。青年学生尤宜学习礼貌,操练上等谈话,养成优良风度。嗣后各级学生有被发觉不履行是项规定者,将受申斥并处罚。至若贩夫走卒之粗俗口吻与油腔滑调,更非本校学生所当仿效,概在禁止之列。愿全体学生共勉之
钟灵中学要求学生談话时必须使用国语,这样才是“操练上等谈话”,而绝不能夹用其他方言,以此营造出讲国语、用国语的浓郁环境和良好氛围。
(三)内容不够全面
在1941年颁布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中,对“说话”教学有明确要求:
(1)说话的教材,教员应预编案例,作为语言材料。语料分三种如下:
①有组织的演进语料,每套要有一个题目;每句要单说动作的一步,但不可太繁琐;要从一个主位说起,并且要容易看,容易做,每套的句子不可太多。
②会话的语料,要集中在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上,而且要有一个有趣味的题目。
③故事的语料,要合于儿童生活。
(2)问答、报告等的练习,要就实际生活中选定题材。
(3)演说、辩论等的练习,除由教员规定题材外,亦得由儿童自由选定题目。
(4)国音的分析和拼合,和各种语气、语调的练习,教员应编定进度表,分期实施。[3]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小学说话训练的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有组织的语言材料的练习、有趣味的日常会话、故事等的讲述练习、报告等练习、简短的演说练习、国音拼合等练习。这一时期的著名教育家沈百英也主张,小学说话课的形式主要包括六种:日常用语、演进语料、日常会话、简短故事、普通演说、浅易辩论[8](P28)。
与之相比,东南亚华校国语科的“说话”训练就显得相对单薄一些。宽柔等华校虽然也比较重视“说话”教学,具有一定的说话训练意识,但是有关说话训练的项目却不够全面、具体。从上文华校的“谈话”与“谈话方式”来看,其内容至多包括三个方面:日常用语、演进语料和日常会话。再从宽柔学校国语科的教学要点来看,该校是将说话、读文、作文、写字进行混合教学的,其中涉及说话的内容主要是国音的声韵问题:“高级段之读音,务须注意国音之声韵。切记朗诵每一句中,有长短快慢之分别;每一课中,有起承转合之语气。最好读文与谈话无异,使闻其声者”,“中阶段之读音,亦须注意国音拼音法”[4](P47)。其他说话课的内容则概未涉及。
就东南亚华校国语科谈话的教法而言,与专业的说话训练也有一定差距。从相关资料来看,在华校国语科教学中,对说话的声音、语调、礼貌、技巧及矫正方法都很少涉及,对不同年级、不同水平学生的说话要求也不够具体、完善,因此,专业教科书中有关说话训练的内容在国语教学中难以完全体现。同时,以当时颁布的国语课程标准相衡量,华校的谈话训练也显得不够系统、健全。
二、读文教学
(一)教化色彩逐渐弱化
受时代背景及国内教材的影响,民国早期的华校国语教科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与道德色彩。课文中提到,凡是中国人,都要尊重中国的国旗,购买中国国货,爱护自己同胞,人人要把身体好好锻炼,以报效祖国,爱国意识十分浓厚。同时,宣扬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辉煌,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不过,华语教材的当地化、本土化意识较为淡薄,对华侨华人居住地的历史文化很少提及,即使收入教材,有时也与事实不符。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华校国文教学的教化意味就不那么明显了。比如,在1941年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教学要点”分为“意义、文字、插图和编排”四个方面。而在宽柔学校的“教学方法”中,就没有包括“意义”的相关内容[4](P67)。
(二)教学方法相对粗放
很多东南亚华文学校都制定了国语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如宽柔学校将其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个阶段,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其中,对“读文”高级阶段教学方法的规定尤为详细:“高级段之读音,务须注意国音之声韵,切记朗诵每一句中,有长短快慢之分别;每一课中,有起承转合之语气。最好读文与谈话无异,使闻其声者。可以了解词意,鼓励儿童自寻字典,预习功课。课文稍长者,令儿童轮流诵读,如有错误,立即指正。多采默写默读方法,避免随声附和之积习。”[4](P47)可以看出,这里主要是涉及到读文的声韵、语速、语气、诵读、默读等方面。至于各学年的教材形式、教材内容,以及读文教材的文体分类、文法组织,则付之阙如。
我们不妨将宽柔学校“读文”的教学方法与当时国内的课程标准进行比较,这里以1941年颁布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第二学年的读文为例:“(1)有组织的语言材料;(2)简易有趣味的日常会话;(3)简短故事的演述;(4)音的分析和拼音;(5)生活故事、自然故事、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的记叙文;(6)书信、布告等的实用文;(7)儿歌、杂歌、谜语等的韵文;(8)继续第一学年各式单句;(9)简易的复主语、复宾语、复述语、复附加语等的各式单句;(10)字和词;(11)主要的标点符号;(12)浅易的儿童图书;(13)国音注音符号。”[3]与国内的课程标准相比,东南亚华校对读文的规定就不够具体、明确,而失之于笼统、模糊,这就会导致在实际教学中缺乏可操作性。总体来看,南洋华校国语文的教学是比较粗放的。
(三)教学体例与国内一致
这里以马精武等编著的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为例,来考察当时东南亚华校是如何安排“读文”的教学过程的。在此书的编例中,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主要内容有:
本书每课的项目分教材、教学目的、教学时间、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各科联络和参考资料七个部分。
教学过程:
一.动机:各课均列引起儿童学习动机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由谈话或问答入手;由时事或偶发事项入手;由观察图片和实物入手;由他科的作业与本教材有关连者入手。
二.预习:此项由教师先加指导,使儿童于课外行之,以培养其自学的能力。
1.概览。2.摘记及检查。3.参考。
三.默读及考查
1.默读。2.考查。
四.解释
1.补充订正。2.解释疑难。
五.朗读 注意读音的正确与否和声调的适当与否,分为:指名讀、接读、分组读、以及教师的范读。
六.深究 此项应用思考过程,重在训练儿童的思考力及读书能力。分为二目:
1.事实;2.文字。
七.吟味。
1.想象;2.美读。
八.整理
1.段落大意;2.内容纲要。
九.练习
1.问题解答;2.讲述;3.造句;4.节短;5.加长;6.补充;7.改造;8.仿作;9.补充阅读;10.其他。
十. 表演;各科联络;参考资料。[9]
与同期用于国内的相关教材相对照,我们发现,两者的内容和体例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见,民国时期的很多华校的国语教材都是来自国内的,其内容也都是针对母语教学而设计的。同时,在国语教学体例、教学方法方面,也是仿效国内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如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的《初级国语教学法》[10]就是如此。
三、写字教学
与说话教学相似,民国时期东南亚国语科的写字教学也很少单独设课,只有少数学校将它列为一门课程。如印尼的直葛学校就规定,写字课程在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共开设四个学期,其中,小二每周一节,小三每周两节[11](P37)。大多数华校都是采取混合教学的方式,将写字与读文、作文放在一起进行训练。同时,有些学校对学生的课下写字还有严格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奖惩措施。一是每周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大小楷作业。如钟灵中学1949年1月25日国文学科会议通过一项硬性规定:在校学生“大楷每周三页,小楷二页”[7](P35),该校还将平时的写字练习计入国文科成绩,占比为10%[7](P39)。二是钟灵中学每学年都要举行次数不等的中文书法比赛,学生不得无故缺席,而且比赛的结果是计入平时成绩的[7](P35)。
四、作文教学
(一)分值最重,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对作文教学极为重视,在很多学校的国语科中,作文所占的分值都是最高的,由此可见一斑。钟灵中学1948年1月3日的教研会议决定,国文科批卷定分办法如下:作文占全部分数的40%;测验占30%;日记占20%;大小楷占10%[7](P39)。如果将日记也归于作文之中,那么作文所占的分值就达到了60%。
东南亚华校对作文的训练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这里仍以钟灵中学为例,其作文训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作文课,每两周一次。二是日记或阅读报告,这也是作文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月25日钟灵中学国文科会议决定:“日记每周三篇,如改作阅读报告亦可。”[7](P21)三是尺牍,它也是作文训练的项目之一,该校有《语体新尺牍》[12](P21)等专门教材,初中一年级每周还开设有一节尺牍课。不只是钟灵中学开设了尺牍课程,其他学校也是如此。如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普通补习科1—4年级,每周有2节尺牍课[6](P38)。华语学校之所以普遍重视尺牍训练,周逸休、陆宝忠曾在《尺牍课本》的序言中道出了个中缘由:“尺牍文字乃为实用文中之最重要者。乡间父老送子弟入学第一目的即为写信记账,良以书信账目实为日常生活所必要者也。然今日小学校中之国文科关于实用文字素少注意,乃至高级小学卒业之学生尚不做一文字清通之便条。为父母者于是叹息学校教育之无用,然是岂尽为学校教育之过哉?小学国语书籍缺少应用文字之教材亦一大原因也。”[13]
除了作文课、日记或阅读报告、尺牍这三个常规教学项目外,钟灵中学还有两项课外活动,也与作文训练有关。一是学校的壁报,该校规定:“各国文导师应负责指导各班学生关于壁报之一切事宜,以收宏效”。二是每年两次的全校作文比赛,强调全体学生必须参加:“作文比赛时应通告学生不得任意弃权,违者从严扣分”[7](P29)。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参加作文比赛并不是学生自愿的课外行为,而是国语文训练和考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目标明确,标准恰当
东南亚华校作文的教学目标与国内基本一致,主要是养成学生用文字或语言发表之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个学校在作文的选题与标准上下足功夫,做足功课。
就作文的选题来看,马来西亚宽柔学校规定:“命题性质,合于儿童生活,便于儿童发挥,引起作文兴趣”[4](P31)。可见,这一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于儿童生活;二是便于儿童发挥;三是引起作文兴趣。它基本上是合乎民国时期国语教学的权威标准的。俞焕斗的《高小国语科教材和教法》在论及儿童作文“命题法”时,也指出:(1)利用机会命题;(2)儿童自己命题;(3)多出题目,供学生选择”[14](P122)。
就作文的标准来看,马来西亚宽柔学校对每一阶段学生的作文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中年级之作文,口述笔述并重”[4](P27),“高级阶段之作文范例,可以思想无误,层次分明,格式恰合之实用文、普通文为主”[4](P21)。就高年级的作文而言,主要有三项标准:一是在立意上要思想无误;二是在逻辑上要层次分明;三是在文体上要格式恰合。俞焕斗在论及作文范例时,也列出了四条标准:(1)程度适合;(2)思想正确;(3)层次清楚;(4)字句适当[14](P125)。除了第一条之外,其他三条与宽柔学校的标准基本重合。
(三)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1.从生活中激发热情。宽柔学校在讲作文教学方法时提到:“应以儿童经验所及,或想象所至为依归,利用时令及环境中已发现之事实为主体”。这基本符合俞焕斗作文教学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随时随地指导儿童抓住创作的机会”,他还指出:“当老师的最好能在课外常常和儿童在一处游息,以便在休闲生活中随时随地指导儿童抓住创作的计划,使能自由发表。照这样办,即使儿童毫无创作天才,但指导的结果也必定有相当的成绩。”[14](P122)
2.文体顺序安排合理。马来西亚宽柔学校对学生的作文实施分层次、分阶段、分文体教学,低级段的作文,以造句、记述故事为主:“低级段之作文,可令其缀字造句,进而记述故事”。到了高级段,随着水平的提高,则以实用文和普通文为主、说明文和议论文为辅:“高级段之作文范例,可以思想无误,层次分明,格式恰合之实用文、普通文为主……说明文、议论文辅之。”[4](P21)可见,其作文教学的安排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3.“审慎”和“迅速”兼顾。就当时学校作文教学的实际状况来看,比较重视学生“审慎下笔”的功夫,却很少注意到“迅速”这个条件[14](P125-126)。相对而言,东南亚华校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做到了“审慎”和“迅速”兼顾。如马来西亚钟灵中学就有严格规定:“本学期之学生作文……应当堂交卷”,“作文时间,学生须带笔、砚、墨,并当堂书写,以便学校当局临时检查”[7](P23)。
4.开端和善后照应。有位老师在探討作文课的状况时说到:“教师轮到作文课时,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文题,学生交卷后,经增删斧削,恒费了一番大力。分发之后,学生也只在文卷中一察其分数或等第,而内容如何,甚少详加研审。教师因时间不足,断不能一一详为解释。相沿如此,可谓两失其益。在教师方面,对批改文簿煞费苦心,而在学生方面,仍未见有何得益。”[7](P23)对这种老师、学生“两失其益”的问题,通常是采取以下方法来加以解决:首先,文题的选择应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文题要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其次,要口述和笔述相结合,先让学生说出来,再让其写出来;再次,不能只给学生一个文题,而不讲怎么做,要结合学生口述的情况,重点讲解作文中应注意的事项,同时给出范例;最后,批阅的作文发给学生后,不仅要求学生仔细揣摩、详加研审,还可以要求学生按照批阅的意见重新修订一遍。这样一来,作文教学的开端和善后就可以照应到位,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从而有效改变“两失其益”的局面。
5.作文练习保证数量。作文教学如果要取得成效的话,首先要有一定的数量作为保证。除了作文课、尺牍课等课堂教学外,东南亚华校还在课下、假期等时间给学生布置作文任务。如1949年7月19日,钟灵中学国文科会议决定:本学期作文之篇数规定在秋假前四篇,秋假后四篇,如遇作文时间适值假期,亦须嘱学生补做[7](P34)。
作为在中国政府注册的海外侨校,民国时期的东南亚华校一直遵守相关机构的政策与规定。从国文科教学的四个分支来看,读文和作文颇受重视,不仅课时多、作业重,而且安排周全、规定详尽。这是因为华侨华人子弟接受华语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要通过读书来汲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通过写作来表达华夏文明的精神气度。而写字(书法)教学和说话教学一般不单独设课。写字、说话都是学生的基本功,它们贯穿于国语科乃至所有学科教学的全过程,因为说好中国话(尤其是国语)、写好中国字,是每位华夏儿女最基本的文化素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体来看,东南亚华校国语课的教学设计是比较符合当时学生的实际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不仅如此,通过说话、读文、作文和写字(书法)教学,还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了各种文明的交融互鉴。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华校国语科的教学设计也可以为当今的华文教育提供深刻的启示与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于锦恩.民国时期华校国语文考试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7,(6).
[2]于锦恩.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国语课程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8,(3).
[3]1941年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EB/OL].http://www.pep.com.cn/xiaoyu/jiaoshi/tbjx/kbjd/jxdg/201008/t20100818_663535.htm.2020-06-23.
[4]马来西亚宽柔学校.宽柔校刊[M].马来西亚:宽柔学校,1941.
[5]曹贤文.海外传承语教育研究综述[J].语言战略研究, 2017,(3).
[6]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纪念刊[M].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1938.
[7]马来西亚钟灵中学.钟灵中学校刊(复兴第四号)[M].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1949.
[8]沈百英.小学说话科教材和教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9]马精武,朱文叔.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37.
[10]新加坡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初级国语教学法[M].新加坡:上海书局,1955.
[11]印尼直葛学校.印尼直葛学校纪念刊[M].印尼:直葛学校,1934.
[12]金湛庐.语体新尺牍[M].上海:中华书局,1936.
[13]周逸休,陆宝忠.尺牍课本(初级小学用)[M].新加坡:众兴出版社,1938.
[14]俞焕斗.高小国语科教材和教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