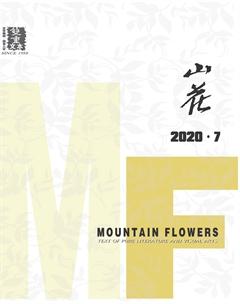翁丁记?
黛安
烟火翁丁
火塘在屋子正中。没有灶,一只三角铁架支在火上,大锅,小锅,大壶,小壶,做饭,烧水,都在这只架子上。它支撑着翁丁佤族一家人的日子。火塘不熄,常年燃着粗而长的木头。北方的乡下,灶膛里多是玉米根、玉米秆、玉米槌、麦秸,从灶膛一眼就望见了田野。那些柴禾不耐烧,火苗轻飘,柔软,需要不停地往灶下续柴,人不能离开。小时候夏天烧一顿锅,汗从头发梢流到脚后跟,完了往门口一站,风一吹,真是美!所以,老家有句话:哪里凉快?棒子地头,饭屋门口。棒子地,就是玉米(苞谷)地。夏天在地里干活,玉米秆子高过人头,叶子多而密,唰啦啦,唰啦啦,又闷又热。到了地头,一钻出来,小风一吹,顿觉清爽。我们偶尔也烧木头,但都是用斧头劈成窄细的木条,或干脆是捡来的枯枝。翁丁不。翁丁大气。翁丁也种玉米,但秸秆不烧,砍下来任其烂掉肥地,只烧木头。木头粗的仿佛人腰,细的也要阔于碗口。而长度,若竖起来,比人高是很寻常的。佤族一词本意即为住在山上的民族。翁丁四面皆山,林高树密,有一种树,生来就是为了烧火的,越砍,长得越旺。还有,森林里,总有一些树在莫名死去。或许是像人一样老死的。死去就要砍下烧火。死去的树在火光中重生。所以,在翁丁原始部落,随处可见一堆堆码得齐齐整整的木头。走近了,会看见一根木头的年龄。没有两棵树的年轮是完全一样的。就像人的指纹。那是翁丁人的日子,是日子里的刻度和温度。木堆旁边闲置着一把弯刀,一只竹篓,一副篾筐,一绳晾晒的各色衣物,像一张张油画,静立在岁月里,任时光像一只猫,轻轻在上面走过。
木头大,人就不会被火拴住了。把添满水淘好米的锅往铁架子上一蹲,就去忙其他活计了。日子一天到晚,也说不上多忙,但也闲不住。猪在圈里,鸡在街上,芭蕉、茶树、水稻、谷子、玉米、菜蔬在地里,地在山上,山在寨子外。每一样都在时空里排好了序,等着人去收拾。织布机随时拉开着架势,蒸锅米的时间就能坐下来再织一小截布。翁丁织布一直用最古老的腰机织法。腰机由几根木棒、木刀、竹签组成。人坐下后,双脚蹬住撑经木的两端,绷紧经线,然后一遍遍地提综、穿梭、打纬。人们日常的衣服床单围巾背包,哪一样都离不开布,都要女人一毫米一毫米经经纬纬地织出来。布的颜色,没有谁统一规定,织布的女人想怎么织就怎么织,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织完往那一挂,好看。高山流水里长大的女人,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蓝天白云,红花绿草,看到的都是大自然最本真最纯粹的颜色,对美的感知,是天生就存在于骨子里的。那布是艺术美的范畴,更是寻常百姓日子的一部分。翁丁人的日子,都是翁丁人自己一样一样经纬分明地整理出来的。
大木头是经历过世面的。里面有天地日月,雪雨风花,经了沧桑的大木头懂人心。大木头只管自己烧,不用人守着。火苗真大,真多。锅底下满满的鲜艳的火苗,锅的四周也是满满的鲜艳的火苗。火燎着锅盖了。
翁丁偏,二三十公里外,翻过几座山,就是缅甸了。仅仅七十年前,翁丁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屋子一律为中国南方典型的杆栏式二层茅草房——一楼养猪啊牛啊羊啊鸡啊狗啊,二楼住人。我来的时候,翁丁正值雨季。翁丁的雨,一下就是几个月。在雨季,只要哪天还没下雨,那一天的夜或黎明就不会按时到来。一天中,一定要等到至少一场雨。也许就是雨的缘故,茅草屋脊陡,坡长,密严,只向天开了一扇小芭蕉叶大的窗,整个房屋像一间暗室。可是火让茅草房里明亮起来了。黑篾桌亮汪汪的,黑竹凳亮汪汪的,黑铁锅亮汪汪的,黑水壶亮汪汪的。竹木的黑立柱亮汪汪的,竹木的黑地板亮汪汪的,竹木的黑墙壁亮汪汪的,竹木的黑屋顶亮汪汪的,蜷在火塘边睡觉的大黑猫亮汪汪的。常年不熄的火塘,日日夜夜的烟熏火燎,屋里什么都成黑的了。翁丁是一幅油画,黑是它的主色调。那是岁月的黑衣衫,是日子的黑包浆,是一个民族的黑皮肤。在色彩的王国,黑侵蚀并战胜了其他任何颜色。黑是一只罐子,把所有其他的颜色都一一盛在了里面。主人不在跟前,火把主人的日子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都照得亮汪汪的了。
也有不黑的物件。一摞洗净的瓷碗,亮汪汪的,是月亮栖落在了茅草房里;几瓶去年采的野蜂蜜,亮汪汪的,是金子融化在了茅草房里;三两个垂挂在钉子上的七色手织布包,亮汪汪的,是一抹彩虹升起在了茅草房里。它们是画面恰到好处的点缀。它们让黑的更黑,让黑迸溅出火光来。
最黑最亮的是火塘正上方一米见方的竹木置物架。它在佤语中有一个质朴的名字:格啦。佤语只有语音,没有文字,把佤语的发音用汉字写出来,就像看着照片给人做了一件衣衫,不知合不合体。我所在的小黑客栈,格啦由五纵两横七根木条框成,上面铺一张篾片编的席子。佤族人炒菜一向不吝食油,柴火又旺,热锅烹沸油,饱含油花的浓烟直冲向格啦。年深日久,格啦覆满了厚厚的油污,晶亮的油珠垂懸欲落。置身事外的异乡人,如我,真想拿把弯刀刮一下,刮出格啦竹木原本的素色面目;或者,弃掉旧的,换一架新的。但没有谁家这样做。只有异乡人才那样想,因为他是异乡人。那不是他的日子。异乡人是落到格啦上的一滴水,浮在表面,渗不进去。他在那里看不到自己的归宿。黑得透亮的格啦,是佤族人眼中的美物。佤族人的每一餐饭,每一顿烟火,忠心的格啦都无声地如实记录了下来,层层覆盖,层层叠加,像太阳覆盖太阳,月亮叠加月亮。它是智者,是翁丁最持久的写实主义者。
格啦上,什么都放。竹篓,篾筐,布口袋,眼镜,红梅牌的香烟盒,十字形的木质绕线器,芦笙,笛子,葫芦丝,独弦琴……想用时,手一伸就取下来了;用完了,随手就搁上去了。有的就长久地闲置在那里,比如墨镜。小黑家的格啦上就放着一副墨镜。墨镜是适宜油烟熏烤的么?每个物件都是黑油油的,触摸时,有浓郁的粘滞感。日积月累的日子粘住了手,把掌心的纹路一遍遍拓下来了。
小黑客栈家的男孩泥块七八岁,正是顽皮的时候。我老家说,七岁八岁狗都嫌。因为能作。不分地域,哪的孩子都一样,没有他们作不到的地方。一天,泥块把一个鸟窝从树上整个端下来捧回了家,里面有四颗小拇指肚大小的鸟蛋。泥块把鸟窝放在一只小竹篾筐里,扣上盖子,放在格啦上让它熏着。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泥块每天都把小蔑筐抓下来看。我问他,能孵出小鸟吗?能。他很肯定地回答。孵出来过?我又问。嗯。他想了想。我说,熏了这几天,也不知现在鸟蛋里面什么样了,是不是正在长羽毛。泥块看了我一眼,问,你想看看吗?我看着那几颗鸟蛋,犹豫着。他已经捏起一颗,我突然明白了他要做什么,想阻止,鸟蛋已经落在了地上,薄薄的壳摔破,蛋液流了出来。我虽然预料到了,还是禁不住叫了一声。一个生命,就此结束于我的好奇与一个孩子不安分的手中。泥块捡起一根小细木棒,拨拉着蛋液说,看,它正在变成鸟,这是它的头。我伸长了脖子,想从粘稠的蛋液里看出生命形成初期的奥秘。然而一切都停止了,我们阻止了一只鸟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作完,又把盛着另外三只鸟蛋的小篾筐放回到格啦上。火塘宽厚地容忍了我们天性里的顽劣和任性。
格啦之上,还有一个几乎纵贯整个茅草屋的大置物架。十几根碗口粗的整棵的竹子,担在两根粗大的檩木上。照例,平铺上一张竹席。小黑客栈家,两捆新破的竹条撂在上面,越熏,竹条越柔韧,编出来的物件越结实。十几个新编的竹篓、竹凳、篾桌、篾筐也扔在上面,横七竖八。人丟上去就不管了,好像忘了。就是要把新的放老,熏老,烤老。什么时候足够黑了,足够老了,新鲜易折的劲头没有了,好了,拿下来了,顺手而好用。时间,在烟火中,把生活细节中易伤害人的锐气一一消磨掉了。物件是,人亦如此。翁丁的人夫妻不绊嘴,婆媳不吵架。都和和气气的,安安静静的。我说你听。你说我听。那些为人处世的尖锐的棱角,一代一代,让火塘的烟火熏烤得柔软而温驯。那是整整一个民族的和睦与谦卑。
蹲上锅就去忙的主人闻到米香回来了。回来就垫块毛巾把锅端了下来。米熟不熟,她不用掀开盖子看就知道。是木头的烟火告诉她的。佤族的每个人都是木头的密友,懂得木头的语言。此刻,不见了火苗,火塘里红彤彤的,是木炭了。先前又大又多又鲜艳的火苗刚好蒸熟了一锅米。麻利地换上炒瓢,淋上油,把柴往里推推,大木头噗一声重新噼噼啪啪燃起来。不管什么菜唰一声倒进去,烟火中,香气冲出来,茅草屋整个都香了。
烟火柔韧而柔软。烟火中,翁丁的日子是圆的。吃饭时,一家人围着圆圆的篾桌坐一圈。小黑客栈老板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问他们小夫妻,如果国家允许,还要再生吗?他们十分肯定地说,生。我戏谑地问,不会越多越没人管你们吧?他们吃惊地看着我,怎么会?不会的。不可能。从来没有过。弟兄几人,必定有一个要养父母的,与父母同住。他们认真地反复说。我信。小黑的奶奶跟着大儿子,大儿子没有了,跟着大孙子。但是,只要有点风吹草动,谁有能力谁就跑在前。就在昨天,小黑还开车带奶奶去县城看病,说奶奶胃不舒服。我想起我们村曾经的宝玉二奶奶。年轻时,她扑扑棱棱生了五个儿子,可是到头来,自己不得不在池塘边搭了个窝棚,夏天对着一池塘的荷花冬天对着一池塘的冰过日子。孤寒是一根弹性十足的橡皮筋,它一点一点拉长着宝玉二奶奶的寿命,使她九十九岁时仍种着一畦菜养着一窝鸡并且每天出来寻下在各处的鸡蛋。后来,五个儿子一个接一个相继死去了。还是她的大孙子,那时已经六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把她接回了家。然而宝玉二奶奶很快就得了小脑萎缩,谁都不认识,天天挎着一个小篮子嚷着回娘家。她最终死在了那个窝棚。孙子找到她时,她手里握着一张照片,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说,那个女人是宝玉二奶奶的娘,那个小女孩,是宝玉二奶奶。
佤族信奉万物有灵,从不训斥小孩子,说会把小孩子的魂吓跑,所以规矩也是活的,方里有圆。吃饭时,长辈没坐下,儿孙谁都不可动筷。然而一旦吃起来,孩子们就随意了,可以用手抓着吃,可以躺在地上吃,可以没吃饱玩够了回来再吃。不高兴可以哭,可以闹。没有约束,没有训斥,自由如鸟。不急,小孩子的性子是生的,像一块洋芋,火塘还没把它烤熟。熟了就软了。篾桌就在火塘旁。火光一跳一跃,照亮了一家人黑红的脸。
翁丁的夜也是圆的。忙碌了一天,晚饭后,一家人终于可以围坐在一起好好说话了。这时候,老人通常要抽烟。烟是自家种的,烟叶是自家烤的,烟袋也是自己做的。竹木做杆,竹根做烟袋锅子。烟锅很特别,像一只仰面朝上的大麻雀。烟杆一尺长的二尺长的二尺多长的都有,弯下腰,伸进火塘头一偏一吸就点着了。不用烟袋的,就吸水烟。一只大竹筒水烟袋杵在地上,人抱着,脸扣在上面,呼噜噜,呼噜噜,水在里面滚。对于北方人来说,不知他们是吸还是吹。小黑客栈家,小黑的父亲老黑往往这时候会从格啦上取下芦笙或单弦琴,吹一段,拉一段。泥块五岁半的妹妹来了兴致,不是唱佤族歌就是跳甩发舞,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她鲜亮活泼得像一滴跳跃的水珠。火塘像一个慈祥的老者,没有言语,却什么都看在了眼里。
深夜,人睡了,牛睡了,猪睡了,鸡睡了,鸭睡了,猫睡了,鸟睡了,虫睡了。都睡了。连天空和大地也睡了。而火塘不睡,大木头不睡。火塘是夜晚的眼,是夜晚的看护神。大木头把火苗小心地藏进体内,只隐忍地亮着,暗红的光若有若无。茅屋内黑色的物件仿佛消失了,与黑夜彻底融为了一体。火塘像一只忠实的狗,倾听着一家老小起起落落的呼吸。晨起,只需把木头拨一下,对着微弱的火光噗——噗——噗——地吹,大木头就又烧了起来。烟火中,翁丁一天的日子又开始了。
油彩翁丁
天地间都是雨。每一根茅草都吸足了水,闪着湿淋淋的光。翁丁,黑褐色的茅草屋仿佛一群打湿了翅膀的鸟雀,静立在群山中。雨顺着茅草流下来。一条条亮汪汪的雨线,一粒粒圆滚滚的雨珠。
几户人家的茅草呈浅黄色。那是不久前新换的。落在上面的雨也浅黄而新鲜。再淋几场雨,再晒几场太阳,它们也成黑褐色的了。新的最终会成为旧的。旧到朽,又重新新起来。在翁丁,时间不偏不倚,会让一切趋于一致。
雨水顺着北高南低的弹石路往下淌。淙淙流水,叮叮咚咚,在古老的村寨弹响了一把竖琴。石头是就近山上采来的,大的小的,凹的凸的,尖的圆的。翁丁人随意惯了,当初也没怎么好好铺,似乎撂在那里就完了,不平不整的,石上奔跑的雨水激起了小小的明亮的水花。背着竹篓的女人不知从哪里才回来,光脚走在雨中。雨水没了她的脚踝,裙角是早就湿了的。一生见惯了雨的女人,从不会在雨中慌乱地奔跑,她们走得不紧不慢,从容有致。天上所有的雨水,地上所有的石头都认得翁丁的女人。翁丁的女人,软的时候是一滴雨,硬的时候是一块石头。她们一生行走在软与硬之间,自由如风。
从初夏到秋,雨断断续续,但每天都要下,像是翁丁的日记。只要哪天还没下雨,那天的时间就停止了行走。雨季,光阴和雨像两个结伴而行的旅人。雨迟了,光阴停下来等雨。雨一来,那一天就平淡无奇地过去了。雨季的翁丁,一天中一半的时间,都是浸在雨里的。时间在翁丁以雨的形式呈现,湿答答地鼓胀着。
那时候,水稻浸在雨里。茶树浸在雨里。苞谷浸在雨里。几百年的大叶榕小叶榕浸在雨里。无数牛头骷髅浸在雨里。人头桩浸在雨里。青绿的大芭蕉浸在雨里。喇叭形的黄蝉花浸在雨里。此起彼伏的鸡鸭猪狗的叫声浸在雨里。青蓝的炊烟浸在雨里。人的喜悦和忧伤浸在雨里。翁丁远去的历史浸在雨里。雨水是最好的油彩,把覆着阿佤山茅草的翁丁涂抹得湿润淋漓。
阿佤山多茅草。茅草卑微。然卑微的茅草几乎承载了翁丁所有的美。茅草的翁丁注定属于油画。在翁丁,我遇到了一位油画家。他先我三两天到。那天,我在雨中,他在茅草檐下。不经意间望到时,他正在专注写生。雨在他身边滴落成一副透明的帘子,让他也成了一幅画。那一天,他画板上的翁丁是深浓的赭栗。翁丁小,纵横三两条街,我在翁丁穿行,便常常看到他。他每次都找寻新的视角。有时在一棵树下,有时在一座茅屋旁。他要把从不同方位看到的翁丁先存到心里,再搬到画板上。周围,有时围着几个衣衫不整的黑脸庞的半大孩子;也有时,是一两个背孩子的妇女。含着长烟袋的佤族汉子偶尔也会停下来。他们静静地看画家怎样神奇地涂抹他们的翁丁。那一天,画板上的翁丁是浅浅的黄绿。他提亮了茅草,压暗了花木。大多数时候,画家一个人,面对画框,背对着所有的云雨和喧嚣,沉默着,一声不响,一画就是大半天。有时一幅画分明好了,他却突然用刀刮掉某个地方,重新修改。改天空,改背景,改茅草,改大地。握着画笔的他是王,有权力随心所欲地表现他的翁丁。他把带去的颜料和画板都用完了。每张翁丁都不同。深浓的浅淡的。馨暖的孤冷的。清透的暧昧的。粗犷的婉约的。氤氲的蒸腾的。夸张的规矩的。写实的写意的。他独到的目光触及了翁丁几乎所有的神秘。那是他一个人的翁丁。是艺术的翁丁。是人类的翁丁。是从历史走来即将消亡的翁丁。一定还有他想画却画不出来的。一个久远的民族,一个原始的部落,不是几支颜料就能调和得出来的,不是几张画板就盛放得下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画。这场雨与那场雨不同,这场日落与那场日落不同,画面就发生了变化。翁丁,也许它本不需要任何人描摹它,想象它。天地才是它最好的画板,时间与自然,才是它最好的画笔。
那一天,画家又在画板上反复涂抹茅草,我站在他身后,只觉翁丁远去,那些茅草,变成了北方的麦草。
在北方,五月端午,布谷鸟的脆叫一滑过天空,麦子就黄了。走在田边,能听见饱满的麦粒里汁液汩汩流淌的声音。那是真正的天籁之音,是人间最丰美的音乐。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割了,脱了粒,麦秸晒干,挑着垛起来。田野里,打麦场上,村前村后的空地上,到处是浑圆金黄的麦垛。那是北方的乡村诗意最为丰沛的时候。上天的画作,不用修饰,不用涂改,可以直接端放到人间的画布上。七月多雨。暴雨总是从天上直接倒下来。父亲会赶在雨季前,挑最劲道的麦秸,把它们捋好,打好,爬上屋顶,把看起来可能要漏雨的地方重新苫一遍。父母从不給我们讲虚妄的道理,他们把道理都放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里。从那时我就知道,柔软的未必没有力量。一根麦秸轻易就折断了,可是一捆麦秸,连暴雨都拿它没办法。老天爷敬重一捆麦秸。我站在天井里仰头看。天空之下,屋顶之上,只有父亲。父亲把我家的天空顶起来了。麦秸里储存着从冬天到初夏整整大半年的太阳,暖熟的香气在整个天井里飘荡。父亲永远都会在。他会每年在麦收之后暴雨来临之前修一次房顶,给我们的生活补上一块补丁。那些岁月里,有了那块补丁,我们的日子就接近圆满了。修好屋顶,我扶着木梯,看着他一阶一阶下来。那时父亲四十岁多点,年轻时在省城上过会计学校,会跳交谊舞,会弹脚踏琴,会吹口琴,会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打乘方开方,是乡间少有的有学识的儒雅而英俊的男子。就像我从未想到很多事物会离我们而去,我从未想过父亲会消失。但他消失了。那年的农历二月末,三月初,麦苗正青柳芽正黄的时候,突然,父亲像一棵被人连根拔走的草,突然间在大地上消失了。天空与我家屋顶之间,突然就空荡荡的了,只有风。风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比铁都硬。那时候,父亲早已经把麦秸的屋顶换成了青瓦。他大约早就预知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反常地用整整一个二月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账。然后,像一粒尘埃回归泥土,他从容地,一声不响地从椅子上滑落下来,把生命先是交给了惊诧的母亲,接着交给了忧伤的我们,最后,交给了大地。
一幅画结束时,我坐在画家对面,看着他,想说说那些麦秸,或许,他的画板能让曾经消失的神奇般重现。但终于没有。还是他说,他小时候,家里房子的屋顶是稻草的,墙是土墙。我说,我家也是土墙,屋顶……然后,迅速低下了头。我家屋顶的麦草像一堵墙堵住了我的唇齿,我说不出。一田野的麦,汹涌而来,堆在翁丁。
梵高也画过茅草屋。二零一七年七月,我在澳洲,正值世界首次梵高画展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馆海外馆举行。所展四十幅油画与二十五幅素描皆为梵高生前真迹。油画多表现自然与田野。他野马般自由的思想和滤镜般的眼睛使得画面清澈烂漫。荷兰也种麦。他笔下熟透的麦田、收割的麦捆都是金黄色,那样明艳,绚丽,闪着光,若触之,亮汪汪的金色的颜料瞬间就会把手染成金色。然名为《茅草屋》的那幅画却是蓝绿色的。大块倾斜的蓝天,一长排绿色的茅草屋,屋前大块海水般起伏的蓝绿杂糅的草丛,成团的树冠,成团的白烟……骄傲与狂野的梵高就在画里面。看梵高的画休想平静。只是看他的画,就会深深爱上他。若他活着,自荷兰飞抵翁丁,不知,翁丁敛翅的灰雀一样的茅草屋,在他笔下,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或许,仍然是明亮到要把画布穿透的金黄。
那是一个画家的情绪的颜色。尖锐,傲慢。他在冒险。
梵高说,我的冒险,不是靠主动选择,而是被命运推动。
命运最终把他推到了一把手枪和一粒子弹跟前。他只是选择了扣动扳机。
这是唯一的结局。他的画从来都在表达他的不羁。他的画里有一股狂风。
他一直都是疯狂的,只是没人发现。
而翁丁的画家,平静的外表下,同样有着一颗桀骜的心。为了艺术,一节手指曾飞离了他。因为有人告诉他,在大学里,只要与老师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就不会挂科。年轻的他愤怒不已。最终,那节要被他废弃的手指又复归原位,自然,是在楼下找到的,差点就被狗吃了,然后用手术线缝上的。因为他要握画笔。他再怎么清高,都要在他的画笔面前低下头颅。从此他对自己说,这一生,他只牢牢握紧画笔与自由。只要两者在他手里,世界就存在了。因此他笔下的翁丁,也是荷兰梵高的翁丁了。
晴和雨的翁丁是不一样的。那是大自然两种迥异的画风。最接近梵高的,当是傍晚。雨一停,太阳就出来了。翁丁的太阳是从雨里霍然跃出来的一盏神灯。这时候,一贯灰色调的茅草屋明亮了起来。青色的弹石路,绿色的芭蕉树,黑脸颊的奔跑的孩童,叫唤的黑皮猪,啄食的土鸡,慵懒的大黑猫,茅檐下晾晒的各色衣物,采茶归来的女人,骑摩托车开拖拉机的男人……翁丁的一切都是暖橙色的,散发出神性的魅人的光芒。西方,山的那一面,正在日落,天空在燃烧,彩云翻滚。天地间,自上而下,一幅大油画布,在翁丁铺展开来。
今昔翁丁
在翁丁,我从容穿行出入于它的街巷与茅草屋。唯经过寨子后的人头桩时,总是惊惧间匆匆而过。人头桩一旁是几株巨大的生长了数百年之久的小叶榕,裸露在地表的粗壮根系盘虬缠绕,踏在上面,像踩着无数翻滚的巨蟒。浓厚交错的深绿色树冠更是严严实实遮蔽了头顶的苍穹。
忽一日,久雨骤停,一轮明艳的夕阳悬在西天,遂走至翁丁至高点看油画般的日落。只顾贪恋好景致,不觉间晚了,翁丁迅速隐没在了凉寒的黑魆魆的暮色里。顺着弹石路往回走,感觉哪里不对,一抬头,几根人头桩已经凛凛然竖在了眼前,一股杀气腾腾的血腥味似乎随即扑面而来。
昔日的佤族,据说,素有“猎人头”的习俗。
司岗里《创世歌》曰:葫芦里来,司岗里生。阿达是先,阿达为根。寂寂寞寞,空空无无,乌乌乌乌,刮起了风。是说,佤族的祖先阿达是从岩洞里走出来的。佤语“司岗里”即为“从岩洞出来”的意思。佤族人深信,是主宰天地万物的梅依吉女神创造了他们。为了得到梅依吉永世的护佑,他们采取了最高祭祀方式——像打猎一样杀人,將猎取来的人头献给通天的女始祖梅依吉。
猎取人头并不是随意掳个人就杀了,他们寻毛发旺盛的,最好长发络腮,即具有粗犷之美的男子。据说这样才能谷物丰茂。
新鲜的人头使得整个寨子欢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祭祀开始。将新人头供奉在祭台上,原来的从祭台取下,搁在木桩顶端的竹笼子里。然后,专门停放大木鼓的房门哗然打开,健壮的男人叉开双腿甩开膀子抡起鼓槌用尽全身每一分力气敲击木鼓。咚——!咚咚——!咚咚咚——!浑厚宏阔的鼓声像是来自大地深处的呐喊,越过寨子上空,响彻天际,抵达万物之神梅依吉耳畔。做木鼓的是神林里长得最美的一株株红椿树,砍倒,截取最直最圆的一节,两米多长,一米多粗,掏空。在佤族人眼里,木鼓是通天的。激越的鼓声就是他们与梅依吉之间特有的语言。木鼓响,人头痒。每次鼓声的响起,必是意味着一颗人头的落地。盛装的人们在鼓声里跳甩发舞,唱《祭头歌》:
为了生命的平静,
我们的神啊梅依吉,
我们衷心为你献上最美的酒:
保佑我们的谷子长得好,
保佑我们的人不会生病;
为了部落的安宁,
我们的神啊梅依吉,
我们衷心为你献上最香的肉:
保佑我们的部落不受攻击,
保佑我们的部落永世昌盛……
人们笃信献上人头敲响木鼓梅依吉就听懂了他们的心声,就会赐给他们生命的平静和部落的安宁。他们不断猎取人头,一根根人头桩上,摆满了不断替换下来的旧人头。
翁丁解放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茹毛饮血。解放后,佤族才停止了通过猎取人头进行的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祭祀方式。
然而,当我向八十三岁的魔巴询问猎人头的旧事时,他说,这个习俗在佤族里以前有过,但不是他们翁丁的佤族,村子后面的人头桩是后来才夯进地里去的,目的是为了让原始翁丁看起来更神秘。
我想这极有可能。毕竟,翁丁四面环山,三四百年间,群山之巅的一小片圆圆的天空像一个魔咒将翁丁严严地封住了,外面鲜有人知。某一刻,当强大的信息终于将翁丁打开了一个缺口,它新鲜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翁丁人有理由让它呈现得更加刺激,从而不同寻常。而即使佤族其他地方的猎人头,想必也是人们想象的成分居多。
在翁丁, 处处可见悬挂在树木或树桩上的牛头骨骷髅。惊骇的大眼睛,惨白的大牙齿,不知是不是每一头被镖杀的牛最后惶恐状的定格。倒是伸向天空的弯刀般的大牛角,在日落后的薄暮时分,像一道剪影,具有了一种壮烈的美感。
人的生命是梅依吉赋予的,然让人的生命持续下去的,却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谷物。谷的丰歉,佤族人认为,一定有神秘的谷神在天上掌管着。因此,佤族镖牛祭祀谷神,无疑成了庄严而隆重的仪式。在翁丁,昔日的镖牛桩现在依然竖立在广场上,成了一场又一场镖牛的见证。
被镖之牛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黑色健硕的公水牛。牛大,牛角才大,牛头供奉给至尊的谷神,才能佐佑谷穗颗粒饱满。镖牛之前,魔巴先念经,镖牛手也会喝下一大碗酒——虽是祭祀,大约,镖杀一头大黑牛还是需要些胆量的。将牛拴至木桩,在左肋心脏部位标记好,镖牛手手持尖利的镖枪,猛地刺向牛的心脏。一枪毙命是最完美的,否则就要连续镖杀,直到牛在愕然中轰然倒地,鲜血喷流。
自然,紧接着,木鼓惊天动地地响起来,人们怀揣想象中的丰收景象,昼歌夜舞。而这样的祭祀,一年要举行多次。每次,都是人们的狂欢混合着一个生命的悲壮的结束。祭祀过的牛头无处安放,就挂在了树上。慢慢的,翁丁数不清的树上就挂满了数不清的牛头骨。它们无一不龇牙瞠目。而在佤族人眼里,那是被赋予了神性的,是神圣与心愿的载体,是天地之大美。
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远去了。
如今的翁丁,连镖牛也已很多年没有过了。雨季,朽腐的人头桩无声地爬满了湿滑的青苔,蒙尘的木鼓静静地闲置在架子上。巨大的木鼓已经不是人类与苍天对话的神器,它在漫漶的光阴中完成了自己的通天使命。
人头桩彻底失去了它的意义,然木鼓并未被遗弃。年节时,翁丁的佤族人通过表演拉木鼓来释放自己的喜悦。在这里,木鼓是用来拉的,而不是敲的。在木鼓的两端凿上孔,拴上长长的粗麻绳,全寨的男女老幼,身着盛装,先把木鼓拉到神林里举行祭祀仪式。仪式由魔巴主持。他一身黑衣,红头巾在额上缠几圈,几支长而挺的白羽毛插在头顶。那羽毛一走一晃, 魔巴就像从戏曲里走出来的人物。念经,杀鸡,等把鸡血淋到木鼓上后,魔巴本人就一跃跳到木鼓中间,挥舞着手臂高喊“嘿呀——嘿咿——嘿嘿哈——”,早已把麻绳握在手里的众人跟着一齐大喊:嘿呀!——嘿咿!——嘿嘿哈!——嘿呀!——嘿咿!——嘿嘿哈!——高亢嘹亮的号子声在幽静的神林里久久盘旋回荡。众人一边喊号子一边拉着木鼓跑。人分前后两组,前面的人往前拉一段后,后面的人恶作剧般反过来往后拉一段,有点像拔河。整齐的号子声中不时夹杂着欢快的笑声,全寨子的人,仿佛都成了少年。就这样往前拉拉往后拽拽地将木鼓拖到昔日的镖牛桩前,把先前杀的鸡挂到木桩上,人们开始手拉手绕着镖牛桩围成一大圈唱歌跳舞。古老的翁丁,在歌舞中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鼓本为敲的,声音才是它美的所在,而这样被拖在地上拉来拉去,不知,是鼓之幸还是鼓之哀?
我有时候会走进木鼓房,拿起木槌敲几下。像是沉睡的人被突然唤醒,清越的鼓声中更多的是冷寂与孤独。我是把翁丁的往昔和今日融在一起敲的。然而我既没听到翁丁的往昔,也没听到翁丁的今日。蒙尘的木鼓,安静极了,也落寞极了。它的身躯无声地活在今日,灵魂依然在昔日里咚咚作响。
佤族人黑。仿佛一朵朵黑玫瑰。他们属矮黑人血统,又称尼格利陀人。天生的黑皮肤让佤族人对黑色充满了敬畏与向往。素日,大家会把锅底灰与泥土用牛血拌在一起涂在额头眉心处。圆圆的一抹,像一粒黑痣。早些时候,佤族人甚至还把牙齿染成黑色。他们酷爱穿黑衣服。他们希望自己通体都是黑的,自内而外,黑得彻底而纯粹,像黑夜一样黑,融入到夜色里,自己也成为一小片夜色。他们唯一改变不了的是血液的红色。因此,红与黑,这来自身体的两种天然色彩,成了佤族人至上的追求。
幾年前看过朋友一张照片。画面上,一大群裸着上身的男人正在往不管谁身上肆意涂抹泥巴,每个人全身自发根至脚尖全是泥,像一群泥土的雕塑。身在其中的朋友大张着嘴笑得非常开心,像个大孩子。仔细看,原来“泥塑”里面不乏女人,虽未半裸,但一身的水与泥,衣服紧裹在身上,高低凸凹,也是一目了然。
后来知道,这是佤族的“摸你黑”,一个近十多年来才兴起的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后举行的盛大节日。泥并非简简单单的普通泥土,而是由多种中草药配制的据说可以护肤的一种泥状涂料,佤语里称为“娘布洛”。娘布洛本为佤族传说中的不死草,谁若得到它,谁将会长生不老,获得永恒。摸你黑举行时,恣情玩乐的人们,至少在那一刻,生命回归到了泥土,回归到了大地。那一刻,即为永恒。
佤族,日子走到今天,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早已成为几个仅仅存在于书面的静止的词语。翁丁逼仄昏暗的茅草房,再也承载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现代生活舒适度的追求。
我在翁丁的日子,是它最后的时光。经过一片片翠绿的稻田,在一两公里外,取代翁丁原始部落的翁丁新寨已经建好,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石膏板墙壁,统一的灰蓝色树脂瓦屋顶。根据巫师魔巴通过鸡骨卦看来的几个适合乔迁的日子,人们已经陆陆续续将家搬了过去。家里的锅碗瓢盆搬走了。猪叫声搬走了。鸡鸣声搬走了。狗吠声搬走了。炊烟搬走了。老人的烟袋搬走了。孩子的哭闹与欢笑搬走了。火塘冷下来。街巷里的脚步声一天比一天稀疏。世世代代生活了近四百年的寨子,渐渐沉寂下来。
那些日子,翁丁真静。太阳静静地升静静地落,静静地晒着翁丁;月亮静静地出静静地没,静静地照着翁丁;雨静静地下静静地停,静静地淋着翁丁。雾霭静静地来静静地去,静静地笼着翁丁。翁丁像一幅静物,白的云彩,灰的茅草,青的弹石路,绿的花草树木。我静静地行走其间,静静丈量着翁丁的每一寸寂静。只有当忽然间雨住天晴,浓彩的晚霞铺满了浩荡的长空,高地的绿细竹叶与绿阔芭蕉闪着暖黄的釉光,才意识到,古老的翁丁,并没有完全被安静淹没。
然无论如何,再去翁丁,面对的,必将是一个空寨子了。翁丁像一个旅人,从历史深处的道路上踽踽走来,最终,又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对于翁丁,我没有太多的悲喜。如果有留恋,也只停留在它原始的茅草房带来的视觉审美上的冲击以及远古的神秘传说带来的心灵上的撞击。如果我是翁丁人,我把愿望删繁就简,素朴到只需要一张洁净的床与一张洁净的书桌,翁丁都给不了我。它每一间茅草房都昏暗,狭小,遍布油污。洁净,从来无处安放。只有新的翁丁,才能盛下我小小的理想。
翁丁原始的神秘、粗野与美,是一树繁花,终究是败了。
新寨的房屋明亮、通透。去往新寨的路宽阔平整,两旁遍植火焰木与菠萝蜜树。现在还不到火焰木红的时候,有一棵菠萝蜜树却已挂了果,三两个挤在一起,沉沉地垂在晨昏里。有几株不知名的树——后来知道叫夜来香——于细碎的绿叶里涌出一团一团的白花,夜幕至而香气出,夜愈深香愈浓,人们走在去往新寨的路上,很是欢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