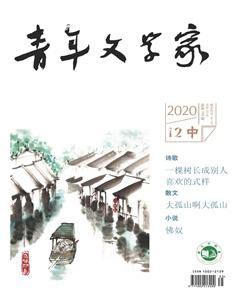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此情可待》
摘 要: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把女性看成是另外一种人,即“他者”,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在《此情可待》中,以兰英为代表的女性人物正是男权主义思想占主导社会里的“他者”,但面对“他者”身份,兰英并没有完全妥协,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抗,逃离“他者”的身份。
关键词:“他者”;兰英;《此情可待》;逃离
作者简介:李刘阳,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法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2
一、引言
《此情可待》是华裔法籍作家程抱一于200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小说,程抱一刻画了一个丰满的女性形象——兰英。兰英她本性淳朴、心地善良、吃苦耐劳。除了女主人公兰英,小说中还有自私自利的福春娘。她们都是男权统治社会里的受害者。波伏娃在她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中表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波伏娃认为当今世界是由男性所主导,女性处在与男性对立的地位,是属于低于男性的“第二性”。在《第二性》的作者序中,波伏娃引用了本达(Benda)在《于里埃勒的报告》所提出的观点:“男人的身体的重要性和女人身体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无关紧要的……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考虑自身,可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考虑她自己。”[2]波伏娃還指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的性,丝毫不差。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3]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是依附男性而存在的,是“他者”,扮演着“第二性”的角色。
《此情可待》中的女性人物正是男性主导社会里的受害者,但她们并没有就此妥协,而是企图超脱男性主导社会的压迫。因此,本文将分析《此情可待》中女性人物“他者”身份的体现,以及她们对这一身份的超越。
二、“他者”身份在《此情可待》中的体现
《此情可待》的故事所对应的时代是明末清初。在当时的社会中,传统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思想占据主导。“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则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夫为妻纲”则要求妻子必须服从于自己的夫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思想对女性的规定和要求与波伏娃所提出的“他者”和“第二性”所对应的身份遥相呼应。不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遥远的西方世界,女性都处于弱势地位,被看作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扮演着“他者”的角色。
在《此情可待》中,兰英就是“他者”。兰英原是陆老爷的孙女,本来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但是家道中落。他的父母将她许配给赵家,为的就是重新光耀门庭。兰英的婚姻并不由自己的意愿,而是由父母之言决定,她的婚姻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即使是原生家庭也没有给兰英寻得一个可靠的寄托,而是把兰英的婚姻当作家族重现荣光的手段。这便印证了“三从”中的“未嫁从父”思想。兰英在婚姻大事的抉择中,她没有话语权,她被迫依附于自己的父亲,扮演着自己父亲支配下的“他者”角色。
兰英与赵二爷的这段两性关系的前期阶段,兰英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赵二爷是主体、是“第一性”,而兰英则是相对次要的“他者”。婚后,兰英遭遇了两次流产。在好些年间,兰英一直病着,兰英的容貌不如以前,因此赵二爷将她如废弃物般弃之一边,另谋新欢,接连娶了两位姨太。兰英在这段婚姻中是不幸的。兰英和赵二爷的婚姻并不是中国古代的个例,而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一个缩影。上至一国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婚姻都离不开“三妻四妾”。这种婚姻制度不仅一方面提高了男性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男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又是对女性的迫害。
兰英不仅在婚姻关系中备受压迫,她作为赵家一员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一次秋收过后,强盗来了,带走了兰英作为人质。强盗带走兰英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财,强盗如果得到了赎金,兰英就不会受到伤害。但赵家并不着急,也不拿钱赎她,最后还是外人帮助了兰英。由此可见,兰英在赵家中甚至没有被当作一个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在赵二爷眼中,兰英的存在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兰英是赵二爷的“他者”,是赵家的“第二性”。因为在赵二爷看来,兰英只是他的,只是赵家的一个附属品。
兰英从婚姻的决定权到婚后的生活,她始终都处在“他者”这一地位上,她受到来自赵二爷的压迫,被定义为“第二性”,在两性关系中没有平等的话语权。这一时期的兰英是被男性所摆布的傀儡。
在《此情可待》中,围绕着赵二爷,至少存在四个“他者”,她们分别是兰英、福春娘、二姨太以及一个被他奸污过后又被变卖到青楼的丫头。女性都扮演着“他者”这一角色,被定义为“第二性”。她们没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任由男性糟践。波伏娃曾说:“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我们逐渐成为了女人。”兰英以及小说中其她的女性人物,她们本应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和社会里一直存在的男权思想使得她们成为了女性,成为了“他者”。
三、对“他者”身份的逃离与超越
兰英前期的个人经历是坎坷的,她被迫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第二性”。面对这般现状,兰英并没有就此妥协,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唤醒自我意识。兰英从赵二爷的生活圈跳了出来,卸下了赵二爷妻子的角色,一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再受赵二爷的支配。
波伏娃认为,女性作为“他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了女性的被动,女性很少有机会能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女人一直依附于男性而存在。[4]因此,兰英为了逃离“他者”身份,为了超越“第二性”,她不再依附于赵二爷。她选择另一种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兰英虔信佛祖与日俱增,德行昭彰,兰英还被信徒们视为圣女。而此时的赵二爷,因为遭到棍打之后,两腿瘫痪,性格也变得更加乖戾,对兰英也更加的冷漠。但兰英对此全不在意,她已经摆脱了对赵二爷的依附,不再从赵二爷身上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兰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她常去大庙烧香,参加各种虔信活动。她还更尽力地接济贫困之人,每日中午都在花园后门施食。兰英通过她的诚心和她的善举寻回了自我意识,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一个依附于男性的女人。对于那些贫困的人来说,兰英就是天赐的福祉,没有人能够取代她。此时兰英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兰英超越了“他者”的身份,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女。这正是兰英自我解放、超越“他者”身份的一个体现。
兰英和赵二爷的婚姻是父母所安排的。但按照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兰英本着“既嫁随夫”的理念,也许可以平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赵二爷一直都没有把兰英当成一个平等的伴侣,从本质上来看,赵二爷一直把兰英视为自己的附属品,而且是可以被替换的附属品。面对失败的婚姻、令人失望的丈夫,兰英没有就此妥协。一次,兰英生病时,前来给他问诊的正是三十年前就一见钟情的男子——道生。在道生的主动下,两个人得以相认。在这一次问诊中,兰英和道生的手紧紧相握。兰英与道生手握手的亲密接触,正是兰英对所遭受的婚姻的冷漠与不幸的强力反击。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兰英一直与道生这位真正的爱人有着联系,兰英会利用去寺庙拜佛的机会,去跟道生寒暄几句。此时的兰英不再是男女两性关系中被压迫、被制约的被动方,而是拥有同等对话地位的独立人。在中国古代男权思想主导的社会里,“三从四德”的思想颇受推崇,而“三从四德”正是对女性的要求,也是男性把女性置于“他者”、“第二性”地位的证据。在“四德”中,“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二;“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是对家族所有的人谦恭有礼。显然,我们在兰英和道生的爱情关系中看不到兰英的对丈夫忠诚不二的态度。面对名存实亡的婚姻,兰英突破了“忠诚不二”原则,而这次大胆的突破正是兰英作为独立女性,自主追求爱情的表现,同时也正是兰英对“他者”身份的逃离,对“第二性”的摆脱。
赵二爷的姨太福春娘和伙计朱六也有一段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在这段男女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福春娘对“妇德原则”的突破。福春娘背叛了赵二爷,是福春娘在对受压迫的现状说“不”。与此同时,当朱六利用这段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来威胁福春娘的时候,福春娘并不害怕,也没有妥协于威胁,而是设计除掉了朱六。不论是作为赵二爷的姨太,还是作为朱六的情妇,福春娘都没有完完全全失去自我,她敢于向男权说“不”。在我们看来,福春娘并不是一个本分的女性,她甚至有几分狡猾,然而这正是福春娘对“他者”身份的超越,无关方式道德与否。
在这部小说中,兰英对“他者”这一身份的超越与逃离的过程之中,她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追寻了自己的真爱,而且她的人格魅力也越来越大。此时的兰英不仅超脱了,而且再一次吸引了以前厌弃过她的男人——赵二爷。赵二爷对兰英重燃好感。但当赵二爷想再次从兰英身上获得欲望满足,再次想把兰英置于“他者”位置的时候,兰英毅然地拒绝。从兰英最后的选择和赵二爷再次被吸引的情节中,我们看到了兰英已经完成了超越、逃离“他者”地位的目标。此时的兰英不再是依附赵二爷存在的“第二性”,而是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四、结语
《此情可待》中的女性人物,兰英、福春娘、二姨太以及叫不出名字的丫头,她们都是受男权主义压迫的受害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他者”、“第二性”的缩影。在传统道德的要求下,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活。但是其中的兰英和福春娘并不始终妥协于来自男性的压迫,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摆脱“他者”的身份。正如波伏娃所预测的那样,女性是可以超越男性,是可以在社会中寻找自我的存在,去追求自我的个人价值。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
参考文献:
[1][2][3]西蒙·波伏娃著. 陶铁柱译.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
[4]盛文琪. 浅析波伏娃女性主义视角下“萨拉”的超越[J].文学教育,2019(09).
[5](法)程抱一著,刘自强译. 此情可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