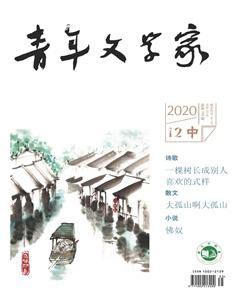真善美的乡村空间形象
摘 要:刘第红《花神之约》中的非虚构散文,通过田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碰撞、社群空间与个体空间的交融、物质空间与人文空间的辅成,体现了湖南省新化县梅山地区乡村空间形象的素朴特质,包括乡村生活之真、乡村人情之善、乡村景色之美。
關键词:刘第红;《花神之约》;非虚构散文;空间关系;真善美
作者简介:汪楚琪(1996-),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外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04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通俗的。”他的一生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认为自己从山村中走出,到梦寐以求的繁华闹市中求学、工作、生活绝不是个别现象。确实不是“个别现象”,湘籍作家刘第红与威廉斯一样也是从山村走入繁华闹市的。刘第红在素朴的湖南乡村空间中成长,品味了乡村的景之美、情之善、文化之真;在繁华的广州城市空间中写作,经历了从田园空间向城市空间、从社群空间向个体空间、从物质空间向人文空间的转化。
威廉斯始终认为:“培育他成长的充满邻里友爱和互助合作精神的乡村社区,更有资格被称为纯粹的文化。”[1]他对于乡村社区文化的追忆和褒扬支撑起了整个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文化是通俗的。“工人阶级的英国或许造就不出弥尔顿们和简·奥斯汀们来,但威廉斯认为它造就了至少有同样价值的自身文化。”[2]与之相似,刘第红的童年乡村生活书写也是在确证一种“有同样价值的自身文化”。“童年一再被书写,童年生活的意义被重新发现,我似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令我自己都觉得颇为惊讶。”[3]童年和乡村于他而言是一笔蕴藉颇深、容量颇丰的文化宝藏,从中他找到了写作的灵感和自我的精神归宿。刘第红笔下的湖南省新化县梅山地区的乡村空间与威廉斯出身的英国威尔士边境工人阶级乡村社区——虽然时间上相差半个世纪、地域上相隔半个地球——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第红在《花神之约》的后记《写不尽的童年》中提到:“我的童年系列散文,如果算上《七色花》,再加上这一本,一共是五本。中间三本分别是《穿裙子的云》《白蝴蝶 黄蝴蝶》《芍药仙子》。”[4]作为他的第五本童年系列散文,《花神之约》分为“非虚构”和“童话散文”两辑,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其中的“非虚构”散文。作家的写作对象包括家乡的人、家乡的风物、家乡的民风民俗、家乡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以及童年的家庭生活等,71篇非虚构散文关注到了湖南乡村空间形象的方方面面。
在威廉斯空间文化研究理论、列斐伏尔和索亚的空间理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人本主义地理学理论观照下,本文试图对刘第红散文集《花神之约》中的非虚构散文所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的湖南乡村空间形象进行研究。
一、景之美:田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碰撞
刘第红在不少篇章中将其童年在梅山地区的田园空间中的乡村生活与其现今在广州的城市空间中的都市生活并峙。笔者在这个部分将重点围绕叙写人文景观——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天马奔腾》和叙写自然景观——下雪的《雪之歌》两篇文章进行阐释。在这两篇文章中,作家看似只是在写某一个事物或者是天气现象,实则将写作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都拉得较长,从几十年前家乡的天马山写到20世纪90年代的广州再到如今的天河体育中心,从儿时冬天对下雪的期盼写到如今广州温暖的气候,颇具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主体与对象选择上的张力。
在《天马奔腾》中,作家与天马一同经历了人生的四个阶段:儿时,家乡梅山地区有座天马山,“看上去就像一匹昂首挺胸的骏马”,作家“无数次爬上天马山,在山上飞奔”;20世纪90年代,作家流落广州街头,因为天河体育中心的建筑外墙由天马山的石头造成的水泥砌成,只要凝望它“伟岸的雄姿”,作家“就感到特别的亲切”;而今,作家已“在广州立足、扎根”,会在空闲的时间去天河体育中心锻炼身体;未来的某一天,“天马”会载着作家的梦想,奔腾飞翔在更加辽远的天空之中。“天马”的意象贯穿全文,作家以乱中有序的时间顺序将“天马”与自己从田园空间到城市空间的人生经历关联在一起,在“天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敢于拼搏”、“永不言弃”、“创造奇迹、超越自己”等等。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Modern Novel)中认为,现代城市的“光明与黑暗”造成的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转化“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的源泉——世界从可知的变为不可知的,从共同体的变为个人感性的”。[5]对于刘第红的非虚构散文来说也是如此。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转化是其“文学想象力的源泉”,也是其非虚构散文写作成文的诱因:正是因为作家身处城市空间,心系田园空间,才会有二者的对照,才会有对后者的追忆和留恋。可以说,这种转化是其写作梦想之“天马奔腾”之缘由。
其次,作家从熟悉的田园空间来到陌生的城市空间,生存空间的转化使得他感到“身处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孤苦无依的飘零感油然而生”,也就是说他的客观“世界从可知的变为不可知的”,那么在主观上,他便从天河体育中心——由家乡天马山的石头制成的水泥砌成的建筑外墙上寻找熟稔的心理安慰,他对于未来生活的迷茫和惶恐都被自我寄托在了相对熟悉、可知的天河体育中心这一空间象征物上。
作家在《雪之歌》的写作上处理较为特殊,通篇写雪,却并无清晰的语言表明下雪的时间,读者只得从文章后半段的门窗外的景物和“伙伴们”的行为来推断:文章描绘的是一场童年家乡的雪。作家将儿时冬天在乡村空间中对于下雪的期盼与现在生活在广州城市空间中对于“无雪可看”的叹惋融合,更凸显出雪这一气候现象对于自我的情感意义和心灵分量。文章末尾写到,雪之歌“在为冬天唱着一首挽歌”,“又是迎接春天的颂歌”,“既是哀歌,又是欢歌,乐中有悲,笑中有泪”。作家希望通过“雪之歌”表达的哀伤和欢乐、惋惜和歌颂的复杂情绪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时令的脚步”,也是因为在童年的田园空间与中年的城市空间的对照中,感受到了二者统一于同一个个体的矛盾和冲突。
在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和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1940-2015)的空间理论中,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能够在“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中趋向统一,第三空间是“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6],“同时包含其他一切真实与想象的空间”[7],具有“全然实际”[8]和“彻底的开放性”[9]等特点。“雪之歌”中的两个空间在作家身上的趋向统一就是如此,他不单单是在写雪景,也是在写看雪的个体所处的文学空间——在时间空间都在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城乡意象、城乡关系、城乡环境、城乡结构等要素的变迁。
作家在其非虚构散文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个体情感,但实际上反映的是空间变迁背后生活方式与“情感结构”的变异。文本通过对于个体情感和真实社会关系的再現,超越文学表征的表象,从而显影出隐藏在背后的——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相互对立、不断疏离又不断融合的过程,以及身处其中的自我在文学空间中的矛盾、分化、超越的状态。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城乡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10]作家很清楚这一点,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这一点。
二、情之善:社群空间与个体空间的交融
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1930-)著有《恋地情结》(Topophilia)等人本主义地理学著作。他将客观的地理环境与人的主观情感相互关联并进行阐发,提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Topophilia。此词源于希腊语词汇“地域”和“钟爱”,“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11]。
《花神之约》的非虚构散文中的人、事、物几乎都是在家乡的乡村空间中建构而成的,作品的地域感和空间感特征十分明显,处处展现了刘第红对于家乡乡村空间的“恋地情结”。作家在作品中将客观的空间环境与自我的主观情感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自我对于家乡乡村空间的依恋与感怀。这种情结难以切实和直接地被认知和度量,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从作家对于外在环境的观察视角和对于家乡人事的回忆细节中去感知。
一个人自始至终“钟爱”的“地域”只有家乡,“恋地情结”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这种情结作为一种感知,不只与个体身处的环境相依附,也与个体和社群之间的文化认同相融合,它是个体在精神、情感、认知等领域中与社群相互连结的桥梁、纽带。作家钟爱的不只是家乡的“个体空间”,也对“社群空间”中的乡人乡情格外依恋,在二者的交融中,构筑了家乡乡村空间中的情感景观。
以《饭桌的“秘密”》《隐秘的生日》《彼岸花》《丰盛的夜宵》《请客》、《人情簿》《新房里的火种》等7篇以叙事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为例,作家在其中通过展现家乡乡村空间中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融来凸显乡情之质朴与良善。《彼岸花》讲述“死亡”,《请客》和《人情簿》讲述“节日宴请”,《新房里的火种》讲述“乔迁”,《隐秘的生日》讲述“过生日”,《丰盛的夜宵》讲述二十年前断炊时向熟人借柴米油盐烹饪夜宵的生活故事,这些都是与亲戚朋友、乡亲邻居的交往场景以及过年过节、生老病死的乡村习俗。也就是说,在乡村空间的形象构建中,地域社群所坚持的宗法与习俗、个人与社群交融的情感体验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借用段义孚的“公共象征”与“情感领域”两类空间概念来说,前者“被人为刻意地创造出来,并被刻意地赋予了某种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处于中心地位;后者“则是自发形成的,它是联系人们私人感情的纽带,在人们无数次的自发造访当中,它业已成为私人记忆的沉淀和寄托”。[12]
拓展来讲,“公共象征”好比是作家家乡乡村空间中的社群空间,包括《彼岸花》中的丧事、《请客》和《人情簿》中的节日宴席、《新房里的火种》中的乔迁庆典、《隐秘的生日》中的生日餐等。这类空间蕴藏着群体性、地域性、公共性,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中展现出某一地域乡村社群共有、共享的文化习俗与宗法规则。它们被刻意创造出来、被强行赋予特殊意义,比如在《新房里的火种》中,“我”被要求晚上去四奶奶的新屋里睡觉,否则后面的人就“睡不热”[13],这一习俗就被特定区域的人类社群共同视为重要的乔迁仪式。
而“情感领域”好比是作家家乡乡村空间中的个人空间,这类空间具有个体性、私密性,是个体自发并私下里形成的。比如在《饭桌的“秘密”》中,作家将家族传统、家风家训、家庭教育、家庭氛围都作为“秘密”寄托在一张小小的“饭桌”上,认为饭桌是家庭的镜子,“照出了女主人的面容”[14],并不是所有的乡村家庭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正是这些“情感领域”成为了联系个体与家庭的情感纽带,也是个人的情感寄托:作家只要想起家乡的饭桌,就能回忆起与之息息相关的家庭的温暖、母亲的勤劳、家人质朴无华的真情。
三、文化之真:物质空间与人文空间的辅成
威廉斯对文化做出了三种定义:一是理想性定义,是指人类的全面的完美理想状态、过程、境界;二是文献性定义,是指人类的理智性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三是社会性定义,是指有关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从狭义来说,社会性的“文化”并不试图概括所有的一般文化形态,而仅仅是指特定人类群体的文化;从广义来看,就特定人类群体文化而言,社会性的“文化”并不仅仅涉及这个群体中理想性和文献性的“文化”,同时也会扩展到这个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即文化是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日常的。[15]
也就是说,在威廉斯看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止是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历史、修辞、语言等人类创造的理智性或想象性的成果才是文化,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它们保留文化一词,每个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都是文化,文化包含着所有的事物。“文化是通俗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16]刘第红家乡湖南梅山地区乡村空间中朴素的生活方式、他现居的广州城市空间中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威廉斯展现的是学术之外的文化涵义,而刘第红在他的非虚构散文中展现了乡村空间中真挚而质朴的乡人乡情,对于作家来说,乡村空间中的人文与物质因素影响了其创作观念、素材和活动。
比方说,我们从作家的《百家菜》《扁担》《鹅比狗狠》《草叶上的阳光》等状物的散文中,领略了乡村空间中的物质空间的充实。即使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可能是缺衣少食,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匮乏,但是从物质空间的角度来看,作家的生活天地远比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要广阔得多,作家对动植物的认知、对食物的尊重、对农具的了解远比我们从教科书上读来的“文化”要深刻與生动。
又如,通过作家的《底线》《顶针》《被子打烂裤子》《对联肚子》《“狠”就一个字》《寄给远方的信》等写人的散文,读者仿佛能够亲身去认识、结交作家成长的乡村人文空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写作手法上,作家多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抓住人物身上最具特色的一个点来作文章。这些生活在湖南乡村空间里的普通人,从未受过所谓的“精英教育”,但是从他们的生活实践、生活经验中升华出来的东西,他们的产品、观念见解、言语辩论都是这一人文空间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非虚构散文中的《肩上的超市》《渐行渐远的身影》《讨米的婆婆》《瓦匠的背影》《远去的打铁声》等5篇文章,为我们构筑了别具一格的乡村人文空间。它是由几位从事特定职业的个体组成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货担郎、卖砂罐的人、讨米的婆婆、瓦匠师傅、铁匠师傅的身影。这个群体代表着在当代城市空间中销声匿迹的传统生意人、手艺人和乞丐,随着互联网商务和生产专门化的展开,乡村空间中的各种传统职业也渐趋消亡,乡村“被强行加与了一种秩序:社会的和经济的秩序”[17],“一种纯真的、传统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秩序的侵袭和破坏”[18]。但是在刘第红的非虚构散文中,读者又能找寻到些许过去乡村人文空间中的可贵的文化踪迹。
同时,文化的重要性是不可比较的,每一种文化、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独特的闪光之处,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比另外一种更加敏感多变、文明开化、意义深远。身居城市的读者不应当用陈腐的精英主义和利己主义论调,看似高尚地来对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的乡村文化评头论足。事实上,“乡村与城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干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密不可分的。”[19]
在“花城”广州,刘第红书写童年记忆,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花神”之约。他的写作从乡村空间普通孩童的日常生活入手,在田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照、社群空间与个体空间的交融、人文空间与物质空间的相辅相成中,为读者呈现了湖南乡村空间中的美景、真情和文化传统。
列斐伏尔有言:“每个社会空间都会通过自身的形态和布局对居于其中的人产生影响。”[20]“空间都是客观化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空间的客观化,最终,也是精神空间的客观化。”[21]我们研究乡村空间形象,就是希望回归到当时的社会空间,更加贴近作家的精神世界,并探寻该空间对作家和读者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薛君彦(译), 刘胜坤(译), 薛飞(译). 纪念雷蒙·威廉斯[J]. 国外理论动态, 2009(6):75-76.
[3][4][13][14]刘第红.花神之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9: 229, 229, 104-108, 40-41.
[5] 杜心源. 都市空间与新感觉派的身份认同危机[J]. 现代中文学刊, 2006(5):11-16.
[6][7][8][9]【美】爱德华·索亚, 陆扬译.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02, 88, 86, 72.
[10]何卫华. 威廉斯与文学表征的“对位阅读”——以《乡村与城市》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为例[J].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32(4):131-137.
[11]刘苏.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J]. 人文地理, 2017(3):44-52.
[12][20] 林渤. 雷蒙·威廉斯小说《第二代》的空间理论研究[J]. 文教资料, 2011(16):25-27.
[15]【英】雷蒙·威廉斯, 刘建基译.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北京:三联书店, 2005, 101-109.
[16]【英】雷蒙·威廉斯, 高路路. 文化是通俗的[J]. 上海文化, 2016(10):14-23.
[17][18]【英】雷蒙·威廉斯, 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乡村与城市[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173, 69.
[19] 【英】雷蒙·威廉斯, 祁阿红、吴晓妹译.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245.
[21]【法】亨利·列斐伏尔, 李春译.空间与政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