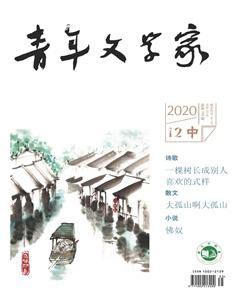超性别恋爱观下的女性反思
摘 要:庐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首创描写女同性恋的女作家,在她之后四五十年才有陈染、林白对这一话题续写。本文就庐隐等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同性恋爱下隐含着对于女性自我的反思来进行探索,并且就女性同性恋爱这一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理解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自身的反思。
关键词:女性作家;女同性恋;女性反思
作者简介:费尚暇(1997.1-),汉,安徽宣城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2
愛情是文人笔下亘古不衰的话题,但是传统的,或者说伦理上的爱情是基于异性之间的,男性和女性的结合创作出爱情,是公认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同性之间的恋爱,在传统的眼光下是畸形的、变态的。但是在思想先进的女性作家眼中,女性同性恋爱关系,更多的是将女性从男性社会中脱离开来,逃离男性伤害的一种手段。在这类女性作家的笔下,男性的介入给女性带来的只有苦闷,在排除男性和对于男性的欲望之外,女性之间的情感是她们可以彼此慰藉的乌托邦。这种女性之间的同性之爱,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慰藉与心理上的补偿,更多的是女性作家借这一大胆的话题表达对男性、对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抗拒。
一、启蒙下的姐妹之邦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不仅有“人”的觉醒,还有长期被压迫在男权下的女性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也让女性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生存的意义,她们开始试图摆脱长达千年压迫在女性头顶的封建男权思想,尝试逃离以男性为主流的话语写作,开始以“女性”为写作的基本点。庐隐无疑是当时女性作家中表现女性启蒙最为深刻的一位。在同时期的女作家开始抒发“自我”,控诉封建男权对女性的迫害,亦或者歌颂女性伟大的时候,庐隐已经开始反思这场在男性主导下的女性启蒙是否能够真的给女性带来解放。庐隐大胆地以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爱情来表达对于现代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启蒙和女性解放的不信任,她以这种违反传统社会道德的女性情感认同建构起乌托邦式的女儿国。
在庐隐的作品《海滨故人》中,最先表达了女同性恋的倾向。《海滨故人》中的女性们渴望“在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书,教那天真的孩子,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1]。在这里,女性脱离了家庭的繁琐和桎梏,不必承担作为母亲、子女的责任。女性来到这隔绝了男性的海滨之地,用这理想之地来逃避对于未知命运中妇女角色和婚姻归宿的恐惧。
如果说《海滨之地》只是庐隐对于女性同性恋试探性的写作,那么在《丽石的日记》中,庐隐完全放弃这种遮遮掩掩的女性之爱,而是用热烈、大胆的笔调描写两对同性恋人之间的经历。庐隐用这种大胆、叛逆的情感对传统道德提出抗议,也对女性处境的思考,对于女性出路的探索。在《丽石的日记》中,庐隐描写了女学生丽石和沅青相恋的过程。丽石的身边不乏男性的追求,但是丽石从异性身边无法获得心灵的安慰。当丽石听到身边好友归生向她讲述自己和海兰失败的爱情时,她对于异性之间的爱情更加失望。让丽石对于异性之间感情彻底绝望的是好友雯薇婚后变得憔悴。“雯薇结婚已经三年了,在人们的观察,谁都觉得她很幸福”[2],一段在大众眼中幸福的婚姻生活却给当事女性带来的是悲哀和痛苦。丽石觉得和异性的结合无法获得心灵的愉悦,对异性的爱情、婚姻产生恐惧和失望。这时,丽石和女友沅青互通心灵,在这里爱情对象的性别已经变换。她们渴望以两个人组建的乐园去抵抗男性主导的社会。庐隐对于同性恋的描写表面上是个体对于情感的选择,实质上是对社会上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对于高高在上的男权社会的批判。
女性的思想解放不是依靠几个文人知识分子的呐喊就可以实现的,积压在中国女性身上几千年的封建男权思想像一座密不透风的暗室,虽然五四新思想给这座暗室开了一小扇窗,透露出点点阳光,但是这弱小的光芒还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解放。
二、同性书写下的自恋倾向
镜像理论认为,同性也是镜像化自我的形式之一,因此女同性恋可以称作是自恋的一种变异。对于女同性恋来说,女同性恋可以让女性团结起来并且在情感上逼迫男性承认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林白的小说中,女性同性恋更多的是表现女性的自恋倾向,是对于女性内在的自我审视。
林白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自恋情结更多表现出对于女同性恋的恐惧,也是作者对于女同性恋能够带来女性解放的不自信。在林多米和南丹的交往中,感情是单向的,南丹会因为多米随手给的一件衣服而开心,而林多米对此只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情感上的不公平让她们的爱情注定只能是悲剧,所以当林多米接到南丹充满爱意的表白信件时,想到的是中断这段感情。“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3]显然《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具有自恋情结。这种内在的自恋倾向让林多米在这段同性情感之中只体会到一种被入侵的不安感,这种不安随着南丹情感的加深,进而渐渐演化成恐惧。在南丹被允许留宿的夜晚,林多米却噩梦连连,她梦见自己被一个面容模糊的人侵犯,而这个人仿佛就是谁在身边的南丹。林多米便推断这是自己对于南丹的抵触,梦反映出林多米对于女同性恋的排斥。然而,在南丹看来这个侵犯的人正是林多米自己,这也看出林多米一直回避的问题本质是她恐惧的是真正的自己,恐惧真正的带有同性恋倾向的自我。林多米对于同性恋的恐惧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固有的观念——对于同性恋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自我本质的怀疑和恐惧。
林白借意萍之口说出,“我们只是要一种比友谊更深刻的东西,我常想,我活在世界上什么是我最想要的呢,就是爱一个人,这个人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彼此能激发出深情”[4]。这是林白构建女同性恋群体的初衷,以同性恋群体来抵抗男权社会,获得女性自身的解放。但是林白笔下的女同性恋并不是完全的同性恋者,更多的是一种自恋的倾向,这种内在倾向让林白关注于女性精神家园的寻找,试图通过自恋式的内在观察来构建新的女性内心世界。
三、私语下的女性反思
相较于庐隐的姐妹之邦、林白对于女同性恋的似是而非的描写,陈染笔下的女同性恋更加袒露,对于女性内心的思考更加深刻。陈染对于女性之间的认识更加深刻,她否认性别观念,将自我处于超性别的意识下观察女性之间的情感。
陈染以“我”反抗男权话语下女性不自觉的自我束缚。陈染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我”观察和反思作为女性的自我,她将自己置放在一个房子里,赤身裸体的在镜子前自我凝视,在孤独与否定中寻找自己,陈染的作品始终是私语式的写作。《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无处告别》等作品中陈染都描写了女性之间的恋爱,就如同她自己说的那样将“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的女主角黛二眼中,男性并不重要,男性对于黛二仅仅是身体的需求,就如同一只雄健的动物,在男性里寻求不到情感的慰藉,黛二转身便将情感投射到同性之间,伊堕人就是她的情感慰藉。陳染的女性写作是在不断地怀疑自己的性别、否定自己的性别,这也造成她的作品里对于性别的模糊和怀疑,在她的作品《麦穗女与守寡人》,以梦魇的方式演绎女性的心理,“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和生活幸福的英子之间的情感既可以是边界模糊的同性之爱,也可以是陈染作为女性的自我映射。“我”不是一个期待着男性保护的柔弱形象,而是充当另外一个女性的保护者,“我”清晰地意识到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而我在这残暴的社会里期待能够庇护女友。这是一种性别的转换,这里的“我”担任的是传统男性的角色,“我”对于英子有着某种期待:即使身处暴力的男性社会中,也希望她藉于“我”的保护可以逃脱女性的宿命;同时也将她从传统的幸福中拉扯出来,迫使英子接受“我”的命运,分担“我”的人生。这里是陈染对于女性心理把握的一个转变,也是对于女性心理探寻的进一步的深化,在这里不仅仅是聚集姐妹之邦来抵抗男性社会的不公平,而是主动出击成为一个“引诱者”。陈染笔下的女性心理更加复杂,女性在性别意识边缘挣扎,是彻底否定性别秩序的存在,坦然承认女性之间恋爱的合理性,同时承担被世界边缘化和放逐的风险;还是背负女人“熟悉的痛苦”,继续在男性社会和自己做斗争,这就是“失去笼子的囚徒”。看似获得了自由,却被社会内在秩序所自我禁锢。在《麦穗女与守寡人》里临的就是这一临界点的选择,只是她并未走出男性所代表符号的桎梏,选择愈加艰难。陈染对于女同性恋的描写是不加掩饰的,在她的笔下,男性角色被淡化,但是对于女性之间情感的她又疑虑重重,她在选择的边缘不断挣扎,为此她笔下的黛二不断地出走,将自己流放。
陈染笔下女性之间的情谊比庐隐笔下的姐妹之邦拥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不再是单纯的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起来对男性社会秩序的反抗,更多的是对于女性地位的探寻。女性不再是作为“第二性”来看,而是将性别意识打破,这种对于性别意识的破坏最直接的路径就是女性之间的情感,借此来破坏男性对于女性的传统认知。但是陈染对于这条路又保持着怀疑,她怀疑女性之间情谊的牢固性。她敏锐的观察到女性之间的情感深刻而脆弱,她知道女性之间的背叛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崩溃与绝望,所以她笔下的是直面冷酷现实的女性社会理想。
结语: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男性群体占据社会的主导权,因此对于女同性恋的描写其实是一种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作家对于女同性恋的书写也是为了寻求女性在人的意义上的公平地位。从庐隐到陈染、林白都致力于构建女性群体来抵抗男性,消解男性话语的控制权,但是无论是庐隐海滨之地的姐妹之邦,还是林白笔下自恋下的女主人公,亦或者陈染“破开”的女子协会,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女性在社会中寻找公平的地位,冲击了男性话语的霸权,但是,对于女同性恋意识的自觉,并不是与女性解放程度成正比,这也是女权主义作家容易陷入的误区,在庐隐之后,林白、陈染发现这个问题,对于女同性恋群体开始警惕,她们开始转向女性内心对于生存的焦虑,展现出在女性主义抗争中的困惑与挣扎。
注释:
[1]庐隐.海滨故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庐隐.丽石的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林白文集2[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5.
[4]林白.瓶中之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