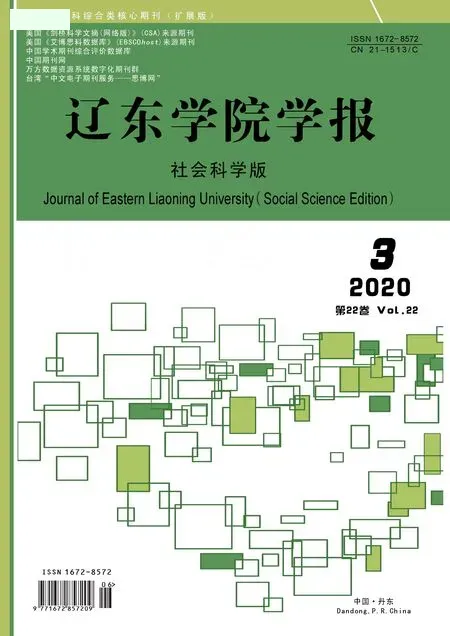《庄子》屈骚神话人物意象比较研究
孙伟鑫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
《庄子》与屈骚皆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源头,前者为散文领域浪漫文学之旗帜,后者为诗赋浪漫文学之开创,历来皆以庄骚并称。此二书中关于神话人物的描写颇多,就此二书神话研究而言,学界成果颇多,主要从源流、宗教、文化、仪式、神话意象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将《庄子》与屈骚作品中的神话人物意象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相对不足。故而笔者以《庄子》及屈子所做的25篇骚赋为材料,以期梳理庄子及屈子在神话人物意象塑造方面之差异。
一、凄哀婉转的悲剧之美与“道”之中平
纵观屈平一生,其人生经历无疑是悲剧的,其作为楚国贵族,初得楚王赏识,“王甚任之”[1]1527,然楚王昏庸,误信谗言,重用佞人,致使屈原放逐流放,最终“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1531。屈平个人际遇使得屈原作品中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九歌》为代表的诸神意象。《九歌》本为祭娱神灵之歌,其中有诸多神灵描绘,虽含众多美好意象,然其中又吐露出凄哀婉转的悲剧之美,以“美”抒“哀”,故而屈骚笔下虽诸多美景、美人、美物,但却透出一股巨大而又哀伤之无奈。
屈骚《云中君》中先是寥寥数句书写云神尊贵威严及排场:“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2]59-60作者思及云中君,唉声长叹,日夜不止,忧心忡忡,在思慕云中君之背后,流露出的却是屈原的悲情,是思君不得之无奈之情。再如《湘君》所言: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61
此处王逸认为是:“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荡,既设祭祀,使巫请呼之,尚复犹豫也。”[2]61即言湘夫人尽心打扮以后,乘舟尽兴而来,然湘君迟迟不见,于是湘夫人便吹洞箫而抒其哀怨,吐出对湘君之思念,表现湘夫人内心中淡淡的孤独与忧伤。其后无论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2]63-64或:“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峕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2]64-65皆言湘夫人求见湘君不得,以抒其伤感幽怨之情。虽朱熹以为此篇为:“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3]36然无论此篇之主旨为朱熹所言忠君之旨抑或王逸所以为:“而谓湘夫人,乃二妃也。”[2]66皆不可否认此篇表达湘夫人思慕湘君而不得见的凄哀幽怨心态。再如《山鬼》所言: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82-83
屈子以“三秀”“石”“葛草”“杜若”等意象,塑造了一位多情“山鬼”却求君不得的形象,以采美草、饮山泉、休憩于山林之间描述“山鬼”内心之彷徨与惆怅,又随着雷声绵绵,阴雨霏霏,猿啼哀伤,“山鬼”辗转反侧,描绘了一幅萧瑟凄婉的场景。屈骚笔下之神,拥有数量繁多的美好意象,如“山鬼”打扮则是:“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2]81山鬼的载具则是:“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2]81可此种种之美,皆浸淫悲伤之情,体现屈子无可奈何之感。通观《九歌》,诸神之意象,如《湘君》中:“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2]64《大司命》的:“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2]71-72抑或《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2]74又或《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2]84-85由此可知,整个《九歌》弥漫着一种极为艳丽而悲伤之至的复杂情志。屈子所塑之神灵,虽赋予其活泼绮丽之美,有美草、华服,又有异兽、车舆。然沾染着屈子身上浓郁的悲伤气息,故而屈子将自身之悲情以此种爱情悲哀的方式呈现,因此其笔下的神灵意象具有一种凄哀婉转之美,同时亦是屈原内心孤独彷徨之体现。
反观《庄子》之中,“美”及“丑”并非是其写作之目的,其散文之目的在于阐“道”说理。庄子尤重自然之道,如其认为马应该是:“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齿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4]244当伯乐对马进行驯化之时:“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4]244由此见得,此处庄子籍“马”之意象以喻“道”,此为《庄子》一书的基本思想,而遑论其意象为“美”或“丑”。其于神话人物一道亦是如此,如《达生》之中,形象荒诞而无人形之神: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诶诒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去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4]517
此处庄子描写了五个形象之神,分别为罔象、峷、夔、彷徨、委蛇。罔象为水中之神,陈鼓应引司马彪注云:“状如小儿,赤黑,赤爪,大耳,长臂。”[4]519峷、委蛇则如下文所写:“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4]519此处《达生》之主旨在于说养神,所谓“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4]500,因而此处藉桓公心神不宁之事,写诸多神怪,以证得心神释然而病痛除之道,喻养神之重要性,无多余的感情色彩。再如《应帝王》之浑沌,庄子云: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4]249
“鯈”“忽”之训释,诸代有异,然从其于“浑沌”并列而称看,应为神话人物。此处庄子笔下之浑沌,用以喻真朴之民,因统治者屡立苛政,不堪重负,终致命丧。故而庄子此处以寓言之法写神话人物,其目的为伸其“无为而治”之政治主张,本质之目的在于阐“道”之思,故而其神话人物仅为其手段,而非沾染上情绪色彩。
因此可见,屈骚塑造神话人物意象之意图在于藉神灵形象之美好,反衬其求而不得,去国怀乡之悲,《九歌》《九章》之中诸神意象即是最好之例证,此种思想感情与《离骚》《天问》等思想感情是相近的。在《离骚》之中,屈平虽上天下地之寻求,然终却求而不成,无奈去国,此种上下天地又四方求索的壮阔意象,终究成了巨大又无奈之情感漩涡。故而,屈骚中之神话人物意象始终笼罩于此种深沉厚重又缠绵悱恻的意象之下。反观《庄子》中的神话人物意象,其写作目的是以阐“道”之主,非以审美为主要写作对象。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庄子则不仅不像近代美学的建立者,一开始即以美为目的,以艺术为对象,去加以思考、体认,并且也不像儒家一样,把握某一特定的艺术对象,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5]30因此,也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庄子在塑造神话人物意象之时,并无现代之审美观,其神话人物意象塑造目的是以说理为主,常喜以暗喻出之,且不喜明喻。故而读者读之,并不会产生情感世界共鸣,而是对“道”的服从与认可。由此,庄子对神话人物之描写是以“道”为纽带,与屈骚“美”为主之神话意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尊崇高洁与不忌卑贱
屈骚神话人物意象之中,其神灵之形象多为高贵之躯,居于芳香之所,雨师洒道,雷师清道。如《九歌》中即有大量关于美神之描写。《东君》为《九歌》中一篇目,描绘日神之形象: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躯,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地徊兮顾怀。[2]75-76
王逸注云:“《博雅》曰:‘朱明耀灵,东君,日也。’”[2]78由此可知,东君即为日神无疑,此骚铺写“东君”出场时的威状,以龙为车,以云为旌旗,凸显日神慷慨无私,从容不迫之形象,使人不由心生美好。再如《大司命》中对大司命之神之描绘:“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2]70即对大司命出场作了铺叙,凸显其作为天神职位之高。而“灵衣兮被披,玉佩兮陆离”[2]71则是对其华美服饰进行之描写。通过此两方面描写,一位身着华服,佩华戴玉的神灵形象便出现于读者眼前。如果说大司命为英俊美貌之男神形象,而少司命则为温婉娴静之女神形象。《少司命》首先吟唱供神之所,其文云:“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2]73其后描绘少司命之容颜为:“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2]74通过环境及神灵形象之塑造,可见得神之体态美好与清洁。
屈骚中此类例子比比皆是,又《云中君》之云神形象: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灿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2]59
云中君身着华服,体态美好,居于寿宫,驾龙车以遨游于天地之间,故而给人一种高贵神秘的审美感受。除诸神灵外,另有“龙”“凤”等高贵灵物之描写,如《离骚》中便有:“驷玉虬以椉鹥兮”[2]26、“麾蛟龙使梁津兮”[2]45等描述,而“凤”之意象,则如《远游》中:“凤皇翼其承旂兮。”[2]177或《怀沙》中:“凤凰在笯兮,籍鹜翔舞。”[2]147又《离骚》:“凤皇既受诒兮。”[2]34“龙”“凤”等意象,皆是屈骚中作者驱策之对象,而此诸多神话意象,皆为美之体验感受。而屈原意象之中象征恶之名物,如茅、椒、鹈鴂等,亦非恶俗之意象。
反观《庄子》中,如雅正之儒家不同,《庄子》意象不忌卑贱之物,如《齐物论》中云:“民事刍养,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4]90再如《德充符》中“食于其死母者,少焉?若皆弃之者……”[4]172,此种意象,不仅不忌卑贱,甚至略微恶俗。就其神话人物而言,并未如屈骚之中神灵之美,而是不忌卑贱,铺平叙述。笔者将《庄子》中具备神性特征之物亦纳入考察范围内,以期全面梳理《庄子》其中神话人物意象。前文所引之《达生》诸神之意象,如罔象、峷、夔、彷徨、委蛇,皆为样貌卑丑之物,如峷,司马彪注云:“状如狗,有角,文身五采。”[4]519又如夔,成玄英注为:“大如牛,状如鼓,一足行。”[4]519又彷徨,司马彪注为:“状如蛇,两头,五采文。”[4]519从以上诸意象中可看,庄子塑造之神话人物,相较屈骚之神话人物意象,则不看重文采,其根本目的还是阐“道”说“理”。《秋水》中所塑造之“河伯”及“北海若”之形象,就文学本位而言,将河伯塑造为一自大狂傲之徒,如其言:“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4]442
观《庄子》及屈骚中神话人物意象之差别,探其缘由,其一乃屈平庄子二人出身及人生经历之不同。《列御寇》云其:“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4]829《外物》云:“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4]751其见梁惠王之时,“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縻系履而过魏王”[4]552,由此可见,庄子家境中落以后,其生活较为贫困,然其自得其乐,不以为苦。故而庄子对恶俗之物能够忍受。同时,以“道”之观点看,诸神并无高下之分,即有如藐姑射山神人之美,亦有藉黄帝与舜等帝王之神抒发“道”之朴素。除此,庄子之创作,喜用奇言,故其意象选取上,便选许多其他诸子不屑之选。反观屈平,其与楚王同姓,出身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2]3,其对普通百姓生活不甚熟稔,虽遭放逐,然从其作品看,其对祭神之仪极其熟悉。三则,屈平选择神话意象的目的在于体现其自身与神灵之高洁,故而其笔下之神皆体态美好,身披华服,神明开道。作为贵族出身的屈平,对不符“美”之事物皆敬而远之,其对恶俗之物有一种本能排斥,而对高贵之物有天然的喜爱,故屈平即便需表现反面意象,亦不会同庄子一般选取过于卑贱之意象。
三、楚文化为根基与自我创造
纵观楚国建国至其灭亡,其国信巫重祠,《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6]1327屈平之时之楚地亦不例外,如屈原笔下运用最多之意象之一香草,便为时楚地文化活动中重要之物,以香草为装饰及祭祀之礼极为普遍。可见,屈原作品中之香草意象是当时楚文化在其思维中之自然表现。范文澜认为:“屈原是在浓烈的巫风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作品无论在内容、风格还是艺术境界上都打上了巫风的鲜明烙印。它与楚神话、楚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楚国数世称雄的辉煌一起,再加上屈原天才般的诗人气质,共同成就了屈赋奇诡浪漫的艺术风格,而巫风无疑是其中最有价值的元素。”[7]68正是由于楚文化之背景,楚人从香草中看到的并不是实质之草,而是寄托原始宗教情感之物,将其中精神灌注于香草之中。就神话人物意象看,亦如是,如无楚地对神鬼崇拜之心理,屈平不可能以神仙形象折射其自身形象。
在《楚辞》中,如《东君》之日神,古书中多称为“羲和”,然此称为“东君”,即是受到楚地文化之影响。姜亮夫先生认为:“按《周礼》云:‘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则日月古载祀典甚明。《仪礼·觐礼》云:‘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记·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玄端朝日于东门之外’。则祭日必于东方行之,盖日出于东,故迎日于东,而其神亦曰东君矣。”[8]239由姜亮夫先生之考证可知,“东君”之名称由来,本身已有楚地神明之背景,而屈原则创造性地改造了这种神话人物意象。再如屈骚中云神之形象,云神在传统宗教及祭祀典礼之中,地位不高,然屈原将其列为《九歌》一章,却可以看见楚人祭云神的文化,遑论湘君、湘夫人、山鬼等典型带有楚地文化背景意象。而河伯、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等神,通过作家的改造,呈现出不同以往之形象。正如《文心雕龙》云: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9]505
此言文学之创作,实则与“才”“气”“学”“习”有关,而屈原出身贵族,自身神圣性不必多言,其个人之忠信清廉、刚正不阿之性格,更为后世文人所倾慕。其自身之“博闻强志”便是对其自身修养而言。故屈骚之神话人物形象塑造,可以说既带有楚文化之根基,同时加入屈原自身创造性之改造及使用,形成了极具特色之意象群。
反观《庄子》一书,学界一些观点认为庄子之文化背景为楚文化抑或南方文化,其代表人物如朱熹[10]383、王国维[11]1等,然据刘生良先生考证,庄子之文化渊源实则出自商宋文化[12]27,其认为庄子生于宋国,身上携带着“被推翻的殷商民族整个集团的‘无意识’和祖祖辈辈苦闷压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感受”[12]29,因而形成了庄子奇特的个性。由此,《庄子》诸多意象皆以“奇”闻名,其神话人物之塑造亦不例外,如《逍遥游》之具神性特征之“鲲鹏”“藐姑射山神人”,《秋水》中长寿之龟、《天地》中黄帝形象、《让王》中舜之形象等皆为庄子以奇情怪想所改造之意象。庄子以独特的视角及手法对事物进行再加工创造,究其缘由,因《庄子》本为说理之文,其离奇怪诞之意象是以“道”之视角让其相连,并使得它们变得光怪陆离又奇诡怪异。
总而言之,屈原笔下之意象更多是楚地文化之改造物,有着楚地的文化意蕴,而《庄子》之意象主要是基于殷商文化背景之下之自我创作,其以理性之思维,抒发浪漫之时,不重情感之表达,相较屈骚而言,感情色彩不甚浓烈。
余 论
通过上文分析梳理可知,《庄子》中神话人物意象与屈骚神话人物之意象塑造实有不同,其区别之处在于:
其一,屈骚之神话人物意象塑造,浸透着凄哀婉转的思想感情色彩,而《庄子》的神话人物意象则为“道”之中平,其缘由在于屈原望通过神话人物之悲,宣泄自身去国怀乡之感,而庄子则为阐“道”而创作,其审美感情中并无哀乐之差别,故其神话人物之意象主要是为其思想服务。
其二,屈骚神话人物意象塑造,崇尚高洁,所塑造之神话人物皆居宫室,着华服,美草美花数不胜数。《庄子》之神话人物意象则不避卑贱,甚至有些丑恶。究其缘由,实于庄子、屈平二人出身境遇与创作语言风格有密切之关联。
其三,根源于楚地文化与自我创造。屈原与楚王同姓,其出身高贵,远避邪污,其笔下之神话人物意象,具有楚地之深厚文化基因,同时在楚地神话人物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改造,构成其独特风格之神话人物意象。而反观庄子之神话人物,其言亦以奇言出之,然其文化之背景为殷宋文化,更多为自己独创,显示出不同诸子的意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