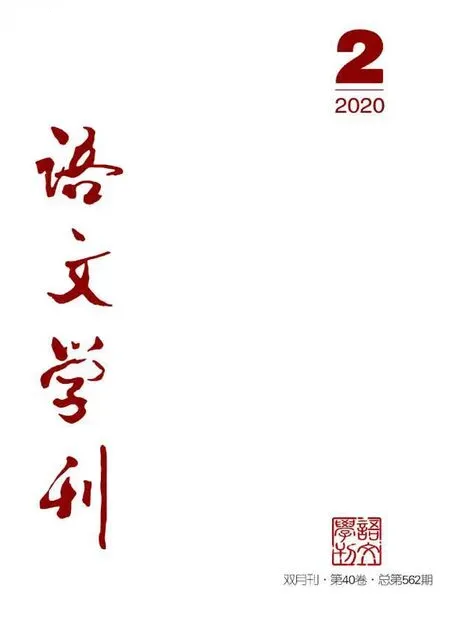现代汉语“乖戾”动结式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沈梅英
(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乖戾”(idiosyncrasy)现象指“整体不能从部分预测出来”的“一形多义现象”[1]323-328,如汉语“吃+NP”结构就通常显示出“语义组构乖戾”[1]327,“吃父母”是原型构式“吃饭”等的衍生,但其语义却不能简单从字面结构组合中直接读取。“乖戾”动结式是指 SVRO 基本动结式衍生出来的非常规动结式种种,如歧义动结式“张三追累了李四”、错位/倒置动结式“茅台酒喝醉了他”等等。其句法与语义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研究也呈多视角、多维度势态。
一、“乖戾”动结式研究现状
(一)构式核心不对称研究
有关动结式核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结式属“单一核心”还是“多元核心”之纷争上。有“‘核心统一说’与‘核心分离说’之争,也有‘词汇核心说’和‘功能核心说’之争”[2]2-13。赵元任(1968/1979)认为“动补结构的中心在前一部分”[3],Thompson (1973)提出“词汇规则”[4]来强调动词的核心地位。但Lu(1977)的观点是“动词和补语都各自承担语义功能”[5]。李临定(1984)则认为补语是动结式的“中心语”[6],并用“省略法”验证其观点。他认为像“小孩子吓哭了”之类动结式只有动词可删除,补语不能删除。而范晓(1985)认为李临定的“‘职务替换验证法’很难确定动补的结构中心,更不能得出结构中心在补语上的结论”[7]。他认为按李的验证法,汉语动补结构会有动词核心语、补语核心语、双核心语及无核心语,如“她哭昏了我的脑袋”就属无核心动补结构。马希文(1987)[8]则用“‘增扩’检测法”[9]17-23来验证诸如“帽子吹掉了”之类动结式语义核心与句法核心的一致性。但袁毓林(2000)[10]49-61指出了马希文(1987)以受事主语句来测试语义中心的观点的缺陷,认为“动词独立成立,而补语做谓词却不成立”[11]163-172。沈家煊(2003)也指出“按照‘向心结构’理论进行检测,实际上并不能检测出动补结构的结构核心”[9]20。
“单一核心说”的短板促使一些学者将动结式的语义核心和句法核心进行分离考量,赋予动结复合词V1和V2不同的核心职能。袁毓林(2000)[10]49-61从历时和共时视角论证了汉语动结式句法核心问题,认为现代汉语动结式的句法与语义核心并不完全平衡,动词是句法核心,补语是语义核心。沈家煊(2003)也指出“有必要将意义核心(semantic core)和结构核心(syntactic core)区分开来。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9]20。任鹰(2001)基本持相同观点,认为动词和补语“都有可能成为在句法功能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成分”[12]。宋文辉(2004)则从范畴视角来考量,他认为“句法核心是一个典型范畴。典型的句法核心同时具有语义和形态两种核心特征,而非典型句法核心则不一定二者兼备”[11]164。
Alsina et al.(1997)认为汉语动结式是一个由多个具有核心特征的谓词构成的“复杂谓词(complex predicate)”[11]164,其在句法和形态表现上相当于一个谓词性成分。因此,他们提出了从整体视角考证汉语动结式功能特征的研究思路。熊仲儒和刘丽萍(2005)也将动结式核心确认为功能范畴。他们认为,如果将功能范畴确认为核心,则动结式不仅适用于“‘右向核心规则’,而且可以让核心的信息真正地在复合词中得到保留”[13]。杨大然(2018)也认为“‘功能核心说’可以较好地实现语义核心和句法核心的统一”[2]3。他认为,在构建动结式时,汉语“受主施宾”倒置结构的句法核心是VCHANGE,其论元选择与V1和V2本身的论元结构无关。但是,文旭和姜灿中(2019)则认为功能范畴中心论是通过“莫须有的抽象语法范畴”来解释动结式特例,“未能完全摆脱‘动词中心论’和英语动结构式研究思路的束缚”[14]28-33。
(二)构式论元层级限制研究
此类研究关注动结式复合操作层面及其论元配置。学者们认为动结式是经题元操作而成的复合词(V1V2)(V2 也可以是形容词),其中每个组成动词都贡献自己的题元(Li 1990[15]177-207,1995[16],1999[17];Her 2007[18]等)。李亚非在此领域进行一系列的研究,Li(1990)认为动结式复合词(V-V compounds)题元按层级分配,由题元同指(theta-identification)、构式题元栅(a structured theta-grid)和核心特征渗透(head-feature percolation)三者互动形成符合语法的(well-formed)动结式复合词[15]177。Li (1990)采取V2论元与V1题元共指(theta-identification)关系及相关论旨角色在层级关系中凸显程度的差异性说明“宝玉骑累了马”歧义产生的原因[15]183。Li的观点与Jackendoff (1972)[19]、Baker (1988)[20]、Larson (1988)[21]、Grimshaw (1990)[22]和Dowty (1991)[23]等所持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不同的题元角色是按层级模式跟句法论元联结的。
Cheng & Huang(1994)认为,决定动结式句法性质的并不是动词V1的题元结构,而是谓词类别[24]46-51。他们参照普通谓词的分类方法,将“追累”“气死”之类动结式分为“(非)作格性谓词”“及物性谓词”和“致使性谓词”,并依据“V1”事件特征分为及物/非作格形式交替[动结式V1活动类[V2状态类/状态变化类]]类别和致使/作格(或非宾格)形式交替[动结式V1非活动类[V2状态类/状态变化类]]类别。杨大然和周长银(2013)则认为“Cheng & Huang(1994)依据V1的事件类型来判定动结式的句法性质并不可靠”[25]46-51。他们基于Huang et al.(2009)的轻动词理论对诸如“王五喝醉了酒”动结式的补语指向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动结式补语V2所指向的论元必然是由词根√V2携带的轻动词Lv1筛选出的事件客体,在句法中投射到内部论元位置”[25]46。杨和周所依据的轻动词理论假设是动结式V1和V2是词库内合成性动词的词根,该词根所携的轻动词由动结式概念化事件类型所决定。
朱佳蕾(2016)认为,每个动结式的构成并非都遵循一套词库层面的复合或派生规则,其题元结构和论元结构也并非可以依据这套规则推导而出[26]571-586。质言之,动结式并非都是个个在词库中储存。朱依据Reinhart(2002)的题元系统(Theta System)理论框架对“骑累”类等动结式词库和句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考察与分析,认为“骑累”之类动结式的构成是“词库-句法界面”[26]571复合形态操作所致。这种操作并不要求动词的题元都必须投射到句法。她认为“所谓的违反题元等级的施受倒置现象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是复合题元操作和相应论元映射的结果”[26]580。沈家煊(2004)则认为“仅仅从动词和补语的论元结构和题元出发”是无法对“追累”类动结式“语法和语义做出充分解释的”[27]3-15。沈先生认为两个原因导致这种不充分性:其一,动结式的意义不能完全依赖动词和补语的意义推导而出;其二,动结式意义受制于动词和补语各自的词汇选择[27]3。沈家煊(2004)进而认为动结式的语法和语义是许许多多因素之间互相联系和互相限制的结果,是关于各种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其具体内容光用句法上的论元结构和语义上的题元结构是无法涵盖的”[27]14。
(三)构式句法语义关系研究
这类研究大多关注致使语义关系和事件性质。学者们,如 Cheng & Huang (1994)[24]、Huang (2006)[28]、熊仲儒(2004)[29]471-476、王琼和伍雅清(2005)[30]17-23、王寅(2009)[31]、吴淑琼(2013)[32]、崔婷(2015)[33]、程工和杨大然(2016)[34]526-539、冯丽娟(2017)[35]等都认为动结式用来表述一个由使因事件与使果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结构,分别对应于活动与状态, 两者间具有致使关系。熊仲儒(2004)指出“动结式是一种致使表达, 反映使因事件与致果事件的致使关系,使因事件是一种活动”[29]471。他专文讨论了在认知语言学背景下决定汉语动结式致事选择的多重因素,认为转喻机制选择不同事件活动参与者作致事,从而,在认知层面上解释了“茅台酒喝醉了他”之类倒置动结式的合法性。程工和杨大然(2016)也认为“动结式复合词是包含两个子事件的复杂结构,前一个动词V1表示活动,它以一个表示结果/状态变化的事件为补足语”[34]526。他们提出“结果/状态的核心是一个表示变化的轻动词BEC,其标志语由与结果相关联的论元占据,其补足语由词根担任”[34]526。沈家煊(2004)[27]、施春宏(2007)[36]、张建理和麻金星(2016)[37]19-31、彭芳和秦洪武(2017)[38]、沈梅英(2017)[39]463-472等也支持动结式事件性的观点,认为此类构式的成立条件是两个子事件间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其显现形式关系越紧密,反之亦然。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语言学领域对事件结构的研究始于Vendler(1967)。Vendler从时间结构特性角度对动词的意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Vendler(1967)根据终结性、持续性和同质性等时间结构特征把英语中的动词分成状态、活动、达成和完结四类[40],后来这四类动词也被称为四种事件类型。王静和伍雅清(2008)认为“Vendler提出的事件类型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发生体态转换,即直接宾语、附加语,甚至是主语等因素都会影响事件类型的确定”[41]。由此,他们认为单纯从动词包含的信息来划分事件类型是不够充分的,还需要相应的限制条件来压制词汇语义表征中论元与句法结构的投射过程。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提出“一个事件至少有一个论元的限制条件”(Argument-per-subevent condition)[42],认为编码到谓词的体态信息不是句法结构的唯一决定因素,编码到句法结构中的体态信息也会影响谓词的具体解读。
Hale & Keyser(1993,1998)、Ramchand(2001,2002)和Tzong-Hong Lin(2001)认为在英语动结结构中事件结构的整个过程发生在词汇-句法层面,而在汉语中这一过程发生在显性句法层面[30]20。王琼和伍雅清(2005)认为汉语事件结构中,不必把两个基本动词的词根限定在活动体和状态体之内,动词可以和任何轻动词合并,“汉语事件谓词的语义性质”[30]20决定了这种合并的灵活性。他们认为将非主事性致使结构以及颠倒性致使结构中外部致使短语删掉可变为单一的成事事件结构,形成致使-成事交替现象。“张三骑累了马”“语义上的歧义产生于结构上的歧义”[30]20。熊学亮和魏薇(2014)认为倒置动结式“那包衣服洗累了姐姐”是“特殊的语义因素”[43]所致。他们从词汇致使句和构式致使句视角对此类语言现象进行了论证,认为前者是动词本身的[致R性]将致使力传递到使果事件;后者是构式本身的[致V性]使主语间接进入了使因事件,再导致使果事件的发生。熊学亮(2017)指出“追累”动结式成立的原因在于复合词之间的“语义紧密度低且激活的是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致使关系的两个认知事件”[44]。沈梅英(2017)认为错位动结式“那瓶酒喝醉了张三”合法因素之一是使因子事件“张三喝那瓶酒”和使果子事件“张三醉了”有共指事件参与者“张三”且两个子事件之间因果关系恰当[39]465。
由此可见,某种程度上说,事件参与者共指关系及论元限制确实可以从句子内在结构解释其生成理据。但有时这种语义与句法间的关系更具复杂性,单一的内在因素解释理据性欠全面。因此,未来对特殊语言现象充分理据的挖掘有必要将句法与语义、语境、语用等多重互动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使解释更全面、更系统。
二、“乖戾”动结式研究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学界对汉语动结式语义句法关系复杂多样性的研究关注度极高,成果显著。但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大多研究只停留在论元、语义、句法等语言内部层面,忽略了构式语义、句法、语境和语用的共时整体性及互动过程中所隐含的复杂性,未能宏观提取相关现象的共享特征,以致对句法语义不匹配“乖戾”动结式生成动因的解释欠全面、研究遗漏尚存。
鉴此,汉语动结式“乖戾”现象研究除刻画其语义、句法内在特征外,有必要在原则和规则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所谓的“特例”的根本性质及其生成机制,使“特例”成为分析模式中的“常例”,进而系统刻画动结式形式层面的能产性、图式性和组构性所致意义层面的丰富性和歧义性。因此,未来对汉语“乖戾”动结式的研究更多将基于语言形-义配对“隐含复杂性”(hidden complexity)[45,46,47]概念,关注其语义、句法、语境和语用多重界面的互动研究,探讨句法构造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动因所在。
(一)构式词汇语义选择限制动因研究
严辰松和刘虹(2018)认为“‘动结式’是由S、(O)、V和R构成的完整句式,而非仅指V+R结构”。“这类句式的概念结构可用[do’(x, y)]CAUSE[BECOME predicate’(y/z)]表示”[48]。这一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以往对动结式研究仅围绕V1V2或VR/VC展开的局限性,将施事、受事等也纳入构式范畴,拓宽了研究视野。歧义或错位/倒置致使动结式属于动结式范畴,因而具备动结式语义结构特征,即述语动词(V)所表示的动作发生而导致补语动词(R)所表示的状态的出现或变化。无疑,整个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征跟动词和补语所联系的词汇选择有关,或说与词汇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有密切相关。
从现有研究来看,上述“乖戾”动结式句法对语义的选择通常受词汇性状的限制。构式中动词“V”通常具有“动态性”、“致使性”,排斥“状态性”;而补语“R”则往往接受“状态性”,排斥“动态性”,且具备“非恒定性”和“非初始性”特征,通常情况下,具有极量或高量语义的词允准进入。这种词汇-语义特征的对立性也就成了构成“VR”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构式词汇性状关联性偏离原型范畴,那么,构式义的表达必另有语用动因。因此,未来对非常规动结式意义的解读不能仅局限于语义或句法单方面因素,而应将语境、语用意图等多重动因考虑在内。
(二)构式形义映射关系制约动因研究
句子的意义源于动词和构式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特征表现为动作参与者角色和构式论元之间的融合[49]。这种融合通常基于语义相近的动词与论元实现的相似性,并体现为语义与句法之间的“映射关系”[50]。以错位致使动结式为例,该构式句法结构[S VR O]跟普通动结式句法结构并无二样,但其句法结构与题元层级相悖。常规情况下,参与者角色和论元一一对应,如果两者不对应,构式则对动词进行压制,迫使动词添加或削弱参与者角色。
从语言类型学视角下,汉语属“意合语言”,其语法呈隐性;英语属“形合语言”,其语法呈显性。因此,英语句法规则不一定适合解释汉语特殊语言现象。从历时语言学角度看,“汉语动结构式是致使构式的一种可能型式,它与致使构式存在历时继承关系,是汉语史上因为使动用法衰落和双音化致使语义由动词使动用法向连动结构转移的结果”[14]32。文旭和姜灿中(2019)提出了基于层级观和互动观汉语动结式句法语义界面新型分析框架[14]32,这一框架为如何在语言类型学和历时语言学视角下开展汉语非常规动结式语义-句法映射关系完型特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构式属性与隐含复杂性动因研究
Traugott和Trousdale(2013)指出,一个构式包含三种属性,即能产性(productivity)、图式性(schematicity)和组构性(compositionality)[51]。一般来说,具有高能产性、高图式性、弱组构性特征的构式往往语义包含性较大,构式意义的不可预测性较强。因此,这类构式的隐含复杂性特征比较明显。如,错位/倒置动结式属高能产性句式,其线性排列特征为[XP+V1+V2+NP2],其中XP可以为 NP,即V1述语动词的受事/客体,可以是对象、受事和工具等事件参与者角色,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VP和句子S,还可以实现为体词性成分NP。XP 表层方式多样,在使用中可获得不同的释义。图式性通常与能产性呈现正相关,图式性程度越高,构式的能产性也越高,反之亦然。
错位/倒置动结式是非常规构式,是常规动结式在文本、语用和语义等因素互动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其语义不完全等同于各部分意义的总和。因此,其组构性较弱。概言之,此类“乖戾”动结式具有典型的隐含复杂性特征, “其句法结构不能完整传递它们想要表达的意义,解码时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语用推理”[52]。李临定(1986)曾指出动结式“最能体现汉语结构简练而意义丰富的特点”[53],其丰富语义的识解需要听者/读者从简洁的字面表达推断其所隐含的真正动因,“而对这种动因的考察超出了语言本体研究的范围”[37]29,需借助生活体验及百科知识,从动态视角来分析语言的意义所在。维特根斯坦(2001)曾指出“词在实践中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54],对构式意义的理解也在此理中。由此看来,一些语言本身无法全面解答的问题,在哲学范畴中或许能找到更充分、全面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