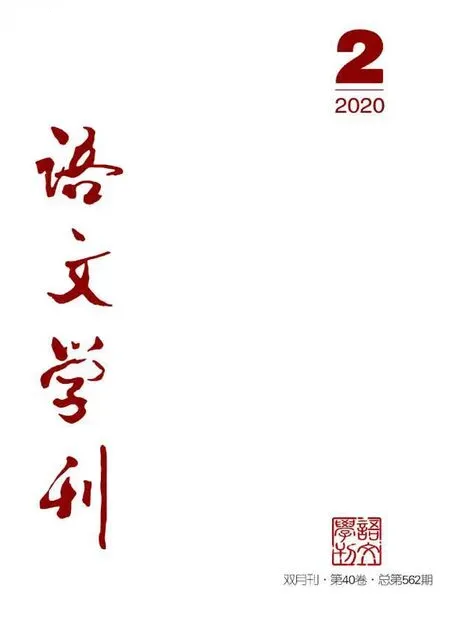《文心雕龙》:“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巅峰
○ 王万洪 杨雨佳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杨雨佳,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论与文化。
一
有关《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研究,有“折中”一说,以周勋初、王运熙先生为代表。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一文将刘勰的文学思想视为折中派,与当时(齐梁)裴子野等守旧派和萧子显、萧纲等趋新派相区别[1]。王运熙《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一文认为对永明文学及其以后文学的“新变”现象,可分为反对派、赞成派与折中派,以裴子野等为反对派,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为赞成派,而刘勰与钟嵘、萧统等为折中派[2]。周、王两位先生将齐梁文论派别三分的论述,虽然具体划分稍异,但意见基本相同,其立论的基点,是齐梁时代广阔的社会风尚与文学理论背景。刘勰的文学思想是“折中”齐梁文论的产物。
笔者认为,上述两家的意见有其合理的一面,即“知人论世”的一面;但是这个“折中”文学思想并不是复古与新变直接结合的产物,“折中”说在看到时代背景等外围因素的同时,即重视“知人论世”的同时,忽略了“以意逆志”,即对《文心雕龙》内证的分析和研究。《文心雕龙》全书高举的文学尚丽大旗,并非刘勰取法时风的产物,而是在哲学依据上取法文学原道、自然生丽的产物;并非魏晋玄学思潮重情论性、“馥采曲文,经理玄宗”的产物,而是远取儒家雅丽、阴阳诡丽、楚辞奇丽的结果。相反地,魏晋宋齐的文学之美与文学之丽,恰恰是《文心雕龙》除“枢纽”论以外,在几乎所有篇章中加以贬斥的对象。刘勰以为,“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近代文学浮浅诡俗、讹滥丛生,取法不正、争奇斗艳,“竞今疏古”“莫肯研术”,思想内容已经不雅,即使尚丽,也是轻艳浮浅之丽,因此,要求“执正驭奇”“正末归本”,以“圣文雅丽,衔华佩实”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文学创作。于是,《文心雕龙》跳出时风,上寻自然之道,渊源儒家经典,远远超过当时“复古、新变、折中”三分的理论水平。如果以“文学自觉”称呼六朝文学抒情尚美的特点,那么,《文心雕龙》雅丽思想是对“文学自觉的再次自觉”,是对“文学自觉”感性过度的理性回拉。
二
古代文学理论界讨论甚多的关于“文学自觉”的命题,有汉代开始说(张少康、袁济喜先生等)、魏晋自觉说(鲁迅先生开端)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①。诚然,汉代文论与创作实践体现了鲜明的尚丽特色和“文学自觉”的萌芽,但是,因为文学本质特征的抒情性、审美性是明显依附于汉代经学与政治王权的,因此,尽管《毛诗序》“情动于中”、《礼记·乐记》“和乐之美”、扬雄《法言》“丽淫丽则”等文论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自觉”的命题仍然无法得到独立的回应。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两汉时期对屈原与楚辞的若干评价,这些评价往往出现互相矛盾的对立意见;即使同一个人的评价,也往往因为其所处立场与角度的差异而呈现大相径庭的分歧,比如班固等。这样,真正摆脱经学附庸、探索文学纯粹特质的理论主张,是在汉末建安的曹丕与西晋年间的陆机才开始的工作。曹丕、陆机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诗赋欲丽”“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的尚丽文体风格论,提出了作家气质与文章风格类型的“文如其人”论,提出了文章功能的“伟业不朽”说,提出了文学鉴赏的态度意见,提出了文学写作思维探索与“物—意—文”的写作过程理论,对“物感说”“灵感论”“言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和具体主张——这些直接关系文学审美、抒情、思维、风格、内容、功能、鉴赏的具体意见,直面写作本质与过程,直面实践与意义,直面技法与鉴赏,这才是文学真正自觉的到来。
文学理论的自觉探索是文学创作自觉的保证,《文心雕龙》的理论水平超越了之前“文学自觉”的文论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序志》来分析《文心雕龙》何以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序志》篇有一段话,专论“文学自觉”的文论主张: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②流别,弘范③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3]610-611。
这一段话涉及魏晋时代的一些著名文学理论家及其著作,累计有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论》④、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六家,其后又简述了东汉桓谭与刘桢、应贞、陆云四家“泛议文意”的主张。上述十家中,应玚《文论》与应贞文论今已不传,其余八家的文论主张我们都还能够看到。尽管挚虞《文章流别论》与李充《翰林论》仅剩残文数条,但仍和桓谭、曹丕、曹植、刘桢、陆机、陆云的文论主张一起影响到了《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更是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和深入研究⑤。
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文,以论述文学评论为主,其文体风格、文气清浊、文体差异、鉴赏态度、文学功能诸说,对《文心雕龙》的刚柔风格论、文体风格论、作家才性论、知音鉴赏论、“树德建言”说有着深刻的影响。陆机《文赋》以论述文学创作为主,其说折中儒道,不仅论述“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之丽,更将重点指向文学创作“如何能丽”的探讨,其思维论、物感说、风格论、情性论、写作过程论等理论,都被刘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诗缘情”一说,直接《毛诗序》与《乐记》,是魏晋六朝诗赋理论中重情尚美一块的理论开启点。《文心雕龙》全书论美谈丽,论述情性,提出诸如“人禀七情,莫非自然”“辩丽本于情性”“情经辞纬”“圣贤书辞,非采而何”“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等等重情尚美的文学理论主张,这既有魏晋玄学的影响,更有曹丕、陆机文学理论主张的直接影响。比如,仅仅以《文心雕龙》的风格类型理论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两家的影响所在。《文心雕龙》论述的“八体”基本风格类型是“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至少从术语运用角度来看,与曹丕和陆机的文体风格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与“说炜晔而谲诳”近似,“炜烨”即“炜晔”字形之异;“精约、显附”二体,即合“论精微而朗畅”之意;曹丕说“奏议宜雅”,陆机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归纳出来的“典雅”一体,正是对曹陆二人所使用术语的继承与发展,如此等等;甚至于“圣文雅丽”的风格,作为八体“得其环中”之核心,与曹丕、陆机之“雅”“丽”文体风格论也是关系密切;同时,《定势》篇论述文体风格的六种基本类型是“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宏深、轻艳”,与曹陆两家所论,一样的极为近似。
但是,刘勰对上述十家文论是报以贬抑之心来论述的。对曹丕等六家,刘勰认为他们“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六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够完整全面,论文不从大处着手,因此评价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他们各自有着“密、辩、华、巧、精、浅”的优点,同时存在着“不周、无当、疏略、碎乱、少功、寡要”的不足,整体上看,对六家是不满的;同时认为桓谭、刘桢等四家没有文论专著,不过是偶有论文之语,即使中肯的话也显得偶然。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上述十家,每一家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多数还具有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在文学史、文论史上影响甚大,比如王充对桓谭极为赞赏——对于如此优秀的前代贤才,刘勰为什么要这么评价呢?
前六家文论广为人知,数量也多,《文心雕龙》对其直接或间接的引用不少,此不赘述。对于后四家,《文心雕龙》中对桓谭论文之语有三处引用。
第一处是在《哀吊》篇中:“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3]168桓谭评价司马相如《吊二世文》“其言恻怆,读者叹息”,有很强的感染力,是典型的“曲终奏雅”的好作品。刘勰引用桓谭的话,是在证明吊体经典作品的基本特点。第二处是在《通变》篇中:“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3]397《通变》简略地论述十代文学发展史,以为“从质及讹,弥近弥澹”,近代文学发展不良,是因为“竞今疏古,风末气衰”所致。刘勰指出近代写作者“近附而远疏”,习染不正,师法不古,“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因此养成不良技法之后,难以改变。桓谭的话是为了证明“刘扬言辞”等“汉篇”的美而有采而发,是刘勰拉来为自己的见解作正面论据的典型。第三处是在《定势》篇中:“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3]407刘勰引用桓谭的话,是为了证明文家“势殊”的存在事实,是为本篇文体风格各有不同的“本采”论寻找到的正面论据,桓谭所说“浮华、实核、众多、要约”的不同风格,是“文家各有所慕”的情性风格论,各体之间并无高下差异,其意思是说应该对各种风格“兼解具通”,不要偏解执一。
对刘桢论文之语则有两处引用。第一处是《风骨》篇:“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3]388刘勰在《风骨》篇中引用曹丕与刘桢论述“文气”的话,认为二者均是“重气之旨”,即所论重视“文气”。《风骨》篇论述“文气”,主张作家“缀虑裁篇”时的“务盈守气”,这样作品才会有“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充实辉光之美,“文气”论实际上是从主体修养角度对“文如其人”论的另一种说法。第二处是在《定势》篇中:“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3]407刘桢的话是认为文学风格有“强弱”之分,主张阳刚风格为美。刘勰认为他论述的仍然是阳刚“文气”思想,不过文学风格虽有“刚柔”之别,但不能片面强调“壮言慷慨”的阳刚风格,其言外之意是认为柔性风格同样重要,应该刚柔兼备,才是对文风的全面把握。这与他在本篇中持有的“兼解倶通”的方法有关,正是因为有了“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的方法论基础,刘勰才对“奇正”“刚柔”“典华”“雅郑”分析得深刻透彻,以“惟务折衷”的态度来客观地分析这些风格各自存在的理由,而不是以个人好恶为准来片面理解。上述两处引文,刘勰一褒一贬,符合自己见解的予以赞美,不合自己见解的予以辨正。
对于陆云文论的引用一共有四处。第一处是在《定势》篇中:“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3]407刘勰以“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也”评价之,认为应该“情经辞纬,先情后辞”,既要重视“文势”,也要重视文采,不可偏废,在论述文势的同时,为《情采》篇打下基础。第二处是在《镕裁》篇中:“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3]426本篇论述文章裁剪,主张不要繁杂,陆机“情苦芟繁”,陆云也“亟恨其多”,不过因为“雅好清省”之故,对陆机以“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相称,刘勰认为陆云仅仅从个人喜好出发而不能公正地论述文学,这是错误的。第三处是在《章句》篇中:“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3]411刘勰认为陆云“改韵从调”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改韵稍快,因此主张与“百句不改”的用韵之法相互结合,以“折之中和”为宜,这显然是刘勰“惟务折衷”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第四处是在《养气》篇中:“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3]511刘勰将王充、曹操等人关于写作伤神的话与陆云“用思困神”的话引用在一起,作为正面论据来支持他“写作宜养气”的谋篇宗旨,这是唯一从正面来看陆云文论的地方。
上述分析表明,桓谭等四家文论有得有失,刘勰认为他们“泛议文意,往往间出”,是有道理的,比如陆云之论,刘勰主要是以之为反面论据来看待。但是,评价他们“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则显得非常严重,如此上纲上线,意在为何?
笔者以为,这正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创新意义之所在。简言之,《文心雕龙》在继承吸收魏晋文学理论“自觉”成果的同时,又对这些“理论自觉”所出现的不足一面进行纠正与提升,呈现出更高、更新、更精的内容与超越时代的特点。《文心雕龙》的“再次自觉”,在《序志》篇中体现有三。
第一,写作动机。《序志》篇明确告诉读者,《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有三,一是求得令名。刘勰以为生命脆弱,为了“树德建言”,一定要写本书留下来。这是《左传》“三不朽”说,与孔子、司马迁、扬雄等人“名德”思想影响的结果。二是方向选择。写作最好的是进行注解儒家经书的工作,但是前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很难超越。刘勰认为文章之“运用”是儒家经典的“枝条”,功能巨大,于是选定写作“文章”。三是写作的针对性。刘勰写作“文章”,不是写诗赋之类的文学作品借以名家,而是写理论专著,专门研究“为文之用心”,针对当下文坛讹滥的离本趋势而发。近代文学不遵守经典的根本规范,形成了很严重的弊病。因此,《文心雕龙》的直接写作动机是为了纠正文坛当下的不良创作,间接动机则是为了著书留名,以求不朽。这就首先确立了一个尊崇儒家、崇古抑今的基调:古代经典是好的,近代文学是该批评的——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大量的文学创作,不入刘勰法眼,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标准,一定会高于“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水平。
第二,体系完备。通过刘勰自述其书之体系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采用“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的《周易》数理来确定篇目数量⑥,吸收道家“自然之道”来作为论文根本,以儒家圣人和经典为论文之体、宗法之经,吸收纬书、《离骚》的优点,在思想取法上广取各家,为我所用,因而立论深刻,论述充分,见解独到。全书“论文叙笔”部分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综合立体方法,篇目众多,“囿别区分”,远比上述十家细致、完备、深刻。“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的二十四个篇章,论述思维论、风格论、技法论、文学史、物色论、作家论、鉴赏论、修养论等等有关写作的全方位问题,并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前述十家所不可比拟的。刘勰以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也就是说,前述十家的文论主张,最多不过是“铨序一文”而已,远没有达到“弥纶群言”的地步。“弥纶群言”就会“照隅隙,观衢路”,文论功能与影响上就会“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益后生之虑”。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文心雕龙》论述的写作之道,理论体系完备充分,在功能影响上确实比上述十家更高更深,而且迄今没有任何文论专著可以超越。
第三,理论方法。《文心雕龙》自觉使用“惟务折中”的思维方法,这是其理论水准超越前人的最根本原因。折中方法论源出儒家、道家、兵家,刘勰也有可能借鉴了佛家的“中道”思维⑦。刘勰认为上述十家文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全面、不完整,因此《文心雕龙》要以全面完整为目标,超越它们。比如,《通变》篇综述历代文风时指出: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3]397。
这一历代文风总括之论,以“黄唐淳而质”与“宋初讹而新”为正反两极,以“商周丽而雅”为折中范式,鲜明地体现了“九代咏歌”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文学发展趋势。运用折中思维论观照之,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心雕龙》以“商周丽而雅”为折中历代文风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以《通变》《时序》为主要载体的“质文代变”的文学发展史论,从而“蔚映十代”,第一次撰成中国文学简史。其开辟独创之功,除了刘勰纵观历史的宏大视野,折中思维方法论的运用助力不少。此外,《章句》篇引用陆云四句换韵的话,认为应该“折之中和”,方可“庶保无咎”;《知音》篇提出了鉴赏的正确态度和“六观”的操作方法,尽管有曹丕《典论·论文》关于文学批评态度与方法的影响,但其理论见解绝非曹丕可比,如此等等。
因此,从写作动机、体系内容、思维方法来看,《文心雕龙》远远超越了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所有文学理论。
三
通观全书,对于汉魏晋十家“文学自觉”的文论主张,《文心雕龙》进行了坚持正确方向、主张重情尚美、提倡文学新变的积极阐释,吸收、运用了相当多的十家文论。但是,曹丕、陆机开启的文学理论“自觉”,最后并没有走在一条健康发展、良性发展的正路上,而是在战乱频仍、世积乱离、残酷血腥的时代政治格局下,在儒学式微、经学崩溃、思想混乱、玄佛思潮乘虚而入的学术思想局面下,文人学者一方面向重情尚美大力进军,逐渐出现了美文丽辞、绮丽巧艳、奢华淫靡的靡靡之音;另一方面恐惧现实谈玄论佛,走向了寄情山水、讽喻外物、远奥隐情、玄虚空淡、为文不用之势。这两种趋势并存而以靡丽轻艳为主,使得六朝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于是在重视文学美丽精神的同时,也对新变轻艳、师法不古、创作讹滥、思想不雅、作用有限的创作实践提出了批评与救弊主张,这一文学理论主张就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雅丽文学思想[4]。
《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从全书来看,其“自觉”体现有三。
第一,理论渊源。《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结合道家思想与其他各家思想为辅助,体现了兼收诸家而独尊儒家的鲜明思想取法。具体而言,“雅”出于儒家,儒家主张“雅丽”并重,而“丽”还有汇聚诸家思想的理论渊源。道家文艺美学思想重视对“美”和“妙”的探讨,同时,从《庄子》开始谈“丽”,《淮南子》大量论“丽”,但是道家论隐幽,谈避世,少论政,不谈雅,即“丽而不雅”。这样,“雅”与“丽”的结合,需要在整体上综合儒家和道家文艺美学思想,才能得到既雅且丽的结果。根据《辨骚》篇的说法,“丽”之渊源之一,来自楚辞之“奇”,汉赋随流而下,“追风以入丽”;另据《时序》《才略》等篇的论述,屈宋楚辞的源头,是“纵横之诡俗”,是出于谈天飞誉、雕龙驰响、飞辩驰术的阴阳家和纵横家。联系《序志》篇对《文心雕龙》书名解释中提到的邹奭“谈天雕龙”的言说之术,瑰丽迂回,虚诞莫测;联系到书中端木赐、烛之武、苏秦、张仪、范雎、蔡泽、李斯等人的游说君王、干预政治的言辞技巧之术,以及孟子的雄辩无敌、墨子的难楚存宋、鬼谷子的《飞钳》精术——这些“诡丽”的言辞技巧,才是辞赋“奇丽”特点的根本来源。这就是说,是语言之“丽”影响到了文学之“丽”,从而形成“言文皆丽”的历史演变脉络。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思想内容与语言文辞的雅正规范,于是,五经之“雅”与辞赋之“丽”的结合,就成为“衔华佩实”的雅丽文学思想。《风骨》篇说“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经典雅正,史书实录,子书技法思想多样而丰富,这不仅是刘勰主张的作文如何才能有“风骨”的取法原则,实际上更是刘勰本人文学美学思想博杂精深、镕铸百家的来源所在。《文心雕龙》一书,其雅丽文学思想除了源出儒家,比较明显地,还包含道家、阴阳纵横、法家、兵家、玄学思想,并融会贯通,熔为一炉。而在所有的这些学术思想中,最主要的是独尊儒家。《文心雕龙》在千年以降的各家思想中吸收精华,在“文学自觉”、重情尚美过度的时风中寻找正途,以求归正。
第二,文论特点。《文心雕龙》立体而丰富,其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内涵特征,体现了“文源于道,郁然有采”的文学本源与文学尚丽的哲学依据,体现了“自然之道”循环相因的新变意识,体现了征圣宗经的经典意识与思想规范,体现了折中“雅”“丽”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上溯先秦、取法两汉的史学意识,既包含了魏晋六朝重情尚美的文学美丽精神,又能崇尚雅正的思想内容,润色华丽的文采,上溯数千年,超越同时代,达到全面、立体地整合所有写作技法与文学规律,并借以指导正确写作的目的。
第三,道器兼备。《文心雕龙》在“枢纽论”中提出具有崇高理论高度的写作之“道”,在二十篇文体论中详细论述各类文体的创作规范与写作得失,在十九篇创作论和五篇批评论部分深入探究写作技法、追求“执正驭奇”、崇尚“执术驭篇”、探索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以此构成全书论述“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使之成为具体写作之“器”。《文心雕龙》既在哲学高度论述形而上之的写作之道,又在技法与创作层面深究形而下之的操作技法,体现了“本乎道,进乎技”的原理性质与操作技术的结合,成为理论性与操作性完美结合的文论主张。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是对数千年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创作得失的整体综合,是对萌芽于两汉、成熟于魏晋齐梁之“文学自觉”的再次理论自觉,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处于“文学自觉”时代文论巅峰的位置。
【 注 释 】
①学术界对“文学自觉”的起始问题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其一,以张少康、袁济喜、詹福瑞先生为代表的“西汉说”;其二,以刘跃进先生为代表的“宋齐说”;其三,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说”,王遥、游国恩、李泽厚等人对此做了进一步引申和拓展,把“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延长至魏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以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主,集中代表这个意见的是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中的看法:“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载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袁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是“文学自觉的标志”的意见很深刻。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心雕龙》还对“文学自觉”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发展思路,超越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水平。
②按:“仲治”,一作“仲洽”,西晋学者挚虞的字。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龙译注》作“仲洽”,杨明照、詹锳等先生认为作“仲治”为宜。
③按:“弘范”,一作“弘度”,字形相近之误,东晋学者李充的字。各家通行作“弘范”。清黄叔琳与杨明照、詹锳、吴林伯等先生以为作“弘度”为宜。
④《文心雕龙》的多数注本以为这里的《文论》是指应玚《文质论》,牟世金先生《译注》认为确实应为《文论》,此文已经散佚,《文质论》与论文无关。
⑤有关曹丕、陆机文论对《文心雕龙》影响的研究文章非常之多。各家主要的意见是:曹丕主要是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陆机主要是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对《文心雕龙》发生了积极影响。
⑥《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夏志厚先生等研究者指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序志》一篇是总目,其余四十九篇是个案专题,对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数理关系。又:周绍恒先生等研究者指出,《文心雕龙》全书避“衍”字之讳,实则因为成书于梁代初年,必须避讳梁武帝萧衍之名“衍”字之故,所以此处改“衍”为“易”。
⑦关于《文心雕龙》“折中”方法论的渊源,“龙学”界有源出佛家与源出儒家之争。源出佛家的意见主要是认为“折中”方法论是龙树“中道”论的产物,以张少康先生论述最为充分,张辰先生等同持此说;源出儒家的研究者认为“折中”观念是儒家“执两用中”“分而为二”“中庸之道”“折累中平”的产物。两说都有道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道家也有中道思维,体现为正反对比的辩证思维模式;兵家也有奇正结合、正反结合而取其适度与适中的思想,实际上,“中道”思维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种传统思维。因此,片面地说“折中”思维方法出自儒家或者佛家的争论,虽然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但是如果注意到《文心雕龙》思想驳杂而以儒家为主导这一点,就应该采取合观各家的方法来讨论“折中”方法论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