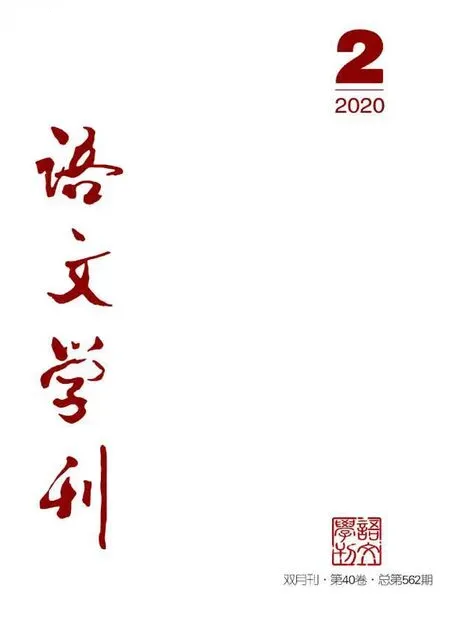清朝入关之前的儒学风气
○ 李贵连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金天兴亡国之后,皇族完颜氏几于族灭,居住汉地的女真人因通婚,或为躲避战乱而隐姓埋名,与汉人融为一体。居近内蒙古地区的女真人因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深,在元代“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1]的政策之下,加入蒙古族群。而金代未迁入内地的东北女真人,遂成为明代女真人的主体及清代满族的先世。
一、服膺天道与勤勉国政——努尔哈赤时期的儒学渊源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生于苏克苏浒河畔的赫图阿拉。《清史稿·太祖本纪》称努尔哈赤:“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2]58努尔哈赤出生的时代,嘉靖皇帝迷信神仙道教,荒怠国政,大明王朝锦绣繁华的背后,已是一片西山晚照。而遍布东北大地的女真各部,却在蒙昧朴野的时空中迎来皎月初升。努尔哈赤时期的辽东女真,主要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三部。每一分支之下,又有许多部落。建州女真主要聚居于抚顺关以东、鸭绿江以北及长白山南麓;海西女真主要居住在东辽河流域及乌拉河、辉发河一带;野人女真则大致散居在长白山北坡,乌苏里江靠海处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由于地处荒远且生产条件落后,女真人长期处于以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状态,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自然是蛮夷之鄙人。
明代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在东北设置卫所,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通过分封有势力的部落酋长,以达到对女真人的实际统治。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经在永乐三年(1405年)进京接受了朱棣的敕谕,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使的爵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虽属女真贵族阶层,但是他们未能继承明朝的任何官方职位,财力权势均非显赫。在部落的权力争斗和仇怨纷争中,只能环卫而居以求保御。觉昌安为振兴祖业以及族人生存考虑,与当时建州女真势力最大的部落酋长王杲结为亲家。据《清史稿》的记载,是为“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2]58礼敦即为觉昌安之长子。此外,还有谓《清史稿》所言之“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都督阿古女”[2]2298中的阿古即为王杲,也就是说王杲同时可能还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①应该是在李成梁讨伐王杲古勒山寨的战役中,年少的努尔哈赤为明军俘虏并成为李成梁帐下的亲兵。《山中闻见录》记载:“太祖既长,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3]努尔哈赤与汉人的密切交往及其所受汉文化的熏陶,促使其开阔视野,宏远识度。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在觉昌安、塔克世被明兵误杀事件中负重要责任的尼堪外兰。努尔哈赤起兵初期,颇具王者之风。在夺取诺米纳的本部萨尔浒城时,于城破之时安顿降民,不使夫妻离散。努尔哈赤不仅每战身先士卒,而且能够不计前怨,廓然大度。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攻打翁克洛城时,鄂尔果尼和罗科射伤努尔哈赤。二人被俘后,努尔哈赤赞其为“壮士”,授职佐领并户三百。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终于杀死宿敌尼堪外兰,建城佛阿拉,自称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2]58,对建州女真的秩序维护及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此,努尔哈赤凭借惊人的勇力和狡黠的智慧,征抚并用,逐步实施其统一女真的谋划。
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被明廷任命为建州卫都督佥事,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充分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陆(又写作龚正六)客于辽东,遭女真扣留,即约在此年前后归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尊龚正陆为“师傅”,对之“极其厚待”[4]。龚正陆为努尔哈赤润色文字、教授子侄。虽然清朝的官方文献人为抹去这位后来涉嫌向朝鲜透露女真信息之人,但他对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的谋划和儒家思想的启迪,具有难掩之功。除龚正陆之外,努尔哈赤时期生活于辽东的汉人文士,还见于《李朝实录·宣祖实录》的“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5],以及载于《满洲实录》的“秀才郭肇基”[6]343等。虽然这些汉人文士并没有留下翔实的史料,但他们在满汉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女真汉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文字作为人类高度文明的重要表征,是凝聚族人和承载民族文化的特定载体。西夏元昊令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西夏文字,完颜阿骨打也曾令完颜希尹和叶鲁二人参照契丹大字和汉字创制女真大字,完颜亶又依照契丹小字创制女真小字。满洲初起时,使用蒙古文字,由于蒙古文字和女真语言不同,所以在实际使用中要进行迻译,显然会带来种种不便。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协女真语言,联属成句,因文见义,是为无圈点满文。其后皇太极时期,又令达海对满文酌加圈点,以区别人姓名及山川、土地之称。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满文的文字语音体系自是更加完善。满文的创制让政令法规的颁行更加便捷畅通,也对普及提高满族民众的文化教育居功至伟。因为无论是学习汉字还是蒙古字,都局限于精英文化圈的范畴。满文依女真语音制成,显然更易于为普通民族所理解和掌握。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皇太极,命令达海等人用满文翻译了《大明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资治通鉴》《六韬》及《孟子》等等著作,甚至还翻译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大诰》作为治国指导。虽然有清一代官方皆三令五申维护承载本民族文化的“国语骑射”,但是满文的创制颁行,却对满族民众学习汉文化起到了辗转的媒介作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定立以旗统民、以旗治民的黄、红、白、黑四旗制度,以后又逐渐扩充至四镶旗,并易黑为蓝。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日益完善,军民日渐增多的同时,最基本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也在其头脑中不断加强。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7]258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7]258虽然战争总不可避免有血腥和残杀,但自古未有嗜杀而可得天下者。如果一味以屠戮为策,只会激起更多更持久的反抗。无论是努尔哈赤所接触的儒家仁政思想,抑或是现实的残酷教训,无疑都会让“天锡智勇”的努尔哈赤学会爱惜民命。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在率兵讨伐乌拉时,莽古尔泰请示渡河屠城,努尔哈赤就明确提及:“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2]2323此外,“治国者以积贤为道”[8](《通国身》),国家族群的兴旺,除有民众的人心所向,还需要贤能之士的倾心匡助。随着国事日繁,努尔哈赤也多次申谕臣下举荐人才,流露其“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9]的渴求。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为建立后金政权做准备的最后一年,令人在赫图阿拉兴建孔庙、佛寺、玉皇庙等建筑。同时兴建的包括承载满族人萨满信仰的祭天堂子,建造其他庙宇的信仰实用主义也比较明显,但是中原文明的精神内核,已经日益取代萨满巫教,成为女真文化的主要面向。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定国号为金之后,即已着手开始其与明廷逐鹿中原的作战准备。在懈怠荒淫的万历皇帝统治之下,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一战,扭转了此前女真处于弱势的战略局势。随着抚顺、辽阳、沈阳、广宁等大片土地的获得,如何统治和治理汉人,平息紧张的民族关系,整顿社会秩序,成为困扰努尔哈赤的紧要问题。天命五年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努尔哈赤竖二木于门,谕令“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10]。努尔哈赤根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在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年)迁都辽阳时,还专门派其子德格类及侄斋桑古安抚人民,传令军士“不许扰害居民,劫夺财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6]332。
有志于取明朝皇帝而代之的努尔哈赤,致力于建立有效的政治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除政治、法律等强权工具之外,还需要风俗、信仰的人文教化和思想羁络。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年),在蒙古兀鲁特部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部来归附时,努尔哈赤谕之曰:“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治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是以道不拾遗,拾物必还其主,皇天所以眷顾,盖因吾国风俗如此。尔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盗贼欺伪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祐。使汝诸贝勒之心变乱为害,而殃及于国矣。今既归我,俱有来降之功。有才德者固优待之,无才能者亦抚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旧恶不悛,即以国法治之。”[6]347-348
虽然蒙古、女真人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对“上天”的敬畏,却对各族民众均有较为普遍的约束作用。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11]所以努尔哈赤在告诫蒙古各部时,抬出“上天”这一足以警戒世人的恒常规范。天命八年即明天启三年(1623年),努尔哈赤在八角殿召阿吉格福晋及众公主,训之曰:“天作之君,凡制礼作乐,岂可不体天心。然天心何以体之?莫若举善以感发其善者,诛恶以惩创其恶者。”[6]358又天命十年即明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在回复科尔沁鄂巴洪台吉的书信中,言及:“盖兵不在众寡,惟在乎天,凡国皆天所立者也,以众害寡,天岂容之”[6]384。中国先秦时期兴起的儒学“敬天法古”核心信念,除是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已经内化为努尔哈赤的价值追求。“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7]30,无论是从“外王”层面的“保天下”,还是从安邦角度的“保其国”,“天道”“天命”,都已经成为努尔哈赤的内心敬畏。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12]45虽然从李民寏的角度看来,努尔哈赤未免于“猜厉威暴”,但是也能够从侧面看出,努尔哈赤的奖善惩恶和上体天心并非虚言,而是雷厉风行之。
在努尔哈赤人生的后期,还时常自如地运用儒家“遵道”“才德”等观念。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年),当八固山额真等问努尔哈赤“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锡之福祉何以永承”[6]349时,努尔哈赤曰: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庶几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6]349。
努尔哈赤在盛京建造了大政殿和十王亭,国政由八旗旗主共商,征战所得也皆由八家均分。这种贵族集权制,将汗王置于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虽然当时中原王朝的帝制也设有约束皇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八王共治”,却从政治组织形式上赋予女真贵族更多的权力。在政治权力的传承人问题上,努尔哈赤所倾向的推举制,也与中原宗法结构下所优先的“立嫡立长”不同。而努尔哈赤将汗位继承人的标准纳入天道、德行的衡量体系,又体现了对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君奭》)[13]390天道观的服膺。
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卫遇到了誓死不退的袁崇焕。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努尔哈赤自省曰:
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14]390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自感时日无多的努尔哈赤训斥诸王曰:
昔我宁古塔诸贝勒及栋鄂、完颜、哈达、叶赫、乌拉、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戕害,以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有……昔卫鞅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又《忠经》云:“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既形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
……
昔宋刘裕谓群臣曰:“自古明君贤相,皆由困而亨。舜发畎亩,傅说举版筑,胶鬲举鱼盐,百里奚食牛,天意何居?”群臣对曰:“君相之任,大任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心志,使之遍虑事物而内不得安,劳筋骨使外不得逸,饿体肤使食不得充,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为君,必能达国事,是人而为相,必能悉民隐,天意如此而已。”
若人之言,诚为善识天意者也。以历艰苦者为君,致令国受其福;以享安逸者为君,致令国受其苦。天见我国之民甚苦,故降吾,身历艰辛,使之推己以及民。吾艰苦所聚之民,恐尔诸王多享安逸,未知艰苦,致劳吾民也。不知有德政方可为君为王,否则君王何以称也?[14]411-414
这段颇长的文字,是人生晚期的努尔哈赤对自己一生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后生晚辈的殷切嘱托。努尔哈赤引用了《史记·商君列传》、马融《忠经》等经典,虽然刘裕与群臣的对话不知出自何典,但是其中所讨论的,其实是《孟子》中的传世之论。努尔哈赤能够如此熟稔在汉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书籍和典故,不难体见其对儒家经世之学的关注和效仿。尽管官方记载中往往充斥着“仁爱德政”的假面,而一边又在粉饰文字中洇透出暴力铁拳之下的汩汩鲜血。《满洲实录》之类记载中的语句也或有文人集团的当时润色和后世加工,但对于经国治世的核心精神,努尔哈赤当是深悉并尽力践行之的。努尔哈赤作为“蒙难艰贞,明夷用晦”[2]62(《清史稿·太祖本纪》)的开国之君,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均有不凡建树。虽然与元代的成吉思汗类似,努尔哈赤也往往有“仇之以仇,恨之以恨,恩之以恩,德之以德”[15]的恣意恩仇,在其执政期间也不止一次发生对汉族民众的野蛮残杀,但努尔哈赤注重任用贤才,不拘亲疏门第,赏罚分明,善于学习,服膺儒家文化,勤力于国家的理政治平,亦可谓瑕不掩瑜,对推动女真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倾心相近与择己所利——皇太极时期的崇儒风尚
也许是由于努尔哈赤在继任者问题上倾向于八旗旗主共同推举制,所以临终并未指定汗位继承人。皇太极最终因文武双全,德行优异而胜出。皇太极誓告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2]62敦勉诸大贝勒等。《商书·汤誓》有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3]127这里的“上帝”,不必做神格化的理解,看作是对“上天”“天道”理性自然的敬畏,是周代以后阐释的主流倾向。努尔哈赤已经把对“天道”的畏惧和“德行”的持守看作君王的内在职责。但是,如何展现自身对“天道”“德行”的践履与追求?努尔哈赤所提供的答案是勤勉与德政。但是勤勉与德政有时难免会局限于“施予者”的主观和高高在上,而皇太极将敦行“天道”的落脚点放在“行正道”,大致包含对“受予者”声音的聆听与对民意的吸纳考量。因为“正道”与否,不在于统治者的自我宣称,而是沉淀于世道人心的考评。《周易·说卦》有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16]《周易上经·离卦》言及:“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17]何以遵循民意而敦行“正道”?皇太极的履行之道是“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礼义”是《礼记》中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礼法道义②;“友爱”是敦勉宗族血亲乃至世人之间和谐团结,不至仇怨相杀的普遍信仰;而“公忠”是《庄子·天地》中拔擢贤才以“公正忠诚、尽忠为公”的用人精神和人格向往③。
皇太极自幼受教于龚正陆等汉人文士,从内心倾慕儒家文化,在当时就以“识字”即粗通汉文,在朝鲜人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中有专意记载[12]44。皇太极即位以后,一改努尔哈赤对待汉人的高压政策,推行民族和解策略。皇太极谕令:“满洲、汉人,毋或异视,狱讼差徭,务使均一。”[2]62虽然在当时的满洲统治区域,真正意义上的满、汉平等还路途遥远,但皇太极毕竟从法令的层面给予了政策支持。从实际行政的角度,皇太极大幅减少了汉人隶于奴籍的人丁,将之编户为民,并选择汉官廉正者治理政事。皇太极即位的天聪元年即明天启七年(1627年),满洲大饥荒,民不聊生,以致百姓铤而走险。如果按照努尔哈赤时期的严刑峻法,定会有大批百姓性命不保,皇太极恻然曰:“民饥为盗,可尽杀乎!”[2]63令人鞭而释之,仍发国帑赈济灾民。皇太极哀悯民生之多艰,而并非一概斥之为暴民乱众,近乎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7]80。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为儒臣设置“文馆”,亦曰“书房”,命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为选拔更多的文人秀士,皇太极谕令:“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中式者以他丁偿之。”[2]64皇太极对文人儒士甚为尊重,厢红旗牛录章京柯汝极乘马,途遇正白旗秀才,嗔怪其不躲避威仪,掌掴其面。皇太极训斥曰:“柯汝极既系礼部参政,如何打秀才的脸,问以应得之罪。”[18]54当时有些富于才华的汉人文士比如宁完我,为保全性命计,屈从于满洲贵族人家为奴。宁完我入直文馆之后,又推荐鲍承先等人,凡此诸人,均为皇太极政权的恢廓壮大建殊大功勋。努尔哈赤也曾对龚正陆、范文程等人优礼有加,但是真正从精神气质上亲近汉文化,倾心委任汉人文士,却要从皇太极开始。《清史稿·范文程传》记云:“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2]2412不管是由于身边文人士子的尽力推荐,还是皇太极自己对科试选拔贤才,抚慰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有深刻认识。总之,皇太极的这次考试既拔擢了二百余名各族生员,也对缓解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努尔哈赤曾经敦勉执政诸人推荐贤才,而皇太极所做的则是从制度层面而非人情方式去选贤任能,有效避免了干谒奔竞和市恩贾义。
当然,皇太极对汉人文士的亲近,源于其经国治世的杰出才华,而非如金熙宗完颜亶一样,似乎更痴迷于汉人的雅歌儒服、琴棋书画。范文程等汉人文士向皇太极所献谋的,也是如何统一区夏,安定百姓,而非进以“宫室、服御、妃嫔、禁卫之盛”[19]。皇太极在亲近文士的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文武各有其用,不可单赖其一。以皇太极写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书信为例,当需要以儒家大义进行劝服之时,儒者之言即为不易之真理,书云:
尓国每以南朝为天子,君也父也;其余皆属夷,小民也。殊不知明朝朱姓之祖宗,果系皇帝苗裔乎?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诚哉是言也。匹夫有大德即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即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之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天下;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朝洪武乃黄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考此诸国主天下时,尔朝鲜世修职贡。由此推之,则天下惟有德者主之耳,奚在继世者始有天下乎?[18]20
当朝鲜文臣阻抑两国达成结盟,反对降顺满洲之时,则宣谕之曰:
彼书生既败两国之好,大兴争战之端,将令此书生搦管前驱乎?抑令诸军荷戈以战乎?设军民罹祸,此书生讵能操儒者之言以相救乎?[18]93
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一直视明帝如君如父,虽然惮于满洲的军事实力,但其实很难从心底真正跨越胡虏视之的障碍,与清朝结成统一战线。皇太极恩威并用,一边不断赏赐恩徕,一边又加以威胁利诱。皇太极既重视文士以求聚拢人心,对儒家王政之德推崇备至并积极致用,同时又秉持兵革之利对威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确称得上深谙允文允武之精髓。
皇太极承努尔哈赤之志,或谓代表当时满洲贵族整体利益,继续着手实施征明大业。此时皇太极的出师理由,已与努尔哈赤时要报“七大恨”的口吻不同,而是升级为“朕承天命,兴师伐明”[2]64。曾经蕞尔小邦的报仇雪恨,在儒家文化战争观的影响下,通过彰显道德使命意识,为己方争取战争道义的合理性。因为“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20](《汉书·高帝纪》)。与顺承天命的口吻相承,皇太极也要尽力体现“仁者无敌”的气象和识度。皇太极谕令:“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之人,父母妻子勿使离散。勿淫人妇女,勿褫人衣服,勿毁庐舍器皿,勿伐果木,勿酗酒。违者罪无赦。固山额真等不禁,罪加之。”[2]64在攻打遵化过程中,蒙古兵扰害罗文峪民众,皇太极严令,掠夺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自杀害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加倍偿还。然而由于满洲“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12]44,不久仍复有蒙古兵杀人褫夺其衣,皇太极令人射杀之。当然,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及其难以完全掌控,满洲军队所过之处,其实也很难完全做到令行禁止。而且从皇太极的心态上来说,他有时候也默许军队能够“有所收获”,所以其所带给汉地普通百姓的痛苦,也是毋庸讳言的。
随着与明兵接连作战得胜及大片土地的获得,皇太极对待汉人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天聪四年即明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谕令:“天以明土地人民予我,其民即吾民,宜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2]65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游猎民族诸如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等等,常常在物资匮乏之时越过长城,深入农牧交集区域甚至是中原内地恣纵抢掠。其视农耕文化下的居民,往往如待宰之肥羊。金代女真人虽以中国之主自许,但是其统治区域局限于北方,而且金代虽然也算人文蔚兴,但在尽伦尽制的内圣外王冀求中,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知易行难。蒙古统治者始终在精神气质上亲近蒙古文化,明确将百姓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自然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对四等民众一视同仁。“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21]2673(《志第五十三·刑法四·斗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21]2675(《志第五十三·刑法四·杀伤》),这样触目惊心的民族压迫政策,赫然出现在元代的国家法典之中。
当然,终清一代,满族人在社会地位、仕途机遇以及福利保障上也优厚于汉人,但是这些都是相对隐形层面的选择性看待,而非专意赋予满人明确的高于汉人的法律特权。相反,“满蒙一体”,“满汉一家”,倒是清朝官方着意宣扬的政治主张。以努尔哈赤论,也许是因为他并未真正看到即将取代明朝皇帝,入主中原的希望,所以对待甚至是辽西地区的汉人,都难以称得上是“近者悦,远者来”[22]137(《论语·子路》)。但到皇太极时,由于崇祯皇帝的刚愎猜疑和大臣们的各图自保,大明王朝已经犹如盲马所驾之敝车,日益驰向万劫不复之深渊。满洲定鼎中原的梦想虽然尚未实现,但黎明前的曙光已经照耀着皇太极和矢志团结的满洲贵族。所以皇太极对待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满洲政权统治下的汉人百姓,有“其民即吾民”的珍惜。也才会认为:“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2]65也只有从内心定立了在汉地建立长远统治的追求和打算,才能真正从心态上贴近以儒家文化为重要表征之一的汉文化。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历代政权都比较注重以史为鉴。从南北朝开始,把皇帝的政令、言行编为实录,已逐渐成为定制。但由于儒家文化亲疏等差的分别,坦白直率的标准往往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2]137(《论语·子路》)。所以本来就颇有“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23](《史通·曲笔第二十五》)的痼疾,倘使君主再如北魏世宗元恪一般“尝私敕肇,有所降恕”[24],未必史官皆能如游肇一般坚执不从,秉笔直书。
天聪五年即明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幸文馆,入库尔缠直房,问其所修何书?库尔缠答为“记注所行政事”之书。皇太极曰:“如此,朕不宜观。”[2]66(《清史稿·太宗本纪》)皇太极对史职的尊重和自觉回避,是对儒家济古维来文化传统的顺承,也是对民心公论和历史道义的敬畏。皇太极又览达海所译《武诠》(《东华录》作《武经》),见其中“投醪饮河”故事,叹曰:“古良将体恤士卒,三军之士乐为致死。若额附顾三台对敌时,见战士殁者,以绳曳之归,安能得人死力乎!”[2]66(《清史稿·太宗本纪》)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25](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史鉴传统,皇太极对嘉善矜恶的追求,不单单是出于取是舍非的道德追求,更多的是出于治国之源层面的积极思考。
也许是皇太极对儒家维护君权的特殊作用有深刻认识,抑或说他对儒家文化有真正心灵上的亲近,所以总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借口以推行儒学。祖大寿据守大凌河,之所以一开始拒不投降,其实担心重蹈白养粹等降顺之后被阿敏、硕讬所杀,城中士民尽被屠戮覆辙的因素很大。因为满洲兵“先年克辽东、广宁,诛汉人拒命者,后复屠永平、滦州,以是人怀疑惧,纵极力晓谕,人亦不信”[26]29。但是皇太极利用此次机会,宣谕:“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2]67
当时的满洲贵族统治阶层比如阿敏、硕讬等,颇多信奉弱肉强食的赳赳武夫,不乏对儒家文化及文人士子谈不上好感之人。而皇太极对儒学及官学教育的崇弘,则对满洲教化氛围的文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仅是满洲的政治国策日益趋近儒家文化,在社会风俗及民间信仰的世俗层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皇太极禁止私立庙寺,喇嘛僧人违律者勒令还俗,原本深受满洲百姓崇信的萨满也越来越受到上至官方、下至民众的理性质疑。皇太极下令:“满洲、蒙古、汉人端公道士,永不许与人家祧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用端公道士之家,出人赔偿。”[18]13-14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萨满之名,但是连类而及,对萨满的贬斥不言而喻。
天聪八年即明崇祯七年(1634),初命礼部考试满洲、汉人通满、汉、蒙古语者,擢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次年,命文馆翻译宋、辽、金、元四史。因为此年八月偶然获得元顺帝传国玉玺,被认为是皇权天授,满洲各旗主贝勒遂积极向皇太极劝进。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改后金为大清。各行政机构或从无到有,或加以改善。不仅设置了旨在纠弹缺失的都察院,还遣官祭拜孔子,力图在政治气象上与帝王之业相侔。当然,在吸取中原文化优胜因素的同时,皇太极也始终保持着不可盲目全盘照搬汉文化的警惕意识。比如在读到《金史》中的金世宗时,皇太极感叹道:
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袖,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2]72
因为金人是满洲的先世,所以格外为皇太极所效法借鉴。在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胡服骑射一直是制敌的有利因素,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也曾经力排众议效法模仿。金代女真人多有效仿汉人装束者,致使骑射技艺渐疏,吸收这一前车之鉴,皇太极谕令礼部,若“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26]37。而终清一代,国语骑射也一直是不可移易的国策。
皇太极称帝之后,清一直胶着于与明廷的战事,凭借精娴骑射和勠力同心,逐渐在对峙中将明朝的元气消耗殆尽。洪承畴、祖大寿等,终因势尽而于崇德七年即明崇祯十五年(1642)实意降清。关于洪承畴投降时的情形,《清史稿·太宗本纪》记云:
上问承畴曰:“明帝视宗室被俘,置若罔闻。阵亡将帅及穹蹙降我者,皆奴戮之。旧规乎?抑新例乎?”承畴对曰:“昔无此例,近因文臣妄奏,故然。”上曰:“君暗臣蔽,枉杀至此。夫将士被擒乞降,使其可赎,犹当赎之,奈何戮其妻子!”承畴曰:“皇上真仁主也。”[2]76
汉武帝时,李陵被匈奴所虏,本不欲真心投降,后因父母妻子皆被屠戮,反迫其真意降顺。明末中国苦于战乱,崇祯皇帝自顾尚且不能,无暇顾及被俘宗室,倒也情非得已。与崇祯的务虚名而处实祸相承,明末士夫亦多躁竞气矜,“噍杀恚怒之音多,顺成啴缓之音寡”[27](钱谦益《施愚山诗集序》)。政治暴虐所致的戾气,在明末充斥一众士人学子的腹心。关于当时的社会氛围,赵园在《说“戾气”——明清之际士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批判》中描述为:“平居贫,临难死,且是可不贫之贫,非必死之死——似与生命有仇,非自戕其生即不足以成贤成圣。”[28]这种对己对人都很苛刻的生命态度,致使明廷上至帝王,下至官员百姓,对被俘投降之人及其家人亲属难以宽容。王夫之曾在《宋论》中,盛赞赵匡胤“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29]。赵匡胤虽出身武职,但是却定下了有宋一代崇尚文治和优待士人的传统。皇太极的崇儒右文虽或不及赵匡胤之敬惧勤谨,但是值明代朝堂“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30]276-277(《子刘子学言》卷一)的离心之际,其宽厚仁和还是颇为人所称赏的。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情即天理’”[30]276(《子刘子学言》卷一),如能善养民心士气,自然万姓归之如流水。
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无疾而终。虽然当时清朝尚未实现入关定鼎中原的宏图大业,但是清世祖顺治皇帝即位朞年,中外即归于统一,不能不归功于皇太极时期的励精图治,从而奠定王政之始基。清前期的八旗王公贵族,骄纵不法之事时有,皇太极总是着意弹压,不甚以其为满洲勋戚,有开国之功而刻意庇护开脱。相反,成为“天下共主”的理想总是激励皇太极敦本务农桑,戒谕诸王贝勒以“治生者务在节用,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2]77。
自然,皇太极之善行,有些是源自兄弟子侄、大臣之谏诤,不能掠众人之美而尽归其一人。有时其所行也不能尽如其所自我标榜,但他继努尔哈赤之后,从其父“草创之武夫,有秋霜烈日之威”,一变而为“颇具开阔之胸度,饶春风和畅之情”[31]。保存国俗的同时,优待汉人,崇儒兴学,大大加快了满洲汉化的脚步,由是才能进一步奄有中原,文教蔚兴。
【 注 释 】
①比如孟森《清朝前纪·显祖纪第九》中所言的“阿古都督为何等人,又不明言。今可断言阿古即王杲之转音,不明言者,讳之也。”见汉史氏述《清朝兴亡史(外八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页。当然也有根据《永陵喜塔腊谱书》记载,言“阿古并非王杲”者,见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中编之《宗谱分析》,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关于王杲与努尔哈赤之真实关系,迄无定论。
②《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96页。
③《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第十二》云:“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见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1978年重印本,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