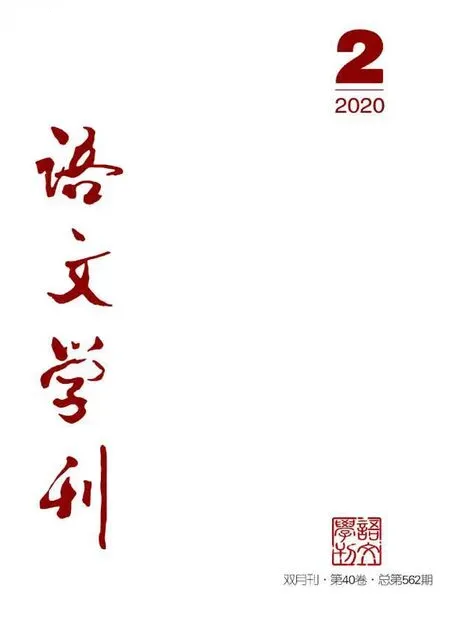《文心雕龙》之文字学
○ 朱文民
(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山东 莒县 276599)
黄侃说:“文者,集字而成,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妄。”[1]191“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非若锻句练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为能也。”[1]195字之不妄是缀字联篇最基本的要求。凡是从事汉语言文字工作者,必须首先闯过文字关。刘勰《文心雕龙》专列《练字》篇,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所以,罗章龙说:“衡量一个人的国学根柢的深浅,首先看他对文字学的造诣。”[2]
我国汉字,由形音义三个质素构成,民国以前把有关这三个质素的学问统称为小学,后来一分为三:研究字形的称为文字学,研究字音的称为音韵学,研究字义的称为训诂学。但是,三者又不可能绝然分开。但是,文字学之谓,民国以来始有此称。刘勰《文心雕龙》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学虽然涉及全书,但是却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练字》《声律》和《章句》篇。我们这里说的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字学,是字形意义上的文字学。
一、刘勰的中国文字发展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立《练字》篇,不是专门讲述文字学,设立的目的是服务于全书的宗旨,即文章写作过程中的文字选用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两大脉络:一是“经学思想”,二是“史学识见”。《练字》篇兼而用之。其史学识见表现在选字缀文,从汉语言文字的产生说起。
汉字是什么时候产生、怎样产生的呢?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多篇涉及文字学:一是《原道》篇,二是《练字》篇,三是《章句》篇,《镕裁》《章表》《声律》等篇也有明显的涉猎。关于字的起源主要在前两篇,刘勰是从《易经》中找到源头的。
刘勰在《原道》篇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庖牺”就是伏羲。刘勰认为,庖牺画的“《易》象”是最早的文字。
刘勰在《练字》篇说:“夫爻象列而结绳移”。这话出自《周易》。“爻”是《周易》中组成卦的符号:“—”为阳爻,“--”为阴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两卦(六爻)相重则得六十四卦,又称为别卦;“爻”含有交错和变化之意。“爻象”是指《周易》中六爻相交成卦所表示的事物形象、形迹。《易·繫辞下》:“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孔颖达疏:“言爻者,效此物之变动也;象也者……言象此物之形状也。”刘勰那个时代,尚未发现陶文、甲骨文,但是,金文已经有所发现。如西汉晚期宣帝的时候,在美阳发现的铜鼎上的铭文,经过好古文的京兆尹张敞识读,是周朝一个叫作尸臣的大臣受到王的赏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3]39。但这只能证明张敞是最早能识读金文的一位学者,其后的文字学家对其意义缺乏充分认识,也就未有把金文纳入文字研究资料范围中。刘勰所用的资料是历史文献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口碑资料。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刘勰是齐梁时期易学大家,所以刘勰的文字学资料首先来自《周易》是可以理解的。《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刘勰说的“仓颉造之,黄帝用之,官治民察”(《练字》),与许慎观点一致,皆为文献系统说。
钱穆先生说:“《易》之为书,本于八卦。八卦之用,盖为古代之文字。”并举例说明八卦分别是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将八卦“因而重之,犹如文字之有会意。……引而伸之,犹如文字之有假借”[4]。“书契”之谓,目前学界意见尚不一致。我们认为“书”和“契”是两回事,“书”是文字,“契”是凭证,初期表现为刻画符号。从刘勰的“书契作”接下来的语境看,已经是统指文字了。
文字是记录言语的符号,因为文字的创造是由言语而来;但是正式的文字形成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至少两种记录言语的符号,这就是结绳和画卦。“爻象列而结绳移”这句话反映了汉字的产生是多元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结绳和画卦,即“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刘勰认为卦象形式的推广,使得结绳记事的形式慢慢地退出,人类进入“书契”时期。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如金文中几个十的倍数的字可能就是结绳记事的遗迹。
关于结绳记事的说法,不仅《周易》有记载,在《庄子·胠箧》篇也有记载,都说是在伏羲神农时期。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中如《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论衡》等书,也都提到“仓颉造书”的传说。后来的考古界李伯谦等人认为黄帝时期距今约4930年[5]。现代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文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6]66这说明刘勰对于文字产生时代的推论已被后来的考古学界所证明。尽管刘勰取用的是前人的资料,刘勰采之为我所用,说明已经是刘勰认可的观点了。
刘勰认为“鸟迹明而书契作”(《练字》),“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原道》)。这是文字发生的文献系统说。而后来的文字学家则结合考古证明,认为文字开始于图像,即图画文字,这也就是为什么六书把“象形”列为第一的缘故。许慎《说文解字序》:“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如果细究,“鸟迹”也是图画,二者并不矛盾。后来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八卦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代替了结绳记事的形式。这与刘勰八卦、鸟迹为文字之始的观点一致。
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名谓文字也。”郑樵《六书略》认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又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字也。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义,子主声。一子一母为谐声,谐声而成字也。”文与字合称为文字,始见于秦始皇《琅琊刻石》。《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是说人们根据客观事物的形象和特征,描摹出它们的形状,所以叫作“文”;“文”是单个物体的形状,人们又把几个物体的形状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就形成了一个合体的“字”,这合体者,不再叫作“文”,而是叫作“字”,这字是由多个单体的“文”繁衍而成的,这种繁衍在文字学上叫做“孳乳”。许慎说是“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里只是说了形声字,还应该包括会意字。“文者,物象之本也”,这个“本”说明单体的物象“文”是形声字和会意字的“原”,或者“母”。前面郑樵的话,大概是本于许慎之言。正是鉴于这种理解,许慎认为单体的“文”不能拆解,只能“说”,合体产生的“字”可以拆解,所以他的大著取名为《说文解字》。刘勰《练字》的“字”当是广义的文字。
唐兰先生认为,早在纪元前中国人就开始研究文字,《史籀》《仓颉》和《尔雅》是最早的文字书。刘勰说:“《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练字》《史籀》《仓颉》篇讲字形,当然《说文解字》主要也是讲字形,《尔雅》讲字义,是训诂学的祖宗。三国时期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韵集》等,应该说是最早的韵书,至此文字学的典籍都具备了。这种形、音、义相互佐证的文字书,便于“该旧知新”组织文章。按理说,研究文字的构造和运用的学问,就叫作文字学。这说明刘勰那个时期已经具备了现在意义上的文字学条件。但是容庚先生认为,文字学之谓,始于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之《中国文学教科书》。他认为:“文字学必包括形音义三者而言。”[7]容庚的这个界定让人一时费解。唐兰认为:“文字学的萌芽,大概在春秋时。《尔雅》据说是周初所作,《史籀》据说是宣王时作,但解说文字的风气,实起于《左传》。”[8]57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国大夫伯宗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秦国医生和(人名)说:“于文,皿虫为盅。”刘勰在《练字》篇说:“《周礼》保氏掌讲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序》有:“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查《周礼·地官·保氏》有:“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这六书之说,已经是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是讲造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这种研究六书的学问,应该称之为文字学。但是在汉代被称之为小学,六朝时期叫作“仓雅学”[6]5。
刘勰所谓“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练字》),这句话也是有历史文献作为根据的。《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当是指周王朝统治全国之后开始的一次文化上的大一统行动,即统一文字,统一语言,统一风教。这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社会都必须采取的措施。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周王权衰微,政出多门,文字也乱了,孔子发出“必也正名乎”的呼声,说如果让他主政,他首先要统一文字。因为“文不正,则言不顺”,政令无法传达至民间。其后至战国,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说明战国时期文字应用比春秋时期更乱。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是采取了与周朝相同的措施:“一字体,总异音,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这就是改大篆为小篆,后又改用秦隶,并统一了字音,实现了孔子“必也正名乎”的愿望。刘勰说的“秦隶兴,古文废”,与许慎观点相同。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说:“‘古文字’这个名称,初见于《汉书·郊祀志》所说的‘张敞好古文字’,汉时通常的称谓却只是‘古文’。因为汉时通行的文字是隶书和小篆,这都是秦并天下以后才兴起来的,所以把秦以前的文字,统叫作古文。”[8]32我们认为古文之谓,是一个相对的称呼。现在通常把文言文称之为古文,而现代文字学上的古文之谓,大都是指大篆之前的文字。有唐虞之古文、夏商之古文、西周之古文和六国之古文。刘勰说的这个“古文”当指大篆和小篆。小篆是秦代文字,隶书简便于篆体,故人们习惯使用隶书,故有刘勰“程邈造隶而古文废”之说,特别是后出的汉隶。但是,刘勰“程邈造隶而古文废”的说法,当取材于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说:秦“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这个“隶兴而古文废”的说法可能不严密,其资料相沿脉络是班固《汉书》、许慎《说文》、刘勰《练字》。现代文字学家胡朴安在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序》和《汉书·艺文志》的有关这方面意见之后紧接着说:“隶书之兴,专为狱史隶人之用。秦时虽灭文重质,然从未以隶书施之高文典册,观始皇各处刻石,皆书以篆,诏版亦然。惟权用隶,可知篆隶之用,在秦固各有所宜也。自汉人以隶写经,隶书之用日广,变更篆体,俗书叠出,千里草为董,白水为泉。篆文之废,不废于秦之造隶书,而废于汉之用隶书也。虽然隶即变更篆体,究竟由篆而出,其间变迁之迹,苟明字例之条,皆可知其意。”[9]
后汉时期,汉隶再变,历经章草、楷化,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正书。这种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正书,中间经历了晋宋以来的别字、俗字的文字混乱期。这种现象,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记载甚详。
刘勰认为:“秦灭旧章,……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练字》)《说文解字序》说是八种字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是秦代规定的文字八体。刘勰说的“六体”之谓,是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是王莽时期改秦八体为六种字体[3]57。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当是刘勰之所本。秦王朝虽然规定书同文,但是因为统治时间太短,未能形成风习,汉初萧何再次用法律的形式统一字体,吏民上书,字或不正,必然治罪。可见大一统王朝对于规范文字工作的重视,所以文字学在汉代得到大发展。刘勰指出孝武之世,司马相如撰写了《凡将篇》等文字书。宣平二帝两朝时期,召集通晓古文的人整理字书,张敞以训正读音传业,扬雄以不常见的奇字编成《训纂篇》等。他们都能熟练贯通《尔雅》《仓颉》两书,这些学问,在汉代初期,因为六国遗老尚在,在当时的大学者那里,无不通晓音义。“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练字》)
后汉时期,文字学转趣疏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他们用字深奥,后汉人读不懂,认为他们是卖弄学问,故意选择一些深奥的文字用于文章,这种认识是不了解西汉文字学昌盛的缘故。刘师培就说:“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书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10]曹魏时期,作文用字,还是有些法度,而《练字》篇:“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刘勰这些话反映的现象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也有相同的著录,南朝如“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北朝丧乱之余,书籍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后世文字学家唐兰说:“六朝是文字学衰颓,也是文字混乱的时期。”[6]18文家作文用字不讲究,随手捡来用上,别字、俗字、自造字满篇多有,事后连自己也不识得了,以至于成了刘勰说的“字妖”。
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来看,大的混乱期有三个: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是晚唐至五代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因国家混乱,王权衰微,政出多门,导致文字形体和读音不能统一。春秋战国时期造成的文字混乱,经过秦汉两代基本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造成的混乱,尽管有刘宋时期扬州都护吴恭撰《字林音义》和顾野王撰《字林》等字书订正,也不能改变局面。至大唐王朝时期的颜师古奉命撰《字样》、郎知本撰《正名要录》、杜延业撰《群书新定字样》(今佚)、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等数次正字正音等措施,虽然使得俗字现象有所收敛,但仍然不能禁绝,民间书手多不遵之。晚唐及其五代,由于国力渐衰,藩镇割据,世风下颓,俗字、别体遂又泛滥起来,从而形成了俗字、别字流行的又一个高潮。敦煌遗书中大量的俗字就是物证,直到宋元雕版印刷盛行才基本克服,但是在民间文学和坊间刻书中仍没有绝迹。诚如任半塘所言:“唐人之俗写,沿汉魏六朝旧习,而集其成。……当时俗写甚为普遍,并不择事而施。”[11]
刘勰《文心雕龙》讲文章学,设置《练字》篇,是有其文字混乱期作为背景的。这说明刘勰《练字》篇的设置,其针对性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字妖”现象,意义不同寻常。
总之,从《练字》篇可以看到,刘勰认为,汉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爻象、鸟迹、书契、籀文、秦篆、秦隶、汉隶、正书等字体。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说:“《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这“神理”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这是从字形上说的。而字义和字音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练字》:“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刘勰指出借助《尔雅》研究字义,与研究字形的《仓颉篇》相互勘用,犹如左右肩股相互配合。《练字》篇说:“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只有了解文字发展的新趋势,才能准确掌握字义,解释古今有所不同,字义的取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别。
二、刘勰练字的意义与规则
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刘勰的知音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这里的“易识字”与刘勰《练字》篇的要求是一致的;“易读诵”与《声律》篇相联系,是指文章写作,不仅要选用读者常见的字,而且还得要考虑能够朗朗上口。现代学人刘师培说:“作文之道,解字为基,……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12]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作者是通过文字表达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如果选用的文字,多人不识得,也就失去了文章写作的意义。
刘勰说:“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即:“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言语是人类交际的声音,声音通过文字符号记录下来,就由声像变成了物象,物象就有了“体貌”。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因此文章就寓居在文字之中,成了文章之宅宇,可谓刘勰之自铸伟辞。《文心雕龙·章句》篇说: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
可见,文字对于文章的重要性。因而刘勰主张作文贵在“练字”,“练字”的“练”,李善注《文选·月赋篇》时说:“练,与拣音义同。”拣通柬,《尔雅》:“柬,择也。”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练字》篇的“练”字曰:“练训简,训选,训择,用字而出于简择精切,则句自清英矣。”刘勰本意是作文要选择恰当的文字组成“端直”的语句,使得文含风骨感召读者,以达到传达作者本意的目的。正是出于这一要求,刘勰才在《风骨》篇主张:“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捶字”是练字,“捶”是锤炼。若选字不精,用词不准,“空结奇字”造成巧言丽辞一大串,词义瘠薄,无法达到风骨之力,对读者起不到化感作用,就失去了文章写作的意义。对于诗文作者缀文练字的故事很多,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八就有一则《诗词改字》,著录了王安石绝句《泊船瓜洲》一诗的修改过程,仅“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就曾经用过“到”“过”“入”“满”字,“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最后形成“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千古名句。黄鲁直诗《登南禅寺怀裴仲谋》中的两句:“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据说这个“用”字是最后选定的。“用”字初用“抱”,又改用“占”,三改“在”,四改“带”,五改“要”,最后改“用”字始定;诗人贾岛写诗“推敲”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至此,《练字》篇的意义明矣!
练字的目的、意义明确了,刘勰《练字》篇提出了练字的四条方法或者说四条规则: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哅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以上是刘勰提出的“练字”的四条规则。刘勰说得很清楚,避诡异问题如同沈约说的,是为了读者易识字,更好地把作者的思想意图通过常见的文字组成的篇章传达给读者。因为魏晋以降,文虽崇尚简约,但是,诡异之弊病仍然不绝。刘勰自己解释:“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这种现象,直到唐代亦然。例如唐·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瓌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於口而听於耳也。”字体“瓌怪”的原因是文人“猎奇”所致。“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刘勰所批“字林”之谓,左思《三都赋》即是一例,如《吴都赋》:
真是“状貌山川”,就用山字旁的字构句;形容江河,就使水字旁的字连篇。郭璞《江赋》更甚于左思《吴都赋》,我在阅读时,如果不借用《中华字海》(有很多字一般字典是查不到的)和注释家的注释,直接不能阅读,如同刘勰说的进入“字林”一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相同偏旁的文字充盈其内,或为了求得双声叠韵,争得“半字同文”,不惜搜肠刮肚,费时十年写成《三都赋》。这当就是黄侃说的“苟以矜奇炫博为能也”。
隋唐之前,文章传播皆由书手抄录,如果书手不慎,选字随便,或只注意读音,不讲究文字本意,或者只凭己意,省略偏旁,也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刘勰所谓“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正是此意。“音讹”者,刘勰举例如“子思弟子,‘于穆不巳’者”,这是指“祀”字之谓,在文献上有用“于穆不巳”者、“于穆不似”者、“于穆不祀”者之别,“巳”“似”“祀”,“音讹之异也”,都是因为书手抄写中音讹而致。“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所谓“文变之谬”,是指文字形变所致。如“三豕渡河”,晋之《史记》本是“己亥渡河”,由于“己”与“三”形似,“亥”与“豕”形似,因而讹变成了“三豕渡河”。刘勰又举例曰:“《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 别’‘ 列’‘ 淮’‘ 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别风”原本是“列风”,列,通“烈”。《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迅雷风烈”,即迅雷烈风,烈风就是大风。“列”与“别”形似,“淫”与“淮”形似。“‘淫’‘ 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正是这种猎奇心理的支配而舍“义当而不奇”而取“理乖而新异”。正如刘勰所言“三写易字”。《抱朴子·遐览》篇也说“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
“联边”和“单复”是一个文章表面观感的美学问题。“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是指偏旁相同的文字累积在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中,前面已经举例言明。“省联边”要求尽量减少用偏旁相同的文字组成句子,否则,会给人以“字林”之感。正是这种“字林”式的文字构句,影响了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说《三都赋》:“等于类书的性质,并没有文学价值。”“权重出”,“权”是斟酌之意,是指要斟酌用字,避免重复,给人以语言贫乏之感。“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这是刘勰说的行话。虽然“相避为难”,作者应该尽量避免。但是,凡事也不能绝对,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如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十四个字,用了四个“死”字,不但不给人以重出的反感,反而加重了起义的正当性、必然性,显示了司马迁的语言驾驭能力和修辞技巧之高超。这说明高明的作者对于重出,避与不避,见机而作,不必教条。“调单复”,就是调配单复。刘勰讲得明白:“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一般来说,独体字相对笔画少,显得消瘦,合体字笔画多,显得肥大。如果“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这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要求,所以刘勰接下来说:“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参伍单复”就是调配“单复”。《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四次使用“参伍”一词,用意皆与《易·系辞上》相同,取“错综”之意,指把肥瘠文字调配的错落有致,即“磊落如珠”。
刘勰在齐梁时期不仅是著名的文章家,也是颇有声望的书法家。我曾在《草书大字典》中,集出六个刘勰写的草字放在拙著《刘勰志》彩页中。《草书大字典》对梁代只选录了梁武帝、萧確、沈约、陶弘景、萧子云、刘勰、王彬、朱异等八人的字,可证刘勰在齐梁时期是著名的书法家。《梁书》本传说:“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该记实之言,说明刘勰对于书品肥瘠文字的搭配和排列,颇有讲究。这不仅是从文义美学意义上的要求,更多的是从视觉美学意义上提出“磊落如珠”的要求。清代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说:
排者,排之以疏其势。叠者,叠之以密其间也。大凡字之笔画多者,欲其有排特之势。不言促者,欲其字里茂密,如重花叠叶,笔笔生动,而不见拘苦繁杂之态。则排叠之所以善也。故曰:“分间布白”,谓点画各有位置,则密处不犯而疏处不离。又曰:“调匀点画”,谓随其字之形体,以调匀其点画之大小与长短疏密也。
戈守智说的是书品的排叠布白问题,刘勰的“调单复”是选字问题,虽有不同,但是从美学意义上看,是相同的要求。刘勰提出一个标准,是本着圣人“宁缺毋滥”的原则缀字成文。“依义弃奇”,不仅选字达意晓人即可,并指出“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与正文字”相联系,其意义就更大了,可见还有纠正晋宋以来文字混乱现象的意义。
三、结 语
刘勰在《练字》篇的末尾总结性地说:
篆隶相熔,苍雅品训。古今殊迹,妍媸异分。字靡易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篆隶相熔”一语,是说我国文字,自仓颉初造之鸟篆、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隶书的演进,后者皆由前者之熔化,而成后者之铸造,彼此相因,不断演变,而始有今日之楷书。刘勰说:“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说文解字·序》言:“或颇省改,以趣约易。”说明文字的每一种形体的演变,都是对前一种形体的继承和创新。文家可以根据文字的形、义从事选择。“苍雅品训”是对前文“《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一语的回应。“声画昭精,墨采腾奋”,是对“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和“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而言。“字靡易流,文阻难运”是对“自晋以来,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一语的承接和概括[13]。
综上,《练字》篇与许慎《说文解字序》是中国最早的两篇文字学发展史。《说文解字序》只谈到东汉,《练字》篇延伸到南北朝,虽然仅有千余字,意义足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刘勰对于汉字产生、发展的流变性和音、义变化性十分了解,且承认文字的形、音、义是流变的,与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比起那些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的顽固派,不知“古今殊迹,妍媸异分”者来说,刘勰识见实在高明得多。现代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一般人不知道文字是时常流动的,他们往往只根据所见到的文字,以为古来文字就是如此,……他们的理由,是:‘父子相传,何得改易’,是‘俗儒啚夫’之见。”[6]114要说谈文字产生的资料是刘勰取自前人成说的话,“练字”的四条规则却是刘勰独创,而对汉字形音义流变性规律的认识,也不是凡夫俗儒所能掌握的。面对汉字文化圈内的“俗儒啚夫”,说明刘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章家和杰出的思想家[14],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文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