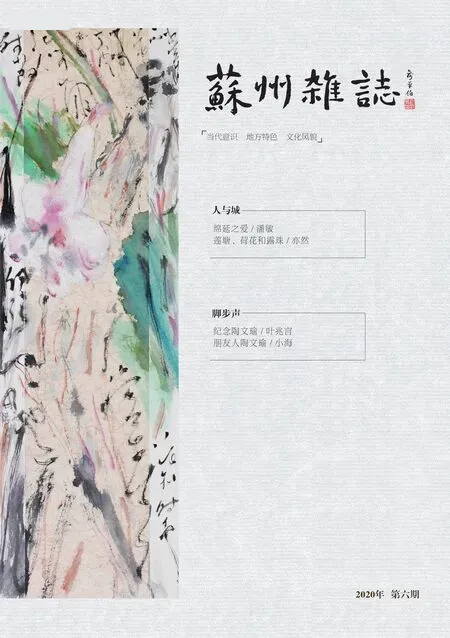吃蟹
非 我
一
翻过夏天的火焰山,秋天就来了。然后,一场秋雨一场寒,等到了秋风硬硬地扎进衣服的时候,江南最热闹的食宴就慢慢展开了。
这个季节吃的热闹,莫过于吃大闸蟹了。我从来不喜欢这个季节里任何一场以一只蟹作为句号的宴席,那根本不叫吃蟹,那只是拿那只做句号的螃蟹来调戏客人的感情,借以提高宴席的规格。四五个好友端坐喝酒聊天,没有二三十只蟹下肚,怎么好意思说是吃蟹?真正吃蟹的宴席,是一群人围剿更大一群蟹。而吃蟹,也根本用不着其他菜式的铺垫和收尾,那都是拙劣的对蟹味的轻慢。蟹和蘸蟹的调料之外,唯一可陪伴的饮品,一盏加饭或者一杯花雕,足矣。
说到吃蟹,就必须连带介绍下用来佐蟹的调料。调料是一醋二姜三糖的混合体。醋必须是镇江的香醋。姜切得越细越好,量要足。糖嘛,我不勉强诸位的口味,但多少要放点,放了才知道糖在这里的妙处。这个配方业已被我那些南到广东、北到北京甚至更北的朋友们踊跃采纳。
苏州人的语汇里,从来没有螃蟹一词,大概是和吴语连续发这两个音不甚利索有关。说到蟹,就说是蟹或者是大闸蟹。稍微小一点的蟹,苏州人就不叫蟹,叫蟛蜞。那时候的大闸蟹本来就家常,所以蟛蜞就更等而下之了,顶多拿来做做醉蟛蜞或者炒个年糕什么的,不会拿来清蒸。

前几年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吃大闸蟹的文字,刚刚写完,颇为得意,第二天电脑和文字就一起被四川流窜过来的四个朋友给撬门拎走了。不速之客是三男一女,一起拎走的还有不少东西。东西倒没让我心疼,文字灭失,实在让我沮丧。这四个朋友半个月后在另一家横行时螃蟹般落网,警察给我送来了其中的一只旧数码相机,我用软件恢复了一下记忆卡,四个人的面目清晰地展示在我面前。之所以我要写一段,恰好是他们在我家行窃的时候,我是被朋友拉去太湖边吃蟹。蟹吃了,写蟹的文字却没有了。朋友说:幸好你不在家,不然那个点你正在睡觉,说不定你就被捆成了大闸蟹,按你的脾气,丢了命都有可能。私下想想,深以为然。
鼓了几次勇气,一直没有恢复关于此篇文字的记忆。内心里的忐忑,是因为觉得那篇失去的文字好。人对失去的,大概尤其会觉得好,害怕许多如珠妙语、花言巧语再也写不出来。今天想想,未必。人于自己的东西,大有敝帚自珍的心态。文字也是一阵阵的癫狂或者理智,一段时光有一段时光的味道。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坐下来再次写写大闸蟹。
二
我是最反对“小资”这两字的人。人对生活状态的要求,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人都希望自己活得好一点,生活中有一点趣味。这个趣味不一定非得蒙上高尚高雅的面具,自己能娱乐自己就好。比如我就认为坐在路边倒杯黄酒,吃吃清蒸大闸蟹是有趣味的。或在北方的排档搞二两“小二”,佐一碗热热的卤煮也颇有情调。
蟹的横行,人所共知。于是,蟹在我的印象里就很有江湖气息和大佬气势。蟹行走江湖的姿态煞是嚣张。因此我们吃蟹也应该嚣张一点。蟹多壳,吃的时候最好能有个地方随便抛洒,一地蟹壳的嚣张,也是局促而规则生活里的一段发泄。文明是一个层面,有时候能给个地方放纵浪荡撒撒野,应该是文明的另一个层面。谁没有点江湖气江湖心呢?
从前,稍微有点背景的老苏州人家里,吃蟹确实都用到蟹八件。蒸好的蟹先被安放在特制的铜砧甚至是银砧上,然后一件件按次序拿器械处理大闸蟹,仿佛医学院学生的解剖课,蟹的遗体按程序被肢解开来,座中每个人都专注地低着头,无声无息地操作,又仿佛在集体为大闸蟹们默哀。此等吃蟹,一点也不酣畅淋漓,在我看不如不吃。
吃蟹,必须热,一凉就失去了蟹的滋味,且腥且臊。所以座中有几位就现蒸几只蟹,不能图省力一下子全蒸完。等待下一拨大闸蟹的过程,恰好是草草擦擦手,朋友间能安心谈天说地的间歇。这个间隙里喝几口黄酒,私下议论一下时局或者臧否一下人物,也颇能借得螃蟹横行的神气。
把酒临风,持螯赏菊。大快朵颐的时候,谁会停下齿颊的工作呢?那是诗词里的境界,现实中实在是“满手蟹油,满嘴蟹膏,满眼蟹腿”。谁真的做些临风赏菊的姿态,一是定然被同食者斥为“装”;二是等你拗好造型,本属于你的那只蟹或者已经被某人私吞了。所以不是在舞台上、镜头前,这一记吃蟹的身段,千万慎用。
即便坐在金碧辉煌的高级场所吃清蒸大闸蟹,在我看来,依然是野餐的局面。而想放肆地坐在马路边豪迈地吃蟹,如今更是个幻想。正宗大闸蟹的身价如此高贵,城市里也不允许我等在马路上放肆。其实让你放肆你也未必敢,那么大的雾霾,你戴着“苹果”或者“微软”的防尘口罩也没法下嘴。所以为了吃蟹,只能做一回缩头的乌龟。我豁出去在家里地板上铺了一层仿人行道砖的塑料布,邀朋友们一起朝上随心可意地扔吐着蟹的那些非食用部分,聊解内心深处的焦躁。
家常吃蟹,就不必这么啰唣。苏州人当年家常吃的往往是面拖蟹,蟹不必大,即使买点蟛蜞也可以。价廉,味道一样鲜美,菜的做法还能将美味成倍地放大。家常吃面拖蟹,大多数人中意的,是菜式里吸收了蟹味精华的面疙瘩和毛豆子,而蟹的本身常被视作多余的东西,最后被长辈们修了口福。
奢侈的吃,父亲也和我说过。或许今天的奢侈,在当年很是寻常。早年的某苏帮菜名馆,当令有一款菜式叫蟹黄油。蟹黄油,顾名思义,即是以纯蟹黄烹制而成。父亲进店,其他菜式一概不取,唯点蟹黄油两份,一份趁热吃完,然后,嘱店家下一碗面,以另一份蟹黄油拌而食之,引为至味。某日和父亲又去这名馆用餐,和现任掌柜说起此味,答曰:成本太高,这一款已无法炮制。
三
1976年的秋天,少年的我还在苏北的益林小镇。一同下乡的姨夫买了一大篓子的蟹,邀我父亲和萧先生饮酒,我才知道,原来苏北也是有螃蟹的,只是不叫大闸蟹而已。
萧先生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文学士、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医学士,颀长的身材,一口北方话,真正的潇洒浪漫和幽默。当年,他和我父亲一同被下放苏北,两人惺惺相惜。我那时节尚年少,不耐烦听他们酒桌上的宏论,听一会就去姨夫家旁边的河畔看看有没有新鲜奇异的故事,因此一并对螃蟹也没有太多的兴趣。
若干年来的秋季,我还时常听父亲念叨,说那一年苏北的螃蟹,并不弱于苏州的大闸蟹,这是热衷于苏帮饮食的父亲唯一对外地食物表示的感慨和赞美。或许因了那螃蟹的肥美,或许是因了对谈者的适意。肥美也好适意也好,总之,那晚的聚会肯定是酣畅淋漓的。
1976年初秋的时候,中国是出了一件大事的。那年秋天,很多人家里挂了一幅国画的印刷品。画,是水墨,画的蟹三雄一雌,似乎有点白石翁的味道,记忆已经久远了。题在画上的四句诗,我却还能记得。诗曰:秋风萧飒蟹正肥,有雄有雌好滋味。捉来不费吹灰力,劝君饮酒莫要辞。
秋天到了,秋风硬硬地扎进衣服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想想有大闸蟹的日子,真是爱得入心入肺,入肝入胃。即使不吃,想想也美。
也罢,还是温一壶黄酒,趁着这秋风,痛痛快快地吃几次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