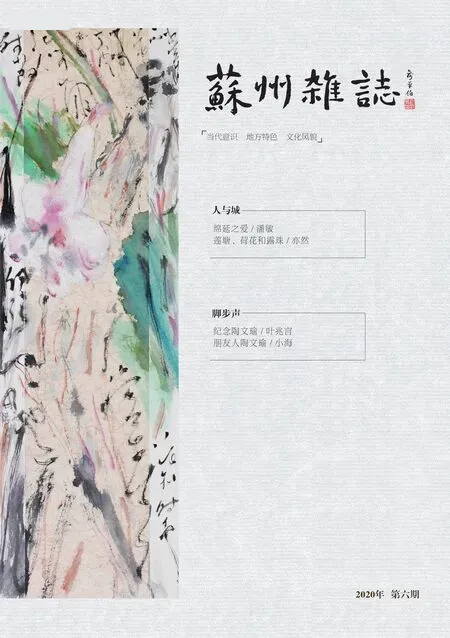诗如野草在风中哭泣
周菊坤
陶文瑜学开车,学得特别仔细,人家学一两个月就能拿驾照,他竟断断续续学了一年。他几次和师傅讲,让我考吧,师傅总说不急不急。在驾校里,有师傅罩着,总算有惊无险。拿到驾照之后,他的爱车就经常挂彩,不到三年,已经十几次碰擦,整车喷漆也已好几次。诗人李德武在保险公司当老总,说,你的车险我来帮你做吧。文瑜说,不要了,你公司要赔本的。

☉ 陆文夫和陶文瑜(右)
有一次朋友来送东西,已经到了家的附近,他坚持要自己开车去十字路口取,送走朋友,他倒车回去,竟把路旁的监控连铁杆一起撞倒,保险公司倒霉,赔了一万多。
文瑜喜欢开车。从家里到青石弄的杂志社上班,不过一公里路,他也要开车过去。自己的住处和单位都没有停车场,他就在附近长租了两个停车位。城里的车位紧张,又贵,他就托人找关系,还是花了将近一万块钱。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文瑜喜欢开了车四处游逛,我经常会接到他的电话:菊坤,我要到东山(或西山)去,我过来看你哦,我自己开车的。言语之间很是自得。十全街上有家面馆,还有老苏州茶酒楼,陆文夫当年创设,经营地道苏州菜,因为《美食家》的影响力,也因为的确有几位名厨掌勺,生意很是不错。如今的十全街已全然不是当年模样了,但文瑜是个念旧的人,仍时不时地去吃个饭,或者去面店里吃碗小馄饨。每次去吃,总要开车去,有一次车停在路边,属于违章,一碗馄饨十元,罚款倒是花了五十元。
文瑜是读书人,于文字轻车熟路,对交通规则却不太熟。要说交通违规只是罚款倒是爽气,关键是现在的违章通常是要扣分的。文瑜经常稀里糊涂违反交通规则,当然也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比如违章停车啊,逆向闯单行道啊(他是高度近视),一段时间下来,就会被扣上四五十分。怎么办呢?有些人常用的方法是花钱买分,文瑜也是,但不用花钱买,他是书法家,他用字和人家去交换,大家乐意。有时他的字行情好,交换抵扣之后还有富余,就存放在别人处,下次还可以继续用。
文瑜写字是有童子功的,但毕竟荒废已久,无法与那些职业书家相比,然而,他悟性高,感觉好,功力虽欠些火候,但形式感很好,注重章法和气息,还喜欢在字旁点缀些花草蔬果,颇有些文人画的气韵。他自诩为“诗人中写字最好,写字人当中写诗最好”,所以,诗人和书画界的朋友都愿意结交他。他也不太临帖,说“王羲之的字有高贵气,我达不到那种境界”,每次临王羲之,最多半个小时,便我行我素起来。
文瑜是作家和诗人,很多人称他“陶老师”,但他现在已不大写诗和散文了,他喜欢别人称他书法家。他擅长小字,写扇面,写尺牍,娟秀文雅,很讨人喜欢,所以就有不少人向他求字,陶老师基本是有求必应,临了,还会额外多赠予一些,比如尺幅写大一些,比如字多写一些,比如人家买得多的就再附赠一两幅,有点像菜市场里买菜,对老主顾总会饶一把香葱之类的。这是做人。大家便都说陶老师是个实在人。陶老师靠写书没赚到什么钱,靠写字倒是着实改善了生活条件。儿子结婚,看中一辆汽车,陶老师盘算了家里的存款,还有些缺口,便琢磨着办场书法展,卖字筹款。书画界不少朋友得知,就纷纷赠他字画,徐惠泉、陈如冬、夏回等等,都是铁杆。陶老师一边收画,一边寻思,四只轮胎着落了,方向盘也解决了。《磨墨写字》的书画展设在文联展厅,开幕式上,捧场的人络绎不绝,多是来贴红条认购的。到了晚上,陶老师和师母用计算器粗略算了一下,买车子的钱已够,便做出决定,第二天撤展。
《磨墨写字》展期仅有一天。这可能是苏州书画史上最短的展览了。
又记:上文写于2018年11月11日。那天,文瑜来太湖看我,要在他主编的《苏州杂志》上开设“新田园诗”专栏,约些诗人,每期写太湖的一处地方。这个想法很有创意,很好玩,我喜欢。他又提出,要我也写两首。我说,我已三十多年不碰诗了,写不来。他说,你行的,12月15日截稿啊。
正题说完,便开始闲聊,当然,主要是听他的“一言堂”。我听得前仰后合,他却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的幽默风趣属于天赋,有点周柏春式的“冷噱”,别人很难模仿的。当然,除了天性,也与他的才情有关。回到家中,我仍然沉浸在与他聊天的快乐之中。在小区里散步,我边走边在手机上打字,基本上是一份聊天记录,很快写完,即刻微信给了他,几乎同时,他回信来了,“写得好的,兄文学品质高,有空替我写点啊。”他的表情藏在文字背后,坏坏的,却又显出诚恳。
岁月静好。12月15日,文瑜来电,催要我的“新田园诗”。事实上,我已忘了此事。听他催得急,我有了压力。晚上有应酬,喝了点酒,到家后绕着小区走路,心里惦记此事,借着酒意,在手机上摁下了一些分行的文字。写的是东山的《银杏》,隔了一天,又在手机上写了首《枇杷》,一并发给文瑜,就算交差了。又过了一个月,我的诗就在《苏州杂志》上刊登了,散发着果香,还有酒气。
这是我三十多年来头一回写诗。我不知道这些文字算不算诗,尽管文瑜在回信中用了一个“好”字来嘉许。但是,从那时起,我倒是逐渐恢复了写诗的习惯,而且,一发不可收,整个2019年,竟写了100多首。从一棵小草,成为一片草地,这要感谢文瑜。我是野草,他是春风。
2019年10月1日,接到文瑜打来电话,说患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托我买个墓地。这让我很震惊。文瑜患病多年,一直病恹恹的身子,但他的乐观与豁达,即或健康人也少见。如此沉重的话题,电话那头却是轻描淡写,与平时聊天一般,很平静,甚至还有些调侃的意味。只是,我听出他的声音里,已经没了平时的中气。我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只有沉默,眼眶里湿润起来。
我终究没能帮到他。文瑜的家人最后为他选了一块墓地,离他父母亲很近。这样也好,去了那边,彼此也有个照应。
文瑜兄是12月3日走的。他走得很匆忙,留在世上的只有他的笑容,和那本叫《随风》的诗集,还有那首《再见吧朋友再见》。“死亡不算新鲜事,活着也不更新鲜。”什么是新鲜呢?他没说。
文瑜的朋友很多,悼念的文章如雪片,印象深刻的有小青、小海、潘向黎、荆歌的文字。他们是我的师友。我没有写只言片语,也没赶上去殡仪馆送他。我遥望那片沉默的山岗,无端想起陶渊明的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我的诗稿越积越厚,文瑜兄却走了,这些诗如野草,在风中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