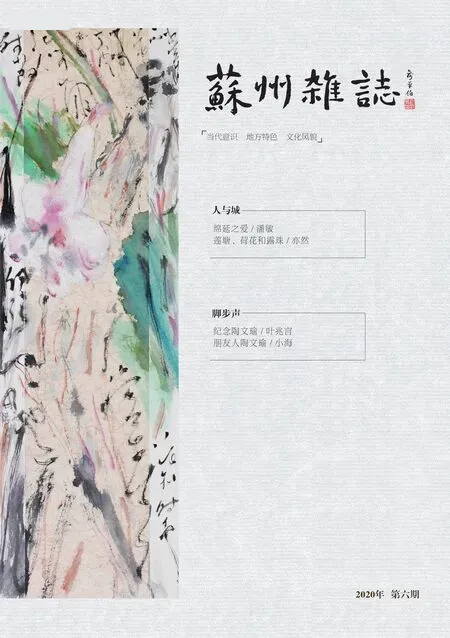朋友人陶文瑜
小 海

☉ 陶文瑜与小海(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居住五年后,有一晚梦见自己的葬礼:流亡欧洲的“爆炸的一代”拉美作家们久别重逢,欢聚一堂,都是他的老朋友。葬礼结束,所有人都走了,马尔克斯想陪他们一起离开,却被朋友们提醒:“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这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这个梦,马尔克斯写了一系列“欧漂”的故事,并以12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如果要让陶文瑜来定义死亡,可能的回答应当也是: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活着就是要和朋友们在一起的。
有一个词,叫“朋友人”。在我老家,老辈人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有讲这个人好交朋友,性格洒脱,急公好义等多层意思。我看过作家俞黑子记录整理的江苏老领导惠浴宇的口述史,书名就叫《朋友人》。可见从前大家还认这个。现时很少用了,老家多用“甩子”这个词,也可能是因为“朋友人”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少见了。
“朋友人”,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陶文瑜身上挺准确的,而且,还少了点江湖气,多了些书生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到苏州报到上班。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内心总有一丝不安,何况敏感如我。作为本地“土著”,陶文瑜是敞开胸怀迎接我的朋友之一。那种一见如故的快乐、坦荡、真挚神情,洋溢在他脸上,让我没齿难忘。难怪古人会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那个瞬间,我脑子里面冒出了老家的一个词“朋友人”。
他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早年,他在靠近十梓街苏州大学老校门的地方曾经开过一家书店,店名就叫“大家书店”。他叫我去玩过好几次。记得是个大夏天,不大的店里面基本没什么人,他一个人,一壶茶,穿条沙滩短裤,半躺半坐在一把躺椅上,吹着电扇看书,来客人也不招呼,懒洋洋的,好像是临时代人家看店的。来了爱书的朋友,立马精神上来,递烟倒水,殷勤款待。“大家书店”,顾名思义,除了自矜外,还有大家的书店之意。所以,这家不赚钱的书店似乎是为朋友们开的。
大家知道他嘴巴馋,好吃。要是一个人躲在家里吃,可没人知道,他自然是要跟朋友在一起吃。听他儿子陶理讲,文瑜在外面顶着美食家的名头,回家却很少烧饭。陶理记得自己小时候,父子俩在家的话,老爸给儿子弄饭,搞一个汤,直接用勺子挖一勺子味精放进去搅搅,把儿子都吓一跳。有时给自己下碗面条,他也要放味精。朋友,嘿,这真要你相信。
他还喜欢为朋友排忧解难。
他真的关心朋友,喜欢主动揽事。比如,朋友甲有难,他无意中得知,一个电话打给朋友乙,若是他认定乙能帮忙解决而不尽心的,有可能会在朋友圈直接宣布和乙绝交,但隔天他又会发布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的消息,因为甲的问题解决了。刚刚被他弄得有点肃杀之气的朋友圈,终于响起了欢乐祥和的鞭炮。
文瑜离开朋友们已经快一年了。现在,到了饭桌上,稍有冷场的尴尬时,就不由得会想到他。他很少喝酒,常常是清茶一杯。可只要他在,保准宾主尽欢。那不叫吃饭,那叫和文瑜一起吃饭。“朋友人”的前提就是个热闹人,他到哪里,就要把欢乐播洒到哪里,哪怕是无厘头的恶作剧,一两句抖包袱的俏皮话,他都说得很机智很高级,夹杂着特有的辛辣、达观、透彻、敞亮的陶氏幽默。
他的诗文也像他还在和朋友闲话聊天。他生前是怎么和我们聊天的,他的诗文就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文瑜走了,但他的诗文还在,记录他诗文的书画也在。他的诗文书画,难道不是为了赢得朋友?
“朋友再见勿话别,莫把伤悲锁眉间”(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诗句),文瑜热热闹闹活过了他的一生,他当然不希望朋友们悲悲切切地怀念他。虽然他走得匆匆,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是朋友们的一个话题。
“我阿牛的?小海。”写到好句子,想到好段子,吃到好东西,每到得意会心时,文瑜总会来电话追问这么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