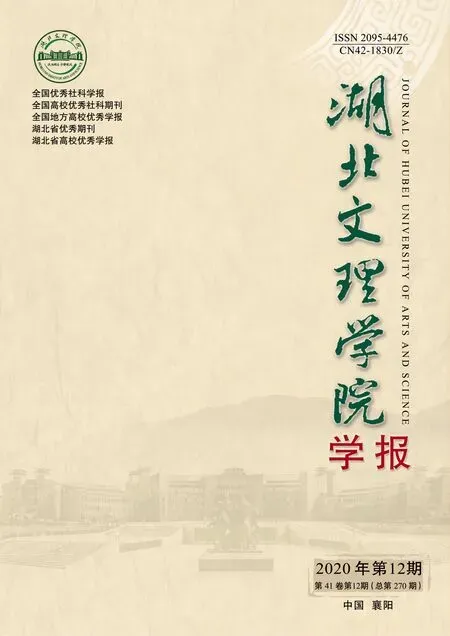歧义容忍度视角下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康响英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语用模糊是语用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名语用含糊、语用歧义。研究语用模糊的论文浩如烟海,但聚焦语用模糊影响因素的文献廖若晨星。分别以“语用模糊+影响”“语用含糊+影响”“语用歧义+影响”为篇名搜索1979—202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得到论文2篇:《语用模糊的交际功能及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认知因素和语用模糊》。从标题可以看出,只有第2篇论文涉及语用模糊的影响因素。当然,有些论文虽然不是专题探讨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所期待的信息:侯国金[1]、邵有学[2]、庞加光[3]、陈爱治[4]、江沈英[5]等借鉴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从认知角度探讨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他们都强调发话人的语用意图,提出语言选择受发话人的元语用意识的指导和调控。发话人借助语用模糊,可以达到提高语言表达的灵活性,实现含蓄礼貌,保护自我的目的。周静、王嵩浩[6]把语用歧义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关联、语境和省略等。梳理这些文献发现,学术界对语用模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系统且有忽视听话人的倾向。到目前为止,鲜有人从受话人的歧义容忍度视角探讨语用模糊的影响因素。然而,“语用模糊是发话人、受话人和社会心理规约共同作用产生的交际策略……言语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话人是否理解发话人的意图”[3]。“话语的意义不是由发话人或受话人单方面发生”[7]。受话人歧义容忍度是影响语用模糊预期效果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本论文拟从受话人的视角探讨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旨在提高人们的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冲突。
一、歧义容忍度
歧义容忍度也称模糊容忍性、模糊容忍度,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Frenkel-Brunswik[8]提出它是一种涉及到个体情绪和认知功能的人格变量。目前,学界对歧义容忍度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Budner[9]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认为歧义容忍度属于人格变量,个体的歧义容忍度值与他对模糊情境的反应密切相关。他编制的16个项目自陈式问卷“模糊不容忍测试”成为后来最经典的测量工具。McLain[10]指出歧义容忍度是一个从接受到拒绝的渐进连续体,显示了个体对待不完整信息的不同态度。歧义容忍度是“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一系列不熟悉的、复杂的或不一致的歧义情景时进行信息知觉加工的方式”。[11]Chapelle & Roberts Mclain[12]认为,在有歧义的情形下,歧义容忍度高的人比歧义容忍度低的人更能够接受模糊不清的事物,更愿意冒险,更容易接受变化。Brown[13]认为容忍歧义者能自由接纳富有创意的可能性,在认知和情感上不受歧义与模糊的干扰,不容忍歧义者受到歧义的威胁时,往往思维僵化并缺乏创意。目前与歧义容忍度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测量及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两个方面。遗憾的是,前人对歧义容忍度的定义片面孤立,忽视歧义容忍度与其他个体差异因素一样,同样会受到性别、社会、文化、年龄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14],且他们多把模糊容忍性作为自变量,探讨它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却鲜有把模糊容忍性作为因变量的研究。本文拟在此做些尝试,分析受话人歧义容忍度中哪些变量影响语用模糊的生成,又是怎样影响的。
二、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
歧义情景指“模糊不清的、零碎不齐的、多重不定的、未经组织的、矛盾相反的或语义不明的信息”[15]。据此,语用模糊就是歧义情景的体现。发话人的话语生成不能只以自我为中心,他必须同时兼顾受话人的立场、情感和身份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话不投机”或者“对牛弹琴”等后果。事实上,语用模糊的形成不仅仅是由发话人掌控,很多情况下受话人也参与其中,其年龄、性别、身份、地位、性格、文化程度、智力水平、主观意图、文化差异等歧义容忍度变量对语用模糊生成机制的影响研究有助于弥补国内外学术界在语用模糊研究中忽视受话人的不足,从而把握语用模糊研究之本质。
(一)年龄
语用模糊是意图性很强的语言选择。它能反映说话人在做出语言选择时的元语用意识。说话人面对小孩时往往会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以适应听话人歧义容忍度。小孩的认知能力也会助力语用模糊的生成。
(1)A:What are they doing there?
B:They are K-I-S-S-I-N-G.
例(1)中,B的回答违反了著名语言学家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却实现了特殊的语用效果:B不想让孩子知道他们正在“接吻”,但必须回答A的问题,于是选择放弃原来的结构客体(kiss),采用新的结构客体(K-I-S-S)即拼读这个单词。语用模糊方式的选择是权衡小孩年龄因素的结果。
(2)幼儿园阿姨:你长得这么漂亮,班里肯定有男生追你吧?
女高中生:没有,绝对没有。
小女孩:好,没人追好啊!
小女孩的话使幼儿园阿姨与女高中生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经询问,阿姨才云散雾开。原来有一天在幼儿园,这个小女孩曾经被一个小男孩拼命追赶,她跑得气喘吁吁,不得不向小男孩跪地求饶。因此,幼儿园阿姨的“追”与小女孩的“追”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追求”,后者是“追赶”。阿姨的话原本没有歧义,但小孩对于语义的有限理解即认知的局限性导致了语用模糊。
(二)性别
性别与语言一直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分别从语调、词汇、句法、话语模式、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性别语言的差异。其中影响较大的是Lakoff,她[16]在《语言与妇女地位》针对语言与性别差异提出了许多内省式假设:男性话语坚强果断、直截了当,展现强势交际风格,而女性话语温和委婉,具有从属性。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男女发音差异、词汇选择和句式结构等静态语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焦点逐渐转移到性别交际策略、交际风格等动态研究,视野比以前大为宽广,涉及话题、打断、语境、沉默、谈话量、最少反映等方面。但是由于两性歧义容忍度差异而引起的交际障碍及解决交际障碍的对策缺乏应有的重视,现有的研究[17-21]都是围绕模糊容忍度对外语学习策略的影响。事实上,两性在日常对话中也存在歧义容忍度差异且能影响语用模糊的生成。
(3)女生: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
男生:漂亮,但我更喜欢看你穿那件粉色的衣服。
男生的回答运用了语用模糊策略,事实上他认为她穿这件衣服一般,但碍于女孩的脸面,不好直说。如果是一男孩问同样的问题,他就会直接说丑。在任何文化中,女性对模糊语、委婉语的偏爱都要超过男性。因此,男性在与女性交谈时,会顾及女性喜好委婉语的倾向。同理,回民男性对自己去洗澡会直说,“我去洗洗身子”,而女性却说,“我去洗洗头发”。因此,性别差异是该男生选择语用模糊的主因。
(三)身份
语言与社会身份是紧密相连的。虽然服饰、食物等外显因素也可以体现身份,但它们不具备语言的身份标志功能。语言有助于建立某种社会关系,身份意识通常通过使用一些语言特征显示出来,身份被看作一种社会变量在语言变量中的映射。Fairclough[22]认为话语在社会主体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两者密不可分,相互映射。语言选择反映并构建社会身份。发话人的身份与他所选择的语言形式与意义相互印证。反之,身份影响发话人的语言选择。身份意识通常会通过某些特定语言特征显示出来。Wardhaugh[23]提出语码的选择反映出一个人希望自己怎样出现在别人面前和对于别人怎样看待你的确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语言选择是构建社会身份最有力的武器。例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高龄女主人公罗丝在向打捞宝石的人叙述她的男友杰克在给她画佩戴宝石的裸体画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4)A:… My heart was pounding the whole time.It was the most terrific moment of my life…
B:So what happened next?
A:You mean:“Did we do it?” “Sorry to disappoint you, Mr.…”
显然,“it”在此特定语境里是指“make love”,但女主人公当时已年逾百岁,在她的孙辈及很多打捞宝石的外人面前直接提及“make love”肯定会很尴尬,所以她用一个语义模糊的“it”来委婉表达,这样更符合自己的年龄与身份特征,同时也更加礼貌得体。因此,权衡自己在受话人面前的身份促成该语用模糊的选择。
(四)地位
语言与社会地位也是紧密相连并相互影响。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日常生活中,由于受话人社会地位的差异,发话人所使用的语言也会有所不同,正所谓“人有三六九等,话是五花八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Norman Fairclough[24]在《话语与社会文化》中指出:“语言比任何其他人类现象都更能反映并揭露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不平等事实。”罗杰.夫勒[25]195-196认为:“读者应该把文本放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通过分析语言结构,再现话语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听话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说话人的言语方式,例如:
(5)一个办事员叫住老板,不安地说:“董事长,我猜有您的电话。”
董事长:“猜?我的就是我的,还猜什么,你这个混蛋东西!”
办事员更加窘迫,结结巴巴地说:“来电话的那个女人说,让那个老……老混蛋听电话……”——《羊城晚报》:不便直说,2001-1-19(B2)
“在某一角色关系中,地位高者趋向于运用高量值情态(如must, certainly, surely),以示其果断性、决定性和断言性。地位低者则倾向于运用低量值情态和中性情态(如perhaps, possibly, may)以示其试探性、对对方敬重和给对方更多的发表意见和做出决断的余地”。[26]虽然办事员几乎可以肯定是老板的电话,但在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董事长面前,为了顾全他的面子,给他事后否认的机会,同时为自己免责留退路,办事员故意使用模糊限制语“我猜”,使自己的话语在意义上不是那么肯定,给老板更多可能的解释,同时给自己留有缓冲的余地。
(五)性格
Grace[27]的研究表明,个性类型是影响歧义容忍度的重要因素。性格作为受话人自身特征的要素之一,对言语交际影响重大,它往往决定发话人的话语逻辑,制约话语交际的风格、方式、过程及对交际效果的预期。因此,我们说话时应当根据受话人的性格调整话语方式,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因为只有语言的接受对象——受话人才能检验发话人的表达效果。例如女生A向女生B借钱,女生B考虑到A的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所以在提建议时就采取了语用模糊的话语。
(6)A:你能借我300元吗?我想买件外套,但是我这个月不好意思再向爸妈要钱了。
B:可以。不过,如果我是你,平时就不会花那么多钱买化妆品。
怎么解读B的回答呢?是含蓄建议?婉言谢绝?间接表达自己对A的做法的不满?(自己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却向别人借钱买衣服),或者几种意图兼而有之?B的意图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A的面子,即A的内敛性格介入了此语用模糊的生成。
(六)语言水平
语用模糊引起的交际障碍往往与言语交际者的语言水平有关。交谈时词汇量、语法等语言知识储备不够,会导致交际过程中词不达意或对牛弹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日益频繁,文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语言问题。交际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再加上缺乏足够的语用知识,出现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不得体的失误,导致跨文化交际中出现冲突或误解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
(7)A:Would you please serve the chicken undressed?
B:No, I can’ t .
A:Why not?
B:You are in China, sir.[28]
例(7)中美国客人提出上菜时他自己浇调味汁,不要女招待事先浇在鸡脯上。然而,女招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undressed”除“不穿衣服”的意思外,还有另一个意义“不加调味(汁)”。她的认知语境所提供的语义记忆和知识是“不穿衣服”,对美国客人的要求无法以合适的认知结构建立相关语境。发话人的“serve the chicken undressed”意图是单一的,受话人的知识水平使得发话人的话语产生了语用意图,其词汇量不足歪打正着地生成了语用模糊。又如:
(8)张明:红梅怎么不来吃饭?
王强:她呀,吃红豆饭吃饱了。
John:哪有红豆呀?
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家喻户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颜色微紫、形如心房的红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相思”。这句话中国人很好理解,王强的回复“吃红豆饭吃饱了”暗示红梅得相思病了,没有胃口,实际上并没有吃饭,但碍于留学生John在场,不便明说,所以选择语用模糊的表达方式,John头脑中缺乏相关意象,“红豆”与“相思”没有发生关联,其知识水平参与了语用模糊的生成。
(七)智力水平
听话人的智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制约发话人的语言选择,如果忽略了这点,发话人的交际意图就会落空。下例中的母亲迎合孩子的智力水平,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
(9)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电影《阿甘正传》)
主人公甘·福斯特的母亲为了使先天智障的儿子更好地理解人生,选用模糊语言化繁为简。母亲的意思是“人生变幻莫测,不可预测”。作为智障人士,阿甘的认知能力只能达到小孩子的水平,他很难理解这么深奥的哲理,因而母亲通过明喻,把未来的人生比作小孩熟知的巧克力,生动形象地鼓励儿子勇敢面对未知人生。
(八)主观意图
听话人的主观意图在特定的语境里也是语用模糊的催化剂。听话人有时故意曲解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达到实现幽默效果或者表达愤怒不满或者转移话题,摆脱困境的目的,使其朝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例如:
(10)Diner: Do you serve crabs here?
Waiter: Sure, we serve everybody.
例(10)中的 serve 是个多义词。食客的原意是“供应、出售”,但侍者曲解成“为…服务”的意思。crabs也是一个多义词,既可以指“蟹肉”,又可以指“蛮不讲理的人”。此语境里,两个多义词的叠用使食客与侍者的话意模糊化,完美实现幽默效果。
(11)Teacher: I can’t bear a foo1.
Student: Your mother can.
对话中,老师的意思是:“我受不了(你这)傻瓜”。学生对老师有悖师德的话非常生气,急中生智,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bear的多义性,故意将它理解为“生(孩子)”,用“你母亲能(生你这傻瓜)!”来回敬傲慢无礼的老师,巧妙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12)“This is a white hotel , ” he said. I looked around .“It isn’t white , such a color needs a great of cleaning ,” I said .“But I don’ t think I mind .”[29]
店主的意思是“这是供白人住宿的旅馆”,而黑人“我”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把对方的话歪曲成“白色旅馆”,并煞有其事地指出这店虽不够干净,但“我不在意”。显然,为摆脱困境,避免正面冲突,“我”故意转移话题,以使交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结果是使店主的话语产生了歧义。
本文的目的是从听话人角度探讨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项成东[30]把语用模糊定义为某一话语在特定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传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的现象。该定义兼顾发话人与受话人的角度,比较全面地概括语用模糊的精髓。尽管上面12个例句都是由于听话人的某个因素引起的,都符合项成东对语用模糊的定义要求,但它们是有区别的:(1)(3)(4)(5)(6)(8)(9)(12)是发话人有意选择语用模糊策略,而(2)(7)(10)(11)中,发话人并不是故意采取模糊手段,而是由于受话人的参与促成语用模糊的生成,后者又可以细分为听话人无意与听话人故意,前者如例(2),后者如例(7)(10)(11)。受话人故意即发话人并没有采用语用模糊的交际意图,是受话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然。当然,听话人无意为之产生的语用模糊,也可能是发话人有意为之,或者是语言本身具有歧义性。
从受话人的视角探讨语用模糊生成的影响因素,对发话人来说有助于知己知彼,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排除意料之外的语用模糊,或者重构话语方式;受话人在语用模糊的生成过程中并不是经常处于被动状态,而是可以主动出击,迫使发话人调整话语方式,使话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受话人与发话人之间的张力平衡有助于减少语用冲突与失误。